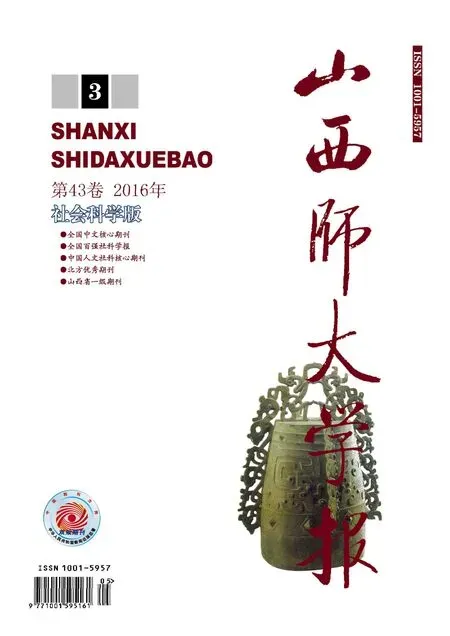论编选者对明清小说文本形态的影响
陈 才 训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哈尔滨 150080)
在论及明清小说文本形态演变时,人们一般都会强调小说作者、评点者、书坊主所起的作用,而忽视了小说选本编选者这一重要因素。其实,编选者在事实上已成为所选小说的“第二作者”。因为,明清小说选编者大多是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来选录他人作品的,正所谓“选书者,非后人选古人书,而后人自著书之道也”[1]661。而且,与诗文相比,小说这一文体的文化地位尤为低微,因此小说选编者之主观因素对小说文本的介入更为随意,他们往往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对小说原作进行多方面的增删改易,由此直接导致小说选本作品与原作之间存在明显差异,随之而来的自然是小说文本形态的演变。
一、因主题与人物形象调整而改变文本形态
缘于特定编选目的,编选者往往会对原作主旨或其中的人物性格内涵作出调整,这势必会在小说文本形态上反映出来。首先,明清小说编选者为突出、强化小说主旨而常常对原作情节加以增删改易。如《喻世明言》中《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对莫稽的负心之举并无惩罚,而抱瓮老人《今古奇观》选录该篇时却增加了以下文字:
莫稽年至五十余,先玉奴而卒。其将死数日前,梦神人对他说:“汝寿本不止此,为汝昔年无故杀妻、灭伦贼义,上干神怒减寿一纪、减禄三秩。汝妻之不死再活,亦是神明曲佑,一救无辜,一薄尔罪也。”莫稽梦觉嗟叹,对家人说梦中神语,料道病已不起。正是:举心动念天知道,果报昭彰岂有私。[2]1318
抱瓮老人之所以增加上述情节,显然与其使“善者知劝,而不善者亦有所渐恧悚惕,以其成风化之美”[3]7的劝化主旨密不可分。芝香馆居士《二奇合传》也选录了《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只不过是选自《今古奇观》,因芝香馆居士特别强调这篇小说以“戒薄幸”*《二奇合传》编选者在所选每篇小说标题下都标有三字小注以揭示其命意,这里“戒薄幸”即为《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之主旨。为主旨,所以他保留了上述惩罚莫稽的这段文字。再如,《醒世恒言》中《卢太学诗酒傲公侯》写卢柟被汪知县陷害而遭受笞杖之辱,他在被押送至牢房时由“两个家人扶着,一路大笑”;抱瓮老人《今古奇观》在选录该篇时将“一路大笑”改为“呼天大笑”,使卢柟之疏狂形象更为突出;而芝香馆居士《二奇合传》从《今古奇观》中选录该篇时将其题目改为《卢太学疏狂取祸》,并在题目下注明其主旨为“戒狂生”,又将“呼天大笑”改为“呼天大哭”,显然芝香馆居士并不赞赏卢柟的疏狂品性,认为他受辱完全是咎由自取。而且,对于卢柟的疏狂举动,芝香馆居士还特意增加了如下议论:
论起此事,若是谦谨的人,也就不难处分。纵是厌恶那贪官,只管分付手下人小心伺候,自己便服游行、如常潇洒。他若不来,我亦坦然忘怀;他若来时,衣冠接待,厚赏跟随,勉强陪他几刻,支吾几句言语,次日又答拜一次便结了帐。他若再来相请,只推不进公门,远嫌自处,权把谦卑两个字顶在头上,便是英雄韬略、明哲保身之道,不致招灾惹怒了。无奈那卢柟一味疏狂,不闻正论,就此一点刚暴惹怒了知县,后来把许大家资弄得罄尽,几乎把命送了。岂是圣贤之理?[4]78
因服务于“戒狂生”这一主旨,《卢太学疏狂取祸》完全颠覆了原作中卢柟疏狂傲岸的正面形象。再者,《今古奇观》中该篇结尾诗就卢柟傲对公侯的疏狂气质大加赞赏:“目蹇英雄不自由,独将诗酒傲公侯。一丝不挂飘然去,赢得高名万古流。”而《二奇合传》中《卢太学疏狂取祸》则将此诗弃之不用,而以如下一诗作结:“酒癖诗狂傲骨兼,高人每得众人嫌。劝君休蹈卢公辙,凡事谦恭是大贤。”这与芝香馆居士“戒狂生”的编选主旨完全吻合。[5]
有的选本为突出小说主旨还时常删节原作中的某些情节成分。例如,与其劝诫目的一致,芝香馆居士《二奇合传》有意删除了原作中的色情成分,他在该选本序中强调:“是书既主醒世,而写生之笔有涉诲淫,则所宜摈者也。”如《醒世恒言》第八卷《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孙玉郎“弟代姊嫁”,在慧娘“姑伴嫂眠”时趁机与其发生关系,其中写到玉郎的心理活动:“此番挫过,后会难逢。看这姑娘年纪已在当时,情窦料已开了。须用计缓缓撩拨热了,不怕不上我钓。”在接下来的具体描写中更是充斥不少淫亵成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玉郎是一个轻薄孟浪之人。抱瓮老人《今古奇观》选录该篇时虽对某些淫秽文字有所删节,但却保留了玉郎的心理活动。《二奇合传》则删去上述玉郎的心理活动而以“心下辗转难安”代之,而且还将原作中露骨的色情成分悉数删除,以“玉郎便与慧娘同寝,他两个少年男女情欲方动,如何禁持?枕边已将上项事件彼此一一说明了”[2]562数语含蓄带过。
另外,编选者有时通过修改原作而赋予人物形象以新的性格内涵,或借此对人物予以评价。例如,《喻世明言》卷九《裴晋公义还原配》中称“原来裴令公闲时常在外面私行耍子”,而《今古奇观》第四卷在选录该篇时将其改为“原来裴令公闲时常在外面私行,体访民情”,虽是细微修改,却有助于塑造裴晋公勤政恤民的正面形象。有时编选者还通过对原作的增删来表明对小说人物的态度,如《醒世恒言》中《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结尾交代李都管本欲侵占邻居刘秉义宅院,而最后其家宅反归刘公,对此作者感叹道:“刁钻小人,亦何益哉!后人有诗,但道李都管为人不善,诗云:为人忠厚为根本,何苦刁钻欲害人?不见古人卜居者,千金只为买乡邻。”《今古奇观》在选录该篇时对以上结尾并未作任何修改,而芝香馆居士《二奇合传》则在该篇结尾将上述批判李都管的诗歌删去,改换成自己添加的一段文字:“后人有诗评论此事都是刘妈妈妄出主意,以致女儿出丑,诗云:牝鸡何苦便司晨?枉逞聪明祸最深。只为闺门无雅教,丈夫认作指挥人。”显然编选者已将批判的矛头对准刘妈妈,因为他不满于刘妈妈在儿子刘璞婚事上不听丈夫刘秉义劝谏的自专做法。同时,《二奇合传》结尾虽然也还保留了赞颂乔太守的另外一首诗歌,但却在引出该诗前额外增加了这样的话:“乔太守保全名节,成就了佳儿佳妇,免致婚姻成仇,刑辱无辜,不愧民之父母。”其实,芝香馆居士通过增删这篇小说结尾的方式表达对人物的褒贬,还是服务于其编选目的,他在该篇小说标题下已注明其主旨为“劝断狱”。
二、因政治生态变迁而改变文本形态
明清易代,小说文本的传播环境随之改变,编选者往往根据政治生态的变迁而对原作中那些不合时宜的敏感字眼作出修改,由此也给小说文本形态带来细微却独具时代特色的变化。
一是清代小说选本在编选明代小说时将其中对女真人或满族人的特定称谓作出修改。如《别本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九选自《型世言》第九回《避豪恶懦夫远窜,感梦兆孝子逢亲》,就将其中的“鞑子”改为“臊子”“贼子”;卷十二选自《型世言》第十二回《宝钗归仕女,寄药起忠臣》,将其中的“鞑子”改为“倭子”。《西湖拾遗》卷三十六《卖油郎缱绻得花魁》选自《醒世恒言》之《卖油郎独占花魁》,作者特意将其中“金虏”“鞑子”之类有碍字眼一律改为“金人”。显然,明清易代,加之清代文字狱的严酷,导致清代小说选本对所选录的明代小说作出以上修订。
二是清代小说选本在选编明代小说时一般会对其中的朝代或帝号称谓作出修订。如《初刻拍案惊奇》第四卷《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冈纵谭侠》中有“此是吾朝成化年间事”,而《二奇合传》在收录该篇时将其调整为“此是明朝成化年间的事”;第二十一卷《袁尚宝相术动名卿,郑舍人阴功叨世爵》中有“国朝永乐爷爷未登帝位”之语,而《二奇合传》在选录该篇时将其改为“明朝永乐皇帝未登帝位”。再如,《今古传奇》卷四选自《警世通言》卷十一《苏知县罗衫再合》,将其“却说国初永乐年间”中的“国初”二字删除。《今古奇闻》卷二选自《醒世恒言》第十卷《刘小官雌雄兄弟》,将其中的“这话本也出在本朝宣德年间”改成“这话本出在明朝宣德年间”。明人周清源《西湖二集》中作品在提及朱元璋时,多用“洪武爷”或“我洪武爷”,分明是明人的叙事口气,如第一卷、二卷、四卷、十七卷、十八卷、二十卷、二十九卷等皆是如此;而清人陈梅溪所辑《西湖拾遗》将其中一些作品收录时,则改称“太祖”,叙事主观色彩大大淡化。同理,《西湖二集》中作品一般称明朝为“我朝”,如第一卷、十二卷、十八卷、三十三卷、三十四卷等,而《西湖拾遗》将其中一些作品收录时改称“明朝”。
清代文言小说选本编选者对原作朝代或帝号等称谓也有修订。以张潮《虞初新志》所收录的某些作品为例,毛奇龄《陈老莲别传》写陈老莲以绘画闻名于世,以致“怀宗皇帝命供奉”;这一表述在《虞初新志》卷十三中则变为“崇祯末,愍皇帝命供奉”[6]629—630,因为清初顺治以“愍皇帝”为崇祯帝谥号。再如,魏禧《魏叔子文集》中的《明遗民姜公传》收入《虞初新志》卷一时改题《姜贞毅先生传》,删去了“明遗民”。陆次云《宝婺生传》中有“顺治初,师破金华”一语,而在《虞初新志》卷九中则变为“顺治初,我师破金华”。这表明一些清人的小说选本,在选录前代小说作品时往往会对相关字句作出改动,这一切都反映出时代政治文化生态的变迁给小说文本形态带来的微妙变化。
三、因艺术加工而改变文本形态
编选者有时从艺术角度出发而对原作加以修改。对于那些游离于小说情节主干的闲笔,编选者往往将其删除。如《醒世恒言》中《卢太学诗酒傲公侯》用一千二百字左右篇幅详写汪县令审理强盗案,对王屠被强盗石雪哥陷害以致含冤而死的前因后果作了极为详尽的交代,然而这与主干情节并无直接关系,实属枝蔓。因此,抱瓮老人《今古奇观》在选录该篇时将王屠与强盗石雪哥之事删去,使情节更为连贯集中。再如,《醒世恒言》第十一卷《苏小妹三难新郎》开篇云:“聪明男子做公卿,女子聪明不出身。若许裙钗应科举,女儿那见逊公卿。”接着就诗歌内容发表长篇议论,历数班昭、蔡琰、谢道韫、上官婕妤之文才,并特别叙及李易安、朱淑真二人的才赋与不幸婚姻,又引述《声声慢》及朱淑真《断肠集》中的诗歌,此后才以下列语句过渡到正话:“说话的,为何单表那两个嫁人不着的?只为如今说一个聪明女子,嫁着一个聪明的丈夫,一唱一和,遂变出若干的话文。正是:说来文士添佳兴,道出闺中作美谈。话说四川眉州,古时谓之蜀郡,又曰嘉州,又曰眉山。山有蟆顺、峨眉,水有岷江、环湖。山川之秀,钟于人物,生出个博学名儒来,姓苏,名洵,字允明,别号老泉。当时称为老苏。”这段入话啰啰嗦嗦长达八百余字。这篇小说被《警世选言》选录后改题《小妹三考秦少游》,其开篇诗改为:“男子聪明为将相,女人聪明主蘩蘋。若使裙钗能应举,小妹端不逊公卿。”原本长达八百余字的入话被删除,开篇诗后直接进入正话:“却说四川眉州苏家,真乃山川之秀,钟于一门,出个苏询,字明允,别号老泉,博学名儒。”同时,还删去原本中“三难新郎”之后苏小妹替苏轼应对佛印长诗的相关情节。这样,改编后的文字更为简洁明快,情节紧紧围绕“三考”展开,不枝不蔓,更为集中。又如冯梦龙《情史类略》中《红拂妓》实为《虬髯客传》,但删去了其中大量与红拂无关的情节内容。
为使行文简洁,编选者还常常删除原作中那些冗赘的诗词韵语。如《醒世恒言》及《今古奇观》中《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描写慧娘之美:“蛾眉带秀,凤眼含情。腰如弱柳迎风,面如娇花拂水。体态轻盈,汉家飞燕同称;性格风流,吴国西施并美。蕊宫仙子谪人间,月殿嫦娥临下界。”这段肖像描写并不见于《二奇合传》。《醒世恒言》与《今古奇观》中《卢太学诗酒傲公侯》皆以大段文字描写卢柟啸圃的园林景致,而《二奇合传》在选录该篇时则将其完全删去。梅庵道人编辑《四巧说》也对原作中那些游离情节主干、以诗词韵语形式存在的枝蔓文字予以删除。如其卷一《补南陔》选自《八洞天》卷一同名之作,原作写鲁翔在科举成功后娶楚娘为妾,其妻“石氏见丈夫才中进士,便娶小夫人,十分不乐。只因新进士娶妾,也算通例,不好禁得他。原来士子中了,有四件得意的事:起他一个号,刻他一部稿,坐他一乘轿,讨他一个小。 当下鲁翔唤楚娘拜见夫人”。划线部分韵文阻隔语脉,因此《四巧说》在选录该篇时便将其删除。再如,《四巧说》卷二《反芦花》选自《八洞天》卷二同名之作,原作写长孙陈“次早醒来,看胜哥时,浑身发热,只叫心疼。正是:孝子思亲肠百结,哀哉一夜席难贴。古人啮指尚心疼,何况中途见惨烈。长孙陈见儿子患病,不能行动,惊慌无措”。《四巧说》在选录该篇时删除了划线部分,因为这些韵文也属冗词赘句,有碍情节的连贯性。而且,梅庵道人还在这段文字中增入个别词语,在“浑身发热”前增入“见他”二字,在“惊慌无措”前增入“一时“二字,这样既使语句通顺连贯,又消除了歧义。
有时,编选者为使结构紧凑,还常常变换原作的叙述方式。如《醒世恒言》中《卢太学诗酒傲公侯》写汪知县欲借钮成之死对卢柟实施诬陷报复,为此小说详写钮成之死真相,但是篇幅过于冗长,且与前文衔接不够紧密,使小说叙事结构松散。为此,《今古奇观》在选录该篇时便删除了其中对钮成与卢柟家人卢才争斗的直接描写,而改由钮成妻子金氏转述给令史谭增。经此修改,小说叙事方式得以转变,从而使情节结构更加紧凑,不致游离主线。因为此时谭增正处心积虑地构陷卢柟而不得,得知此事后他正可借机陷害卢柟以迎合汪知县,这样小说情节便始终围绕主线展开。再如,《醒世恒言》中《李汧公穷邸遇侠客》写路信听到房德夫妇欲陷害李勉,于是他将这一消息及时告知李勉,并和李勉一起逃往常山;而此时李勉不知贴身侍从王太的去向,后来在路上才遇到王太,王太告诉他“因麻鞋坏了,上街去买”,接着二人之间展开了一系列对话,这些描写与主干情节并无紧密联系,显系赘笔。因此,《今古奇观》将其改为李勉在逃亡时本已知道“王太和两个人同去买麻鞋了”[2]206,并将此事告知路信,这样通过叙述方式的改变,省却了原作中李勉逃亡途中路遇王太以及由此展开的对话,使情节结构更加紧凑。
当然,有时编选者因对原作的删改过于随意以至小说情节出现疏漏。如《拍案惊奇》中《李公佐巧解梦中言,谢小娥智擒船上盗》通过谢小娥视角写谋害其父、夫的贼人申兰之外貌云:
只见里边踱出一个人来,你道生得如何?但见:伛兜怪脸,尖下颏生几茎黄须;突兀高颧,浓眉毛压一双赤眼。出言如虎啸,声撼半天风雨寒;行步似狼奔,影摇千尺龙蛇动。远观是丧船上方相,近觑乃山门外金刚。小娥见了,吃了一惊。心里道:“这个人岂不是杀人强盗么?”便自十分上心。
《二奇合传》则将上述文字删节为:“只见里边走出一人来,小娥见了,吃了一惊,心里道:‘这个人岂不是杀人强盗么?’便自十分上心。”[4]259这样小娥“吃了一惊”及随之而来的心理活动产生的原因便缺乏必要交代。
四、因统一体例而改变文本形态
为统一选本体例,选编者还会按照一定标准对原作的形式体制予以加工改造,当然小说文本形态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编选者对原著形式体制的调整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统一标题。如《今古传奇》中有三篇作品选自标题为对句的“二拍”,其余十一篇选自标题为单句的“三言”、《石点头》与《欢喜冤家》等,编选者为统一体例而将这些单句标题一律改为对句。再如,抱瓮老人《今古奇观》四十种小说“命题则琢成对偶”[7]794,也就是说其所选作品相邻两卷形成对偶,如第一卷《三孝廉让产立高名》与第二卷《两县令竟义婚孤女》,第三卷《滕大尹鬼断家私》与第四卷《裴晋公义还原配》,等等。这样一来,编选者就得将选自“二拍”的十一篇作品的标题,由原来的双句改为单句,且相邻两篇标题形成对偶。有的选本还在修改原作标题的基础上为其统一增加了用以揭示该篇主旨的副标题,如芝香馆居士《二奇合传》为更好地揭示小说所“寓劝惩之义”[4]4,在每篇小说题目下统一附以三字小注,这实际上等于为小说增加了副标题,像第一回《刘刺史大德回天》注明为“劝积德”,第五回《裴晋公雅度还原配》注明为“戒逞势”。
二是对引首诗与结尾诗的处理。如《西湖佳话》中作品均无引首诗,除第七、十、十三卷外其他各卷均无结尾诗,但陈树基《西湖拾遗》在其中所选取的十五篇作品即第六、七、八、九、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八、十九、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十八卷,其引首诗与结尾诗皆一应俱全。也有删去引首诗者,如王寅《今古奇闻》选自《醒世恒言》第九卷的《陈多寿生死夫妻》,其中三篇引首诗及其长篇议论文字被悉数删除;选自《醒世恒言》第二十一卷的《张淑儿巧智脱杨生》也删除了原作开篇长诗。
三是删除入话与俗套的诗词韵语。如署为“李笠翁先生汇辑”的《警世选言》共收录六篇小说,其中取自“三言”的第三、四、五、六回皆删减了原作入话部分的文字,像第四回《小妹三考秦少游》选自《醒世恒言》卷十一《苏小妹三难新郎》,原作入话由引首诗出发,纵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之理,接着在头回中历数班昭、蔡琰、谢道韫、上官婕妤、李清照、朱淑真之遭际,此后才转到苏小妹之事,而《警世选言》将入话与头回删除,直接进入正话。再如,《今古传奇》将原作中的入话一概删去,原作中那些用于环境描写和肖像描写的俗滥的诗词韵语多被删除,像卷四《苏知县贼船被害,审姚大罗衫再合》选自《警世通言》卷十一《苏知县罗衫再合》,它便将原作中两千四百余字的入话故事弃之不用,还略去原作中十三处诗词套语,删除了众盗被斩的场景描写。王寅《今古奇闻》中选自《醒世恒言》第十卷的《刘小官雌雄兄弟》便删除了一千一百余字的关于桑茂的入话故事,选自《醒世恒言》第三十三卷的《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删除了近千字的关于魏鹏的入话故事。
五、“副文本”与小说文本形态演变
相对于正文,围绕在作品文本周围的元素——标题、副标题、序、跋、题词、插图、图画、封面则属于“副文本”[8]51。编选者除对小说原作情节内容加以改造外,有时还对其标题、署名等“副文本”加以改动,或以不同心理动机为选本命名,或为所选小说增加一些插图、评点等“副文本”,这也促成明清小说文本形态的演变。
明清小说编选者在选录小说时往往对其标题加以改易。例如,《警世选言》共六篇小说,除选自《古今小说》卷十四的《陈希夷四辞朝命》保持原题目不变外,其余五篇都更改题目,如第三篇《王荆公两谪东坡》选自《警世通言》卷三《王安石三难苏学士》。有时同一篇小说在不同选本中标题各不相同,如《警世通言》中《宋小官团圆破毡笠》在《今古奇观》中改题《宋金郎团圆破毡笠》,在《二奇合传》中改题《宋金郎贤阃矢坚贞》。改易原作标题的现象也时常出现于《二奇合传》《今古奇闻》《西湖拾遗》《别本二刻拍案惊奇》等小说选本中。一些文言小说选本也对原作标题任意改窜或自拟标题,甚至还会出现妄题撰者的现象。以明自好子《剪灯丛话》为例,其卷四所收晋贾善翔《天上玉女记》、吴张俨《太古蚕马记》、汉赵晔《楚王铸剑记》,实际分别出自干宝《搜神记》卷一、十四、卷十一;孙绪《夜冢决赌记》实为《太平广记》卷二八六之《刘氏子妻》,原出皇甫氏《原化记》;卷六所收唐孙頠《独孤见梦记》实为《太平广记》卷二八一之《独孤遐叔》,原出薛渔思《河东记》;宋张君房《织女星传》实为《太平广记》卷六八之《郭翰》,原出张荐《灵怪集》;马龙《渭塘奇遇记》实为瞿佑《剪灯新话》卷三中的作品。改换原作标题及妄题撰者的现象在冯梦龙《情史类略》及由袁宏道参评、屠隆点阅的七卷本《虞初志》中也十分常见。无疑,明清文言小说选本中存在的这种“杜撰书目,妄题撰人,移甲作乙,以伪为真,纷然淆乱”[9]696—697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原作的文本形态。
明清小说选本更改原作题目的原因很多。有时是为统一题目形式体制,如古闽龙钟道人辑《警世奇观》共十八帙,每帙标题均为双句,这需要编者把原作的单句变为双句,如《警世通言》卷十一《苏知县罗衫再合》被编选为第一帙,改题《秋江梦李宏招四友,妒相争惊醒南柯人》;有时即使原作标题为双句,但往往也会被编选者改动,如《无声戏》卷二《老星家戏改八字,穷皂隶陡发万金》被收录为第十二帙,改题为《行好事蒋成哥发迹,美刑厅提挈假同年》。其他像《今古传奇》也将原作题目由单句变为双句,而《今古奇闻》则将原作题目由对句统一为单句。梅庵道人编辑《四巧说》所选四篇小说统一以三字命题,故《照世杯》第一篇《七松园弄假成真》被选入后改题《赛他山》。有时是出于促销策略,如《别本二刻拍案惊奇》将原作篇目“擅加窜易,盖坊肆编集之本托凌濛初书名以求售,其更换窜乱则示其为秘本新出,与原本不同耳。”[10]128
明清小说选本的名称往往与编选者的编选动机息息相关。编选者的传播意识很强,因此他们在选本命名上往往注重迎合读者的鉴赏心理。像抱瓮老人《今古奇观》、王寅《今古奇闻》、芝香馆居士《二奇合传》、梦闲子《今古传奇》等以“奇”为名者,皆为迎合读者的尚奇好异心理。梦闲子《今古传奇》序中反复申说的“奇而不奇,不奇而奇”[11]2,即代表着选编者的命名策略。其他像撮合生辑《幻缘奇遇小说》以及梅庵道人所选四篇故事都有巧合情节的《四巧说》,也都为迎合读者的猎奇心理。至于《艳异编》《续艳异编》《广艳异编》《花阵绮言》《风流十传》《宫艳》《艳情逸史》《艳史丛钞》等,则在不同程度上同时迎合了读者的猎艳与猎奇心理。像《宫艳》专门选录《赵飞燕外传》《赵飞燕合德别传》《飞燕余事》《迷楼记》和《大业拾遗记》《长限歌传》《杨太真外传》,并附录《太真遗事》《梅妃传》;《花阵绮言》《风流十传》等则选录专写男女艳情且带有显著世俗化审美特征的明代中篇传奇小说。当然,这些以“艳”为名的选本的出现也与晚明以来风起云涌的个性解放思潮不无关联。随着阳明心学及泰州学派学说的盛行,重情思想在文学领域得到充分体现,由此催生了像《艳异编》《续艳异编》《广艳异编》《花阵绮言》《风流十传》《宫艳》《青泥莲花记》《情史类略》等以表现男女情事为主的小说选本。而人们对这些选本所表现的情欲也多作出肯定性评价,如《花阵绮言》卷首题词以“卓氏琴心,宫人题叶,诸凡传诗寄柬,迄今犹自动人,而不删郑卫,即尼父犹然,何必如槁木死灰,乃称贞教也”为说。适园主人《宫艳叙》称该选本“虽事以艳传,谁谓以艳伤雅也。若曰白璧微瑕,总在闲情一赋,则丹铅者且搁笔以听廉洛诸公之命”[12]661,强调选本之“艳”远胜于理学家之论调。
读者阅读小说最初都出于娱乐遣情之目的,编选者对此也心知肚明,这从小说选本名称上也能得到反映。嘉靖间洪楩编刊《清平山堂话本》各集分别命名为《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闲》《醒梦》,就是宣扬小说的娱情功能。清人张贵胜所辑《遣愁集》也是如此,其封面“识语”强调“是集名为《遣愁》,意以消遣愁怀为主”,宣称其中小说可使读者“反闷为快,破涕为笑”,希望“识者鉴之”。在“凡例”中编选者再次提醒读者:“是集名为《遣愁》,意以消遣愁怀为主。凡事之可喜可嗤、可羞可怒,或风流蕴藉、颖敏诙谐、庙算经天、阃筹纬地,以及忠孝节义、智愚巧诈、憨痴騃瞩、变怪惊心,无一不备。阅之真堪反闷为快,破涕为笑者,全部皆属正事,而特以解颐绝倒,弁首专合命名之意旨。”常谦尊编选《消闲述异》“专采宋元明以后稗官杂说,摘其怪怪奇奇、可骇可愕者,以娱心目,以供笑谈。”[13]其他像上述所谓猎奇猎艳之作以及《万选清谈》《捧腹编》《谐史》《广谐史》《最娱情》《排闷录》,等等,无一不昭示着编选者的命名动机。
影响明清小说选本命名的因素还有很多。例如,很多时候编选者根据所选小说情节内容拟定选本名称,如步月主人编《再团圆》所选五篇小说都是夫妇再团圆故事,它们是选自《今古奇观》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崔俊臣巧会芙蓉屏》《宋金郎团圆破毡笠》《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裴晋公义还原配》。其他如邹之麟选录《红线》《聂隐娘》《贾人妻》等而成《女侠传》,梅鼎祚编辑历代妓女之事成《青泥莲花记》等,也属此类。选本的命名有时还与编选者的抒愤动机有关。如王世贞在其《剑侠传》序中声称其家中“所蓄杂说剑客甚夥”,因“有慨于衷”而“荟撮成卷,时一展之,以摅愉其郁”[14]卷七十一。王世贞之父王忬被严嵩、严世藩父子所害,而王世贞复仇无计,于是他便通过编选剑侠故事以发抒其愤慨,这可算得上一种文化复仇。有的小说选本名称反映了编选者对小说价值的认识,如《文苑楂橘》之名源自《庄子﹒天运》中“其犹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编选者以此为名是想强调小说在经史典册之外自有其存在价值,不可偏废。而《警世选言》《觉世雅言》《警世奇观》等选本的命名,则体现了编选者的教化劝诫意识。
编选者为扩大选本传播范围,还常常通过插图、评点等“副文本”以招徕读者。如《西湖拾遗》编选者陈树基在该书序中特意提醒读者“绘图卷首”,该选本前三卷皆为图像,依次为《西湖古迹图》《西湖十景图》《西湖人物图》,包括精美插图五十余幅。其他如撮合生辑《幻缘奇遇小说》有插图二十四幅,上海图书馆藏本抱瓮老人编选《今古奇观》中四十篇作品各配有一幅插图,《新镌全像评释古今清谈万选》中每篇作品也配有一插图。一些编选者还对选本中作品加以评点,以期为读者起到导读作用。如张潮在《虞初新志》“凡例”中特意向读者说明:“文自昭明以后,始有选名;书从匡郑以来,渐多笺释。盖由流连欣赏,随手腕以加评;抑且阐发揄扬,并胸怀而迸露。兹集触目赏心,漫附数言于篇末;挥毫拍案,忽加赘语于幅余。或评其事而慷慨激昂;或赏其文而咨嗟唱叹。敢谓发明,聊抒兴趣;既自怡悦,愿共讨论。”[15]4—5《虞初志》卷首有王穉登、汤显祖、欧大任和凌性德所作四篇序,文中有署为汤显祖、袁宏道、屠隆、李贽、钟人杰、邹臣虎,臧晋叔等人的评点。署为“长洲周之标君健甫选评”的《香螺卮》中的作品都有眉批、旁批与总评,而且各卷还标明参订者为“同社”徐文衡、申绍芳、吴思穆、汤本沛、徐文坚、赵玉成、徐遵汤、曹玑、郑敷教,显然该选本是集体合作而成。他如《宫艳》《新镌全像评释古今清谈万选》及《续虞初志》《情史类略》《太平广记钞》《虞初志》《艳异编》《风流十传》等,皆有多少不一、形态不一的评点文字。
有的编选者还在选本中有意增入其他“副文本”以强化编选主旨。《西湖拾遗》编选者陈树基在卷首自序中自称该选本主要“汇古人之忠孝节义政事文章”[16]9,因此他在无任何故事情节、题为“止于至善”的最后一卷中抄录大量劝诫诗文以“感发惩创”。为此,他在该卷自称:“西湖之山水人物,无不禀秀气以生,独擅东南之胜,则志其地、实其人、指其事,既可宗彰瘴之意,而复集《劝孝歌》《遏淫诗》《心身家官四箴》《戒赌十则》于后,以当清夜钟声也。”[16]1927接下来他便依次抄录《梁武帝劝孝歌》《赵石麟先生戒淫十八律》《何梅严先生心身家官四箴》《戒赌十则》。选本最后陈树基又在“后序”中再次申明编选宗旨:“援古证今,一二端即为殷鉴,正必崇而邪必黜,以身涉世,历历可凭,善斯劝而恶斯惩,触目警心,赫赫如昨,拾西湖之遗事。”出于编选者之手的自序、后序及毫无情节可言的最后一卷“止于至善”都属“副文本”,它们都成为编选者申说编选主旨的载体。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有的编选者在对原作形式体制进行改造时,往往会增删其中的“副文本”。以王寅《今古奇闻》为例,其中选自《西湖佳话》者有的在正文前增加了一段实为“副文本”的“小引”,如选自《西湖佳话》卷十四的《梅屿恨迹》在卷首增入一段关于小青之事的引文。有时王寅甚至引录原作中的评点文字,如选自《娱目醒心编》卷十三《争嗣议力折群首,冒贪名阴行厚德》的《许武善能孝于兄弟》,其卷尾便附以近二百字的“自怡轩主人曰”评语,而“自怡轩主人”许宝善本是《娱目醒心编》的评点者,其评点成分当属于“副文本”。再如,张潮自称在编选《虞初新志》时曾对原作“潜为删逸,以成全璧”[17]甲集“选例”,他删除了原作中那些类似于“君子曰”“异史氏曰”之类的论赞成分,像严首升《一瓢子传》结尾的“外史氏曰”、宋曹《义猴传》结尾的“射陵子曰”、曹禾《顾玉川传》结尾的“曹子曰”等,都属于非情节性的超叙述结构,是原作者的抒情性议论,在本质上属于“副文本”,它们都不见于《虞初新志》。同样,冯梦龙《太平广记钞》将许多唐传奇小说结尾的“君子曰”部分或用以交代故事来源的段落也省略了,这些成分也等同于“副文本”。
种种迹象表明,明清小说编选者确已成为所选小说的“第二作者”,从而促成了小说文本形态的演变。毕竟,选本在中国古代是一种特定的批评形式,在小说选本盛行的明清时期,编选者正是通过对小说原作文本形态的加工改造来实现其批评目的的。
[1] 谭元春.古文澜编序[A].新刻谭友夏合集[C].济南:齐鲁书社,1997.
[2] 抱瓮老人.今古奇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3] 姑苏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A].抱瓮老人.今古奇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4] 芝香馆居士.二奇合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5] 程国赋.三言二拍选本与原作的比较研究[J].明清小说研究,2004,(2).
[6] 张潮.虞初新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7] 今古奇观识语[A].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8] (法)弗兰克5埃尔拉夫.杂闻与文学[M].谈佳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9]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10] 孙楷第.戏曲小说书录解题[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11] 梦闲子漫笔.今古传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2] 萧相恺.珍本禁毁小说大观[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
[13] 常谦尊.消闲述异序[A].消闲述异[M].道光二十年(1840)刻本.
[14]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M].万历五年(1577)王氏世经堂家刻本.
[15] 张潮.虞初新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6] 陈梅溪.西湖拾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7] 张潮.昭代从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