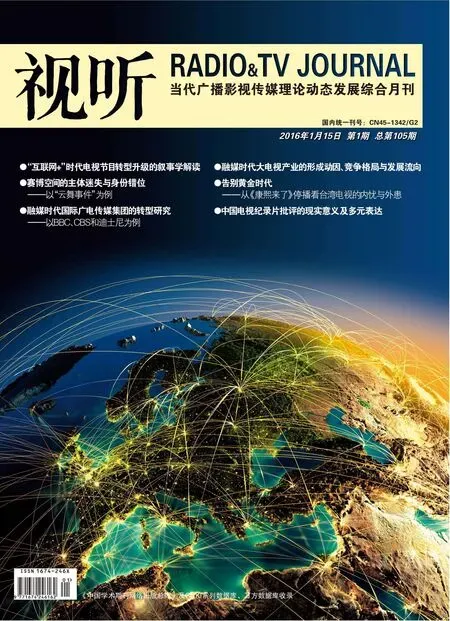赛博空间的主体迷失与身份错位——以“云舞事件”为例
□赖黎捷 卫彦瑾
赛博空间的主体迷失与身份错位——以“云舞事件”为例
□赖黎捷卫彦瑾
摘要:在以互联网为主体的赛博空间里,人的主体性意义被赋予了虚拟化色彩。真实交往与虚拟世界的身份边界被打破和消解。本文以江西省鹰潭铁路医院33岁女护士方某自杀,引发的关于“云舞事件”的探讨为着力点,分析了“云舞”在经历现实生活坍塌与虚拟化身的重建过程中,呈现出的行为动机与心理轨迹。“云舞”在沉溺虚拟/拟态/仿像世界完美形象的建构中,僭越了触手可及的现实生活的种种边界,理想与现实的对峙与冲突加剧了主体迷失与身份错位,最后走向精神断裂。
关键词:云舞事件;赛博空间;主体迷失;身份错位
2015年9月21日,江西省鹰潭铁路医院33岁女护士方某被发现在宿舍自杀。据鉴定,方某系自杀,死因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时间为17日凌晨。随着消息的发布,事件引发网络热议。百度贴吧、大连某高校贴吧、天涯论坛、铁血社区等均有大量网友参与,而在新浪微博,截至10月8日17时,“男获遗产后分手女轻生”话题阅读量高达268万次①。方某生前是网络游戏《梦幻西游》江西区女儿村排名前三的高手,同时也是一个游戏直播平台的音频女主播,拥有数十万粉丝,网名“梦幻云舞”。方某在网络空间的男友也因其自杀事件与之密切相关而遭到“人肉搜索”。这场被广泛关注的事件被称作“云舞事件”。
在新媒体甚嚣尘上之际,以互联网为主体的赛博空间呈现出了多元化、异质性、虚拟状的特征。在这个空间里,个体的主体建构和身份认同充满着无限可能,自我在网络空间变动不居的场景中得以重新塑型。与此同时,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身份边界被打破和消解,网络空间正在建构一种新的“现实世界”。在转型期社会变革语境下,青年网民群体如何建构多重自我,如何应对瞬息万变、碎片化的网络空间,是否面临网络空间的主体迷失与身份错位,日益成为无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本文以“云舞事件”为例,对上述问题作一探讨。
一、现实自我的坍塌与虚拟化身的重建
“云舞”的死亡跟职业无关,与她的网络经历息息相关。在现实空间里,她是一名护士;在赛博空间里,她是《梦幻西游2》游戏的玩家。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身份的差异可以说是导致“云舞”自杀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现实自我的坍塌
学者麦基卓、黄焕祥曾将自我划分为真实我、理想我和现实我。真实我指婴儿的基本天性和人格特征,包括个人生命的所有潜力。但在成长过程中,为了取悦父母,必须修正自己的行为,背离真实我,于是形成了理想我,即可以得到接纳和认可的自我。在大多数情况下,真实我的欲望必须屈服于理想我的要求,二者达成某种妥协,发展为现实我。人的成长,充满了遗弃真实我而产生的自我憎恨,会累积越来越多的负面情绪,感到空虚无助,即本体焦虑。
现实的境遇使“云舞”离心目中的自我越来越远。儿时的“云舞”喜欢独自埋头画画,同学们给她取了个外号“鸵鸟”。也喜欢热闹,好客,和男同学嬉戏,邀同学到家里一起做作业,把自己的画作赠予他人。这一阶段的自我是安静的、热情的,是阳光、外向、有才气、专注的。
然而,随着岁月推移,“云舞”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境遇又让她不得不面对另一个自我:家境平常,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父亲罹患癌症,早早去世,母亲没有工作。这一自我不仅让她孤独、自卑,而且给她的心理制造了诸多的压力。特别是父亲去世后,没有了父亲庇护,加上母亲对她的警惕设防又寄予重责,使她压力倍增。从“云舞”和同学的交流中可知,她的理想自我的定位是趋近于父亲的,性格和善,淡泊功利。“云舞”工作单位和所在城市平淡无奇的状况也令她对现实极度失望:医院、食堂、宿舍三点一线的生活,稀少的病患。这种状况的高度确定性、趋于一成不变加剧了“云舞”的本体焦虑,即现实我与理想我的距离不断加大,使主体感到强烈的失落与恐惧。
现实自我的持续恶化,终于随着父亲的离世轰然坍塌。父亲的离世使“云舞”感到现实空间中的孤立无援:她拿着电话卡到医院一楼大厅外的IC电话上拨通了一个个亲戚、长辈和朋友们的号码,一个个地说“我爸爸去了,麻烦来一下医院”。接到电话,有人会安慰她,“别太伤心了”,也有人只是说,“好,马上来”。母亲几乎崩溃,总是“怪她不争气不上进”,对她警惕设防,云舞自己描述道:“想尽可能地从我这里搜集钱,老了就可以不用担心我不养她”。心脏病犯了,难受得昏天暗地,也不愿告诉母亲,因为她“不了解我需要什么,胡乱强加给予”②。从这些描述不难看出,现实空间里的“云舞”,缺乏亲朋好友的关爱,母亲在自我定位上又与之截然对立。在现实空间里,“云舞”是孤立无援、不被人爱护和理解的。
此后的十年,一面是网络空间里虚拟化身的辉煌热闹,一面是现实空间里加剧的孤独与焦虑,“云舞”试图用虚拟的自我替代现实空间里坍塌的自我。
(二)虚拟化身的重建
所谓虚拟化身,我们可以理解为在虚拟空间或者虚拟场景中将主体意识投射到虚拟角色中,摒弃现实我,重构新自我,将理想的自我形象投射到虚拟空间的生活、工作、恋爱等虚拟行为中。在以互联网为主体的赛博情境中,“云舞”通过编制一套极具表演性、戏剧性的符码,试图打造一个拟象化、理想化的自我,弥补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缺憾,从而追寻马斯洛心理需求理论所指涉的最高层次的自我价值实现。
美国学者欧文·戈夫曼认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处处粘附着表演痕迹,无论是休息栖居,还是日常对话,都是“向他人呈现我们自己”的一种表演行为。“表演就是图谋显示出他的精神、力量以及其他的各种优良的特性。”③在互联网世界里,“云舞”试图通过娴熟运用游戏这一表演形式,展示其优秀品质,成为游戏/虚拟世界的焦点人物。她不仅建立了理想中的社交圈,而且出类拔萃,成为众人追捧的女神。现实空间中的社交活动对她的吸引力远远不及网络空间,玩网络游戏成为她重要的生活部分。大伙聚餐,她早早离去,理由是参加“帮战”。所谓帮战就是在《梦幻西游2》里,每周五、周六、周日晚上固定的项目,是由系统随机分配,两个帮派之间进行的对战。
每一场表演,都离不开“前台”的支撑。戈夫曼认为,“前台是个体在表演期间有意无意使用的、标准的表达性准备”④。前台是表演的聚集地和展示场所。在“云舞”的表演过程中,《梦幻西游2》无疑就是她完成展示表演的“前台”。《梦幻西游2》是一款时下流行的网络游戏,是基于互联网平台、支持多人在线、每个游戏参与者都可以通过控制游戏中的虚拟身份而相互沟通、相互影响的虚拟数字社会的体验过程⑤。操作很简单,玩家只需无限重复一个点鼠标的动作,跟随游戏情节设置,独自或组团队打怪升级做一系列的任务。游戏中还可以与其他玩家语音聊天,互动交流。玩游戏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玩游戏,在这其中,现实世界里的友情、爱情、烦恼、快乐等,都仿真地得以再现。正是这样一个“前台”,成为了“云舞”自父亲去世后的十年陪伴。在网络游戏中的虚拟交流活动逐渐代替了她在现实中的社交活动,在网络游戏中的社交圈也渐渐取代了现实中的社交圈。
在游戏的表演中,“云舞”获得一种现实生活无法得以实现的替代性满足,建构一个迥异于真实世界的理想化的“虚拟自我”。她不再是三点一线的普通护士,而是一位穿戴奢华、实力强大的美丽女子。她的锦衣奢华靡丽,由30个“彩果”染色而成;她的级别已经达到顶级,是175级;她的宠物也是优质宠物:“粉色泡泡”;她的所有技能也都是满级。“云舞”的自我在这里得以完美重建:才华横溢,光鲜亮丽,受人尊崇。
网络游戏具有虚假性表演,不仅为用户提供虚拟场域,而且为受众赋权,令其在其中重拾话语权。在米歇尔·福柯看来,话语权具有较强的权力意味,它是权力的一种象征和符号。而在自媒体时代,话语权逐渐下移,人人都可以成为话语传播者。在游戏世界里,“云舞”不仅可以自由支配游戏装备,而且还可以选择现实生活难以满足的“虚拟婚姻”。游戏中设置有“结婚”这项虚拟制度,抬花轿、新人拜堂、宾客致礼、发放喜糖等现实生活的各种仪式植入了互联网精神,甚至连生孩子、过日子,都可以虚拟化。起初的云舞是审慎而理性的,在游戏里坚持单身多年。她在QQ上曾挂过这样一句签名:“网络太近,现实太远。实在不适合投放太多情感”。2013年底“云舞”在游戏中结识了角色名为“附送折磨”(以下简称“折磨”)的男子。“折磨”加入了云舞所在的团队,与她一起在团队里执行各种任务。2014年“云舞”在一个拥有数十万粉丝的游戏直播平台中担任女主播,“折磨”开始在直播平台观看“云舞”的直播,并为她刷虚拟礼物示好。甚至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云舞的小甜心”。渐渐熟悉之后,二人感情升温在游戏里结婚。“婚后”在该游戏的服务器上,二人更是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游戏,并肩作战,佳绩连连,成为游戏里为人称道的“实力派夫妇”。这时“云舞”的心态发生了转变,把所有的感情都倾注在了虚拟世界里。“云舞”在网络游戏中重建了一个理想我,即实现其关于自我的诸种想象与理想的我:富有才气,受人尊敬和追随,终得如意伴侣。
二、超媒体自我及其对现实世界的僭越
现实生活的压抑与无奈促使“云舞”转向网络空间。网络空间中理想自我的建构不仅重塑了自我,而且重构了生活方式。虚拟的化身与虚拟的生活方式促成了超媒体自我幻象的“完美现实”,这一幻象替代了现实空间的虚空,并渐居主导,僭越了现实世界。
(一)超媒体自我的建构
游戏是人类自儿时起认识自我、建构自我的一种重要方式。游戏将现实同化于活动本身。按照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划分,网络游戏属于象征性游戏。象征性游戏具有把真实的东西转变成人们所想要的东西,从而使自我得到满足的功能。互联网是虚拟性的完美表现。互联网具有多线程技术特征,由此它在时间上可以不同步,在空间上可以无限拓展。借助互联网,人们可以选择性地进行多维展示,由此建构具有无限可能性、开放性的超媒体自我。互联网对于用户而言,主要是为了进行符号交换和自我表现,尽管具有虚拟性,但是它确实具有特殊的现实效应。这些用来展示自我的符号可以与其指示物完全分离开来,用鲍德里亚的术语,它们都是拟像,是没有原作的拷贝。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中,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象程度而不是现实所是)“变成任何你想充当的人”⑥。这样,人们仿佛逃避了现实世界的所有冲突。
法国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在进行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消费运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充满着消费性。消费本身是一种自主性的体现。这种自主性的实现“通过景观、表演、生活、自恋的循环,将自我生活与媒体景观融为一体,建构以自我为中心的独特理解图示。”⑦“云舞”通过网游消费,将游戏表征、生活模式以及虚拟自恋融为一体,开启了集荣耀、理想、虚幻于一体的自我建构模式。“云舞”将自我的故事置入网络游戏的新语境中,并与现实境遇相融合,生成关于自我的拟像,并把自己与其化身的虚拟品质相认同。虚拟身份的建构实际上是对主体所拥有的各种资源的选择和重组。现实中某些被隐匿的身份资源在虚拟身份的建构中成为核心资源。在现实生活里,“云舞”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护士,低调,离群索居,其甜美的歌喉、顽强的竞技精神和团队合作中的指导才能在病患甚少的急诊岗位上难以发挥,而在虚拟身份中,这些资源得以发挥。“云舞”凭着甜美的嗓音在比赛中脱颖而出,被聘为《梦幻西游》江西区唯一一位官方主播,向广大玩家传授各种玩法。每晚八点,《梦幻西游》的游戏直播平台上,许多粉丝都静候着她的声音。她成了网络世界的明星,受人追捧。
在网络游戏中,玩家与其他角色处于同一时空的感受被强化,并进而表现为强烈的虚拟社群归属感。在现实世界里,“云舞”的社交圈几近空白。在虚拟世界中,“云舞”热衷于帮派战争,与帮派玩家一起执行各种任务,共同遵守帮规。在帮派中,“云舞”处于管理高层,有着较高的地位和较多的追随者。帮主南宫还是她无话不说的闺蜜。单身、丧父、不受关注等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被隐匿或者过滤。甜美的爱情、完美的婚姻、高级的装备、高超的玩法、甜美的嗓音、批量的粉丝等,这些聚合了“云舞”关于理想我的种种元素建构了其超媒体自我拟像,并在“云舞”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日渐取代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自我。
(二)虚拟空间僭越现实世界
借助互联网建构的超媒体自我实际上是一种拟像。在此意义上,身份变成了一种空虚的构造,因为在表现身份的符号系统背后不存在任何东西。这种符号过程与自我故事的生成语境是日益分离的。因为把故事重新置入新的语境中正是互联网的典型特征。⑧
起始,她保持着现实和虚拟的平行,但渐渐虚拟空间逐渐与现实世界交叉融合,进而僭越了现实世界。在写给表哥的遗书中,“云舞”写道:“妈妈去世后,一直是他(玩家‘折磨’)陪着我,鼓励我坚强,可我还是做不到,但我很感激遇到他,才让我坚持了这么久”。网络空间中的“相公”在“云舞”心目中履行了真实丈夫和朋友的职责。她将几乎全部的情感和付出投入到虚拟空间。
“云舞”喜欢打简简单单的小怪兽,并以此赚取游戏币和游戏道具、装备。运气好的时候,一个月卖道具装备能赚一两千块。这跟她在现实中的工资相差无几。虚拟空间带来的现实感和实实在在的收入使“云舞”将两个空间逐渐混为一体。她的好友“南宫”发现,“云舞”玩游戏的心态发生了变化,目的性越来越强,一个人开了5个号,“天天都在拼命打,把得来的东西卖钱,把赚的钱都打进那个男的账户”(即“折磨”,她在虚拟空间中的夫君)。
虽然游戏身份是虚拟的,但玩家的主体意志却是真实的。持续推进的虚拟场景的设置和高仿真的人际交往使游戏主体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云舞”在游戏中的行为与现实中的行为风格日趋一致。尽管在网络游戏中,结婚可以轰轰烈烈,设置有抬花轿、新人拜堂、宾客致礼、发喜糖等隆重的仪式,也可通知好友前往观礼,但是“云舞”与“折磨”的网络婚姻选择了低调和悄无声息。熟识其为人的帮友意识到,她可能将此婚姻视同现实婚姻了。
不仅如此,虚拟空间甚至僭越了现实空间。当“折磨”提出与“云舞”分手后,“云舞”向单位请了半个月的假,飞往大连,提出要和吴青(“折磨”的真名)再见一面,“想知道当初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我有权利、有资格知道这些。”“云舞”不顾请假误工带来的损失,用现实世界的行为解决虚拟空间的冲突,已经将虚拟空间的种种置于现实世界之上。在大连的半个月里,二人度过了短暂的情侣般的小日子,这令“云舞”加剧了对爱情和婚姻的想象和梦幻。她选择了虚拟空间表达这种认同:七夕节那天,在剑侠情缘里为“折磨”放了“一个海誓山盟的烟花”。她用这种情侣间在游戏里表达爱意的道具,将其爱情展示给游戏中的玩家而不是现实中的亲友。
虚拟身份并非无条件和完全虚空的,也有其内在的实现机制,依托于主体表现来自现实世界的真实的主体意志。网络空间去除的只是身份的物理形式,而在心理层面,虚拟身份依然保留着真实生活中一些身份特征的印记。
在现实生活中,“云舞”是孤独、缺乏关爱和真心伴侣的,在虚拟空间里,“云舞”试图弥补这些虚空。“云舞”给网友安然发了一封信,写道:“没有谁会长长久久地陪伴我,属于我一个人,除了我的爱人。”对游戏玩家而言,虚拟空间中自由的想象与高仿真的实践比真实的还要真实。玩家的生活变成了虚拟与真实并存的多重结构。这种真实感随着虚拟空间对现实世界的介入程度加深变得异常强烈。
三、双重空间的主体迷失与身份错位
交流是从自我城堡中徒劳的突围⑨。在人际交流的层次上,主要的障碍是双方的意图错位:每听见一句话,我们自然而然地会认为,说话人所指的意义,是我们自己使用这些词语所指的意义。事实往往背道而驰。网络游戏制造了无数可以随时转换或同时存在的身份场所。在一个游戏空间中的有妇之夫,在另一个游戏空间可以假定为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网络用户之所以长时间、高强度地粘合在游戏中,与虚拟身份的自由流动和随意转换不无关系。
在云舞事件中,玩家“折磨”起初是“云舞”所在帮派的一个帮友,还是“云舞”主播节目的忠实粉丝。随着互动推进,游戏空间的“折磨”爱上了“云舞”,甚至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云舞的小甜心”。在“云舞”的心目中,“折磨”从一个追求者成为夫君,同时也是一个可以交心的朋友,对他寄予了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的双重期许。然而“折磨”却与她不同,没有太多的社会经历,网络游戏只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承担的主要是消遣和娱乐功能。“折磨”真名吴青,现实中只是一个1994年出生的辽宁大男孩,是大连一所高校的学生,比方某整整小了十岁。
在网络游戏之中,常常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身份混合:一种是把网络游戏看作是真实社会网络的组成部分,把网络游戏中的身份当作是其所声称的身份,“作为其所是”,另一种是仅仅把网络游戏当作是一种“游戏”或“扮演”,是一种“幻想”世界中的行为,网络游戏中身份只是其所幻想的身份。
交流意图的错位源自两个主体对自身身份定位的差异:“云舞”试图在虚拟空间实现理想我,“折磨”只是将真实我的种种欲望在游戏中释放。当“云舞”以夫妻之道要求“折磨”时,“折磨”却抽身离去,在另一个游戏空间里与玩家“半夏”结为“情缘”。当“云舞”质问“折磨”为什么在另一游戏中另觅新欢,“折磨”回答道“我从来没爱过你,没拿你做过女友,你做的那些事都是自愿的”。“云舞”是在与“折磨”虚拟主体交往中寻求到了比真实还真实的夫妻身份认同和心理归属感,弥补了现实社会自我身份实现的缺憾。当有人打破这种平衡时,她便丧失了主体意识中无比重要的归属和依赖,她的双重期许落空了,导致其迷失现实我,又暂时无法重新建构,陷入主体迷失状态。
尽管“折磨”意识到“云舞”将网络游戏的身份混同于现实世界之后,先是以“寝室的网不好,晚上11点后就要睡觉”“父母反对”为由,冷淡地对待“云舞”,后明确提出分手,试图结束这段交往,但“云舞”坚持用现实世界的行为方式试图挽回这段感情。她与虚拟空间中的“第三者”对质,将所有的财产进行公证,将绝笔信发给对方,寄出以“夫妻之实”名义希望对方继承的银行卡、遗嘱公证书、笔记本电脑等。双方的交流一次次陷入各行其是、背道而驰的僵局。
玩家?恋人?网友?丈夫?云舞事件中的当事人在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的相互交织中重构了多重自我,沉浸于虚拟时空又无法逃离现实世界的主体意志发生错位。不同身份定位的两个玩家,借助虚拟化生存,排遣现实生活中与身份角色相关联的社会化特征带来的压力,同时也因互联网超链接、多元化并存的场景化模式而遭遇身份迷失与主体惶惑。
互联网作为一种信息方式正在改变我们的世界,值得关注的是,它更重要的影响莫过于个体在虚拟与现实的交错中被置换成一个多重、播撒的主体,并被不断质询为一种不稳定的身份。如何在互动、重叠与转换主体建构与身份塑造中寻求自我,对于尚不具有成熟、稳定价值观的青年群体而言,显得尤为重要。
注释:
①中国青年网.女主播遭抛弃后烧炭自杀负心男友遭人肉[EB/OL].2015-10-9,
http://d.youth.cn/shrgch/201510/t20151009_7188994_2.htm
②罗欢欢,李志健,闵珍琪.网络女神的死亡游戏[N].南方周末,2015-10-29
③④[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14,19
⑤何旭东.第九城市网站分析与发展战略[D].上海交通大学,2002
⑥⑧[荷兰]约斯.德.穆尔.赛博空间里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M].麦永雄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81,184
⑦殷乐.电视娱乐:传播形态及社会影响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292
⑨[美]彼德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M].何道宽译.华夏出版社,2003:16
(赖黎捷系重庆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卫彦瑾系重庆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