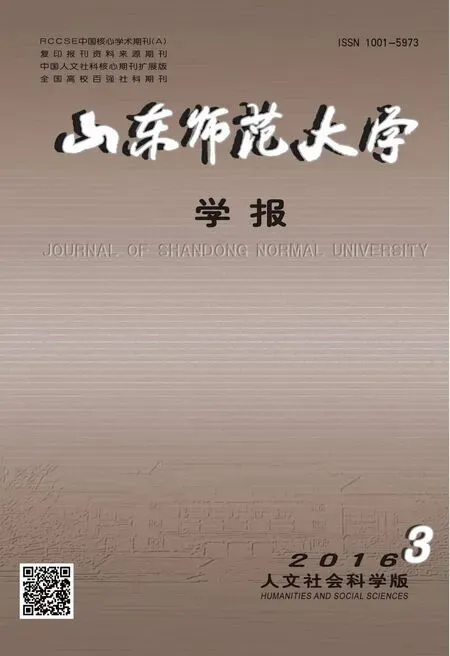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名人博物馆关系初论——以郭沫若研究为例*
张 勇
( 中国社会科学院 郭沫若纪念馆,北京,100009 )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名人博物馆关系初论
——以郭沫若研究为例*
张勇
( 中国社会科学院 郭沫若纪念馆,北京,100009 )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现代名人故居博物馆发展和建设一直处于隔离的状态。从本质意义上来讲,现代名人故居博物馆可以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有形和无形的资料,而现代文学研究也可以将最新的科研成果引入现代名人故居博物馆的日常展览展示之中,两者共同构成填充和反哺的关系。合理充分利用两者的关系,无论从学理判断还是现实应用上来讲,都具有极高的价值和意义。
文学研究;博物馆;郭沫若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6.03.003
2015年8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八版的争鸣栏目,刊登了童庆炳《两种声音一个结论——兼谈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区别》一文,这篇文章从郭沫若纪念馆内所展出的有关《蔡文姬》展品的说明条“为曹操翻案”一句入手,展开详尽的论述,最后得出了《蔡文姬》剧本的主题“是表达千千万万进步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童庆炳:《两种声音一个结论——兼谈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区别》,《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4日。的观点。姑且不论童庆炳最后的结论如何,单就他的研究方法来说就值得我们深思。童庆炳向我们揭示出了目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而又未被重视的视角和方法,也就是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名人博物馆之间关系问题的探讨。
1915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真正拉开了序幕,白话文的创作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一大批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应运而生,《狂人日记》《女神》《尝试集》《骆驼祥子》等不胜枚举,与之相对应的是这些名著的创作者们都成为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学艺术大师。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人以不同文学体裁的创作带领阅读者进入到了一片广袤无垠的艺术世界。随着社会和政府对于文化建设和发展的重视,以这些名人居住过、活动过的地方为基础,建成了各类名人故居博物馆。这些现代文化名人故居博物馆尽管规模大小不一,但都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特别是这些现代文化名人故居博物馆里藏有大量的名人本人创作手札、藏书以及手稿,以及他们与其他文化名人之间交往过程中的通信等珍贵文物。这些文物本应该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博物馆也可以利用其对外宣传教育的功能,扩展现代文学研究的范畴和影响,但是现实情况却是现代文学的研究和博物馆的发展建设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和领域,几乎很少有交叉和融合。那么,这两者之间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关系?探究两者之间的关联,究竟又有怎样的意义呢?
一、现代文学研究与名人故居博物馆分离原因的探析
要阐释现代文学研究与名人故居博物馆之间关系的问题,首先应该明确两者之间的现状。就目前情况来看,两者还几乎处于各自的轨道之中,未能相互影响和促进。造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名人博物馆之间隔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范畴和视野所限
长期以来文学研究者主要分布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而普通民众能够进行文学鉴赏者少之又少,能够从事所谓研究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因此文学研究被深深地打上了学院派的烙印。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西方新的研究方法的引进和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这种学院派的印记愈发明显。不可否认,遵循“学院派”研究路径和方法,会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水平,保持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同步性。但在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些突出的问题,如学院派研究成果的现实转换率不高,很多研究成果未能直接给广大民众以现实指导。特别是一些高级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课题,一般最终都是以结题报告或专著出版等作为结题的最终成果,而研究成果的现实应用方面的推广则几乎被研究者忽略掉了。
这就造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研究成果和现实应用的脱节。仅以郭沫若的研究为例,恐怕现在绝大多数人都认为郭沫若的《女神》是典型的浪漫主义诗作,郭沫若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浪漫主义的先声,类似于:“郭沫若立足于‘五四’时代现实,面向世界潮流,在《女神》的诗歌中,灌注着冲决封建藩篱、改造社会的强烈要求和追求美好理想的无比热力”*黄曼君、朱寿桐:《中国现代文学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7页。这样的论述相当普遍,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中也基本上是把这种结论教授给学生。但最新的研究却不断地在证实,郭沫若的《女神》不仅仅是一部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它还有更深层的意蕴。通过研究,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郭沫若的“《女神》只是郭沫若当时诗歌创作的一个选本,是诗人自己辑录的一个选本,即使诗人以为这五十余首诗可以代表自己那时的创作,但对于文学史的阅读和研究来说,无论如何它们是不可能涵括郭沫若早期诗歌创作的全部内容的”*蔡震:《郭沫若著译作品版本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第65页。。另外,“《女神》却是在另外一个文化环境里诞生的,与国内新文学发生的环境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女神》是一个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在九州地区读书期间创作出来的一个诗歌作品集。‘中国青年’、‘留学生活’、‘日本九州’,这样几组关键词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才是《女神》创作的真实背景,但它们很少,或几乎没有被注意到”*蔡震:《郭沫若著译作品版本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第66页。。《女神》其实“是郭沫若从自己留学经历的一段时间内所写作的全部自由体新诗中选录辑成,在这一段时间内他写成的诗作远不止《女神》中那56首”*蔡震:《郭沫若著译作品版本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第66-67页。。通过以上的这些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肯定会纠正以往我们对这部作品的原初印记,也会为普通读者进一步科学正确认识《女神》提供新的视角。这本应该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目前的现状却是文学研究最新的成果仅仅停留在研究者理论研究的层面上,而很少能够直接影响到普通读者的认知。
2.博物馆旧有的建设理念使然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博物馆建设两者之间的现状,除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自身的历史传统外,其实也与博物馆旧有的建设和存在的理念有很大的关联。随着我国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博物馆的建设越来越受到民众的关注。“博物馆作为对话远古与现代的纽带、联系现在与未来的桥梁,自诞生之日起就以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导向,结合人类的社会实践经验,积极开展着收集和保护藏品、陈列布展以及科学研究等工作,进而在保存自然与人类社会的记忆、传承文化、教育公众、启迪智慧、陶冶情操、休闲娱乐以及作为国家或城市的文化象征等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业已成为人类社会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元素。”*姜涛、俄军:《博物馆学概论》,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页。因此,博物馆已经成为了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关键的是博物馆已经是公众文化教育的主要承担者之一。
伴随着各类专业博物馆的发展,近些年来以现代文化名人为主体的名人故居博物馆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成立起来。这些现代名人故居博物馆有着自己先天的特征和优势,它们既具备一般博物馆以展览为主的特征,也具有名人自身生活场所的特性。因他们所展示的主体大多为广大民众所熟知的历史文化人物,因此这类博物馆更加具有亲和力和吸引力。以郭沫若纪念馆为例,每年到馆里参观的人数不少于5万人,每年还有主题展和外展,参观这些主题展览的人数更是超过了10万余人。另外,像一些免费开放的博物馆参观的人数更是居高不下。如北京茅盾故居就是免费向观众开放的,它每年接待参观的人数近10万人。这些参观的观众从年龄来讲,大到耄耋老者,小到10岁左右的小学生;从学历层次来讲,既有从事高级专业研究的学者,也有普通的市民群众。因此,博物馆已经成为社会公共教育的最重要的场所,也是普及社会科学知识、传播传统文化的有效阵地。目前,为了更好地加强对公众的教育,各个博物馆纷纷改善陈展设施,增加先进的展览手段和技术手段。不可否认,经过上述方式的提升后观众参观的外在环境有了极大的改观,但仅仅考虑这些是不够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更新展览的内容,特别是对于展品的说明,如何能够把对该问题最新的认识成果引进到展览中来,这是目前博物馆展览方面应该首先考虑的问题。
文物是博物馆特有藏品的总称,因此文物的保护和展示是博物馆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文化名人故居因其基本属于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因此馆藏的物品自然而然便被视作文物加以珍藏。而这些文物又与古建类型的博物馆有着很明显的区别,文化名人故居博物馆的文物大多是这些文化名人生前创作作品的底稿、手稿、版本书以及他们所使用过的物品等。对这些文物的保护,多年来,资料保护者都是采用“藏而不见”的方法。他们认为保护就是要束之高阁,就是要秘不示人。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极其被动的保护方法,它既造成了对这些文物资料难以有效利用的现实,也造成了博物馆与其他领域隔阂的弊端。在这种理念之下,相关的研究者们也只好望而却步,合作更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了。
正是在以上诸多原因的作用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相关的文化名人故居博物馆本应该有的联系、沟通与合作便无从谈起了。
二、填充与反哺:两者关系的重新定位
虽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名人故居博物馆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门类,但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对象和现代名人故居博物馆所展示的对象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它们之间的关系本不应该是两条平行发展的直线,而应该是互相促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存在,具体来讲应该是一种填充和反哺的关系。
所谓填充,主要是指名人博物馆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可靠的原始资料,以促进相关研究的深入。这些原始资料既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有形和无形的历史资料都将对研究对象的研究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有形资料主要是指报刊、手稿、书信等纸质媒介所承载的现代文化名人创作、生活等方面的信息。近年来文学研究越来越重视史料的发掘和运用,特别是距离当下较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更是由于研究方法、研究氛围等客观原因,长期以来形成了重宏观轻史料、重阐释轻实证的研究方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史料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这才出现了现代文学研究中特有的“补课”现象。例如,郭沫若研究便是最明显的事例。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有关郭沫若的研究几乎都是理论探讨类型的成果,很少有史料分析的。这种研究所带来的问题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一些结论明显是建立在史实不清、史料错误的基础之上。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们的史料意识不断增强,回到文学发生的现场,回到作家创作的场域成为研究者们的共识。如何回到现场呢?最主要的途径便是借助于“史料”。毫无疑问,图书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最集中的场所,因此到图书馆查阅相关“史料”便成为了常态。但是,现代名人故居博物馆却成了被研究者所遗忘的角落。现代名人故居都是以名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作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因其长年在内居住,因此遗留下了很多有形的历史资料。这些历史资料往往是图书馆中难以见到的。比如,《郭沫若少年诗稿》《樱花书简》等郭沫若少年时期创作资料汇编,这些“郭沫若出川前的诗文、联语多录写在乐山和成都读书的作业本上,一直留存在乐山沙湾”*郭平英、秦川:《敝帚集与游学家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61页。。编者正是在郭沫若少年时期曾经生活过的旧居留存资料的基础上整理而成。再如对郭沫若题画诗研究、郭沫若书法作品研究、郭沫若书信研究等方面的资料大多数都留存在其纪念馆或旧居之中。因此,现代名人故居中留存着大量的可供开发的研究资源。
相对于有形资料来讲,无形资料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化作用更是其他任何机构都无法替代的。无形资料包括居住和生活的环境、居所的陈设等方面。生活的环境是影响作家创作的最直接因素。环境变化,作家创作的风格以及由此反映的创作心态必然会随之发生变化。如在郭沫若研究中有关其后期的研究一直是个薄弱的环节,这其中既有社会认识的原因,也有资料缺乏的因素,另外还有研究方法的问题。研究者们多将关注的视角集中在建国后郭沫若的行为阐述、作品解读等方面,而对于导致其心态行为产生重要作用的居所变更因素几乎无人提及。对于郭沫若后期的研究,如果我们能够从其晚年的居所,也就是现在辟为郭沫若纪念馆的北京市西城区前海西街18号入手进行考察,是不是能有新的收获呢?郭沫若的晚年特别是在1963年以后创作锐减,仅仅只是完成了《李白与杜甫》《出土文物二三事》等考古学论著,《兰亭序》真伪的论辩等文章,而《东风第一枝》和平生最后一部译作《英诗译稿》,则都是在其去世之后才得以问世的。回顾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可以发现无论数量还是质量,显然无法与之前任何一个阶段相比。而且,1963年以后郭沫若的作品更集中于历史与考古研究领域,需要激情与灵感的文学创作略显单薄,且作品社会反响褒贬不一,那个作为诗人的郭沫若不复存在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对于自己这一时期的写作状态,郭沫若是有清醒认知的。他在1962年7月3日致徐迟的信中写道:“旅行是很好的事,我一在外旅行,便可以有些创作,一停顿在京里,就像化了石一样……”在此,郭沫若的话并不是自谦,而是陈述了某种现实。走进郭沫若纪念馆你就会发现,这所院落虽然宽敞精致,但是真正属于郭沫若个人,可以进行思考和活动的空间却寥寥无几,甚至有些小得可怜。现在按照郭沫若生前的原貌保存下来的原状展厅,便清晰地印证了这一点。透过展厅的玻璃窗,你会发现会客室、办公室兼书房、卧室被分隔得清晰明确。在这明晰的分隔中,郭沫若个人的空间其实已经被压缩得所剩无几了。从空间的维度上来看,从会客室到办公室兼书房再到卧室的面积空间是逐步缩小的。单就完全属于个人空间的卧室来讲,这里的布置相对于前两者来讲已经十分简朴,甚至朴素得不能再朴素了。一张棕床、一张单人沙发、一套衣柜,一整套带木盒的《二十四史》,仅这几件简单的物品就已经让本来狭小的卧室显得更加局促了。在这里唯一能够体现出郭沫若个人性情的便是那套《二十四史》。我们可以想象到,每当处理完各种繁杂的政务和公文后,一天归于平静的时候,郭沫若自己一人安静躺在床上顺手拿起《二十四史》中的一本认真研读的场景,再无喧嚣的吵闹,再无无绪的争斗,更多地恢复到了自我沉思的空间,但这属于自我的空间又是那么狭小和局促。
相对于个人空间的狭小,作为会客室和办公室的公共空间却是非常宽大。这个会客厅是郭沫若用来会见重要客人的场所,面积大约有卧室面积的三倍还要大些。因为郭沫若建国后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等重要职务,所以他要经常会见来自各方的不同客人。马蹄型摆设的沙发占据了这间会客厅绝大多数的空间,靠墙角摆放着钢琴。前面的单人沙发是郭沫若接待友人时习惯的坐椅,最尊贵的客人在他左手的位置上。沙发后面的墙壁上,悬挂的是傅抱石专为郭沫若“量墙定作”的巨幅山水画《拟九龙渊诗意》,描绘的是郭沫若笔下朝鲜金刚山九龙渊美景。总之,会客厅中摆设的物品都追求着“大”的原则。细看一下,这里所有的摆设和陈列其实与其他人的会客厅别无二致,更多的是为了待客之道,属于自己的空间几乎没有。
在客厅和卧室之间,略显奢侈的大房间就是郭沫若的书房了,更确切地说是他的办公室。屋内西侧一排高大的书柜倚墙而立,满满排列其上的中外文书籍暗示了他贯通古今中西的学识。书房窗台上满布的一堆堆科学院科学考察报告、国情社会调查资料、待批阅的各类文件,诉说着他公务的繁忙。在这里,一切都被程式化和凝固化了。就是像书房这样一个私人创作的领域,也是向客人们敞开的,已经部分公众化了,在这种情况下私人的话语如何出现呢?所以,我们在他人生最后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中看到,占很大比重的反而是伴随旅行而生的纪游诗作。可以说,只有当他走出这程式化的办公室时才能获得往昔泉涌般的写作灵感。
由此可见,名人故居博物馆不仅可以为现代文学提供有形的文物史料,还可以展示创作者们的生存环境和空间,为研究者们打开一扇新的研究之门。
所谓反哺,就是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可以为名人故居博物馆的建设输送学理性的成果,以提升广大受众的认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目的究竟何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明确“文学充当人际交往的特殊话语,必将有助于一个社会或语言共同体的成员达到对客观事物的共同理解,建立大家认同一致的伦理规范,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强化情感与审美的交流”*童庆炳:《文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38页。的理念。文学研究除了要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正本清源的学理阐释,寻找到研究对象最科学合理的存在意义之外,如何利用研究所得到的成果服务现实也应该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况且文学研究一直也在践行着这一功能。比如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修订、再版与重印的现象,便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推动的结果。从20世纪80年代在高校中普遍授课所采用的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到现在每个大学里基本上都有自己所编写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这些文学史教材不断丰富的内容、修订的结论、变化的体例,基本都是源于相关研究的深化。
但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现实服务功能,除了在高校中作为授课的教材之外,其余的方面表现甚微,这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名人故居博物馆建设和发展的理论提升和现实指导不足。首先从博物馆的功能定位来讲,名人故居博物馆具有辅助教育功能,已经成为学校教育之外的第二课堂。另外,参观观众广泛,有普通民众,有专业人士,甚至还有外国友人等,而名人故居博物馆就是利用其馆藏物品,向来参观的观众全面介绍该名人的人生经历、主要成就,甚至是历史价值。那么,如何向观众进行说明进而达到教育的目的呢?展品的说明条就是主要的形式。这看似简单的说明条的写作却并非简单,因为它不仅要求用最凝练的字句概括出所要说明事物的特征、价值等方面的内容,而且还要具有科学性和准确性。一些基本的史实,如名人出生的时间、地点等方面的内容是固定不变的,这些可以延续下来,但是对于这个人的历史评价、这个人创作作品的意义和美学价值等方面的内容则要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而有所变化,这就需要及时进行更新。如本文前面所引述的童庆炳对于郭沫若纪念馆中有关《蔡文姬》展品说明条问题的质疑,其实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名人博物馆建设之间隔离的例证。如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能够把最新的研究成果运用到名人博物馆的建设中来,必将会对引领观众的认知、扩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影响力起到重要作用。
其次从名人故居博物馆的信息功能定位来讲,名人故居博物馆具有信息聚集中心的功能。比如,在中国大陆境内一共有三个有关郭沫若的纪念馆,分别是北京郭沫若纪念馆、乐山沙湾郭沫若旧居、重庆沙坪坝郭沫若纪念馆。这些纪念馆的存在,主要的原因就是它们都承载了有关郭沫若的重要的文化信息。但是,如何将这些文化信息科学地展现给观众呢?这就需要一个去伪存真的筛选过程,而这个筛选的过程就是要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对现存的物品和信息进行真伪辨别,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保存和归类。北京郭沫若纪念馆这些年来一直致力于郭沫若各种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努力打造成为全国乃至世界郭沫若研究资料的中心。这些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就是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如郭沫若翻译作品版本书的收集和整理,就需要大量有关版本书的研究成果资料。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有本署名为郭沫若译的《黄金似的童年》的翻译作品,经过最新的研究成果确认,此书为假托郭沫若译的伪书。对于这本书,我们当然不能作为郭沫若翻译作品的版本收集起来。由此可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于名人故居博物馆的反哺和建设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名人博物馆建设之间所谓的填充与反哺的关系,其实也是一体两面的事物,两者应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存在。通过名人故居博物馆对现代文学研究资料的“填充”,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对名人故居博物馆发展的“反哺”作用,它们能相得益彰,互相促进。
三、研究这个问题的学理和现实意义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名人故居博物馆建设之间关系的意义,应该从学理和现实两个层面上加以说明。
首先从学理层面上来讲,加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名人故居博物馆之间的关联,可以弥补两者在各自领域发展中的不足,同时也可以促进两者文化内涵的深化和提升。
其次,就文学研究来讲,我们不缺乏利用西方各种理论知识对所研究对象进行学理分析,但是缺乏研究对象的丰富资料。作为研究对象生存过的住所,包括由此住所开辟出的名人博物馆中所收藏的大量创作的手稿、出版的各类版本书、作家藏书,以及对这些博物馆环境的考察和梳理,都应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必不可少的部分。这些对外开放的名人故居博物馆承担着对社会公众教育的重要职责,对此进行文学作品传播学方面的研究,也是实践大众教育功能的一种非常有效的途径。比如,目前有关郭沫若的文学研究中,有关文学创作方法、创作理论以及作品特色等方面已经有了很丰富的成果,但是,有关生存环境对郭沫若创作特色的影响以及创作道路的选择等方面的研究却比较缺乏。而北京郭沫若纪念馆便会帮助解决这一问题,因为经过博物馆工作人员的辛苦工作,郭沫若生前所居住过的环境,甚至是物品的陈列都被非常好地保存下来了,这为相关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实物资料,同时也为郭沫若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
就名人故居博物馆的建设来讲,应充分利用研究界的最新成果更新展览的内容和说明,以最快的速度反哺给公众,会使公众教育能够最大限度地与相关研究成果保持同步性。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名人故居博物馆在研究方面的力量比较薄弱。但是,名人故居博物馆有其存在的特殊性,相较于一般古建类或综合类的博物馆来讲,它主要通过对人物的史事和贡献进行展览和介绍,以达到观众认识和了解的目的。这对于此类博物馆的文化内涵要求更高,特别是对于史事的介绍更要做到清晰准确。但是,名人故居类型的博物馆因受隶属关系和编制体系的影响,造成了科研力量的相对薄弱,这便迫切需要引入外来的科研成果为其服务。比如,北京郭沫若纪念馆中,有关郭沫若相关生平和创作的介绍大多是简单文字的概述,少学理性的解析,很难满足不同层次观众对展览内容的了解需要。如果能够从多层面全方位对其进行解读,应该会收到更好的效果;也可以邀请相关的郭沫若研究专家定期进行专题讲座或是普及教育,这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推助名人故居博物馆发展的有效途径。
再次,从现实意义层面上来讲,明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名人故居博物馆之间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完善两者服务社会的功能。
教育功能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是名人故居作为博物馆的基本特性之一,还是它们两者的交汇点。文学研究绝不仅仅只是学院派的事情,更多的还是要服务于大众,“净化人的心灵,提高人的艺术感受力和审美判断力,激发人的想象力,增强人的创造性和创造欲望”*王长华、阎福玲:《从文学教育的功能与特点看文学课教学改革》,《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年第10期。。就所关注的本体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关注作家作品的方向和名人故居博物馆的建构目标指向是基本一致的,只不过是所呈现的方式不同而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更多的是通过文字的分析和论述去阐释所关注的对象,而名人故居博物馆更多的则是通过图片和实物的方式去展现某一对象。由此可见,两者关注主体的方式不同,但是目的却基本上是相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为了通过对所研究对象的理论阐释,从更高意义上概括出其意义和价值,而名人故居博物馆则是通过展览展示的手段去总结其业绩和贡献。两者最终的目的都是通过各自的方式去引导受众认识历史,提升自我,从而完善社会服务的功能。
中国为现代文学研究和名人故居博物馆虽然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范畴,但是二者之间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如果能够将两者更好地结合起来,那么必将会迎来彼此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实现殊途同归的目的。
责任编辑:李宗刚
An Unitary Probe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and the Celebrity Museums:With the Study of Guo Moruo As an Example
Zhang Yong
(Guo Memorial,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Beijing,100009)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Museums of Modern Celebrities have been progressing independently in a state of isolation due to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reasons. In essence, the Museum of Modern Celebrities can provide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modern literature research can provide items for exhibition in the Museum of Modern Celebrities. They can be the supplement for each other. Either judged by theoretical reasons, or from pragmatic views,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are of great value and significance.
literary studies; museum; Guo Moruo
2016-04-20
张勇(1976—),男,山东枣庄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副研究员,博士。
I206.6
A
1001-5973(2016)03-003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