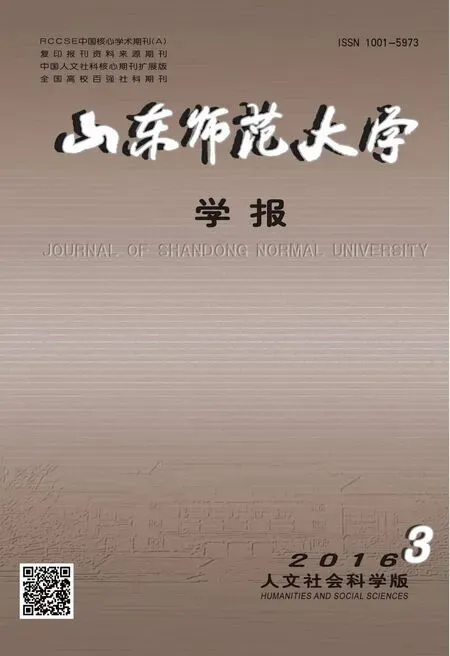论“文学是情学”*
殷国明
(华东师范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上海,200241)
论“文学是情学”*
殷国明
(华东师范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上海,200241)
“文学是情学”提供了探求文学与人、与人生和人性之间隐秘关系的通幽小径。情最贴近人类生命本原,直接源自于人类的本能和原始欲望状态,也最能反映潜藏在人们潜意识中的能量和能力,激发人们的想象和创造力。情之回归,不单是对于压制和束缚人性的各种传统制度与观念的挑战,也是文学回归人性、回归大众、尤其是回归人类日常生活之路。“情学”也许不仅仅是一个文学问题,而人类对于情的认识,也不仅仅止于对文学艺术的探讨,实际上这是一个重新反思人类精神史和思想史,继而更加深入认识人类自我的时机和转折点。
文学是“情学”;人学;心学;情理相通;红楼梦;焦循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6.03.001
文学作为人类生活的整体反映和表现,更作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原本包含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层面,其中不仅有历史、哲学、伦理和道德,也涉及人类理性、思想、感情、感觉等内容。所以,文学不仅是人学,也可以是“心学”、美学和感性学,文学研究更是可以从历史、政治、经济、哲学及思想和道德等各个方面进行,从文学中获取启示。不过,从文学本身来说,从各个不同角度和层面来理解和研究,确实能够促进对于文学的认识,甚至丰富文学的想象和建构,带来文学自身的突破和创新,但是如果过度强调和阐释,也会消解、甚至取消文学自身赖以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更难以真切体验和触及文学之所以魅力长存的缘由。
正是在这种疑虑和困惑中,“文学是情学”开始引人注目,人们试图在种种人类学说和精神构成中找到文学的根脉,在“人学”的框架和语境中更深一步,进入人类尚未能够完全把握和认知的领域,探求文学与人、与人生和人性之间的隐秘关系。这或许不能称之为一种“学”,但确实是一条探寻和理解文学存在和价值之秘境的通幽小径,值得人们穿越附加在文学身上的种种外在理论和观念,回到文学本身,细读、细看和细解文学的奥秘。
一、“情学”:并不突兀的命题
从历史渊源来说,“文学是情学”之义源远流长,早就有人不断提及和论述,但是作为一个命题明确提出者,则要感谢王世德先生。1989年,王世德*王世德(1930—),当代美学家、文艺评论家,编著出版中国大陆第一部《美学辞典》,出版《文艺美学论集》《苏轼文艺美学思想研究》《美的欣赏与欣赏》等多部文集和专著。在《探索》第2期发表《探析“文学是情学”》一文,开宗明义提出“情学”命题,并在文中指出:
既然文艺要动人以情,要使观赏者激引起美感,那么它怎么可能不表现感情呢?不表现感情,不充满感情,就不可能动人以情;要起给人美感的作用,就必须具有审美感情这一本质特征。*王世德:《探析“文学是情学”》,《探索》1988年第2期。
他还如此解说了“人学”与“情学”的关系:
人们常说文学是人学,其特指意义是文学要写人,写人的情感,这主要是指作者的情感。为了表现作者的情感,就要派生出着力表现作品中人物的情感,在叙事文艺作品中就要着力写人的命运。……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学是人的情感,是情学,是表现人情的审美对象。中外文艺反映的生活原型可以变形,但仍感动人心者,靠的就是其中充满人们相通的情理,情的背后有理。如果违背了人间情理,即使反映生活形貌毫厘不差,真实到极点,也只是假象,也不可能感动人。*王世德:《探析“文学是情学”》,《探索》1988年第2期。
如果在这里论者不突然求助于“理”(“情的背后是理”),那么,关于“情学”一说几乎要落地生根了。尽管如此,王世德的观点依然给人一种顿开茅塞之感。而他在文中对于“文学激起审美情感的四个层面”的分析和论述,对“文学是情学”的阐释更有独到之处。
当时,中国新时期思想解放处于高潮阶段,文学不仅迎来了艺术思潮和流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且也触动了人们的历史文化心理,在情感深处掀起了波澜。“文学是情学”命题的提出,还昭示了中国文化变革这样一个事实,即汹涌澎湃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背后,必然涌动着蓄势待发的情感要求,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是相互激发和促进的。而就一场有效的、能够持久的思想解放运动来说,必然要有情感、甚至激情作为基础,作为一种被长期压抑的情感喷发,也无不期待思想和理论的支撑与正名。
这种情形也为“情”在文学理论和批评领域再次崛起提供了时机和语境。例如,朱德发*朱德发(1934—),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著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五四文学新论》《主体思维与文学史观》等专著。就在梳理和研究中国情爱文学基础时,提出了“爱情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的看法。他指出:
情爱之所以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在文学领域具有如此不可取代的地位,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却是它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它不仅与个体人生密不可分,而且在整个人类生活中也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从特定意义上讲,毁灭了情爱就意味着毁灭了人类。文学是人类生存方式和自由意志的表现,当然它要主动地密切关注着人类情爱生活或性爱意识的发展与变化。*朱德发、谭贻楚、张清华:《爱河溯舟——中国情爱文学史论》,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2页。
当然,关于“文学是情学”观念的来源,还可以追溯得更早。*殷国明:《“情学”:文学探寻的归根之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例如,清人焦循就认为:“诗本于情”,他在论及“诗何以必弦诵”时还如此说到“情”之重要意义:“诗何以必弦诵,可见不能弦诵者,即非诗也。何以能弦诵?我以情发之,而又不尽发之,第长言永叹,手舞足蹈。若有不能己于言,又有言之不能尽者,非弦而诵之,不足以通其志而达其情也。”*焦循:《与欧阳制美论诗书》,王云五编:《雕菰集》卷十四,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1936年,第235页。由此,他对于写诗提出了如下要求:
诗本于情,止于礼义。被于管弦。能动荡人之血气,故有市井之心,不可以为诗;有轩冕之心,不可以为诗;有媢嫉之心,不可以为诗;有骄肆之心,不可以为诗;有寒俭狭小之心,不可以为诗;有偏颇怪癖之心,不可以为诗;有矜能斗胜之心,不可以为诗;有雷同剿袭之心,不可以为诗;有妇人女子之心,不可以为诗;是故议论非诗也;谩骂非诗也;谄谀非诗也;俳优非诗也;非不说理,拘于理者,非诗也;非不隶事,滞于事者,非诗也;非不写景,饰其景者,非诗也;非不考古,泥于古者,非诗也。总之,未作诗之先,意中必有所不可已之处,始而性情所鼓,盈天地间皆吾意之所充,若千万言写之而不足者,迟之又久,神渐敛,气渐翕,即而取之无有也,至于鬼神不能通其虑,风雷不能助其奋,而后郁而徐之,积而出之,引而伸之,辞不必至,性已先之,虽简亦深,虽平亦曲,虽率亦神,其文也不縟,其质也不俚,斯庶乎味者而不穷,寻之而愈有也。*焦循:《与欧阳制美论诗书》,王云五编:《雕菰集》卷十四,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36页。
在这里,说“文学是情学”的发明权属于焦循未尝不可,问题在于焦循尚不能尽情言之,仍然在传统的诗教框架内有所顾忌。不过,正是由于他发现并认定了这个“本”,所以也被吾恩师钱谷融先生引之为圭臬,并在论述《艺术的魅力》一文中进行了细致解读。钱先生认为,焦循用以下三句话来解释“诗教”是颇有见地的,即:“不质直言之而以比兴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务胜人而务感人。”实际上,这三句话都是讲情的,正如钱先生所说:“焦循这三句话,如果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当然是未必精当的,我们不能把它绝对化。但这三句话却的确抓住了文学艺术的一个根本特点,那就是‘文学艺术主要是从感情上去打动人的’。”*钱谷融:《钱谷融论文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9-180页。
钱先生还在自己的文章中写下了如此话语:
艺术作品之所以具有打动我们的力量,不正是因为在艺术形象中渗透着作者的强烈而真挚的思想感情吗?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把他从生活中得来的思想感情,凝铸到他所创造的艺术形象时,便也接触到了他的思想感情,感受到了他所经历到的激动,他所尝味的欢喜和悲哀。*钱谷融:《钱谷融论文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2-193页。
而就文学与情学密切关联来说,西方丰厚的文化资源也不容忽视。同样,在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流淌着爱情、激情和浪漫之情的琼浆玉液,以至于人们确信情是人类最古老艺术的精魂所在。这一看法,甚至在苏格拉底时代就十分流行。柏拉图在自己的《斐德罗篇》和《会饮篇》中,就记录了一场事关此后人类思想史发展的争论,其极大影响了日后文艺理论发展的方向;可惜,以往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忽略了这场讨论在文化思想史上的意义。
这场争议的命题是爱情,而焦点就是“情学”是否能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持续扮演重要角色、能否被新的艺术标准和价值观念所接收的问题。这也正是斐德罗要提出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的意味所在:
为什么所有颂神诗和赞美诗都献给其他神灵,但就是没有一个诗人愿意创作一首赞美如此古老、如此强大的爱神,这岂不是太离奇了吗?*[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2页。
显然,斐德罗的抱怨是针对当时希腊学术状态的,抱怨的对象并不是当时的诗人和戏剧家,而是新出现的一些博学的文化人,其中自然包括苏格拉底这样的哲学家。*这在下文中有明确所指,比如提到的普罗狄科写的散文,还有所列举的介绍食盐和一些日常用品用法的著作等。这也说明,在希腊时代,所谓诗的领域是广泛的。他们代表了当时希腊新的思想潮流和学派,显示出那个时代在历史建构和文化观念上的巨大转变。
二、 “情”路漫漫:在人文冲突中时隐时现
显然,这是一次早有定论的人类文化史上的一次大的转折。因为正是由于这次转折,确立了“管理国家的艺术和能力”在西方乃至人类文化和思想学术中的轴心地位,其核心价值如同中国儒家学说中的“王道”一样,就是政治与权力。就此来说,所谓哲学、艺术、道德等人文思想的设置,都不能不受到这种集体、或群体价值和意志的规范和要求,并在合乎国家管理目标的秩序中获得相应的位置和话语权。
这也是当年苏格拉底迷醉于情但又不能不怀疑情、质疑情、设置否定情的原因,也是人类思想文化在其奠基期难以避免的局限性。也许正因为如此,在传统思想体系中,文学艺术始终难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终极的价值取向,总是要依赖诸如宗教、道德、哲学等其他思想的支撑和认定,甚至连美及其美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也难免招人诟病。所以,从苏格拉底到黑格尔,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的终极价值取向一如既往,就是给艺术套上理性的枷锁,使之服从权力话语和理性逻辑的规训。这无异于为一匹充满野性活力的马套上辔头。从柏拉图的理想到黑格尔的“艺术哲学”,再到如今无处不在的争夺话语权的“政治诗学”,西方理论范式与话语似乎已经越来越脱离其生命之源,濒临“终结”的困境。
钟情于情,但是有不能不可之情、限制情、甚至否定情,这似乎是人性不能不承受的悖论和宿命,这并非意味人类没有意识到情感的价值和魅力,而是因为人类为了整体的、群体或集体的生存发展,不能不付出的人性代价。这也正是人类在宗教、哲学、道德等思想文化领域关注、构建和倡扬普遍性原则的渊薮。这种普遍性所关注的不仅是人类自我的确定性和稳定性,而且不能不对人性中过于个人化、个性化的、不稳定的因素加以防范和规避。
这无疑为情、特别是文学艺术中的“情”设置了种种限制,使其理论之路漫长。在中国,尽管自古到今不难发现一条情本主义文学观的线索,从《毛诗序》之“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易经》之“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到陆机《文赋》中的“每自属文,尤见其情”、刘勰《文心雕龙》中强调“为情而造文”,都莫不把情放在首要或重要地位来进行论述;但是说到精深细微之处,总会透出某种悲怆和苍凉之感。
例如,魏晋嵇康写了《声无哀乐论》,从哀与乐角度探讨了艺术魅力的来源,处处流露出对于情感本身的恋眷之感。下面摘录三则:
劳者歌其事,乐者舞其功。夫内有悲痛之心,则激切哀言。言比成诗,声比成音。杂而咏之,聚而听之。心动于和声,情感于苦言。嗟叹未绝,而泣涕流涟矣。夫哀心藏于苦心内,遇和声而后发;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
此为心悲者,虽谈笑鼓舞,情欢者,虽拊膺咨嗟犹不能御外形以自匿,诳察者于疑似也。
然人情不同,各师所解,则发其所怀。若言平和,哀乐正等,则无所先发,故终得躁静。若有所发,则是有主于内,不为平和也。以此言之,躁静者,声之功也;哀乐者,情之主也。不可见声有躁静之应,因谓哀乐皆由声音也。*嵇康:《声无哀乐论》,《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45-150页。
可以说,不仅在艺术创作中,而且在人生中,嵇康都是一个主情论者。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使自己置身于一种险恶的生活环境之中,成为政治、礼教压制和剿灭的对象,最后难逃厄运。
更为引人注意的是,嵇康在艺术主体(哀乐)与本体(声)关系的论说,涉及到情感美学与形式美学之间的种种界限,不仅揭示了艺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而且也为形式的艺术实现和美学意蕴提供了人学基础。这一点,直到20世纪苏珊·朗格提出“艺术是情感的形式”*[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才有比较明确的观念表达。
可见,在人类文化史上,尽管一度对于情有种种误解和防范,却不能完全禁绝它在文学创作中存在,也难以将它永远关在理论和观念大门之外。相反,由于人类各种理性学说和文化规则的打压和排斥,文学艺术似乎成了情的唯一栖息之地。人们唯有在文艺作品中才能找到自己情感的镜像,获得心灵的慰藉,在幻想和想象中获得情感的宣泄和满足。这种情景不仅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生活和生命资源,而且促使艺术理论和批评不断反省自我,突破原有的局限和框架,在艺术理论和观念上不断创新。
在中国文论上,也一直持续着这种突破和创新。例如,在诗歌创作繁茂的唐代,就形成了一种以情为本、缘事入情的诗学方法,即在解读和欣赏诗歌的过程中,务必追溯其情感的发生过程,究其来源,并视之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这方面,孟棨的《本事诗》是珍贵的典范,其卷首云:
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慨。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虽著于群书,盈厨溢阁,其间触诗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因采为本事诗,凡七题,犹四始也。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征异、征咨、嘲戏,各以其类聚之。*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页。
不难看出,在这里,以情为本不仅是一种观念,而且已经渗透到了具体文学批评活动之中,形成了自己的门类和路径。这里不妨摘录其“情感第一”中之一欣赏之:
陈太之舍人徐德言之妻,后主叔宝之妹,封乐昌公主,才色冠绝。时陈政方乱,德言知不相保,谓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国亡必入权豪之家,斯永绝矣。傥情缘未断,犹冀相见,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镜,人执其半,约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卖于都市,我当在,即以是日访之。”及陈亡,其妻果入越公杨素之家,宠嬖殊厚。德言流离辛苦,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访于都市。有苍头卖半镜者,大高其价,人皆笑之。德言引至其居,设食,具言其故,出半镜以合之,乃题诗曰:“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陈氏得诗,涕泣不食。素知之,怆然改容,即召德言,还其妻,仍厚遗之。闻者无不感叹。仍与德言陈氏偕饮,令陈氏为诗,诗曰:“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作人难。”遂与德言归江南,竟以终老。*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页。
在这里,似乎毫无理论和理念而言,却表现了“情”作为贯穿于艺术创作、传播和欣赏整个过程的意味。这或许也说明,情学才是理解和阐释文艺活动的真正钥匙,并不一定要依据纯粹理性和理论进行演绎,而是以具体的生命和生活为底蕴,洞察其人性情采,揭示其艺术真谛。通过这种对于具体的“事”之追寻和有所感悟,不仅令读者为其中闪烁的人性之光所感动和感染,而且很自然地触及到诗之本源,意识到诗意和诗情原本就来自人生,尤其是人丰富多彩的情感生活。
这似乎完全不同于西方形而上学的诗学传统理念,以情为本,以事为镜,以一种具体的、活生生的叙述方式,展示了文学的本相和魅力。显然,就情之风韵来说,中国文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追寻和呈现。如果说,《庄子》道法自然,重在追寻情之精诚,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契合中感悟人生和艺术,奠定了情学的自然之本;《世说新语》在“越名教,任自然”语境中,尽兴展示了人之性情之美,拓展了人之性情的多样性;那么,到了唐代,则迎来了一个以情论诗的新时代。在这一时期,个性的张扬、文学的自觉和情感的放浪形骸,它们互为因果,合为一体,在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方面,都留下了难以复制的精品和极品,深刻影响了中国日后文学的发展,也为中国文学中的抒情传统奠定了论说基础。
由此,如果重回西方希腊哲学现场,就不难发现,中西文艺理论在对待情的问题上,有很多相通、相近的境遇。在那场事关情学命运的讨论中,苏格拉底之所以忽略情的终极价值,继而一定要给情戴上理性的镣铐,是有其人类文化发展的内在原因的,也显示了苏格拉底在人类群体利益和智慧方面的高尚追求——因为此时的苏格拉底思考的出发点不再是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整个城邦和国家的利益,所以连他本人也不否认“我还不能做到德尔斐神谕所告诫的‘认识你自己’”*[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9页。,而只能去关注如何去做一个符合社会理想和理性规范的人——这一点与中国的孔子非常相似。在这里,如果我们希望在他们之间、甚至在中西传统哲学之间,寻找一个相通的价值和观念基础的话,那不妨借用苏格拉底说过的一句话,“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智慧是统治社会的智慧,也就是所谓的正义和中庸。”*[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52页。在讨论爱情的价值时,这段话是通过狄奥提玛之口说出的。显然,这是苏格拉底认同的。
即便如此,在这场辩论中,苏格拉底所表现出的对于情的恋恋不舍依然动人,因为情不仅是人类生命意识中最早觉醒和意识到的元素,也是人类生活中最难以忘怀的记忆,要完全回避、遮蔽和否定其意义和魅力并非易事,需要苦口婆心的文化建构。或许这是连苏格拉底也感到棘手的问题。所以,在进入辩论场所之前,他就表现得十分犹豫,在外面徘徊了很久,迟迟不愿、也许不敢面对众多的对手;而进入辩论之后,他开始也是含糊其辞,并且不是正面迎辩,而是采取了借他人之口的方式来申述自己的观点。好在后来记述这场辩论的是他的学生柏拉图(这一点与《论语》的成书过程颇为相似),所以最终自然把最后的胜算归于苏格拉底。
也许在此时,我们突然会对王国维当年对西方哲学生厌有新的感悟。所谓“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说的正是哲学和艺术的关系。哲学因为依仗的是理性和逻辑,面面俱到,但是未必能给人带来心灵的慰藉;艺术是以情动人,尽管不足以以理服人,但是会令人流连忘返。从《红楼梦评论》到《人间词话》,也正反映了王国维从“可信”的西方哲学,折返回“可爱”的中国文学的心路历程。
这种艺术与哲学、情与理之间的矛盾,也曾给苏格拉底带来过困惑。作为一个经常借助神灵立言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在关键时刻甚至也会忽略神话的意义,申言“只要我还处于对自己无知的状态,要去研究那些不相关的事情那就太可笑了”。同时,对于自己的知识和价值取向,他已经表现出了远离自然的倾向。当斐德罗把他带到城外一棵茂密的梧桐树下的时候,他马上说:“你必须原谅我,亲爱的朋友,我爱好学习,树木和旧园不会教我任何事情,而城里的人可以教我。但你好像发现了一种魔法,能吸引我出城。”*[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0页。
尽管如此,柏拉图还是记下了苏格拉底很多值得后人铭记和回味的名言。例如:
爱本身如此神圣,使得一名诗人可以用诗歌之火照亮其他人的灵魂。无论我们以前对做诗有多么外行,但只要我们处于爱情之中,那么每个人都是诗人。*[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5页。
三、“情学”:如何冲破二元对立结构的限定
显然,尽管在文学创作中情之作用几乎可以视为一种常识,但是作为一种理论命题、或者作为一种学说,却不能不面对种种质疑和挑战。例如,何以从人类文学史乃至精神文化史中,寻求和获取其历史和美学的根基和内涵?如何应对来自既定的、传统的理论范式和思维方式的质疑和挑战?其原因不仅来自情自身的特质和人性状态,而且还出自人类自古以来所建构的人文和理论状态和框架。就文艺理论而言,通过数千年的文化建构,已经形成了自己既定的理性规范和思维方式,其以哲学之思和道德之辩为思想经纬,以相关的知识谱系和概念系统为支撑,各种观念、范畴和范式自有定数,秩序井然,加上近代以来的学院派的专业化、学科化的精致打造,俨然是一座话语等级森严、论说逻辑严谨的精神城堡。由于情一开始就被视为神性、理性和德性的对立面,被排除在思想理论的边缘,所以很难改变自己在整个文化和意识形态格局中的地位,因此也很难在理论上获得自己的话语权——除非人类文化体系和思维方式发生颠覆性的重大变局,人类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重构自己的精神家园。
所以,在人类文化和精神史上,尽管情不可或缺、甚至有时会咄咄逼人,不时向人类既定的道德规范和理论体系发出挑战,但依然不能被视为一种“学”,有自己独立存在的精神领地。
当然,反过来说,情在文学中不可或缺,是艺术活动中的灵魂所在,也并不意味着情拥有一切,决定一切,占据无可争辩的强势地位。相反,正因为情在文化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一直难以与强势的理性规则和道德话语相抗衡,才更贴近和靠近文学世界,在艺术的广阔天地获得庇护。人类的情感体验和记忆,或许唯独只有通过艺术创作才得以保管和留存。
这也是人类至今最感人至深的艺术作品多半是悲剧的缘由之一。就“文学是情学”的命题,也并非意味着文学中只有情,或者情在文学创作中能够统治一切,决定一切。恰恰相反,情一直被排除在理和理性世界之外,甚至不断被各种各样其他理论学说打上“兽性”、“非理性”、“不健康”等烙印,因而使之一直处于文化争夺、争论和争议的涡流之中,或者说,被卷入到了意识形态和话语权的博弈之中,不断被打上各种标签,唯独没有自己发声的机会。
这种被标签、被定义、被作为对立面的现象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即便是对情有所偏爱也难免此劫。例如,《文心雕龙》中就突显了“情与理”相互角力的情景。刘勰一方面不断呈现情在文学中的张力和魅力,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情动而言形”、“莫不因情立体”,认为“故情者文之经”;另一方面,又担忧“情数诡杂”,不断强调“理之纬”的作用。为此,他甚至在《神思》篇中,把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艺术想象也归结于“思理之致”,以“思理为妙,神通物游”为结。*张光年:《骈体语译文心雕龙》,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57页。
这种情与理的冲突和张力,一直贯穿于中国文学理论和创作中。显然,在这种二元对立的结构之中,情与理的地位和状态既不平等也不匹配,而是存在着强与弱、乾与坤、天与地、阴与阳之间的差别。情犹如无家可归的流浪儿,既没有自己的主体性,也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而理则处于精神引领的主体地位,体现着绝对理念和终极价值的一端。正是在这种整体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语境中,情与理的关系失衡了,情不能不受到理、理性的制约,在理与法的规范中寄人篱下,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中显得弱势和孤立无援;而理则能够借助政治、历史、哲学、宗教等各种资源和方式,对脾性古怪的情进行引导、矫正和约束,使之能够在既定的社会制度框架中安分守己,或者在合乎政治、权力、经济和意识形态需求和利益前提下发挥作用。
情理原本是相通的。有情、顺情和尊重情,才能“达理”;而“理”能够站住脚,服人心,也只有建立在通人性、知人情的基础之上。由于种种原因,人类社会会出现种种情理不通的状况。人们或迫于某种利害关系,或由于某种文化规范的要求,不能不压制内心的要求,不能随情所愿,反而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而正是在这种时候,社会往往就会滋生文化变革的要求,出现思想解放思潮。
可见,情理之间的对峙,也是一种文化建构的结果,并非文学艺术本身的情之所愿。而很多艺术家的创作,在很多充满情感表达的文艺作品中,最终所想达到的就是情之理,或者为天下之情争一份“理”。
其实,即便在最为激动人心的艺术创作中,情也不能完全离开理。或者说,情与理也不可能完全分离。单就艺术思维活动,或者就人的心理世界而言,情也只是其中一种要素,一个环节,而且在人类现实活动中,很可能是最脆弱、最无力的要素和环节。刘勰对于“立文之本源”的论说,不能不说更为接近艺术文学创作活动的整体状态:“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刘勰:《文心雕龙》之“情采”篇,张光年:《骈体语译文心雕龙》,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58页。而所谓“情学”所面对的问题是:何以在文学理论中,一定要设置这种情与理二元对立的结构?这种对立的二元结构是否真正反映了艺术创作的内在张力?
所谓“文学是情学”,并不是要否定文学中有“理”,甚至讨论“情”与“理”的关系如何,而是要打破情与理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在一个情、欲、道、理等多种因素并存的文学世界中,找寻被理、理性和理论压抑已久的人性元素,使情拥有自己的主体性。
就此而言,情,尽管最贴近人类生命本原,直接源自于人类的本能和原始欲望状态,也最能反映潜藏在人们潜意识中的能量和能力,激发人们的想象和创造力,但是,由此也注定其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受到种种自然和现实生活的限制,甚至受到压制和压抑,难以得到完全和完整的自我实现。这种实现往往只有通过特定对象化、形式化的途径和方式呈现和展演——而这正是人类文明规范和人文精神源起的张力和悖论所在。文明和文化,一方面会为人类欲望和情感的实现和宣泄提供日新月异的途径和空间,同时又会不断以现实的方式规范它,驯化它,试图把它关在标准、制度、纪律和观念的笼子里。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以情动于中”的文学,自然不仅会最先感受到情之驱动力和生命魅力,而且也是最敏感于“笼子”的约束、最早试图冲破“笼子”的人类活动。
“理”作为人类建构的精神支柱,其文化境遇、待遇和遭遇自然与“情”不同。在人类心理世界和思维活动中,理或许是人类文明规范和规则的体现之一。尤其在中国,理不仅有西方文化中“逻辑”之意,而且拥有合乎道理、规则、制度和权力的近乎天人合一的话语权。因为它是中国古老“礼文化”的抽象化和观念化升华,集理性、理智、逻辑和道德规范于一身,贯穿于人文历史的各个领域和环节,自然也成为拥有权力意志和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因素和环节。所以,即便在文学中的理,也是一种更具有广延性和普泛性的观念存在,其不可避免体现着整个文化和意识形态、甚至政治和权力话语的意志,对于情及其存在状态实施监督、规范、修改和统制功能,尽力使个性的、自由的、灵性的文学,为社会的、规范的、集群的功利目的所用。
因此,与“人”一样,理不仅不孤独,会出现在不同的文化领域,诸如宗教、历史、哲学、逻辑、伦理、社会学等,甚至表现在物理、化学、数学等各个自然科学领域,而且一直被尊崇为人文和科学研究中最不可动摇的品质和原则,被认为是达到真理彼岸的最可靠的船舰。这在精神文化领域也从来如此。例如,就西方基督教而言,“信仰上帝以及知晓他是纯理性的事情,理性不仅不会与信仰有任何的冲突,而且还会为它提供支持”*[美]所罗门:《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张卜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9页。;而对于中国传统道德伦理来说,道德就是一种“理”,只有遵循“理”才能到达至善的境界。而唯独在文学艺术领域,理遇到了自己难以完全征服的对象。也许在人的生命诸种元素中,犹如其中最顽皮、最不愿被驯化和控制的孩子,最容易惹祸生非,也总是冲破和破坏社会既定的文明规范和社会规则,所以会招致更多的理的警告的规训,甚至加强理和理性在文学活动中的建构。而在中国,知识理性和宗教理性薄弱,道德理性对于文学的制约和管控就显得格外突出。
无需论证,人生和人性本身就充满冲突和困惑。尽管为了重获平衡和解惑,人类创造和建构了很多理论和学说,但还是无法满足人们对于情感的向往和迷恋,无时不感受到情感力量的执着和强大。它们时而如万马奔腾,时而使人感到万箭穿心,使人喜,使人忧,使人兴高采烈,使人无法入眠。情到深处、烈处、绵延不断处,人们可以放弃一切世俗偏见,冲破所有既定的现实规范和规则。这时候,任何学说、理论和道理,尽管宏大深刻,面面俱到,似乎也失去了效力,也显得苍白,唯独在艺术作品中方能得到一些共鸣和慰藉。而情学将会在这种人类日益增长的寻求中获得自己的丰华和新生。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周文波作了许多工作,特此感谢)
责任编辑:李宗刚
Literature As a Study on Emotion
Yin Guom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s literature may be interpreted and studied from different angles and on different levels itself, it therefore provides a curved path for exploring the secret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man, literature and life, and literature and human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as a study on emotion”. For, emotion is closest to the life origin of man, and is directly derived from human instinct and, the state of man’s original desire, whereas it reflects most fully the energy and ability hidden in people’s subconsciousness, thus stimulating man’s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The return of emotion is therefore not only a challenge to the various traditional systems and concepts, but a path for literature to return to human nature and to the masses, especially to the everyday life of man as well. Consequently, the “study of emotion” is not merely an issue in literature, and man’s understanding of emotion, too, is not merely an explo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s, for, as a matter of fact, it is the very opportunity and turning-point to introspect once more the history of human spirit and thought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more deeply man himself.
literature as a study on emotion; anthropology; psychology; emotion and reason;ADreamOftheRedMansions; Jiao Xun
2016-05-04
殷国明(1956—),男,江苏常州人,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I02-02
A
1001-5973(2016)03-00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