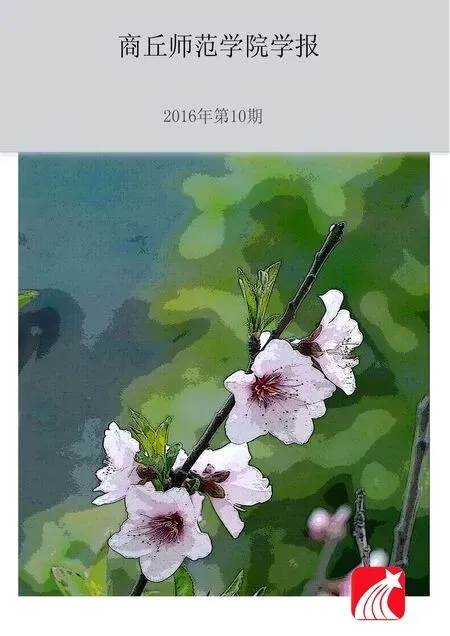论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物质利益思想
杨 植 迪
(南开大学 哲学院,天津 300350)
论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物质利益思想
杨 植 迪
(南开大学 哲学院,天津 300350)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遇到的物质利益问题是他世界观发生转变的重要契机。在这一时期,通过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他看到了不同等级之间存在的物质利益冲突;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使他发现了法的私人利益本质;对摩泽尔地区贫困问题的研究,使他认识到了官僚机构和市民的利益对立。利益对国家和法的支配,使马克思认识到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马克思对于物质利益问题的研究,使他开始告别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并逐步走向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莱茵报》;物质利益问题;私人利益
《莱茵报》时期是马克思的世界观发生根本性改变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开始以一个民主革命者的身份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投身到政治斗争中,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为一无所有者的利益诉求辩护。马克思通过研究莱茵省议会关于新闻出版自由、林木盗窃法和摩泽尔地区贫困问题的几场辩论,发现了隐藏在等级制、法以及官僚机构背后的物质利益问题。普鲁士当局对特权阶级利益的维护,使马克思开始怀疑国家和法是否是理性的体现。
一、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不同等级之间的物质利益冲突
普鲁士政府在1841年出台的新的书报检查令,以看似自由的伪装更大程度上限制了出版自由。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新书报检查令中“自由”的虚伪性。普鲁士政府把限制人民自由的专制要求上升为国家法令,以国家特权维护其特殊利益。而在莱茵省议会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中,不同等级因其背后的物质利益关系而支持或反对书报检查制度。马克思明确地指出:“辩论向我们显示出诸侯等级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论战、骑士等级的论战、城市等级的论战,所以,在这里进行论战的不是个人,而是等级”[1]146。不同等级之间物质利益的冲突,导致他们对新闻出版自由的意见不同。各个等级的辩护人不是为了自由本身去辩论,而是为了各自等级背后物质利益的多少而讨价还价。论战的核心议题不是自由而是利益,论战本身也体现着各个等级的利益对立。“一部分人由于特殊等级的狭隘性而反对新闻出版,另一部分人则由于同样的狭隘性为新闻出版辩护。一部分人希望特权只归政府,另一部分人则希望把特权分给若干个人”[1]198。马克思有力地批判了普鲁士政府颠倒是非,将维护自身私利、反对人类自由本性的书报检查令标榜为“普遍自由”,讽刺了贵族诸侯和骑士阶层为了维护各自的等级特权而支持书报检查制度的狭隘性,驳斥了市民阶层将新闻出版自由归为行业自由的商业领域的片面性,赞扬了农民阶层勇敢智慧地维护新闻出版自由。
“新闻出版有按照自身规律发展的权利,既不能用官方检查令来束缚它,使之依附于国家政治权力,也不能把它划归到行业自由的经济领域,使之卷入商业投机中去。新闻出版有权成为一个不受任何外在力量控制和干预的相对独立的领域,按照人类精神的自由原则健康发展。”[2]出版自由体现着人民精神,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理应作为普遍自由。但是,在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中,人民的公共利益被排斥在议会之外,不同议员代表或因缺乏对自由的现实理解,或因维护阶层利益而认可普鲁士政府将出版自由归为特殊自由。马克思指出,自由的特殊存在是特殊领域内的一般问题。如果自由的某一种形式被否定,那么整个自由都会被怀疑,一旦接受不了自由的形式,那么自由就形同虚设同。自由终归是自由,它是人的本质和本性的体现,是人的全部精神的类本质。马克思认为,新闻出版自由是人类其他自由的基础,因为“新闻出版是个人表达其精神存在的最普遍的方式,它不知道尊重个人,它只知道尊重理性”[1]196。新闻出版自由是人类自由的真正实现,人们通过报刊杂志表达看法,而自由报刊的人民性就在于它是人们自我认识、自我教育的“镜子”。 马克思指出,报刊是历史的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开形式,各个国家的人民都在报刊中表现自己的精神。“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自由报刊是国家精神”[1]179。因此,新闻出版应是不受外在力量干预控制的领域,它应该服从于人的自由精神。马克思批判各个等级代表因其背后的物质利益纠纷而对新闻出版自由讨价还价,他呼吁把出版自由问题回归到自由本身看待。这也显示出在这个阶段马克思对物质利益问题还不够重视。
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中,马克思认识到各个等级关于出版自由的不同意见源自他们背后的物质利益冲突。虽然他此时仍受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影响,将理性和精神看做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从精神自由的角度维护出版自由。但是,他已经看到了物质利益的差别使社会划分成不同的等级,而不同的等级地位决定了不同的思想和行为。各个等级间围绕着各自的利益取向而展开斗争,“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187。物质利益甚至支配着国家机构和立法机关的决策。这也促使马克思开始思考物质利益问题同国家和法律的关系。
二、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法的私人利益本质
由于受到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的影响,青年时代的马克思一直将国家和法视做捍卫人民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正义和理性的化身。然而在现实中,他发现国家和法常常受到私人利益的支配。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林木所有者无所不用其极地维护自身利益,企图将穷人拾捡枯树枝的行为以“盗窃林木”论处,从而彻底断绝穷人的生路。省议会为了保护林木所有者的私人利益,通过了这一法案,把拾捡枯树枝判作林木盗窃,要求捡拾枯树枝者除赔偿林木占有者的林木价值以外,并处以4倍、6倍乃至8倍的罚款。法令甚至还规定,将违反森林管理条例者交由林木所有者论处,强迫违反条例者为林木所有者劳动。这种剥削规定使法律变成对付贫民的手段,法彻底沦为为私人利益服务的工具。
马克思站在底层人民的立场上,撰文抨击了省议会不顾国家和法的理性原则,肆意维护林木所有者私人利益的行为。在省议会的辩论中,贵族阶层的代表以中世纪的“习惯法”为例来论证林木盗窃法的合理性。马克思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贵族的习惯法是将贵族的特权变为法,是“习惯的不法行为”,是“法的动物形式”,因为它是同法律的通用性和必然性的形式相矛盾的。贫民在森林里捡拾枯树枝是一直以来自然界赋予的权利,这与林木盗窃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林木所有者所占有的是生长的树木,而从树木身上落下的枯枝已经不属于活树。省议会将与活树没有关系的枯树枝判为林木所有者的财产,显然是在维护林木所有者的私人利益。莱茵省议会在制定法律上对于不同等级的人采取不同的标准。在涉及贫民的利益时,它抹杀了捡拾枯枝和盗窃林木之间的差别。然而,在涉及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时,它又承认这些差别,甚至在量刑时将用斧子还是锯子砍倒活树都区分开来。这显然是省议会对于贫民和有权势的林木所有者的不公平的差别对待。
代表林木所有者利益的省等级议会把维护特殊利益作为最终目的,将私人利益上升为国家法则,这本身就是践踏了法律的理性和正义。法不但没有保护人民的普遍权益,而且还把对罪行的公众惩罚变成对私人的赔偿。惩罚的权利本应是国家特有的,但省议会却使它由私人掌控,“把惩罚的主体变为被惩罚的对象,把民众的惩罚变为对民众的惩罚”[2]。等级制度导致了穷人贫苦的生活困境,而法的非理性和非正义性更使穷人无法改善这种状况。马克思认为,法律是事物的法理本质的普遍和真正的表达者,它应该以保障多数人的自由平等和正义作为考量。普鲁士当局制定的代表极少数人私人利益的法是对法的本性的违反和亵渎。立法机构不应从私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将拾捡枯树枝和违反森林条例的行为当做罪行而惩罚,它应从国家利益出发,从根源上去预防真正意义上的盗窃。国家要给贫民阶级一定的生存权利以及行使这些权利的现实可能性,而不是去立法剥夺贫民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在不同等级的物质利益冲突时,国家和法律本应作为最公正的法官的角色去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纠纷,然而在现实中,“凡是在法为私人利益制定了法律的地方,它都让私人利益为法制定法律”[1]288。利益就其本性来说是盲目、片面和无节制的,它具有无视法律的本能。莱茵省议会和立法权由特殊阶层控制,因此议会制定出来的法律也必然是代表着特殊阶层的利益。私人利益控制着法律,那么法律显然只能为私人利益服务。虽然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了法律被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控制,省议会代表着等级利益,为特殊阶级的利益服务,但是他还是认定国家代表人民的普遍利益,是超越等级的特殊利益之上的。他试图从国家理性的层面出发,呼吁战胜议会等级制,建立平等的法律制度。“从法律上说,省等级会议不仅受权代表私人利益,而且也受权代表全省的利益。同时,不管这两项任务是多么矛盾,在发生冲突时却应该毫不犹豫地为了代表全省而牺牲代表特殊利益的任务”[1]289。这也说明马克思还没有充分认识国家理性与等级制、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使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产生了怀疑。他看到了在社会现实面前物质利益对法和国家的绝对支配作用,这与马克思关于国家和法的理性认识产生严重冲突。理性国家理论在协调私人利益、等级制和法时难以成立。他批判谴责私人利益,但是在私人利益与法的理性相矛盾时,利益却总是占上风。这使马克思开始认识到物质利益的重要作用。
三、摩泽尔地区贫困问题:官僚机构和市民的利益对立
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看到了省等级议会背后隐藏的私人利益取向,于是,他把战胜特殊等级利益的希望寄托在国家身上。但是,在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的贫困问题研究后,马克思发现,当官僚机构与市民阶层的利益相对立时,反映现实情况的市民利益却被毫不留情地牺牲掉了。这促使马克思开始认清普鲁士政府的官僚本质,从而对他的理性主义国家观进行反思。
1834年,普鲁士政府取消了禁止从国外进口酒的禁令。法国葡萄酒的大量涌入导致普鲁士国内葡萄酒价格大幅下跌,盛产葡萄的摩泽尔地区的农民陷入困境,纷纷破产。他们求助于政府,但是政府却否认了贫困问题的普遍存在。政府将贫困的原因归结于部分葡萄种植者的肆意挥霍,甚至认为葡萄酒酿造者夸大地宣称贫困是试图为自己牟取优待。葡萄酒酿造者指出,政府之所以完全错误地判断事实情况,是因为怀有自私自利的意图。“官员指摘私人把自己的私事夸大成国家利益,私人则指摘官员把国家利益缩小成自己的私事,即缩小成一种把所有其他的老百姓都排斥在外的利益。”[1]372市民的理性反映了贫困的现实,而官员自私自利的意图扭曲了现实。在此,利益的冲突导致政府和市民的立场相互对立。官僚站在自己的利益上看待市民,市民站在自己的角度对待官僚。官僚是掌握实权的管理阶层,市民属于无权的被管理者,当二者的利益相对立时,显然市民的利益要被牺牲。
马克思从客观现实出发探究摩泽尔地区的贫困问题。他根据收集的大量事实资料以及对摩泽尔地区农民贫困状况的深入考察,得出结论:摩泽尔地区的贫困问题是历史地逐步地形成的,它起初是个别情况,但是随着问题的不断加剧和扩大,现今葡萄业种植者已普遍处于贫困的窘境。马克思剖析了贫困问题普遍存在的原因,指出这种情况的产生与作为管理机构的政府是密切相关的。“不能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和国家管理机构无关,正如不能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位于国境之外一样。”[1]364如同人们把某一地区的富裕状况视为国家管理得当的结果一样,摩泽尔地区的贫困状况也同样源自管理机构的管理不当。但是,政府“不但没有承认贫困状况是普遍的,而且也没有表示要消除它所承认的贫困状况”[1]369而只是打算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减轻”农民的困难。这样,本属于管理机构的责任就被巧妙地推卸到个人身上。“管理机构由于自己的官僚本质,不可能在管理工作范围内,而只能在处于管理工作范围之外的自然的和市民私人的范围内发现造成贫困的各种原因”[1]376。下级无视人民的实际利益需求而无条件地按照上级规定的管理原则执行,上级对下级的绝对信任又使他们无法看到事实。因此,当摩泽尔地区农民的贫困问题超出管理者的利益范围时,他们就无视这种贫困,并将原因归结到私人身上。官僚要求人民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放弃应有的权利去适应管理制度,声称在制度下还可以勉强度日。管理机构不是为了维护被管理地区的利益而存在,相反,被管理地区是为了管理工作而存在。人们不仅要忍受物质上的贫困,还要忍受“法律上的贫困”。马克思进一步控诉了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他指出,这种国家中某一地区经常性的贫困状况,实际上体现了现实和管理原则之间的矛盾。行政机关没有责任也没有能力去解决这种冲突,或者说,消除这种“既存在于管理机体自身内部、又存在于管理机体同被管理机体的联系中的官僚关系”[1]377。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也并非完全站在葡萄经营者的立场上为私人利益辩护。他指出,即使葡萄种植者确实处于贫困的状况,也不能无条件地相信他们的说法,因为他们在作判断时必然受到了私人利益的影响。毕竟数量再多的私人利益也终究是私人利益,它不能上升为国家的普遍利益。
马克思指出,对于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必须始终分清两个方面,即私人状况和国家状况。“人们在研究国家状况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既决定私人的行动,也决定个别行政当局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1]363。马克思指出了隐藏在人的活动背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关系”的重要作用,强调要把主观意图和客观关系区分开来,站在客观立场上观察问题。据此,马克思提出以“具有公民头脑和市民胸怀的自由报刊”作为协调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矛盾的第三方因素。这种解决方法克服了两者从属的等级关系,它是在平等的公民权利范围内进行的。只有自由报刊才能使一种特殊利益变为国家普遍利益。马克思希望借助自由报刊来改良社会显然是不现实的。
如果说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认为私人利益对国家和法的支配作用不符合国家理性,那么在对摩泽尔地区贫困问题的评述中,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了客观关系对国家和市民社会的重要作用,这也是他向历史唯物主义迈进的重要一步。
四、物质利益难题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忆:“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形容。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3]31对于这个“物质利益难题”究竟是什么,学界多有争论。段忠桥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他遇到的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指的是他因缺少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而难以对涉及物质利益的争论和讨论发表意见”[4]。如果缺乏经济学理论基础是难事本身,那么又是什么难题使马克思需要运用经济学知识来解决呢?吴晓明教授认为,并不是物质利益问题本身使马克思感到困惑和为难,“使马克思痛感苦恼的是,物质利益问题向他单纯理性的世界观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这种理性世界观却很少能够直接对‘物质利益’问题作出有内容的判断,在问题的解决方面甚至是完全无能为力的”[5]429。马克思的确受到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影响,认为国家是普遍利益的代表。但是,这种理性国家观并非不考虑物质利益,它承认私人利益间的冲突,只是完全不考虑贫困人民的物质利益问题。
物质利益难题究竟该如何解释?其实可以从马克思对物质利益的不同理解来思考。李淑梅认为,“这里的困难不在于他因缺乏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知识而不好表明自己的态度、发表自己的看法,而在于尽管他始终如一地站在贫苦民众的立场上,但他对‘物质利益’的解释上却又不尽一致,有自相矛盾之处。他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但一时又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陷入苦恼之中”[2]。首先,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站在劳苦贫民的立场上批判林木所有者的私人利益,指责私人利益是一种非理性的物欲,而林木所有者的私人利益支配了国家和法律,法沦为为私人利益服务的工具。在评论摩泽尔地区贫困问题时,他又提出要保护葡萄业经营者的私人利益,指出葡萄种植者的私人利益反映了贫困的现实状况,它是一种“市民的理性”,是与代表官僚利益的“官员的理智”相对立的。马克思将私人利益放入不同的具体情境中,产生不同的理解,也导致他对私人利益的态度有所不同。在前者中,他批判私人利益,但在后者中,他又保护支持私人利益。其次,马克思区分了不同的物质利益。在对摩泽尔地区贫困问题评述时,他否定了葡萄业种植者将私人利益宣称为国家利益的做法。“个人,甚至数量很多的个人,都不能把自己的呼声说成人民的呼声……即使进行申诉的私人的信念表达了整个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信念,作为管理机构属下的个别部分和国家的个别部分的摩泽尔河沿岸地区本身,对于自己所属的省和国家说来也只占有一个私人的地位,而私人的信念和愿望首先应该用普遍的信念和普遍的愿望来加以衡量”[1]377-378。在国家的普遍利益面前,任何私人的特殊利益都必须服从。可见,此时马克思还是将普遍利益和国家理性联系起来。然而在摩泽尔贫困问题上,政府作为管理机构不去设法解决问题,却将贫困原因归于个人,只要求人民的绝对服从,而不考虑民众的实际利益需求。在此,政府和葡萄业经营者的私人利益又是相互对立的。马克思分析了利益与出版自由、法和官僚机构的关系,发现了国家理性与私人利益、等级制之间的矛盾,区分了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也阐述了国家、地区、集体和个人等不同利益之间的关系。正是对于利益的不同理解和解释,使马克思在物质利益问题上陷入了困境。
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两次辩论中,马克思认识到,“在这里进行论战的不是个人,而是等级”,各个等级间的斗争又源自背后物质利益的冲突。马克思一直认为国家和法应该超越特殊阶级的利益,实现人的普遍自由,然而现实中国家和法恰恰是被特殊阶级的利益所支配。马克思批判物质利益,但是他逐渐发现,在物质利益面前,国家理性无能为力,私人利益不仅不受国家理性的控制,反而以国家制度和法的形式控制着国家。马克思看到了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作用,他逐渐从精神领域转向物质领域,从对不正义的法和等级制的批判,转向对社会制度的批判,并开始探寻国家制度产生的客观基础。这为他后来研究经济关系和转向共产主义奠定了基础。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李淑梅.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想[J].哲学研究,2009(6).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段忠桥.《莱茵报》时期使马克思苦恼的“疑问”是什么[J].学术研究,2008(6).
[5]吴晓明.形而上学的没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薛明珠】
2016-05-02
杨植迪(1991—),女,河南新乡人,博士生,主要从事政治哲学研究。
A811.1
A
1672-3600(2016)10-004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