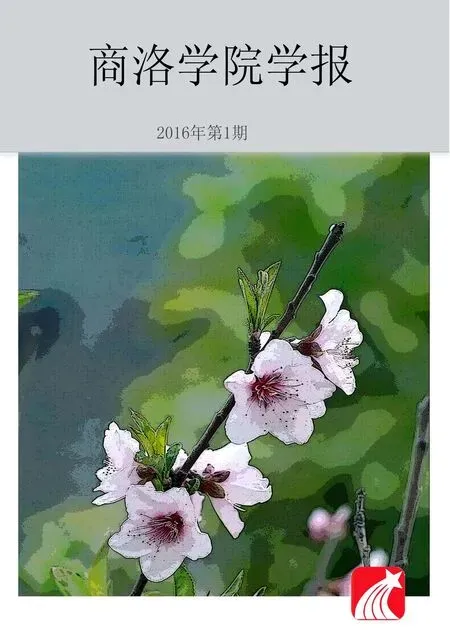“反英雄”的形象内涵:底层性、杂糅性与漫游性
——以贾平凹《高兴》为例
张建军(商洛学院 语言文化传播学院,陕西商洛 726000)
“反英雄”的形象内涵:底层性、杂糅性与漫游性
——以贾平凹《高兴》为例
张建军
(商洛学院 语言文化传播学院,陕西商洛726000)
摘 要:《高兴》是贾平凹在商品经济下主流精神的迷茫困惑和文化矛盾抉择之后的文本性尝试:以社会底层的“实”解决精英阶层的“虚”。文本形式、语言、结构、思想一体性的“反英雄”化写法,虽然并没有得到批评界的价值认可,但正是作者的文本尝试,刘高兴的“悖反”,让社会底层言说了他们自己,而不是被代言。
关键词:反英雄;底层身份;互文性创造;城市漫游
在小说创作上,贾平凹是一位非常具有创新精神和不断突破自身价值定位的当代作家。他紧抓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现代化进程,把视角重点投放在普通人生活或者社会底层生存的主线上。1992年《废都》表现了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初期受经济大潮影响,在生命情感和文化精神方面的困顿、颓废、堕落和迷失。这些先知先觉的文化精英在城市文明进程中的迷惑和彷徨是对中国现代化文明进程的隐性表征。2005年《秦腔》的推出则将其彻底放大并显现:城乡矛盾的二元对立结构在现代化进程的强大趋势下,城市文明以其强劲的前进脚步延伸和渗透到厚重滞后的乡土文化中去,并迫使其土崩瓦解。那么,在这块土地上世世代代生养的农民又该何去何从?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也是贾平凹这位具有浓厚农民意识的知识分子极力想解决的问题。2007年写就的《高兴》就是在以“到达大都市”的方式探讨了现代新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城市中的农民能否也被现代化和城市化?《高兴》这部尝试性文本不管存在怎么样的得与失,都不失为当代文学史僵化局面上的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开拓之作,因为这个试验文本中出现了刘高兴这样一个中国现代化进程意义上的“反英雄”形象。
“反英雄(anti-hero)”是与“英雄”相伴而生且对立的一组概念,是对同一个目的两种不同的反应,中西方产生的都比较久远。这一概念明确的所指和内涵却是指西方叙事文学,特别是与城市概念相关的流浪汉小说。王岚在研究西方文学基础上的《反英雄》一文中,有四个类型界定:积极向上的普通人,从虚幻中惊醒的人们,失去信念的现代人,荒原人[1];而这四个类型完全吻合了贾平凹雕刻的“高兴”群体之全貌:刘高兴具有积极向上的品性,五福之死就是他“从虚幻中惊醒”,行走在城市化工业化和非道德的荒原上,他们真实的灰土色更加衬托出失去传统信念的现代人,或者失去文化主导的空心人之靓丽。“刘”不仅仅是姓氏,表面上,可以看作是穿流而过的渺小与转瞬即逝,实际作者的本意是流传百世,因为他们是消费时代彰显人文精神的“反英雄”形象。文学经历英雄、普通人、反英雄的艺术转变,这是社会时代发展变化导致的文学思潮流变。而《高兴》文本的重要意义就是完整地界定了“反英雄”的形象内涵:身份属性、形象来源与社会价值。
一、“反英雄”的边缘性与底层本色
《秦腔》见证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一步步从农村走出:青年盲目辍学,劳动力大量流失,渴望在城市实现他们五光十色的金钱梦。老幼留守,土地荒芜,农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废乡”。走进城市的农民是否就真的实现了他们的梦想,或者得到城市建设者的身份认可?贾平凹说“我这也不是在标榜我多少清高和多大野心,我也是写不出什么好东西,而在这个年代的写作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学作品不可能是经典。”[2]450文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更应该凸显出文学的现实主义倾向,这种文学底层性的叩问并不是经典性的缺失,而是对文学经典性的重构。赛义德以其自身的民族境遇和知识分子个体困境有感而发:“知识分子若要像真正的流亡者那样具有边缘性,不被驯化,就得要有不同于寻常的回应:回应的对象是旅人过客,而不是有权有势者;是暂时的、有风险的事,而不是习以为常的事;是创新、实验,而不是以威权方式所赋予的现状。流亡的知识分子回应的不是惯常的逻辑,而是大胆无畏;代表着改变、前进,而不是固步自封。”[3]贾平凹没有固步自封,他一直在寻找突破和创新。所以,在这种意义上说,贾平凹是现代社会生存斗争中的一个精神上的流亡者,以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敏锐的时代感,准确把握时代脉博。像刘高兴这样一个悲剧式农村人、城市鬼的形象,社会所强加给他的一系列被迫式生存冒险,实则是贾平凹通过刘高兴的底层之躯,再现他本人的精神流亡。当然,也只有这样的换位思考,文本才能深入地挖掘出底层的本色[4]。
如果把“这些离开了土地在城市里生活的贫穷、卑微、寂寞、和受到的种种歧视而痛心着哀叹着”[2]450的农民比拟成十七、八世纪西方流浪汉小说中艰难和苦涩的人物,这种摹比是准确的,因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目前就处于这样一个初级化的阶段,有很多不完善和不健全的部分,而这些土地流失者的农民和流浪汉有着共同的遭遇和境况。西方十七、八世纪流浪汉小说是在商品主义经济发展基础上的城市小说,流浪汉生存根基在城市,城市也是展现他们视野的广阔舞台。《高兴》文本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创作出版,通过刘高兴这些城市边缘化人群在西安的生存境遇,浓缩了商品经济发展下的城乡矛盾。拾荒者是边缘化人群在城市中的身份,城市的多元化和神秘性造成这些人的冒险经历。作家让刘高兴式的流浪汉走进城市,走近具有话语主导权的城市舞台,通过他们的话语、行动、思想给我们真实言说他们的原生态,彻底打破城市理性框架下被代言和发生变异扭曲的农民形象,所以《高兴》是在中国城市化的初级阶段的一部具有独创意义的流浪汉小说。在叙述视角的选择上,以流浪者的身份来发展和延伸故事情节更有利于对社会底层意识的展现,这也是贾平凹农民出身心理身份认定上,一贯所倡导的乡土关怀。从此意义上说,贾平凹的《高兴》已经达到了他的初期目标,和他的其他作品相比,带有“一种生来俱有的忧患,使作品写的苦涩沉重。”[2]450这种底层意识是在中国社会进行改革开放的转型时期,整个社会都满怀信心地沉浸在城市化、工业化、文明化浪潮的大背景下,对社会底层及其他们所留守的传统文化的一次道义反观、良心自问。
城市化进程一直都是在“高兴”群体的全面参与下向前发展,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声音。感恩意识是作家从人性角度对社会提出的一种奢望,对他们的关注才是当下所必需做的事情。要让底层真正有自己的声音,最主要的是让底层自己表现自己,而不是让作家“塑造”的形象成为底层的代言人。贾平凹五易其稿,最终让他们自己出来用自己的语言来直接地表述他们的心声。“那么,就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我要写刘高兴和刘高兴一样的乡下进城群体,他们是如何走进城市的,他们如何在城市里安身生活,他们又是如何感知认识城市,他们有他们的命运,这个时代又赋予他们如何的命运感,能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觉得我就满足了。”[2]450这种底层意识要真正的实现,“只盖一座小塔只栽一朵月季,让砖头按顺序垒上去让花瓣层层绽开。”[2]450《秦腔》全景式的铺排已经完全不适应。西方流浪汉小说叙述模式和《堂吉诃德》的人物性格互补在某种意义上为贾平凹打开思路,波德莱尔在十九世纪末的巴黎,给我们塑造了城市“漫游者”这样一个独特观察者的身份。《秦腔》中引生的视角,是在乡土文化瓦解意义上的全面体察,这是时态完成式的表达,刘高兴他们却是在城市化影响下,即过程中正在进行时的“流浪”,这就认定了他们与城市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关系,但又是在中心影响下被迫驱动的边缘化人群。主流话语之外的多声部交织,在文本中呈现的就是底层自己的声音,但是必须围绕一条中心主线将这种多声部吵杂交织成一首带有主旋律特色的低声位交响乐。
小说从一开始就引入了刘高兴和五福这一对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式的经典组合,从他们的身份和视角历临了城市的五光十色、色彩斑斓。小保姆、黄八、石热闹、孟夷纯等是他们认识社会的试金石,更是他们自身在城市中的身份群雕。刘高兴、五福、孟夷纯在很大意义上是农村人在现代城市中流动人口的典型代表,社会给他们一个满含歧视和贬义的称呼“盲流”,无怪乎流氓之倒置,与盲目之流的隐含暗示。贾平凹反其道而行之,把布鲁姆的“误读”和“修正”理论在流浪汉小说的叙述模式中产生创新:负负得正,流浪汉小说中的“反英雄”形象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被演绎成人性的“英雄”。一次次的冒险经历,并没有把刘高兴的本性由“清”变“浊”,而是更“清”。他是拾荒者中的一个另类,他身上的理想性和正义性,正是社会精英们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所缺少的,他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对其本真性的保留和坚持,我们无法不对他产生敬意,并与自身形成强烈的反讽。冒死拦车的正义性,对五富生的责任和死的义务,对孟夷纯处境道义上的同情心,对石热闹生存技能的教导等等都是他身上的闪光点,而这就是社会底层的本性。
理想性和人文性的交织在刘高兴身上是其另类的重要特征,因为这些特征往往是我们怀疑其存在的可能性,这是对文化中心论者优越性的侧面批评。刘高兴理想化的爱情在现实面前最终灰飞烟灭,但这种对于爱情的浪漫主义表征是对社会底层生活理想的最真实传达。箫是刘高兴人文性的重要标志,表述了他对城市的忧愁喜乐,远远超出了“骂娘捣老子”的粗俗。在深层上,教育五富和黄八要以一种平和地心态对待城市的很多不公平与歧视,这又是何等地宽容与气度。究其根源,“西服”是刘高兴接受城市化和文明化的形象标志,“剩楼(圣楼)”是对自身能够被城市化的空间起始点,象征美好的未来,这些最终都服务于他们潜意识中认同的“领导”形象,“领导”是在城市化物质背景下对乡土文化中人文性的内在认定,也是他们在消费时代中尊严与灵魂的高贵体现。“一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已经成为久远意义上的乡土农民形象,在城市文明中的社会底层是“说这说那,表情丰富,笑声爽朗。我就说了一句:咋迟早见你都是恁高兴的?他停了一下,说:我叫刘高兴呀,咋能不高兴?!”[2]450所以从此种角度上来看刘高兴的形象是真实的,并不是作家在凭空虚构的底层角色。他们也是有丰富的思想和情感,用欢笑诠释自己的悲苦生活。
二、“反英雄”的互文性形象杂糅
“反英雄”在中国土壤上产生,也是新文化运动思潮影响下“西学东渐”的重要内容之一,与传统的本土侠义形象有精神的相似之处。所以文本中的“反英雄”形象就是在互文性背景下的再创造,正如卢梭所说:“没有他人的帮助谁也无法全部享受自己的个性。”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认为,“诗的传统——诗的影响——新诗形成”乃是一代代诗人误读和修正各自前驱者的结果。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一书中虽然只是就浪漫主义诗歌进行具体研究,但从诗学的角度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小说领域。《高兴》就是在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和鲁迅的《阿Q正传》的基础上形成的“误读”和“修正”。在其理论的六种修正比(修正方法)中,《高兴》主要使用“苔瑟拉(Tessera)”,即“续完和对偶”,有针对性地对前驱作品进行续完或者解构。有了前驱作品,“一种对偶式批评必须以此认识为基石,因为它是每一位强者诗人追求隐喻的最大动力”[5]5。贾平凹就将隐喻包含在这种“对偶式批评”中。影响产生焦虑,焦虑迫使创新。在塞万提斯和鲁迅两位强大前驱作家的影响下,贾平凹创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刘高兴这样一个乡土意义的“反英雄”典型形象。恩格斯说:“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6]即便这样,典型也是有前驱存在。马尔罗说:“每一个创造都是一个答复。”这种“答复”对于贾平凹是创造了现代意义上有似于堂吉诃德和阿Q形象,但又区别于他们的这样一个刘高兴。读者和接受者在此“答复”的形象中读解出一个时代的气息和社会进程的意义,“反英雄”也许在人文传统中是一种情感上的悲哀与苍凉。
对于诗人来说,斯芬克司之谜不仅仅是一个‘初始情景’的谜,也不仅仅是一个人类起源的神秘,它也是一个更为阴森可怖的关于想象力之优先权的谜。一个诗人仅仅解出这个谜还是不够的,它还必须使他自己(以及他理想化了的读者)相信:没有他的介入,这个谜是无法编出来的[5]36-46。那么贾平凹在关于斯芬克斯之谜阴森可怖的想象力上充分发挥其介入性,对其进行对偶和续完。让我们对刘高兴这样一个“反英雄”有了更加深入地认识和思考。
刘高兴在“苔瑟拉”的对偶和续完方面结合了堂吉诃德和阿Q的两个影响源,所以下面就结合这两个影响源展开其“反英雄”特性:首先是改名的续完。堂吉诃德的改名是为了增加其家族的贵族谱系性,希望能彻底地将其骑士小说迷的身份在心理认知上转变为有光荣传统的游侠骑士,是虚化的概念。刘高兴在两种境遇中的改名是对自己身份的观念转变,“刘哈娃”是乡土文明的符号表示,而“刘高兴”则是对城市文明的认可和肯定,是对其适应城市身份的第一步行动。贾平凹将堂吉诃德的自为改名发展到刘高兴的时代环境逼迫其社会身份转换。由虚转实,由无意义的指代发展到强烈的象征意义。“阿Q”和“刘哈娃”所包含的愚昧、落后、憨厚、淳朴的单面指称符号已经完全不适应于立体化地再现农民个性特点。而“刘高兴”充分体现出老庄哲学智慧与辩证。整个作品前半部分的苦中作乐式的轻松幽默,结尾或死或去的灰色调子,刘高兴在其中选择无可奈何的忍受。这一切可以说就是对其“高兴”的最佳诠释。贾平凹在后记中说:“这一次主要是叙述人的彻底改变,许多情节和许多议论文字都删除掉了,我尽一切能力去抑制那种似乎读起来痛快的极其夸张变形的虚空高蹈的叙述,使故事更生活化,细节化,变得柔软和暖和。因为情节和人物极其简单,在写的过程中常常就乱了节奏而显得顺溜,就故意笨拙,让它发涩发滞,似乎毫无了技巧,似乎是江郎才尽的那种不会了写作的写作。”[2]450这些底层人物的真实话语往往在文学表达的过程中被文人知识分子用他们流畅的话语所代表,文学史上有很多底层人物,但他们都是处于失声状态的。所以还他们以真实和话语权就成为一种要求和必然,让他们用自己的话语来显现自己的原生态。那么刘高兴就成为底层人物形象一个鲜活立体的代表。与阿Q相比,意义可想一般。
其次,人物性格的续完和填补。文本的原型刘高兴把人的平等比喻成瓷砖,只是“命运把他那块瓷砖贴在了灶台上,我这块瓷砖贴在了厕所么!”在二十多年后的对比中坦言:我是闰土!贾平凹赶紧制止他,说你胡比喻,他可不敢是鲁迅,刘高兴还是说:“你是不是鲁迅我不管,但我就是闰土!”[2]450贾平凹借用《故乡》中鲁迅与闰土在乡土意义上的关系对比,潜在地阐释了文本《高兴》中刘高兴与五富在城市氛围中的关系:文人性和农民性。也即在刘高兴这样一个人物身上杂糅了乡土文化的传统性和城市文明的教化感,这种过渡中的复杂便是现代城市意义上农民的丰富性和饱满化。文人性是阿Q之流绝不敢奢望得到的,但农民性又是刘高兴等人的生命底色。“我吃惊地发现,我虽然在城市里生活了几十年,平日还自诩有现代的意识,却仍有严重的农民意识”[2]450。农民意识是知识分子对社会底层的深深关怀,文人性则是流动性农民对现代化进程的积极介入的态度表征。所以从此种意义看刘高兴和五富的性格应该是互补的,就如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但是《高兴》文本又从时间意义上将刘高兴的性格特点划分出三个板块:五富是刘高兴过去乡土文化架构下的现实性的真实面;刘高兴则是自己身份转换时期理想和现实交织,思想混乱的迷惑面;而韦达是刘高兴城市文明理念指引下,走向所谓成功的异化面。五富死亡是城市文明对乡土文化挤压和蚕食的隐喻。肾是生命之源和先天之本,在本文中有创造发展的内涵。刘高兴带着寻找另一个我的愿望,认为韦达是其生命中成功的一半,却发现他是换了肝脏(与心同解)。韦达有同音隐喻之意,即伟大和为达(为达目的,不惜一切)之双解。所以韦达就是城市化刘高兴成功但却发生严重异化变形的指代,而他身上的文人性就成为横亘在他和韦达之间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最终无望地留下,成为城市的孤魂野鬼。在此意义上看阿Q式的麻木不仁就是一种结果性的观瞻,而非刘高兴过程性的演示。
第三,精神价值的续完。刘高兴“是拾破烂人中的另类,而他也正是拾破烂人中的典型,他之所以是现在的他,他越是活得沉重,也就越懂得着轻松,越是活得苦难他才越要享受这快乐。”[2]249这样一群城市边缘化群体,一直以来,被忽视其存在精神价值。而刘高兴所高扬的精神价值,就是坚持有尊严的生活和追求纯真的爱情生活。刘高兴与五富在城市中的一次次拾荒之旅就像堂吉诃德与桑丘·潘沙的骑士冒险一样惊险刺激。堂吉诃德希图以骑士的勇敢来匡扶正义和拯救世界,他的失败是对自身身份的否定;刘高兴则妄求以拾荒者的卑微显现出不屈不挠的高贵灵魂,这种失败是对社会底层的精神赞美和对社会道德缺失的痛心。城市不需要堂吉诃德式的拯救英雄,需要的是刘高兴这样历史垃圾堆中不辨其本来色彩的破旧古铜镜,反观每一个过路者。刘高兴把阿Q的尊严充实了,并有了耀眼的光辉。
杜尔西内娅在堂吉诃德的骑士冒险历程中是一种符号化的表示,是为了增强其对冒险之举的现实投射。杜尔西内娅不是那么美,也不是贵妇人,这就是塞万提斯对骑士传奇的“续完和对偶”。刘高兴想以把肾卖给城市来盖房子结婚的愿望,彻底被打破后,空留下一双与乡土文化根本不融和的高跟鞋,这是故事缘起的线索更是发展的暗示。刘高兴带着寻找另一个自我和自己纯真爱情生活在城市的想象,与五富开始了城市的历险之旅。高跟鞋在乡土意义上是理想爱情的物化,但在城市文明中却最终被妓女孟夷纯的形象所代替。“她是妓女,但她做妓女是生活所逼。她不清白,在这个社会,谁生活的又清白了呀?!”[2]217从城市文明而来的自由恋爱带给孟夷纯家毁哥死的深重罪感,在城市文明中她又误入以恶偿罪的陷阱。所以孟夷纯是有着丰富时代内涵的,与刘高兴一样的城市流浪者,她是刘高兴的梦想和希望,更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刘高兴所了解的锁骨菩萨是从乡土意义上对孟夷纯形象的指正,这种指正是他正义性的体现,更是其理想性中阿Q精神胜利法的外露,表达了社会底层在强大的城市文明面前的辛酸和无奈。阿Q出于面子的原因也摸了一下小尼姑,如果说是带有乡土意义上的色空概念,那么刘高兴对于孟夷纯则已经发展出情感上的两性关系。这一切,都是贾平凹在前驱作品基础上对文本发展中爱情对象的充实、丰满,是对阿Q精神的正面误读,“误读”中让我们看到阿Q精神更应该包含这种价值意义,而不是在那个时期的狭义化。
三、“反英雄”的城市漫游与人文精神
“反英雄”产生的重要土壤就是城市基础上的个体流动,这种自由流浪是在人文意义上对传统、阶层和社会的反观性评价。所以漫游大都市就成为一个必要和客观的表现方式。“到达大都市”的概念在现代文学上最早出现在矛盾的《子夜》中,是作为文学与政治的城市背景来所反映的,后来张爱玲的作品中有所继承和发扬,但不是作为中心议题出现的,而是从城市眼光中表现人,分析人,这种表现手法真正意义上是一种“他者”集体性眼光的折射,或者说就是集体性的言说纷纭,而不能真正凸显出文学性的形象本色;“到达大都市”是通过商品经济的价值和天平衡量出个体的真实价值。因为人类在欲望的诱惑面前把灵魂交给善于隐形的靡非斯特,一步步走向不可挽回的罪恶深渊。靡非斯特及其所能的提供实现人类欲望满足的舞台,主要是为了实现与上帝之间的赌约;商品经济是一面个人主义的魔镜,每一个你所需要了解的形象都会原形毕露。在城市中展现欲望,书写人性。又何尝不是作家与城市这样一个具象化的靡非斯特之间的赌约。把人类交给城市,交给城市隐藏、包装下的潜意识和欲望,还原出伊甸园之前的亚当和夏娃。人性是文学的最终旨归。所以,《高兴》就是在城市舞台上的一出人性斗争大戏。
城市在本质上是对精英文化的定义和表达,由此衍射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论的观点。从《圣经》开始已经有了对城市罪恶的最早记载。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和索妮娅可以说是对商品经济下城市罪与恶的最好阐释,他们到西伯利亚的惩罚之旅真正是远离罪恶和自我救赎。波德莱尔的“漫游者”和刘高兴这些城市流浪汉一样,在惊艳之余带来的是对城市文明的审视,更是对人性的魔镜式反观。他们没有拉斯蒂涅式幸运“人生三课”的教导和指点,完全是在社会精英看来是“无意识”行为的意义上,去征服一个没有他们一席之地的城市,他们有的只是传统的正义性和淳朴的理想性,城市对于他们就如堂吉诃德面对每一次不可预测的骑士冒险,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乡土文明的正义性和理想性与城市文明的险恶性和现实性是两套完全悖立的价值体系,失败就有其必然性。这种探讨是一种尝试或者是一种对农民未来生存空间可能性的文本模拟。
城市文明又是对传统爱情的彻底摧毁,虽然建立了一种两性关系上的情爱,却带有很浓郁地物质基础性和情爱交换性。引生喜欢白雪是在传统乡土意义上建构的一个理想爱情典型,当然在刘高兴身上也体现了理想爱情的影子,但是他对孟夷纯的正义性是在爱情基础上通过金钱来实现的,和孟夷纯有过两次不太成功的两性关系。在对孟夷纯这个人物形象进行塑造之前的高跟鞋描写,很多研究者认为是恋物癖的观点。恋物癖的倾向是在城市文明的基础上产生,并对理想爱情的完美性和整一性进行物质化的分割。所以刘高兴对孟夷纯的爱情是物质基础上的单相思情爱,因为他绝不可能像引生那样采取断根的行动,以保证城市文明侵袭下纯洁的乡土理想爱情。这种情爱的泛化即是城市中的色情场所、黄色笑话、下流舞场、性骚扰、肆无忌惮的性活动等等。最为主要的是城市文明在瓦解乡土文化的意义上把刘高兴他们带向了城市,把乡土意义上的“漫游者”引生变成了像孤魂野鬼一样飘荡的刘高兴,把传统爱情的守护神白雪变成了洋溢物质情爱因素的丑恶化身孟夷纯。
拾荒者分三六九等:韩大宝在混到破烂王级别后的内在异化、拾荒者内部因钱财而遭迫害,刘高兴侄子对狗和刘高兴的显著差异。韦达换肾到换肝的隐喻转变都在阐明城市文明下商品经济对个体人的物化和异化,整个社会都在高扬金钱意识至上的理论,人性在商品经济的强势下是那样地弱小和无能。孟夷纯带着破案的希望在城市中通过以罪换恶的方式想求得正义的结果,自己最终却在监狱中彻底对人生和她周围的城市坏境进行思考。文本最后走向:五富成为飘荡在城市上空的孤魂野鬼,刘高兴孤身一人漂泊在这样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城市。这就是他们一群在城市寻找理想,失去土地的流动性农民,在没有根基的城市建立乌托邦,只能象一个梦一样在白昼不留一丝痕迹的消逝。塞万提斯:人生如戏。刘高兴又何尝不是如此:城市梦想如戏,具有后现代戏剧性意味和社会底层的辛酸无奈。但刘高兴形象中人文性一面,或者具体说,就是农民意识浓厚的知识分子贾平凹,通过这样一个底层视角给我们对城市生活作了一番独特的体验,陌生化带来的不是视角上的惊艳,而是灵魂上的震撼。“废人”是在现代城市意义上文学对社会底层人价值的褒赞。
四、结语
2007年《高兴》出版,批评界形成了对贾平凹作品“废都”“废乡”“废人”三部曲“废”之概念界定。贾平凹的“三废”和商州系列小说却完全真实的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农村变迁和农民流变,贾平凹用商州视野和“高兴”身份在鲁迅阿Q意义上以小见大。《高兴》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在文学意义上终结者或者转折点。这一拐点位置决定了文本本身所包含的契机和增长点。首当其冲的是,“反英雄”形象在城市文明中的底层身份或者底层意识,虽然在以往的文本也是存在的,但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大背景下,更显示出这一概念的时代性和整体性。这不单单是文学家的叙述,更是思想家和政治家的问题。它在现时代所承载的社会责任是:“好的文学作品应当具有教育第一流政治家的能力”[7]。在时代意义上,《高兴》是一曲现代城市流浪者的悲歌[8]。“废人”不废,更是一部“反英雄”的时代赞歌,切合鲁迅先生对平民作为民族精神脊梁的指证。
参考文献:
[1]王岚.反英雄[J].外国文学,2005(4):46-51.
[2]贾平凹.高兴[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3]爱德华·W·赛义德.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57.
[4]任梦池,张晓倩.质疑山寨板《高兴》的民间狂欢[J].文化学刊,2009(5):89-92.
[5]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M].徐文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6]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致敏娜·考茨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53.
[7]沈从文.沈从文文集:11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
1982:203.
[8]张碧.消费名义下的狂欢与悲悯——论《高兴》中文化资本与知识分子立场的博弈[J].商洛学院学报,2015:29(5):3-6.
(责任编辑:李继高)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033(2016)01-0007-06
doi:10.13440/j.slxy.1674-0033.2016.01.002
收稿日期:2015-09-12
作者简介:张建军,男,陕西礼泉人,硕士,讲师
"Anti-hero"Image:Subaltern,Intertextuality Creation and Rambling——With Jia Pingwa's Happiness as an Example
ZHANG Jian-jun
(College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Communications,Shangluo University,Shangluo726000,Shaanxi)
Abstract:Jia Pingwa's Happiness is an attempt to the literary texture in the situation of commodity economy which causes the main social current in spirit puzzle and cultural contradiction.The novel sets off the elite"virtual"by the subaltern"real"and gives off the concept of"anti-hero"from the points of form,language,structure,and thinking.Although it is not recognized by critics,the novel let its characters speak for themselves rather than endorsement through"contradiction".
Key words:anti-hero;subaltern;intertextuality;ramb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