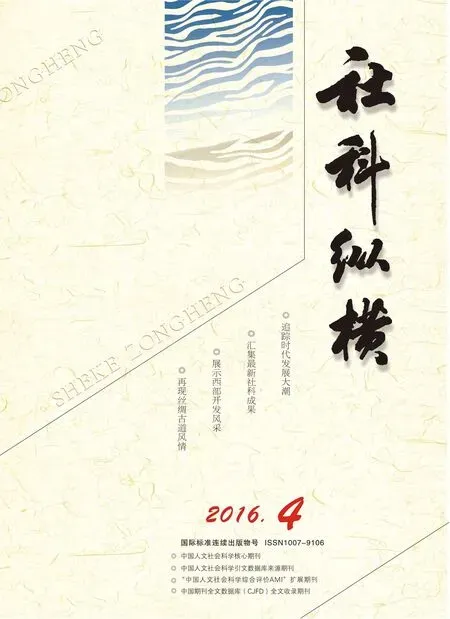近代山西分家析产行为探析
张文瀚 郝 平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近代山西分家析产行为探析
张文瀚郝平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分家析产是近代山西社会非常普遍的行为,而分家单是分家行为的一种重要凭证。通过研究分家单可以很好地揭示近代山西的分家流程及分家背后的原因。本文通过对山西清徐王氏家族两份分家单研究,以揭示近代山西分家的原因、流程及民间习惯。
分家析产山西分家单
分家古称“分关”,意指分割财产,各自过活。按照郑文科教授的解释,分家是家发展出“房”成了“家族”以后,又将“房”从家族中析出,建立新的家或家族的过程。[1]众所周知,在传统社会中,中国人崇尚多子多福的理念,传统的中国家庭大多子女众多,枝繁叶茂。而分家不仅有助于子女独立生活,而且有效避免家族内子女间的矛盾,因此分家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较为普遍的行为。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分家行为中,起影响作用的除了官方颁布的法律外,还有当地形成的民事习惯。两者共同规范和调整着人们在分家析产中的权利与义务,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及方方面面的利益。随着时间步入到近代,社会朝着法制现代化的方向迈进。但当地固有的民事习惯还在延续,在社会中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而这些民事习惯与社会风俗完整体现在分家单中。
“分家单”即分家时的产权清单,又叫“分关书”或“拨单”,是分家行为的重要凭证。分家以后,如发生田土争讼或土地买卖,到官府诉讼或过割时,此契约文书是要出示官府,由其查验而具有法律意义的凭证。作为分家行为的重要凭证,分家单的成立与生效是从根本上证明分家行为成立与生效的证据,因此,通过研究分家单,可以有效揭示家族的分家制度,从而反映当地的社会生活。
现从山西清徐东青堆搜集有两份分家单,内容上涉及同一家族内一支四辈的分家情况,时间上一份是咸丰七年,另一份是民国十三年。这两份契约为我们研究近代山西的分家制度提供了一扇窗口。
一、两份分家单中的分家事例
现有两份分家单,第一份是咸丰七年的分家单,第二份是中华民国十三年的分家单,当事人均是山西清徐的王氏家族,且两份分单中的当事人之间具有直系关系。第一份的当事人是王瑞临、王泰临。咸丰七年,王瑞临、王泰临兄弟遵奉母命分割家中房产土地等财物。下面是咸丰七年分家文书:
分家之事实为振家,在同居未免口角,惟析产则各自捡勤。今遵母命,援请家长将房产地土沟均两股,问天讨卦,捏纸团为公。长子王瑞临分到南房二间、东房五间又南西房一间,院内有茅厕半间属伙南面,东西分坌,伙占伙行。异日南面东分坌坎,门费钱公摊。北面东边分坌系随东房相连小横畛坟地九亩南一半六周零四垅,半系瑞临。又分到秦房角地五亩,以契为据,此系奉母拨与二孙女妆奁之资。次子当面讲明,永无反悔。至法库门房产属伙所得房租。凭母通年每一股拨钱四十千余,俱是伊母养老都交母手,不准擅取使用。又活契地数段,南场一块俱由母管,属所有一切钱粮两股分拨,打来干粮,均分顶纳。现在所有钱项、所得租项、所该钱项俱属母承管。异日百年之后,再为均分,长子王瑞临执此存照。
咸丰七年同家长立
中人:王世华王上智(家长) 姚世清(亲家)王建壁[2]
第二份的当事人是王普威,王殿威,王振威兄弟兼长门侄子俊文立契分家。由于王振威在东北,王俊文在泽州,因而分家主要是由王殿威主持的。原有的房产土地也被同样被均分。下面是分单:
立分析书人王普威,王殿威,王振威兼长门侄子俊文等。今奉母命,邀请家长将祖遗留房产地股均分。卷纸团为公,问天讨卦。长门俊文分到院正面南北长二丈九尺,又分到秦房冉地五亩。殿威分到院东面,南北长五丈六尺,又分到大横畛地七亩。普威分到院西一半,南北长五丈六尺,又分到韩家地五亩半,小横畛地一亩半。振威分到院南面,南北长二丈九尺,又分到疙瘩地三亩半,吴王坟地三亩半。小横畛地一亩半拨与家母养老。小横畛地四亩半、所有院内余地、茅厕街门均属伙占伙行。惟振威刻在东省,应分到之房产及地土全是家母完全主办。然而每年利害,家母自行担负。又俊文刻在泽州,亦是伊母主办。至于房契,殿威暂先执掌,惟地契各归各家,日后兄弟侄四家,那家光景度之好歹,不可搅扰。此是各出情愿,永无反悔。一样四张,各执兑约一张。恐口难凭,立此为证。一切钱粮,四股均分。
中华民国十三年六月十七日
后批另有南场一块准其四股伙使用
家长王泽临
中证人王执恭王广元秦绍先(书)
契约左上书:
长门后文分到老院正面空基计南北长二丈九尺,于民国二十五年出让与殿威为业。同中作价大洋五十元整,其已付清。
中证人王建纲[3]
二、分家的原因
分家是传统社会民间社会中存在的行为,但是这种行为并不为官方所提倡。自汉代始,国家就提倡父子兄弟同居共财。在唐代,国家有法律规定:“若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4]到清代时,有进一步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孙不许分财异居”。[5]
虽然官方并不鼓励分家的行为,但分家仍是民间社会非常普遍的一种行为,远至殷商时代,民间就有“析居异财”的行为。[6]清水江领域的苗族和侗族地区也有“姜不分不辣,家不分不发”的民谚[7]。事实上,家庭就是要不断分化,不断扩大的,而国家的压制行为并不能阻碍分家析产的发生。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王氏家庭选择分家,而不选择维持原有的大家庭呢?在咸丰七年的分单中,王瑞临和王泰临提出了理由:分家之事实为振家,在同居未免口角,惟析产则各自捡勤。从王氏兄弟的视角来看,分家并振兴家族的重要手段。事实上,维持一个大家庭是十分困难的。大家庭既是家族成员的共同体,也是家族经济生活的结合体。从家族生活的角度看,数世同堂使得家族成员内部的矛盾日趋尖锐,兄弟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家族生活出现裂痕。从家庭经济生活的视角看,大家庭的生产经营并不如小家庭的效率高。分家既能消除大家庭生活中的矛盾,又能提高自己家庭的生产效率。因而分家也就成为王氏家族的选择。在民国十三年的分单中,家庭对祖辈财产的分割更多是出于划分责任的考虑。如分单中所说:日后兄弟侄四家,那家光景度之好歹,不可搅扰。祖辈财产的均匀分割可避免同辈之间由于财产的继承而产生矛盾。
三、分家的内容
分单中的分家包含两方面内容,一者是对父辈财产的分割,二者是对分派后辈的家庭责任。
父辈财产的分割由王氏家族的家长或族长主持,在上述的两份契约中均表明了家长在分家中的重要地位。如咸丰七年的“今遵母命,援请家长将房产地土沟均两股”。由于遗留家产的复杂性,很容易导致后辈质疑家产分配的不公平,因而家长利用其在家族内的权威,对家产进行均分,让后辈心服口服,避免其产生矛盾。在之后的家产分配过程中,家长捏纸团,让后辈自己捏阄。
在家产的分配过程中,山西的分家析产体现了“诸子均分”的原则。在分家单的开头,都写有“均分”字样。以民国十三年分家单为例,“长门俊文分到院正面南北长二丈九尺,又分到秦房冉地五亩。殿威分到院东面,南北长五丈六尺,又分到大横畛地七亩。普威分到院西一半,南北长五丈六尺,又分到韩家地五亩半,小横畛地一亩半。振威分到院南面,南北长二丈九尺,又分到疙瘩地三亩半,吴王坟地三亩半。小横畛地一亩半拨与家母养老。小横畛地四亩半、所有院内余地、茅厕街门均属伙占伙行”。从中可以看出四人分别得到了房院四面,同时有将土地七拼八凑,使得家庭财产尽可能平均分配。
母亲的生活保障也要在分家单中注明。在分家之后,大家庭被拆分为小家庭,母亲的生活就成了问题。一般来说,养老费用有四种来源途径。一是提取膳田,收租养老。二是一家子轮流供养膳食,每月上交一定的油盐粮食等。三是从存众积累中提取赡养费用。四是划拨纹银。[8]王氏家族采用第一种方式。在咸丰七年的分家单中提出拨一定数量的钱用于母亲的赡养,“凭母通年每一股拨钱四十千余,俱是伊母养老都交母手,不准擅取使用”。民国十三年分家单中提出将家中土地作为母亲的赡养之资,“小横畛地一亩半拨与家母养老”。
结语
从上述分家单的情况来看,之所以分家主要是解决内部家庭矛盾,促使后辈独立。就分家的流程而言,族长秉承“诸子均分”的原则,主持分家析产,以公平分配家产和落实赡养责任为核心,通过对现有土地房产合理搭配,进行分家析产。近代山西的乡村社会凭借这些合理的分家析产制度,有效地维护了家族的正常生活和发展。
[1]郑文科.分家与分家单研究[J].河北法学,2007(5).
[2]郝平整理.晋中文书第一本,jz-00010[Z].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
[3]郝平整理,晋中文书第一本,jz-00004[Z].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
[4]长孙无忌.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236.
[5]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6]李亚农.李亚农史论[M].上海:上海出版社,1962:14.
[7]吴才茂.清代以来苗族侗族家庭财产划分制度初探——以天柱民间分家文书为中心考察[J].凯里学院学报,2013(2).
[8]章冬梅.清中期至民国婺源县分家制度研究[D].南昌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3.
K26
A
1007-9106(2016)04-0111-03
张文瀚(1991—),男,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郝平(1968—),男,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史、灾荒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