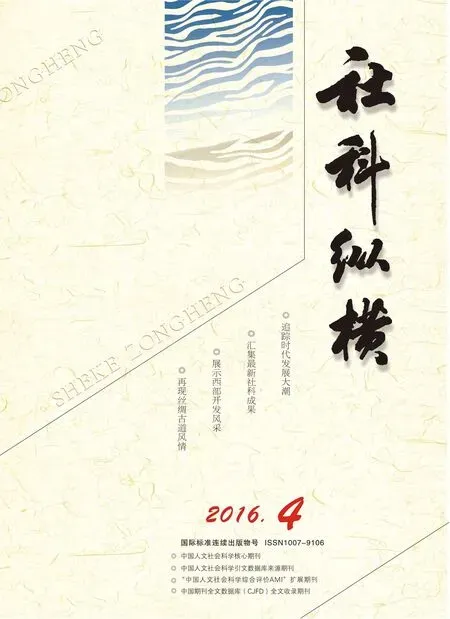以食为镜:革命、动员与日常
——以山西省北大寺为中心的微观史研究
马红玉 马维强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山西 太原 030006)
以食为镜:革命、动员与日常
——以山西省北大寺为中心的微观史研究
马红玉马维强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山西太原030006)
“民以食为天”。食物是人类生存的根本,也是近代中国社会革命话语变革中一个富有特色的“名词”与“尺度”。丈量食物的“少与多”、“好与坏”、“管与放”等等,可以从中窥视到建立在“食物”基础上的社会革命的一种动员。这种动员,通过对“食物”人类必不可少的物质的分配,从而干涉与引导了革命。文章立足于微观史学,试图以山西省一个普通的村庄北大寺为例进行深入的剖析,力求解读食物折射下的社会革命、动员与日常。
食物革命动员日常
革命话语,不是一个个僵硬的词汇,恰恰相反,它十分生动且富有极强的对比性,人们通过革命话语产生的这种对比,往往用来处理自身与革命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中,最为人们所关注的便是“食物”。“民以食为天”,传统中国社会,物质生活极为困难,近代以来人口的急剧增加,更导致了食物的稀缺性,“吃”便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围绕这一话题,“食物”的分配便成为了近代以来各个革命话语时期中最为重视的一种稀缺资源,通过对这种资源的分配和管理,人们整合着社会的革命、变革,乃至日常的社会生活。大至城市,小到村庄,均通过“食物”建立起了社会革命话语的体系。北大寺这样一个内陆的小村庄也被革命的洪流携裹着开始发生转变,这些转变中最直观,最明显的便是每个家庭中餐桌上食物的变化。
一、水与土:北大寺的自然与生产
北大寺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晋祠镇,与山西省历史名胜晋祠仅一路之隔。与北大寺村相邻的是南大寺村,这两个村庄名称中的“大寺”,指的是崇福寺,现已拆迁至天龙山。《太原县志》载:“崇福寺,在县南五里大寺村。北齐天保二年,僧永安建。唐大历二年修,会昌五年废。元至正初重建,寻废。明洪武十年重建。”①据村中老人描述:“在我们口头上不叫北大寺,我们原来一直叫大寺,后来南面有了南大寺,本来叫下大寺,老百姓是叫上下大寺的,上北下南吧,后来就变成南北大寺了。过去人民一说大寺的就是我们村,一说下大寺的就是那个村。”②
北大寺地势南北延伸,村庄土地位于向南呈开放形的广阔河谷平原,土壤肥沃,西部倚靠吕梁山脉分支,气候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日照充足,四季分明。晋水流域土壤肥沃而略带碱性,是北方地区少有的适于农耕的“水田沃土”。[1]村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三班连夜转,九顷不靠天”。“三班连夜转,指的是水磨,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的加工条件非常好,水磨白天晚上一直在加工粮食,九顷不靠天,那时候我们村的地大概在一千亩左右(1959年村中有耕地1259亩,其中水稻田876亩,其余小麦等种植383亩。③),九顷就是九百亩,90%以上的土地都不怕天旱,也不怕下雨,下雨我们这个地方(地势)比较高,水马上就流到沙河里去了,如果要是汾河水淹到我们这里的话,那就整个太原城就全淹了,虽然村中土地是个坡地,但是它水利条件好,不怕天旱,其他地方天旱不长粮食,我们这儿有晋祠水保障它,什么时候想浇就可以浇水的。而且晋祠的水温度适宜常年温度很高,即使是三九天把手伸到水里也不觉得冰凉。”④
村民口中提到的晋祠水指的就是晋祠水系的四河渠系之一的陆堡河。晋祠水的开发利用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至唐贞观,中长史李勣架汾水东引,令民汲饮后,为中河。又一派为陆堡河,流入大寺等村,其南派流入索村等处,为南河。”[2]此处提到的大寺正是本文关注的北大寺村。长期以来,北大寺作为陆堡河首村,享有便利的用水条件。积累千年的农耕经验,也使当地村民在当地自然条件中如鱼得水,在水与地中找到了最好的平衡。
在传统农耕时代,大多农民“靠天吃饭”,遇上风调雨顺的光景,便获得丰收,但逢旱涝灾害,则会出现歉收甚至遭灾的情况。由此可见,北大寺在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土地和水利方面具有多数村庄未具备的优越自然条件。
二、“旧社会”:革命要来了
在北大寺村民心中,新旧社会的区分界限十分明确,即新中国建立前后。许多老人在访谈中几乎都提及到建国前生活的“苦日子”。问及如何“苦”,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把“食物”作为起点,展开描述。由于北大寺地理位置紧邻太原城,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内战时期,北大寺都因其丰富的粮食产量成为不同“政府”战备军需粮的提供者。甚至在某些交叉时期,当地村民还需要为不同的“政府”提供多份军需粮。⑤
在深入北大寺村民中访谈时,多位被访谈者提及抗日战争时期的“李二连吃大米事件”。[3]“日本人在太原地区待了五六年,那时候就只有2个日本人在晋祠驻守,由伪军宪兵队为日本人做事。日本人不让村民吃大米,我那时7岁,给人家看场,收到的大米全被日本人拉走了。种大米的(村民)向宪兵队举报李二连偷吃大米,李二连就被绑起来往肚里灌凉水,然后再倒过来把水吐出来看有没有米粒,结果一粒米都没有,日本人为了做宣传,又将李二连吊起,用刺刀剖开他的肚子,看里面是否有大米。他其实哪敢偷吃呢。”⑥正如被访谈者这样感叹:“亡国奴,真可怕,两个日本兵就把这里看死了。”
除日本人外,还有国民党来抢粮食,抓人。⑦当地人成国民党为“二战区”或者“钩子军”。原因在于“抗战时期,咱们山西是第二战区,阎锡山是第二战区的司令长官,所以人们就叫把他的兵叫成二战区,还因为他们是第九路军,所以也叫钩子军。”⑧这些“二战区”或“钩子军”常常会连夜抢走村民收到仓库里的粮食。当仓库中缺粮会没粮时,村民还会被分配任务,翌日需交多少粮,否则便会被枪毙。另阎锡山还曾实行“兵农合一”政策,每户除交粮以外,家里的男壮丁也会被抽去当兵。“那会叫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意思就是(如果)你们家有三个男孩就一个去,五个就两个去当兵,后来就是不是抽丁了,实行抓丁,就是抓住年青的(男子)就去当兵。”⑨
由此可见,北大寺在解放前期,虽长期占有得天独厚的农业区位,但常年战争,不同军队的肆意掠夺,加之劳动力由于征兵极度短缺,村民长期处于粮食短缺的状态。甚至村中地主也不甚富裕。“我们村里头比较像样的地主就一家,姓李,后来破产了。他之前是在外头搞什么买卖,挣了钱回来买地,后来世道太乱,生意破产了,他也死了,他家就败落了,最后是因为他家地比较多,就变成地主了。可是其实我们村里的老百姓都叫他倒运(太原方言,意为倒霉)财主。”⑩在此种情况下,便急需“革命”,因此在解放军到村庄时,村民主动为其预备住处,为“革命”出力,以求得尽早得到稳妥的环境,重新开始劳作生产。
三、“翻身”:我们有饭吃了
美国学者韩丁曾在其著作《翻身》序言中专门解释说明“翻身”一次的含义:每一次革命都创造了一些新词汇,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词汇,其中一个重要的词就是“翻身”。它的字面意思是“躺着翻过身来”。对于中国几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4]由此可知,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翻身”这一事件正在中国广大农村同步发生。北大寺也不例外。
基于北大寺优良的耕作条件,土改后,村庄生产迅速恢复,村民生活也日渐有所起色。但由于基本生产资料缺乏,村庄响应国家号召,开始在村中搞互助合作。开始由比较贫穷的几户人家建立互助组,这些人家多数都连个牛没有,毛驴也没有,拿回那个楼⑪来种地,三条腿的,都是人拉的。这些互助组渐渐联合,最终成立村中第一个初级社,迎辉社。村中一些富裕的(村民)随后也成立了一个社,叫争辉社。大风暴⑫时期,两个合作社合并,当时还有一部分农民没有入社,通过大风暴以后就卷进来了,合并后的高级社仍叫迎辉社。到人民公社时期,北大寺为晋祠人民公社下辖的北大寺管理区。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深入开展,管区范围逐步扩大到南大寺、北大寺、晋祠、长巷、东苑、索村等周边村落,主要涵盖水稻田种植的村庄。但好景不长,随着困难时期的到来,管区也随之解散,各村庄又恢复到原先管理状态。
虽管理形态经历了复杂变化,但农业增产,食物种类增多是不容忽视的。早在上世纪60年代,北大寺南边的南大寺村由于土地条件更为优越,水稻亩产过千斤,并因此被评为典型,并在全国推广[3]。北大寺由于有部分土地为坡地,但即便是在困难时期,每亩产量也为七八百斤。⑬晋祠公社也因此受到中央表彰,刘少奇同志还亲临晋祠公社,指导农业生产。他在与各公社干部座谈中就储备蔬菜,修建水库,开发山地发展多种经济等问题提出重要指导意见。[5]除以水稻麦子为主的细粮耕种外,粗粮耕种也同步进行。此外还专门开辟菜地,由菜队专门种植。
粮食丰产后,粮食的储存也值得重视。村中以小队为单位设立仓库,并由专人看管。粮食储存离不开村民口中的“金棍棍”。“金棍棍”指苇子。苇子按照长度可分为数个等级。一丈三以上的苇子可算作一等苇子。一等苇子一百根可卖三块多钱。⑭有些村民因此还会给苇子施肥,除杂草。集体化以后,村中的苇子就主要用作储藏粮食。每年收割粮食后,白天把粮食铺开成粮食堆摊开晒,晚上收起以后就把苇席盖上就把苇席盖上去。这种用苇席储存粮食的方式在当地叫“席洞”。席洞为长条形,粮食晒干后,将席洞圈一个大圈,把口封上。这样是一层席洞。席洞还可以数层累加。底层的粮食放满之后就会在其上再圈一圈席子,这样叫“接洞”。以此方式,席洞可以存放到房顶的高度。在当时的条件下,这已经是最能减少虫子老鼠毁坏粮食的储存方式了。
集体化时代后期,村办企业盛行。村内办了许多粮食价格厂,藕粉加工厂⑮等,以便村民能更好地享受食物丰富后给村民生活带来的巨大转变。由此可见,“旧社会”村民的食物短缺并非天灾,多为人祸。在村民“翻身”后,获得土地,加之良好、平静的社会环境,北大寺村民迅速恢复生产,填补了过去食物短缺的空白。
四、结论
北大寺占据自然优势,却在“旧社会”面临来自多方的“人祸”,导致村民食不果腹,在此种压迫下,村民的日常生活开始与革命紧密相连,继而“翻身”,拥有土地,终于获得食物。从“无”到“有”,见证了一个村庄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命途转折。北大寺只是中国的一个普通村庄,它之中包含着属于自身的独特性与片面性,但从微观的视角出发,辅以丰富、深入的口述资料,我们可以避免刻板地“就史论事”,从而阐释基层民众对于革命是如何亲身感受与实践的。笔者从“食物”这一角度出发,讨论在革命背景下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以期最大限度地还原和重复历史真相。
注释:
①太原县志·卷三·祀典.道光六年(1826),36页.
②访谈对象:武福星,男,71岁,太原北大寺人。访谈时间:2014年9月12日.
③访谈对象:武福星,男,71岁,太原北大寺人。访谈时间:2014年9月12日,访谈对象于1966年——1971年在村内担任村内党支部书记.
④访谈对象:武来有,男,79岁,太原北大寺人。访谈时间:2014年9月12.
⑤访谈对象:武福星,男,71岁,太原北大寺人。访谈时间:2015年3月6日.
⑥访谈对象:武德长,男,76岁,太原北大寺人。访谈时间:2014年9月12日.
⑦访谈对象:武福星,男,71岁,太原北大寺人。访谈时间:2015年3月6日.
⑧访谈对象:武福星,男,71岁,太原北大寺人。访谈时间:2015年3月6日.
⑨访谈对象:武福星,男,71岁,太原北大寺人。访谈时间:2015年3月6日.
⑩访谈对象:武福星,男,71岁,太原北大寺人。访谈时间:2015年3月6日.
⑪当地方言,一种犁地的工具.
⑫北大寺村民将1958年人民公社时期成为“大风暴”
⑬访谈对象:武福星,男,71岁,太原北大寺人。访谈时间:2015年3月6日.
⑭访谈对象:武福星,男,71岁,太原北大寺人。访谈时间:2015年3月6日.
⑮访谈对象:武福星,男,71岁,太原北大寺人。访谈时间:2015年3月7日.
[1]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M].北京:三联书店,2007:139.
[2]太原县志·卷二·山川[M].道光六年(1826):10.
[3]太原市农业合作史编辑委员会.太原农业合作社(典型合作社)[M].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66.
[4][美]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M].北京出版社,1980.序言.
[5]太原市南郊区政协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晋阳文史资料(第三辑)[C].第3页,第4页.
[6]晋祠公社革委会.北大寺村辩论会材料.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晋祠镇北大寺村档案资料.
[7]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3.
K26;K27
A
1007-9106(2016)04-0107-04
*本文为2015年度山西省高等学校科技创新项目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小人物与大历史:政治变动与集体化时代乡村日常生活史研究——以平遥双口村为例”。
*
马红玉(1991—),女,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2013级中国史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马维强(1977—),男,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