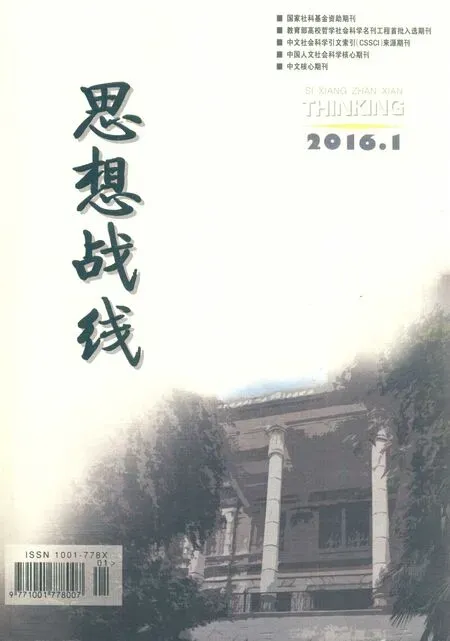中缅边境勐龙镇缅甸籍僧侣的策略性生存与地方性管理调适
张振伟,高 景
中缅边境勐龙镇缅甸籍僧侣的策略性生存与地方性管理调适
张振伟,高景①
摘要:中国南传佛教地区缅甸籍僧侣的非法跨境流动及居留,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现有的边境管理政策在解决这一问题方面还有待完善。根源于传统宗教文化内容的拜义父义母这一拟制亲属关系,被信众与缅甸籍僧侣重新运用,为缅甸籍僧侣的社会融入及针对他们的管理提供了有效途径,进而为边境地区境外人员的管理制度调适提供了地方性经验。
关键词:缅甸籍僧侣;策略性生存;管理调适
从历时性眼光来看,中国的边防与边境管理工作的重心已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军事防卫过渡到现阶段的边境服务与全面发展。*王亚宁:《建国以来中国边防工作重心的嬗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但由于现代民族国家明晰化的边界及制度化的管理方式,同边境地区的自然条件及边民自由往来的历史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加之边境地区差异化的现实也难以纳入到统一的制度建设中,因此边境管理面临一系列的问题。*罗圣荣,赵鹏:《西南陆地边境管理问题研究》,《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这其中,与人口跨境流动与管理有关的问题尤其突出。*参见何跃《中国西南边疆境外流动人口的区域管理研究——以云南为例》,《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12期;吴喜《中越边境云南段 “三非”人员问题的原因及对策》,《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吴喜《中缅边境地区云南段 “三非”人员管理及应对》,《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张爱华《滇缅边境地区非法居留问题思考——以德宏州边境地区为例》,《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而中缅边境地区缅甸籍僧侣的跨境流动,因涉及宗教内部的沟通与联系、宗教与政府间的管理与调适、全球化背景下的人口流动与国家管理的应对等一系列复杂议题,因而对它的讨论就显得更有必要。
景洪市勐龙镇因位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与缅甸的最近一条陆路通道上,也是南传佛教从缅甸传入西双版纳的必经之地,而被选做考察缅甸籍僧侣跨境流动问题的田野点。*本文的田野调查资料来源于作者2013年1月至2月和2015年8月两次赴勐龙镇的田野调查。勐龙镇辖22个村民委员会,164个自然村。2012年年末总人口103 474人(不含农场),其中常住人口83 461人,本地户籍人口74 318人。有傣、哈尼、布朗、拉祜、彝等19个少数民族。在本地户籍人口中,傣族共42 373人,占57%;哈尼族21 885人,占29%;拉祜族4 592人,占6%;布朗族2 796人,占4%;汉族2 147人,占3%。勐龙镇东南部与缅甸东掸邦第四特区接壤,并与老挝、泰国相邻,国境线长64.4千米。目前,勐龙镇有11条车道、17条便道可以通往第四特区。*景洪市地方志办公室:《景洪年鉴2010年》,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91页。勐龙镇傣族、布朗族全民信仰南传佛教。全镇现有76个傣族及布朗族村寨,72座佛寺,47座佛塔。*数据来源自勐龙镇佛教协会2012年统计数据。通过对缅甸籍僧侣进入勐龙镇,并由此引发的边境管理问题的梳理,以及他们凭借与信众共同建构的拟制亲属关系来实现被当地社会接纳及社会融入这一结果的分析,能为针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国家及社会管理提供地方性经验,同时展示这一特殊群体的拟制亲属关系在国家与民间的差异化管理与需求之下的重构与调适,为超脱亲属关系研究的家庭、血缘桎梏提供思路。
一、缅甸籍僧侣的跨境流动与边境管理制度的张力
缅甸籍僧侣大约从2001年前开始大规模流入勐龙镇。在前民族国家时代,由于国界的不清晰及边境管理的有限性,这一区域存在僧侣的自然流动现象。20世纪50至70年代,由于中国境内宗教管理制度的变迁,曾经出现僧侣外流的现象。20世纪80年代之后,得益于橡胶树、香蕉等高产值农作物的种植与生产,勐龙镇村民的经济收入有了明显提升。在获得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当地的餐饮、服饰、跨境贸易等也有了明显发展。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使得当地年轻人不愿入寺为僧。再加上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与当地传统上青少年入寺为僧的时间相冲突,绝大多数适龄青少年选择接受学校教育,放弃学业到寺院中做僧侣的青少年非常少,因此出现本地籍僧侣数量逐渐减少甚至缺失的现象。与此同时,村民的宗教需求并没有随着本地籍僧侣的减少而减少。当地村民在经济收入提高之后,纷纷捐资重建或翻修寺院。在村民看来,新建的、漂亮的寺院如果没有僧侣入住,实在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在此背景下,2001年左右,勐龙镇范围内开始出现从缅甸邀请来住持的僧侣。此后,缅甸僧侣的数量逐年递增。截至2012年12月,勐龙镇共有僧侣315人,按僧阶从高到低分别是“祜巴”9人、“都”108人、“帕”198人;其中缅甸籍僧侣共54人,按僧阶从高到低是“都”16人、“帕”38人。*数据来源自勐龙镇佛教协会2012年统计数据。
缅甸籍僧侣来到勐龙镇,主要是通过以下两种渠道:第一,本寨的亲戚、朋友介绍,并通过来往商人、朋友联系;第二,以祜巴勐*祜巴勐,中国籍僧人,1964年生于缅甸,1990年回国,自2000年起任大勐龙镇中心佛寺大方丈,2013年夏圆寂。为中心的僧侣交流圈。勐龙镇与相邻的缅甸边境地区的村民有发达的亲属及朋友网络。这种亲友网络虽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度衰落,但随着近些年跨境种植及跨境贸易的发展,又重新得到复苏和拓展。通过这类渠道介绍缅甸籍僧侣进入勐龙镇非常方便。多数勐龙镇的缅甸籍僧侣是通过这类渠道进入中国境内。祜巴勐是勐龙镇的僧侣领袖,在勐龙镇最大的佛寺——景龙佛寺担任住持。他年轻时在缅甸修行10余年,与缅甸籍僧侣相熟颇多,在中缅僧侣中都享有较高威望。部分村寨也通过祜巴勐介绍缅甸籍僧侣来本村的佛寺。
案例1,曼景宰佛寺DWH访谈录:*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涉及人物均采用化名。
我从泰国回到缅甸1个多月后,也就是2011年6月份,就接到了勐龙镇曼光掌村小组的邀请,希望我来这边寺庙住。给我带来这个邀请的是允龙村的运输司机。他们往返于大勐龙和南板,跟曼光掌村的人很熟。接到邀请后,我就启程来到了景龙佛寺,见过祜巴勐后,就被曼光掌村村小组的人迎回了寺庙担任住持。后来发生了一些事,1年后,我又回到了缅甸。2012年6月,曼景宰佛寺上一任住持和小和尚一起还俗。佛寺里面没有了和尚。村里人都为此事很着急。村委会召集全村人讨论了此事,最后大家都同意到缅甸找佛爷的提议。事情决定后,从允龙来上门的岩应说他认识我,于是他就打电话给我,我就约着4个小和尚一起来了。
案例2,曼飞龙佛寺PHL访谈录:
2010年,我的朋友DL被请到曼飞龙村佛寺当大佛爷。当年10月份,曼飞龙佛寺最后1个本地小沙弥还俗。DL主动向村小组的人提议,再从缅甸请几个小和尚或佛爷来。于是,应DL、曼飞龙村小组之邀,我和DHL就结伴来这边了,一直住到现在。
案例3,景尖村YJZ访谈录:
景尖佛寺2006年开始从缅甸请僧侣。当时,佛寺里只有1个本地僧侣,为了防止佛寺空着,我们便想从外面请和尚来。但是勐龙镇其他的寺庙也缺佛爷,请不来。我们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祜巴勐。后来,祜巴勐就请来了4位缅甸小和尚,村小组的人去景龙佛寺把他们迎了回来。
事实上,缅甸籍僧侣在勐龙镇的跨境流动,给勐龙镇的边境管理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首先,勐龙镇的缅甸籍僧侣在跨境流动时,绝大多数是通过非法渠道进出边境。由于勐龙镇与缅甸掸邦第四特区之间有众多的连接通道,而第四特区政府对边境的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失控状态,单靠中国一侧的边境管理难以防控所有的进出途径。同时,如果按照合法途径进入勐龙镇,无论是通过护照还是边民证,在停留时间上都有一定的限制。这对需要在中国长期停留的僧侣而言存在诸多不便。因此,绝大多数在勐龙镇住持的缅甸籍僧侣,皆是通过小路,以偷渡的方式进入中国。其次,通过非法途径进入之后,缅甸籍僧侣在勐龙镇的居留也明显违反了境外人员出入境的相关管理政策。由于进入途径非法,因而这些缅甸籍僧侣的停留时间往往也没有限制。这些都给相关的管理工作带来问题。第三,缅甸籍僧侣的非法进入与停留,还违反了国家的相关宗教管理政策。按照1998年1月1日由云南人民政府颁布的《云南省宗教事务管理规定》第七章第二十七条规定:“宗教团体和宗教教职人员邀请国(境)外的宗教组织及宗教人士来访或者应邀出访,应当报经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同意后,再按有关规定办理报批手续。”*《云南省宗教事务管理规定》,《云南政报》1998年第3期。
尽管存在这些违反边境及宗教管理制度的问题,但由于南传佛教地区维持了很长时间的平稳交流局面,因此地方政府和民众对境外僧侣都采取一种相对宽松的默许态度。在勐龙镇各佛寺住持的缅甸籍僧侣,基本没有报经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同意,而是在当地村民的邀请下,缅甸籍僧侣非常方便地就从缅甸来到勐龙镇,并长期居留下来。
总体而言,勐龙镇缅甸籍僧侣的跨境流动的背景,是相似的宗教文化及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直接动因是中国信众的合理宗教需求,便利条件是勐龙镇与第四特区间通达的交通途径。但是,缅甸籍僧侣的非法流动与居留也违反了中国的边境与宗教管理政策,成为一个亟须面对并解决的问题。
二、缅甸籍僧侣的策略性生存
尽管缅甸籍僧侣非法进入勐龙镇并居留违反了国家的相关管理制度,但经过地方政府和村民的不断摸索,当地逐步形成了针对缅甸籍僧侣的一系列临时性管理措施,来保证确保缅甸籍僧侣的跨境流动与居留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以使得当地村民正常的宗教生活得以维持。所有进入勐龙镇的缅甸籍僧侣,都需要到景龙佛寺拜见祜巴勐。之后,由祜巴勐或者村小组的人将这些缅甸籍僧侣的相关信息上报镇佛教协会。由镇政府和镇佛教协会制作统一的花名册和联系方式,并确定相应的监管人员(一般由佛寺管理小组组长担任)。镇佛教协会还承担了对缅甸籍僧侣违法行为的监管职责,并驱逐违法或违教规的缅甸籍僧侣。勐龙镇的72座佛寺被分作6个片区。佛教协会指定片区内的1座寺庙为主管寺庙,主管寺庙的住持对该片区佛爷有教导义务。同时,依托南传佛教每半月1次的结集制度,主管寺庙的住持对缅甸籍僧侣的宗教素养等进行考核。
案例4,曼龙扣佛寺DJ访谈录:
曼龙扣佛寺主管附近7座寺庙。按照当地习俗,每半个月1个片区的佛爷会到主管寺院持戒1次。届时,主管佛寺的大佛爷会根据最近发生的事情,教导其他佛爷一段时间。如果个别佛爷出现行为不端的情况,则会单独教导。但如果佛爷所犯错误过于严重,比如偷摩托车,与村里的女性谈恋爱等,主管佛寺的佛爷会告诉村小组的负责人和祜巴勐,把犯错的和尚赶走。在这方面,缅甸佛爷和中国佛爷是一视同仁。
在被纳入到当地政府和社会的管理渠道之后,通过非法途径进入勐龙镇的缅甸籍僧侣可以暂时不用担心被遣返及受到处罚,但在日常及寺院生活中仍需面临一系列的调适。尽管勐龙镇的信众与缅甸籍僧侣为同一民族,在语言、宗教信仰等方面基本不存在差异,但由于中国与缅甸近些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使得信众与缅甸籍僧侣在饮食、居住、出行、对经济行为的理解等方面已经出现明显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缅甸籍僧侣在勐龙镇住持之后,由于社会结构的缺失,使得他们在与信众的交流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障碍,同时也使得他们缺乏以平等的地位直面信众的信心和勇气。
在社会网络缺失且需要一系列调适,尤其需要承担中国政府可能施加的惩罚措施情况下,缅甸籍僧侣流入勐龙镇的趋势并没有停止。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一方面是由于经济收益的提高,弥补了缅甸籍僧侣所面临的种种风险;另一方面是由于缅甸籍僧侣凭借与信众共同建构的拟制亲属关系,弥补了社会网络缺失所带来的心理及社会问题。
案例5,景尖村YJZ访谈录:
一般来说,信众供来的钱中有三分之一分给僧侣、三分之二留作寺院积累。分给僧侣的钱由僧侣自己支配。寺院积累的钱主要用于修缮寺庙、水电费等的开支。去年那次最为盛大的赕佛仪式结束后,僧侣分得了1万多元,寺院获得了3万多元。在僧侣分配收入时,佛爷跟小和尚是有差别的。1个佛爷1年约有80 00~10 000元的净收入,小和尚也有2 000~3 000元的收入。住持的收入则会更多一些。根据估算,寺院中缅甸籍僧侣每年所获得的收入约为他们在缅甸获得收入的5倍。
在物质基础之外,为了弥补缅甸籍僧侣社会网络缺失所带来的不稳定感及挫折感,同时也方便村民与僧侣之间的交流与管理,缅甸籍僧侣与信众共同建构了一套拟制亲属关系——即缅甸籍僧侣拜认1户村民为义父义母。
担任缅甸籍僧侣的义父义母并没有明显的身份限制,主要根据村民的自愿。义父义母需要承担的职责主要包括为缅甸籍僧侣购置僧衣、蒲扇、被褥等用品,同时邀请亲友到家中举行庆祝活动。有的义父义母还不定期给予缅甸籍僧侣一些经济补助。在寺院生活期间,缅甸籍僧侣需听从义父义母的教导。准备还俗时也要征得义父义母的同意。
案例6:僧侣PW义母YXXW访谈录:
2010年3月份,景尖村佛寺请来了第一批缅甸和尚,总共4位。其中1位便是16岁的来自勐勇曼勒村的PW。当时是第一次请国外和尚来村里,大家对此情况都不熟悉,愿意当他们干爹干妈的人还不太多。于是村干部带头“拿”了4个和尚。说“拿”是因为,他们也是通过抓阄的方式来确定谁来认谁。这批带头的村干部包括村长、村支书、出纳、佛寺管理员。村支书YXXW“拿”了PW。YXXW为认PW作干儿子总花费在5 000元左右,其中4 000元用来办酒席,1 000元用来买被褥、僧衣、日常生活用品。
案例7,景乃佛寺DZ访谈录:
我来到景乃佛寺之后,村长给我找了干爹干妈。他们都是景乃村务农的村民,50岁左右,家里有两个孩子。拜干爹干妈时,他们还宴请了亲戚朋友,花费了五六千元。他们给我买的袈裟也是泰国进口的,质量很好。
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地区,每年都要举行一次斗骆驼比赛。斗骆驼时,两头骆驼各自弯下头,用前额撑住对方,并设法用力把对方推倒在地上。当其中一头取得胜利后,主人还得竭力把它们拉开。
亲属制度是对于主观归属、安全感和个人身份的一个主要关注点。*[挪威]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小地方,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董薇译,周大鸣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59页。通过拜义父义母这一拟制亲属关系,缅甸籍僧侣正式获得当地村民的接纳和认可,获得了同当地人一样的象征性身份和地位。同时,拜认的义父义母这一拟制亲属关系,也增强了缅甸籍僧侣在同当地村民交流时的信心和勇气。通过这一拟制亲属关系,缅甸籍僧侣被正式融入到义父义母的亲属关系和社会网络中。据此,缅甸籍僧侣的亲属关系及社会网络得以在勐龙镇重新建立。义父义母不但成为他们在当地最为重要的依靠,也充当了他们重建社会及亲属网络的基础与桥梁。
案例8,僧侣PW义母YXXW访谈录:
PW拜YXXW为义母之后,隔一两天就会来到YXXW家。他会跟YXXW家人一起吃饭,然后在二楼客厅睡个午觉,起来后跟老人聊聊佛经的事就回转寺里。虽然PW很腼腆,但是可以看出他很喜欢这个家。YXXW经常在饭桌上教导他要好好念经书,学习好傣文。不管以后是继续做和尚还是还俗,学好傣文对他来说都是有益的。PW在寺里很听话,学习经文也很刻苦,很多僧侣不知道的事他都知道。PW曾经在缅甸还学过画佛像,到这边没事就画画佛像,还送过我们家一幅。PW的父母跟我家的关系也很好,我们认为自己有相同的儿子。这边有大的佛事,我会打电话邀请他们过来。他父母来了之后既是参加活动,也是来看望孩子。PW也会把他攒的部分钱拿给父母,有时候还包括金银。
案例9:景乃佛寺DZ访谈录:
我的干爹干妈家就在村子里,离佛寺很近,经常给我们买菜。每个星期我都会去干爹干妈家坐一下,聊聊家常。我来到这边两个月后,经常被请到附近村寨做佛事活动,开始都是走着去。干爹干妈知道后,就买了1辆摩托车送给我,说这样我去哪里都比较方便。
缅甸籍僧侣在勐龙镇的策略性生存,一方面得益于传统宗教文化背景下地方政府与社会针对他们的弹性管理策略;另一方面是经济收益的提高弥补了他们需要面临的一系列风险;更为重要的是,缅甸籍僧侣与村民主动建构的拟制亲属关系,提升了他们的被接受度与社会地位,也重建了他们的亲属及社会网络。
三、缅甸籍僧侣生存策略的文化根基
缅甸籍僧侣与村民主动建构的拟制亲属关系,根源于南传佛教地区普遍存在的拜义父义母习俗。拜义父义母是南传佛教地区僧侣出家及晋升仪式中必备的程序。通常而言,青少年在出家仪式中拜1户村民为义父义母。等到小和尚晋升佛爷,就可以拜好几家义父义母。如果是非常罕见的晋升“祜巴”仪式,拜的义父义母可能多达几十家。与缅甸籍僧侣拜勐龙镇村民为义父义母的仪式内容相比,南传佛教传统仪式中义父义母需要承担的职责大致相同,同样需要为出家的小和尚或晋升的佛爷购置僧衣、蒲扇、被褥等用品,并杀猪宰牛宴请宾客。在寺院生活期间,小和尚或佛爷也需听从义父义母的教导。准备还俗时也要征得义父义母的同意。一些小和尚或佛爷即使在还俗之后的很长时间也与义父义母保持了比较亲密的关系。
案例10:*资料来源于笔者2010年1~6月在勐海县勐遮镇的田野调查。
2010年4月勐海县勐遮镇曼坎赛村有1位大和尚准备晋升佛爷。这是该村近20年来首位晋升的佛爷。在正式的晋升仪式举行之前,大和尚需到各位义父义母或亲友家中进行拜访。每位义父义母都为大和尚准备了僧衣、被褥、经书等物品。大和尚每到一家,都要先念诵一段经文,以示父母大家都作为佛祖的信徒,此番行为能得到佛祖的庇佑等。之后举行沐浴金花水仪式。沐浴结束后,义父义母或亲友在家中宴请宾客。大约1个小时后,大和尚接着拜访下一家。由于需要拜访的义父义母及亲友数量众多,整个拜访过程持续了一周的时间。
南传佛教的拜义父义母,具有世俗与宗教互惠的象征意义。这是尽管承担义父义母要付出一定的花费,但村民对此仍趋之若鹜的重要原因。村民的这种行为与中国南传佛教特殊的教义与行为规范有直接的关系。中国的南传佛教是一种重仪轨轻教义的宗教。多数信众对教义的理解停留在信奉佛祖得福佑,做赕越多福佑越多的层次。*龚锐:《圣俗之间:西双版纳傣族赕佛世俗化的人类学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7页。与东南亚地区最为重视通过个人修建寺庙或出家为僧来获得功德的观念不同,*Nash,Manning,The Golden Road to Modernity,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65,p.116;Tambiah,S.J.,Buddhism and the Spirit Cults of Northeast Thaila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pp.146~147;Spiro,Melford E.,Buddhism and Society:A Great Tradition and its Burmese Vicissitudes(Second,Expanded Edi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originally 1970),p.109.勐龙镇的信众由于是集体建造寺院,并且越来越少的信众有出家为僧的意愿和行动,因此信众更多地通过以个人的名义举行一次大赕,或资助他人出家为僧来获得福佑。在当地人看来,通过承担小和尚或佛爷乃至“祜巴”义父义母的责任,可以很好地履行自己作为佛教徒的职责,在完成了世俗层面拟制亲属关系建构的同时,还可获得一份额外的福佑。
除了世俗与宗教的互惠之外,通过拜义父义母这一拟制亲属关系,来巩固或拓展社会关系和亲缘网络也是其重要意义之一。通过拟制亲属来加强社会交往与群体整合,已经得到学者的关注。*参见罗忱《高排苗族的拟制亲属与群体整合》,《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蓝希瑜《认表亲:赣南畲族拓展“社会圈子”的实践》,《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蓝希瑜《认而不亲 差而有序:赣南畲族“认表亲”研究》,《思想战线》2012年第1期。这一研究视角甚至扩展到与拟制亲属关系联系密切的拟制亲属称谓中。*参见黄涛《村落的拟亲属称谓制与“亲如一家”的村民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黄涛《村落拟亲属称谓制的社会功能》,《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6期;张立丹;张希玲《拟亲属称谓习俗的文化功能》,《边疆经济与文化》2006年第3期。在南传佛教传统仪式中,由于拜义父义母要承担较多的费用,但在宗教生活层面可得到丰厚的回报,因此部分家庭邀请血亲或姻亲担任要出家的青少年的义父义母,将拜义父义母作为加强亲缘间网络的契机。也有部分家庭邀请关系较好的朋友作为将要出家孩子的义父义母,将已有的社会关系加强为拟制亲属关系。
在传统南传佛教拜义父义母仪式中,担任出家仪式中青少年的义父义母是花费最多,也是福佑最多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出家仪式在南传佛教地区最为普遍,对于整个南传佛教地区社会的影响也最大。另一方面,在南传佛教地区男性社会化的过程中,出家的重要性也要大于晋升佛爷与“祜巴”。晋升佛爷与“祜巴”由于举行的频率相对较低,同时担任佛爷或祜巴的义父义母不止一家,每一家的花费相对于出家仪式期间的花费也较少,因此获得的福佑也较少。
尽管村民与缅甸籍僧侣共同选择拜义父义母作为缅甸籍僧侣建构社会网络的桥梁,但与缅甸籍僧侣有关的拜义父义母仪式与传统的仪式之间仍有差别。在传统的南传佛教拜义父义母仪式中,义父义母最为重要的是承担出家或晋升仪式期间的费用。一旦小和尚或佛爷正式进行寺院生活,村民的集体供养就能满足他们日常及寺院生活的基本需求。义父义母对他们的扶持就降到次要地位。同时,由于南传佛教并不强调僧侣与日常生活和原本社会网络的隔绝,加之绝大部分小和尚和佛爷最后都会走向还俗成家的道路,出家为僧只是他们社会化过程中一道通过仪礼,因此与原本的家庭和社会网络保持连接,是绝大部分南传佛教僧侣必备的功课。传统的南传佛教僧侣大多在本寨寺院出家,无论是小和尚还是佛爷都居住在父母及亲友建构的完整的社会及亲属网络中,这套网络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支持。小和尚和佛爷一旦还俗,能很快转变角色,成为这套社会及亲缘网络中的一环。通过传统仪式缔结的义父义母关系,小和尚或佛爷在还俗之后仍与义父义母保持联系。与传统仪式相比,缅甸籍僧侣由于在还俗之后大多要返回缅甸成家,因此很难与义父义母保持联系。同时,由于缅甸籍僧侣在缅甸出家时已经拜认过义父义母,因此在勐龙镇重新拜认义父义母时,能为义父义母带来的福佑就相应减少。因此村民对承担缅甸籍僧侣的义父义母责任时的重要性认识也有所降低,所付出的花费也相对较少。在勐龙镇,成为一个出家的小和尚的义父义母要花费1万元左右。与此相比,成为一个缅甸籍僧侣的义父义母的花费一般在四五千元左右。
缅甸籍僧侣拜认的义父义母,充当了他们与无形的国家政策之间的具象化象征与缓冲。非法越境并居留的缅甸籍僧侣,对中国的边境管理制度和宗教管理制度并没有一个非常明晰的认识。在建构拟制亲属关系之前,尽管他们清楚非法越境并停留违反了中国的边境管理制度,但即使被遣返,除了回缅甸一段时间之外,并不会给他们带来心理上或思想上明显的负面效果。也就是说,这些缅甸籍僧侣非法越境及停留的违法成本相对低廉,由此中国的边境管理政策对这些缅甸籍僧侣的管理效果不甚显著。但在建构起拟制亲属关系之后,义父义母成为边境管理及宗教管理制度的宣讲者和具象象征。在地方政府与缅甸籍僧侣之间,也有了一个可以承担传话员及执行者的缓冲角色。由此,缅甸籍僧侣对中国的边境管理及宗教管理制度有更加直接且清晰的认识,同时还担负起保护义父义母在当地社会形象与名声的职责。一旦这些缅甸籍僧侣发生了违反教规或违反法律的事情,他们不但要接受被遣返回缅甸的事实,还要接受义父义母在当地社会形象或名声受损的结果。这对于接受了义父义母经济资助及社会网络支持,建构起密切的亲属关系的缅甸籍僧侣而言,同样是一个难以接受的结局,需要承担心理及思想上的谴责。因此,从结果而言,拟制亲属关系,降低或避免了缅甸籍僧侣在勐龙镇境内发生违法违规事件的可能,维护了缅甸籍僧侣在当地和平流动与居留的局面。
事实上,通过拜义父义母建构起的拟制亲属关系,成为了地方政府与社会针对缅甸籍僧侣管理措施的有效补充。由此建构起的一整套地方及社会管理体系,保障了缅甸籍僧侣在勐龙镇相对稳定的生活及地位。在勐龙镇,边防部队和地方政府每年都举行针对“三非”人员的驱逐行动,但大多数僧侣能在这些政府行动中保持相对超然的地位而不受打扰。即使是在罕见的相对严格的驱逐“三非”人员的行动中,缅甸籍僧侣的被驱逐过程也相对婉转。
案例11,曼迈半佛寺DD访谈录:
勐龙镇每年都进行人口巡查。人口巡查时要求要把非法入境的外籍人员都遣返回去。但如果景洪市政府没有要求严格执行遣返决定的话,各村也不会要求本村外籍僧侣离开。如果景洪市政府要求严格执行相关决定,各村村长在遣返外籍僧侣时也往往会说:“出来这么久了,回去见见父母吧”。这样被遣返回去的僧侣约等于享受了一次探亲假期。过了一二十天,待人口巡查活动结束,这些外籍僧侣又返回中国。
拜义父义母来源于南传佛教传统文化内容,其世俗与宗教互惠的象征意义,使得其具有加强及拓展亲属及社会网络的功能。缅甸籍僧侣运用这一拟制亲属关系工具,重新建构起在中国的亲属及社会网络,为他们在勐龙镇的长期居留提供了帮助。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拟制亲属工具,丰富了勐龙镇地方政府和社会针对缅甸籍僧侣的管理方式,在刚性的政府管理制度之外添加了柔性管理措施,保证了勐龙镇缅甸籍僧侣的跨境流动与居留保持在一个稳定的局面,满足了当地信众的宗教需求。
结语
有效的边疆治理应当依据边疆问题的内容和特征,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周平:《我国的边疆与边疆治理》,《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2期。缅甸籍僧侣大量进入并长期居留在我国南传佛教地区,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常见的现象。更加合理有效的管理制度,还处于进一步探索完善中。在这方面,勐龙镇民众与缅甸籍僧侣建构的拟制亲属关系,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及社会探索出的一系列针对缅甸籍僧侣地方性管理措施的一个有效补充。如何将地方社会的传统策略转变为制度性措施,可以成为建设针对缅甸籍僧侣的政府与社会相结合的管理框架的一个有益尝试。同时,广袤的中国边疆地区的自然及人文环境、不同民族或人群的历史文化及宗教信仰、国家间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及边境管理制度等等一系列的差异,都应被纳入到国家边境管理制度制定的视野中。不同区域存在或已制定的地方化的管理措施,也应被国家管理制度充分考虑或吸纳。由此,中国的边疆治理才能切实有效,边疆地区才能保持稳定与繁荣。
(责任编辑 陈斌)
作者简介:张振伟,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云南 昆明,650091);高景,云南经济管理学院财经商贸学院讲师(云南 昆明,650106)。
基金项目: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南传佛教地区僧侣跨境流动与寺院管理创新研究” 阶段性成果(14CMZ040);云南省教育厅项目“中国南传佛教地区‘佛迹’与信众朝圣行为研究”阶段性成果(2012Y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