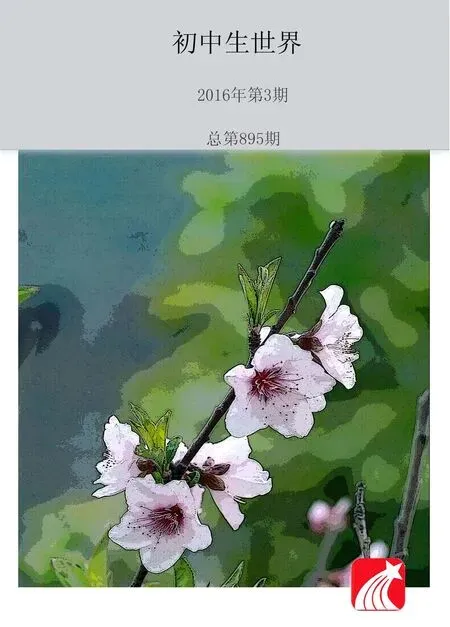燕子住哪儿去了
赵霞
燕子住哪儿去了
赵霞
父亲在清理檐下的一个燕子窠。我看见的时候,小小的泥窠已经被整个端了下来。父亲正举着一根长棍,把粘在壁上的燕泥刮干净。他的脚不时踩在泥窝下方那一摊怎么也清除不净的燕子屎的痕迹上。
我记得这个燕窝的由来。春天里,一对燕子飞到我家楼台屋檐下叽啾个不停。它们来回穿梭了不一会儿,檐角就开始粘起一小坨一小坨的泥块。父亲发现后,赶来守在檐下,拿竹竿把刚粘起的泥团一一抹掉。两只燕子衔着新泥回来,也不计较,从头开始做窠的工程。父亲的竹竿随即跟上。它们绕着竹竿头旋飞,叽啾不已,却仍是飞进飞出,锲而不舍。父亲终于拗不过它们,把檐下的占有权让给了这对燕子。
这早已不是燕子第一次选在这里做窠了。最初是在二楼的阳台,我们刚搬进新居不久的时候。敞开的阳台一角,一个燕子窠不知什么时候筑成的,里面很快就有了一窝叽喳的燕雏。母亲蛮高兴的,因为燕子做窠有着安居的好兆头。然而不久她就苦恼起来,不断落下的鸟粪在阳台水泥面上留下一大摊难以清洗的腌臜印迹。父亲遵照老法,在燕子窝正下方悬起一个方正的纸盒。可惜大燕子飞来飞去,并不十分买纸盒的账,附近的阳台地面上仍溅开着一朵朵白黑相间的屎花。
入秋时分,燕子一离开,父亲赶紧把燕窠清掉。可惜到了来年春天,也不知是不是去年的那一对鸟儿,照旧赶过来做个新窠,把这里占住。
没多久,家里阳台包了整面的合金玻璃窗,倒不是为了燕子的缘故,而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这么一来,燕子自然飞不进来了。原先清不掉的那一块粪迹,地砖一铺,干干净净的。
第二年,二楼阳台是清净了,一楼的檐下却迎来了又一对燕子。同样的一幕于是再度上演。父亲和燕子各不退让,这样的相持,成了若干年春秋季里的时节定例。
我想起小时候,燕子做窠都是直入人家屋里。那时的老屋平顶无一例外地排着一棱棱黝黑的横梁;横梁上必定有几枚长钉,用作拴系铁钩悬挂咸鱼、饭篮及其他生活用具。燕子来时,往往选定其中一根带长钉的梁柱衔泥做窠,因为有了铁钉的支撑,做成的燕窠牢固而结实,这和人类做房子起大梁应是一个道理。一个燕窠做成后,年年春天都有燕子来占窠,据说往往还是最初的那一对。燕子是农人的伙伴,燕窠则有安家的好寓意,老辈人对它们的到访习以为常。只有一桩麻烦:它们住在窠里,时常撅起燕尾,随地“出恭”。大人们对噼啪落下的燕子屎并不十分介意。略考究些的人家,会在燕窠旁加钉一两枚小钉,拴上一方接秽的木板,但成效总是有限。家家推门进去,先看见堂屋地面中央一堆燕屎的印迹,这成了记忆里老屋天然的一部分。
燕子喜欢向阳而敞亮的人家。我家老屋门开在巷子偏深处,又比别家多个转折,它们便不大乐意造访。只有一年,一只大燕子不知怎么盘旋进家门,在横梁下徘徊良久。我盼望着它在这里安下家来。可惜它只绕了一绕,又飞走了。
我因此格外羡慕家里有燕窠的小伙伴,燕子做窠的时节,也爱窜到别家去溜达观望。这份羡慕,有一多半是因为小燕子的缘故。大燕子在燕窠里住下不多久,小燕子就出世了,叽叽地聒噪不已。那些不时露出在燕窠边缘的扁而嫩黄的小燕喙,在小人看来是件很奇妙的事情。我们常踮起脚努力引颈张望,想凭着探出来的燕喙或燕尾弄清小燕子的个数。大燕子飞回来了,每个小燕的脖子都伸得老长,叽叽地叫唤着抢食,我们也紧张地数着。听见“啪”的一声,一坨燕子屎落下来,好像是大燕子在表示它的不满。
偶尔,有羽毛未长全的小燕从窠里掉出来,不知是跌落还是挤落。大人见了就扔,我们会偷偷地养起来,拿小虫子喂它,但总是喂不进去。可能是摔伤了的缘故,过不多久,它就死了。我和几个要好的伙伴养过一只小燕子,用绵软的蚕豆衣给它铺床,掰开燕喙喂它。第二天,小燕子就死去了。我们拿花瓣裹着它,在天井里给它起了一个土冢。
但父母们不许小孩子玩燕子,据说摸过燕子羽毛会生一种可怕的燕疮。这种燕疮,我从没见人得过,但它的名称对小时的我们颇有震慑的作用。因为害怕得燕疮,我们从不敢像捉麻雀那样去捉燕子,每次偷偷喂过小燕子,都要跑到河边努力地洗手。现在想来,有关燕疮的告诫,可能是农人流传下来的保护家燕的一种方法。
20世纪90年代初,村子里旧式的老屋纷纷拆建,翻成新式的厦台屋。一些人家的子女自立门户后,嫌老屋式样古旧且不耐冷热,也愿意新造厦台。新屋的平层是钢筋水泥的材料,不再有裸露的梁柱,只有粉砌的平顶。燕子不适应这突然的变化,起初还想缘着平顶中央垂下的灯线做窠。这在主人家自是不允许的。此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老屋的时代,白天不管有人没人,家家的大门总是敞开着,只把半高的木腰门一阖,既亮堂,又通风。有时人一早出门,晚上才回来,就把内室的门用锁拴上,堂屋照样开着。燕子飞进飞出,不受一点儿阻碍。换成厦台屋后,一律是紧闭的高门,人一离家便阖上,燕子也不得入。
千百年来,燕子头一次被逐出了家门。但它们还惦着这热闹温暖的居所,于是退而求其次,迁居到了屋门外的檐下。没有长钉,就选一个壁角,缘着一角三边的力道,继续衔泥做窠。
但檐下也渐渐容不下它们了。老旧的砖屋换成厦台屋后,楼上楼下的水泥檐壁也成了各家的私人地盘,主人家耐不住燕屎的肮脏,不大乐意这些鸟再来筑窠。不知情的燕子飞来,才衔了几口泥,就被赶走了。但它们也不气馁,有时主人家一不注意,燕窠已经筑成,按老人的讲法,此时端掉未免罪过,只好等入秋燕子飞走后再除。然而不久,新屋敞开的阳台一律包起了金属框的玻璃窗,外墙又陆续贴上光滑的瓷砖。这些新材料不像粗糙的水泥面那样耐得住燕窠的粘力,这么一来,屋外的墙角檐头也不再宜于燕子落脚。一个个燕窠从檐下被铲落,从此再没有出现在这里。
过去那么多燕子,现在都住哪儿去了?我忍不住替燕子们担忧,于是专门去查燕子的习性,知道它们除了在人家屋檐下做窠,也会在树洞和沙岸钻穴。难怪屋里屋外的燕窠被除落后,每年春天,照例可以看见停在电线杆上的一排燕子的身影。
只是,这还是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些燕子吗?我想象着很久以前的某一天,这些喜爱与人类同居的鸟儿从野外迁居到了人家屋檐下,继而登堂筑窠,成了这屋里的另一半居客。古往今来,一代代燕子与人同起而作、同室而栖。许多年后,这些热爱人间生活的燕子又被人们从屋里逐到屋外,最后重新回到旷野。燕子和人类之间绵延千百年的家的联结,从此中断了。
然而,失去家园的不只是燕子吧。在告别燕子的时候,我们也丢失了一个和燕子共居的家,一种有燕子来分享的生活。不知道这该是燕子的悲哀还是人的悲哀。
(选自2015年第1-2期《美文精粹》,本刊有改动)
鉴赏空间
《呼兰河传(节选)》中,萧红用细腻传神的描写、超凡脱俗的想象、新颖别致的比拟和清新活泼、率真自然的语言,回忆了自己童年时在祖父的后花园里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天真欢乐的生活,表现了亲近自然的幸福与快乐,寄托了对故乡的怀念以及对自由纯真生活的向往。在这美丽的后花园里,花果鸟虫都成了“我”最亲密的伙伴,人与自然就这么和谐友好地融合成一幅令人怦然心动的温馨画卷。
本文则将旧时人们对燕窠的珍视、对燕子的爱护和现在对燕窠的“清剿”、对燕子有意无意的“驱逐”相对比,在回味以前燕子给人们带来幸福感的同时,认真思索了这样的问题:人类在追求更高质量的现代生活的同时,该如何和大自然和谐相处呢?
现代生活步步高,这本来无可厚非;而人与自然更好地友好共存,更是现代文明的应有之义,因为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读有所思]
你如何看待文中的父亲清理檐下的燕子窠的行为?你认为怎样做才合适?(蒋光红/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