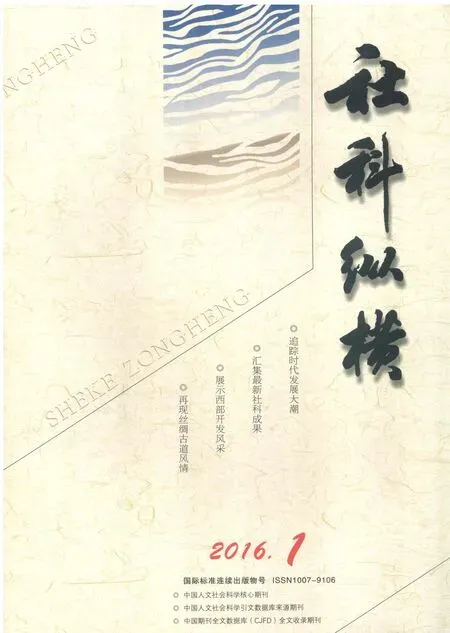浅论清政府选择广州作为“一口通商”口岸城市的动因
邢甲志(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50)
浅论清政府选择广州作为“一口通商”口岸城市的动因
邢甲志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广东广州510050)
【内容摘要】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下令关闭了闽、浙、江三处口岸,独留广州一口对外通商。此后一直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五口通商”时止,广州成为近代以前中国大陆惟一开放的口岸和中西交往的前沿。乾隆帝在四个通商口岸中选择广州作为一口通商的口岸城市,究其原因,除了当时广州的中外贸易兴盛外,还在于其他三个口岸已形同虚设,众多因素的合力作用导致广州口岸脱颖而出。
【关键词】广州粤海关一口通商口岸城市
清朝初年,为了防范郑成功等抗清势力卷土重来,巩固刚建立不久的满洲贵族政权,清政府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中国南海的海上贸易受到沉重打击,统治者的赋税收入大幅度下降,同时也激起了沿海人民的激烈反抗。在平定台湾之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正式停止海禁,翌年在广州设立粤海关,在福建厦门设立闽海关,在浙江宁波设立浙海关,在江苏松江设立江海关,作为外国商船来华贸易的指定地点,后人将其称之为“四口通商”。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为抑制外商向北方港口扩大贸易的企图,遂将对西方贸易限于广州,特许广州作为中国惟一合法的海上对外贸易口岸,即所谓的“一口通商”,它的一系列管理制度被称为“广州制度”(Canton System),[1]一口通商所施及的特定对象为“外洋红毛等国番船、番商”,而对于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等东洋、南洋诸国,则不在此限,且中国商人仍可由四海关出海贸易。[2]此后,包括以中西贸易为主的涉外活动,主要在广州这一个口岸进行,“广州制度”一直延续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规定“五口通商”时止,广州独领中西贸易风骚85年。在这段时间里,广州成为西方人唯一可以进入和从事贸易的中国口岸,也成为古老中国大门紧闭后的唯一窗口和欧风美雨进入中国的唯一通道。
清政府对于“一口通商”口岸城市的选定至关重要。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在海外贸易蓬勃发展的时候,走向全盛的清政府为什么要对西方世界关闭其他口岸,仅留粤海一关对外通商呢?[3](P21)广州何以能担当独口通商的重任?对这些问题,有关论著虽有涉及,但无专门探讨。而这些问题对于管窥清政府在进行重大决策之际对各种因素的考量,以及深层次认识广州在当时的历史地位、中外商贸交流及政府财政收入等都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笔者通过对相关档案资料、学者著述及报刊等史料的梳理,试作一探析,尚祈学界教正。
一、广州作为中外商贸文化交流中心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
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沿海对外贸易历史源远流长,广州具有悠久的开放传统和“千年外贸港市”的美誉,是历史最长的口岸城市,这是由历史、机遇、地理位置决定的,也是由天时、地利以及人的因素共同造就的。
1.广州地理位置优越。广东远离中央政府心脏,历来是华洋杂处之区。广州地处广东省中南部,南海之滨的珠江口,珠江三角洲北缘,为西江、北江、东江三江汇合处,中国的第三大河——珠江从广州市中心穿流而过,中国南方最大的海滨城市和商业市场。[4]自古以来就是中外海上贸易的枢纽,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门户。
2.广州对外贸易历史悠久。广州古称番禺,是一座具有两千多年悠久对外交往史的城市,一直是中国华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广州就是热带珍贵特产的集散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秦汉时期(约公元前226—公元220年),广州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就与海外交往频繁。[4]到唐宋时期,广州已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东方大港,并首设全国第一个管理外贸事务的机构——市舶司,总管对外贸易。另外还有“蕃坊”,供外国商人居住。从五代到北宋,广州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和通商口岸,贸易额占全国98%以上。到了元代(约公元1206—1368年),世界上同广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与地区有140多个。至明代(约公元1368—1644年),广州便有了“出口商品交易会”。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在广州设立粤海关,作为管理对外贸易的行政管理机构,其任务是管理外贸及征收关税,这是中国政府最早设立的海关,[4]它标志着自唐代以来一千多年的市舶制度的终结和近代海关制度的创始。[5]
3.广州具有独特的外贸优势。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政府将对外贸易的商人从牙行中分离出来,招募了十三家较有实力的牙行经纪人,指定他们与到达黄埔港的外国商船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始称“广东十三行”。在十三行设立的“洋货行”,被认为是外贸组织建立的标志。[6]十三行是清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广州以对外洋船出口为主体的对外贸易,操作专业、环境宽松、贸易规模巨大。从此,随着十三行进出口的贸易额节节增长,“广州十三行”进入全盛时期,广州成为清代对外贸易中心。[6]
4.广州港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其贸易对象遍及全球。在中国许多的外贸港市中,有的虽然开港很早,但很快就衰落了;有的有着全国地位的大港,却是开港较迟的;只有广州开港最早,并一直保持着国内第一流的大港的地位。[7]得天独厚的人文地理优势,使传统的海外贸易中心广州,成为清朝开关后西方商船首选的黄金口岸,形成了固定的贸易路线和通商惯例。广州黄埔港洋船云集,商贾辐辏,这里拥有通往世界各主要港口的环球贸易航线,贸易对象遍及全球。
二、保持沿海统治的安定,维护稳定的政治局面
海防条件是当朝天子决策时首先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虎门海口是洋船进入广州的要塞,这里有“金锁铜关”的天险,这种地势决定了其最有利于凭险防守。虎门至广州的中途港黄埔,是从水路抵达广州的必经之路,这里多沙淤水浅之处,没有中国引水员带领,洋船难以自由进出。虎门至广州的这条水路,被称为通海夷道,处处有官兵设防。而浙江的宁波、定海口岸,其地势却是海面辽阔,无险可守,洋船杨帆就可直达腹地。浙江是华夏文明礼教重地,岂能成为洋人的集市。清政府不希望带有殖民主义背景的西方商人逼近京师重地和江南漕运财富中心。[3](P34)因此,乾隆在上谕中说“虎门、黄埔在在设有官兵,较之宁波之可以扬帆直至者形势亦异。闽浙向非洋船聚集之所,海防亦得肃清。”[8]在清政府看来,粤海关的地利与防务已具备应付西方商船的能力。因为洋人要进入广州,必经虎门和黄埔等要塞,官府在此可监视洋人及其船舶,而宁波、厦门、上海等北方口岸比广州更靠海,官府很难控制洋船的行动。所以,从海防的角度说,广州比其他沿海口岸更具安全优势。
洋商北上威胁到清政府统治是其考虑的另一重要因素。18世纪中叶,由康熙帝开创的四口通商局面已经走过了70余年,前来进行贸易与投机的外国商人日益增多,尤其是当时的英国商人不断派船到宁波、定海一带活动,就近购买当地的丝、茶等商品。乾隆皇帝在江南巡游期间,亲眼目睹了在江浙一带海面上,携带着武器的外国商船络绎不绝。英船忽然闯入海滨要地,引起了乾隆乃至整个中央政府的巨大震动。时任闽浙总督杨应琚向乾隆帝奏报,洋船高大如屋来去无常,尤其是船上装载炮械,云集天朝商港,这对于沿海清军水师是个巨大的威胁。[3](P23)在清朝海疆大臣看来,海防的宁静高于一切。这种形势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认为江浙是华夏文物礼教之乡,而且物产富庶,如果让外国势力打进去,会对其统治不利。
采取措施管制外商活动是其必然选择。为了进一步防范外商与国人交往,两广总督李侍尧于1759年提出《防范外夷规条》,经乾隆皇帝批准,成为清政府第一个全面管制外商的正式章程,规定不许外国商人直接同中国百姓和官吏随便接触,外商纳税、向清政府呈递禀书均由行商代办,外商在广州居住和活动也由行商负责监督。[9]除广州外,沿海各地实行禁海。至此,中西方所有的商贸和政治、文化交流,瞬间便集中到了广州一地。[10]
三、基于宫廷财源的考量
设在广州的粤海关在乾隆帝的心目中具有特殊地位,它可为宫廷提供可观的财源。乾隆时期,户部每年向内务府拨款60余万两,但这并不能满足皇室庞大的消费,粤海关成为皇家“自筹资金”的重要途径之一。粤海关大把的关税收入,源源不断地进入皇帝个人的“小金库”。在乾隆朝的奏折中,关于贸易情形的报告,几乎成为粤海关的一项专利。由于是皇室经费所系,就连粤海关每年到港的洋船数目,皇帝都要亲自过问。根据清宫关税档案记载,粤海关每年的税银有3%移交广东布政司藩库;3%留作海关之用;70%解交户部;24%划归宫廷内务府。[3](P41)粤海关有自成独立的系统为宫禁服务,支持着皇室财政的运转,它好像皇帝身边的一个秘密口袋,为内库聚敛财富和支付费用。厚利招来了皇权的格外青睐,以至于皇帝对粤海关的管理充满了家族的意识。粤海关的巨额税收,是皇家内务府的重要财源,而内务府恰恰是负责皇家宫廷生活的,正因为这样,作为粤海关最高官员海关监督,历来都是由皇帝的心腹出任,其地位与行省督抚大员相等,不受督抚节制,直接向皇帝和户部负责。四海关中,只有粤海关是皇帝钦定海关监督专管,而闽、浙、江三海关皆由地方官吏兼管。可以说,粤海关的税收和财务直接牵动着宫廷生活命脉。粤海关有如此突出的地位和特殊的作用,统治者在制定贸易政策上的倾向和取舍也就不言而喻了。
广州为皇家提供大量的珍奇洋货。来自广州的洋货贡品,为宫廷带来前所未见的奇巧玩物,增添了许多奢侈与消闲。清代帝王的生活无不奢靡铺张,皇帝及其家人“集天下物用,享人间富贵”,是天朝财富最大的消费者。地方大吏每逢节庆时节,都要进献当地物产给天子,以博取皇帝的欢心,这在清代实际已衍生成一种制度。广东被誉为“金山珠海”,是皇家的“天子南库”。皇帝后妃对舶来品的特殊欲望,极大地刺激了广东督抚、粤海关监督依靠十三行这一洋货市场竞相采购进口货之风,从而带来宫廷内的洋货热。不遗余力地效犬马之劳,为天子办理内廷供应成了粤海关的重要职责。翻阅清宫进单、贡档,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在全国各地的贡品中,广东的洋货是最有特色的。乾隆年间,十三行每年进口洋货上千件,其中有一半左右是由广东官员作为贡品送入皇宫。[3](P38)送入宫内的一些珍奇之物,价值连城,数目惊人,皇室的胃口也越来越大。粤海关以稀世珍宝和舶来洋货报效献纳,结欢于皇帝,同时也要无休止地接受圣上的御差。[3](P38)可见,粤海关、广州洋行与宫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的存在直接牵动着皇帝个人的生活。
四、四口通商有名无实,中外贸易实际上一直集中在广州
四海关贸易时期,大致形成了这样的格局:设在松江的江海关,主要对国内沿海各港贸易;设在宁波的浙海关,主要对日本贸易;设在厦门的闽海关,主要对南洋各国贸易;设在广州的粤海关,垄断了对西方各国的贸易。[3](P32)广州在管理与通商制度方面,凭借自身各种优势,造成一口通商的事实。[11]早在17世纪时,小规模的通商是在许多地点进行的,但是却有集中广州的倾向。英国在福州的商馆时开时闭,1700年前往定海开辟商馆失败。广州贸易条件优越,英国便逐渐放弃其他商馆,将贸易中心移至广州。其他西方国家也效仿英国,把贸易重点转移到广州,这样中西贸易已成一口之势。[11]相比沿海其他开放的口岸:浙江宁波海岸滩浅水急,不适宜进行大规模海洋贸易;浙江舟山和福建厦门都不是理想的大贸易市场,因为这里的商人普遍缺乏资金,与他们完成订货要五六个月,而在广州通常是三四个月。经过多方对比权衡,英国的商人们认为,广州是世界上通商条件最好的口岸之一,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3](P12-13)。
从康熙年以来,表面上看是四口通商,实际上中西贸易一直集中在广州。从四海关的外国船只到关数量以及税收看,粤海关与浙海关、闽海关、江海关相差悬殊。因此,清政府停止其他三个海关“有名无实”的对外职能,只启用广州的粤海关作为对外通商的口岸,无论就政治成本还是经济成本而言,都是合算的,也是合乎情理的。[12]西方世界研究中西关系史的奠基人,在中国海关长期工作过的美国人马士编著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给我们提供了广州通商时期的第一手资料。根据书中开列的《英船到华数目统计表》看,从1685年康熙开海,到四港通商结束前的175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到中国各口岸的商船共计189只。[3](P32)其中粤海关有157只,占总数的83%;厦门17只,占总数的9%;舟山15只,占总数的8%;江海关无英船到达。其中1737年至1753年这16年间,英船进口全在广州。说明四海关开放时期,主要的对外贸易集中在粤海关,其他三处仅是陪衬。[3](P32)
五、结语
综上所述,清政府之所以选择广州作为“一口通商”的口岸城市,是由当时各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政治上,由于清政府是满洲贵族以少数人统治大多数的汉族人,他们既害怕人民的反抗斗争,又害怕人民联合海外势力颠覆其政权。出于对西方国家殖民侵略的戒备心理,清政府实施一口通商政策实际上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对外来势力所采取的一种本能的戒备和排斥,毕竟外国商船的纷至沓来为清政府平添了无穷的忧虑,广州一口通商既顾内忧,兼防外患,稳固统治。经济上,广州的对外贸易有“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之称。粤海关的巨额收益,又直接牵动着宫廷生活命脉。从人文的角度看,广州拥有当时成熟的洋行制度和经商人才,足以承担国家对外贸易的重任,这是其他口岸所无法企及的。[3](P32)地理上,广州距离北京更遥远,即便发生洋人骚乱等威胁清政府统治的不测事件,控制起来也比其他三个口岸更容易些。在广州实施一口通商,还能够使中外贸易更加规范化、制度化,也易于政府对外统一管理。[13]一言以蔽之,众多因素的合力导致清朝统治者在选择一口通商的口岸城市时,广州便成为其不二选择。
参考文献:
[1]李庆新:历史视野下的广东与海上丝绸之路[J].新经济,2014(06).
[2]段玉芳:1757年“一口通商令”形成原因的综述[J].前沿,2013(20).
[3]李国荣:帝国商行:广州十三行[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
[4]邢甲志:浅论英国选择广州、上海等五城市作为通商口岸的动因[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3).
[5]徐桑奕:明清时期中央政权南海管制式微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J].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4(06).
[6]杨荷卿,言民:十三行——见证广州“千年商都”,亚太经济时报第1767期[N].2006- 09- 25.
[7]李大华,周翠玲:广州的深度组合[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
[8]《清高宗实录》卷五五○,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戊戌.
[9]倪月菊:洪仁辉与“一口通商”[J].中国海关,2010(12). [10]石大泱:粤海关档案记忆旧中国外贸沧桑[J].山西档案,2008(01).
[11]徐映奇:清代闭关锁国政策新论[J].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01).
[12]廖声丰:乾隆实施“一口通商”政策的原因[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03).
[13]周正庆:清代的一口通商及此间的对外贸易问题[J].历史教学,2000(06).
*作者简介:邢甲志(1967—),男,广东社会科学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 9106(2016)01- 0096- 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