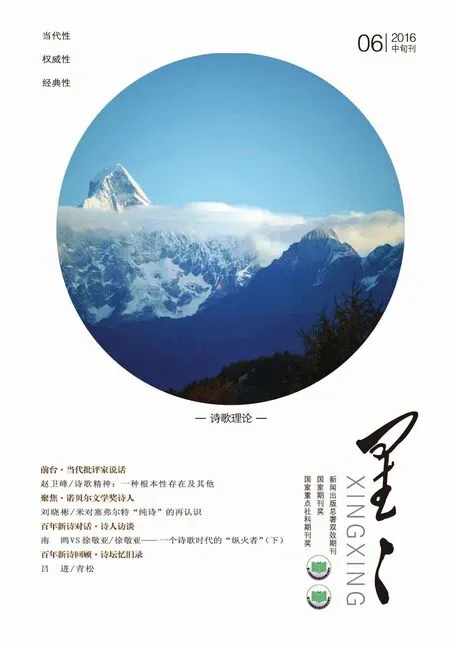雅努斯之门
孔育新
雅努斯之门
孔育新
雅努斯是尽职的门神,清晨开启,阳光朗照,晚上关闭,夜如澄湖。后来,雅努斯管辖所有大小门户乃至过道,掌管一切开端和终结,由此它长着两幅面孔,一张环视过往,一张神往未来。突然,雅努斯忧伤起来,因为它只在时间的节点出现,却进入不了时间……
“我信这世界终将敞开,如最初的一日。”时间的缝隙,未来的窄门,拘厄于世界川流之逼仄的灵魂,凭信阳光之芒突围,渴仰着天堂之门的开启。世界依然黯淡,沐浴于阳光之下的黯淡,家园依然辉煌,漂升于暗渊之上的辉煌,带着太阳烙印记忆的洄游之旅,悲怆而又虚无。于弥留之际莅临的救恩,言说着尘世的凋敝,也言说着拯救吊诡的喑哑。时间的绽开与收束,神秘而突兀,有如天启,然而没有绵延,也没有繁衍。雅努斯站在那里,转动着门枢,转换着两副面孔,雅努斯只是一个门神,它和门融为一体。
《院子里的小野花》已经开败了,低垂的花瓣如经历与母亲吵嘴之后垂泪的孩子。傲娇的孩子(抑或花儿)肆意挥霍着青春,并以为可以继续肆意下去,然而死亡老练地蕴藏于花儿(抑或孩子)的怒放中,并给予突然袭击。孩子(抑或花儿)在眼泪中洞悉和体验着雅努斯的悖谬,突感着花儿一样的青春——抑或或青春一样的花儿——之不可依恃,只好在青春的伤逝中领受、反思着命运,寻找新的依存。向死而生,诚如海德格尔所言,面对死亡之悬临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面对只有一次的生存,剥落所有的虚骄、沉湎,脱却日常世界的羁绊,围绕虚灵自身自由旋舞。时间已经成熟,花开就盛大地开,花落就缤纷地落,不离不弃,不粘不滞。
“既然觉者如释尊告诉我们生老病死是轮回的巨流,既然饕者如浮士德都不能让美好的时光停留一刻,既然那个早夭的酒鬼克鲁亚克曾经喊过:‘永远在路上’,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变老之前远去呢?”浪子马骅于冰川脚下的明永村(藏语愿意为明镜台)驻足,面壁雪山,凝思而成空灵通透的《雪山短歌》。“上个月那块鱼鳞云从雪山的背面/回来了,带来桃花需要的粉红,青稞需要的绿”。天现鱼鳞云,不雨风也颠,四季开始了新的轮转,然而与“我”无关。“我”渴求爱情降临,渴望精神的交流与慰藉,渴望命运的突转,渴望新的未来。雅努斯开启了春天之门,却只有自然的量度,没有预约的救恩,在桃花红、青稞绿、孩子闹的春天,“我”的精神世界晦暗如常,孤独如昨。没有灵性吹拂、没有未来召领的喧腾世界,“有点鲜艳,有点脏”。“我”爱的是什么?“我爱的不是白,也不是绿,是山顶上被云脚所掩盖的的透明和虚无”。
“除了你以外,谁也不能得到允许走进这道门,因为这道门是专为你而开的。现在我要去把它关上了。”在卡夫卡小说《审判》中教士讲给K的寓言里,守门人忧伤地关闭了乡下人的律法之门,正直的守门人如正直的雅努斯,然而他又是暴躁和忧伤的雅努斯。他不断地提醒乡下人可以无视他的阻挠而进入(尽管他也说现在不能进入),他和乡下人盘桓终老,一直等待着乡下人的成长和顿悟,而律法之门一直洞开。乡下人比他幸运得多,临终看到法的大门里射出来源源不断的光线,守门人却作为法的忠实门徒,没有自由,他因职责所困而无缘窥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雅努斯之门,但大多数却摆脱不了自我招致的愚昧,没有勇气独立开启。要敢于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康德的启蒙之音破空而来。《我信》追忆着太初的永恒澄明,试图呼唤、叩响着一千重门外的雅努斯之门,然而没有道路,只有深渊;《院子里的小野花》在雅努斯关门的冷漠中,在悲伤垂泪中经验着生死有道的命运;《乡村教师》中乡村场域和教师视野发生着内在的分裂,孤零零的“异乡人”在而不属于这野花缭乱的世界,他洞悉着雅努斯之门的透明与虚无,以及透明和虚无背后的热切召唤:打开!进去!
忧伤的雅努斯,依然尽职地守门,阳光依然朗照,夜色依然如湖。忧伤的雅努斯,想把钥匙交到每个人手里。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根据课文《乡下人家》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