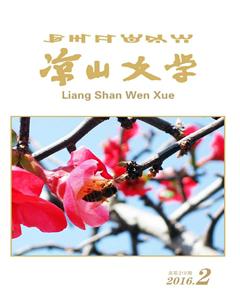在乡下教书的日子
周书华
从小生活在山里,对大山的黑暗和孤独,山里的夜晚、雷电、泥泞,乃至它的雄伟、险峻组成的道道重叠的屏障,都会给生于此长于此的人以无法回避的不安和忐忑,这种感受会让人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未来和前途……而那时唯一的愿望就是向往能翻过眼前的大山,站在山顶上看看山外到底是什么样的。
晃眼已是中年,身居闹市的我,却又总是在向往回到大山。或许每一个人都可能看到自己的世界。每一个时刻都可能重新发现世界。在生活的过程中,我们回想过往,总会发现自己在人生的路途上遗失了许许多多的美好......
当我们努力地去记忆一些东西的时候,很多东西也就真正地成了储存在内心深处的文档,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一人翻出来看看,读读,慢慢品味,品味这有点忧伤的美,享受这份轻轻惆怅,淡淡的自足。
一
贫穷的小村子给了我生命,抚育我成长,让我度过了既困苦又快乐的时光;也是这里的落后和贫瘠,决定了我以后的生活轨迹。为了跳出“农门”,用知识改变命运,十四岁那年,我第一次远离父母,到镇上的住读学校读书。我用父母辛勤劳作给我换来的生活费触摸着小镇的肌肤。这座小镇的冷漠和陌生,给我留下太多饥饿的感觉,所以我很矛盾也很迷茫地盼着早日回到村里,或许只有回到村里,那种饥饿的感觉才能被父辈的沉稳充实一些。
1995年,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着实为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困惑,不知道自己将走向何方。就这样混沌焦灼的熬煎着,陪着父母下地干农活,清理田间的杂草。直到有一天,在村里任村支书的父亲对我说,离家不远的小学校里缺一名语文代课老师,校长听说我刚下学回来,每月80元工资,问我愿不愿意去试试,我听了以后,说去看看吧。
来到学校,接待我的校长比我年长几岁,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挺斯文随和的。大概是自己总觉得在家里憋苦的熬着还不如换一个环境,让自己好好地思考一下下一步该怎么走出去吧。就这样,我成为了一名临时的乡村教师,学校安排我教四年级学生的语文课。那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吹到我们这个信息闭塞的小山村,胆大的一部分年轻人带着美好的梦想去了广东深圳,而我,却留在了村子里,让脚步每天去丈量去学校路途的宽度和坡度,做了一个“孩子王”。
二
学校是解放时期政府没收当地一唐姓乡绅的宅院,典型的江南四合天井的屋子。因考虑到办学教室太少,政府又在四合天井的一边再修建了一圈石木结构的瓦屋,便成了当地最好的小学。学校四周绿树成荫、环境宜人。校门前有一棵几个大人才能合围的皂荚树,西侧有一棵高大的青檀树,上面有好几个鸟儿休憩的巢……
当时隔6年后再次回到这里教书时,还是没什么变化。校舍依旧,只不过是换了许多比我稍长或同龄的人而已。这些人里面有我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都是年轻富有想象力的一群年轻人,所以相互之间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教山里孩子的语文课,感觉还是比较轻松。那年我19岁,年轻充满活力,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劲儿。不像后来,当生活的画卷在我面前一一展开时,才发现生活原本不过如此,远没有我想象的美好。当老师是很辛苦的,成天和一帮不想读书的山里孩子打交道,有时要走崎岖山路去学生家里家访、批改作业还要备课,生活单调也很乏味,每天见到的只是巴掌大的一块天,很少有令人激动的事情发生。
放学后无事可作,就和同事喝酒,拼命作践自己。成长是一部青涩的青春孤独史。青春仿佛是一张皱巴巴的废纸被我随意丢在风中。用一个词可以形容这段灰色的生活经历,那就是迷失,深深的迷失。晚上我躺在黑漆漆的房间里,听着窗外的小河里的流水无声无息向着远方流去,心里说不出的迷茫痛。远方,只能留在失眠人的梦想里。那时候,我唯一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走出山村,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去工作和学习,哪怕是短暂离开也好,我在山村已经呆腻了,感觉非常憋闷。我郁郁寡欢地活着,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消磨光阴。我一生中最值得珍视的青春岁月,都在用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和周围的人事对抗,结果是弄得自己身心疲惫,越发感觉人生没有多大意义。我后来逐渐意识到这样下去异常危险,就试着改变自己的人生观,可深入骨子里的东西不是说改就能改变的。多年来我一直试图从文字中去发现自己,找到自己,让迷失的灵魂回归体内。在经历了一段长长的苦涩生活后,我开始拿起笔来,零零星星地记下自己的感受,并从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保持内心的宁静。虽然我没有写出令人满意的东西,我想只要有梦想就努力去追求,总有实现的那一天!不管是在过去、现在抑或是将来,我都希望自己能勇敢的写下去,让文字成为心灵栖息的地方。
三
处于青春激扬的年龄,对外界充满了向往。当面对自己所处的现状时,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我开始让自己安静下来,慢慢地品味这种属于只有自己才能体味到的一种苦涩又有些落寞的生活;每天看着高耸入云的九台山,心早就飞过山顶,飞过山巅的那一片云朵,谁也不能感受到我内心的彷徨和苦闷。日子在这海拔800余米的村落里,展现出了它亲和力的一面;山村的阳光很明媚,大山的空气很清新,大山上的映山红花儿开得红艳艳,乡村的鸟叫声很自然;口干时,就地采一片叶子随便在身旁找个甘甜的井泉舀上一口,那水也是清醇香甜的;如果从学校到回家的路让你的脚步感觉很累,就随意找块石头坐下,绝对不会在你衣衫上留下任何污迹;缕缕微风掠过,带来了花香,带走了一路的辛劳,那些自上而下的溪流声让人心神舒畅,那一缕缕从树叶间遗落下来的阳光,让人神清气爽,心驰久远……
乡村的根生长在很远的地方,在秋冬季节,村子是属于飘渺的云雾和雨丝的,所以村子里的人和事也像这缥缈的雨雾一样,拥有的只是飘渺的希望。从小就在云雾雨丝里长大的我,对云雾和雨丝是很有感情的,因此,我特别喜欢乡村那充满希望和生机的春天。
因为是山区,没有厂矿,没有化工厂,所以乡村的天空蓝得没有任何悬念,云朵也是纯洁的,一如这里的人。村子周围群山环抱,夏天的乡村,有如铺上了一层绿毯子,草绒中有点点野花,虽不芳香,不娇柔,但也很漂亮。草地间,有很多被当地人称为“地瓜儿”的小粒野果,像草莓,虽然它只是很卑微地生长在河沟边、田坎上,但比草莓更加珍贵,因为只有生活在这里的人、到过这里的人才能一睹它的风姿,才能一品它的甜美;走出大山,就别想再能遇到它,它属于大山,属于那片美丽的土地!山路的两边,常常有叫做“刺泡儿”的矮小灌木丛,上面结满果子,到了春末夏初,满树的小果子便红了,那些是可以吃的。在没有毛毛细雨的午后,可以躺在“刺泡儿”树下的草地上,腹中饥饿时便翻身一颗“刺泡儿”,翻身一把“地瓜儿”,再看看《今古传奇》的杂志、或者是《书剑恩仇录》的小说,其实日子过得也十分潇洒恬然。
不远处的坡地上,不时会有牛羊马的影子在眼前移动,它们是安静悠闲的。站在山顶看远处的山,一座山顶连着另一座山顶,总是看不到山的尽头,眼界就无比的开阔,心绪就无比地酣畅。
教书的日子里,我们几位都是单身汉的老师在上自然课的时候,带着各自班上的学生,爬上学校后面的山岗上眺望山下热闹的集镇,想象集镇的喧嚣和闹热。一路上,歌声、林间的鸟叫声、虫鸣声,以及放牛娃的吆喝声,会淹没我们的惆怅及孤独,如一丝清风掠过心坎儿,一切都是美好的。这时,我们是快乐的。
山里人淳朴,每到杀年猪时都会接自己孩子的老师去吃饭,以表示对老师的尊敬。席间,喜欢喝一种用包谷酿造的酒,老师和家长之间没有拘束,没有间隙,任凭这种液体把烦恼和心中的苦闷麻醉,让日子模糊成充满激情的歌声;那些歌声在山与山之间回荡,然后把人带到遥远的地方……
就这样,从走上讲台那刻起,我便学会了喝酒。
兴许,把歌声传到远方的人永远没有离开,也永远不可能离开;而离开了的人却用另一种心声,把自己永远地留在了那里,即使在很多年以后,他的叶子和根都化为了一把泥土散落在他乡!
四
那是山里的最冷的一个冬天。寒冷的日子收缩着白昼毛绒绒的边缘,把黄昏散落成一堆空寂而无聊的核桃皮,那遗留着变了色果皮的皱摺里,被风填满了怨恨。那悲愤满腔的风一路奔跑一路哭泣,眼泪化做屋檐下一串串锋利的冰凌,在渐渐生起的暮蔼中闪着理智的柔光。光秃秃的杨树上,最后一片枯叶带着对天空的眷恋,飘然落在褐色的土地上,开始了生命的升华。
在冬天无聊的日子里,我透过玻璃对着一棵杨槐树发呆。杨树长在操场边上,寂寞的树杈之间坐落着一个鸟巢,它无论清晨和傍晚都醒着,如灰色天空俯视人间的眼睛,闪烁着警惕的目光。每当清晨的时候,几只乌鸦在上面探头探脑,俯视着每一家的烟囱,似乎那袅袅饮烟里飘荡着温暖的希望,让它们眼神里闪着嫉妒的光芒。傍晚那些返巢的乌鸦围绕着树回旋着,如逆风中扬起的树叶,一声声忧伤的叫声使天色骤然暗淡下来,黑暗从四面八方袭来,很快就吞噬了所有的房子和树林。乡下的夜寂静无声,偶尔传来几声犬吠,仿佛一切都进入了梦乡。
屋里,铸铁炉子上搁着一把冒着热气的铁壶,壶里的水在滋滋地响着,似乎整个夜晚的内容都被浓缩在铁壶里,不停地翻滚和叹息着,如母亲喋喋不休的絮叨。炉膛下煤灰里埋着半熟的土豆,屋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香味,填充着晚饭后空寂的时光,让这段时间在甜味中发酵,最终酿出一坛浓郁的好酒。隔壁寝室的一位40岁张姓女老师仍旧在飞针走线,似乎她每晚的时光都耗费在一块块布料上,那些各种颜色的布料摇曳着鲜花,在灯光下一点点枯萎,从一件鲜艳的上衣沦落到一双新鞋的鞋底,每一个针脚都是生命中的感叹号。她儿子的玩具车一辆接着一辆摆在门口的水泥地上,其中一辆可以遥控的坦克在地上缓慢地蠕动着,像一只神态自若的乌龟,淡定地朝她家门口爬去,最后一头拱在门槛前不能动弹。整个屋子里充满倦怠的气氛,只有夜的呼吸在窗帘上起伏,把形形色色的故事收纳在黑色的口袋里,让风追逐着那些故事中的人物,让它们在一夜筋疲力尽的奔跑后,清晨安然地睡在石头的窗台上。
清晨,我站在学校厨房的门槛处,看着给我们做饭的梁师傅手里抱着一棵白菜从地里回来。南方的冬天,地里除了白菜、菠菜,就是萝卜,梁师傅的菜种的很好,用得是农家肥,很少用化学肥料。管理也很到位,从不允许我们接近菜地去侍弄他的这些蔬菜,似乎那里面隐藏着无数的秘密。天气太冷,所以把白菜如何过冬是头等大事。
梁师傅做法和周围的人很不一样,他挖一个长方形的土坑,把外皮晒去水分的白菜放在坑里,上面遮盖一层用稻谷草编成的草甸子然后盖上土。以至那一片荒地里,布满了大小不一的土坑,就像一条深褐色的裤子上布满新旧的补丁,一直要持续到春天。然而,这个讲究的南方人,他的菜窖一开始就显的有点特别。他先赶走所有在地里游荡的小孩,才开始神神秘密地刨着土坑,并不时地伸直了腰后环视着周围。他刨的那土坑确实特别,要比一般人家的大两倍,而他们家晒的白菜却并不比别人家的多。我开始纳闷,看到他拖了几根胳膊粗的树干去地里,虽然十分好奇却也不敢跟在他身后,总感觉他阴郁的目光如箭一般,扫在人身上很不舒服。
那一天清晨,我到操场打完篮球后,发现挨着学校旁边一何姓人家的白菜一夜之间没有了踪影,地上零落地散着几片干白菜叶,还没有来的急收拾。我顺着痕迹朝找去,进入了那片满是土坑的地里,但梁师傅的身影并没有在那,一堆隆起的新土边就是他的菜窖。那个菜窖盘卧在菜地中间,就像一个地主傲视着周围的青菜萝卜。一个四四方方的木框,镶嵌在土堆的中间,显然是菜窖的入口处。木框上是翠绿的合叶,连接着一个还散发着松树清香的原木新门,一把铁锁赫然挂在上面。从此那把锁就经常进入我的梦境,闪烁着诱人的光芒。
大雪过后,我会站在路边的高处,俯视着那片被雪覆盖的土地。看着雪地上一双大人清晰的脚印一直通往被雪覆盖的土堆,一个草绿的人影一点一点矮了下去,最后被雪地吞噬,大地一片寂静,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我眼睛不眨地盯着那个菜窖的入口,期待里面会有声音传出来。然而一切都阒然无声,只有一群麻雀落在雪地上觅食,然后又轰然飞走,雪地上似乎没有留下痕迹。一直看见那身影又一点点冒出地面,我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等到他小心地抱着一棵碧绿的白菜走向我时,我的眼睛却转向一边,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
一天例会,校长向大家宣布一马姓老师将从另外一所学校调过来,对于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而言,更多的人聚集在一起会更热闹。
马姓老师的到来,让冬天的日子充实起来,这位老师身材瘦小活跃,虽然年龄上比我大四岁左右,身上却显然带着经过风浪的闯劲。他最值得骄傲的事,是在读师范期间坐火车去了首都北京看了天安门、长城和故宫等我只有在书上和电视上见过的名胜古迹。每每说起时,他眼睛里就闪着激动的光芒,仿佛从黑夜里走出来见到曙光一般充满了喜悦。每到这时,他激昂的语调总能让我的思绪飘荡,飞到那红旗飘飘的天安门前,被为伟人和蔼目光沐浴的人群里,一切仿佛都在那里重生。
学生放学后,我跟在马老师的身后,绕过一排杨树,朝一片被残雪覆盖的荒地走去。这片藏在杨树后面的荒地,平时很少有人光顾,里面布满了一个个用稻草和竹子搭的草棚,它们一列列排列有序,安睡在寒风凛冽的冬天。草棚下面是装白菜的地窖。马老师猫着腰前行着,我默不吭声地跟在后面,鞋底下的湿泥越积越多,脚下的重量也越来越沉,最后竟让人站不稳脚,像一个前后摇晃的不倒瓮。我每一次抬腿都要微斜一下肩,才能那脚从地上拔出来,宛如在不停地拔着两只萝卜。到了地窖的一端时,竟有些气喘吁吁,浑身热乎乎的发热,我脱掉了头上的绒帽,忽然高兴地摇晃着身子叫了起来。一道木门上挂着一只锈迹斑斑的大琐,大约主人离去匆匆竟忘了锁,或者说根本就没有锁过。我心里一阵窃喜后,就像是意外得到了一件向往以久的宝贝。我用询问的目光看着马老师,他没有说话极快地环视了静悄悄的周围,然后上前快速地拉开木门。
木门吱呀一声开了,一股潮湿的气息迎面扑来,让人想起秋天缠绵的细雨,和那雨水滋润的菜地。我和马老师毅然走了进去,脚踩在潮湿的土阶上,浑身忽然有种走在田径上的轻松,如提前进入了春的季节。在暗淡的光线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地下甬道,除了一米宽的路一外,两边摆满了一层层的白菜,空气里飘着一种温暖腐烂的白菜味,和一种睡梦中的恬静。我一边往里走着,一边用手抚摩着一棵棵白菜,似乎企图把它们在沉睡中唤醒。但是它们却睡的那样沉,从身体飘逸出的梦境在空气中相互碰撞着,并发出微弱的亮光,就像是夏天的营火虫。我把它们看的更清楚了,它们头挨着头呼呼大睡,完全不顾角落里胡萝卜们朝笑声,不顾辛辣的气味撒向它们。那些白菜在睡梦中笑着,笑声冲出菜窖融进呼啸的北风中,那被笑声挤到一边的木门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像是在郑重其实地打着节拍,加入冬天的合唱。那些酣睡在梦中的白菜们,梦中的游离让它们忘乎所以,滚掉那些干枯的外衣,赤裸着白嫩的身体,在暗淡的菜窖里梦呓着……
一直远处传来清晰的说话声,我和马老师才从那菜窖里溜出来。我兴奋地头上冒着微微的毛毛汗,蹦蹦跳跳地跟在马老师身后,朝单身寝室走去。路经那片满是土坑的荒地时,那个土堆下的菜窖对我的诱惑消失了,我不再猜想那里面的内容,大有黄山归来不登岳的感觉。从那一天起,我知道了白菜灵魂的秘密,之后的每一个冬天里,我开始对它情有独钟。
五
学校的房屋在当地是最好的建筑,在这个小山坳里静静地生长了多年,也迎来送往了很多不同的面孔。每天睁眼醒来,眼望四周都是山,秋冬季节的早晨,学校周围大山都会被云雾缠绕着,那种缠绕,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缠绕,而是让人平添千丝万缕烦恼的缠绕。云雾里夹杂着雨雪,夹杂着枯萎的树叶,一个冬天就那样无禁止地下啊下,下得人心里充满惆怅,下得地上全是泥泞,风一吹,全变成僵硬的冻土。
在那个看不到远方的山坳里,我呆了一年。
一个深秋的清晨,我和山村像一对相爱多年的恋人,终于到了该分手的时候。在不得不选择离开这座熟悉的小学的时候,我还是落泪了。因为我知道,这样的离开,或许就是永远!即使我在这座小学校的某个教室或者某张课桌上留下了某种痕迹,甚至把自己和某个角落用一种影像资料保存下来,也不敢保证岁月在你离开后,是否会残酷地抹去这些遗留的印痕........
教书的这一年时间,给我留下了很多记忆,让我对大山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也改变了我对大山的一些看法。因为有了工作,减少了内心里的焦虑和烦恼。
当然,离开村子里的学校,并不意味着憎恨甚至想要抛弃我的村庄和我的大山,只因为远方的某一个地方,有我需要去认识的世界,我的心里住着另一个陌生的世界需要我的探寻。那里也许有霓虹灯在闪烁,有车水马龙的穿梭,给了我太多的诱惑。害怕大即使有发自内心地感到害怕和恐惧,但也必须要硬着头皮去面对。我毅然而然背上简单的行囊,用还显稚嫩的肩膀扛起只有属于我自己未来大山的一只棱角。当然,这种“扛起”有期冀、有矛盾和困惑,但更多的是对美好向往的一种憧憬。
告别了我的山村我的学校,来到500多公里之外的警营中。几年后又辗转到了我现在工作、生活的城市。一棵被移植到另一片天空下的树,初来乍到,水土不服,存活的艰难可想而知。更何况,人的生存远比树的生存还要复杂得多。我是这个城市的寄居者,这种暧昧的身份让我内心惶恐不已,我必须付出比别人多出十倍、百倍的努力,才有可能找到在这个城市的立身之地。生存的悬石在头顶上方高高垂着,压力空前陡增,几乎令我喘不过气来。我需要给自己找到一个固定的居所,让心从此安定下来,不再感觉漂泊无着,可面对节节攀升的房价,却一次次使我望而却步。这个城市的房价大大超过了我的心理预期。经过无数次的比较甄别后,我最终在一份购房合同上战战兢兢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从此有了明确的人生方向,知道今后该怎么去努力了。我不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抵达天堂还是坠入地狱,谁也无法告诉我。
在这座喧嚣的城市里,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的思想和灵魂,依然还时不时地跟随着梦,回到那个开满映山红花,还有牛羊和“地瓜儿”的地方,坐在一棵小树下,静静地望着蓝蓝的天,让思绪停止!想象自己是一闲云野鹤,永远停留在故乡。可我却发现,我已经回不去了,真的回不去了。
时过多年,从那所小学走出去的人,现在分布在大江南北,有老板、有博士,有县上领导,也有还在那片红土地上务农的……
如今,那所小学也已修缮一新,老式的瓦屋已不复存在,那棵伴随我成长的皂荚树和青檀树也已消失不知到哪里去了。而挺拔、巍峨、高耸而又青葱的的九台山,厚重、古老,默默地一如既往的屹立在那里,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出生、成长、老去,直至长眠于她的怀抱!那些远去的时光虽已过迁,但定格是我们记忆的永恒,一切依稀如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