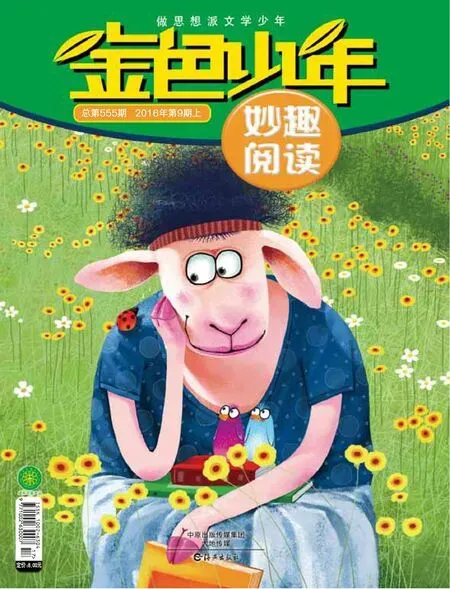爱收集报纸的戚二哥
沈伟东/文
潘婧/图
爱收集报纸的戚二哥
沈伟东/文
潘婧/图
我小时候,在西北山塬上的一个煤矿生活。
我家在煤矿的西山矿工窑洞,不远处的西山头有一排长长的两层青砖家属楼,它们被楼前的篱笆分隔成一家家小院子。戚二哥一家七口就在楼头,挨着一排厕所。夕阳西下,西山头漫天的燕子盘旋着叽叽喳喳,天空中厚重的晚霞像浇铸的铁水由亮红渐渐转暗,黑夜便从地下蔓延起来。
这个时候已经吃过晚饭,嘴角有点疤痕的戚二哥窝在他三四平方米的小砖窑洞里,翻看他收集的报纸。书本大的小窗外,有花椒树散发出的香味传来。那是上世纪80年代,十七八岁的戚二哥收集了20多家省报、60多家地市报的报纸,还有一些工矿报和几十本破旧的小说。
晚上,安静的黑暗里,嗡嗡的蚊虫飞来飞去,15瓦的灯光下,我们几个小兄弟拥在他砖头垒的小床上看报纸、看书,想象煤矿外面的人和事。戚二哥有很多历史文化故事和哲学想讲给我们,比如孔子的出身、人类的起源、永动机的发明,等等。他还写文章投稿,珍惜地收藏了一沓退稿信。
阅读、投稿,让我们知道山外还有比晚上聚众打牌、喝酒更有意思的事情。
那时的生活简单而寡淡。我们站在西山看西天起伏的山影,阅读让我们知道了比这山影更遥远的地方。书报里的人和事,激荡着少年们的胸怀,铅字印刷的文字把这群煤矿子弟的少年时代的底色印染出不少色彩。
后来,中学毕业了,瘦小的戚二哥到街头摆了一段儿修鞋的摊子。没活儿干的时候,他就瑟缩着身子在寒风里读报看书。在街头讨生计不容易,读书看报耽误生意,收入也就刚刚够糊口。
再后来,我去省城读大学了。戚二哥结婚了,有了一个叫一团黑的儿子。戚二哥写信让我帮他收集大学的报纸。我放暑假回煤矿的时候,戚二哥已经不摆修鞋摊子了,开始下井做矿工。由于时间不凑巧,我和他总是见面很少。到了西山头,有时候我看见他皮肤黑黑的儿子在院子门前的土堆里滚着玩,心里有些酸酸的。他的房子几个兄弟帮着扩大到20多平方米,戚二嫂说,家里不够住,堆了半屋子的旧报纸和旧书。
大学毕业后,我到更遥远的地方去了。戚二哥还给我写信。
信里,戚二哥有很多关于生命、社会的思考,也谈他在伸手不见五指的井下巷道里想自己的出路。有时,煤块会在他的身后哗啦啦落下来,掩埋住支撑巷道的枕木。他继续恳求我帮他收集报纸,支持他集报。在信里他还说,他已经收集了国内几百种报纸,还在煤矿的工会搞了一个报纸展。他还想收集国外的报纸,可惜没有途径。
我敬佩他的坚守,帮他四处留意,积累了一大包报纸。可遗憾的是,那年春节我乘火车回陕西,凌晨打了个盹儿,一抬头,行李不见了。就这样,我存了大半年的报纸也不知流落到了何处。
戚二哥知道后叹了好久的气,嘱咐我继续帮他留意。他拿出一份矿区的报纸,指着上面一篇报道了他的报纸展的几十个字的消息给我看,非常欣喜的样子。我也为他感到高兴。
有一年回煤矿,我听说戚二哥失踪了。这才知道有一天他说去下井,就再也没有回来。矿上井口储存柜里他换下的衣服整齐地摆放着,上面还有本没有读完的书。
戚二嫂呼天抢地,年迈的父母也老了很多。有人说,老二读书多,有不少奇怪的想法,也许是厌倦了这样的生活,去寻找他想要的生活了。
我当时想,他也许到了大城市,也可能到了深山出家当了和尚。很多年以后,他也许会突然出现在西山头。
很多年后,我回到煤矿,西山头已经矗立起一栋栋住宅楼。那时,盘旋半空的燕子们和戚二哥的小砖房子一样已经杳无踪迹。戚二哥收集的那些报纸,那些旧书,也许已经和老房子的旧砖瓦一样成为废墟的一部分。读了很多书,脑子里有很多稀奇古怪思想的戚二哥依然“失踪”着。
转眼20年过去了。而今,我已步入中年,时常想起青少年时期的戚二哥,想起戚二哥在幽暗的灯光下给我们读报纸,挂满花椒的树枝在夜风中摇曳。
戚二哥,你现在在哪个世界?你是不是还在整理着报纸和旧书,用圆珠笔在字数为300字的稿纸上一笔一画地写文章,偷偷地跑到邮局投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