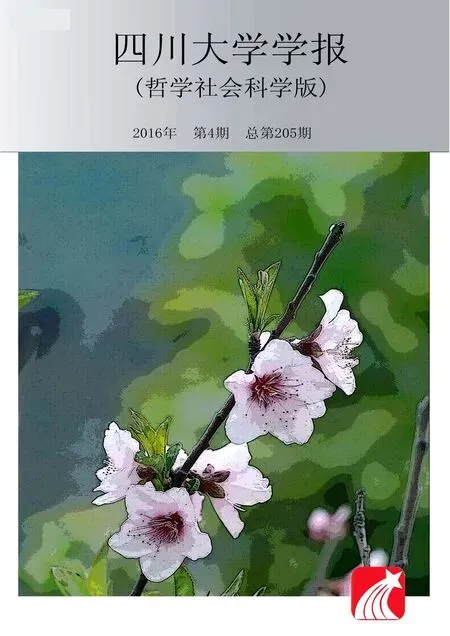文艺转向与“革命文学”生成
——郭沫若赴广东大学考
周 文
文艺转向与“革命文学”生成
——郭沫若赴广东大学考
周文
摘要:郭沫若赴广东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是1920-30年代“革命文学”生成、建构、扩张过程中的关键事件,但长期以来相关史实细节却并不清晰。追问郭沫若南下的邀请人及其动机,以及相关的人事纠葛和思想交锋,有助于呈现现代中国文学与政治的特殊关系。同时,在民国社会历史情态和“大文学”视野下重新梳理这一文艺事件,可以探讨文学参与社会的路径和方式,亦能揭示现代文人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
关键词:大文学;郭沫若;陈公博;广东大学
“当知识分子遭遇政治”是一个广为学人关注的话题,在现代中国更是如此。从“二十年不谈政治”到创办《努力周报》主张“好人政府”、从《新月》杂志的犀利政论到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胡适与政治尤其是他与蒋介石之间复杂的所谓“君臣”关系,不断激起后世学者的关注,成为烛照现代中国思想史的一面镜子。与胡适经历相似的还有丁文江、蒋廷黻、翁文灏、傅斯年等。相较于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政的普遍关注,多数人将“左翼”知识分子的从政视为一种革命理想和激情的必然选择,缺少对时代语境、思想脉络乃至现实人事纠葛的分析和梳理。比如郭沫若是怎样由以“纯文艺”为事业的诗人转变为“革命者”?仅仅因为翻译了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须知那封郭沫若说他因翻译该书而发生思想剧变的信件是在翻译完成近两年之后发表的,与其南下赴广东大学一起构成“转向”事件,这本身实际是一种立场的选择和姿态的宣告。以往的研究过分强调翻译带来的思想转变,而对史实细节缺少足够的关注,这导致现实的偶然性被过滤,相应的必然性被夸大。
1926年3月18日,郭沫若与郁达夫、王独清等一起乘新华轮赴广州任广东大学(同年九月改为中山大学,以下简称“广大”)文科学长。这是郭沫若从“穷文士”迈向“革命者”的关键步骤,更是现代中国文学青年投身革命经典范式的开启。长期以来,关于这段史实,学界多依据郭沫若的相关回忆,认为“他经瞿秋白同志推荐,由林伯渠同志代表党组织安排广东大学聘任郭沫若为文学院院长”,①肖斌如、邵华:《郭沫若传略》,《郭沫若研究资料》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4页。郭沫若也“立即回信表示接受邀请,并要求添聘郁达夫和王独清”。②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00页。然而,郭沫若的回忆只是他的听闻或猜测,可信程度究竟几何他也没有把握,因为“秋白自己却不曾对我说过”。③《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278页。广大作为国民党欲“党化”的大学,是国民党内部左、右势力争夺的要地,而文科学长又不是普通的教职,故中共在聘请郭沫若的过程中能否发挥决定性作用很值得怀疑。有研究者就认为,“郭沫若的南下广东,理应主要是由国民党人的意愿促成,共产党人则从旁推动了此事”。*蔡震:《在与国共两党的关系中看郭沫若的1926—1927——兼论与此相关的史料之解读及补充》,《郭沫若学刊》2007年第1期。那么,广东大学抑或广东革命政府选择郭沫若担任文科学长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什么促使郭沫若下定决心远赴广州,以及田汉为何未随郭沫若等一起南下?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郭沫若与陈公博
以郭沫若所取得的成就来看,广东大学文科学长在其诸多头衔中显得似乎有些微不足道,但该职位却是他“从政”抑或说是其革命事业的起点。在当时的文化界,论学问、资历,郭沫若等人作为文艺界的后起之秀,并不具备十分崇高的威望;论关系、人脉,他们与广东国民政府也无直接可靠的联系;而且他们都还很年轻:1926年郭沫若34岁,郁达夫30岁,成仿吾29岁,王独清28岁,但四人却均被聘为教授。同时,除郭沫若担任文科学长外,郁达夫也有任英国文学系主任的行政兼职,后改任出版部主任。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据中山大学校史所载之《国立广东大学规程》,“文科学长”不仅是“中国文学系、英文系、史学、哲学4系”(后来包括教育系、社会科学组、心理系)等学系的最高决策者,更是当时广大“全校最高决策机关”校务会议的核心成员。*以上资料见黄义祥编著:《中山大学史稿(1924—1949)》,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7、62-63页。综合该校对创造社其他成员的聘任,广大及其背后的“革命政府”对文科学长郭沫若的重视,堪比蔡元培治下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这种支持在后来的“择师运动”中也得到了有力的体现。显然,诚如前述研究者所言,这种聘请和支持的力度均非中共所能直接参与和完成的。那么,郭沫若的“蔡元培”究竟是谁呢?
陈公博在郭沫若南下广东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此人的汉奸身份,相关文献史料长期未受重视。陈公博当时是国民党的核心人物之一(在39人组成的国民党权力中枢——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陈位居宋庆龄之后,排名第七),兼任广东大学代理校长,该校函聘郭沫若正是在陈执掌期间酝酿,而完成于褚民谊任代校长之时。换言之,假设仅有瞿秋白的推荐,没有陈公博的积极推进,郭沫若南下广东很可能付诸东流。如此,则郭沫若与陈公博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在郭沫若的回忆录中有多处涉及陈公博,但几乎都是轻描淡写,无褒无贬,但若仔细审查,却似另有乾坤。郭沫若在《北伐途次》中说陈当时已被“任命为湖北财政厅长”,*《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80页。但陈公博却说“这次湖北省政府……将省政府分为两个委员会,一个是政务委员会,以邓演达为主任委员,一个是财政委员会,以我为主任委员”。*陈公博:《寒风集》(第四版),上海:地方行政社,1945年,第68页。另据《郭沫若全集》的注释,詹大悲“一九二六年随北伐军往武汉,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第37页;又据陈文学《掬一腔热血,铸不朽丰碑——记著名政治活动家詹大悲》(《党史天地》1998年第8期)记载:“北伐军攻克武昌后,詹大悲回到了他曾经多年战斗过的武汉。他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武汉分会委员、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建设科长、湖北省财政委员会委员、代理财政厅长兼湖北官钱局产业委员会主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等职。”虽然当时是战时,官员体制常处于变动之中,但核心人员的位置等级还是可以理清楚的。陈公博无论是邀请郭沫若赴广大时还是北伐时期都是郭的上级,在即将成立的湖北省政府中的位置是与邓演达并驾齐驱的,*在国民党内,陈公博的位置比邓演达高,北伐时期,陈在国民党权力中枢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39人)中位于宋庆龄之后排名第七,而邓演达只是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4人)之一。参见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172-173页。可在郭沫若的笔下却只是一个“湖北财政厅长”。这又是为何?
在郭沫若写作《北伐途次》的1936年陈公博尚不是汉奸,作为郭沫若赴广大的邀请人,陈在郭沫若自传中多次以“路人甲”的身份出现,这种看似无爱无憎的平常表述的背后却是郭对陈有意无意的轻视。笔者以为其原因当和陈公博与邓演达及郭沫若在革命过程中方法策略的对立有关。
陈公博在其回忆录中多次表达对邓演达的不满和诋毁,如:
邓演达拿着总司令行营主任的名义,乱发军饷的条子……我气极了,后来在武昌总部行营我们便抬起杠。
“湖北的财政情形你知道不知道?怎样你可以乱下条子?”我气极了说。
“难道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个军的犒赏费十万,那个军的犒赏费五万,又是必要的吗?每个月连正当军饷都没钱,那里再可以随便犒赏?”
“这是总部的命令,不是我的”,演达还很倔强。
“那里是总部命令,还不是邓演达的胡闹吗?”我斥责的说,“这样命令我绝不接受,我请你来接收这个财政委员会,我来干你的行营主任。”
陈公博在回忆录中甚至通过丑化邓演达来标榜自己:
一夜我刚跑到校外,远见一丛人正在那边扎梯,忽然听了有些嘈杂声音,原来是邓演达在那里指挥士兵和农民扎梯子。
“限明早五时以前都要扎起,不扎好便枪毙”,邓演达这样命令。
“你看梯子这样多,人这样少,今夜没有法子扎好”,一个湖北口音的农民这样申诉。
“非扎好不行,违抗命令的枪毙,”邓演达又大声的重申命令。
“我们不是士兵,不受谁的命令,我们是来革命的农民”。几个农民喧杂着抗议。
我走上前去,看这台是下不了,农民都停手不工作了。我拉着邓演达说:“我们还有别的任务,走罢”,一面对那班农民说:“今夜一定能扎好,只要你们努力。你们要明白,武昌城能否攻下全靠你们,你们若不努力,那是你们愿意北军长住在湖北”。
陈公博与邓演达及郭沫若的冲突,并非争权夺利抑或意气之争,而是在革命方法与策略上的根本不同。郭沫若在《北伐途次》中回忆的“郭聘伯”事件,即是这种冲突的典型反映。据郭沫若回忆,因为不能理解邓演达对郭聘伯的处理,他甚至负气要辞职,邓演达一方面耐心地解释说:“你的见解是很正确的,但是实际上是旧社会的力量太大,我们的力量太弱。我们革命军的内部便有极大的旧势力磅礴着,我自己是有好多说不出来的苦处的”;另一方面,邓又在给他与郭共同的朋友孙炳文的信中诉苦说:“革命的苦楚易吃,同志们的气难受,我恨不曾在武昌城下战死”。那么,究竟是什么让邓演达抱怨郭沫若“不懂策略,办事太幼稚,……是一位感情家”*《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第98-99页。呢?实际上,迫使邓演达批评郭沫若、释放郭聘伯的,正是以陈公博为首的“财政委员会”。
根据陈公博回忆,郭聘伯的靠山刘佐龙,即派一个营的士兵找郭沫若要人的倒戈军阀(陈公博恭称为“刘先生”),实际掌控着北伐军在武汉的主要财政(军费)来源:
可是那时财政委员会虽然叫做湖北全省的,但实际的范围只握有汉口和汉阳两镇,各县新占领,实在谈不到有钱粮,……这样财政仅留下一个法门,那就是特税了,所谓特税就是一种鸦片烟捐,特税在吴佩孚治下的汉口,素不公开,……财政是没得可谈,还是筹饷要紧,不管鸦片烟不鸦片烟,非把特税拿到手上,财政是丝毫没有办法。……但特税和盐税依然支配于刘先生的人,盐税收入不多,倒可请他维持,至于那特税就非设法拿过来不可,……这件事情后来又经过无数曲折,才决定仍有刘先生所信任的赵先生办理,不过可以许可我们派一个监察员,每月所收特税可以交给我们,但我们如果交不足十五军的军饷,应该在特税照扣。*以上所引陈公博的相关回忆,参见其《寒风集》(第四版),第101、67、101、103、79-82页。
郭沫若要杀郭聘伯,刘佐龙派一个营的士兵去要人,眼见着郭沫若可能要断送北伐军在武汉的钱粮,邓演达又怎能不着急呢?文人从军,最难克服的是讲服从和讲策略。郭沫若说他对“革命的现状”“最大的不满意是万事都讲‘策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第101页。虽然郭沫若可能对邓的苦处有深切的体味,但他仍然难以接受妥协,对陈公博在新旧势力间游走、无原则地讲策略自然也极为反感,这种对立情绪也是日后郭沫若公开反蒋的思想根源。也就是说,郭沫若与陈公博在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就已然分道扬镳,二人的革命实践未能真正合辙同轨。这种分歧无疑影响到郭沫若的回忆叙述,对他赴广东大学的邀请人陈公博,郭沫若显然不愿多提。可以说,郭、陈二人在郭沫若南下广东之前并无交集,此后亦未深交。那么,陈公博最初积极邀请郭沫若的动因何在呢?
二、革命与文艺
陈公博邀请郭沫若南下担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方面,出于个人政治利益的算计,陈公博急于从广东大学代理校长的任上抽身;另一方面,郭沫若反对“革命和文学是冰炭不相容”,主张“文学和革命是完全一致”,认为“文学是永远革命的”,*《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34-37页。这一认识引起了陈公博的深切共鸣,也应和了广州国民政府的革命主张和革命需求。国民政府对郭沫若的礼聘,并非单纯地指向郭沫若个人,而是对以郭沫若为中心的“革命文学”的召唤。革命与文学由暧昧真正走向联姻,此次创造社核心成员集体南下是标志性事件。
广东大学第一任校长为邹鲁,1925年11月“西山会议”后被罢免。此后,据1925年12月1日《广州民国日报》报道,国民政府聘请北京大学教授顾孟余担任校长,但由于顾氏不能即刻赴任,校长一职暂由陈公博代理。由于邹鲁在广大经营多年,势力深厚,自其离任后,不少教授亦随之辞职,广大的经费问题也随之凸显,陈公博为此颇为头疼。廖仲恺曾经评价陈公博“过于聪明”,而陈公博自己理解“所谓太聪明,就是对于个人的利害太清楚”。*陈公博:《寒风集》(第四版),第241页。在身兼数职的陈公博眼中,广东大学代理校长微不足道且是个苦差事,多次请辞,以致谣言四起。为此,1926年1月29日《广州民国日报》“学务消息”特以《广大学生会注意校长问题》专事问询,称“现社会风传有顾氏不来,陈氏辞职谣言,闻该校学生会对于此事非常注意,决定开会讨论”;又据该报1926年2月4日“学务消息”记载,广大学生会因校长问题于“三日上午十时,谒见汪主席”,获得的答复是“政府自接陈代校长辞职书后,以难觅人主持,已请陈代校长延任一个月,在此延任期内,政府自当极力物色其人”。*《广大学生会注意校长问题》《广东大学消息种种》,《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29日、2月4日。从开始定期两个月到被迫延期一个月,当时尚属国民党“左派”要人的陈公博,对于个人利益得失算计得十分精细,眼见无法推掉广大的责任后,因急于做出成绩,陈着手清理邹鲁势力的同时极力招揽人才,尤其是支持革命的左翼知识分子。郭沫若当时在上海与“孤军派”“醒狮派”混战,其主张旗帜鲜明、文笔形象生动,引起了革命阵营的广泛关注,瞿秋白、蒋光慈亦因此与郭相识。在这种情势下,无论是出于瞿秋白的推荐,还是陈公博自己的关注和考量,郭沫若的确能解陈的燃眉之急。因此,出于清理邹鲁“右派”势力的需要,也出于个人政治利益算计的考虑,广大代理校长陈公博对“左派”知识分子,尤其是能堪当重任的革命文人,真可谓“求贤若渴”。
1926年2月18日《广州民国日报》刊文《陈公博代理广大校务之措施,四大计划经已次第实现》,并称“现陈氏以代理时期已满,本身兼职务过多,精神不能集中,叠请政府开去校长职务,早日选员接替”。在即将离任之际,为再度彰显自己的成绩,在同一天同一版面,陈公博刊文《陈公博函催郭沫若等南归》,其“南归”二字意味深长,至少在陈公博的宣扬中,郭沫若已经答应他的邀请了。显然,陈公博是将聘任郭沫若担任文科学长视为自己代理广大校长的主要政绩之一来加以宣扬的。陈公博的这篇催促郭沫若赴任的文章是一篇颇具时代特色的公开函,副标题是“现在广州已充满革命紧张空气,愿全国有思想学者集中努力革命”。在这封850多字的函文中,陈公博用极少字数简单客套地称“已经读了不少先生的著作”,并且“还拿夜间编辑的余时来读先生和国内文学家的文章”之后,就直奔主题,现身说法阐述“革命”对“文学”的倚重。哲学专业出身的陈公博借反驳哲学与革命无关论,来强调“至于文学与革命的关系,在各国文学,更无地无时不表现其精神”,并以自身经历来举证,说他“二十岁以后的行动,全受了文学的影响”。笔者以为,陈公博在函文中的表态理应是真诚的,其邀请的方式也可谓特别,几乎没有对郭沫若个人的吹捧,更没有攀结所谓的私人情谊,通篇所言的核心,正是“革命”与“文学”的关系。
实际上,此时郭沫若“文学和革命是完全一致”的主张,与其早期所力行的纯文艺事业并不一致,而郭沫若的文字之所以能够引起广泛的同情和关注,也与其纯文艺事业的困顿体验有关。以创造社诸君为代表的文学青年“弃X从文”,献身文艺事业,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文艺是社会根本改造的步骤之一。然而,这只是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文学青年的美好初愿,后“五四”时期,各种“主义”与“问题”的论争,尤其是以“三·一八”惨案为代表的严酷现实不断击碎青年的“文学梦”。在不断重新思考文学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后,1925年5月郭沫若做了一次名为《生活的艺术化》的演讲,强调“生活的艺术化”;对此,郁达夫也曾说“我们的生活过程,就应该没有一段不是艺术的。更进一步说,我们就是因为想满足我们的艺术的要求而生活,我们的生活的本身,就是一个艺术的活动,也就可以说是广义的艺术了。……艺术毕竟是不外乎表现,而我们的生活,就是表现的过程,所以就是艺术”。*郁达夫:《文学概说》,《郁达夫全集》第10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6页。在《艺术家与革命家》一文中,郭沫若宣称只有象牙宫殿里的顽民和自诩为实行家的好汉才会认为艺术家与革命家是不能兼得的,因为“言说便是行为的一种”,而“艺术的制作便是艺术家的事业”,虽然艺术家不能严格践行自己的“宣传”,但却和“实行家拿一个炸弹去实行革命是一样,一样对于革命事业有实际的贡献”。比如,“俄国的革命一半成功于文艺家的宣传,高斯华士(Galsworthy)的《法网》(《Justice》)一剧,改革了英国的监狱制度,这是周知的事实”。由此,郭沫若大胆地断言:“一切真正的革命运动都是艺术运动,一切热诚的实行家是纯真的艺术家,一切志在改革社会的热诚的艺术家也便是纯真的革命家。”*郭沫若:《艺术家与革命家》,《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192页。该文最初发表于1923年9月9日上海《创造周报》第18号。这已不仅是“生活的艺术化”,而是“革命的艺术化”了。
郭沫若对文学的越界和泛化行为必然招致批评,对此他连发数文辩解。对敌意的批评,他表示把“文学家”摒诸化外的,“真是笑话”,主义学说并非被某类人所包办;对善意的规劝,他亦声明:
我从前是诚然做过些诗,做过些小说,但我今后也不曾说过就要和文艺断缘。至于说到我的思想上来,凡为读过我从前的作品的人,只要真正是和我的作品的内容接触过,我想总不会发见出我从前的思想和现在的思想有甚么绝对的矛盾的。我素来是站在民众方面说话的人,不过我从前的思想不大鲜明,现在更鲜明了些,从前的思想不大统一,现在更统一了些罢了。但是要说从事于文艺的人便不应该发表些社会思想上的论文,这是无论在哪一国的法律上都不会有这样的规定的。要说从事于文艺的人便不应该感染社会思想,这是根本上的一个绝大错误。*《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第22、23-24页。
郭沫若通过“表现”而完成的由文艺向生活、革命的跨越可谓是当时知识分子普遍心理的反映,也是文艺与政治在现代中国近一个世纪的亲密联姻的思想根源。因此,陈公博所言绝非虚词,而是“革命”和革命家对文学的期待和热望的真实反映。
三、郭沫若的态度
陈公博对郭沫若的招揽,其实正是“革命”对“文学”期待。有学者在考察北伐时期南北双方的宣传策略之后总结说:“北伐时期‘宣传’之功用被南北各方视为一种‘无形之战力’,首次受到国人的高度重视和娴熟运用。”*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中国近代通史》第7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93页。郭沫若与广州革命政府之间深刻的互动关系在此得到生动的说明,郭沫若呼喊着的“革命的艺术化”对广州革命政府有着极强的吸引力,尤其他在与“国家主义派”论战中的突出表现,赢得了国共两党职业革命家普遍的尊敬,这本身即是他胜任广大文科学长的资本,是其南下最核心的内在动因。至于无论是瞿秋白的推荐,还是陈公博的招引,均是外在的因素。郭沫若与陈公博并无交际,与瞿秋白也不过一面之缘,无论如何相见恨晚,也不能成为依托,郭沫若回忆他南下前的心情时所说的,“当时的广东虽然是我们的希望所寄系着的唯一的地方,而又有仿吾先在那儿,有达夫答应同去,但我不知怎的,总觉得有点畏途,觉得这一去好象要受着欺负”,*《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 第293页。即是这种外在人事关系顾虑的一种真实写照。事实证明,这种顾虑是多余,在广东,因为“革命”他又结交到更多影响到他后半生人生轨迹的朋友。
关于广东大学邀请其担任文科学长的真实内因,郭沫若虽未明言,却也是有自知的。在谈到广大聘请他的因由时,郭沫若先说“后来陈豹隐对我说过,这事是出于秋白的推挽。但秋白自己却不曾对我说过”。紧接着下一节又说:“文学和革命的关系,在当时的人多是认为不能两立的。就在现在,有好些风雅之士依然在维持着这种见解,所谓‘反差不多’运动便是这种见解的具体表现了。这种人的根本见解是以‘艺术’或‘美’那种东西为先天存在的什么,这种东西是超绝时空的,因而以这种东西为对象的人也就应该‘度越流俗’,于是乎他也就不差不多了。这种想法,正是典型的观念论,因为他们把那种由历史的发展所生产出的东西,不作为历史的成果,而认为历史的起源。……真的,当吴稚晖还未风雅化,唱着文学与革命不能两立的时候,我受了他的反面的暗示,却想到了文学与革命的一体。”*《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278、279-282页。因为分节的关系,这好几页的议论文字与对瞿秋白的回忆分开了,因而研究者多侧重郭沫若对瞿秋白推荐的猜测,而忽略了后文对“革命与文学”关系的长篇大论,这些议论在《创造十年续编》回忆文体中显得冗长,且与后文赴甪直参加婚礼的回忆不相干,因此其用意很明显在于承接前文的叙述,对国家主义、对“孤军派”、对瞿秋白的来访以及其赴广州的原因做一种自我合理化的叙述。可见,郭沫若对自己赴广州内外各种因由与契机有着相应的认知。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赴任广东大学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不是瞿秋白推荐、广大聘请,郭沫若就必然应招。且不说郭沫若曾有谢绝北大和多次推拒“武昌师大”延聘的先例,当时广大同时还聘请有田汉,田汉即因受到“醒狮派”的遏阻*《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292页。没有与郭同行。以往研究称“一九二六年二月底,当他接到广东大学的来信,聘请他去做文科学长的时候,他很快就决定接受聘请,而且不久即择期启程,奔赴广州”。*易明善:《郭沫若在广州》,《郭沫若研究专刊》第2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3页。这一说法沿袭郭沫若多年后的回忆,包括时间在内的多处细节均不准确。赴广大任教对郭沫若而言绝非一次轻松的选择,实际上仅就双方达成协议来说,就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时间。1926年2月3日《广州民国日报》“广大学务之近訉”中刊出一条以“聘郭沫若为文科学长”为题的专访消息,其中赞扬了郭沫若“作品之妙,几乎无人不知”,且“有革命精神”;2月10日陈公博写信催促郭等南归赴任(该信发表于2月18日《广州民国日报》,即前述函文);3月5日广大似乎已经确信聘请郭沫若为文科学长;*《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5日发布消息称“文科学长一职,前代校长陈公博,经聘请郭沫若主持,在郭氏未到任之前,由陈公博代理……”。3月10日左右郭沫若收到聘书和旅费,3月18日启程赴广州。*《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294页。值得一提的是,“文科学长”的诱惑并未彻底消除郭沫若的疑虑,所以此次南下他会“总觉得有点畏途,觉得这一去好象要受着欺负”。综合上述材料,可以看出郭沫若对赴广东大学任教考虑甚多:在可见的利益与长远的发展之间,郭沫若更看重后者。“文科学长”固然可诱,但成仿吾、郁达夫、王独清的同聘才是促使其动心的客观要素,郭沫若多年之后还坦言,他将传说中王独清“和汪精卫的秘书曾某相识”视为“援兵”。*《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293页。作为一名着眼于未来的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经历过泰东书局的招聘、创造社的聚合离散,在上海、日本之间徘徊之后,依旧在沪卖文为生,在“歧路”“漂流”中生活于“水平线下”。所以尽管思想观念上的阻碍早已不是问题,但影响郭沫若是否去广东的因素还有很多,其中的现实因素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与“孤军派”、醒狮派决裂后,郭沫若当时在上海的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昔日同乡、同学的挤压,导致他的生活压力徒增,这无疑也是促使其南下的客观外因之一。可是即便如此,郭沫若的妻、子一开始并未随行。作为四个孩子的父亲,郭沫若已深知理想和现实的距离,故而尽管他早已申明自己的转向,早已经和曾经的同乡、好友、国家主义者们分道扬镳,而把革命的广东视为“希望所寄系着的唯一的地方”,但与当年“弃医从文”相比,郭沫若对这一次的选择实际非常慎重。
四、“到民间去”
郭沫若关于南下广州的回忆在既成事实的前提之下有一个自我合理化的潜在叙事逻辑,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后见之明”对纠缠不清的思想分歧而言,就犹如一盏“明灯”规定了叙事的方向。诚如有学者所言“信奉了马克思主义的郭沫若与信奉国家主义的孤军社同人有着相同的知识起点”,*李怡:《国家与革命——大文学视野下的郭沫若思想转变》,《学术月刊》2015年第2期。郭沫若也将自己政治意趣的产生归为孤军社同人。*参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144页。但由于郭沫若的南下,国共两党对国家主义派的批判政策无疑加剧了他对国家主义派的敌视态度,这种“自我清算”有明显扩大化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其关于南下广州的回忆叙述。
首先,孤军社并非“国家主义派”,且据何公敢的回忆,在孤军社同人眼中郭沫若被视为其早期成员之一。何公敢是孤军社继陈慎侯之后的“主脑”,“曾留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历任厦门大学总务处主任、商务印书馆什纂部部长、福建省政府秘书长、福建盐运使、财政厅厅长等职,一九三三年‘闽变’时任闽海省省长,抗日战争以后,从事民主活动,建国后曾任福建司法厅厅长、省人民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民盟福建省委员会副主委。终于1977年”。*参见何公敢:《忆〈孤军〉》,《福建文史资料》第13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内部资料),1986年,第134、153页。在郭沫若上海“卖文为生”期间何公敢予以其很大的帮助。郭沫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时,何公敢担任“总政治部设计委员兼任第三厅第四科科长”。孤军社中与郭沫若发生冲突的林灵光,与国家主义派曾琦等人走得很近,然而他也不是“国家主义者”。林灵光(原名林植夫)出身福建海军世家,同盟会会员,曾加入“复兴社”,同时也是叶挺的秘书、中共特别党员、出色的敌工部部长。*林灵光的经历十分复杂,很难将其简单归类。他不仅是中共特别党员、新四军出色的敌工部长,也曾答应过刘健群加入复兴社(俗称“蓝衣社”);他见过孙中山、宋教仁,与蒋介石也能直接联系,陈果夫、陈立夫亦曾一度将其视为自己人,在被俘的新四军高级将领中,除了叶挺,唯一活着的就是他;他在蒋介石、陈铭枢之间做双面间谍,在对“中共”的态度上也很难窥见真意,作为新四军出色的敌工部长,解放后他去见上级饶漱石,时任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却不肯和他见面。详见陈子谷:《怀念林植夫同志》,《革命人物》1985年第1期。显然,将孤军社称为“国家主义派”是值得商榷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政治、历史、哲学大辞典中,查阅不到“孤军派”词条。“孤军派”作为一个政治派别只在郭沫若笔下或《简明郭沫若词典》中*李标晶:《简明郭沫若词典》,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51-452页。存在。郭沫若将孤军社视为国家主义派来批判,有浓厚的“自我清算”意味——郭沫若深知那些与孤军社同人共享的知识起点如果没有合理的走向,可能导向危险的境地。因而,对“国家主义”的批判一直是郭沫若思想逻辑自我合理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实际上,正如我们今天很难对“国家主义”或“国家主义派”作出明确的指认一样,郭沫若对“国家主义派”或“国家主义者”的指认同样模糊而不准确。郭沫若的判断多基于以下具体而明确的事实:这些孤军社的朋友们反对与苏俄联合的暴力革命,将苏俄与主张阶级革命的中共视为洪水猛兽,将国民政府视为军阀之一,主张在约法的框架下进行渐进式的改良——这正是激烈反共、激烈反对与苏俄合作的“醒狮派”曾琦等人的主张,他们积极鼓吹所谓“国家主义”,自称“国家主义派”。而殊不知,当时不少知识分子对苏俄、对暴力革命都持谨慎的保留态度。
郭沫若的这种自我清算自然也影响到他对朋友田汉的叙述。如前文所示,广东大学一开始不只邀请郭沫若,同时也邀请有田汉,但田汉却并未前往。郭沫若后来回忆说:
寿昌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人,那个学会本来就带有很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寿昌在前虽不必便是怎样鲜明的国家主义者,但他在那一方面的朋友特别多。一种团体无论是怎样自由的集合,多少总是有点立场的。一个人无论是怎样超脱的性格,入了一种团体也自会带着那个团体的意识。寿昌以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而参加创造社,他在出马的时候便不怎样热心,可以说仅是出于对我个人的友谊。初期创造社本没有标榜甚么主义,但至少可以说是非国家主义的。这种意识和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隐隐成为对立。*《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165页。
少年中国学会有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不假,但却也有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活跃其中,显然说少年中国学会是田汉南下的羁绊是不准确的。实际,可能影响田汉选择的是少年中国学会中的两个人——左舜生和曾琦,他们是田汉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介绍人,彼时正是“国家主义派”的两名核心骨干。
有学者甚至将田汉视为“醒狮派”成员,如小谷一郎就在其论文的注释中认为,“醒狮派”的机关刊物《醒狮周报》(当作“《醒狮》周报”)的发起人有:“曾琦、李璜、张介石、罗增益、萨孟武、黄仲苏、余家菊、何公敢、林骙(灵光——小谷注)、田汉、舒新城、陈启天、左舜生13人。”*小谷一郎:《郭沫若与二十年代中国的“国家主义”、“孤军派”——论郭沫若“革命文学”论的提倡、广东之行、参加北伐的背景及其意义》,《左翼文学的时代——日本“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31页。笔者并未在该刊中找到发起人名单,小谷先生据何所列尚待考证。其所列“孤军派”中的罗增益、萨孟武、何公敢、林骙等在1926年左右两社合并未果后就很少在《醒狮》上发文章。
其实,田汉与“醒狮派”其他成员有着显著的区别,他在《醒狮》上发表的文章多为文艺作品(如连载翻译武者小路实笃的《桃花源》),其在《醒狮》上开辟“南国特刊”,采取的是郭沫若、成仿吾所拒绝的“用文艺来作政论的附属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83页。的合作形式,主要是如“郭沫若与AA女士”“胡适之与白鹤泉”“李季与骡子”等“文艺杂话”“文艺特刊”类内容。1967年,田汉在交待“左舜生和《醒狮周报》”时说,“我那时虽向往进步,但对政治派别认识极浅,当左劝我替《醒狮》编副刊的时候我没有拒绝,只要求出南国特刊。左也答应了。特刊出了几个月。有人问我:‘你怎么加入国家主义派了?’我说:‘没有啊。’他告诉我醒狮的政治背景,我才注意问题的严重。这不是个人交谊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我才赶忙把特刊停出了。幸亏我不曾参加过整个《醒狮》的编辑工作,更不曾参加国家主义派的组织,所以牵扯还少。”*《田汉全集》第20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573-574页。经查,田汉在《醒狮》主持的“南国特刊”只持续到1926年初,即郭沫若等人南下广州之后他便终止了与《醒狮》周报的合作。田汉在《醒狮》的告别之作是电影剧本《到民间去》,连载于《醒狮》第74、75期。这是一部意味深长的作品。
田汉在“南国特刊”上发表《到民间去》是在1926年3月20日,就在两天前,郭沫若、郁达夫、王独清已经登上新华轮南下广州。作品的男主人公叫“郭其昌”,与“张秋白同学于沪上某大学”,二人经常“聚饮于校旁一咖啡馆,高谈社会改造,慷慨悲歌,大有古烈士风”,“但以性格言,张强而郭弱”,女主人公乃咖啡店侍女卢美玉。毕业后,高谈阔论的张秋白不仅大胆地向美玉求爱成功,在接收家产纺织厂后变本加厉从事投机买卖且事业辉煌,而郭其昌则受青年怪农人和贫民窟教育家之影响,变卖所有从事“新村”实验,为此不惜变卖祖传“古瓶”于张秋白。美玉渐识秋白真面目,遂离开张而与郭“抱吻”于新村的黄昏之中。张秋白投机失败,“妻父”亦因“政治关系见杀于敌”,其妻亦随父下世,张沦为乞丐,携“古瓶”前往新村,郭、张、卢三人的三角恋关系以张秋白的自杀而告终。剧尾,郭其昌与美玉于秋白墓旁合跳所创之“新式民间舞”,坟头之花亦与之共舞。
“郭其昌”显然是郭沫若与田寿昌的混合体,而张秋白的形象亦隐约可见田汉的影子。广东大学同时邀请田汉、郭沫若,唯郭沫若南下,田汉羁留上海。田汉在郭沫若南下之际发表《到民间去》,其寄托的复杂情感和思想的矛盾自不言而喻。1923年,郭沫若有一首诗这样写道:“朋友们怆聚在囚牢里——/象这上海市上的赁家/不是一些囚牢吗?/我们看不见一株青影,/我们听不见一句鸟声,/四围的监墙/把清风锁在天上,/只剩有井大的天影笑人。/……啊啊/我们是呀动也不敢一动!/我们到兵间去吧!/我们到民间去吧!/朋友哟,怆痛是无用,/多言也是无用!”*《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323-324页。多年之后,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还如是解说道:“在出《周报》时吼过些激越的腔调,说要‘到民间去’,要‘到兵间去’,然而吼了一阵还是在民厚南里的楼上。吼了出来,做不出去,这在自己的良心上感受着无限的苛责。”*《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184页。田汉将电影剧本命名为《到民间去》,又给主人公取名“郭其昌”,其用情感宣泄的指涉自是明确的。田汉十分看重该剧,同年,由南国电影剧社自筹资金,田汉自任导演,借新少年影片公司的场地、器材拍摄该剧,最后因经费拮据未能拍摄完成,对此田汉表示了永久的遗憾。
郭其昌在剧本中“组织新村”实验,更有明显的指涉。“新村运动作为一次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试验,……倡导者与活动分子中,相当一部分人,似乎是顺理成章地从空想社会主义走向科学社会主义,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建人和骨干力量,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就有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等人。”*钱理群:《“五四”新村运动和知识分子的堂吉诃德气》,《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在剧本“命意”中,田汉写道:“一念为公,则见义勇为,奋不顾身,弱者或变而为强。一念为私,则患得患失,不知所可,强者或变而为弱。”*《田汉全集》第10卷,第11页。田汉此时是否真的认同或信奉了共产主义恐怕难以确认,但他对底层民众的关心和同情,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憧憬确是真诚的,这为日后田汉真正的“左转”奠定了基础。
田汉羁留上海,郭沫若显然有些耿耿于怀,而与之对应的是,田汉本人的反应同样很大,这都充分说明,南下广州对郭、田二人来说,都不是一次轻松的选择。更可以看到的是,在左翼知识分子的从政经历中,其选择与文学的勾连往往更加直接和紧密。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他们的文学作品具有非同寻常的时代感召力,但在“纯文学”的视域中,其影响力却得不到有力的体现。尽管“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非文学的世纪”的说法有些夸张,但称“政治化思潮影响和制约着20世纪大多数年代文学的基本走向”*朱晓进等:《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页。却也切中肯綮。通过对郭沫若南下广州诸多史实细节的梳理,就会发现《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到民间去》《创造十年》《创造十年续编》等作品中浓厚的现实价值关怀,其意蕴值得我们长久的涵泳;同时更能体会到,在重视文献史料的梳理和阐释的前提下,避免政治模式的生搬硬套和概念的固定化、模式化、“上帝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279-280页。重提回到“大文学”本身*李怡:《回到“大文学”本身》,《名作欣赏》2014年第10期。对现代文学研究有不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
(责任编辑:庞礴)
作者简介:周文,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后、讲师(成都610064)
基金项目: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文史互动视域下的郭沫若抗战历史剧”(skq201623)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16)04-0097-10
A Textual Research on Guo Moruo Working at Guangdong University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in the View of Great Literature
Zhou Wen
Abstract:Guo Moruo's working as chairman of liberal arts school at Guangdong University is a key event in the process of gener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during the 1920s.But for a long time the related historical details have not been clear. Uncovering the motivation of the host person who had invited Guo and the relevant complex personnel is vital to understanding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Restudying this literary event in the view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Great Literature helps explore literature participation in society and understand the change of the spirit of modern intellectuals.
Key words:Great Literature, Guo Moruo, Chen Gongbo, Guangdong University
§民国文学的学术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