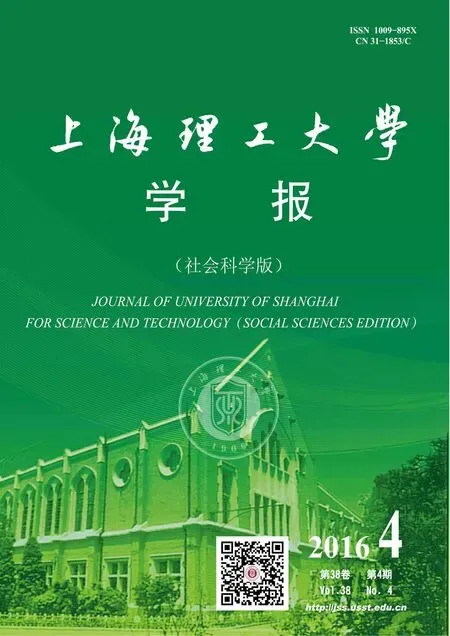大学英语教育改革之我见
吴国玢
(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 200093)
大学英语教育改革之我见
吴国玢
(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 200093)
通过对印度和中国的英语教育及其效果进行比较,阐述了我国大学英语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进而分析了国内大学英语教育的问题所在,建议目前的大学英语教育应该尽快向ESP转型。最后,从组织落实、教材编写、师资培训和观念转变等方面就如何转型提出了若干项具体建议。
大学英语教育;特殊用途英语;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改革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各国国力的竞争,与其说是科技和经济实力的竞争,不如说是人才的竞争。我国这样的大国能否在全球化时代里真正崛起于世界强国之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拥有一支庞大而富有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队伍。笔者认为,所谓复合型人才的基本含义就是既精通自己的专业业务又有较强英语能力的能文能武的人才。由于英语是目前世界先进科技知识和经济发展信息的主要语言载体,是国际商务往来和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汲取、引进、消化、利用先进理念和尖端技术的必备工具,因此一个国家人才队伍的英语能力实际上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软实力。由此可见,大学英语改革并非单纯的教育问题,而是一个提升国家软实力,涉及国家战略,甚至需要顶层设计的重大问题。换言之,认认真真、切切实实地搞好英语教育改革对于建设一个强盛的现代化中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应当予以高度重视。
一、大学英语教育改革的迫切性
我国现在的大学英语教育乃是典型的应试教育,弊端甚多。尤其在大力推行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CET)制度以来,英语教学质量引起一些院校师生和社会人士的质疑,要求改革的呼声此起彼落。我国外语界目前对大学英语迫切需要改革虽已形成共识[1-2],但究竟迫切到什么程度,恐怕仍然是一件见仁见智的事。事实上,我国的大学英语教育改革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程度。这样讲到底是不是有点过甚其辞乃至危言耸听呢?笔者以为最好还是让事实来给出回答。本文想从一个特别的视角来观察并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以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警觉。下面列出的一组事实旨在对北美洲的华裔与印裔移民和留学生做一比较。
凡是访问过美国硅谷的人,一定会在各家科技公司的高管群体里看到许多亚裔面孔并留下较深的印象。但仔细了解下来,其中身居高位的科技人员,尤其在大牌科技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CEO)的却大多是印裔移民。近年来在跨国公司中出现了不少印裔领军人物,包括微软的全球CEO萨提亚· 纳德拉(Satya Nadalla),谷歌的CEO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Adobe的CEO山塔努·纳拉杨(Shantanu Narayen)以及百事公司的董事长兼CEO卢英德(Indra Nooyi)等国际一流人才。此外,以哈佛商学院院长尼廷·罗利亚(Nitin Nohria)为代表的一批印裔院长们也相当引人注目。事实上,与印度人相比,中国人即便在美国普通职场中的表现也逊色不少。第一代华人移民中除非个别人自己创业做老板,否则在美国公司里做到初级经理的都不多,至于做到高级经理甚至CEO一层的,则更是凤毛麟角。同样是第一代移民,印裔初级经理随处可见,高管和CEO也为数不少,远远超过华裔移民。其实,印裔的成功例子遍及各行各业,数不胜数,难以一一列举。难怪有人认为,在少数族裔争夺美国和加拿大职场地位的这场战斗中,中国人已经输了(The battle is over,and we lost)。下面再来看一下收入情况。
不久前公布的美国人口调查结果显示,美籍印度人是所有种族中收入最高的,家庭收入中位数居然达到了91 195美元!远超白人的50 740美元,也超过了华裔的84 300美元。很明显,上述收入上的差异印证或映射了华裔与印裔在社会地位或事业成功方面的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提及的这些印裔人士(包括杰出人物)大多是第一代移民,而非第二代、第三代移民。他们早期所走过的路与改革开放后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他们都在各自国家完成中学或大学本科学业,然后出国留学、工作、移民。第一代华裔和印裔移民可以说都是各自国家的精英,学术背景条件和基数(起跑线)也大体相当,为什么他们在北美洲职场上的表现差异如此之大呢?当印裔移民进入跨国企业并且不断往上升的时候,中国人都到哪儿去了?有人说那是所谓的“玻璃天花板”效应。但是如果美国的企业的确存在针对少数族裔的“玻璃天花板”,为什么印度人没有被挡住呢?印度移民在人数上不及中国移民,但他们的成功率为什么会明显高出呢?笔者以为,除了历史、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原因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华裔与印裔在英语能力上的差距。印度人讲英语虽有浓重的口音,但阅读、写作和口头表达能力出众,书面英语规范。我们中国人虽然听印度人讲英语有点费力,但白人却完全听得懂,沟通起来毫无问题,因为人家的语法、逻辑都很贴近正规英语。反观中国,英语只是作为一门必修的语言课程进行教学,许多精英都是成年之后才到美国,他们的英语能力跟印度人相比难免明显落后。毋庸讳言,英语是印度人的巨大优势,却是中国人的巨大障碍。
下面请再看一则媒体报道:
加拿大联邦公民及移民部(CIC)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获得快速移民邀请的中国公民人数有531人,仅占1.2万名同类移民总数的4.1%,不仅远低于印度(2 687人),还明显低于菲律宾(2 514人),也低于英国(951人)和小国爱尔兰(682人)。更加令人扼腕的是,这531位中国公民中85.5%是已经在加拿大境内工作或留学的人员,而在中国境内获得邀请的只有99人,仅占0.8%,是印度或菲律宾移民的一个零头。加拿大移民律师Steven Meurrens坦陈,中国人英语较差是快速移民受阻的最主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印度的国家软实力的不断积累和提升,其硬实力也在逐渐显现出来。近年来,印度的IT产业、制药业、航空航天技术、军事现代化等均有引人瞩目的发展。印度目前已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和八年全免费教育制度。迄今为止,印度已经有八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覆盖物理学奖、化学奖、医学奖和经济学奖等奖项。印度出版的科技著作数量居世界第八位,有18种科学杂志被收入具有世界级水平的《最新刊物目录》[3]。而且印度发展的后劲还相当充足,不容小觑。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上所列举的事实和数据直接反映出三十多年来我国英语教育的效果,表明我国英语教育大大落后于与我们毗邻的印度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迅速采取有力措施进行改革。中国政府虽然每年对英语教育都有大量投入,但收益并不理想,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还有没有补救的空间和急起直追的可能?如果可能,那么应当如何对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进行切实有效的改革?回答并解决这些问题都是当前的紧迫任务,刻不容缓。当今世界各国都已逐渐意识到教育问题的重要性,将它当成国家长远战略问题来对待。美国更是把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提升至事关国家安全的高度。我们当然也切不可等闲视之。
二、我国大学英语教育的问题所在
笔者在海外有几位从事高等教育的印度朋友,对印度的英语教育略知一二,因此试图通过对两国英语教育的比较来找到我们的问题所在。也许有人会说,印度人的英语能力强是因为印度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然而,问题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如果反问一下,那为什么澳门没有多少人会讲流利的葡萄牙语呢?为什么中国香港人的平均英语水平并不像印度人那样明显高出中国大陆人多少呢?因此仅仅从历史上找原因是远远不够的。关键原因还得从教育体制和教学模式方面去找。
中印两国同处亚洲,同属四大文明古国,历史源远流长。两国的文化都是东方文化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更具可比性的是,两国都是世界人口大国,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印度人跟中国人一样有自己的国语和方言,他们的印度语(Hindi)是主要的官方语言之一。实际上印度的地方语言比我国更复杂,不同地区的语言差异也更大。印度朋友告诉我,从印度的一邦到另一邦就像到外国一样,各地的语言、宗教和习俗都不一样。这种情况使印度政府不得不规定其官方语言多达22种,以满足南北各邦之间相互沟通和交流的需求。英语当然也包括在这些官方语言之中,而且还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全国通用的语言,就像我国的普通话那样。印度刚取得独立时,如果从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出发排斥英语的话,那么就没有今天印度人的英语能力。所以现在看来,当时印度政府的这个决策是对的。从实际效果看,这一决策非但没有损害印度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反而为印度的科技和经济长期发展开通了一条顺畅的信息交流渠道,为其实现全球化打好了坚实的基础。
印度的教育制度明文规定要在有条件的地方实行完全的英语和本国语言相结合的双语教育。私立的中小学从一年级到十二年级全部用英语讲授各门学科,即以英语为教学语言实行全英语教学,同时开设一门印地语(或地方语)课。公立学校则实行双轨制且分为两类,即英语学校(Only English Schools)和印地语(或地方语)学校。在印度的高等院校里,理工科全部采用英语教材,用英语讲授;文科类专业除了个别课程用印地语(或地方语)讲授之外也全部用英语讲授[4]。教师们一般不使用统一的教材,而是给学生开出一系列参考书目(以英语为主),让学生自己阅读、分析、思考。考试时强调让学生根据对教材和参考资料的阅读理解阐述自己的观点,重点放在思辨、逻辑、联想和创新上,无需死记硬背[3]。这些做法与发达国家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相比之下,中国的大学英语只是作为一门外语课来学习的。这门课程的学习仅限于课堂内和课后作业,而与其他课程、日常生活、学校、家庭和社会几乎毫无关系。学习英语课的唯一目的就是应付英语四六级考试。而CET的考试方式又迫使学生完全浸泡在应试技巧和模拟试题的海洋之中,他们得到的鼓励是猜对答案的技巧,是对词汇和语法的机械式记忆,而不是掌握语言工具的应用技能,从而完全陷入了应试教育的怪圈。师生们对于大学英语这门课程也只能抱着“你考什么我就教什么”“你考什么我就学什么”的消极态度[2],被迫陷入题海大战,完全无暇顾及语言的实用交际能力和信息承载能力。很明显,这种学用分离的教学模式所造成的必然后果就是:费时颇多,收效甚少。大多数大学生学了十几年的英语却还是“半聋半哑”,遇见外国人听不懂、讲不出,读完科技文献原文后仍然一头雾水,英语写作则更是勉为其难。尤其是将CET成绩与学位证书直接挂钩之后,学生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包袱,承受着附加的心理压力。他们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应付英语考试上,从而严重影响了其他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学习,出现了舍本求末,甚至本末倒置的不正常现象。不言而喻,这种完全是人为的无形浪费所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
综上所述,可知中印两国英语教育之间确实在多方面存在着差异。简而言之,这些差异也许可以归结为在一个“用”字上的差异。印度学生学习英语的目的不是为了应付考试,不是为了学英语而学英语,把英语当成一件点缀品,而是为了使用英语这个工具去获取其他各种知识,包括自然科学、人文或社会科学等各个不同领域的知识。只有掌握好英语工具,他们才能学好其他各门学科,别无他途。由于这些学科的教材全部都使用英文原版,教师又用英语授课,所以整个教学过程就成了一个“用”英语的过程:使用英语工具去掌握其他专门知识。这样的做法使学生既学到了专门知识,又提高了英语能力。不难看出,这种教学模式在相当程度上接近于我国部分专家近年来大力提倡的专门用途英语ESP(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课程[1]。关于ESP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至70年代,其英文名称也从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s(特殊用途英语)演变为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专门用途英语)。目前国内外学者,尤其是国外学者使用后者居多[5-6]。笔者认为,无论采用哪一种名称,ESP的实质就是将英语与某种专门知识整合在一起,做到“学用结合,边学边用,在学中用,在用中学”,突出了一个“用”字。因此现阶段在我国大力推广ESP课程有望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以往学用割裂的弊端,显著提升大学英语的教学效果。实际上,从目前情况来看,用ESP来取代大学英语(CE)可以说是一项最现实可行的改革措施,因为迄今为止除了双语教学之外,似乎还未见有人提出在“用”字上下功夫做文章的更好办法。然而双语教学要求教师除了英语以外还必须精通专业。这样的师资目前在我国还极度匮乏,一般的英语教师难以胜任,因此成为其发展的瓶颈,无法迅速推广。反之,ESP却能为大批大学英语教师的转型提供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其转型的跨度和难度都远低于双语教学,比较易于实行。何况,其中转得好的教师今后还会有机会成为双语教学的强大支撑或后备力量。顺便提一句,我国的大学英语在严格意义上其实还不能算是一门ESL(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或“二语”课程,而只是一门外语课程EFL(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因为第二语言的原意是指人们在本国内学习并使用的一种非母语的语言,是在本国内与母语有着同等地位的通用语言。例如,广东话是广东人的母语,而普通话就是广东人的第二语言。与外语学习相比,二语学习必须具有更好的语言环境和教学条件。
印度的英语教育实际上是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来进行教学的,是一种二语教学。英语是印度最重要的官方语言之一,又是印度全国南北各邦的普通话。那里有着相当优越的语言应用环境和师资条件[7]。很明显,我们不能也没有必要照搬印度的英语教育体系和教学模式,因为毕竟国情不同,而且差异甚大。但是,我们却完全可以根据中国的国情借鉴印度英语教育的成功之处,为我所用。关键问题在于要抓住其精神实质——学习英语与使用英语的紧密结合,要在“用”字上下足功夫做好文章。毋庸置疑,改革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使之摆脱应试教育、学而不用的困境,向ESP转型是目前阶段的一条必由之路。
三、大学英语教育的具体改革措施初探
不比不知道,比了才知道。对于我国大学英语教育中目前存在着的诸多弊端,无疑应当尽早进行改革。其中有些弊端可以立即加以克服或消除,比如终止执行英语四六级考试与学位证书挂钩的制度。但实现CE向ESP的转型从总体上看却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不宜急于求成,而应当有规划、有步骤地进行。首先,要做到上上下下统一思想,转变观念,明确此次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解决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学用结合这个核心问题。在改革过程中应该突出重点,抓住要害,循序渐进,稳中求快,逐步实现大学英语向ESP的转型。与此同时,在有条件的地方可考虑将双语教育纳入外语学院(系)的管理范围。因为ESP与双语教育的目标完全一致,有互补性,可以异曲同工、相辅相成。但目前的双语教育和专业英语教学(由专业教师任教的本专业英语科技文献阅读课),大体上仍由各系或者各专业教研室自行负责管理,与外语学院(系)基本上互不相干。事实上,目前个别专业英语教学由于疏于管理而流于形式甚至名存实亡。这种分散独立、各自为政的局面如果能得到统一有效的管理,相信大学生的总体英语水平会有进一步的提高。可以预期,这样双管齐下甚至三箭齐发的改革效果很有可能会比单独搞ESP的效果更好。不过本文的讨论重点还是放在大学英语向ESP转型的问题上。归结起来,大学英语教育的改革需要依次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组织的落实
像大学英语转型这样比较复杂的重大改革,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是无法顺利进行的。组织上不落实就只能停留在“大家急,大家喊,结果大家不管”的状态。没有组织机构,靠个别单位、个别教师单枪匹马也必然是无济于事。其结果很可能是数年过去了,仍然原地踏步,没有多少进展。为了充分调动或发挥各地高校的积极性,笔者建议刚开始时可采取“百花齐放”的方针试点,不必急于成立大型的全国性领导机构,而是先在外语教育比较发达的大城市和沿海省份成立大学英语改革指导委员会之类的机构,并在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下由地方上的外文学会牵头具体指导大学英语的转型和双语教学的推广和管理。主要任务可包括成立ESP教材编写团队编写教材,培训师资队伍并进行考核,颁发ESP教师证书和双语教师证书,制定持证教师的激励机制和相关规定,组织教学观摩、学术交流和学术研讨会等各种活动,不断探索改进教学方式和考试方法,以及开展国际合作,聘请以英语为母语的外籍教师和有资质的海归华裔教师来我国培训师资或任教,等等。
(二)教材的编写
新的教材首先必须与大学生的某一门基础课、技术基础课或专业课的内容相结合,成为一本ESP教材,亦即必须摈弃以前那种与其他课程毫不相干的单纯外语教材。其次,新教材的内容必须来自原版教材,做到保持原汁原味。笔者建议首先选择物理学这门基础课作为编写ESP教材的突破口。理由如下:其一,大学物理是现代科学技术亦即绝大多数理工类专业课程最重要的基础课,同时也是一门覆盖面大、使用范围很广的课程,这门课作为必修课或选修课不仅为理工类学生,而且也为文科类、商科和医科类的学生开设;其二,国际上英文原版的物理教材较多,其中包括当今一流物理学家的杰作,可供选择的范围较宽;其三,与内容范围狭窄的专业课程相比,物理学的内容相对宽泛、普及,专业性不强,易于理解;其四,与数学、化学等基础课程相比,物理学的知识性、实验性、趣味性强,原版教材文字优美,图文并茂,贴近日常生活,容易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其五,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师绝大多数在中学时代学习过物理学,有一定的基础。综上所述,可知选择物理学作为突破口有利于减轻大学英语教师实现向ESP转型的困难,有助于提高向ESP转型的速度和效率。
根据Hutchinson & Waters(1987)的观点,ESP的特征组成ESP课程的教学大纲。这些特征就是所谓的需求分析(needs analysis)或目标情景分析(target situation analysis)。ESP教材的编写必须遵循真实性原则,其课文内容必须取自相应专业的真实语料(即原版教材),应突出其目的性明确和实用性强的特点。真实性(authenticity)是ESP教学的灵魂。只有真实的语篇(authentic texts)和真实的学习任务(authentic tasks)才能体现出ESP教学的特色。ESP教材的内容应力求匹配,书中除了介绍专业名词术语和语法以外,还应包含修辞、篇章分析等语用知识[2],以及科学家传记、发明故事和科学史上重大事件等章节或栏目,用以拓宽学生视野和思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思维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如果难以找到一本符合上述所有要求的现成原版英文教材,可以收集多本合适的原版教材进行编写。
(三)师资的培训
如果有了好的ESP教材却没有好的教师去教,那么这项改革显然也是无法进行下去的。因此可以说,师资培训的成功与否是大学英语教育改革成败的关键。换言之,大学英语向ESP转型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师资培训是否成功。正如卢思源教授所言,我国的外语教育改革目前已进入深水区,大批大学英语教师要分流,要转型,要发展。然而由于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师除了英语和语言学知识以外,一般不具备任何其他专业知识,所以转型意味着要求他们进行再学习,接受培训或再教育。培训方式应以“请进来”为主,即尽量延聘以英语为母语的外国专家来培训我们的大学英语教师。但在有条件的地方也可考虑采用“派出去”的方式,把教师派遣到国外高等院校接受短期培训。另外,今后的英语教师进修内容也应逐渐向ESP倾斜,作为一项教育改革的配套措施。对于大学英语教师而言,转型肯定是一种挑战,但也应看到转型实际上也是一种机遇。早转比晚转好,转得快比转得慢好。有人将单纯的外语知识比作“毛”,而将某种专业知识(包括文学、语言学在内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比作“皮”,是有一定道理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谚语用来比喻事物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或依托,就难以生存下去(A thing cannot exist without its basis)的道理。不少外语教师觉得自己的外语知识除了用来教学生之外,似乎没有多少其他用处,产生出空泛或不踏实的感觉。笔者相信,向ESP转型可以为他们的英语知识找到“一张皮”,即一个坚实的依托或落脚点。换句话说,这次转型实际上也是在为大学英语教师改变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拓展他们的职业生涯提供一个良机。当然,教师们也完全可以根据个人的特长和兴趣爱好来选择自己愿意结合的专业,甚至提出申请编写自己的ESP教材。那么,怎样才能当好一名ESP教师呢?Dudley-Evance & St.John(1998)指出,ESP教师应该充当以下角色:他(她)首先必须是一个合格的英语教师,而且必须是一个合格的课程设计者,并能为学生提供实用可行的教学资料;他(她)既是专业教师的合作伙伴,也是学生的合作伙伴;他(她)必须是一个合格的教学研究人员,还应该精通ESP的测试与评估[6]。
(四)教学观念的转变
大学英语向ESP转型不仅必须更换教材,而且也必须相应地改变教学方式和考试方式。这就要求教师首先须转变教学观念,要彻底扭转以教师为中心、以灌输为核心的传统教育模式。灌输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输入,学生被动地接受,往往会消化不良,吸收甚微。所以尽管输入十分重要,但若没有学生的主动参与和师生之间的积极互动,没有重新构建和输出,输入就会失去效率甚至失去意义。ESP课程固然需要教材,但教师不能一味地依赖于教材,只靠一本教材“吃饭”。相反,英语教师应该向学生推荐几本英文原版的参考书或印发一些英文参考资料,让学生自己围绕着教材阅读、分析、思考、质疑、推理、类比和创新。考试时应强调让学生根据他们对参考资料的阅读理解阐述自己的观点,重点放在思辨、逻辑、联想和创新上,摈弃死记硬背的陈旧学习方式,彻底告别英语四六级之类的考试形式和制度。
四、结束语
我国大学英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也正当其时。目前我国国力正在迅速提升,国际合作和国际影响正在不断扩大。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国家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和投资力度也在逐年增加。这是支持我们进行大学英语改革的有利条件。大学英语教育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参与人数众多,任务比较繁复艰辛,可谓任重而道远,但前景十分光明。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坚定信心,团结一致,努力工作,那么我国的英语教育必将在数年内以全新的面貌展现于亚洲和全世界。
[1] 卢思源.ESP/EST纵横谈[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3(2):83-89.
[2] 李兴福.专门用途英语与传统大学英语[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7(3):201-205.
[3] 万大林.探索培养国际一流人才之路——印度英语教育的启示[J].课程·教材·教法,2004,24(9):84-89.
[4] 郝素珍.印度英语教育对我国的启示[J].市场周刊财经论坛,2003(12):37-38.
[5] Hutchinson T,Waters A.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 A Learning-centred Approach[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6] Dudley-Evans T,St John M.Developments in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7] 王芬.中印英语教育比较刍议[J].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学报,2008,10(2):53-55.
(编辑: 朱渭波)
On the Reform of College English Education
Wu Guobin
(CollegeofForeignLanguages,UniversityofShanghaiforScienceandTechnology,Shanghai200093,China)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necessity and urgency of the reform required for college English education in China.It compares the English education system and its effects in China with those in India,and demonstrates how and why the reform is urgently needed.The writer suggests the college English curriculum be transformed to the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ESP) program asap.In addition,he offers recommendations as to how this transition can be achieved including organiz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reform system,creating effective teaching materials,training ESP teachers and helping them change their perspectives on teaching.
collegeEnglisheducation;ESP;ESL;reform
2015-11-22
吴国玢(1940-),男,教授。研究方向: 科技英语、工程热物理、物理学。E-mail:wugb6688@126.com
H 319.1
A
1009-895X(2016)04-0301-06
10.13256/j.cnki.jusst.sse.2016.04.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