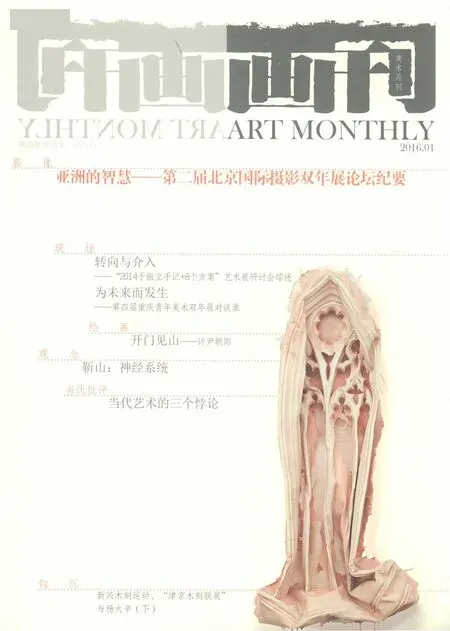当代艺术的三个悖论
马钦忠
当代批评
当代艺术的三个悖论
马钦忠
毫无疑问,当代艺术是当代美术馆众多展事的主流,无论走到欧洲、走到北美、走到日本,凡是繁荣发达之城一定有层出不穷的当代艺术活动置入其间;它的活动频度的指标值几乎可以看成是一座城市当代前沿的风向标,比如纽约、巴黎、威尼斯,回到中国,比如北京、上海,每一年总是有众多让人眼花缭乱的当代艺术展……
当代艺术展,不是活在当下的艺术家的艺术展,而是指以前卫的、先锋的、探索的价值观和思考方式介入当代人类社会的一种价值判断和公共知识生产方式,当代艺术展为这个时代的人文思想和判断创造高度和深度。这是我赞美、支持、推进这项活动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理由。
然而,我所说的“三个悖论”正在严重地侵蚀着当代艺术的人文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以下“正题”、“反题”并非形式逻辑严格意义的“非此即彼”,而是既有“此”亦有“彼”,既会有彼此交叉又可能有彼此对立。我的论述仅针对其中最典型的艺术现象。
第一个悖论:从艺术的基本属性走向反艺术属性
正题:当代艺术的人文精神的表达和探索,是以艺术的思维和艺术的方式进行的,它具有概念思维的属性,但不是概念思维的形象传声筒。
反题:发生在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当代艺术演化成了一场场观念演出,变成了拼命追求哲学意念的视觉和空间游戏,最终成了种种哲学观念的视觉翻译物,结果,谁的游戏出奇,谁的视觉翻译等同于哲学观念,谁就是当代艺术的“明星”,于是艺术死亡了。
综观20世纪诸多艺术流派和艺术思潮的此起彼伏,无不有一个观念主导。立体派追求数学和几何学的“科学观念”,未来主义深陷科技在20世纪之初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的盲目崇信,超现实主义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影响而沉迷于反理性的视觉创造,等等,但这些“观念”的主导,不是以“观念”的方式,而是以艺术的方式,落实在形、色、空间等视觉艺术的元素之内去解决和思考艺术的问题。
艺术的问题不是哲学的问题,艺术更不是艺术史扮演哲学史或思想史的,插图才是艺术发展的高级阶段。不幸的是,当代艺术正在朝这条死胡同奋进。美国艺术哲学家阿瑟·丹托(Arthur C Danto)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艺术要终结了。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尼古拉伊·泰拉布金(Nikolai Tarabukin)就对印象派以来的形式主义提出了批评,特别指出了从画的文学趣味和深度空间的幻觉技术制作走向平面,以使平面深度也同样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印象派通过光影创造幻觉,未来派力求静态画面动态感,构成派以点、线、面进行机械创作。“在完全丧失了杰出艺术家的基本特征的前提下,走向了同工程、技术和工业合作的道路”的结果,构成派的画作是“毁掉绘画”、“毁掉自我”。尼古拉依坚持认为“绘画不可能逾越表现的这些界限”,“对赤裸形式进行实验室的操作就是把艺术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阻止它的进步,将它引向穷途末路”。
这里必然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即杜尚 (Marcel Duchamp)。今天的当代艺术耍弄观念之风、玩弄现代游戏,始于这位智者,同时也是一位搅局者。
依据他的研究者和传记作者卡尔文·汤姆金斯 (Calvin Tomkins) 对杜尚的《被单身汉剥光衣服的新娘》的解释,这个装置的主旨是新娘和九个单身汉的“爱恨情仇”——第一幕新娘是发动机,是欲望源,是所有人类运转的核心、内燃机、爱情汽油库。分泌的“动力”是九个男性化的单身汉的欲求、渴望、追逐。所有的生命行为都为新娘的性欲望的激发而产生互斥、争斗、矛盾、排解。第二幕处女的神圣化即“无知的欲望”、“空虚的欲望”……从而新娘既允许又愿意“神采奕奕地满足”她自己的欲望:既被动又主动,即“永远楚楚动人而不被强奸,她永远处于欲望和占有之间的过程之中”[1]。这种看似很精妙的解说,几乎可以推演到任何场景之中,只要有兴趣,但除了编造还是编造。可是沿着这条道路,此风几乎成了艺术家比拼智力和构造能力的实验物。
我们随便可以找到太多例子。比如徐冰的《新英文书法》用这种指代游戏的构想不可谓不精巧和智慧。用他设计的一套解读方法,说英语的人通过简单培训,即可读懂他造的字。意义是什么?以艺术的方式说的跨文化沟通的消除文化误识误读?这种文化设计早已有了更好的样本——世界语,其作用几何?
可用人工智能领域的挑战者、著名语言哲学家赛尔的“中国屋”的假设加以类比,其设定是赛尔想象自己在一个屋子里,屋子有一个传入窗口和传出窗口。他的任务是通过充分练习之后,用中文符号编写答案传出。赛尔的质疑是在这个屋子里除了你编好答案供选,他不可能具备用中文的理解能力。设计如此完美的世界语没有人用它去建构跨文化的平台的境况与此类似。这堆符号没有供世界人滋养的文化储备,换句话说,精美的游戏系统没有落地的价值锚地。
到当代美术馆的众多展览,随便就可以找到这种指代游戏的无意义劳动。诸如一个装置艺术展,艺术家的创作说明上为你指明A物代表AX,B物取自何处,代表BX,D、C物是艺术家患病之时天天接触之物,因此代表CDX……于是美术馆演化成了这种指代游戏的坟场,一出生就死亡了。假如视觉艺术不是依靠视觉直接阅读理解意义,这个“视觉艺术”之谓还有存在的意义吗?
最典型的代表是今年的威尼斯双年展的获奖作品,即安德里安·派普(Adrian Piper)[2]的作品。此次组委会给她的颁奖词是:“通过个体的主体性——她自身,她的观念以及大众——革新了概念艺术的实践。”
且看她是如何革新“概念艺术”的。
作品要求:参观者与自身订立诚信合同,言必行,言行一致,以达到个体责任的终身表演。有三份合同供选择。且说其中之一:
“我们什么都买不起,但我会说到做到。”然后到“可能的信托注册台”去进行这场言行合一的自我道德自塑的游戏。
在我看来,或许是颁奖人没读过康德(Immanuel Kant)的《纯粹道德实践》和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的《正义论》,误把这个关于社会与自我的公平正义主体的基础建立的论证看成是派普的首创了。在我看来,这就是一节课堂道德小实验派对,而派普使之成为一个自己与自己演出的图解设计。
按此路径,当代艺术已成了哲学和思想的图解与说明,用形象示动的方法搬到美术馆或视觉艺术活动现场。视觉是有的,但意义外在于它;意义是有的,但是由视觉图解加以翻译。那我们还要这种艺术干吗?
第二个悖论:普遍的艺术人文精神的生产与商业利益机构操纵的艺术精神呈现之间,无法保证由此生产出来的艺术人文精神的公共性
正题:当代艺术活动是人文精神探索和关于生命价值理念拓展的公共的普适性的知识生产,它与私人利益和谋取私利是对立的。
反题:当代艺术活动离不开私人利益集团,他们组成运营的本质即是为了利益而来,因此,从前提上就不具备公共性人文价值生产的前提。
视觉艺术的发展离不开商业的支持,甚至可以说任何一种文化活动都不可能离开商业的后台作用。从文艺复兴的达·芬奇、拉斐尔到米开朗基罗,如若没有作为资金后台的梅迪奇家族的“艺术偏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精彩作品传世。近代英国的公共艺术赞助制度,更是对英国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需要明确的是艺术支持和赞助的资金支持的保障作用,不等于直接的商业利益的谋求,不是为了获取投入和产出比的巨大回报。因而对艺术家的创作和思考没有干涉,是在热爱艺术、崇尚艺术前提下的对艺术家的人文探索的基础生存条件的保障。
进入20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在他的《现代艺术哲学》第四章专门讨论了现代艺术的命运。核心就是说现代艺术失去了古代社会的庇护人和赞助人。美术馆、国家该如何以收藏、怎样收藏、谁决定什么人的作品该收藏的问题等等制度设计,解决艺术家的自由创作和探索不受利益左右而保证艺术人文的公共性意义。
而今天,我们正受到这种境遇的严重威胁。
在此,从“正题”向“反题”转化的典型例子以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Yayoi Kusama)的前后期创作为例。草间弥生早期以自己的裸体涂上斑点的行为表演挑战男权社会对女人的偏好性的观看社会惯例,带有强烈的挑战男性主导的社会习俗的颠覆意义;而近期以斑点演化出的奇妙色彩幻境,融入流行时尚,虽然被非常追捧,实质上不过是装扮成为有文化展演意义的取乐于参观者的观念演出,其后台是以商业利益为主导的“伪艺术”的美术馆嘉年华,没有什么人文价值的深旨。
我的质疑是:由画廊以及众多经营性机构从事的艺术产品如何能保证“正题”所述的人文意义的公平正义而不是以所谓文化的名义从事的商业陷阱?
比如,兴起于20世纪末的英国艺术家群体YBA[3],其幕后操控者为杰出广告人出身的推手查尔斯·萨奇(Charles Saatchi),他为这一批艺术家提出了重新研究日常庸俗事务的主张,即生死情爱、性、暴力、死亡、毒品的沉迷、淫欲的放纵、窥阴癖的死亡赞歌。其中的杰出人物达米恩·赫斯特一半商业智慧一半文化巫术,装神弄鬼,再加一剂营销妙方,便把《不确定时代的浪漫》推广成为全球瞩目之名作。且看此作“名”在何处:
耶稣和其门徒,死亡、殉教、自毁和升天,按教堂教义陈放,以直观的置景看到耶稣和他的十二门徒的仪式化死亡。神圣的陈列,摆放的是实验室的器皿、锤子、斧头和血迹斑斑的塑料管。每一个物品代表一个特殊门徒的殉教,母牛和公牛的头淹没在代表门徒的装满甲醛的玻璃橱窗中,放在中间的是标本。
这是在挑战西方人文化中的道德底线。基督教教义是一个实验室的殉教仪式的手术和制作标本示范。作品是对萨奇说的死亡、暴力、放纵的人文思考还是在公然嘲讽基督殉教是一场实验室演出?只不过场景不是医院而是教堂。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博得“关注率”。
更有甚者如安德勒斯·塞拉诺(Andres Serrano),他做了一件作品,在美艳无比的从上而下倾泻的红光里展现浸在液体下的基督受难。光影的技术运用营造出充满神圣感的氛围,但塞拉诺却告诉你浸泡基督的液体是艺术家自己的尿液,其作品名即为《尿溺基督》。得知如此,你会如何看待作品的意义呢?
塞拉诺专干这个活,他还用超高速摄影拍下他的血、尿、精液等等喷泻之时的“迅速之美”。
你能说这个“美学”有什么意义?不过是用超高速摄影拍下的一个技术产品,不过是人们不太会特别关注的“污秽”之物而已,但他的工作却成了美术史书写的话题和不停讨论的对象,塞拉诺也大有成为艺术史的代表人物之势。像这种无聊的“话题”美术史叙述常常成为诸多艺术史书写的大篇幅内容,艺术史竟成了话题和事件营销的附属品!
更有恶俗如杰夫·昆斯(J e f f Koons)之流,此君更是一位打着反思商业文化庸俗的幌子,却与商业利益合为一体营销的典范:这种直接把商品放大并放置在美术馆“指称”当代艺术的行为,实则是把江湖术士的骗术、伪艺术主张、艺术精准营销、制造事件传播合成一体的新的美术馆活动样式,是对当今时代人文智慧的最大嘲讽。中国艺术家中,蔡国强可视为其中一个出色的仿效者,他的“当代艺术”基本与此套路一致。蔡国强在西方美术体制和中国美术体制以及官方重大事件中总是能找到他的“当代艺术”的切入缝隙,让人们看到“当代艺术”的强大的应变能力和变通性。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他的火药爆炸,无所不尽其极,从西方到东方,从美术馆到各种重大嘉年华节庆,不论是爆在纸上成为天价拍品,抑或爆在东方空中成为盛世欢歌、爆在西方的天空成为文化交流的范例。每一点均可获利,这是以艺术的名义精准营销并全方位通吃的典范。你能相信这里面会有公共的人文精神?!这是十足的伪艺术,是以当代艺术的名义赚取的一把黑白通吃的利益“手术刀”,靠着这把“手术刀”,他打造了无数个实实在在的商业机遇。我不否认也不反对蔡国强的上述商业工作,我要说的是与当代艺术的人文价值一点关系也没有。
当代艺术所谓的“主流”现象和话题几乎均由国际性的艺术经营机构操纵和策划运筹,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件“文化盛事”,而背后无一不有各种利益集团筹划利益市场。而在表面上,各种传播方式,各种受雇艺术人和策展人,或间接或直接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进行所谓的文化意义的挖掘和艺术价值的公共意义的生产。对此,我的质疑是:
其一,这样生产或创作出来的图像及其雇佣者所诠释的“精神”是真实反映了这个“艺术界”的人文状况与思考的面貌了吗?
其二,由这些巨型机构操纵所登载在各种媒体、出版物上的无数“话题”艺术史思考和撷取的资料来源,能够反映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吗?或者说,这个状况难道没有为商业利益集团左右和操纵以及绑架的嫌疑吗?
第三个悖论:美术学院的当代艺术教育和美术馆活动之间的悖论
正题:美术馆作为当代艺术活动的主要场所,是针对公众审美教育和人文精神拓展及公共视觉知识生产的公共空间,不是当代艺术家谋生的职业场所,更非少数拥有专业技能的人展销专业产品的“俱乐部”。
反题:当代艺术的活动和思考特征表明,它不是一种职业技术行为,而是一种借助物质媒介工作的思、情、意的综合性创造,因此它是不可进行程式化的教育过程;但为满足众多的国内国外的当代艺术展事活动,一个职业化的技术大军的训练,于是便在我们的美术学院应运而生。结果我们便看到越来越多的职业当代艺术家,做着非常职业的艺术活动,而这个活动便越来越局限于这个技术化的职业圈子,从而使当代美术馆出现的当代艺术活动走向了背离美术馆宗旨的对立面。
“正题”的问题涉及当代美术馆这一公共空间的人文价值探索和生命理念拓展的公共性意义。从这个方面说,它不是一个创造具体的使用物品的职业劳动场所,而是启迪、开智、提炼和塑造时代的智慧高地,见证着特定时代人的生命深度与肤浅、健康和病症、完美与缺陷、塌陷和充盈。简言之,在这个场所产生的人文精神与生命价值的锚地有这样三个方面:时代智慧和生命情感探索的当代高点,传递创新的人文价值和引爆点,诠释经典的新历史境况的当代原点。
“时代智慧”是指对当代人文境况的呈现和把握,展现时代忧患,激发创造激情;“传递创新”的人文观,是指勇于反叛既定的戒律和所谓准则,履行人文精神继承和创新的历史使命;诠释“经典”的新历史情况的“当代原点”是指,你哪怕是沿袭传递固有的经典样式,但却赋予当代意义的精神价值,为当代人文精神诉求拓展了新的精神自由生长的空间。
在本文中我无意详细阐述我的上述原则,我的目的只是在于为我的下述论述和解释提供基点。
我的“反题”问题是:实验艺术的创作和思考方式,是一种阅历、一种感受、一种体验和价值判断。反之,当众多美术馆和从事当代艺术活动推广的机构协同满足众多美术馆和展场机构进行这一活动之时,必须要一大批从事当代艺术创作活动的产业大军,必须要有众多的“思想”、“价值”、“意义”被生产出来。推导出的结论是:“思想”、“价值”、“意义”必须由一大批并有代际承续的产业大军作为准备。于是,便有了“实验艺术教育”。
疑问接着而来。
实验艺术教育是专为美术馆展事活动培养职业大军还是思想生产者?如说是前者,显然,他们学装置、学观念、学观念影像,研究行为艺术观念,如此等等,显然难以到其他行当去谋生,是专门针对当代美术展示场所活动的一项专门技能。那么,这样一项专门技能一定会产出“思想者”吗?反之,这由职业技能教育而着眼于培养当代艺术“思想方式”真的是通过这种方式被培养出来的?从道与艺的关系上说,任何一门教育都一定会预设“道”的原则和“艺”的技艺,非为当代艺术教育所独专。那么进一步的追问是:“思想者”是实验艺术教育出来的吗?
正是这样的悖论,我们看到美术创作“思想”呈现的现状:
第一个特点是美术馆成了生产“意识工业”(Consciousness Industry)的作坊展示基地。可举一个艺术家莫里斯(Robert Morris)为例。他在1968年发表的《反形式》一文里主张不要明确形式、不要恒久性、不要轮廓,因而他用特别工业化的方式创作作品,无聊而乏味,直观、易懂但却全无意义,是杜尚的挪用的拙劣版。按他的主张,谁都有权利指认山货店为美术观念的呈现。这种噱头在当今美术馆展览中层出不穷。
第二个特点,当代艺术变成为一场点子的比赛,变成为“无中生有”的臆想竞赛的名利场。我并不是反对“想象力”在当代艺术创作中的作用,但它必须是“想象”,必须要有人文精神指向的锚地,在人的生命情感和社会向度上产生唯有艺术才专有的作用力。这个作用力不是催生出来的,不是模仿编造出来的,它产生于艺术所特有的精神品质。康德、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以及到了20世纪后半叶的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无不是从精神与生命价值的内在直接性上去看待艺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新希望的。
但是,当这个与生命价值的内在直接性的精神创造转变成为一个庞大的专业训练出来的生存工具,以后台的技术化、程式化、利益化的操作和隐性运营,打着公共文化利益的名义,告诉我们这如此等等的工作在进行着人类社会的拓展的自由的隐喻的时候,实质上已失去了根本的基础。我们很可能是在美术馆这个以公平正义、公众文化福祉的名义建立的活动场所,为职业策展人、艺术投资商、各种投资基金,直接雇用或间接雇用的专事美术馆活动的这一类职业艺术家的合谋,制造着一个所谓的人文精神,着眼点便是它背后的商业利益。
为此,我们很难保证,这不是一个以当代艺术的名义述说的欺世谎言。
美国艺术家纽曼(B a r n e t t Newman)在《第一个就是艺术家》中说道:
文字记载中最早的人类欲望证明世界的意义是无法从社会行动中找到的。审视《创世纪》的第一章,即对人类的梦想提供了一较佳的线索。对古代作者而言,不能理解的是:那最早的人类亚当,是派来地球做苦工,做社会动物的。作者的创作冲动告诉他:人的初衷是要做艺术家,他把他放在伊甸园,靠近分辨善恶的智慧之树,在神最直接的启示中。该作者及其读者所了解的人之堕落,也不是像宗教家要我们相信的从仁慈到罪恶的堕落,而是亚当吃智慧之果后,开始寻求创造的生命……[4]
这个“寻求创造的生命”一定不是生产出来的,一定不是培训出来的,一定不是投资人投资而收取回报后变成公共文化的价值的;它一定是扎根在艺术精神的锚地——人的生命行程之中的。
2015年11月27日
注释:
[1]【美】卡尔文·汤姆金斯《杜尚》,湖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94-97页。
[2]安德里安·派普(1948-),美国概念艺术家、哲学家。
[3]YBA是Young British Artists的缩写,意为“年轻的英国艺术家”。这一称号源自萨奇画廊1992年的同名展览。YBA的艺术家,多半毕业于伦敦的歌德史密斯学院(Goldsmiths College),其中的代表人物有达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特雷西·埃敏(Tracey Emin)、吉莉安·韦英(Gillian Wearing)等。
[4]Herschel Chipp编《欧美现代艺术理论》③,吉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