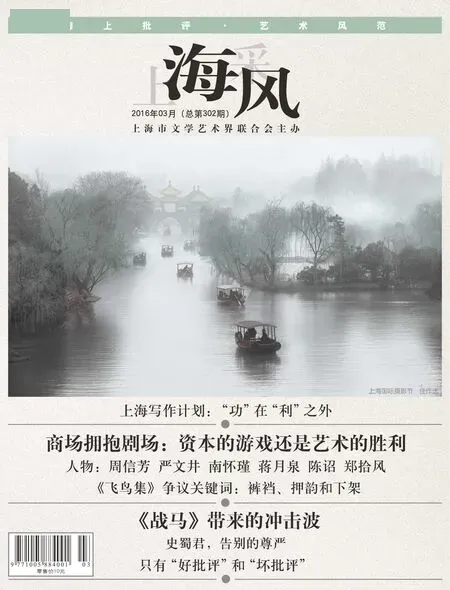评弹一代宗师蒋月泉与师友之间
文/吴宗锡
评弹一代宗师蒋月泉与师友之间
文/吴宗锡

蒋月泉是近现代评弹流派唱腔传唱最广的“蒋调”的创始人,他对评弹表演的主要手段“说噱弹唱”都有很高的造诣。新中国建立后,他致力于评弹表现现代生活的书目建设和艺术的革新提高,他参与编演的现代中篇《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海上英雄》《王孝和》《江南春潮》《白求恩大夫》《人强马壮》,以及长篇《夺印》等,都为评弹书目和艺术的创新发展打开了新的生面,他还为传统长篇书目《玉蜻蜓》《白蛇传》的推陈出新、整理提高作出了卓著的成果。因此,被评弹界以及广大听众,众望所归地推崇为“一代宗师”。
蒋月泉在艺术上的杰出成就,诚然主要在于他的超群秉赋和刻苦敬业,同时,也是和他的善于思索、虚心学问、尊重领导、敬师爱徒、广采博纳等优点分不开的。他的这些优点突出地体现在他与老师、门徒、搭档,以及上海评弹团的同仁们的交往、合作、情谊之中。
蒋月泉与老师
蒋月泉最初师从评弹艺术家钟笑侬学传统长篇弹词《珍珠塔》。唱《珍珠塔》的,都唱“马调”唱腔流派,钟笑侬的风格,更注重唱调的语言因素,明快流畅,长于叙事。但蒋月泉以唱委婉柔美的“俞调”打下了深厚的功底,他偏爱细腻抒情,且又不喜欢《珍珠塔》这部书的书情书性。于是,他就改投以说《玉蜻蜓》著名的张云亭为师,学说《玉蜻蜓》。不过,对于钟笑侬他一直执弟子礼,非常敬重。蒋月泉进了上海人民评弹团之后,还曾推荐钟到团里担任艺术顾问。
张云亭出身艺人世家,说表凝练细致,熟谙评弹结构、技法,语言精到。能敷陈书情,丰富内容。蒋月泉跟了他,在说功上打下坚实基础。张云亭有一个习惯,每天下台后,躺在榻上想书,琢磨书艺书情。每有心得,便随手记在香烟空壳上,顺手抛进身后的字纸篓里,日久后,积聚了一大篓。蒋月泉满师时,师母见他勤奋好学,将篓中的空壳字条悉数送给了他。蒋月泉如获至宝,拿回家去,仔细研读,不但丰富了自己的书情内容,而且还从中学到了结构书情、提炼语言的方法要领和技艺。
蒋月泉早岁因在电台演唱开篇而一举成名。他在江浙码头书场演出时,一次借宿与他在同码头演出的姚荫梅处。晚间二人促膝交谈,谈到书艺和声名,姚荫梅坦直地对他说:“你的弹唱很好,但说还不能与之相配。声名很响,名实未必相符,好像小身体穿了一件大衣裳。”听了姚荫梅的直率诤言,蒋月泉并不感到不快和气馁。从此他更奋力于自己书艺的全面提高,注力于说噱技艺的研究。
蒋月泉在弹唱《玉蜻蜓》的“同册”中,十分钦佩周玉泉的艺术造诣。周玉泉曾向有“翡翠玉蜻蜓”美誉的名家王子和学艺,又形成了蕴藉飘逸的“阴功”风格,并创始了自己的“周调”唱腔流派,是上世纪30年代驰名上海的三大单档之一。但周玉泉的老师王子和是张云亭的胞兄(张云亭入赘张姓),故若论长幼辈分,周玉泉应是蒋月泉的“隔房师兄弟”,属于同辈。然而蒋月泉心仪周玉泉的艺术造诣,为了艺术,尽管那时蒋月泉也已是驰誉沪上的响档,他仍然愿意降低辈分,拜周玉泉为师,虚心受教。在学艺三年之后,又充当周的下手,拼档一段时间。从此,蒋月泉的书艺,有了全面的飞跃提高。他后来说:“我有幸得到了这样一位好老师,正如临摹到一本好的字帖,打下了正宗的扎实基础。”今天脍炙人口流传最广的唱腔流派“蒋调”,也就是在“周(玉泉)调”的基础上创始发展而成的。1961年,周玉泉到上海演出,在一次上海人民评弹团的宴请会上,蒋月泉说:“我拜了周玉泉先生才取得今天的艺术成就。”而周玉泉接着说:“有了你这样一位学生,也使我增光不少。”应该说,二人说的都是实情。
蒋月泉与搭档
蒋月泉为周玉泉当了一段时间下手后,自翻上手,曾与师弟钟月樵拼档说《玉蜻蜓》,钟月樵说书认真规矩,弹唱也有功力。蒋钟档是上世纪40年代上海的“七煞档”之一。1948年,蒋月泉又与自己的大弟子王柏荫拼档。王柏荫也曾跟张云亭学艺,又曾随蒋月泉聆听周玉泉的演唱,其书艺书风和蒋月泉更为接近。在拼档演出期间,两人在下台之后,常切磋书艺。有时散了夜场,步行回家,两人住得较近,便一起边走边谈,讨论书艺。往往学生把老师送到家门口,欲罢不能,老师又把学生送回他家门口,还是谈论不完,又送来送去,反复几次,最后还要站在家门附近马路转角的一只高大的邮筒旁边,谈到夜深方才分手。用蒋月泉的话来说,“真是比谈恋爱还要热络”。由于他们师徒情深,对艺术有着共同的热爱,对书情理解较深,演出时配合默契,上世纪50年代初,成为沪上著名的双档。
王柏荫的学生苏似荫,一度也跟蒋月泉听书学艺,并当过他的下手。上世纪50年代初进入上海人民评弹团,受到团内的多位名家辅导,成了中年演员中的佼佼者,被誉为团中的“硬里子”。在1984年举行的“蒋月泉艺术生活五十周年纪念演出”时,蒋月泉师徒、祖孙三代同台,拼档演出《玉蜻蜓》选回。蒋月泉上台的开场白,先自谦了几句,然后介绍说:“坐在下首的是我的学生王柏荫,他的书艺精湛,有些地方已超过了我,是‘青出于蓝’。”接着再指指坐在王柏荫旁边的苏似荫说:“那边还有一位‘胜于蓝’呢。”一句成语经蒋月泉的活用,既介绍了他与王柏荫、苏似荫的关系,又表达了他对后辈的称扬,博得了满场热烈的掌声。人们赞赏他的机敏、睿智,也称道他的虚怀若谷,一时传为美谈。
1959年,上海人民评弹团为了集中艺术力量,根据团内拼档优化组合方针,对主力双档作了调整。蒋月泉开始与朱慧珍拼档。朱慧珍在评弹听众中向有“金嗓子”之誉,蒋月泉曾评价说:“她功底扎实,唱的‘俞调’‘蒋调’严谨官正,契合法度,技艺全面。她的书艺称得上是纯、真、正。”拼档时,二人正值盛年,一心扑在艺术上。团领导为他们配备了作家陈灵犀,合力整理传统长篇书目《玉蜻蜓》和《白蛇传》,三人团结合作,可谓“珠联璧合”。蒋月泉后来回忆这一阶段他们双档的工作情况时说:“这阶段中我们全部的生活内容,也即是全部的工作内容,可以说,就是:默书,想书,搭书,说书。每天上台说一回新写的书,上午排,下午说,傍晚修改,夜场再说,下了台还要讨论研究,也无暇再顾及别的什么了,但是合作愉快,感到充实。”

蒋月泉与朱慧珍同台表演
蒋月泉、朱慧珍的唱功都是上乘的。他们有着共同的艺术追求,为塑造动人的艺术形象,抒发真挚的感情,他们发展了“蒋调”“俞调”的新腔,并创造了男声“蒋调”与女声“俞调”的对唱,对评弹弹唱作了开拓性的发展,被听众称为“蒋朱调”,成了评弹男女声对唱的一种典范。他们又在团领导的策划、辅导下,完成了《玉蜻蜓》《白蛇传》中的菁华选回《庵堂认母》《端阳》《合钵》等的加工整理,对文本和表演艺术都作了精心的创造,成为传世的经典书目。蒋月泉后来一直说:“这一段艺术生活是令人难忘的。”
1960年代后,朱慧珍因患病,不得不辍演。蒋月泉由领导安排,与当时的青年演员余红仙拼档,改编、排演长篇现代书目《夺印》。余红仙嗓音嘹亮,响弹响唱,朝气蓬勃,但缺乏严格的说唱基本功训练。蒋月泉弹唱细腻,抒情,讲究韵味;而说表又以温文飘逸,注重结构、修辞见长。拼档之后,蒋月泉以前辈对后起精英的爱护和责任感,通过排练、演出,精心辅导。一个时期下来,余的书艺有了较大的长进。拼档演出的新的长篇书目《夺印》,受到了陈云同志的称赏和听众的欢迎。
蒋月泉与合作者
除了演出长篇的拼档合作以外,蒋月泉还在演出多部中短篇时,与上海评弹团的多位艺术家同台合作演出。对于这些合作者,蒋月泉总能发现和称扬他们的特点和优长,并称揄配合。
蒋月泉曾多次与刘天韵同台演出,曾在刘天韵创演的选回《义责王魁》中担任下手,起书中的反面角色王魁。书中刘天韵起的义仆王忠在训责王魁时,有一档用“陈调”唱的唱篇。为更好地表现人物,使演出取得最佳效果,蒋月泉特地为刘天韵将这档“陈调”作了辅助加工。在演出中篇评弹《林冲》的《血溅山神庙》书回时,蒋月泉和刘天韵分起林冲与陆谦角色。当林冲举刀砍向陆谦时,林冲口念:“陆贼,林冲与你何仇恨,杀人放火丧良心,今日相逢取你的命,手执钢刀杀仇人!”起陆谦的刘天韵做功十足,一声接一声连连哀求:“林兄,林兄!”他声嘶力竭的哀号中流露出了人物的虚伪狡诈和阴险奸刁。蒋月泉说:“刘天韵这样充满激情的表演,能勾起自己满腔的愤恨,有力地把刀劈下去。和其他人拼档,就缺乏这种激情,总觉得手中的刀劈下去时,表演的仇恨和狠心不够。”

弹词名家蒋月泉和刘天韵同台演出
徐丽仙在1951年演出书戏《众星拱月》时,为蒋月泉发现,推荐进上海人民评弹团。进团之后,显示出了她的音乐才能,谱唱了《罗汉钱》《情探》《新木兰词》等多部新作,受到听众热爱,声誉鹊起。开始时,蒋月泉心中不服,便在家中反复研听徐的《新木兰词》录音,总结出了其创腔和演唱艺术的优长,便主动为她揄扬、推介。有人贬抑徐丽仙,说她“只善唱,不善说”。蒋月泉和徐丽仙拼档说过现代短篇《错进错出》,他听到这些议论后,就出来以拼档演出《错进错出》的切身感受为徐丽仙辩护,说:“《错进错出》这回书,对演员要求很高,上下手‘搭口’要紧凑,节奏要快,就像打篮球一样,传球接球,快慢高低,不能差一分一毫。徐丽仙说这回书,角色到位,分寸感强,与上手配合默契,十分出彩。这就说明,她是善说的,而且说功相当扎实。”
蒋月泉曾与杨振雄同台演出中篇评弹《王佐断臂》。在《说书》一回中,杨振雄起陆文龙,蒋月泉起王佐,有大段唱篇。他自弹三弦,由杨振雄琵琶伴奏。蒋月泉的润腔,十分精细,对伴奏要求很高,在演唱之后,他对杨振雄的伴奏较为满意,称道说:“杨振雄弹的琵琶虽然是‘清点子’,但他懂艺术,理解书情和人物,衬托恰到好处,唱的人能够充分发挥。”此外,他还多次称扬张鉴国的伴奏也十分好,能使唱的人感到舒服。
蒋月泉在演出长篇《林冲》时,曾邀张鸿声和他与朱慧珍拼“三股档”,起鲁智深角色。后来在多部中篇中,都与张鸿声合演。他常称赞张鸿声书艺精湛,善于创造角色。在《海上英雄》中张鸿声起了自夸却又胆小的敌军官苗科长,《白虎岭》中张鸿声起了贪欲颟顸的猪八戒,《江南春潮》里则刻画了情急之中抓头发、吹电话筒的敌轮机长等。蒋月泉说:“张鸿声会刻画人物的性格特点,表演生动,而且有放噱的特长,他表演的角色很能取得喜剧效果。”蒋月泉是深谙同团的艺术家们的优长的,也乐于在谈艺时加以宣扬。
蒋月泉和作者
弹词开篇《杜十娘》早在上世纪30年代,由蒋月泉在电台播唱而成为广为人知的“蒋调”代表作,但作者的姓名一直不详。直到1982年,上海人民电台转来了一封给蒋月泉的信,才知道作者名朱恶紫,是苏州黄埭镇人,当时已经年逾古稀。蒋月泉收到信后,立即写了复信,并在电台宣传,对作者为自己提供演唱内容表示恳切的感谢,又称赞开篇符合评弹的演唱规律,叙述晓畅。其实,开篇《杜十娘》的演唱之所以受到听众欢迎,更主要的还在于蒋月泉的唱腔幽美,韵味醇厚。是“蒋调”为开篇赢得了成功。
与蒋月泉合作时间最长的作者,当首推陈灵犀。陈灵犀原是一位资深的报人,在沪上与唐大郎等齐名,曾任《社会日报》编辑。1949年,他应蒋月泉之约,为他编写长篇弹词《林冲》,后来也进了上海人民评弹团,成了一位专业评弹作家。有一段时间,他的主要任务便是与蒋月泉、朱慧珍合作整理传统长篇《玉蜻蜓》《白蛇传》。陈灵犀的文笔很好,但毕竟缺乏上台的经验,对评弹语言不够熟悉。在书写、排书时,需要常常与蒋月泉切磋探讨,交换意见。陈灵犀能听取蒋月泉的设想、要求,蒋月泉也能虚心尊重陈灵犀的创作和建议。长篇书目在书场上演,一天一回,书情延续,不能中断。每天“等米下锅”,写一回,排一回,演一回,演过之后,还要根据听众反应,进行修改,工作十分紧张。要等书目告一段落,才能放松一下。有一次,在苏州,二人得空,去留园吃茶,对坐了三个小时。有时,扺掌倾谈,滔滔不绝。有时,默然相对,不发一言。对此,蒋月泉讲:“所谓知己,最难得是相处随便,可以随便谈谈,可以随便不谈,彼此心照,可称神会。”陈灵犀也说:“这也是友情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吧。”还由于这种友情的契合,他们合作编演的《庵堂认母》《厅堂夺子》《大生堂》《林冲》等都成了评弹的经典书目。
数十年来,蒋月泉与师生、同仁们的交往共事中,这样契合融洽的事例是很多的。尤其在他参加了国家举办的上海人民评弹团后,加强了对人生价值和艺术理想的追求,提高了对工作对生活对群体的认识和思想境界。纯正的艺术原就需要出自内心的真挚感情,蒋月泉也把这种真挚的感情融入了对事业和同仁的热爱之中。
在恐怖肃杀的“文革”浩劫如火如荼的高潮时期,工宣队和造反派逼迫他写对领导和搭档的“批判、揭发”,蒋月泉贴出的大字报上,却写着“朱慧珍是好党员,吴宗锡是好领导”。观看大字报的人无不为他捏一把冷汗,而他却默默地忍受着劈头盖脸的酷烈呵斥和辱骂。人们看到他一言不发、面无表情的样子,觉得他似乎已经麻木迟钝,却又感觉他内心燃烧着炽烈的爱。
晚年他在香港养病,想为心爱的评弹艺术做点什么,但体力衰颓,力不从心。他回忆过去的工作,也想念过去一起为艺术事业奋斗的同事们。
1993年12月17日,他写信给我,说起自己衰病的近况,还说要为艺术再作点贡献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他回忆过去在评弹团的工作,写道:“许多年来,有一点成就,皆党的领导所赐,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并还说,“想起了过去,少不了也常想起你。”看了信真令人感动。
作为一位高尚的敬业的艺术家,蒋月泉对艺术对师生对同仁的感情是热烈和真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