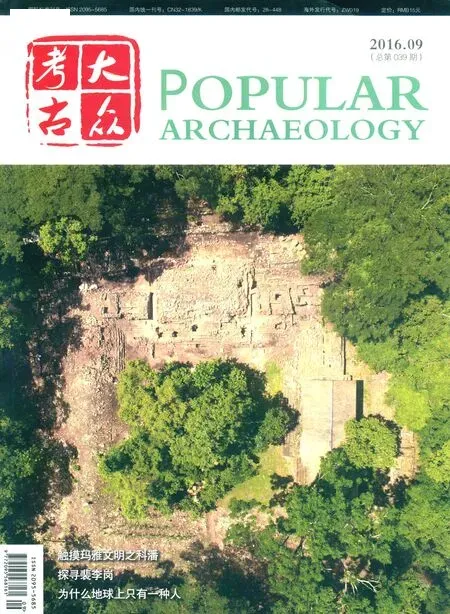考古学为人类观察生产力的演变规律提供重要启迪
考古学为人类观察生产力的演变规律提供重要启迪
生产力中人是主体,但“工具”却是直接的载体。富兰克林说过:“生产工具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指示器”;马克思也讲:“生产工具所代表的劳动手段是劳动所在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为此,考古学者十分重视古代生产工具的发现和研究,并由此判断社会的生产水平和发展阶段。
1836年,丹麦学者汤姆森在《北方古物指南》上提出了他于1816年就已发现的人类经历过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三个时代”说。这一学说使得人类对从旧石器时代到文明诞生时期的物质文化形态特别是生产工具的形态有了明确的先后演变序列和时代特征的总结性认识,为考古学乃至博物馆的历史陈列分期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所以有学者认为“汤姆森发起了一场平静的革命”。
汤姆森的“三个时代”说虽然开始时是以北欧地区的材料作为立论的依据,但是却成为具有全球性意义的考古学视野下人类生产工具演变的指导性理论。以中国为例,同样经历过这三个时代,只不过中国的“铜器时代”已经步入文明时期,而进入“铁器时代”时,“封邦建国”的政治体制已经达到一定的发达程度,从而呈现出文明早熟性的特征。
考古学材料所揭示的生产工具的三个时代演化规律,不仅对于观察人类史前时期乃至历史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演替有重要意义,而且还有助于人们从更加广阔的视野下认知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总体变化规律,从而具有了重要的思想史价值。以中国考古学资料为例,“三个时代”说实际涵盖了中国史前时期、夏商周时期、秦汉到明清时期三个大的历史阶段;就中国“农业文明”发生发展而论,至少从石器时代石制工具开始,到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工具,再到战国及此后的铁工具,成为观察不同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物质文化标志。
让我们把目光从古代延伸到近现代。人类在18世纪末开始,告别“铁器时代”而进入了“蒸汽机”或“机器”的时代,一个全新的“工具系统”成为新生产力和“工业文明”诞生的标志。这样的一种新型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在19世纪中叶也进入了中国并演化发展到今天。我们可以发现,从三百多万年前开始的石器时代到四五千年前的铜器时代,再到两三千年前开始的铁器时代,在“机器时代”到来之前,人类主要是运用“体能”与工具的结合而形成基本的生产力,“机器时代”则需要“技能”与机器的结合,因为其动力的很大部分已由机器所取代,而且,从机器诞生之后,走过了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等不同阶段,动力越来越由机器本身所承担,“技能”的重要性越益显著。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人类发明了“计算机(器)”,以“计算器”为主要功能的新的生产工具,“数学”这一科学上的皇冠开始进入生产工具领域,仅仅过了不到100年的时间,“计算机”或者说“电脑”已经把人类的生产力表现方式从“技能”推到了“智能”阶段,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信息化、智慧化等为代表的新生产力席卷全球,它以数字工具与模拟人类思维能力有机结合的方式促进了人类生产力迈上了更高的台阶。这让我们想起诸多名言:首先是它基立于“科学”的进步而产生,而马克思说,科学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其次是“数学”全面融入普遍联系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中,而“数学”被历代学者们看成是宇宙得以存在的秘密,是“自由”的某种表达,是一切科学的皇冠,如毕达哥拉斯说“数统治着宇宙”,雅克比说“上帝是一位算术家”,康托说“数字的本质在于它的自由”,赫尔曼威尔说“数学是无穷的科学”,马克思说“一门科学,只有当它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能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等等;第三是这种新工具所具有的“思维”能力让它部分代替了“人脑”,而人之高级思维能力的产生是人能够创造和推进文化的根本力量。
正是基于考古学对于人类工具在数百万年运动过程中所表现的变化规律以及对于史前社会和古代社会奠基性作用的认知,人们才会从后来的以“机器”的产生及其演变乃至“计算机(器)”的出现及其所代表的新的革命性生产力的产生,发现了生产力演变背后所呈现的人类从“体能”到“技能”再到“智能”的演变及其与工具之间关系的契合所代表的人类总的生产力演变规律的把握。可以说,考古学家的发现为人类认识生产力演变规律奠立了第一块理性的基石,而生产力的演变趋势则为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社会的出现展露出黎明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