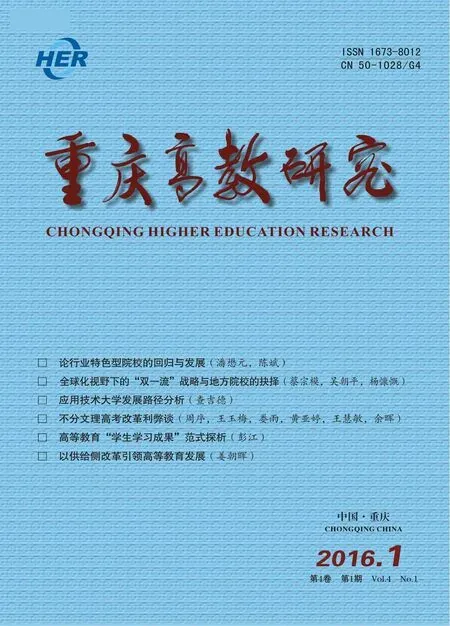抗战时期西南地区高等院校科研特征研究
贾红旗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 重庆 北碚 400715)
■ 西部高教论坛
抗战时期西南地区高等院校科研特征研究
贾红旗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重庆北碚400715)
摘要:抗战期间,伴随着高等院校迁入大后方,中国学术科研的空间布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这一时期的学术、科研取得了丰硕成果,并呈现出四大显著特征:学术研究,顽强执着;技术创新,支持抗战;注重实证,卓绝前行;史哲研究,昭启自信。抗战的实际需要、资源相对集中、政府政策支持和国际社会援助等因素,对西南地区高等院校学术科研特征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抗日战争;西南地区;学术研究;特征
抗战爆发前,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主要分布在京津、苏沪浙和广东等地区,学术科研成果也集中在这些比较发达的区域,而且学术研究偏重于理论,不注重实用技术。抗战爆发后,中国的学术科研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影响和破坏,战区的科研活动难以为继,大量科研院所纷纷向后方迁移。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内迁使得学术研究的空间布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西南大后方成为学术科研的中心,呈现出特定时期、特定区域的特点。
一、抗战时期西南地区高校院所的科研概况
战时西南大后方的科学研究获得“跳跃式”发展是伴随着战区的高等院校和数以千万计的科技人员内迁而实现的。在抗战期间,西南地区汇集了中国最优秀的高等院校和学术界的全部精英,他们都是战时西南地区科学研究最有价值的资源。同时,根据科研发展的内在需求,学术刊物在重庆、昆明、成都、桂林等高校聚集区大量复刊或创办,《现代科学》《中国化学会会志》《公路月刊》《中华医药杂志》《边疆人文》《华西边疆学会杂志》《农院专刊》等在各个领域都发挥了承载和传播学术成果的重要作用。
战时环境下的科学研究,不仅要注重纯学术理论的探索,还要加强实际技术的创新。这既符合学术发展的内在需求,又能满足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需要。作为相对稳定的西南地区,学术研究在各个学科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理科研究在抗战8年时间里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百篇论文,出版了多部有影响力的学术专著。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广泛而深入:物理学方面有马士俊、王竹溪、王淦昌、束星北等对原子能、热学、中微子、相对论等的研究;数学方面有陈建功、苏步青、陈省身、华罗庚对三角级数、微分几何、微积分几何、解析数论等的研究;化学方面有郭质良、张其楷等对纤维废物、有机药物的研究;地质学方面有李四光、丁毅等对地质构造、矿产资源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在当时大都是世界性的、开拓性的,对我国乃至世界的科学发展都发挥了较大的促进作用。应用技术方面,如冶金工业、兵器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农业科技等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据统计,1938年至1944年在机器、化学、交通、电器等领域的专利申请高达423项,是战前总和的两倍,有力地支援了战时生产生活的需要。
人文社会学科同样成就斐然。冯友兰、金岳霖、唐君毅、陈寅恪、蒙文通、钱穆、闻一多、朱自清、王力、吴宓等学者分别在哲学、教育学、史学、文学艺术、语言学等领域出版数部专著,影响深远。最具特色的是内迁高校对西南边疆民族教育的调查研究。西南联合大学、华中大学、华西边疆研究所、金陵大学等科研院所深入西南边陲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地考察少数民族的宗教、教育、经济、社会等状况,取得珍贵的一手资料,在我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性意义。
二、抗战时期西南地区高校科研的特征
(一)学术研究,顽强执着
科学与技术是不同的,它是一种纯理论性的知识,并不是可以直接用在战场或者工厂的工具。虽然科学研究成果不能直接应用到现实的生产生活中去,但战时西南地区的科学研究在艰苦的环境下依旧维持着,并获得了诸多成就。1944年,在印刷条件极其艰难之下还有80余种学术刊物出版,可分为以下六类:一般性质17种,纯学术性质(包括地学土壤)32种,农业14种,工业7种,医药13种,科学教育2种。加上蓉昆桂黔以及西北各地,总计起来应有100种以上[1]172。1939年在上海出版的《科学》杂志收到绝大部分来自大后方的科学论文,超过1938年的51%,《科学》的篇幅为之增加[2]。在以后的诸多年份中收录的来自大后方的学术文献亦逐年增长。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优秀的学术论文在国外著名刊物上发表。仅通过李约瑟主持的中英科学合作馆推荐介绍至国外发表的学术成果,在1943年就有30篇,1944年和1945年增加到108篇[3]74-75。其中涉及物理学21篇,数学14篇,工程学11篇,生物化学、生理学、药物学及内分泌学17篇,气象学、地质学及地理学4篇,化学4篇,实验形态学16篇,动物分类学及昆虫学6篇,植物分类学及菌类学5篇,植物生理学及病理学12篇,动物病理学及寄生虫学7篇,细胞学及遗传学8篇,农学1篇,人类学、社会学及经济学8篇,科学史1篇,杂类3篇。在一个几乎完全没有工业化的国家,处于最严重的战时情况下,这些数字一定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科学水准相当高的证据,是“一项优异的工作”“一项最辛苦而仔细的工作”[3]75-76。在科研和教学过程中,各个领域内的学者出版了诸多优秀的学术专著。如自然科学类有周培源的《激流论》、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苏步青的《曲线射影概论》、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郭祖超的《医学与生物统计方法》(上、下)等,社会科学类有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闻一多的《楚辞校补》等。
(二)技术创新,支持抗战
战前,我国科学研究一直十分落后,主要工业品依赖进口。在日本的军事封锁下,中国的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受到严重威胁。若要坚持长期抗战,依赖进口是不现实的,所以工业建设必须自给自足。为此,1939年11月20日筹建了全国特种工业研究委员会[4]12。当时确定的特种工业研究范围为:其一,与兵工事业有关者:钢铁,非铁金属及合金,光学玻璃,国防化学。其二,与生产事业有关者:液体燃料,内燃机,机械工具,化学药材(药品)。其三,与特殊工业相关者:航空工程,无线电,医用药品。虽然该委员会最终没有成立,但是各类研究项目通过其他途径分别在不同的机构得以实施,并很快取得了成果,通过技术创新有力地支持了抗战。如西南联合大学对工业燃烧引擎、水力涡轮机和锅炉的研究,重庆大学对钢铁、木材、钢筋混凝土以及道路材料的研究,刘克生的5吨小型炼铁炉,张钊的转缸式飞机发动机,侯德榜的侯氏制碱法,徐卓卿研制的新型氧化铬和刘仙洲承担设计的工业燃烧引擎、水利涡轮机等。再如各种类型和口径的火炮的制造,多种类型飞机的研制,试验17 455次终于成功的飞行竹制副油箱的广泛使用,第一架军用望远镜的成功制造,战时道路桥梁科研的广泛开展及成果的应用,用木炭、煤油、桐油等作代用燃料的研制和使用等等,都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满足国防建设需要的同时,各科研机构还注重对本地区农村的生产生活进行必要的研究,并获得了重大成果。中央农业实验研究所注重蔬菜、水果、茶园的改良和蚕桑优化、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四川大学的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研究重点长期放在水稻、柑橘、井盐、制糖、油气、林业方面。农学院杨允奎、杨开渠培育了数十种米质优良、早熟、高产、抗病害的水稻良种,在四川地区推广,至今仍收效益[5]45-46。
(三)注重实证,卓绝前行
抗战前的科学界,“一般研究自然科学的人,不免有些偏重书本和室内工作,对于自然界的认识,终感不足”[6]。同时由于西南地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科研工作者很难到达这些地方进行实地的调查研究。战争爆发后,各高等院校及专家纷纷西迁,西南地区便成了最重要的科研基地,尤其是崇山峻岭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这些地方对于生活在发达舒适地区的科研学者来说是陌生而又充满惊喜和挑战的。
1939年,中华自然科学社发起成立西康科学考察团,实地考察气象、地理、农林等。同年,中英庚款川康科学团实地考察生物、地质等。中央研究院地质所在所长李四光的带领下,先后考察了广西全部、湖南、湖北西部、江西、福建大部的地质矿产,并绘制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地质地图;另一部分人到河西走廊研究石油地质,并勘探出我国早期最大的油田——玉门油田。上述科研调查活动摸清了我国西南、西北地区的生态、资源和地质条件,也有效区分了西南、西北地区的自然差异,留下了丰富的科研资料,为战后开发西南和西北地区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同时,社会科学的研究也转向西部边疆问题与民族、社会问题,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拓展了新的研究视野,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1941年社会学家李安宅在成都发起成立华西边疆研究所,他本人及研究所成员曾深入西康研究藏族各教派的详细情况,发表了多部研究边疆问题的专著。1942年,西南联大成立了“以边疆人文为工作范围,以实地调查为进程,以协助推进边疆教育为目的”的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对云南峨山、玉溪等县聚居的纳苏、苗族、哈尼、傣族、彝族等偏远少数民族语言、风俗、社会经济和地理环境进行了深入调查[7]128。在此过程中先后完成《漠沙土语》《元江水摆彝语》《大明庵寨黑倮语》《三马头倮语》等调研报告。除此之外,还有金陵大学、大夏大学等院校对西南社会和特种民族风俗的调查[7]129。
(四)史哲研究,昭启自信
抗战时期我国社会科学成就斐然,尤其是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领域,成就了一批享誉中外的学术大师,产生了一批影响深远的著作。在国家正值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拥有强烈爱国情怀的高校知识分子清楚地意识到抵御外侮、取得抗战胜利,必须增强国民自信心,特别是建立在本国历史和哲学基础上的国民自信心。抗战时期大量的人文社科论著表现出弘扬民族精神、为抗战服务的显著特征。史学大师钱穆注重传统文化对民族自信心的建构,这一时期先后创作出《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虽然文中有夸大异族残暴统治、贬低异族王朝对中国文化发展所做贡献等内容,但完成于挽救民族、挽救国家于危难之际的全面抗战形势下,对于弘扬民族文化、提升民族自信心具有很大的作用。雷海宗在此间完成了《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的撰写,该著作提出“中国文化周期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只有中华文明拥有“第二周期返老还童的生命”,期望通过抗战产生第三周期的新文化。这一论断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也表达了中国必胜的信心。
梳理中国哲学,从哲学中也能寻找到民族精神之精华。冯友兰在战时著成《贞元六书》,之所以起名为“贞元六书”,意指中国社会的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即将到来。《贞元六书》是冯友兰将中国哲学融入抗战生活的具体体现。他曾坦言:“抗战时期,本来是中日两国的民族斗争占首要地位,这就更加强了我的民族观点。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认为中国过去的儒家思想既然能够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使之成为伟大的民族,使中国成为全世界的泱泱大国,居于领先地位,也必能帮助中华民族,度过大难,恢复旧物,出现中兴。”[8]255在国难时期民族危亡之际,无论是史哲还是文学都在积极地为中华民族寻找精神武器,呼吁民族团结,提升民族自信,引导着中国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三、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科研成就的成因分析
(一)实际需要: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
战时西南地区科学技术以及人文社科的迅猛发展得益于两方面的需求:外在需求是基于抵御日寇侵略的国防建设需要;内在需求源于大后方经济迅速发展对科学技术的依赖以及人们对精神层面的追求。
迁移大后方后,国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恢复国防工业,建立了一批大型工厂,其中涉及电力、冶金、采矿、机床、汽车、机械制造、桥梁道路、电讯和水利等工业。这些工业企业的发展对科学和技术的依赖程度很高,必须有相关科学和技术的支撑。所以国民政府军政部、经济部、交通部和教育部共同协作,推进高校科学研究,以满足国防工业对科学技术的需要。
战时经济是战争影响下的经济,经济的发展与战争有密切的联系。以重庆为例,战前重庆拥有民营工厂28家,而且规模小,设施简陋。战争爆发尤其是武汉沦陷后,省外的工厂大量迁往重庆,其中轻重工业企业有225家,占内迁企业总数的50%,占迁入四川工厂总数的90%[9]46。国民政府的经济中心转移到了重庆,改变了当时西南地区生产力低下的状况。1939年,内迁工厂先后投入生产,为适应人民生活需要,振兴国民经济,国民政府还在重庆新建了诸多工厂。随着工业生产的大发展,重庆商业贸易也开始繁荣起来,重庆也替代了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另外,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时期,广大劳动人民对精神层面的需求也日趋强烈。他们不仅需要在精神上坚定中国抗战必胜的信心,还要在闲暇之余阅读文字,愉悦内心。作为大后方的西南地区对各种出版物具有很高的需求。
总之,抗战后,重庆接受了来自东部发达地区的大批商业、工业、金融业与兵工企业,促进了重庆经济的大发展、大繁荣。作为战时全国经济中心的重庆以及全国经济重心的西南地区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科学和技术的支撑。战时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战时西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时,战时经济的发展对科学技术的创新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资源集中:各高校间精诚合作
抗战爆发后,大批高校云集西南地区。一方面,由于校舍、设备、图书的短缺,它们选择共处一地,共用资源,比如华西坝、沙坪坝、夏坝和白沙坝。另一方面,由于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的需要,它们选择强强联合或者互相配合,比如西南联合大学、西北工学院等。
战时相对安全的蓉城华西坝在华西协和大学的基础上,吸引来自东部地区的4所教会大学和中大医学院,5大院校积极合作,各取所长,共用教学和实验设备,校际之间频繁开展学术交流,不仅开拓了学生的学术视野,还有利于促进科学研究。其中,最为成功的是中大医学院、齐大、华大联合医院的设立,由三校选拔优秀教师充任医生,学生可在医院实习,为医学研究提供良好的学术条件和氛围。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中央地质调查所、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中央大学地质系、中山大学地质系、浙江大学史地系地理组、重庆大学地质系和西北大学地质系等参与大后方的地质调查活动[10],发现了西部地区的丰富矿藏,为西部地区资源开发、服务抗战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会同经济部矿冶研究所、兵工署研究所、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西北工学院矿冶研究所及中央钢铁厂合作对钢铁、非金属及合金进行研究。兵工署理化研究所会同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及各大学合作研究国防化学[4]13。
(三)政策支持:政府出台相应的法规和奖励政策
抗战初始,国民政府在“抗战建国”的总方针下注意到科学技术对于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重大意义,积极组织协调科研机构和相应人员大规模内迁。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国民政府能够如此注重科学技术,出台相应的保护政策,一定程度上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940年国民政府为提高学术标准、鼓励科研事业成立学术审议委员会,对于国内成绩优异之学术著作,其中包括科学著作,分别予以奖励,这亦是长期抗战时推动科学研究的一种措施[1]175。
从1937年到1944年,为发展科学技术以服务战时需要,国民政府拟定颁布了一系列条例法规:
第一,奖励工业技术发明。1939年4月经济部修订的《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就战时各种战备物资短缺的现状,抛弃“理想主义”,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奖励战备物资“代用品”的研发。这对于发展战时工业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二,奖励仿制“替代品”。1943年4月经济部公布《奖励仿造工业原材料器材及代用品办法》,奖励范围以“仿造工作已脱离试验阶段,工业上能多量制造者”及“代用品以就地取材确能代替原物品之功效者为限”[11]。奖励分为甲乙两个等级,奖金由5千元到10万元不等。在这一规定下,科研人员对各种原材料和器械进行研制,不断有发明创造涌现,缓解了战时大后方工业原料、物资器械短缺的问题。
第三,其他各部委也出台了一系列奖励政策。1941年5月31日,资源委员会成立工矿业技术奖励审查委员会,对资委会所辖企业的技术奖励工作进行管理;又于两年后成立发明创作审查委员会,制定《发明创作给奖办法》。通过定期表彰发明创造,鼓励科研人员积极参与到实用的科研中来。在此期间,其他部委也出台了相应的奖励办法,如教育部的“著作发明及美术奖励规则”、卫生署的“奖励医药技术条例”、兵工署的“兵工新发明评奖委员会规程及给奖标准”等[11]。在此情况下,各部委积极与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合作,联合研制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物资设备,对科研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四)国际交流:促进学术科研能力不断提升
中外科技交流是战时西南地区科学研究快速进步的重要条件之一。首先,自战时起,我们一向依靠外来的图书、仪器、文献、药品,旧的遗失,新的不能增添,研究工作当然受了极大影响[1] 166。其次,战时中国与国际的学术交流几近封闭,中国需要将自己的学术成果介绍出去,也需要引进外国专家学者来指导或交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建立了统一战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为了帮助中国发展生产,增强科技力量,以支援前方作战,以美国为首的盟友国家,对中国给予了技术输出,派遣战时中国急需的公共卫生、水利、水土、机械和矿冶专业技术专家来华,帮助战时中国的生产建设。
在向中国输出技术方面,以美国最为突出。1942年至1946年,美国先后派遣多批专家学者到中国。1942年,美国向中国的军事、经济、教育、交通、水利和卫生等部门共派出专家学者30余人,他们所具备的专长在造纸、油矿、钢铁、卫生工程、生物化学制品、有机化学、无线电话制造及设备、航空工程、畜牧学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促进学术交流方面,以英国最为突出。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重庆建立了中英科学合作馆,该机构分纯粹科学、工业科学、战时工业及医学4组,分别就中国战时需要的技术与科学进行不断探索,取得显著成果。据记载,中英科学合作馆任务共13项,内容分为两大类:第一,以合作馆名义,通过英国文化委员会供应中国科学界所需要的图书,并从印度购买科学研究需要的仪器和化学药品。第二,通过合作馆向世界各国介绍中国科学界的研究现状和成果。李约瑟博士不仅竭力介绍中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在国外发表,邀请专家学者来华讲学,而且还撰写多篇论文向世界介绍战时中国的科学现状,如《中国西南科学》《川西的科学》等。英美等盟国的交流活动在战争的黑夜中打开了一扇投射光明的窗口,对战时中国学术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对于抗战期间我国高等院校科研呈现的特征归因,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史料和数据进行更详细的剖析,这里恕不一一展开。总的来说,肩负抗日救亡和民族复兴重任,大批具有爱国情怀的学者团结一致、不遗余力地保存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命脉,在政府奖励政策和国际援助的推动下,孜孜不倦,辛勤笔耕,潜心研究,自强不息,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不因抗战而中辍,亦使我国的科学研究在条件空前恶劣的环境下形成了雄厚的智能优势,迎来了我国教育、科学和文化发展的空前繁荣时期。
参考文献:
[1]卢于道.抗战七年来之中国科学界[G]//孙本文.中国战时学术.重庆:正中书局,1945.
[2]编辑部.一年回顾[J].科学,1939,23(12):807.
[3]李约瑟.战时中国的科学(一)[M].台北: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
[4]程雨辰.抗战时期重庆的科学技术[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
[5]陈光复.在抗战激流中前进的四川大学[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委员会.抗战时期西南的教育事业.贵阳:贵州省文史书店,1994.
[6]朱家骅.科学研究之意见[J].科学世界,1942,11(1):1-4.
[7]侯德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高校内迁史略[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
[8]闻黎明.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9]黄友凡,彭承福.抗日战争中的重庆[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10]黄立人.黄汲清与抗战时期的中国地质事业[G]//徐朝鉴.重庆文史资料:第43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11]张凤琦.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述评[J].抗日战争研究,2003,13(2):108-128.
(责任编辑蔡宗模余志祥)
Study o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Southwest Are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JIA Hongqi
(Faculty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Beibei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with the massive moving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to the rear area of the war,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had indicated huge changes. Under severe environment,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had also harvested great achievements, and indicated four notable characters: catching up on scientific research; basing on reality to proceed with technology innovation; dwelling on the frontier area substantially; connecting philosophy research with national calamity. The social and war requirements, the relative concentration of resources, the policy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helping hands from international societies, had influenced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s in a large scale.
Key words:Anti-Japanese war; southwest area; scientific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12(2016)01-0044-06
DOI:10.15998/j.cnki.issn1673-8012.2016.01.007
作者简介:贾红旗(1990—),男,山东济宁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研究。
基金项目: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2013年度重点课题“抗战时期西迁重庆高校大学精神研究”(CQGJ13B126)
收稿日期:2015-08-08
引用格式:贾红旗.抗战时期西南地区高等院校科研特征研究[J].重庆高教研究,2016,4(1):44-49.
Citation format:JIA Hongqi. Study o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southwest are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J].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2016,4(1):44-49.
--западе Кита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