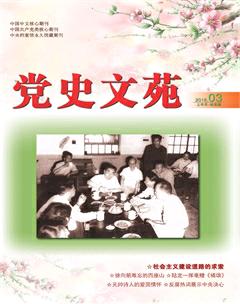我的三年 知青生活
汪建策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是一句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非常广泛的政治口号。
我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1972年,我初中毕业于九江市第二中学后,便待业在家,成了一名“待业青年”。待业期间,我在长江之滨的水岸码头当过搬运工,整天做着抬石头,扛木材,装卸砂石、煤炭等临时性的杂工,每个月能挣几十块钱的收入,补贴家用。
1975年隆冬的一个傍晚,正当我们全家人准备吃晚饭时,忽然接到居委会的口头通知,让我晚上8点钟到“东方红公社”(现为浔阳区甘棠街道办事处)开会。会上公社主任和“乡办”(上山下乡办公室)负责人介绍了有关“知青”的先进事迹,动员广大适龄青年积极报名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第二天上午,没有多加考虑,我就在父母的陪伴下到九江市第一派出所(现为浔阳公安分局甘棠派出所)注销了城市户口,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下放知青了。这个看似轻率的举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人生未来的走向。在今天的人看来,主动注销城镇户口到农村去,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却是一件非常符合时代潮流的举动。由于注销户口的时间已经临近年关,又逢农闲时节,所以我没有立即去知青点报到,打算过完春节后再去。
我属于“厂社挂钩”式的知青,这种模式就是工厂与公社挂钩,联合创办知青点,把分散在各家的知青集中起来,以便统一管理。
1976年4月8日这一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比较大的转折点。这一天,我从城市来到农村,成了一名实实在在的知青。早晨7点多钟,厂里派出了一辆“日野”牌大卡车,在分管知青工作的厂领导带领下,来到了我家的住地,父母亲将我的生活用品搬上车,父亲陪着我一起前往下放的知青点。一小时后,我们来到了知青点——九江县周岭公社关山林杨。陌生的环境、满眼的翠绿,是我到这里后的第一印象。这里没有城市中的喧嚣,满眼除了山丘就是田地,还有不远处的几栋破旧的村舍,空旷的田野中,不时地传来几阵鸡鸣狗吠之声,似有填充寂寞之意。
下车后,林场书记和带队干部在几个老知青的陪同下,走过来迎接我们这些刚加入知青行列的年轻人。寒暄一番后,书记简要地向我们介绍了知青林场的基本情况。他说:这个林场叫“关山林场”,山上种了几千亩杉树,都是知青几年来的劳动成果,所以叫“知青林”。山的北面就是过去非常热闹的姑塘老镇,那里有60亩的林场知青水田,再过几天我们就要去准备“春插”了。
听到这里,我在心里想,水还这么冷,插下去的秧苗能活吗?后来才知道,由于当时推行的是双季稻,“早稻”秧苗必须在五一节前插下去,否则就会耽误晚稻栽插的时间,影响收成,说明自然农业对节气的要求是严格的。
说起姑塘的水田,当地的老人告诉我,这里原本是没有水田的,现在的水田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围湖造田”中形成的。这些水田原来都是鄱阳湖的湖汊和姑塘镇的港湾。历史上当地的人主要是以捕鱼为生,过着靠水吃水的渔舟生活。从老人们口述的故事里,不难看出他们对往日的生活充满了记忆。
姑塘的衰落是从南浔铁路开通后开始的,交通运输格局的变化,渐渐地使姑塘失去了历史的辉煌。此前的姑塘,是一处非常繁华的商埠集镇,它地处鄱阳湖之滨,是鄱阳湖进入长江与长江通往江西内地的水路必经之地,江西的许多土特产品如茶叶、夏布、药材、瓷器等都是在这里集散,现今的姑塘湖岸边还存留有许多用麻石垒砌的石码头和驳岸遗迹。
三年的知青生活,我的大半劳动时间是在姑塘度过的,从春插、双抢到秋收。在这里我看到了城乡之间的差别,真正体会到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含义。第一年的知青生活,按照当时的政策,每个知青每月有12块钱的生活补助和半斤油、5两肉、40斤大米的计划指标。换言之,当知青的第一年,你即便不劳动也能维持基本的生活,这在当时叫做“过渡期”,从第二年起就得自食其力了。
在我们的知青林场生活区内,建有3栋青砖灰瓦房,共有20多间,每3个知青住一间房屋,除住房外,集体食堂、小车间、猪圈、晒谷场都有。一日三餐由两个老农专门替我们做,每天7点吃早饭,然后就是劳动。锄草、垦地、种田、植树,不断地重复着几乎相同的生活节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知青生活是单调乏味的。为了找到一点慰藉,我养成了读书习字的生活习惯。几十年来,虽然没有找到书中的“黄金屋”,但精神却没有成为沙漠。令我一辈子值得庆幸的是,在知青点里我结识了相守一生的妻子,印证了“有缘千里来相会”的古训。
岁月蹉跎。1978年12月,我应征入伍了,生活转入到了另一个阶段。?
责任编辑 /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