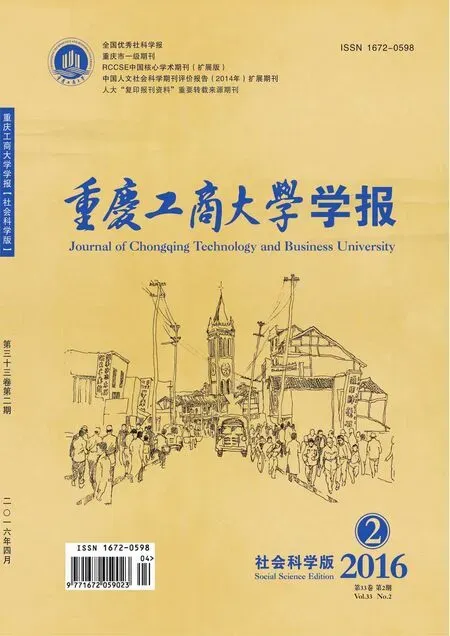劳动力城乡转移与家庭外部关系的实践——以甘肃东乡族为例
劳动力城乡转移与家庭外部关系的实践——以甘肃东乡族为例
摘要:劳动力的城乡转移无疑会对家庭的外部关系产生影响,不同的流动形式对外部关系的选择有其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不管是生活重心在农村的“半漂式流动家庭”还是生活重心在城市的“全漂式流动家庭”,其对亲属关系都同样倚重。不同的是,在农村的“半漂式流动家庭”除了对亲属关系的倚重外,邻里之间的关系在其日常生活中也显现出重要性,而在城市中的“全漂式流动家庭”则更多的是依靠业缘关系、乡缘关系、社缘关系等。
关键词:家庭外部关系;“半漂式流动家庭”;“全漂式流动家庭”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户籍制度的松动,劳动力的城乡转移越来越趋于常态化。他们往返于城乡之间,对城乡社会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而这种冲击发生最深的领域就是他们自身的家庭。对于生活在甘肃省东乡县大岭村的东乡族人来说,他们的流动形式以家庭中男性劳动力个人季节性流动为主,全家迁移常年在外流动为辅。根据家庭流动的人数、家庭生活的重心以及家庭成员的内心感情,大岭村的流动家庭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家中男性劳动力因各种原因(如进城打工、做生意、工作调动等)季节性外出,妇女、儿童、老人留守,家庭生活重心还在农村,但家庭成员之间长期分离、聚少离多,我们可以称之为“半漂式流动家庭”;一种是全部家庭成员因各种原因一起进城,家庭生活重心完全转移到城市,但户籍却仍留在农村,家庭各成员之间不用长期分离,这种家庭被称为“全漂式流动家庭”。
家庭外部关系主要包括与亲属和邻居之间的关系。前者既有建立在父系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家族关系,又有建立在母系血缘关系和姻缘关系基础上的姻亲关系等;后者主要是由于地理上的临近形成的邻里关系。劳动力的城乡转移无疑会对家庭的外部关系产生影响,不同的流动形式对家庭外部关系影响的程度、方式不同,“半漂式流动家庭”和“全漂式流动家庭”在应对这种影响时,对外部关系的重新选择和建构有其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
一、亲属关系:重家伍轻亲故
东乡族一般采取宗族聚居的居住格局,亦即同村或同坊聚居,它以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结合为基础,大岭村就是一个典型的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多重关系重合的村落。在传统的东乡族村落社会,这种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双重保障使得村民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团结协作精神,他们世代相传的传统就是彼此在生产与生活中的互助。
在东乡族社会,最重要的亲属关系是建立在父系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家族关系,东乡族称为“家伍”。并且按照亲属关系的远近,把“家伍”分为“亲家伍”和“老(大)家伍”。“亲家伍”一般是同一祖父的后代,“老(大)家伍”一般为同一曾祖父或太祖父的后代。东乡族一般把通过母系血缘关系或姻亲关系结成的亲属关系称为“亲故”。
大岭村共有6个社,虽然并不是每个社都只有一个家伍,但同一家伍的人一定生活在同一个社,这样就意味着同一家伍的人非常邻近。因此,在生活中,大岭村和东乡族的其他地方一样,家伍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亲家伍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既有物质上的交往,又有情感上的交往。“半漂式流动家庭”和“全漂式流动家庭”与家伍的交往内容主要包括生产生活上的互助、结婚盖房子等重大事务上的金钱借贷等。当我们在村里问到有关的问题时,村民们是这样说的:
“我们家的房子是后来重新盖的,以前的老房子塌了,盖房子的时候政府给了八千多,我盖这个房子总共花了四万,剩下都是我哥哥他们帮我出的钱。当时盖房子的劳力也主要是我哥哥家的,他们虽然在外面做生意,家里的人只要在,都过来帮忙了。再就是女的干不了的,我从社里找了几个男的。现在他们这钱也不要了,送给我了,他们日子都过得挺好的。”
“我给儿子盖房差不多花了两万块钱,都是贷款的,亲戚朋友家里富裕的也没有几个,所以借不上,而且借一两个月就要还。我们家的麦子有时是自己种,有时和弟兄合伙。现在也就是顾得上就自己收,顾不上就合伙。”
“我们家兄弟五个,当时盖房子的时候兄弟们帮忙出力了,但钱都是我自己出的。我老婆娘家的哥哥来帮着做了几天就回去了。其他人也没有帮忙,就我们几个做着呢。”
可以看到,当“半漂式流动家庭”遇到盖房子、农忙等需要金钱和劳力的事情时,多数还是由亲家伍的兄弟提供全部或大部分的帮助,而依靠女儿或者母亲建立的姻缘关系,只是作为亲属关系,在需要的时候给予礼节性的帮助,包括象征性的金钱帮助和短时间的劳力帮助。这从一个侧面也印证了为什么东乡族社会会有喜子的偏好和多子的偏好。伊斯兰教在传播过程中受到传统儒家文化“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以及东乡族社会恶劣的生态环境、气候条件以及贫瘠的土地,基于宗教和现实的原因,对劳动力的质量和数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东乡族社会普遍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生女儿是给别人生的,只有儿子是自己家的。儿子,在东乡族家庭中,成为最重要的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因此,在传统父系农村,兄弟多就意味着力量大,没有人敢欺负,在家庭遇到诸如盖房子、结婚或丧葬等重大事情时就能互相帮助;兄弟少或者没有兄弟,明显势单力孤,在家中遇到大事时,就只能寻找老家伍的兄弟或是寻求村中其他人的帮助。
“全漂式流动家庭”虽然生活重心已经转移到城市,但当家中遇到困难时首先还是会向家伍寻求帮助,然后才寻找其他的亲属。
马有布,在兰州开店卖旧门窗、旧家具。“我在兰州开这个店大概要十万的成本,都是在龙泉乡贷款的。一个户口本可以贷五万,还有五万也是贷的,是我家伍的哥哥帮着贷的,贷出来借给我。”
实践具有策略性,策略是实践之源[1]。大岭村的亲属实践表明,具有血缘的亲属关系网络是大岭村家庭重要的关系资源。
有学者通过调查发现,在家中男性劳动力外出之后,女性亲属关系的重要性上升。在开展经济合作中,妇女获得了更大程度的自主权,可更有效地追求她们的自身利益,积极地建构自己的关系网;在抚养孩子时,年轻的妇女从其母亲和其他女性亲属那里获得帮助、支持和友谊[2]。也有学者指出,妇女建构亲属的过程就是抵制和远离传统的公婆等长辈为权威的亲属关系,重视和强化与娘家、邻居等关系的过程[3]。可是在大岭村,呈现的却是另一番光景。
大岭村的亲故关系,也就是姻亲关系,并没有以妇女为中心积极建构,在亲属关系的选择上,通常女性也会遵循以父系为主的关系序列。当笔者问到留守妇女在自家有困难或有事时会找谁帮忙,大部分人的回答都是自己丈夫的兄弟。生活在这里的人至今还认为女儿一出嫁,就是“泼出去的水”“嫁出去就没了,是别人家的人了”。在丈夫外出打工期间,“半漂式流动家庭”中的那些留守妇女,既要从事家务劳动和农业生产,又要照顾孩子和赡养老人,因此,对外的依赖性较强。但这种依赖的对象也多限于丈夫的父母和丈夫的兄弟,而和自己娘家的关系则多是由于节日或家里有人结婚、生病、盖房等事时的礼节性走动。下面是几个个案的讲述:
马阿英社(女),62岁,老伴在精神上有些问题,随时需要人照顾。“家里有两个女儿,都结婚了,但是放不下婆家那边过来照顾我们,所以没来照顾。她们离这里不太远,但是由于家里情况来不了,经济上也帮不了多少,每次来就给个一两百的,生活上会给一些鸡蛋、肉等。”
马哈力麦(女):“通常家里有什么事我们都是和隔壁孩子的叔叔伯伯家互相帮忙。我娘家离得近,平常走动也是有的,这时候就不带礼,像家里有事的时候,再比如说过节的时候,斋月的时候走亲戚去就要带上点礼,一般就是茶叶、冰糖,有时候就拿上三舍礼、四舍礼还有五舍礼(三舍礼是在茶叶和冰糖的基础上再加上桂圆,四舍礼是再加上杏脯,五舍礼就是再加上红枣之类),要是碰上有人结婚或生病,就是拿个鸡啦拿一些鸡蛋、肉啊去看一下,再给个一两百块钱,关系好的就两三百,一般的就一百,再一般的就拿个五十。”
马小花(女):“我娘家有兄弟姐妹五个,我是最小的,上面有一个姐姐三个哥哥,农忙的时候,虽然娘家靠得比较近,但是干活的时候,因为娘家底下的地也特别多,自己的农活也特别多,所以没有时间来帮我们。”
马龙台(男):“她娘家的亲戚一般都不怎么上我们这来,有啥事或者过节的时候,都还是以我的兄弟姐妹为主。”
但是,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马阿英社的情况比较特殊。给老伴看病的钱都是两个儿子从舅舅家里借的,一人借了一万多,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老伴兄弟家都比较穷,帮不上什么忙;另一方面,因为自己弟弟是卖木材的,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好。除了给老伴看病的钱,她家大儿子盖房子的木头也都是从舅舅那赊账借回来的。因此,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亲属关系实践的复杂性。
地理距离一般和亲属关系的亲疏程度成正比,居住的距离近,亲属间的实际来往就越多,相互之间帮助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当然亲属关系也就越紧密;但是,也有学者指出,血缘和姻缘不是亲属关系成立的充分条件,而只是必要条件,别人是否视你为亲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能否满足他人的利益以及你满足他人利益能力的大小,与亲属的亲疏成正比的是你满足他人需要的能力的大小[4]。因此,在大岭村,虽然血缘关系很重要,但亲属“关系的远近”和“关系的亲疏”之间并不总是重合的。关系的远近,是指血缘的远近,这显然是固定不变的。关系的亲疏,是指往来的频度和感情上的亲密程度,血缘的远近可以成为关系亲疏的一个前提,但这不是绝对的,它也会因为双方利益的不同或其对另一方的期待不能得到满足而淡漠甚至彻底疏远[5]。
二、邻里关系:淡化与强化同在
对每一个家庭来说,不仅要和亲属家庭之间发生关系,而且和非亲属家庭——邻里之间也会发生关系。邻里作为中国社会中除家庭之外的另一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在人们的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习惯中,一直把“亲”和“邻”联系在一起,因此,民间很早便有“远亲不如近邻”的说法。大岭村的人际关系以自己的家庭为中心,由邻里、社和村落逐层向外推衍,越往内关系越亲近,越往外关系越疏远。
东乡族村落由于地缘观念产生的亲族观念特别强,所以显示出很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形成了村民之间互助协力的传统。包括在婚丧大事上的协力互助、房屋修建时的协力互助以及耕种收庄稼打碾场时的换工互助等。在传统东乡社会,村民之间的互助协力主要是基于血缘、情感基础上的援助行为,他们有共同的社会生活,有统一的风俗习惯,大体一致的思想意识,有宗教信仰、道德力量的共同约束,在生存的压力下互相联合、互帮互助。但协作是双向的、互相的,在交换合作中也难免会出现合理化的算计思想,然而这种思想却不是绝对的等价交换,而只是某种程度上合理的对等原则。
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真正改变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的农民流动。村民的流动为大岭村的宗族、家族活动以及彼此之间原有的互助协作关系的改变提供了契机。原有的家族关系出现分化,在涉及金钱借贷方面更加倚重亲家伍关系。当笔者问到“近10年中,您家庭是否有因结婚、生重病、建房(装修房)等需要他人资助的事件?如果有资助,谁资助最多?”时,回答最多的是男方的兄弟和男方的父母;原有的在耕种、收割庄稼、打碾场时的换工互助现象减少,当被问到“在最近一年中,农忙期间谁给您帮助最多?”时,回答最多的依次是邻居、男方的兄弟;原有的在修建房屋时的帮工互助现象也因村中男性劳力的外出而减少,男方的兄弟和邻居成为主要帮工来源。总的来说,在大岭村,父系血缘关系的重要性依然延续,但大家伍的联系已经随着村民的流动越来越松散,出现弱化倾向,而亲家伍的联系则得到加强,更加紧密、更加全面化,以女性为中心建构的亲属关系以及现代化的市场雇佣关系在这里还处于萌芽阶段。
大岭村的关系网络主要是以男性为主体建立的,随着村中越来越多男性劳力的外出,村民的日常交往,包括日常的交流、家里的婚丧嫁娶或者是农忙时候的互助,都因为“主体”的外出而有所减少。特别是对那些“全漂式流动家庭”来说,由于他们常年生活在城市,与原有村落的邻居已经没什么联系,只是在村里有重大事情如老人生病或去世时会回去,这个时候才会去邻居家里顺便坐坐,而他们在城市的左邻右舍,都是因为生意的关系临时住在一起,以前并不认识,因此,彼此交往的程度非常有限,情感支持和经济上的借贷更谈不上。
在乡村生活的“半漂式流动家庭”,除了主要依靠家伍关系外,邻里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多表现为几家在农业生产上的互相协助和盖房、仪式活动中的互相帮工。这样的互相协助和互相帮工体现的是乡村社会的人情交往,是通过双方之间的情感交流、物质交换达到共同获利和共同发展,是讲求互惠平衡的。杨阿么力的情况可以说明“半漂式流动家庭”之间在农忙时的互相帮助,而一旦一方退出,另一方还生活在农村的家庭就会主动再去寻求新的“合作对象”:
“隔壁他们在的时候,两家虽然不是兄弟,但是也会互相帮着干,隔壁的走了之后,我们家因为劳动力缺少了,很多地都种不了了,只能让别人种了。他们搬走也有个五六年六七年了吧,自从他们走后,家里面有什么事,我们就找隔一个房子的另外一家。”
盖房子是农村的一件大事,大岭村的每个父母一辈子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为儿子娶媳妇和为儿子盖房子,这两件事几乎要花尽他们一生的积蓄。以前村里人还没有大量外出的时候,盖房子帮忙的人很多。可是,现在据村支书说:“因为男人都出去打工了,别人也不会因为你家盖房子专门跑回来帮忙。现在盖房子都基本上靠家伍帮忙,村里社里那些关系好的也会来,其他就没什么人了,再不然,就是你有钱的你就雇人,没钱你就自己多干点。”笔者的访谈也证实了村支书的这种说法,马太恰是家中的老小,他家盖房子的时候哥哥家既出钱又出力,因男性劳力不够,所以他又雇了几个同社的人。杨么乃家盖房子的时候,钱都是自己出的,哥哥家帮忙出劳力,妻子娘家的哥哥也来干了几天,其他再没什么人,就他们几个干着。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盖房子这一以往对村民来说的大事,现在已经随着村里男性主体的缺失而没有了普遍的帮工现象。而且,现在,雇工的观念已经被一部分村民接受,不管这种接受是自己的主动选择还是被迫接受。房东负责买好盖房的材料,其他的具体事宜交给小包工头管,待房子盖好后,付给包工队工钱即可。在这整个过程中还有没有其他人帮忙,则和房东盖房的时间、亲家伍的经济和劳力情况,以及自己在村里的人际关系有关。
在遇到婚丧嫁娶等仪式活动时,邻里的帮工行为要比在盖房时普遍。像和岘社因为是同一个家伍的,所以邻里不仅是单纯的邻里关系,还有亲属关系。当社里有红白事的时候,外出打工的人都会回去帮忙。这种帮忙虽然主要指劳动力方面,但在仪式上的随礼也很重要。礼钱的数目不定,多的500元,少的100元。其他社的情况是,在婚嫁的时候家伍的都会回去,邻居会不会回去则要看具体情况,即使回不去,留守的妇女也会过去帮忙做饭等。但是在有丧事的时候都会回去,甚至在老人生病的时候也会回去探望。没有亲属关系的邻里,随礼的数目不一定,多的100元,少的50,甚至30元的也有。据村民讲,这主要看自己家的经济情况,情况好就会多出,情况一般或不好的就会少出一点。但是,活动的范围基本上以社为单位,而不会波及整个村。村民们明确表示,不是同社的村民婚丧嫁娶,他们是不会回去的。
“半漂式流动家庭”和“全漂式流动家庭”也积极扩展建立在生意基础上的业缘关系,当然,这种业缘关系和乡缘关系、社缘关系有时候是交互重叠的。对于大部分出售旧家具、旧门窗的人来说,他们可以利用这些关系得到有关拆迁的最新信息,获得货源的供应;对于那些在建筑工地上打短工的人来说,他们可以利用这些关系互通信息,或者寻找更好、给钱更多的工程;而有的人也会在金钱借贷方面依靠生意上的朋友,马一不拉就属于这样的情况:
“我们盖这个房子的时候跟别人借了七八千,总共花了两三万。钱都是掌柜的跟自己做生意的朋友借的。”
社会的变迁引起了邻里关系的变化,出现“局部强化、整体淡化”的发展趋势。局部强化指的是由于大量青壮年的离开,使得农村传统的生活方式发生变迁,一些邻里之间出于相互帮助的需要,强化了他们之间的邻里关系。总体淡化指的是由于农村生活方式的变化,减少了邻里之间的交往活动,影响了邻里关系的建立,使得邻里关系在整体上比以前淡化了[6]。我们在大岭村的调查实际也反映了这种趋势的存在。从整体上来说,由于人口的流动,男性劳力的缺失,过去邻里之间有事大家一起办的情况已经减少,在盖房上表现尤其明显,市场经济的雇工已经大量代替传统的帮工。对邻里关系影响、冲击最大的当然属“全漂式流动家庭”,一方面,他们多和老家的亲戚联系紧密,同社的人只有在家里有婚丧嫁娶等大事的时候才会回去;另一方面,他们在城市中的邻里关系也因居住的暂时性和流动性,交往的深度和紧密度有限。从局部上来说,农村的剩余人口都是一些老弱妇孺,他们在村里的青壮年男性外出之后,在生活上、生产上实际更需要彼此的帮助和照顾。所以有的家庭就会在有困难的时候主动寻求和临近家庭的相互合作和照应,就算中途有人“退场”,他们还是会在有需要的时候重新和别的家庭建立这种联系。因此,在局部上邻里关系也有强化的特征。
费孝通先生曾经用“差序格局”来说明传统中国乡土社会最基本的结构特征。在乡土社会,不但亲属关系表现为“差序格局”,地缘关系也表现为“差序格局”。很显然,我们在大岭村的调查再一次印证了费先生“差序格局”概念的解释力和生命力。大岭村的实际情况表明,伦理、情感依然是维持这个小社会人际关系的主要维度,利益取向已在某些方面萌芽,但还没有真正使得交往关系形式化、理性化和商业化。
三、总结与思考
在大岭村,随着男性劳动力的流动,原有家庭结构发生变化,而这些流动家庭在应对这种变化产生的影响时,对家庭外部关系的选择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是,不管是生活重心在农村的“半漂式流动家庭”还是生活重心在城市的“全漂式流动家庭”,其对亲属关系都同样倚重。不同的是,在农村的“半漂式流动家庭”除了对亲属关系的倚重外,邻里之间的关系在其日常生活中也显现出重要性,城市中“全漂式流动家庭”同以前在农村的邻里之间已基本没有联系,而在新环境中暂时形成的新邻里关系并没有发挥和传统乡村社会邻里之间那样紧密的互助和协作,虽然大家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但交往的程度不深,基本上都属于“泛泛之交”。而且,这种家庭外部关系重构的主体还是家庭中的男性,女性的人际关系似乎在丈夫外出后依然隐藏在男性的身影后,并没有凸显出来。
不管是“半漂式流动家庭”抑或是“全漂式流动家庭”,现在主要都还是一个“经济共同体”,家庭整体主义至上的观念使得个人情感和个人目标让位于家庭的整体利益和目标,家庭的经济功能居于首要位置。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流动使得家庭的生活环境发生改变,可供现实选择的外部关系框架变窄,但是这些家庭依然遵循着保障家庭正常运行和维护家庭稳定的首要目标,实践着家庭外部关系。
流动带给家庭的冲击是巨大的,也给家庭带来了一系列诸如子女教育、夫妻关系和老人赡养等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仅仅依靠单个家庭的力量是无法得到妥善解决的。因此,这些家庭必须依靠它们所拥有的外部关系来获得帮助。但就实际情况来看,单个家庭目前所拥有的外部关系数量和质量都有限,我们必须在此基础上,发挥集体的力量,来应对这些问题。也就是说,对于“半漂式流动家庭”, 我们要发挥原有农村社区的作用,重建社区联系,加强社区援助,使得“半漂式流动家庭”在其主要男性劳动力外出之后,也能在生活中获得物质上和情感上的支持和帮助,减少外出人员的后顾之忧。对于在城市中生活的“全漂式流动家庭”,我们要发挥流动家庭所属社区的作用,积极开展活动,了解和关心流动人员在城市的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子女上学难以及随流老人看病难等现实问题,使他们在城市能有尊严的活着,并最终使得他们作为公民平等地享受国家赋予的权利和资源,不会因为户籍的限制而有所差别。“半漂式流动家庭”和“全漂式流动家庭”所处的是两个不同的社区——一个是传统的乡村社区,一个是现代的城市社区。虽然同样是要建立社区支持和社区援助,同样都需要社会政策的鼓励和大力支持,但在具体做法上却因为“社会结构”的不同而应该采用不同的实践措施。
[参考文献]
[1] 侯均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356.
[2] 潘鸿雁.对非常规核心家庭实践的亲属关系的考察——以翟城村为例[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6).
[3] 李霞.依附者还是建构者——关于妇女亲属关系的一项民族志研究[J].思想战线,2005(1).
[4] 刘楚魁.试析正确处理亲属关系[J].广西社会科学,2002(6).
[5] 杨善华,侯红蕊.血缘、姻缘、亲情与利益——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中“差序格局”的“理性化”趋势[J].宁夏社会科学,1999(6).
[6] 常小美.后常庄的邻里互助研究——以丧葬仪式为例[D].合肥:安徽大学,2007.
(责任编校:杨睿)
Practice in Labor Urban-rural Transfer and Family Outside Relation——Taking Gansu Dongxiang Nationality as an Example
LIAN Fu-rong
(SchoolofPhilosophyandSociology,LanzhouUniversity,Lanzhou730000,China)
Abstract:The labor urban-rural transfer obviously has effect on family outside relation, different transfer forms have the similar and different selections of family outside relations. No matter whether “semi-drifting transfer families” whose living cores are in the countryside or “the whole-drifting transfer families” whose living cores are in the cities rely heavily upon the relative relations, the difference is that besides depending upon the relative relations, the “semi-drifting transfer families” in the countryside also rely heavily upon the neighboring relation in daily life, however, “the whole-drifting transfer families” in the cities more depend on business relation, town-originated relation and village-originated relation and so on.
Key words:family outside relation; “semi-drifting transfer families”; “the whole-drifting transfer families”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 0598(2016)02- 0078- 06
[作者简介]连芙蓉(1982—),女,陕西渭南人;民族社会学博士,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城乡社会学研究。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4LZUJBWZY052)
[收稿日期]2014-08-11
doi:12.3969/j.issn.1672- 0598.2016.02.012
连芙蓉(兰州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兰州 73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