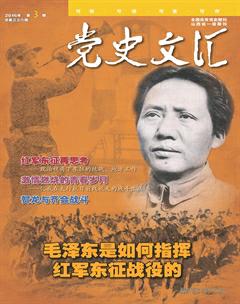艺术视野中的毛泽东
对艺术的特殊理解
毛泽东并非艺术收藏家,却算得上是一位不错的艺术鉴赏家。他在艺术方面有一种特殊的理解。1956年4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他说,“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
8月2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与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谈话,其中对文化艺术规律的论述,相当精辟:
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
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现在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搞,听凭人选择。外国的许多东西都要去学,而且要学好,大家也可以见见世面。但是在中国艺术中硬搬西洋的东西,中国人就不欢迎。艺术有个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
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
……
特别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为八股。过去有人搞八股文章,搞了五六百年。形式到处一样就不好。
……
演些外国音乐,不要害怕。隋朝、唐朝的九部乐、十部乐,多数是西域音乐,还有高丽、印度来的外国音乐。演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亡了,我们的音乐继续在发展。外国音乐我们能消化它,吸收它的长处,就对我们有益。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
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这样争论就可以统一了。
……
这是毛泽东几十年以来对艺术的切身感悟和深刻思考!这当中也包括了他对在故乡的切身体验的思考。
我们有必要来回顾一下他在故乡的艺术体验经历,就像他家居生活的其他几乎所有的方面一样,故乡是他的根,也影响着他一生的爱好倾向或习惯。
毛泽东的艺术体验和思考经过长达80多年的漫长时间——韶山的17年是他的第一阶段。同时,我们应当注意到,毛泽东的艺术领域基本上涵盖的范围是语言的艺术(诗歌、散文和口头表达)和视觉的艺术(书法)、听觉的艺术(戏曲、音乐)、综合的艺术(表演)。这几者常常是交汇在一起的,其规律也是完全相通的。
在私塾里,毛泽东受到了正宗传统文化的陶冶——对于先生来说,他们授以课读,主要是为了让学生识字,其次是囿以儒家礼法。艺术导引,则是无意的熏陶。
6年的私塾生涯,毛泽东以他聪慧的资质,以超过与他同窗共室的人们的速度和效率,从四书五经、唐诗宋词中吸取着营养,并开始开出最初的艺术花朵。从南岸的诗对:“濯足——修身;牛皮菜——马齿苋”到井湾里的《赞井》诗,他的起步是令人惊奇的。书法,也由描红到临摹欧阳询、钱南园,我们从他这一时期留在《诗经》《论语》等书籍封皮上的墨迹,可以看出他最早的书法,是非常工整秀穆的。
当然,对戏曲的爱好与其他艺术品种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同步的,只是自从离开家乡,他对戏曲的爱好一开始就表现着兼收并蓄的特点。
从这诸多的风俗习惯中,我们可以抽出对毛泽东影响深远的艺术之线。这条线是汉苗交织、雅俗同在的一条线,既有远古苗民的遗存,又有近500年中移民从江浙带来的艺术之风,既有山间田野的口头艺术,又有祠堂庙宇的祭祀演艺之乐。
毛泽东早年在故乡的听戏观剧主要在大路边、地坪里和庙堂中。春节里,龙灯一般从初四五耍起,耍到元宵节,团有团龙,族有族龙,后来一般按土地庙的管辖地域(大致相当现今一个村,如毛泽东家所在地域属于关公庙管辖),从团防局和各族祠堂一直耍到各家各户,费用按田亩分摊。为图吉利,龙灯都要进堂屋。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远远地听到锣鼓唢呐声,早早打开堂屋门,点上灯,龙就进了屋,绕香火堂几圈在前坪耍起来,伴随着花鼓和湘剧高腔的“关云长”,还有一跃一跃的狮子,真是喜气洋洋!毛顺生高兴,早准备了一个不大不小包封,毛泽东兄弟则一挂挂地放响着炮竹。龙灯的苗文化味道比较重,花鼓戏则是典型的湖湘地方戏。正月十五的灯节则带有十分明显的中原文化特征。
过了春节,属于韶山和湖湘本土的娱乐活动(准确地说是娱神活动)则是端午的划龙船,比较近地观看龙船赛是在银田寺前云湖(韶河)上,远的更壮观的则要到百里之外的湘江,各团各境的船一边击鼓一边喊着号子,竞相争先,岸上则是人山人海。相应地也会有一些古苗民留下来的艺术形式开演。
这些都是民间的公共娱乐活动,而在清明、中元、重阳诸节里,各姓氏都要在各自的祠堂开祭。毛家的祠堂专设戏台,祭祀之后,族人就有看戏的机会,多是花鼓戏和影子戏。
另外,毛泽东还爱跑到清溪寺去看热闹。每当关公的生日(农历六月廿四)和观音菩萨的生日(农历二月十九),清溪寺都会有大的祭祀活动,这些活动当然带有浓浓的柏香味和虚幻的色彩。毛泽东总是陪伴着母亲虔诚地感受着这种宗教的气氛。
毛泽东还有一个接受地方戏曲和文化熏陶的时机,那就是婚、丧的礼仪。其中婚嫁礼俗,大多来源于中原文化,多是儒家的一套,而韶山的丧礼却是儒、释、道、巫杂糅:祭祀多用儒家的礼节,超度则纯是佛家的那套,种种禁忌和晚间的唱夜歌,则是特别富于南楚山区神秘文化特征和苗民遗俗的东西。endprint
毛泽东少年时代见得最多的戏种,无非是花鼓戏和湘剧高腔,还有影子戏,前两者多在过年的时候能看到,后者则是祭祀的时候或者给长寿老人庆生的时候演。影子戏多用湘剧高腔,清越而高扬,许多时候带有一种悲壮和凉意,有浓浓的楚地古风,内容却是正宗的中原文化曲目,与毛泽东后来喜爱的一些剧目非常相近,有《关云长》 (韶山方言“关文长”) 《薛仁贵征东》 《樊梨花 (薛仁贵的儿媳) 征西》 《铡美案》等等。
总的说来,毛泽东早年接受过多种艺术形式的熏陶,这是他喜爱民间艺术和戏曲艺术的根源。
艺术给他以灵感
毛泽东后来离开韶山,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对视觉和听觉艺术的爱好也向东西南北乃至外国艺术延伸。对艺术的喜爱和欣赏,使他在紧张的环境中得到休憩和放松,甚至直接开阔了他的思维,拓展了他的战略空间,他每每从中获得难得的休闲,也得到了种种灵感。
在故乡,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毛泽东没有专门的艺术欣赏而只有随大家一起的感受,在征战途中,他只能偶尔得暇与民共乐。就算在他到达延安特别是进入北京城,有了稳定的家居生活之后,欣赏听觉艺术和视觉艺术的机会多起来,也从来没有沉湎其中。他对艺术的欣赏一方面是出于他在忙碌的工作之余的休息或调整,另一方面则是出于他对民族优秀传统的喜爱和重视,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倡导和创造。
中南海毛泽东居住处留下大量唱片、磁带,内容包罗万象,从戏剧、相声到国内外各种舞曲、古典音乐,应有尽有。其中,各种戏剧,尤其是京剧、昆曲占绝大多数,这是毛泽东由少年到晚年一直爱好音乐、戏曲的明证。
毛泽东在中国300多个剧种中特别钟情由徽剧、昆曲、秦腔等深化而成的京剧。他正式接触京剧是从延安开始的。当时有一大批充满活力的艺术家和青年才俊来到延安,他们把京剧等艺术也带到延安,使物资极度匮乏的延安有了都市精神生活的活力。
京剧的出现几乎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同步。在中国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人民浴血奋战的时候,这个剧种拔地而起,那种黄钟大吕,抒发的正是民族悲壮的心声。毛泽东是一位史家,又是一位救国的英雄,同一种情感在延安与国统区和上海、北京间发生着共振和共鸣。毛泽东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喜欢京剧,看似突然,深层次上实则正是这种共振与共鸣的体现。
据李银桥回忆:毛泽东转战陕北时经常唱的是《空城计》《草船借箭》;到达西柏坡后常听高庆奎的《逍遥津》、言菊朋的《卧龙吊孝》、程砚秋的《群英会》;进入北平前后,毛泽东最喜欢《霸王别姬》。
如果仔细捉摸,我们会发现,毛泽东听戏的轨迹竟然暗合着他和中国共产党伟大事业的发展轨迹,也有着他对革命进程的深刻思考,仿佛他一方面在听着这些历史上发生过的大戏,一方面又在现实的中国演绎着新版的历史大剧,于是他时常借鉴历史的经验,告诫自己和人们不要重蹈覆辙。
由此看来,我们不能从纯艺术的角度去研究毛泽东对京剧和其他戏曲的爱好与欣赏。
毛泽东对京剧的喜欢并非全盘的拿来主义,像思想的其他许许多多方面一样,毛泽东的艺术思想也在延安走向成熟,其触角也伸向中国的传统剧种,包括京剧,京剧在延安得到了改造,被注入时代的气息和抗战的精神。
他在繁忙工作之余听听京剧,看看边区文工团员演出的秧歌戏,也不全然是休闲,而是带着思考。
1949年3月,他带着在延安时期添置的手摇留声机进入北平。那些曾给予他不少欢乐的京剧唱片也随之走进庭院深深的中南海。不过,这时已今非昔比,大都市的繁华毕竟不可与延安边塞的荒凉同日而语,毛泽东有条件添置更多的唱片了。后来,他有了录音机、电唱机,也有了藏量丰富的种种戏剧、音乐磁带。
1957年4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率最高苏维埃代表团访问中国,毛泽东亲自到首都机场迎接,并代表中国政府向伏罗希洛夫和他所率领的代表团致欢迎词。在确定文艺招待演出的剧目时,有人提出演一出比较轻松的京剧,也有人提出演一出典雅的昆曲,争来争去,最后,大多数的意见是怕苏联人听不懂京剧和昆曲,决定全部改为歌舞类。节目内容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大为不满:“一定要有戏曲,而且要演昆曲,昆曲听不懂,难道京剧就听得懂吗,昆曲载歌载舞,而且一定要演昆曲《林冲夜奔》,一定要是最好的昆曲演员来演,就让‘活林冲侯永奎来演吧,我也要去看。”
毛泽东亲点《林冲夜奔》,并陪伏罗希洛夫观看。当侯永奎唱到“管叫你海沸山摇”时,毛泽东带头起立鼓掌,全体中央领导和在场观众也随之起立鼓掌。伏罗希洛夫虽有些莫名其妙,但还是对中国戏剧产生了兴趣。
毛泽东曾多次请文艺界人士进入中南海演出。在看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等京剧大师表演京剧折子戏时,毛泽东还建议由侯宝林等相声演员表演几段轻松幽默的相声。他多次邀请侯宝林到中南海表演。
北京刚刚解放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一般在原来的美国驻华使馆听侯宝林表演相声。他通常坐在第三排的中间位置。这里放着两把藤椅,一把是毛泽东的,另一把是朱德的。有一次,叶剑英、彭真为毛泽东等准备了一台文艺晚会,毛泽东得知侯宝林将出场,才来到东交民巷的北京市委机关礼堂。侯宝林、郭启儒合说了一个新段子《婚姻与迷信》,毛泽东听后称赞:“侯宝林是个天才,是个语言研究家。”返回居所的路上,毛泽东还在对侯宝林的演技赞不绝口:“侯宝林对相声有研究,他本人很有学问,将来可以成为一个语言专家。”后来,他还看过许多侯宝林表演的段子,如《字象》《关公战秦琼》等。
1959年至1963年,马季所在的广播说唱团每周至少两次去中南海演出,共演出100多个中小型段子。毛泽东经常去听,他最喜欢听马季表演的揭露江湖医生骗人伎俩的《拔牙》和张述今创作的《装小嘴儿》。
1963年,马季下乡到山东文登县创作,写出 《画像》 《黑斑病》 《跳大神》 等作品。毛泽东知道后高兴地说:“那好,演一演,我听一听。”看完演出,毛泽东握着马季的手说:“还是下去好!”
毛泽东家里留下的唱片、磁带当然不能说他都听过,有些则是工作人员安排舞会时常备的舞曲。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有时在客厅里跳跳舞,以此运动身心。这些舞曲唱片有《村舞》《恋歌》《新年》《陕北民歌》《东方舞》等,也有一些外国音乐,如维也纳音乐《无穷动》《拨弦波尔卡》等。
磁带中还有殷承宗的钢琴独奏《北风吹》,刘德海的琵琶《十面埋伏》,曾永清的笛子《骊珠梦》 《罗成叫关》,郭向的管子《铁弓缘》,项斯华的古筝《文姬归汉》,闵慧芳的二胡《逍遥津》《卧龙吊孝》 《连营寨》等。
毛泽东公务繁忙,不可能经常到剧院听戏。20世纪50年代初,中共中央办公厅曾多次组织戏剧界、相声界的名流进中南海为首长们专场演出。但是这种请人演出的办法也不能长久,毛泽东连这个时间也无法保障,工作人员想出了两全其美的办法:将大师的演出录音放给首长们听。于是,工作人员弄来不少磁带,有京剧、昆曲、河北梆子、湖南花鼓戏,毛泽东便可在工作之后静静听上几段。
早先,工作人员为毛泽东添置了一部德国制造的录音机。20世纪60年代初,南京无线电厂生产出我国第一代柜式收录放三用机。毛泽东为中国能生产出这种性能不错的录音机而欣喜不已,从此便一直使用这部录音机。
无论从习惯上说还是从思想、精神上来说,毛泽东都是一个“简约派”,但他并不是一个生活单调、乏味的人,他的精神世界是极其丰富多彩的,他的思维方式也是极具创造性的,物质上的极低追求与精神上的极高追求是他个体人生的统一。
(责编 王燕萍)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