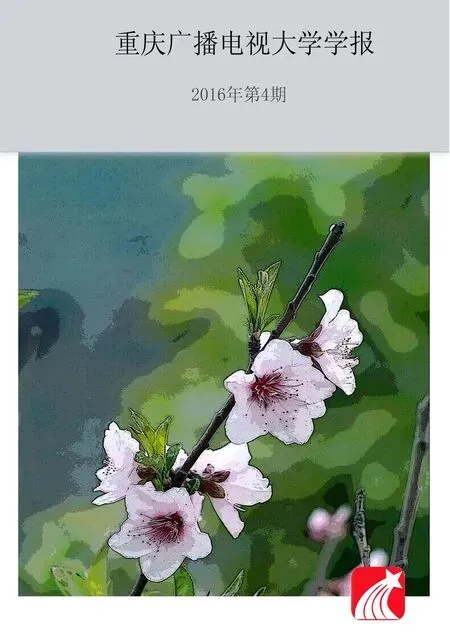艺术与科学的同构——科学起源于希腊艺术说刍议
谢江平
(天津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87)
艺术与科学的同构——科学起源于希腊艺术说刍议
谢江平
(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387)
现代科学的源头之一是希腊艺术。希腊悲剧中“人生活动的秩序”必然性是“自然秩序”必然性的反映。希腊悲剧体现了科学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必然性。在认识论上,希腊艺术持模仿论,其“美智同一”说在美与知识之间架起了桥梁,为艺术与科学的统一奠定了基础。模仿论所倡导的美学形式主义及其“数”的研究为自然知识的量化提供了数学基础。此外,希腊民主制度所孕育的论辩精神促使人们对知识的有效性、合法性采取反思的态度,这种怀疑精神对科学的发展极为重要。正因为如此,可以断言“现代科学起源于希腊”。
艺术;科学;必然性;模仿说;数
科学起源于欧洲,而“希腊总归是欧洲的母亲”[1]11,因此,要探讨科学的起源就必然绕不开希腊。怀特海有言,“希腊人对自然的看法(至少是他们流传到后世的宇宙观)本质上是戏剧性的”[1]12。他认为,现代科学的源头之一就是希腊艺术。怀特海的“科学起源于希腊艺术”说为我们探讨科学的起源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一、悲剧与必然性
许多古代文明在技术乃至数学、天文、医学等自然知识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但人们却把希腊文明奉为科学的源头。这是因为希腊人的思想与智力活动中有一些超越其他文明之处。劳埃德认为,自米利都学派开始,希腊思想家的思考有两个重要特点“使他们的思考有别于之前的希腊或非希腊思想”。第一个特点是“自然的发现”,第二个特点是“理性的批判与辩论活动”。
所谓“自然的发现”,指的是希腊人懂得“自然现象不是因为受到任意的胡乱的行为而产生,而是有规则的,受着一定的因果关系的支配”[2]7。这种因果关系的必然性在自然界表现为“物理的定律”,在悲剧中则表现为“无情的命运”。就自然观而言,希腊的自然观仍有很强的神话味道,神学思想在他们的宇宙观中经常出现。泰勒斯曾宣称“一切事物都充满了神”[2]8,但在解释自然现象发生的时候,泰勒斯却不认为自然现象的发生是神意所导致的,希腊科学一开始就把神意给撇开了。希波克拉底医派的医生在讨论“圣病”(癫痫)之时,就认为“圣病”并不比任何其他疾病更非凡或神圣,只是由于它与其他疾病截然不同,才“被那些一般百姓在既无知又惊奇的情况下认为是神的天罚”[2]53。希波克拉底医派的医生认为,“圣病”完全是出于自然的原因,而非神意的作弄。尽管在希腊文学描述中,自然仍受神意的随意拨弄,如地震和闪电被归结为宙斯或波塞冬的愤怒,但悲剧家则以另外一种方式提供了一种命定的必然性,那就是命运(Μορα)。怀特海认为,悲剧中冷酷无情的命运,“是现代思想中的自然秩序”。因为悲剧,希腊“学术也就因之和无情而不以人意为转移的事实建立了联系”[1]21。
作为希腊的两大剧种之一的悲剧(Tragedy),其本质并非指表达“伤心、哀恸、怜悯”的表演。希腊语Tragedy之Trag,原义是“雄兽”,Edy则为“祭歌”,即伴随音乐和舞蹈的敬拜式祭唱,合在一起就是“雄兽祭歌”。Tragedy形式庄严肃穆,有学者建议将Tragedy译为“肃剧”,以表达其“庄重”“恭敬”之意。悲剧之“肃”就在于感慨人生和命运之无情。“悲剧的本质并不是不幸,而是事务无情活动的严肃性。但这种命运的必然性,只有通过人生中真实的不幸遭遇才能说明。”[1]15命运(Μορα)作为“一种事实——一种法则”,比自然和诸神更为原始,“甚至诸神也要服从于这样一种力量”[3]47,诸神也难逃天命。尽管诸神和人不甘于天命并与之搏斗,但最终都难逃大劫。“由于命运是一种先定的天命,因而它也是一种自然的道德法则。没有人能摆脱命运,无论是希腊人、特洛伊人还是诸神。它隐藏在一切事物的背后,是一种制约自然界的运动和生长的永恒原则。”[3]47作为事物运行的法则,命运总是冷酷无情的,无论如何,悲剧性事件总是不可避免地发生,无可逃避,而这正是现代科学所持的观点。正是由于这一点,怀特海认为,“今天所存在的科学思想的始祖是古雅典的伟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等人”[1]15。
希腊悲剧中命运的必然性概念并非源自悲剧本身,它是希腊生活中的普遍观念。在希腊,悲剧中“人生活动秩序”的必然性不过是“自然秩序”必然性的一种映射。正如怀特海所言,悲剧中的必然性“是当时一般严肃的观点传播到文学传统中来的结果。在得到这个有力的表现形式之后,它又转过来加深了本身发源的那一个思潮”[1]15-16。正是在希腊悲剧中,人们看到了科学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必然性。
二、模仿说与“美智同一”
科学与艺术的另一个关联就是艺术的写实主义。“写实主义艺术的兴起是形成我们科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因素”[1]50。狭义的写实主义诞生于18世纪,而作为一种认识生活、反映生活的原则和精神的写实主义则早已存在。在古希腊,写实主义表现为模仿说。
柏拉图是对艺术模仿说进行系统阐述的第一人,其模仿理论集中体现在《理想国》卷十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绘了三个世界:理念世界、现实世界、艺术世界。就本体论而言,柏拉图认为永恒绝对、不生不灭的理念世界才是“第一实在”。现实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是有缺陷的第二存在,艺术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是“第三实在”。柏拉图认为,艺术是“摹本的摹本”,“和真实隔着三层”。诗人和画家对现实的模仿不但没有向真实靠拢,反而背离了世界的本来面貌。“从荷马起,一切诗人都只是模仿者,不论是模仿德行,还是模仿他们所写的一切题材,都只得到影像,并不曾抓住真理。”[4]76艺术的模仿是亦步亦趋、照猫画虎,因而是等而下之的格局。在艺术和真理的关系上,柏拉图作了彻底的否定。就认识论而言,柏拉图否定了艺术的真理性质,但柏拉图的模仿说开启了美与真理关系的讨论,在美与知识之间架起了桥梁,为艺术与科学(知识)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美与知识,快乐与求知得到了统一。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深藏于我们的天性中。每个人都能从模仿的作品中得到快感,这种快感不是一般的感性之娱,而是和理性认知有关。有些东西本身虽然让人倍感痛楚,“但当我们观看到此类物体的极其逼真的再现时,却会产生一种快感。这是因为求知……是一件最快乐的事”,“人们乐于观看艺术形象,是因为通过对作品的观察,他们可以学到东西”[5]47。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的快感来自于认知,这种解释有别于柏拉图。在柏拉图那里,艺术恰恰是靠感性取胜。“模仿诗人既然要讨好群众,显然就不会费心思来模仿人性中的理性部分。”[4]84它迎合人性中低劣的非理性部分。悲剧拿“旁人的灾祸来滋养自己的哀怜癖”,喜剧则投合人们“本性中诙谐的欲念”。一些平时引以为耻的东西,在戏剧中“你不觉得它粗鄙,反而感到快乐”[4]86。柏拉图认为,诗人只是靠技巧取胜,“借助文字的帮助,绘出各种技艺的颜色;而他的听众也只是凭文字来判断”,“因为文字有了韵律,有了节奏和乐调,听众也就信以为真”[4]76。如果把这些抽去,它就只剩下一个无生气的躯壳。总之,艺术远离了理性,远离了真理。
在艺术本体论上,亚里士多德放弃了柏拉图的理念说,肯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因此也就肯定了模仿它的艺术的真实性。亚里士多德认为,诗(艺术)的模仿具有普遍性,艺术的模仿不是对现实世界的简单抄录,而是通过可感的艺术形象再现一般的普遍真理。在论述诗与历史的关系时,亚里士多德认为,诗与历史的区别不是形式的因素,而是内容的不同。“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5]81诗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写作。与历史相比,艺术是对现实更高、更深的把握。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诗的目的是从个别的、具体的人物和事件中找出普遍的意义,揭示事物发生、发展的普遍规律。艺术不是与真理隔着三层,而是与真理密切相关。总之,艺术活动不仅仅是一种愉悦感官的审美活动,而且还是一种与认知和真理相关的活动。正如卡西尔所言,“对于希腊精神来说,美始终具有一种完全客观的意义。美就是真,它是实在的一种基本品格”[6]268。
模仿理论将美等同于认知,在审美趣味上强调“逼真”。模仿论的此种倾向表现了美学上的客观主义态度,即“美智同一”,美与知识的统一。“美智同一”意味着艺术与科学的同构。正是因此,怀特海从希腊艺术中发现了科学的所在。
三、作为艺术形式的“数”
在柏拉图那里,艺术模仿的是理念,也是形式。在西文中“理念”和“形式”是一个词,都是Eidos。理念与形式的一体化特征表现了希腊美学的形式主义倾向。在希腊,“数”是最重要的“理念”(“形式”),数学是一切知识中的最好形式。数被柏拉图“看成是理智世界的真正中心”[6]275,“知识必须具备数学的形式,否则就根本不是知识”[7]27。
其实,早在毕达哥拉斯那里,美就被认为与“数”密切相关。毕达哥拉斯认为,“美是数的和谐”。和谐是由比例、尺度和数造成的,是以各个组成部分的数学关系为基础的。在毕达哥拉斯看来,数是最高实体和事物的真正本质。数的原则统治一切,无论是道德还是审美,均可还原为数。毕达哥拉斯很早就在数的研究中发现了能产生“和谐”的比例关系。在音乐中,琴弦的长短比例决定了音乐的音程。和谐的音乐,乃是一种数的关系。音乐节奏的和谐,是由高低长短、轻重不同的音调按照一定的数量比例所组成的。不仅音乐的和谐是由数的比例所决定的,建筑雕刻中的黄金分割也是一种数学比例关系。公元前1世纪罗马著名建筑师维特罗维奥在《建筑十书》中把古希腊美在和谐、美在比例的理论发展为建筑中的美的理论。他认为,建筑物的各部分,即高度和宽度之间、宽度和长度之间能构成一种适当的比例,因而各部分达到一种对称时,它就是美的。这种情况同样也适用于雕塑或绘画。在雕塑和绘画中,人体的美也是数的比例关系。如果艺术家创造的人物从头部的下颚到上眉的轮廓占全身的十分之一,那它就是美的。
鲍桑葵认为,希腊艺术中无所不在的和谐和规律性,“象征着次序分明、秩序井然的行动或生活的最高抽象关系”,“美的基本理论是和节奏、对称、各部分的和谐等观念分不开的”[8]4。总之,这些关系本质上都是数。“数学成了希腊艺术的语法”,黄金分割法是希腊艺术自觉遵守的法则,希腊艺术成了“几何学的无声讲述”。就艺术实践而言,希腊的建筑和雕塑也充分展示了人体和物体结构的静态的数学比例与和谐的数量关系。据艺术史考察,希腊雕像和建筑都是按照一定比例关系建造的,像阿波罗、雅典娜等雕像,都是按黄金分割的比例制造的。巴底农神庙的外观也体现了一种数学上的均衡和比例。在数学原则的支配下,美不过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对象本身具有的自然属性及和谐的数量关系与形式结构,审美则成了对对象的数量关系和形式结构的认识性把握。
希腊艺术中的这种数学关系,在模仿论看来,不过是自然事物本身的数量关系的一个反映。在希腊,自然、宇宙本身就是数学化的。艺术中的比例、和谐不过是几何学在艺术中的应用。劳埃德认为,“毕达哥拉斯学派最早试图为有关自然的知识提供量化的数学基础。这就促使他们成为一种思想进展的发起者,该进展日后对科学尤为重要”[2]25。希腊人对科学最重要的影响,就是给了科学以必要的计算、推理和证明能力,而这主要是来自希腊人的数学研究。“科学所缺少的推理能力从数学方面借来了,这是希腊理性主义的痕迹。”[1]22这种将自然数学化的倾向在《几何原本》诞生之后达到了高峰。数学的应用和证明在《几何原本》诞生之后,“在许多其他很不相关的领域内被引作一种理想方法,遍及了从神学到医学(盖仑甚至在解剖学和生理学中也试图移植几何学风格的证明法)的各个领域”[9]41。始于希腊艺术中的数的研究,促使人们把数学应用于自然事物,有益于增进人们对自然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对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辩术”与知性生活的竞争性
艺术概念是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含义。今天我们所说的艺术在古代是不存在的。在西方,Arts这个概念最初指的是技艺(Tekhne)。希腊语Tekhne一词在汉语中通常翻译为技术学,意指针对某一技巧的论文。这里所说的技巧并非手工技艺,而是修辞、演讲、逻辑等“高级技艺”。在古希腊,修辞、演讲、逻辑与音乐、戏剧、诗歌、雕塑、建筑等都属于艺术的范畴。修辞、演讲、逻辑是作为论辩的技巧而存在的,希腊人好辩,并在论辩中展现了很强的技巧性和知识性。哲学中所言的“辩证法”作为一种“以问答求知识的方法”[10]128,指的就是论说言谈的技巧。苏格拉底将辩证法视为“真理的助产婆”,可见论辩与知识关联之密切。罗素认为,希腊广泛存在的“无拘无束的论辩的习惯”[10]130有助于科学的成长。
希腊公共辩论的习惯与希腊广泛存在的民主制度,特别是雅典的民主制度密切相关。与其他政治制度相比,民主制度的实施依靠的是说服,而不是强制。在雅典,只有使人信服才能推行自己的主张,而不是依靠暴力或命令强制,人们只能运用说理的力量。因此,在希腊保持着一种高度发达的辩论文明,这种辩论文明是希腊民主精神的体现。希腊人表达思想的形式通常是公开演讲辩论,以及与演讲相伴的一系列质询和答辩会。这些活动会趁公共聚会之机举办。在希腊,公共政治生活空间往往也是艺术表演空间,“剧场也是政治论坛,……剧场里的观众构成了一种政治聚会,相当于公民大会”[11]130。在公共聚会之际,只要有人要公开演讲,人群就会聚拢过来。在这种情形下,要克敌制胜就要靠雄辩的口才给人留下深刻的视听印象,故而希腊人对修辞学——一种说服人的技巧——的兴趣与日俱增,甚至出现了专门靠教授修辞为生的智者阶层。
要在辩论中取胜,仅有一套雄辩术显然是不够的。辩论并非只靠言辞之利,要在论辩中取胜靠的还是摆事实、讲道理,靠理取胜。“正是由于这种纯粹说服的不足感,刺激了推理模式的发展,有了这种推理模式,就更具有说服力,不仅可以让听众当场信服,而且还能得到真理。”[9]41辩论带动了逻辑证明的研究,逻辑、证明赋予论辩以一种终极的说服武器。希腊精神生活中的好辩风气反映了希腊知性生活的竞争性。由于辩论和竞争的需要,古希腊思想家对自己的理论方法和证据常常采取反思的态度。这种态度对科学的发展极为重要。正是由于激进的质疑和对知识的有效性、合法性的要求,才促使人们发展出一套确定无疑的逻辑推理来为知识提供辩护。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成了推理证明的理论典范。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不但对“论证的分析担负着赢得辩论、并让对手闭嘴的任务”,而且它的“目标是要得到任何人都不得不同意的东西,一个无可置疑的真理。”[9]55正是由于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的“希腊数学的公理—演绎证明与法庭修辞学”密切结合,才赋予知识以严格的确定性,为科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此外,希腊的论辩术也赋予了知识以科学所需要的质疑气质。默顿在《科学的规范结构》中提出了科学的四条规范,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有条理的怀疑主义”。默顿认为,大胆的怀疑是任何有作为的科学家应有的行为规范,怀疑精神为科学知识的扩展提供了认识论的契机。
托比·胡佛在《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中指出,中国之所以没有成为近代科学的发源地,原因在于“中国数学和科学思想的不足之处在于它缺乏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托勒密的《至大论》和《行星假说》的行星模型中所包含的论证逻辑”[12]46。同时,中国的知识氛围也缺乏一种论辩与质疑的精神气质。伯德指出:“自始至终,儒家学说都反对把辩论作为发展知识的方法。”[12]262在儒家那里,好辩是良好礼仪的一种缺失,是“推理者道德败坏的一个信号”[9]52。孔子有言,“巧言令色,鲜矣仁”,“不知其仁,焉用佞?”在孔子看来,佞不利仁,佞指的就是能言善辩。中国人之所以不喜欢辩论,是因为中国人并不推崇怀疑和批判精神。在中国,学习是“一种基于课本的学习,学生背诵课文,并且只有熟记课文之后,才能指望开始解释其中的意思。此外,他们崇尚传承和维持,而不是批评”[9]170。托比·胡佛等人的相关论述,反证了希腊拥有作为科学发源地所具有的独特精神气质。
五、结语
就古希腊而言,艺术一词也包含手工技艺,但手工技艺在希腊并没有登上知识的殿堂。一方面,古代技术以生产实践经验为基础,主要涉及有关手工操作的诀窍和制品的秘方。而掌握这些诀窍的工匠大多出身下层,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有知识有文化的希腊公民却不屑于从事手工劳动。在希腊,科学的学术传统与技术(Tekhne,也指艺术)的工匠传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融合,只是到了近代,由于实验科学的出现,才弥合了两者的裂隙,并由此导致了近代科学的诞生。但在希腊也偶有例外,毕竟在技术活动的某些领域中可能存在包含较多科学内容与较强智力的智识传统。这在阿基米德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阿基米德是杠杆原理、浮力定律的发现者,在数学方面也成就卓然,但阿基米德的身份更多是机械师而非科学家。阿基米德发明过许多机械装置,如为灌溉而发明的螺旋扬水机。丹皮尔认为,“力学和流体静力学的起源应该到实用技术中去寻找,……当观察同在几何学中学到的演绎方法结合起来的时候,这两门科学就有了坚实的基础。把这两门科学放在坚实基础上的第一个人是叙拉古的阿基米德”。“他的工作比任何别的希腊人的工作都更具有把数学和实验研究结合起来的现代精神。”[13]41在阿基米德身上,科学的学术传统和技术的工匠传统得到了很好的结合。阿基米德是近代实验科学的先驱,就此而言,希腊艺术(技术)与近代科学密切相关。
事实上,追溯科学一词的词源也可知科学与艺术的密切关联。尽管自伽利略时代以来,科学与科学家早已是一种事实存在,但是直到19世纪上半叶才有“科学家”(Scientist)一词。剑桥哲学家威廉·惠威尔首创了这个词。“当时,他意识到英语中并没有专门的词来统一指称化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电化学家以及其他研究自然界的人”[12]19,于是根据英文词汇Artist构造了Scientist一词。最初人们试图抵制惠威尔造词之举,尽管如此,Scientist还是被沿用下来,并被人们广为接受。正是由于艺术与科学的这种密切关联,怀特海才认为,科学起源于艺术,尤其是希腊艺术。也正因如此,怀特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中宣称,“现代科学起源于希腊”[1]21。
[1]A.N·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M].何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G.E.R·劳埃德.早期希腊科学: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M].孙小淳,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
[3]安东尼·M·阿里奥托.西方科学史[M].鲁旭东,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4]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5]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注.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6]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 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7]H·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M].伯尼,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7.
[8]鲍桑葵.美学史[M].张今,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
[9]G.E.R·劳埃德.古代世界的现代思考——透视希腊、中国的科学与文化[M].钮卫星,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
[10]罗素.西方哲学史[M].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1]魏凤莲.古希腊民主制度研究的历史考察[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130.
[12]托比·胡佛.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M].周程,于霞,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3]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宗教和哲学的关系[M].李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1.
(责任编辑余筱瑶)
10.3969/j.issn.1008-6382.2016.04.001
2016-07-03
天津市高等学校创新团队培养计划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TJKS15—009)。
谢江平(1976—),江西吉安人,哲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B83 ;G3
A
1008-6382(2016)04-00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