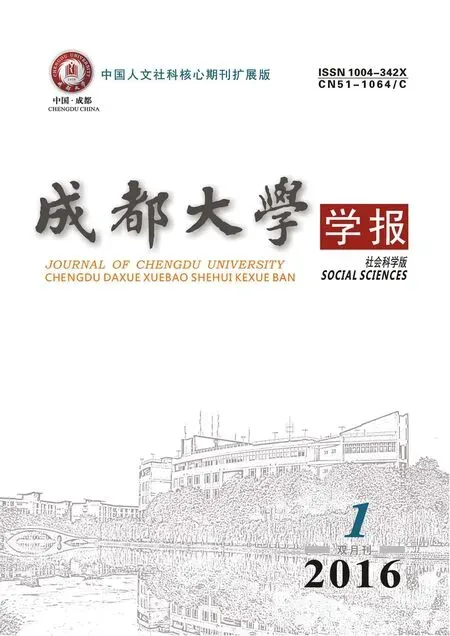民国文学史视野下通俗小说家“著史现象”考论*
——以张恨水的1930年为中心
康 鑫 刘晓红
(1.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2.成都大学 期刊中心, 四川 成都 610106)
·文艺论丛·
民国文学史视野下通俗小说家“著史现象”考论*
——以张恨水的1930年为中心
康鑫1刘晓红2
(1.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河北 石家庄050024; 2.成都大学 期刊中心, 四川 成都610106)
1930年的张恨水投入大量精力进行文学史料收集和考证。他对通俗小说渊源的考证显示出对小说研究初步的学术积累。除张恨水外,民国时期通俗理论的相关论述,多出自于身为通俗小说家的作家之手,他们从创作实践出发,随感式地论说有关通俗文学创作的相关问题,这成为民国通俗小说家表达文学观念的特殊方式。这些关于文学史零散但鲜活的论述应成为当下研究者建构现代通俗文学理论重新返回的历史现场与理论原点。
民国文学;张恨水;著史;1930年
张恨水一直有写一部中国小说史的心愿。以往的研究者多关注作为小说家的张恨水,对于他的学术思路很少提及。这与张恨水的研究论著没有完成、相关文学理论论述过于零散有关。事实上,从关于著史一事只言片语的记述文字中,依然可以窥探出张恨水的文学理论思想及其学术眼光。1930年的张恨水投入大量精力进行文学史料收集和考证。他对通俗小说渊源的考证显示出对小说研究初步的学术积累。除张恨水外,民国时期通俗理论的相关论述,多出自于身为通俗小说家的作家之手,他们从创作实践出发,随感式地论说有关通俗文学创作的相关问题,这成为民国通俗小说家表达文学观念的特殊方式。这些关于文学史零散但鲜活的论述应成为当下研究者建构现代通俗文学理论重新返回的历史现场与理论原点。
杨义先生曾以“张恨水:热闹中的寂寞”为题,论述过张恨水在学术界遭遇的“冷遇”。他说“张恨水是什么?他的读者很多,但真正的知音者少,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热闹中的寂寞。”[1]近几年,张恨水遭受“冷遇”的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可以用“热闹中的热闹”来描述张恨水受到的追捧。张恨水的小说不断被翻拍成电视剧热播。从《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到《纸醉金迷》,张恨水可以称得上是小说被翻拍最多的民国作家之一。央视收视率颇高的《百家讲坛》及时抓住观众的兴奋点,连续推出五期“张恨水系列”讲座,邀请袁进、孔庆东、徐德明、张中良、汤哲声五位知名学者为观众解读张恨水小说。学术界近几年对张恨水的研究也取得了颇丰的成果,张恨水的家乡安徽省潜山县前后举办多次国际性的张恨水研讨会,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对这位民国小说家给予了多方位的关注。张恨水研究在新世纪突然“热”了起来。
一时间,张恨水的知音似乎一下子多起来,从“冷遇”到“热捧”固然是个令人兴奋的转变,但前后如此极端的转变也颇令人感到迷惑。张恨水在民国和当下两度“热”起来的缘由何在?在“冷”与“热”两种极端情绪背后是否说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张恨水热”有更多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地方?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考量民国大众文化潮中的“张恨水现象”?这些问题,都未被学术界予以足够的关注。如果从这些问题出发,继续追问下去,会发现杨义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张恨水研究中存在“热闹中的寂寞”的质疑,今天仍具有警示意义。笔者将在下文对研究界较少关注的张恨水在1930年的一段特殊的心路历程展开论述,以此剖析张恨水对现代通俗文学创作的独特认知与实践。
一、张恨水的“著史愿望”:为通俗小说著史
写一部中国小说史是张恨水一直怀揣的愿望,尽管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院派学者。通过著述文学史这一具有学术倾向的心愿可以透视出其背后凝聚着张恨水对文学特殊的生命体验。以往的研究者多关注作为小说家的张恨水,对于他的学术思路很少提及,即便提及也常常引述张恨水及其子女的记述,将它当作一个普通的事情看待。这与张恨水的研究论著没有完成、相关文学理论论述过于零散有关。事实上,从关于著史一事只言片语的记述文字中,我们依然可以窥探张恨水的文学理论思想及其学术眼光。“三十年代的北京,对学者教授的尊崇在职业作家之上。许多作家都逐渐放弃或减少写作,去从事学术性研究和在大学教书。张恨水虽然创作了许多小说,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但他深受小说是‘小道’的传统观念束缚,并不推崇自己的职业。他向往从事学术研究,他热心研究中国小说的发展。”[2]张恨水是否是因为不推崇小说家的职业而热心于学术研究尚待商榷,但是这些足以凸显著述小说史在张恨水生命中所占据的位置。“著史愿望”背后隐含的一系列动机值得我们仔细探究。
张恨水为何有小说史写作的欲望和动力?究竟是哪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困扰着他?也就是说,张恨水写作小说史的文化针对性是什么?他对小说史有兴趣的特殊性何在?在小说史中,张恨水试图提出什么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作者和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
作为“新闻工作的苦力”的张恨水,少有精力和工夫顾及编辑、创作之外的兴趣、爱好。家庭生活的重担迫使张恨水必须不断地写作,不得不“卖文为生”,不过他深感这绝非乐事,如他所说:“于是看见卖文之业,无论享名至如何程度,究非快活事也”。[3]由于常年不停地写作,他几乎成了“文字机器”。但张恨水一直有写一部中国小说史的愿望,稍有闲余就到处搜集善本古书,为写小说史做准备,但这个愿望最终未能实现。“可惜遭到‘九·一八’大祸,一切成了泡影。材料全部散失,以后再也没有精力和财力来办这件事”。[4]“这一些发掘,鼓励我写小说史的精神不少。可惜遭到‘九·一八’大祸,一切成了泡影。不过这对我加油一层,是很有收获的。吾衰矣,经济力量的惨落(我也不愿在纸上哭穷,只此一句为止),又不许可我买书,作《中国小说史》的愿心,只有抛弃。文坛上的巨墨,有的是,我只有退让贤能了,迟早有人会写出来的。”[5]由此可见,造成小说史没有完成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九·一八事变”造成以往收集的资料全部失散;第二,繁忙的工作使张恨水没有多余的精力投入这一浩大的著史工程;第三,战事导致国内形势巨变,个人财力紧张,经济上无力收集珍贵的古书。由此可见,未完成的中国小说史均是外力所致,绝非张恨水本人主观方面造成的。
张恨水本人以及子女曾在回忆文章中多次提及他想写中国小说史的持久愿望和努力。他的女儿张明明回忆说:“他有个愿望是写一部中国小说史,可惜没有如愿,我把他的愿望转述读者,希望我们的同胞,无论是在中国大陆上的、台湾的、香港的或是海外华人,能完成几部小说史,以慰藉在动荡的年月中度过一生的老一辈文人。”[6]张恨水自己也说:“关于我的小说事业,除编撰而外,一年以来,我有点考据迷,得有余暇,常常作一点考证的工夫。起初,我原打算作一部中国小说史大纲,后来越考证越发现自己见闻不广,便把大计划打消,改了作中国小说史料拾零,最近我又怕人家误会是片断的,改名中国小说新考,万一这部书能成功,也许对中国文学问题有点区区的贡献。”[7]上述两次彻底改变小说史的著述思路,主要原因是他考虑到本人的能力和手头掌握的资料所限。
中国文学史著述是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教育体制影响,在中国兴起的一种文化需求。“西式分科教育形态也因西学的纳入,逐渐成为学堂授习知识的主要方式。随着西式分科教育的施行,其背后所代表的西方知识分类系统,也因此而透过制度化的形式渐渐开始影响中国传统的知识结构,并促使近代学术体系出现重大的转折”[8]。在“西潮”冲击之下,中国的研究学者受到西方文学史研究方法、叙述体例的影响,逐步开始著述中国文学史。由于文学史多应用教学需要,产生于新式教育体制之内,因此,其著述者多为在大学担任教职的学者。鲁迅曾说:“我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先因为要教书糊口,这才陆续编成的”,“这三年来不再教书,关于小说史的材料也就不去留心了。因此并没有什么新材料”。[9]鲁迅所说确为事实。如果不是教学需要,也许如今许多声名赫赫的文学史家都不会从事文学史撰写。作为职业报人和业余作家,张恨水有别于鲁迅和那些在高等学府担任教职的教授、学者,将编写文学史作为完成教学任务的一部分并以此换取薪酬。①著述文学史属于学院派的思路,这并非是身为小说家的张恨水所擅长的。在这种情况下,不是大学学者的张恨水对著述文学史的持久愿望就显得尤为特殊。既然,著述文学史并非必须完成以换取教职薪酬的方式,那么,张恨水是在一种怎样的生命状态下萌生著述一部中国小说史这一愿望的呢?这一持久的愿望是否能投射出张恨水潜在的文学史意识呢?对张恨水在1930年前后生活状况的分析也许有助于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
二、在创作与学术之间:张恨水的1930年
纵观张恨水一生,其在学校担任教职的日子是极为有限的。“1931年,父亲在四叔和一些朋友的鼓励下,以自己的稿费出资,创办了‘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又因他的声望,被推举为校长,兼教中国古典文学和小说创作,但不过问具体校务,日常工作由四叔主持。”[10]“父亲偶尔讲讲课,也多是语文之类。”“学校划了一座院落作为校长办公的地方。父亲住在学校里,除了教书,什么意外的打扰都没有,能够静心静意地写文章、看书。”[11]张恨水仅有的这次教书经历,颇有“客串”的意味,其上课内容也集中在自己的专长——文学鉴赏和文学创作上,并不涉及系统的文学史教学。此外,他居于学校出资人和校长的位置,只教几点钟的国文,另外就是跑路筹款。这与普通教师以教学、科研为主要工作是完全不同的。由此可见,作为教学所需而撰写文学史并非张恨水必须所为之事。
文学史写作是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和时间的工程,并且无法迅速地换取稿费或版税。1930年,张恨水因对成舍我苛刻的给薪方式不满,辞去《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的编辑职务。②之后的一段时间,张恨水有了难得的闲暇,也让他有更多的精力专注于小说史资料的收集。“父亲自1930年2月辞去了《世界日报》工作以后,没有编务缠身,可以一心一意地写作,心情也愉快”,“父亲也要给自己‘加油’,每晚登床以后,总要拥被看一两点钟的书。他看的书很杂,文艺的、哲学的、社会学的,他都要看。此外,几本长期订阅的杂志,也是每期必读的。他说,必须‘加油’才能跟上时代,理解时代,这也就是所谓的‘画眉深浅入时无’了。”“这时父亲的‘加油’,兴趣偏重于考据。”[12]张恨水也多次在回忆文章中提及自己的这个爱好和努力。《我的创作和生活》中这样写到:“这时,我读书有两个嗜好,一是考据,一是历史。为了这两个嗜好的混合,我像苦修和尚,发了个心愿,要作一部中国小说史,要写这部书,不是光在北平几家大图书馆里可以把材料搜罗全的。自始中国小说的价值,就没有打入四部、四库的范围。这要到民间野史和断简残编上去找。为此,也就得多转书摊子,于是我只要有功夫就揣些钱在身上,四处去逛旧书摊和旧书店。我居然找到了不少,单以《水浒》而论,我就找了七八种不同版本。例如百二十四回本,胡适就曾说很少,几乎是海内孤本了。我在琉璃厂买到一部,后来在安庆又买到两部,可见民间蓄藏是很深厚的。由于不断发掘到很多材料,鼓励我作小说史的精神不少。[13]张伍在《雪泥印痕:我的父亲张恨水》中也追忆了张恨水为写作小说史所作的准备,“父亲说,北平是个文艺宝库,只要你有心,肯下工夫,就不会没有收获。苍天不负苦心人,父亲搜集了许多珍贵的小说版本,仅《水浒》一书,他就收集到了七八种不同的版本,就连被胡适先生自诩为124回的海内孤本,父亲在琉璃厂买到一部,后来在安庆又买到两部。又如《封神演义》,只在日本帝国图书馆里有一部许仲琳著的版本,国内从未见过,父亲居然在宣武门小市上,买到一套朱本,上面也刻有‘金陵许仲琳著’的字样,只可惜缺了一本,若是找到这本及其原序,那简直就是一宝了。父亲不仅在犄角旮旯的书摊小市上去找,也到一些私人收藏家去看,他曾在一位专门收集中国小说的马毓清先生那里,见过一部《三刻拍案惊奇》。这些挖掘出来的宝藏,使父亲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觉得写小说史的心愿能够实现了,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欣喜。不料就在他准备全身心投入到《中国小说史》的写作中去之时,‘九一八’国难来临,他辛苦搜集到的宝贵资料,后来都毁于战火之中,此后,他再也没有经济能力,也没有精力去寻觅那些珍贵无比的小说史料了。父亲要写《中国小说史》的心愿,终究只是一个心愿!”[14]
实际上,即便是1930年2月辞去《世界日报》编务工作之后,张恨水的闲暇时间也只能说是相对宽松一些,他仍有许多“文字债”。“他每天从上午9点开始写作,直至下午六七点钟才停笔。晚饭后,偶尔和母亲去听场京戏或看场电影。否则仍是继续写稿到深夜2点。”[15]“这一时候可以说是他的创作高峰期,写下了大量的脍炙人口的作品,像被人们称之为‘张恨水三大时代’的《黄金时代》(后易名《似水流年》)、《青年时代》(后易名《现代青年》)、《过渡时代》及《满江红》、《落霞孤鹜》、《美人恩》、《欢喜冤家》(后易名《天河配》)、《杨柳青青》、《太平花》、《满城风雨》、《北雁南飞》、《燕归来》、《小西天》、《艺术之宫》等等。”虽然同时为几家报刊写稿,但仍要负担一家十几口人生活的张恨水并非真的有闲并且有钱,作为职业编辑和作家的他,其实没有必要去做著述文学史这种耗时耗力而且不能立即有所收益的事情。这就有必要追问,完成一部中国小说史在张恨水心目中到底有多重要?它在张恨水整个文学创作历程中处于怎样一个位置?
创作小说史的动机,必然是由一系列问题开始,并在解答这些问题中展开“史”的叙述。首先,张恨水对小说史著述的心愿完全处于对中国文学历史的独到理解。“他认为中国小说,始终未能进入中国‘文学殿堂’,在追求仕途经济的大人先生们眼中,稗官小说不过是‘雕虫小技’,在‘四部’、‘四库’那样的正史中绝无其立身之地。只能到民间的野史和断简残编中去寻找。”[16]显然,为中国以往不被重视的中国小说著述写史,发掘、还原小说应有文学史地位是张恨水写作《中国小说史》的直接愿望,也是最大的动力,并且他更进一步地将问题具体到提高中国通俗小说的文学史地位上。由张恨水为准备小说史写作而搜集的资料来看,他所关注的小说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比如《水浒传》、《封神演义》、《三刻拍案惊奇》,也就是说,他想写的是一部中国通俗小说史。近代以来,一批思想革命的先驱试图以小说为工具启发民智,进而达到政治变革的目的。因此,中国小说变革面临的一大任务就是提高小说地位,使小说进入文学殿堂,得到社会认可。晚清,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使“君子弗为”与被称为“小道”的小说负载起社会启蒙的任务被推至文学的中心。张恨水提高小说地位的着眼点显然有别于梁启超的启蒙目的,他将眼光回溯到中国传统通俗小说的资源中,试图发掘以往被遮蔽的通俗小说这一文学资源,并以此开启了自己对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改良之路。
为了写作小说史,张恨水认真研读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郑振铎的研究文章,他将自己初步的一些研究体会写成了《小说考微》发表于1932年7月25日的北平《晨报》:
予尝谓中国小说家之祖,与道家混。而小说之真正得到民间,又为佛家之力。盖佛教流入中国,一方面以高深哲学,出之以典则之文章,倾动士大夫;一方面更以通俗文字,为天堂地狱,因果报应之说,以诱匹夫匹妇。唐代以上,乏见民间故事之文,否叫通俗文字既出,自慰民间所欣赏。而此项文字,冀便于不识字之善男信女之口诵,乃由佛经偈语脱化,而变为韵语。在敦煌文字中,今所见太子赞与董永行孝等文,即其代表也。惟故事全用韵语,或嫌呆板,于是一部分韵语故事,间加散文,盖套自佛经中之“文”与“偈”而成者。久之,又变为两体,一部分韵语减少,成为诗话词话,一部分仍旧,而弹词生矣。[17]
这篇研究札记考证了通俗小说的渊源,显示出张恨水对小说研究初步的学术积累。
文学创作与文学史著述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事业,完成它们所需要的个人资质、心性、文学积淀等方面的素质也是颇为不同的。写小说要求敞开思维、发挥想象、着力渲染,而以“考据”与“历史”为两个基点的文学史著述则要求具备做学术研究的平达通识、顾及全局。这两方面的素质在同一个人身上往往很难达到统一和平衡。作为一个才思敏捷、想象力丰富、擅长编故事的小说家,我们很难设想,张恨水能如此沉浸于古书堆中,冷静地辨识、考证书的各种版本。天马行空的文学创作与冷静严密的学术著述两者很难兼得,加之战时世事巨变,张恨水写作中国小说史的心愿也一直被搁浅了,只是对于这个怀揣已久的心愿,他心有不甘,所以后来不断提及此事。只是后人无法看到一部独具特色的中国小说史,不免令人遗憾。但通过这个未完成的心愿,亦可以发现张恨水对通俗小说文体的自觉意识。
三、现代通俗小说理论研究的初始阶段:通俗小说家的文学史
民初至民国二三十年代的通俗小说理论可以说既丰富又贫乏。说它丰富,是因为当时已提出了许多不同于传统古典通俗文学的新命题;说它贫乏,是因为这些命题大多没有深入、系统地展开论述,多是停留在直观感受和常识性表述阶段。此时,小说理论所使用的论述方法与中国传统小说批评家一样,大都习惯采用序跋、随感、评语、“发刊词”、“小说丛话”等形式,随感性地发表关于小说的理论见解。例如,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绪言、《小说丛话》,李伯元《中国现在记》楔子,《月月小说》发刊词,《小说林》发刊词等等涉及文学理论的序跋、随感大量出现。到了1960年代,郑逸梅《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和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略》依然采用从创作经历出发,以感性的话语方式论述文学理论的著述范式。大体说来,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理论研究在1949年以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至1960年,代表性的成果便是上文提及的《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民国旧派小说史略》以及张恨水的《我的创作和生活》一文。1960年代,与张恨水出生于同一时代,并且同样以通俗小说家身份行走文坛的郑逸梅(1895-1992)、范烟桥(1894-1967)完成了民国通俗小说理论建构的尝试。郑逸梅《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1961)、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略》(1962)这两部论著均是在历史叙述的基础上,升华出关于通俗小说的理论认知。书中通过对各自亲身经历的民国历史和相关文学活动的回忆、总结,触及到关于通俗小说与社会生活、通俗小说的真实与虚构之关系的诸多理论问题。此外,它们所提供的文学史料也为后学研究通俗小说的本体特征奠定了基础。1963年,张恨水完成回忆自己人生历程的文章《我的创作和生活》。这篇长文与郑逸梅、范烟桥的著述思路颇为相似,依旧从作者创作经历的追述中勾连起相关的文学活动并由此延伸及对小说理论问题的探讨,比如对章回小说的理论论述,对武侠小说的历史渊源与发展等问题在书中均有所涉及。
四、小结
张恨水有关文学理论的论述几乎没有形成专门的、系统的论著,除了《我的创作和生活》这篇文章之外,涉及其文学观以及小说理论的论述多散见于他的散文、小说序跋中。近代以来,由作家本身论述文学理论的现象非常普遍。民国时期,通俗理论的相关论述,多出自于身为通俗小说家的作家之手,他们具有非常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从实践出发,随感式地论说有关通俗文学创作的相关问题,是当时许多通俗小说家采用的方式。可以说,这既是民国通俗小说家表达文学观念的特殊方式,但也极具自身的局限性。相对零散、缺乏理论深度的点论抑制了后来通俗文学理论系统建构的进程。但是,这些作家自述为后人保留了最生动和鲜活的历史资料,它们是当今研究者建构现代通俗文学理论必须重新返回的历史现场与理论原点。因此,剖析张恨水的文学观还需重新回到这些零散的相关论述中。
注释:
①鲁迅因在北京大学等校兼课,需要课本而撰写《中国小说史略》;后因在厦门大学任教,须编讲义而完成《汉文学史纲要》。
②1930年4月20日《世界日报》发表张恨水《告别朋友》一文,说明辞去编辑职务的原因:“为什么辞去编辑?我一支笔虽几乎供给十六口之家,然而生活的水平线总维持着无大涨落,现在似乎不至于去沿门托钵而摇尾乞怜”,表示出对成舍我给予薪酬的不满。
[1]杨义.张恨水:热闹中的寂寞[J].文学评论,1995(5).
[2]袁进.张恨水评传[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
[3]张恨水.哀海上小说家毕倚虹[N].世界晚报,1926-05-29.
[4][5][13]张恨水.我的创作和生活[M]//写作生涯回忆.合肥: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
[6][11]张明明.回忆我的父亲张恨水[M]//写作生涯回忆.合肥: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
[7]张恨水.我的小说过程[M]//写作生涯回忆.合肥: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
[8]刘心龙.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M]//罗志田.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9]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10][12][14][15][16]张伍.雪泥印痕:我的父亲张恨水[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
[17]张恨水.小说考微[N].晨报,1932-07-25.
(责任编辑:刘晓红)
2015-12-30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5CZW048);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项目编号:HB15WX016);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SQ151208)阶段性成果。
康鑫(1981-),女,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刘晓红(1981-),女,成都大学期刊中心副研究员,文学博士。
I207.409
A
1004-342(2016)01-9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