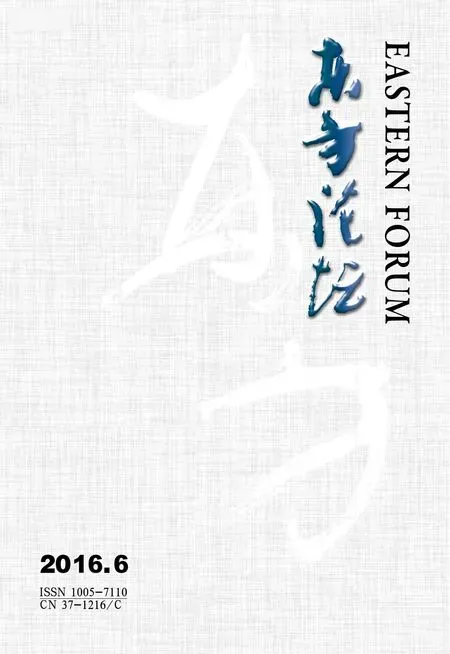纷 乱 将 至
——拉什迪《求婚者》解读
李 升 炜
(1.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875;2.西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纷 乱 将 至
——拉什迪《求婚者》解读
李 升 炜1,2
(1.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875;2.西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在《求婚者》中,拉什迪诠释了20世纪60年代伦敦一个功能失调的移民社区因大英帝国的解体而出现的误解、困境和暴力。在帝国的末日阶段,随着梦想的印度和梦想的英国这一对概念的消褪与奔溃,帝国神话的破灭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英语语言作为一种曾经权威、绝对的系统,被剥夺了其权威性,被拆解、被歪曲。殖民时代的神话破灭了,或被打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将怀旧的过去变成了破坏性的“向前”,并取代了历史的现在的杂糅叙事。处于过去和现在、神话和历史、边缘和中心、定位与错位、官方语言和经改造的语言的交汇之处的拉什迪,在这个短篇中成功地编汇了一种“杂糅的民族叙事”。
《求婚者》; 帝国神话; 分裂; 错位; 杂糅
引言
拉什迪是英语文学世界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国外关于他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其《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 1988)的出版引发了东西方世界的一场热烈的辩论,这场辩论围绕西方社会赖以存在的价值观,特别是关于言论自由、亵渎,以及宗教在世俗社会中的作用。国内的拉什迪研究起步较晚,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而欧美和印度的拉什迪研究已极具规模。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长篇小说《午夜之子》(Midnight's Children, 1981)和《羞耻》(Shame, 1983),至于对他《求婚者》(“ The Courter ”)及其所属《东方,西方》(East, West,1994)小说集,学界则少有人进行专门而深入的研究。实际上,《东方,西方》这部短篇小说集对于理解拉什迪的创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无论是其松散、开放、倒置的谋篇布局,还是诸如杂糅、混合或大杂烩一类的写作技巧,抑或是颠覆传统、构建杂糅的“第三空间”的主题,《东方,西方》都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位置,它也可以解读为拉什迪本人对他引发的那场规模庞大的辩论做出的某种注解。更有甚者,对该短篇小说集探讨的东方和西方的关系问题,也可以对国内自“东方主义”这一术语出现后,关于东方和西方关系的论争作为某种参照,尤其是对华裔作家相关主题的文学作品解读提供借鉴。
而小说集《东方,西方》中的《求婚者》在英语文学世界不但激发了叙事的兴趣和技巧的革新,而且在许多方面成为后殖民小说的典范之作。《求婚者》讲述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一个孟买的穆斯林家庭移居到伦敦的故事。他们起初在贝斯沃特一个非常破落的地方生活,随后搬到肯辛顿一个体面的豪宅里。叙述者是家中唯一的儿子,以回忆的方式讲故事。故事的核心是玛丽和迈斯之间的爱情故事。玛丽是信仰天主教的孩子们的印度奶妈,迈斯来自铁幕东端一个不知名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前是国际象棋高段棋手,在叙事者家所在的豪宅区做看门人。最初,玛丽的英语不好,她发不好字母“P”这个音,把看门人(porter)迈斯说成“求婚者”(courter)。尽管他们沟通有问题,迈斯和玛丽相处得很好。小说中描写的暴力事件主要有两个。有像滚石乐队和披头士乐队打扮的两帮恶棍,他们想恐吓,也可能是敲诈叙述者所住的那个富人区的两个印度王子。看起来像滚石乐队的恶棍,怀疑迈斯隐瞒了那两个印度王子的住所,痛打了迈斯。“披头士们”则误将叙事者的母亲当作王公B的妻子,对她极尽言语的侮辱。这件事发生后,玛丽和迈斯之间的爱情不再像过去一样了。玛丽神秘的生病了,并最终决定返回孟买。
一、“分裂”和“错位”
要谈“分裂”和“错位”,有必要先简单了解一下“模仿”(mimicry)在殖民过程中所处的中心位置和发挥的操控作用,以及它与幻想和神话的关系,因为这个概念对拉什迪的很多作品都是很重要的。我们都很熟悉麦考利(Macaulay)《印度教育备忘录》(Minute on Education,1835)的重要影响①早在1835年2月,当时的英国公共教育总会会长、政治家麦考利在其著名的《教育备忘录》中为印度制定了一套教育方针,提出在印度创立西式的教育制度。目的是形成“一个阶层,他们虽有印度人的血液和肤色,但有英国人的情趣、信念、道德和智慧”。这一思想主导了当时的印度教育,甚至影响到印度独立以后的教育。。在该《备忘录》中,他规约了一名印度精英人士,其“自我”部分是借来的,并描述了印度的精英人士是如何通过模仿和文化的双重性被培养而成的。阿尼亚·伦巴(Ania Loomba)在研究杂糅和模仿时,一再强调这种策略的重要意义:“当然,其基本前提是,印度具有模仿能力,但从来没有准确地再现英国的价值观,他们对于自我和‘真正的英国’之间永久性差距的认识,确保了他们的顺从”[1](P173)。
拉什迪的写作恰恰位于这个“差距”的动态基点之上,他揭示了由于帝国神话的破碎而导致的功能失调(dysfunctionings)和暴力伤害,并探讨了如何治疗或处理这种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方式。实际上,模仿的观念以及它与帝国神话的重要联结,都可以看作是大部分后殖民文本试图解开和并重新定义自己文化身份的方式。V·S·奈保尔(Naipaul)的小说《模仿者》(The Mimic Men)和他本人关于《幽暗的国度》(An Area of Darkness)的评论,可以很好地证明这一点。他认为:“凭借其身体之天赋,任何人的模仿能力都无法和印度人相比”。[2](Piii)奈保尔的写作,从根本上讲,是关于“身体之天赋”的,本论文认为用“历史的约束”来描述拉什迪的写作更为恰当。
二、梦想印度Vs梦想英国
梦想印度和梦想英国相互连结、相互作用的固有观念和“历史的约束”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它们都基于同一主张,即,基于模仿的、人为制造的神话或幻想。虽然本论文主要涉及梦想的英国,这也是拉什迪的短篇小说的中心议题,梦想的印度是同一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无需详细回顾由吉卜林、E·M·福斯特、保罗·斯科特等人所构建的浪漫和迷人的“英属印度”神话,因为这种神话是用来弥合印度的梦想与异域的、扑朔迷离的和敌对的现实之间差距的,这种现象过去是,现在依然是持久而强大的神话。汤姆·奈恩(Tom Nairn)给“英国统治的怀旧情绪”(Raj nostalgia)的延续做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
仿佛本能地知道,将英帝国主义从其摇摇欲坠的状态中解救出来是不可能的,所以诗人转向一个更安全的过去。这种倒退的运动将他们置于一种模式中,此模式也是二十世纪其他思想运动的特征——转向基于狭隘的英国帝国主义基础之上的保守的梦幻世界。[3](P261)
然而,更危险的是,由这种“梦想世界”创造的“永恒的差距”的确导致了一种“玩笑印度”(“joke India”)的出现。拉什迪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因其模仿、不恰当的语言和“非英国式”的行为,不可避免的成为受害者。刘易斯·伍加福特(Lewis Wurgaft)从恐惧、性欲、黑暗和冷漠等方面,分析了他称之为“英国永远无法穿透的、位于印度的心脏,无法回避的谜”。他认为:“本土生活的神秘被死亡和黑暗的力量所控制,而死亡与黑暗蔑视每一种理性的期待”[4](P133)。玩笑和对印度人模仿英国人的嘲笑将成为常见的防御方式,以抵消这种不解和非理性的恐惧。
另一方面,这个梦想印度需要梦想英国的补充性的镜像所平衡,新一代的印度英语作家质疑、声讨和解神秘化的正是这一点。对此,拉什迪本人是如此解释的:
我从小对某种英国有一种亲密的了解,甚至对它有种友谊的感觉:一种梦想的英国,由国际板球锦标赛组成(Test Matches at Lord's),[...] 由伊妮德·布莱顿(EnidBlyton)①伊妮德·玛丽·布莱顿(1897-1968),英国儿童作家,其著作自20世纪30年代起在世界上极为畅销。布莱顿的作品已被翻译成近90种语言。她的写作题材非常广泛,包括教育、自然历史、幻想、神秘和圣经叙事。《诺迪》(Noddy)、《知名五人》(Famous Five)、《秘密的七》(Secret Seven)和《冒险系列故事》(Adventure Series)。和比利·邦特(Billy Bunter)②真名叫做威廉·乔治·邦特(William George Bunter),是查尔斯·汉密尔顿(Charles Hamilton,笔名弗兰克·理查兹,Frank Richards)在其作品中塑造的格雷夫莱尔学校(Greyfriars School)的一名男生。该系列作品在1908-1940年间刊载于男孩的故事周刊《磁石》(The Magnet)。之后,邦特广泛出现在小说、电视、舞台剧和连环画中。组成[...]。我希望到英国去。我等不住了。[5](P18)
梦想印度的“黑暗”,带着其潜在的性威胁,是英国不得不掩盖并试图控制的。在帝国结束之时,它在梦想英国和印度人在英国的“无家感”(unhoming)和“重建家园的理想”(rehoming)相关的多种暴力形式是密切关联的,并已被除拉什迪以外的作家,如韦达·梅塔(Ved Mehta)、尼拉德·乔杜里(Nirad Chaudhuri)和V. S. 奈保尔(Naipaul)等写进了文学作品,并在出生于英国的印度流散作家,如汉尼夫·库雷什(Hanif Kureishi)笔下得到进一步的发挥。然而,梦想印度的诙谐和屈尊的语调常常转化为失望和怀疑,因为梦想英国的神话被种族主义暴力所粉碎,有时是由表面上具有幽默意味的语言误解所引发的。例如,《求婚者》中叙事者的父亲错将“奶嘴”(nipples)说成“乳头”(teats),导致被女售货员掴耳光。这不是偶然事件。《求婚者》第六部分指涉一名政客,在某种意义上,他主导着这个故事:“后来,新闻上说,一个留着稀疏胡子,长着疯狂眼睛的诡计多端的英国人,声称要警醒移民的危害”[6](P189)。“浪漫的民族主义者”“激情帝国主义者”、(梦想)英属印度的热爱者,伊诺克· 鲍威尔(Enoch Powell),在打破印度人的梦想英国方面发挥了主要的作用。《求婚者》中精心设计的种族主义攻击、羞辱和暴力,若依据鲍威尔的政策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事实上,像拉什迪的《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和库雷西(Kureishi)的《郊区佛陀》(The Buddha of Suburbia)③《郊区佛陀》 (1990)是印度裔英国小说家哈尼夫·库雷西(Hanif Kureishi)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印英混血年轻人在伦敦的成长经历。该小说获得了当年的惠特布雷德小说最佳处女作奖(The Whitbread Prize for Best First Novel)。库雷西的写作风格丰富多变,颇具后现代主义的戏仿、反讽的味道。但另一方面,他的写作并没有脱离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语境,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他对英国社会的质疑和反思。中的伦敦,如果参照“鲍威尔主义”,也会同样得到更好的理解。然而矛盾的是,“鲍威尔主义”本身为各种版本的“梦想印度”和“梦想英国”间的虚幻假设了桥梁。汤姆·奈恩认为:
如果英国的民族主义仍然可以用如此不适当的象征来定义,那是因为其核心有一种古老的弱点。古英语时期甜蜜的农村反映出某种一直缺失的东西,英国民族身份本身缺失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长期以来,这种缺失明显地和某种积极的、转移的存在相关,那便是英国的帝国主义思想。[3](P262)汤姆·奈恩更进一步指出:“英国的民族主义,以猥琐的种族主义形式,获得了重生”。[3](P269)据此,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移民的梦魇,例如《求婚者》中各式各样暴力的、种族主义的攻击——叙事者的母亲和女仆在大街上因为被搞错身份受到攻击,暴徒拿着刀子威胁她们,骂她们是“他妈的阿拉伯人(wogs)”,这证明了“伦敦正在杀死女仆玛丽”的事实,移民“无根”的严重后果和移民到一个陌生的、被误解的环境中的悲惨遭遇。拉什迪通过所有这一切想要表现的是,他所构建的梦想英国出了问题:“韦弗利之家(Waverley House),成为了激情的床第婚姻(bed marriages)之所,放荡的男人和未满足欲望的年轻人在那里滥饮”[6](P190)。
三、纷乱将至——《求婚者》的语言学解读
帝国的终结和神话的粉碎以及幻想的破灭是相互关联的,那些神话和幻想曾帮助稳固殖民权威和被殖民者的两极格局,原本各种“英国本地人”现在变成了“从次大陆来的移民”。当意义变得延缓(deferred),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变的紊乱”,和过去一样,现在依然可以通过英语语言充满活力和自由的爆炸,看到英国社会的杂糅现象。拉什迪的作品对表现这一过程非常重要。它包含许多丰富、模糊的多样性,不同的、对抗的话语以玩弄的方式强调了不可靠性和模糊性,通过提供各种新的、可替代的呈现模式,颠覆并挑战现状。虽然是在一个微观的层面,研究他的短篇小说往往可以揭示一套系统,这套系统包含了编码的结构和文体特征,它们成为拉什迪长篇小说的决定性因素,并强调了重新定义这种分类的过程。
为了探究这个过程的语言学意义和英语语言摇摇欲坠的权威性,我们具体地来分析一下《求婚者》的文本结构。首先,《求婚者》的基本框架结构是拼凑而成的。小说标题含义模糊,作者通过这种模糊性,提请读者注意名字的偶然性,以及由此影射的文化身份的流动性。在拉什迪的世界里,人一生中不再仅有一个固定的、正式的名字。求婚者原来是看门人,但他同时履行了这个名字所包含的两个功能。以类似的方式,依据双关、读音相似,或某些个体特征等,小说中许多人物都被冠以绰号,如肯定的玛丽(Certainly-Mary)、孩子害怕的扎德(Baby-Scare-Zade)、混淆的多多(Mixed-Up,the Dodo)等;他们甚至会有几个不同的名字,如父亲、阿爸(Abba)或牛头怪(Minotaur)等。绰号或一人多名的现象,一方面暗含了多重视角,另一方面也表明,每个人的身份是不断变化的,只能通过其他人在他们文化框架中的观察才可以被定义。叙事者本人无疑带有部分自传的特征,他没有名字,当他在东方与西方之间徘徊时,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双重的视角,将不同的故事结合在一起,并最终以近乎定型或漫画的形式呈现给读者,例如小说中两个沉迷于性事的印度人,便是以半匿名的方式指涉王公B和王公P。
同样,为了创造喜剧性效果,拉什迪明显地热衷于颠覆和改造英语单词。例如,将“p”写成“f”,所以“有请”(yes please)变成了“好吧,跳蚤”(yes fleas),或将“p”写成“ck”,于是“去购物”(going shopping)变成了“变得令人震惊”(going shocking)。这种语义创造在小说中虽然很多,但只是初步的尝试,后来,他戏谑地发明了像“黑猩猩茶”(chimpanzee tea)或“极为详尽的”(empurpled)这样的短语,并玩弄语义的误解,如将“奶嘴”说成“乳头”。
此外,通过将印度词汇写进他的文本,“杂糅”或使英语“印度化”,明显地反映了他“为我们自己的目的改造(英语)”[5](P17)的主张。当然,这种做法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很普遍,但拉什迪诙谐地对之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将这种改造扭曲成一些语调扩张、生动活泼的表达,例如“嗨!阿拉-图巴(Allah-tobah)!亲爱的”。在他的文本中,不时地出现诸如“阿叉”(achha)这样的词汇,以及英国人对印度移民使用“三次”(thrice)、“通心面”(macaroni),“山路”(ghats)等词的具体用法时,会引起的嘲笑或认为他们语义不清的讨论。
同样,拉什迪在文本中融入了各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迥异的对话,实现了一种丰富、多样化的“众声喧哗”(heteroglossia),也丰富了小说的基本结构。文本中既有种族主义者的辱骂:“他妈的阿拉伯人(wogs)[…]你他妈的快过来,你他妈不知道他妈的该怎么做啊。你他妈为什么不滚回他妈的窝吉斯坦(Wogistan)?”[6](P204),也有温文尔雅的回答:“现在请原谅我们 [......] 我们不是你们要找的女士”[6](P203)。无名的叙事者本人的声音很有趣,因为他的身份,在更大的意义上来说,仍有待确定。他的双重焦点,或拒绝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做出选择,以及他的不确定性,意味着一种充满戏剧性的对比的摆动,他既表现出一种近乎傲慢的“叙事者的浮华”:“自从他的大脑弥漫着困惑,他一度肯定的事情,已经让他失望,他几乎不再能确定任何事了”[6](P176),也显示出博学:他会使用像“回文地”(palindromically)①palindromically的词根是palindrome,“回文”,源自希腊语“palin”(παλιν,back,“回”)和“dromos”(δρóμoς,way, direction,“路,方向”)。“回文”指的是一个单词、短语或数字,反过来读和按顺序读是一样的,就好比DNA链一样。这样的表达,同时也有一种不成熟的滑稽,例如他这样描述自己:“那时我十五岁,和没事的公鸡一样冲动”[6](P179)。但也许最明显的,是拉什迪通过对自我评价的嘲讽,使用叙述的括号或旁白,直接地暗示读者哪些是应该怀疑的,哪些是用来颠覆叙事者的叙述的,从而形成一种反讽的距离,这种技巧贯穿整个文本,使得叙事同时在两个层面发挥作用。这种疏远的技巧,成为拉什迪立体式小说写作的概念性特征:“当印度感觉像天堂一样遥远(如今,天堂似乎变得更加遥远,但是印度和地狱,却近了很多)”[6](P175)。
而且,所有文本中不同的对话通过一个欢快的、变化的和丰富的“间文本”(intertext)联结起来,包括当代文化的因素或1960年代的声音:流行歌曲、动画片、连环漫画、西部片、童谣、圣诞颂歌等等,因其众声喧哗的无处不在。它们可以抵消故事所包含的残忍的绝望,表明这些可替代的话语或声音与故事并存,与它们对抗或进行补偿,就像影射在文本马赛克表面的伦敦,可能会搅乱或杀死故事中人物,但它也提出挑战,诱发刺激。
和这些声音相对的是,拉什迪在文本中将沉默作为另一种可能的对话。迈斯(Mecir)因为中风,已经说不出话来,没有任何真正的语言能力,但仍然可以工作并经营一段恋情。此外,他还是国际象棋冠军。或许拉什迪故事想要真正表达的信息是,作为战略游戏的国际象棋可以作为交流成功的可替代方式,它跨越了不同的地域和语言,冲破了国籍、社会阶级和历史时期的界限。《求婚者》中下国际象棋的人物,渡渡(Dodo)、混淆者(Mixed-Up,指迈斯),当然还有玛丽,在战术家和策略家之间权力平衡基础之上,创建一种新的独立的秩序,一种新的配置。叙事者表现了对他们的尊敬,将他们描绘成能够克服困难,战胜失败,失去家园后又重建了家园的人,他们拥有智慧,是精英分子,但这种精英的形成不是麦考利认为的愚蠢的手段,比如模仿。
在所有拉什迪作品中,对英语语言颠覆的例子司空见惯。其中,幽默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幽默清楚地表明了能指和所指之间荒诞的间隙,反映了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绝对权威的荒谬性。幽默起到了挑战和颠覆的作用,是“半玩笑、半讽刺的”(“tongue in cheek”)①《牛津英语词典》对“tongue in cheek”的解释是“幽默讽刺的、没必要当真的”。在英语文学作品中,有关“tongue in cheek”最著名的例子也许是乔纳森·斯威夫特1729年所作的散文《一个小小的建议》(“A Modest Proposal”),斯威夫特在文中用“tongue in cheek”的滑稽说法,建议爱尔兰人把自己的儿女卖给有钱人吃。关于“tongue in cheek”的起源众说纷纭,一种说法认为它源于戏剧表演艺术,演员为了避免在不适当的时候笑场,通常会把舌头伸到两腮处,体现一种滑稽的效果。“不诚实的”叙事者采用的主要策略。
结语
《求婚者》是一个典型的、微观的后殖民短篇小说,许多拉什迪更为知名的小说特点在其中初露头角。众多相互对抗的话语所呈现的欢快的、令人振奋多义性,形成了一种新的、解放性的叙事张力,各种杂糅的声音影射了英国和英语语言在同一时间动态变化时的一种真实性。拉什迪通过构建20世纪60年代伦敦一个功能失调的移民社区,探索、诠释并解神秘化了因大英帝国的解体而出现的误解、困境和暴力。在帝国的末日阶段,随着梦想的印度和梦想的英国这一对概念的消褪与奔溃,帝国神话的破灭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英语语言作为一种曾经权威、绝对的系统,被剥夺了其权威性,被拆解、被歪曲。殖民时代的神话破灭了,被打乱了,正如霍米·巴巴所说:“一种杂糅的民族叙事出现了,将怀旧的过去变成了破坏性的‘向前’,并取代了历史的现在”[7](P318)。拉什迪处于过去和现在、神话和历史、边缘和中心、定位与错位、官方语言和经改造的语言的交汇之处,他成功地编汇了一种新的“杂糅的民族叙事”。
[1] Loomba, Ania. Colonialism/Postcolonialism [M]. London: Routledge,1998.
[2] Naipaul, V.S. An Area of Darkness [M]. Harmondsworth: Penguin,1968.
[3] Nairn, Tom. The Break-Up of Britain [M]. London: New Left Books,1977.
[4] Wurgaft, Lewis D. The Imperial Imagination [M].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P,1983.
[5] Rushdie, Salman. Imaginary Homelands: Essays and Criticism 1981-1991[C]. London: Granta/Penguin,1992.
[6] Rushdie, Salman. East, West [M]. London: Random House/ Vintage,1995.
[7] Bhabha, Homi K. “Dissemination: Time, Narrative, and the Margins of the Modern Nation”, in Nation and Narration [C]. Bhabha. (Ed.). London: Routledge,1990.
责任编辑:冯济平
Ongoing Unstuck: A reading of Salman Rushdie's "The Courter"
LI Sheng-wei1,2
(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5, China; 2.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
Salman Rushdie's "The Courtier" was published as the fi nal contribution in Rushdie's collection entitled East, West. In it, Rushdie explores, decodes and demystifi es the misunderstandings, dilemmas and violence resulting from the breakup of the British Empire,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a microcosmic, dysfunctional, immigrant community in London in the 1960s. This article tends to examine how "The Courter" is organized around the key post-imperial elements of disjunction and dislocation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for language and writing. The joyful and exhilarating polysemy of so many competing discourses generates a new kind of liberating narrative tension, an authenticity of hybridized voices at a time of dynamic change for England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The myths of the colonial period are shattered and dislocated. They are replaced by a hybrid national narrative that turns the nostalgic past into the disruptive ‘anterior' and displaces the historical present. Rushdie, poised as he i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past and present, myth and history, margin and center, location and dislocation, language and languages, to transform, disrupt and displace as he assists, masterfully, in the compilation of a new "hybrid national narrative".
"The Courtier"; British Empire myth; disjunction; dislocation; hybridization
I106
A
1005-7110(2016)06-0092-05
2016-09-2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方早期中国文学史纂及其影响研究”(14ZDB086)子课题“英国早期中国文学史纂及其影响研究”;北京师范大学自主科研基金项目(文科)“英语短篇小说——从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SKZZB2015023,本项目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社科一般项目(SKQNYB12017)
李升炜(1978-),男,甘肃天水人,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生,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