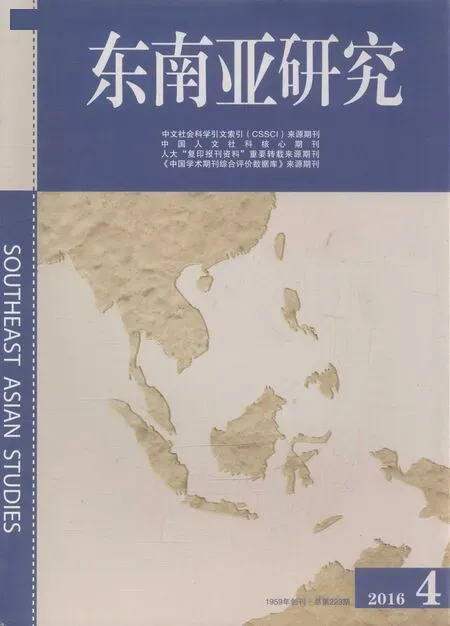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侨批业之视角
程 希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研究与交流部 北京 100007)
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侨批业之视角
程希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研究与交流部北京 100007)
侨批;华侨华人;中国;侨批业;侨批局
随着“侨批档案”成功入选2013年6月的《世界记忆名录》,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认识到侨批(银信)的特殊价值及其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世界意义,侨批这一世界文献遗产的抢救、保护与研究也得到了积极的推动。但是,曾经承担着侨批的收揽、中转、派送以及汇兑、解付之职责,兼具国际金融和国际邮政两大功能的侨批业、水客业,却并未受到更多的关注,特别是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轨迹以及作用和影响,更是鲜见学术探讨与总结。随着侨批局(或银信机构)遗址的不断荒芜破败或被征用开发,它们正在迅速而彻底地淡出历史的记忆。今年是中国邮政开办120周年,本文拟从中国转型、构建为近现代化国家以及融入“世界体系”进程的视角,考察和揭示侨批业、水客业在中国近现代邮政及金融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与作用,并进而再次认识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及其对于中国的意义。
前言
中国人跨国流动产生的华侨华人(中国海外移民)曾经对中国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特殊意义,其跨国汇款(即“侨汇”)同样如此。对于近现代中国来说,华侨华人“特殊性”[1]的成因在政治层面上首推“革命之母”说,而从经济层面探究其深层的原因还是华侨华人的经济实力,所谓“华侨对祖国之经济贡献,莫过于华侨汇款”[2]。曾经作为侨汇集散、转运、兑付主要载体的侨批业,正是这一特殊意义以及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见证与缩影。为更好地展开讨论,笔者需要先说一下本文对侨批(银信)概念的认识,主要是为了强调侨批与侨汇*侨汇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赡家性侨汇是中国近代侨汇主体;侨批汇寄的款项基本都属于赡家性侨汇。参见林家劲等《近代广东侨汇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1-130页。的关系。
侨批(银信),也称“批信”,形式上是钱、信合一的邮寄函件——华侨华人从海外寄回国内、以汇款为主的家庭书信兼汇款凭证;所谓“有钱无信叫国际汇款,有信无钱叫跨国家书”*从功能上说,侨批与现在常见的邮局汇款单相似,但又有两大显著不同:一是外观形态上,侨批有信封,信封上写明“外付xx元”;二是在流程上,收到侨批的人要有“回批”(即收款人回信)。。就本文的视角来看,侨批的核心和意义所在是其国际汇款的属性。对于中国而言,侨批(银信)是来自特定群体(华侨华人)、出现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地域、由特定机构或个人经营、呈现为特定服务形态的跨国汇款(凭证);因地域方言的特定表述和发音,如今形成了约定俗成的特指——侨批、银信(广东五邑地区专称其为“银信”,广东、福建两省其他地方现多以“侨批”统称之。为叙述方便,下文统一称为“侨批”)*从目前常见的解释看,闽南语称书信为“批”,潮汕地区所称的“批”专指寄款信件,因而侨批、银信也被称为批信,二者互为代称;因民间视“异族”为“番”,闽粤把“出洋”、“出国”称为“过番”,故侨批还被称为“番批”。。
侨批是中国侨乡的历史特色、形成基础和主要标志。侨批属于侨汇,是侨汇的一部分、一种或一个类别,即侨汇并非就是侨批。侨乡之所以成为侨乡,侨汇是必要条件。侨汇是移民与国家之间最实质性的联系。曾经承担着侨批的收揽、中转、派送以及汇兑、解付之职责,兼具国际、国内邮政及金融两大功能的侨批局,是传统侨乡兴盛的最显著标志,也是最具活力且最富人文底蕴的机构。
在海外和闽粤等地侨乡之间为华侨、侨眷传递侨批的个人或私营商业性机构、民营组织,在日具市场规模和信誉度后,形成了提供专门服务的“水客业”或“侨批业”,并出现了专营此业的“侨批局”以及相应的同业公会*侨批业同业公会的成立,反映出侨批业的规模化、成熟度,也表明了该行业的制度化、规范化。。一般来说,侨汇出现及经营的方式大致经历了由海外华商在贸易往来中顺便带送,职业水客专门递送,商行、银号或批信局兼营、主营或专营,再到纳入新式机构(银行或邮局)业务的过程。当然,这些方式并非是相继替代的关系,在侨汇具有重要社会和经济影响的百余年间,它们始终是并存的,并基于广府、东江、潮汕、海南、闽南、广西等地域特色和地缘网络形成了不尽相同的侨批业景观。无论是零星水客还是蔚为大观的侨批业,全然是基于伴随移民现象而出现的民间(主要是侨乡社会)需要而自发形成的,体现出反映市场需求和服务市场需求的特征,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先于近代银行、邮政的产生。据族谱资料,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即有菲律宾蔡姓侨民汇款回福建石狮的记载[3],此为目前已知的关于侨批的最早记载。这与国内史学界认为“明代晚期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主流看法,可谓是不谋而合、相互映证的。
另据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侨批最迟出现于18世纪80年代(清乾隆年间),直至20世纪70年代侨批业归口银行管理而逐渐消失,最后的侨批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历时最少在200年以上[4]。而最早的合法侨批局则应是清政府被迫开放五口通商后才出现——1856年开办于汕头的德利信局是目前国内有据可查的最早侨批局[5],现知福建最早的侨批局是1871年在晋江安海镇设立的郑顺荣批馆[6]。与侨批名称的多样化一样,侨批局亦另有“银信局”、“批信局”、“侨汇庄”(广西)、“汇兑局(庄)”、“批局(馆)”等多种名称。从民国时期的归口管理看,均属民信局性质,但因其兼具邮政与金融两大功能,而且是跨国邮政与金融的功能,又有别于当时的其他民信局而被称为“批信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批信局多被称作“信局”、“民信局”;经营侨批的行业则被明文规定统称为“侨汇业”[7]。
综上所述,本文想特别指出的是侨批属于侨汇的性质,是侨汇的原始和自发形态,是私营或民营的侨汇,即一定是通过个人(水客)、私营商贸机构(兼营侨汇)以及其后出现的专营侨汇的、但同样是私营或民营性质的侨批局来提供相关服务和经营的。
强调侨批局或侨批业的私营性质,是为了基于市场(自由竞争)与国家权力(国营垄断)之间的关系更好地认识移民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以及华侨华人在中国近现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处境。此外,侨批与侨批业的消失是耐人寻味和值得深思的。特别是对于新中国这样一个以公有制著称,却在特定历史时期不仅未取缔私营侨批业,反而在历次激烈的政治运动冲击中对其给予各种“网开一面”的“适当照顾”,并且曾经专门制定侨汇政策,发行侨汇券,设立侨汇公司、侨汇商店、侨汇专柜,使用侨汇留成、侨汇供应、侨汇物资、赡家侨汇、建筑侨汇等专有名词,从而形成一度蔚为大观的独特金融商业景象。如果一味从华侨华人爱国爱乡、家国情怀、促进侨乡建设的角度来认识侨批与侨批业,似乎无法充分解读侨批与侨批业的兴盛荣衰。
一 中国近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与侨批业“特殊性”的形成
“中国试图通过自我改造进入现代国家体系的首次尝试发生于清末‘新政’时期。这也可以说是中国政权进化中一个划时代的时刻。”[8]而从外部力量和因素而言,这一“改造”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的签订开始就已被触发和催生了。正因如此,中国向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融入世界体系的进程;或者说所谓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进程,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就是中国按国际规则塑造成为近现代国家的过程,甚至可以说,中国近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与融入世界体系的进程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体两面。近现代华侨华人及其相关事物正是这二者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国家主权的挽回和修复,大国地位的被动维护或积极追求,在晚清以来一直被奉为至高无上的原则、极具敏感性的核心利益和始终不曾放弃的首要目标。邮权被视为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系国家大一统的重要支撑;金融对于一国国计民生之意义更毋庸赘言。这使得国家主导下的邮政专营与金融统制成为中国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性工程,最直接、最明显地体现了国家职能履行的正常与否和对社会掌控力之强弱。然而,侨批业是全球化贸易开启时代及中国近代市场经济的自发产物,在大清官邮开办之前,中国已有数千民信局、侨批局及其分支机构经营邮递、汇兑业务[9],这又使得中国从一个封建国家向现代化国家的转型、塑造的甫一开始,便注定会遭遇国有体制(官营垄断)与私营企业、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或反动的种种博弈。国家主权与大国地位的认知与挽回、修复与维护,使得“国进民退”成为这一过程中的必然历史现象;民信局、侨批局与国营邮政、国有银行的关系是这一历史现象的反映或缩影。
从侨批的起源来看,它是在全球化的初始阶段,随着海洋贸易的发展而产生的。晚清“新政”之前,是侨批业的自发形成与自由发展阶段。晚清“新政”是清政府在内外交困、江河日下的形势下,不甘没落衰亡,力图扭转帝国颓势、维护大国地位所做的最后一搏,中国近现代民族国家的自我塑造也可视为自此开始。侨批业的“特殊性”大致可见于如下多次反复的“国进民退”的历程中。
(一)清末国家邮政开办初期侨批业“特殊性”的初显
清末,一方面因传统官府邮驿制度日趋衰败,两次鸦片战争后包括邮权在内的国家主权不断丧失,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的开启,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满足社会需求的新式国家邮政体系。1877年,福建巡抚刘传铭在台湾架设第一条电报线,成为中国自办电报的开端。1888年,刘传铭在台湾自行设立邮政总局,管理台湾全省邮务,这是中国独立自主开办邮政业务的开端。此前20年,则是由被称为“大清海关掌门人”的英国人罗伯特·赫德,在中国各地海关兼办和试办邮政。1896年,张之洞奏请成立大清邮政获准,“大清邮政局”宣告成立,中国近代国家邮政由此建立。1898年,大清邮政局国内汇兑业务在一些大城市开办。
大清官邮的邮政机构最初在全国仅有20多处,而其时经营邮递业务的民信局及其分支机构已有数千家[10]。随着大清官邮的开办,国家邮政及金融与民信局、侨批局之间也拉开了管制—排斥、竞争—利用、限制—妥协、支持—合作,直至最终取缔—合并等多个回合、几经反复博弈的序幕。
鉴于《天津条约》(第四款)等不平等条约的签署,对于列强在中国开办的所谓“客邮”*“客邮”是指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美﹑日﹑德﹑俄等国先后在中国沿海口岸及一些大中城市私自开办的邮政机构。,清政府只能听之任之,但管控和取代民信局,可谓是清政府统一邮权的“攘外必先安内”之举。1899年颁布的《大清邮政民局章程》开篇即规定:“不准商民寄信为业,以期利权不致外溢……”。章程还规定,民信局须向官局挂号登记,“除挂号民局外,所有商民人等不得擅自代寄邮政局应送之信件,违者罚银五十两。”[11]大清官邮同时还与外商轮船订立合同,规定:“在中国通商口岸只能承带中国邮政局随时交来之信件,其余无论何人及何信局交来往来中国各码头之华洋文信件,一概不得接带。”[12]当时不论是水客或侨批局,所有信、款均由专人携带,自由出入国境。这些规则的出台,无疑也使侨批业受到很大影响。
通过各种排挤、限制民信局和侨批局的行政手段和管理办法,加之充分发挥官营邮政资源和经营等优势,至1904年大清官邮局所很快就扩张到1300处[13]。在官邮力量薄弱之处,民信局尚能维持。对于侨批局,大清官邮更是不得不另行对待。这是因为侨批局并非如其他民信局那样仅限内地投递业务,其业务不仅跨国、越洋,海内外一体相联,而且投送侨批邮件已自成一套规则,乃至未写明地址的侨批,侨批局也能妥投送达,而官邮局所对此运营机制尚无法破解,因而也就无从介入侨批业。故侨批局虽也被纳入挂号管理,需按总包贴足邮资交大清官邮寄递,但实际上是贴足邮资后,仍由侨批局自行投递。对此,《大清邮政章程》的规定是侨批局可“向收信人按其自定条规收取”资费。当然,由于侨批局实质上侧重的是金融业务,即在海外的侨批局收进的是当地的货币,而在国内支付的都是国内正在流通的货币,其自行收取的资费是汇兑手续费而非邮费[14],因而也被官邮视为与“邮政无关”[15]。此为侨批业最初的“特殊”情形。
(二)北洋政府挽回国家邮政利权背景下侨批业的自行其是
辛亥革命后,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主权问题是共和国建国进程的根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也必须以国家统一为政治前提。共和政制下的新“大一统”与国家主权的掌控成为互为表里、相互支撑、双向互动的二位一体。侨批业纳入国有化经营是新的邮政“大一统”所必需,进而也是中国现代主权国家构建之必需。
辛亥革命后,邮传部改名为中华邮政,隶属交通部,对侨批的寄递方法仍按大清邮政规定办理。1913年北洋政府宣布裁撤全部旧式驿站。1914年,北洋政府要求民信局和侨批局领取营业执照,试图以此管控和限制民信局、侨批局的发展,但因这一时期的主要目标为收回被列强侵害的邮政利权,加之军阀混战、南北对立,因而北洋政府对民信局和侨批局实际上无力监管,民信局和侨批局在很大程度上仍享有广泛的自主性,政府的控制是初步的、有限的。一些侨批局不仅不领取营业执照,还趁机扩张业务[16]。
自1917年起,以宣布与德国断交和参加一战为契机,北洋政府开始了积极挽回国家利权、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废约、修约外交,列强在华“客邮”也由此开始陆续撤销。
1918年,北洋政府明令取缔民信局。1919年7月1日,中华邮政开办邮政储金业务。对于侨批局,则基本仍沿用大清官邮的管理办法,要求侨批局到邮政局挂号登记,只是增加了对侨批局从国外运回的邮件总包需开包检查并加盖“中华邮政”印记的规定(主要在广东实行),然后还是发回侨批局自行投递[17]。
1920年10月,中国首次参加万国邮政联盟大会(第七届),签订了一系列相关国际邮政条约,并再次提出撤销列强在华所有“客邮”的要求。1921年,北洋政府公布取缔民信局条例。1922年2月1日的太平洋会议终于通过了中国提出的撤销外国在华“客邮”的议案。至1922年底,列强在华开办的“客邮”,除日本在旅大地区及南满铁路沿线和英国在西藏的邮局外,一律被撤销。国家邮政利权收回、邮权统一取得重大进展。
(三)金融、邮政统一的强力举措下国民政府对侨批业的区别对待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次年,以东北易帜为标志,中国也再次实现了形式上的国家统一。1931年5月,国民政府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开始按照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案再造民国。1927—1937年,是被称为“黄金十年”的时期。在此期间,中国被进一步卷入世界体系之中[18],国家政治建设与经济发展进入快速提升阶段,使得中国在近现代化道路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国家大一统的行政控制力也在不断强化中。就本文的论题而言,即是在推进包括侨汇经营的国家金融体系建立的同时,国民政府继续致力于统一邮权,重点转向国内民信局及侨批局。
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全国交通会议,会议决定于1930年内一律取消各地民信局。同年,中央银行建立。中国银行被指定为专营国外汇兑业务的专业银行并成为经营侨汇的主要机构*至1936年前,闽粤两省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也先后成为经营侨汇的指定机构,并在国内外广设分支机构。。随后,国民政府还针对邮政业开展了“改造运动”,意图将民信局、侨批局纳入国家邮政体系中,要求各民信局、侨批局一律挂号登记;1929年2月,再次重申挂号登记的要求,并要求挂号登记后的民信局、侨批局最迟于1930年底关停,另营他业。其间,民信局以“有补于邮局”等理由一再陈情,呼吁宽限;汕头侨批业公会也与汕头邮政局多次谈判。最终,在海内外压力下,国民政府不得不暂缓对民信局、侨批局的厉行取缔措施。这一回合,虽然因侨批局及其同业公会态度强硬而占上风,但国民政府取缔民信局、侨批局,统一国家邮权的信念并未改变,退让只是暂时的。
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在上海设立了直属交通部的邮政储金汇业总局。1933年4月起,实行“废两改元”政策,统一了混乱的银本位。银本位的统一遏制了钱庄对金融市场的操纵,客观上也起到了管控侨批走私、侨汇黑市交易的作用。1933年10月,交通部再次呈请行政院取缔民信局,以实现“统一邮权”。据此呈报,行政院通令各省市军政机关,要求在1934年底前,一律取缔民信局,并严查私运邮件。侨批局原本也在一并取消之列,但终因侨批局及海内外侨界力量的抗争,在争取侨汇方面国家邮政机构尚力不足逮,交通部邮政总局将侨批局与民信局作了区别对待,规定:“专营国外侨民银信及收寄侨民家属回批者,定名为批信局”,“批信局必须到邮政局登记备案领取执照,每年一换”;自1934年起,“批信局执照每张收手续费国币五元,其余照原有章则办理”[19]。自1935年1月1日起,国内所有民信局终于一律停办,邮权的统一又推进了一步。侨批局虽受到加强管控,但终究“不在取缔之列”,而且通过申领执照被纳入邮政管理体制后,取得了“合法”地位[20]。这是侨批业第二次受到“特殊”对待的情形。
1935年3月,因邮政与储汇分合之争,邮政储金汇业总局改称邮政储金汇业局,划归邮政总局隶属,并开始经办侨汇业务,成为国家金融体系“四行两局”*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以及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中的一局。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废止银本位,以纸币(法币)代替银元,实现了货币统一。侨批业受到的最大影响是币制改革后,稳定了外汇牌价,使得上海对汕头侨汇的转驳作用几乎完全消失,但厦门侨汇未受此影响[21]。
在政府加强监管的情况下,未到邮政局登记挂号领取营业牌照的侨批局,即属于走私性质的非法经营,业务受到一定影响,但对于整个侨批业而言,只是增加了一个政府管控的环节而已,未能从根本上制约其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通过登记挂号、申领牌照“合法化”后,侨批局的经营规模反而在总体上是不断扩大的[22]。
(四) 抗日战争背景下侨批业为国家邮政发展所作的特殊贡献
侨汇业务对于国家邮政来说是一项新兴事业。抗日战争爆发前,邮政总局的邮政储金汇业局在国外尚未有分支机构,其侨汇代理范围有限,加之办理侨汇经验缺乏,相关手续、流程、制度也不完善,因而邮政的侨汇业务远不如侨批局。为改变这种现状,一方面,邮政总局从调查侨批局情况入手,效法侨批局业务流程和经营方式,筹办和推行邮局汇款;另一方面,在侨批业因日军不断扩大侵华战争而陷于困顿、萎缩的情况下,积极与国内外侨汇机构建立业务代理关系,特别是与华侨银行和侨批局相互合作,不断拓展侨汇业务。这一时期,侨批业的运作模式以及分布于海内外的侨批局、水客网络,成为国家邮政借鉴和借力发展的依托,可谓是侨批业在无形中为国家邮政发展所作的“别样”特殊贡献。
1937年初,邮政总局要求广东下属各局详细调查广东各地侨批局的业务状况,以资借鉴效法[23]。同时,通过顶牌借壳、拉拢讨好等办法,积极介入和借力侨批业。如晋江(泉州)最大的侨批局——合昌信局于1937年4月宣告关闭时,中国银行泉州支行管辖行——厦门分行立刻出面承顶了其牌照,采取力求快速收批、解付的操作程序,外加在海外各埠有办事机构、资金雄厚且信用可靠的优势,海外侨批局纷纷联系该局委托侨汇解付业务。厦门被日军攻陷后,合昌信局趁全市侨批局处于停顿状态,独家冒险通过鼓浪屿转递侨批,解清全部批款,顿时声誉雀起,委托其解付侨汇的南洋侨批局一时激增至183家,几乎囊括了闽南的全部侨批业务[24]。
又如,由于在客属地区的侨批业中主要是水客活跃,收汇面相当广。为拉拢水客,争取水客外汇,据《梅州市金融志》载,1940年2月2日,广东省银行丙村办事处主任蔡汉芳、会计朱启修就在该行的二楼设宴招待区属水客,赴宴者达数十人。银行通过联系感情、沟通汇路,发展银行的侨汇业务,使得这一时期水客也成为国家银行争取侨汇的有力助手[25]。
从1937年初开始,邮政储金汇业局及广东邮政管理局还积极与中国银行、广东省银行、越南西贡东亚银行、香港信行公司、澳门民信银号、新加坡华侨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菲律宾交通银行、西贡东方汇理银行等国内外金融机构建立业务代理或合办关系,以收揽侨汇、拓展侨汇业务。其中业务往来最多的,主要还是华侨银行。特别是邮政局与新加坡华侨银行合办侨汇的手续与制度,因较成熟、周密而成为各地邮局与其他金融机构合作的范本。
1938年1月,邮政储金汇业局引用新式汇票单据,“专为华侨汇款之用”,并规定了办理此项汇款业务的五条手续。至1938年7月,广东、福建大部分邮局开始承办华侨汇款;同年9月,广东邮政管理局与华侨银行订定办理南洋群岛及海防等埠华侨汇票,并制订了更为详细的“办理华侨汇票细则”[26]。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在金融方面还出现了与侨批业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重大变化——外汇管制。1937年8月15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了《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7条,揭开了战时强制性金融管理的首章。1938年3月,通过财政部相继公布的《外汇请核办法》、《购买外汇请核规则》等,国民政府开始实施外汇管制。官价外汇由此被垄断,黑市交易随之而起。此举是战后侨批业“外汇逃避”现象不断猖獗的直接诱因。
1939年6月,邮政总局发布定于侨汇开办一周年之际(1939年8月末)开展为期两周至一月的“扩张侨汇业大运动”的通令。此时的背景是侨批局因日军加紧南侵而纷纷停业或内迁,邮政总局开展这一运动不仅是想保证和扩大侨汇收入,更是意图借“民退国进”之机,加强邮政侨汇业务。在借力侨批业扩张侨汇业务的同时,为了宣传邮政汇款的信誉,在与侨批业的竞争中取得进一步优势,邮政储金汇业局还从加强自身管理、改善服务着手,规定了邮局办理侨汇的五大原则:迅速、不索酬金、不强令收款人具保、汇款直接投送至收款人家中、无法投递之汇款即速退回。[27]
此外,为保证“海外侨胞有大宗汇款回国,充实外汇”,除拓展国家邮政侨汇业务外,国民政府还以“支援抗战”为号召,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向海外华侨华人募捐、发行债券,并向海外侨界大力宣传将侨款交由国有银行或其委托银行经汇。1939年,财政部制定了《吸收侨汇合作原则》《银行在国外设立分行吸收侨汇统一办法》,除要求各国有银行采取措施积极争取侨汇外,规定由中国银行统筹各国有银行侨汇收入,营建便利侨汇接收的金融网。对此,广大华侨华人踊跃响应。从1937年7月至1939年2月,海外侨胞通过国有银行在海外的分支行和代理处捐款金额达217,248,875.44元[28]。
从1938年到1942年短短几年间,在国内外侨界的通力合作下,特别是借鉴和借力于侨批业,邮政储金汇业局的侨汇业务迅速发展,取得可观成绩,侨汇办理日渐成熟、规范,经营制度日趋完善,服务信誉不断提升,吸收侨汇总额大幅攀升,在整个侨汇业中“国进民退”格局逐渐形成。1937至1941年被称为“侨汇的发达时期”[29]。除侨汇外,以各种可歌可泣的壮烈义举投身、支援抗日战争也是华侨华人继辛亥革命后掀起的第二次爱国主义高潮,是海内外侨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又一突出贡献。
(五)“东兴汇路”与侨批业为国护“侨”的特殊贡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来自东南亚方面的侨汇被切断。为继续沟通侨汇、救济侨眷,1942年初,以陈植芳为代表的潮帮侨批局业者不畏艰难险阻,积极探索绕开日寇封锁线的新汇路。在多次探索新汇路失败后,在越南海防经营“和祥庄”、“和利兴”侨批馆的陈植芳终于摸清了中越边境一带的地理环境,在当时归广东辖属的东兴镇试汇成功,就此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侨汇生命线——“东兴汇路”。该汇路连接东南亚各国及国内多个地区,全程长达3000余公里,由国外和国内两段汇合而成。国外主要有曼谷线、西(贡)堤(岸)线、金边线、老挝线,国外段由侨批局批工运送,他们逢路坐车,逢水乘船,无车船就靠双腿行走,途经越南海防市到芒街镇,再偷渡越境抵达东兴集结。国内段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从东兴经钦州—梧州—柳州—贺州(膺扬关),再翻山越岭过广东连县—韶关—河源(老隆)—兴宁,由侨批局批工自带;二是由东兴—钦州—南宁—韶关—兴宁和东兴—钦州—遂溪—河源—兴宁,通过东兴的邮局、银行的汇路直接汇寄,实际是当时中华邮政的邮路。由于兴宁是国内段的最后一个邮局,而潮汕地区已沦陷,所以潮汕地区的侨批局还要派批工去兴宁邮局领取侨批,再秘密分发到潮汕及邻省福建的侨眷手中。“东兴汇路”之辗转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为保证这来之不易的侨汇顺利接驳,国民政府也以东兴为中转站,在东兴特设广东省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办事处,对各侨批局给予全力支持和配合,方便、帮助吸纳接收从越南等地汇驳至东兴的侨款,再通过重庆、桂林、韶关等分支行辗转解付侨乡。为保证批款安全,国有金融机构还动用军队武装押运批款。
新汇路的成功开辟,拯救了在战争和饥荒状态下苦苦挣扎的潮汕地区侨眷,源源不断的侨汇收入也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是为这一时期在国家的支持下,侨批业为国护“侨”(既指归侨、侨眷,也指侨汇)所作的特殊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胜利后,“国进民退”的态势旋即恢复。为减少直至取消侨批业,1946年中华邮政又规定,国内侨批局不能接驳受理国外非其分号之批包,而海外侨批局在国内没有分号的,也不准增设。然而,随着内战爆发造成的混乱以及1948年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失败,侨批业一度处于失控状态,充斥着地下钱庄和外汇、外钞黑市交易,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解放初期。
二 意识形态斗争与侨批业“特殊性”的再现与凸显
取缔侨批业是自晚清以来一直未能实现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后,以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为崇高使命和迫切目标,又厉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公有制,私营(民营)的侨批业更当在取缔之列。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在特定历史时期,新中国不仅沿袭了晚清以来对侨批业“例外”对待、“特殊”处理的做法,而且在意识形态斗争贯穿始终的历次激烈的政治运动中,都能对其给予各种网开一面的“适当照顾”,并且以发行侨汇券为标志,专门制订了侨汇物资供应政策,设立了专为华侨和侨眷供应特供商品的华侨商店。从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因侨汇而享受特殊供应成为计划经济体制下蔚为大观的金融商业景观。
(一) 20世纪50年代:“冷战”格局下为国护“侨”模式的重启与侨批业“特殊性”的再度强化
由于百废待兴,新中国既需要营造海内外侨界拥护新中国的向心力氛围,又需要华侨华人在资金、技术、外汇、外贸方面真金白银切实的支持,因而“办好侨汇”在新中国建国伊始就是侨务工作的重要目标。1949年11月22日,中侨委举行第一次主任及各处室负责人联席会议,研究中侨委工作任务的四项职能并起草组织条例,第一个讨论的事项就是“关于便利侨汇问题”。根据侨批业在争取侨汇、沟通汇路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新中国决定对其采取“维持保护,长期利用”的政策;同时“加强团结和管理,使之逐步纳入国家的轨道,成为国家吸收外汇的一种代理机构”。
随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冷战”格局在东亚确立,侨批业又被寄予了在反封锁反限制斗争中发挥特殊作用的厚望。为此,侨批业为国护“侨”重启为“冷战”模式。这不仅使得侨批业受到“特殊”对待之情形愈益凸显,侨批业的“特殊性”也进而扩大和延伸至所有与华侨华人相关的事务。
为恢复和争取侨汇,新中国一方面对侨批业加强管理,整顿、取缔侨汇黑市交易,规定侨汇必须向银行结汇;另一方面,采取多种安抚、优待、奖励措施。1950年10月,全国归侨、侨眷福利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侨批业派代表出席会议。会议提出对侨批业实施“外汇归公,利润归己”的政策,取消旧的双程邮资,改由财政部拨付,税务改为自报查帐,手续费定为12.5‰。1951年下半年全国财经工作已趋统一,华南分局公布了《华南侨汇业管理暂行办法》,将侨批业改称侨汇业,在侨批业中进行重估资产、确定股东、正式建帐等工作,宣布发给侨批业按收汇额的5‰的奖励金(1953年增至7.5‰,后来又增至10‰)。当时侨批业把此项奖金分配给国内企业、国外批局、国内职工,三者各得1/3。与此同时,发给侨批局经营执照,给予一定合法利润,明确宣布“侨汇归公,利润归私”。借助一系列政策措施,新中国通过国有银行逐步控制了侨批业的经营活动,使其走私套汇的不法行为逐步减少,侨批业开始纳入新中国的发展轨道。
1953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国务院前身)发出《关于“侨批员”身份及待遇等问题》的指示,规定在侨汇业务中一律用“侨批员”这一名称。指示肯定了“侨批员”对于争取侨汇、沟通与加强华侨侨眷和祖国的联系起到“相当大”的作用,明确指出对于“侨批员”应给予华侨身份,享受与华侨同等的地位和待遇。1954年中央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公布《侨汇业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共有5章,分为总则、业务范围、报告制度、奖惩、附则等。1955年4月广东省根据该办法,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公布了《广东省侨汇业管理暂行办法登记部分施行细则》,为侨汇业经营管理制定出更为具体的实施办法,管理制度日趋完善。
1953年底全国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后,粮油食品等都实行凭证限量供应。中侨委根据海外华侨的意见,提出侨眷可以根据所持侨汇的多少,发给侨汇证,根据侨汇证上记录的侨汇数额,供给他们一定数量的粮、油、糖等属于统购统销的物资。由于当时正值全国“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的大气候,方案刚一提出,便招致不少反对意见,认为这个方案是反对统购统销,但不久,在国务院财经委支持下该方案便成文下发执行了。
1955年1月,中共中央转发广东省委《关于在反肃运动中处理侨汇问题的报告》,要求各地认真执行侨汇政策,对侨胞汇款,须坚决保护;对反革命的侨汇,亦应遵照法律手续和银行规章,加以适当处理。次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贯彻保护侨汇政策的命令》,《人民日报》配发了《贯彻侨务政策,坚决保护侨汇》的社论,再次明确侨汇是侨眷的合法收入;重申国家保护侨汇的政策,不仅是国家当前的政策,而且是国家的长远政策。为纠正违反侨汇政策的错误做法与行为,1955年广东省共审理侵犯侨汇案件669宗,其中判刑137宗,判死刑8宗。福建省也查处了一批贪污、冒领侨汇的罪犯。
与此同时,为了照顾回乡探亲的华侨和归侨、侨眷日常生活,各地又推出了多种优待照顾措施。如广东省1955年规定侨眷大米供应量每人每月平均不低于24斤,1956年增加到26斤至30斤。广东省人民政府还专项拨出大米2000万斤,油、糖各100万斤,布10万匹,供侨户举办婚丧喜庆的特殊需要。1956年8月中央为了保证对归侨、侨眷的粮油供应,促进侨汇增加,决定当年免调广东省5亿斤粮食;给福建省增加1.5亿斤销售粮指标,同时拨给食油600万斤,批准福建省从华侨建筑费中抽出10%的自备外汇统一进口建筑材料,解决侨汇建筑的需要。
1956年为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之时,各地工商业进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然而对于侨批业的有关指示精神却是,按照更密切国内外侨批业的联系,不降低国内侨批业从业人员的收入,照顾原有股东,尤其是国外股东的利益,提高侨批业积极性的原则,侨批局仍维持私营名义,沿用原牌号,继续分散经营,停征营业税和所得税,其资金一律按私人股金处理。此可谓侨批业受到“特殊”对待之又一显著情形。此外,中央还规定了侨批业的利润分配比例,年终分配以“四马分肥”办法,除提取公积金之外,资方提取75%,职工占25%。这项规定激励了国内侨批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努力开拓业务和加强服务,积极揽收侨汇。
1957年7月30日,根据国务院“关于争取侨汇”的批复指示,各省开始根据侨汇额核发一定比例的物资购销凭证(即侨汇券)给国内收汇人,侨汇券持有者在专门商店或柜台购买紧俏商品或生产物资。对此,廖承志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1957年9月)上系统、明确地重申了归侨侨眷区别于国内一般人民的特殊情况——与海外华侨华人的侨汇联系,要求“充分照顾归侨、侨眷特殊情况,要根据他们的特殊情况制定具体政策,而且要帮助农民群众和干部认识这种特殊情况,且认识到这种特殊情况还将长期存在。”[30]
1957年10月以后,广东全省实行凭侨汇证增加物资供应的办法,开办了专门供应华侨特供商品的华侨商店,华侨可凭侨批封向华侨商店换取侨户购物登记证。1957年11月,福建省也发出《关于凭侨汇收入增加物资供应的通知》。1957年12月,中侨委发布的《关于华侨、侨眷、归侨、归国华侨学生身份的解释》,再次将“侨批员”列为“有华侨身份”者。该解释中关于侨眷身份的认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侨汇为依据的。1959年起,凭侨汇证供应物资的办法在全国推广。
为尽可能地纠正极“左”思想对争取侨汇工作的干扰,自20世纪50年代起几乎在所有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斗争中都会针对海外华侨和归侨侨眷出台相应的保护性政策。如1953年6月至1953年底新解放区土地改革时期,不仅由政务院先后颁布了《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处理办法》《关于土改中处理华侨土地、财产的九点办法》,对华侨地主成份的划定提出了区别对待的规定,严禁以侨汇收入多寡而任意提升和确定侨眷的阶级成份,而且在土改后期就开始着手提前改变华侨地主、富农成份的工作[31]。
新中国初期,在部分利益冲突(如邮费与汇率及物资供应)以及意识形态高压下(如视侨汇为特务费与剥削所得),为了更多地争取侨汇,依然出台了保护侨汇、便利侨汇、吸引华侨华人投资的政策,并且对侨批业做了种种让步,使得民国以来管控、限制、整合侨批业,实现邮政、外汇国有化经营的进程似乎出现了逆转,侨批业的特殊性、华侨华人的特殊作用、侨务工作的特殊地位也随之骤然凸显,形成了堪称世界上最庞大、最完善,也是最独特的侨务系统及其侨务工作[32]。
(二) 20世纪60年代:在意识形态名义下侨批业终成“民退国进”之定局
1960年3月以后,全国统一的侨汇证已下发使用,侨批封上不必再加贴“侨户购物登记证”和加盖购物登记印章,只在发放侨汇证后加盖“已发给物资供应证票”、“侨汇证票已发”等印章,但批款不足5元不发侨汇供应证。
1958年以后,由于过份强调侨务工作要为阶级斗争服务,在“大跃进”运动中,刮起了一股“共产风”、“平调风”,出现了不少侵犯侨户合法权益的现象,加之为缓解1959年以后严重自然灾害导致的生活物资匮乏,国家采取了准许海外华侨华人进口粮食、副食品的临时性措施,引发了1958年之后侨汇的大幅度减少。为了迅速扭转侨汇下降的趋势,1961年中共中央批转了中侨委《关于农村整风运动中对平调归侨、侨眷房屋、家具,侵占侨汇等的处理意见》,并于当年10月发出了《关于争取侨汇问题的紧急指示》。所谓“重点侨乡”的说法也在此期间形成。从1959年到1965年,国家每年都下达争取侨汇的数额指标,广东、福建被要求必须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当年侨汇指标的侨乡就被称为“重点侨乡”。
1962年后,为配合和支持争取侨汇,同样针对海外华侨和归侨侨眷出台了相应的保护性政策。如1962年,中共中央批转了中侨委《关于“海外问题”的报告》《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关于妥善处理侨眷、归国华侨的就业和精简问题的请示报告》,等等[33]。
然而,随着1966年5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所有涉侨的“特殊性”均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国家保护侨汇的政策被攻击为“侨汇挂帅”,凭侨汇票证供应部分商品被说成是“特殊化”,侨汇收入被视为“剥削”、“资产阶级生活”等等,甚至诬蔑侨汇是“特务活动经费”。在侨汇工作上,首先是凭侨汇证供应物资的办法被取消,已发放的侨汇商品供应证宣布作废,一些归侨、侨眷也因而有侨信不敢收,有侨汇不敢领。
1967年,根据中国银行对侨批业进一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采取联合经营的指示精神,中侨委下达了《进一步对侨批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文件([67]206号),侨批业开始实现统一领导、统一核算、统一经营、共负盈亏。侨批业的私营性质不复存在。
1967年下半年,华侨投资公司也停止吸收华侨股金,1969年以后华侨投资公司被撤销,从而使得华侨华人在华投资完全中止,也更加剧了侨汇收入的减少[34]。
为此,1968年1月20日,中侨委给国务院写了《关于处理侨户被查抄财物的请示》,重申:“侨汇是侨户的合法收入,对侨汇所有权和使用权,仍应继续予以保护。对查抄的侨汇(包括侨汇现款、存折、投资于国营华侨投资公司的股票、领取的股息),除属于侨户中的地、富、反、坏、右或其他不法分子的按中央有关规定处理外,其他应一律退还本人。”1968年2月,国务院批转了中侨委的这个请示,保护侨汇的工作在艰难的环境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实。但此时,中侨委自身已成为“文革”的重灾区。1969年6月,中侨委被正式撤销,侨务工作划归外交部,但其行政地位只是领事司下属的一个侨政处。接着,各级侨务部门也相继被撤销,各级侨联组织完全瘫痪。侨批业和全国各行业一样陷于停滞和混乱状态。
(三) 20世纪70年代:侨汇特殊意义的尾声
文化大革命后期,侨汇物资供应逐步恢复。1973年,国务院下达文件(国发1973年53号),指示“侨批业应归口银行”。因各种原因,实际归并工作直至1976年才开始,至20世纪70年代末,广东、福建两省侨批业的业务、人员及财产全部并入中国银行。侨批业作为一个行业由此消失。
1977年9-10月,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出恢复侨务机构,并强调“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35]。1978年1月,国务院侨办设立,性质和职能与过去的中侨委基本相同;4月,全国侨联恢复活动,侨汇物资供应也全面恢复。自此,虽然中国被排除在由欧美主导的世界体系之外已近30年,但始终分布于“世界体系”中的华侨华人被视为中国发展的“独特机遇”,其独特作用之一便是成为中国再度打开国门后应对汹涌的全球化浪潮、迅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一条捷径[36],侨务工作由此进入新中国第二个“兴盛时期”(1978年—20世纪90年代初)。
改革开放以后,物资供应日渐丰富,供应票证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在1980年以后的侨批封上,已不再加盖“已发侨汇商品供应证”、“已发侨汇证”的印章[37]。1980年8月,中国出席了国际贸易组织(ITO)过渡委员会,由此开始了从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长达20年的艰难历程。这不仅“体现了中国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姿态”[38],也是新中国再次通过谈判缔约的形式积极主动融入世界体系的开始*1954—1955年,中国通过谈判缔约的形式宣布放弃“双重国籍”是试图以新的姿态加入世界体系的首次尝试。参见潘鲁生《侨务与外交关系研究——中国放弃“双重国籍”的回顾与反思》,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年,第140页。。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也就在这一年,侨汇券退出历史舞台,侨汇商店以及专门为华侨华人与港澳台同胞进口商品提供服务的机构等陆续关停、改制、并转。华侨华人的特殊作用、侨务工作的特殊地位也随着侨务工作“社会化”的讨论*所谓侨务工作“社会化”,是指随着中国不断扩大开放,社会方方面面都可以开展侨务工作,侨务工作无需再由专门的侨务部门独家垄断。参见王棠编著《侨务春秋》,中国国际出版社,1997年。书中《侨务工作“社会化”的质疑》和《侨务工作“社会化”的再质疑》两篇文章反映了当时这一话题的争论情况。日渐消退。1995年6月,以《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颁布为标志,中国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随之由在闽粤侨乡设立经济特区的“地区倾斜”逐渐向 “产业倾斜”过渡,侨务工作传统的地域性优势也因而不再“一枝独秀”。中国由倚重侨乡(与华侨华人的“海外关系”)转为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与融入“世界体系”及经济全球化。同年7月,中国正式提出加入世贸组织的申请。此后,不只侨批业退出历史舞台、侨批彻底消失,侨汇在对中国侨乡经济、对外贸易中的重要作用也不复再有。
侨批业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生生不息,甚至能跨越新旧两个社会,一直生存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其间,侨批业一方面因与国营邮政业务交叉和利益冲突而屡遭管控、限制、打压、取缔,另一方面又因国营邮政建设需假以时日,以及侨汇为国家贸易、国际收支平衡、侨乡生计维持与发展建设所需而一再获得例外、特许、放宽、优惠等特殊待遇。从中国邮政、金融发展史和侨务政策沿革的角度考察侨批业之于中国近现代邮政及金融的地位与作用,可显见其获“特殊”对待一以贯之,而与政府的更迭、政权的性质并无必然关联。这是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目标的始终如一使然,也是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及其无形而巨大的动能所致,还与华侨华人及其相关行业、事务对于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作用密切相关。
三 中国融入世界体系进程中侨批业“特殊性”的兴衰
根据杜赞奇“国家政权内卷化”*参见〈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6-68页。的概念,“国家政权欲摆脱社会权力的影响,……但它却无法使得自身完全官僚化,以致于只能依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扩大其行政职能,而这又必将阻碍国家政权的真正扩张。”[39]这种二律悖反,决定了侨批业乃至侨务工作在一定时期的特殊作用,也决定了其特殊性的衰退或消亡。对于中国而言,其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塑造或构建,又是与其融入世界体系进程交汇相融的。因而,在认识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思考中,除了华侨华人对中国近现代民族国家构建所作的贡献和发挥的影响之外,他们在中国融入近现代世界体系的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的处境也是值得关注的。侨批业“特殊性”的兴衰,或者说是侨批业的兴盛与衰亡,也与此密切相关。
本文所说“世界体系”,是指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定的国际关系体系,也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近现代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国际关系体系,它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确立了国家主权和平等原则。该体系所确立的建立在主权、平等和领土完整基础上的基本原则至今仍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此后各种国际关系体系的肇始。国际关系体系又往往表现为“条约体系”,即通过缔结双边或多边条约(协定、协议、宣言等),形成不同范围、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政治经济体系。为基础、以全球化为趋势构筑的世界性近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笔者认为,自1648年10月24日欧洲诸国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及1688年底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并于18世纪60年代—19世纪40年代完成工业革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全球化早在古代就开始了,是一个缓慢和复杂的过程,只不过在最近的二三十年里发展迅速。笔者认为,全球化起始虽然可溯源至15世纪末16世纪初,以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标志,但具有实质意义的触发起始于18世纪中后期,以工业革命为标志;因劳动力跨国流动而形成的移民活动,是全球化的重要内在因素和外在表征(全球化的主要内容之一和组成部分,也是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以来,以国家主权至上为原则、以缔结条约为支撑和保证的区域性及世界性近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开始逐步形成;与此同时,以贸易(自然资源、工业产品)、人员(劳动力)、资金、信息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为标志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显现并不断加速。世界体系与全球化是动态的,也是交汇相融的。华侨华人是国际移民大军或跨国流动人员的一支,探讨华侨华人及其相关事项,比如本文所要探讨的侨批业与侨汇,将其纳入世界体系与全球化的语境下,无疑是有助于拓宽视野的。
1869年成立的万国邮政联盟,使邮政事业实现了全球系统化,成为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1914年3月,在历经30余年的努力后,中华邮政加入万国邮政联盟。邮政融入世界体系是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一个方面。万国邮政联盟是中国加入的第一个世界性国际组织,标志着中国成为邮政主权国家[40],通过邮政融入世界体系是中国以国家名义平等、自主、积极主动融入世界体系的实质性开端。华侨华人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先锋,华侨华人在中外往来跨国活动中形成的相关事物或现象,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阶段性产物,或者说是以华侨华人为载体的“西风东渐”的历史性特色。然而,吊诡或悖反的是,国际邮联的规定却正是取缔、限制民信局、侨批局的依据和凭藉。
(一)融入世界体系使得开办邮政、维护与统一国家邮权获得有益支持
融入世界体系,首先要“仿照西法”办事和遵守国际规则。中国近现代邮政的开办,即是如此。1861年,还仅是代理李泰国署理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向掌管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建议依照西法兴办国家邮政,因彼时清政府正疲于剿灭太平天国,对此未予理会。1866年,已任总税务司并将总税务署从上海迁至北京的赫德,在海关下设立邮务办事处,发布邮件封发时刻表和邮寄资费,开始兼办邮政;1878年,赫德在天津等地利用掌控中国海关的权力和便利试办中国邮政;正式创建于1896年的大清邮政实际上是在赫德掌控的海关邮政的基础上开办的,故隶属于海关,且由赫德兼任“总邮政司”。
如前文所述,“仿照西法”也是管控和取缔民信局、侨批局的理由。1899年颁布的《大清邮政民局章程》开篇便指出:“案查欧美各国邮政事宜,统归各国之政府经理。”
加入万国邮政联盟后,万国邮政联盟条例与各国通例被中国援引为统一邮权的合法性依据,对外如此,对内亦然。对外即是迫使列强撤销在华“客邮”。1920年10月,中国首次参加万国邮政联盟大会,即由北洋政府全权代表刘符诚在会上提出撤销“客邮”的要求。1921年,北洋政府外交部正式照会美、英、法、日四国,要求撤销其在华“客邮”,同年11月,在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会议上,中国代表施肇基宣读了中国要求撤销“客邮”的宣言,声明外国在华设置“客邮”是非法的。1922年2月1日,太平洋会议终于通过了限期在1923年1月l日前撤销外国在华“客邮”的议案。此后,各国在华“客邮”,除日本在旅大地区及南满铁路沿线和英国在西藏的邮局外,均在1922年底撤完。
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便旋即开始新一轮取缔民信局、侨批局的努力,其理由同样是“仿照西法”:“邮政为国家专营事业,久为东西各国之通例……按诸邮会各国通例,民间经营递信事业,应在绝对禁止之例。”[41]1933年10月,同样以“邮政为国家专营事业,乃世界各国通例”为由,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再次提出取缔民信局,以实现“统一邮权”。1935年最终取缔民信局后,邮政管理局也使侨批业纳入到国家邮政的实际管理之下,如除要求侨批局到邮政局登记挂号、领取执照外,还借助国际邮政公约,对侨批局在寄递方式、批信和回批的邮资等事项上进行规定与要求,这反映出国家的邮政职能因融入世界体系而得到加强的趋势。
(二)特定历史时期侨批业与中国融入世界体系之悖论
侨批业之重要,首因并非是其替海外华侨华人和国内归侨侨眷传递书信,而是其收揽侨汇、办理汇兑的业务功能。1949年以后,其“特殊性”之显现,也盖因国家倚重于此。
抗日战争时期,因组织、调动各方力量全力抗战的迫切需要,国民政府未有“取缔侨批业”之令。通过各种战时管制,国民政府一方面以全民族抗战为号召,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主导力和控制力,另一方面通过加入世界反法斯同盟这一特殊背景进一步融入世界体系,特别是在国际政治关系方面。换言之,中国在战争背景下进一步融入世界体系的客观结果,是“国进民退”的继续乃至强化。这在侨汇业务方面的表现,便是国家邮政和金融机构已悄然形成绝对优势。然而,随着战争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东兴汇路”的开辟既显示出侨批业自发、原始、极富冒险精神的顽强生命力,又成为保持中国与世界体系联系的活跃渠道与有力支持。“东兴汇路”开辟后,大量侨批流经东兴市场,银行、钱庄等金融机构及从事各种经营和服务的商铺店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此期间,广东省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以及民营的光裕银行、华侨联合银行等金融机构纷纷在东兴设立办事处,大力发展侨汇业务。虽仅历时三年半时间,但战时跨国金融枢纽的地位,使得东兴被冠以了广西“小香港”之称。
新中国成立后,因“冷战”格局及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陷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包围与制裁,融入世界体系的进程停滞不前。虽然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发展方面可以依靠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但是随着中苏关系很快出现裂痕,中国的国际处境更为不利。而为了保证国家建设和正常推进经济发展,又必须有正常的对外贸易和金融业务,即必须借助国际贸易体系和金融体系。在被封锁和陷入孤立的情况下,中国再次借助和倚重华侨华人作为与世界体系保持联系与交往的渠道之一,侨汇上升为国家外汇的主要来源,侨批业为国护“侨”模式再启。争取外汇的特殊重要性,使得侨批业“特殊性”再现且被强化,其“民退国进”的趋势神奇地止步于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化巨变中。
侨务部门是当时少数拥有对外联系渠道的政府机构,争取侨汇的重要职能使得新中国侨务政策在与意识形态激烈冲突的情形下被赋予了“适当照顾”的特殊性,也使得新中国侨务工作特殊地位具有了现实合理性。对于通过华侨华人接洽国际贸易体系和金融体系的倚重,使中侨委得以会同有关部门多次出台了决定侨务工作在中国特殊地位(华侨华人在中国特殊性)的侨务政策——特别是以争取侨汇为目的的政策。还值得一提的是,除通过侨批业和吸引华侨投资*1957年8月,国务院公布了《华侨投资于国营华侨投资公司的优待办法》。争取侨汇外,新中国还于1957年春创办了“广交会”,即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创办“广交会”的目的,也是为了通过出口创汇,冲破欧美国家的制裁和封锁,为新中国开辟出一条对外交往的通道。在改革开放之前,参加广交会的贸易洽谈商主要也是华侨商人和港澳同胞*如据陈云纪念馆陈列的《国内动态清样》(1973年11月27日,第593号),当年参加秋季广交会的商人共有13,641人次,其中港澳同胞、华侨商人达8463人次,占62%。。所有这些都使得侨务工作在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出现了第一个兴盛时期,然而侨批业却几乎是在侨务工作迎来第二个兴盛期(改革开放至20世90年代初期)的前夕最终消亡,其个中缘由和揭示的问题——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及其对于中国的意义耐人寻味。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朝鲜战争结束未几,中国便试图通过与印尼谈判、签订《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以一种新的姿态融入并改造世界体系。但颇具悖论意味的是,此举同样是以华侨华人及相关事务为切入口。中国通过该条约宣布放弃自清末以来一直奉行的双重国籍政策,要求侨务工作服从和配合外交工作的大局,此后由支持华侨华人“落叶归根”转变为引导华侨华人“落地生根”。由于此时距新中国建国不足5年,此举与新中国“欢迎华侨回国定居”口号的反差太大,因而一时难以被接受,甚至被认为是急于把华侨“推出去”的激进之举,使华侨为中国外交局面的打开付出了“太大的代价”[42]。此举虽然因为当时中国内政与外交的诸多因素并未能得以落实和推进,但确实反映了新中国外交战略与策略的重大调整意图,更是新中国以一种新的姿态重启融入世界进程的开始[43]。这种新的姿态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表达,以及对于世界体系中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诉求。
总体而言,中国融入世界体系势头强劲之时,也是侨批业实际上处于“民退国进”的境遇之际。反之,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进程受阻时,则侨批业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呈活跃之势,与华侨华人相关的其他事务一样,成为维系和保持中国与世界体系之联系的涓涓细流。
(三)中国融入世界体系“新征程”的开启与侨批业的终结
中国“朝贡体系”不断瓦解、由封建王朝向近现代国家艰难转型的过程中,也即“世界体系”西风东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华侨华人作为中国走向世界、参与全球化的践行者,是领略西风欧雨的先行者,是中国构建现代国家的助推力量,也是后来中国获得“后发优势”的示范和先导。华侨华人作为沟通与联结中外的桥梁和纽带,成为中国借以融入“世界体系”的一条捷径,因而对于中国近现代化具有特殊意义。侨批业反映了华侨华人走出国门后与侨乡社会以及中国经济的基本联系,是凸显这一特殊意义的最主要例证。
然而,华侨华人与侨务工作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往往凸显于国门乍开仍闭之际,一旦中国全面开放,或所谓全方位与国际接轨,融入始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由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这一特殊意义便会消退乃至不复存在。侨批业之彻底消失,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其国际背景正是中国加入联合国并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和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侨批业的消失预示着中国融入世界体系进程的重启。
正因如此,1972年以后,虽然极“左”路线盛行,侨批业也被正式纳入到国有银行之中,但寄到中国大陆的侨汇却逐年增加,并在1980年前后达到顶峰。这一阶段侨汇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原因显然与中国融入世界体系进程的重启密切相关,中国加入联合国并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意味着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和封锁逐步取消,也强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外交局面的打开,特别是东南亚华侨华人众多的国家陆续与中国建交。
同样可以作为中国全面开放与侨批业终结之间关联性佐证的是,1979年以后由于回乡和出国探亲和旅游观光的华侨、侨眷逐年增多,有不少侨汇被出入境人员直接带入,不通过中国银行汇入;同时,“以物代汇”*即华侨及港澳台同胞携带家用电器与衣物等回大陆。、“以单代汇”*即华侨及港澳台同胞在国外或香港买货,凭单报海关后在内地取货。的现象也剧增;1981年以后在侨乡及国内大中城市炒买炒卖外汇的现象也水涨船高,黑市外币兑换价比国家银行外汇牌价要高得多。因此,通过中国银行汇入的侨汇大幅度减少。1979年至1989年,国家侨汇年收入由近7亿美元逐年下降到约8000万美元*实际上,由于自带侨汇、“以物代汇”、“以单代汇”现象的大量增多,表面上看是侨汇收入减少了,但从国家外汇收入总额来看却是大大增加了。参见孙仪《侨务知识讲座》,内部编印,1989年12月,第284-285页。。尽管侨批业归并银行之后,中国仍制定了一系列新的侨汇政策与措施[44],1978年恢复了对侨汇实行发放侨汇物资供应券的政策,1982年3月国务院还曾下发《关于做好侨汇工作扭转侨汇下降的通知》,但侨务工作的重心还是逐渐为目标更高远的招商引资政策所取代——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但侨务工作“社会化”的议题也开始沸沸扬扬。1995年,中国颁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随之由在闽粤侨乡设立经济特区的“地区倾斜”逐渐向 “产业倾斜”过渡,侨务工作传统的地域性优势也因而不再“一枝独秀”。中国加入WTO后,计划经济体制进一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入转变,中国出台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物权法》和《劳动合同法》等一系列对深化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有着重大社会影响的法律。特别是2007年3月16日,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在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获得通过。该法规定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所得税制实行并轨,进一步终结了被认为是经济特区的“最后一项优惠政策”,即对外商投资给予的税收优惠。
从中国融入世界体系进程的角度来考察,上述法律规章均呈现出与WTO所要求的“国民待遇”原则趋同的特征,也就是不断限制和取消保护性(即特殊优惠)或歧视性政策,从原来的“内外有别”逐步趋于“内外一致”。然而,这一变化却是与侨务工作在中国以“与外有别”,且“与内有别”的“特殊性”为依据和特征的历史地位及现实需求相抵触和冲突的。所谓“与外有别”,最突出的工作理念便是“华人不同于一般的外国人”。而《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则是侨务工作关于华侨华人及其相关事务“与内有别”主张的集中反映。
随着中国融入世界体系进程的深入,吸引、争取侨汇的理念先是被以华侨华人为媒介和示范的招商引资所取代,而后招商引资又为更进一步的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口号的与国际接轨,以及参与“游戏规则”制定的目标所取代。
综上所述,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及中美关系正常化,已经预示着中国全面改革开放进程的启动。加入或在一系列国际组织中恢复地位,即意味着与“国际接轨”,意味着相应权利与义务的分享,意味着需要遵守有关国际条约、公约、协定、规章,等等,因而,融入世界体系的进程实际上也是国内事务改革的一种“倒逼”机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进程便是最充分的例证。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近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或塑造)与融入世界体系的进程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体两面。中国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塑造或构建决定了侨批业特殊性的形成与侨批业的兴盛,中国融入世界体系之广度和深度则决定了侨批业特殊性的衰退和侨批业的消亡。正因如此,华侨华人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其相关行业的特殊作用、侨务工作的特殊地位,都是凸显于中国国门乍开还闭之际,亦即融入世界体系进程的起步阶段。
结语
中国被动卷入由工业革命触发的经济全球化以及由《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肇始的近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不得不向着现代民族国家的方向转型和发展,并在积极融入这一世界体系的同时,维护和追求大国地位、力争话语权重和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这一发展方向,自清末以来就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无论是新旧政权的更迭、政权阶级属性的变化,还是国家外部环境的良好与否,都未改变这一趋势。当然,其间发展进程有过不同程度的曲折反复。就本文的论述而言,侨批业的“特殊性”是探讨华侨华人在中国近现代进程中所扮演角色及其境遇的最典型例证。
纵观民信局、侨批局与国营邮政、国有银行的关系,其中既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深刻揭示了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及其无形而巨大的动能,也反映出在融入世界体系的进程中华侨华人对于中国近现代化具有的特殊意义。本文认为,侨批业是中国近现代金融与邮政的开拓与奠基者之一,折射出中国近现代邮政业、金融业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中国通过这两个行业构建现代国家、融入世界体系的进程。
由于侨批与侨汇并非一个概念,侨批局与侨批业也不可等量齐观,因而侨汇与侨批局、侨批业折射出的是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各种不同关系。侨汇作为一种可靠的“非贸易国际收入”是国家建设所需,对国家经济是有益的;侨批局、侨批业与国家则既互惠互补,又有利益冲突,既合作互助,又有竞争对峙。侨批首先惠及的是个体(侨眷)与群体(华侨华人的家庭与家族)的关系,兼利地方(侨乡)与国家;侨汇主要惠及的是国家外贸收支的平衡,意味着反映国家大一统体制的专业化管理水平。侨批业“国进民退”是国家统一、主权宣示之必需,其过程反映了国家邮权的扩张,也是国家行政一体化加强的体现。
民信局、侨批局的终结之势始于晚清中国近现代邮政体系的建立。经过北洋政府的短暂过渡,并在积聚了一定基础和实力后,国民政府最终取缔了民信局,同时将侨批局纳入到邮政监管体系中。取缔侨批业的趋势因抗日战争而中断,侨批业又因新中国的建立而一度“中兴”。“根据查尔斯·蒂利的界定,所谓(民族)国家政权建设就是一个国家试图拓展、强化其控制的过程。”“尽管(新中国)采用了(对旧政权)否定的方式,它的最基本之处仍坚实地继承了自己的历史。中国又终于‘作为中国’得到了新生。”“换言之,它不仅要继承清朝的版图,而且也要继承清末以来诸政权建设民族国家的历史经验。”[45]尽管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侨批业采取了保留、宽容的态度,华侨华人以及侨务工作也被赋予了相应的“特殊性”,但新中国终究还是继承了近代以来将侨批业收归国营的目标,并最终实现了这一目标。
侨批业的发展历程,既“从一个侧面深刻地反映了近代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嬗变”[46],是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博弈与较量,也是中国融入世界体系进程的表象与映证。侨批业兴于华侨华人为代表的社会力量通过海洋贸易、跨境流动等方式自发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肇始,随着中国以独立民族国家身份自主加入,乃至积极追求融入世界体系的进程而终于消亡。
以服务和处理华侨华人及其相关事务为职能的侨务工作是近代以来中国外交的晴雨表之一。国际环境不利、外交处于困顿弱势时,侨务的重要性和地位往往凸显;而外交因国际机遇而活跃时,侨务便退居其次而无所谓“特殊性”、“敏感性”可言。晚清以来,就中国侨务与外交的关系而言,如果说《大清国籍条例》是中国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在以欧美列强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中被动而又积极维护大国地位的开始,那么1954年新中国宣布放弃“双重国籍”的决断,则是中国在国际政治方面主动且独立自主地加入该体系的重要举措和具有深远意义的尝试。20世纪70年代初,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合法席位及中美关系正常化为标志,中国开始了以国家身份真正、全面地融入这一世界体系的新征程。曾经在新中国侨务工作中占有特殊重要性的侨批业之终结正是这一背景的产物。其后,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以及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是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新的重大里程碑,使华侨华人及其相关事务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进一步消退。
侨乡之所以成为侨乡,一定是因为有侨汇;而且,一定是在国门开合之际,侨乡的地位、作用、特色与氛围才凸显。晚清如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如此,改革开放初期同样如此。比如我们说,正是在晚清中国被西方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之际,华侨的概念才日益明晰,侨乡的风貌才日渐成型;正是在1978年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之际,侨务工作再次受到重视,华侨华人再次活跃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现在纵然海外华侨华人人数已增至6000余万,然而,无论是侨乡的特色,还是华侨华人的独特作用,抑或侨务工作的特殊性,还是侨务政策的倾斜照顾,均未见有与此规模增长相适应的与时俱进。此不仅是因为华侨华人及其相关事务对于中国“特殊”意义的终结,也是中国融入世界体系之愈来愈全面和深入使然。
近代以来华侨华人及其相关事务在许多方面是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先导和示范,他们所形成的跨国优势、网络组织以及经济实力还成为中国借以融入世界体系、实现“后发优势”的捷径,即邓小平所说的“独特机遇”论。但吊诡和悖反的是,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广度越大、程度越深,华侨华人及其相关事务的特殊地位与突出作用反而愈益消退!这是本文特别给予关注的。同时,本文还想特别指出的是,在华侨华人及其相关事务被赋予以特殊意义的历史背景下,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其实至少有三种情形:一是华侨华人对中国的贡献与支持,二是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合作和互利,三是华侨华人与中国的矛盾和冲突。这三种情形都是值得深入考察和研究的。此外,还需引起注意的是,侨批业是基于市场经济萌发的自然产物,在欧美对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仍有异议的当下,正如曾为福建省副省长,时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的刘明康所说,国内侨批业虽然被取消了,但这一特殊金融组织的一些经营特点、经营方法和经营手段,对今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金融体系仍然有许多可借鉴之处[47]。
时光荏苒,星移斗转。原先作为近代工商业文明和民族国家重要标志与支撑的邮政业、金融业,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在当下又出现了与时俱进的某种轮回:国营邮政业务日渐萎缩,与“巡城马”*在广府和四邑一带,负责侨批在国内递送业务及收取“回批”的水客,被称为“巡城马”或“巡马”。参见林家劲等:《近代广东侨汇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页。相仿的“快递员”重现于异军突起、方兴未艾的快递业中;地下钱庄时隐时现地活跃于以“新侨乡”著称的浙、闽两地,成为外汇、金融市场上不可小觑的汩汩暗流。因而,虽然侨批已成为世界记忆遗产,但对于涉侨文博界和华侨华人研究而言,应加大对侨批收藏、保护、展示及文创开发的力度,在深化和拓展国际移民书信和爱国爱乡、亲情族谊或侨批业自身的历史发展、经营情况等的研究之外,还应更好地审视其与当下的历史关联,并思考其对于未来的借鉴意义。
【注释】
[1] 参见程希《华侨华人:作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及其与中国的关系》,《东南亚研究》2005年第1期。
[2] 冯元:《略论解放前广东省华侨汇款》,《侨史学报》1987年第1期。
[3] 林金枝、庄为玑:《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福建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页。
[4] 目前发现最后的侨批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参见《侨批既是家书又是汇款单》,http://fujian.hexun. com/2012-12-04/148654779.html;福建省档案馆编《中国侨批与世界记忆遗产》,“前言”,鹭江出版社,2014年,第1页。
[5] 马承玉:《广东侨批研究》,湖北集邮网“文章中心”,2006年11月29日,http://www.hbjy88.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4615
[6] 潭江:《侨批业的兴衰》,《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10月20日。
[7] 参见1951年3月1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公布的《侨汇业管理暂行办法》。
[8][39][45] 魏磊杰:《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何以可能——评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2016年2月16日,http://www.aisixiang. com/data/97129-3.html
[9][10] 邮电史编辑室:《中国近代邮电史》,人民邮电出版社,1984年,第34页。
[11] 仇润喜主编《天津邮政史料》(第一辑),北京航空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87页。
[12][13]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邮政》(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之八),中华书局,1983年,第87页,第121页。
[14][24] 吴宝国:《侨批与金融》,2008年2月1日,http://fw.hqcr. com/html/139/200802011458371495.html
[15] 邹金盛:《潮帮批信局》,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2000年,第43、50页。
[16] 袁丁、陈丽园、钟运荣:《民国政府对侨汇的管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4页。
[17] 袁丁、陈丽园、钟运荣:《民国政府对侨汇的管制》,第54页。
[18] 袁丁、陈丽园、钟运荣:《民国政府对侨汇的管制》,第8页。
[19] 袁丁、陈丽园、钟运荣:《民国政府对侨汇的管制》,第17页。
[20] 当然,也有一些侨批局因无法合法注册而被迫转入地下。参见袁丁、陈丽园、钟运荣《民国政府对侨汇的管制》,第198页。
[21] 姚曾荫:《广东省的华侨汇款》,商务印书馆,1943年,第26页。
[22] 袁丁、陈丽园、钟运荣:《民国政府对侨汇的管制》,第113页。
[23] 袁丁、陈丽园、钟运荣:《民国政府对侨汇的管制》,第70页,
[25] 梅州地方志编委会编《梅州市金融志》,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32页。
[26] 袁丁、陈丽园、钟运荣:《民国政府对侨汇的管制》,第73页、79页、91页。
[27] 袁丁、陈丽园、钟运荣:《民国政府对侨汇的管制》,第86页。
[28] 《国民政府战时经济政策》,http://www.cq. xinhuanet.com/subject/2005/2005-07/28/content_4747049.htm
[29] 柯木林:《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研究(1945-49)》,http://www.87994.com/read/06d78684881679221b48d982.html
[30][33] 毛起雄、林晓东编著《中国侨务政策概述》,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第81页,第87-98页。
[31] 这一时期相关侨务政策参见毛起雄、林晓乐编著《中国侨务政策概述》,第66-86页。
[32][42][43] 程希:《侨务与外交关系研究——中国放弃“双重国籍”的回顾与反思》,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年,第9页,第130页,第140页。
[34] 王永魁、王占刚:《“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中侨委》,《百年潮》2015年第8期。
[35]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论侨务》,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6页。
[36] 龙登高:《海外华商经营管理探微》,香港社会科学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225页。
[37] 蔡焕钦:《侨批见证国家的侨汇物资供应政策》,2008年2月1日,http://fw.hqcr.com/html/139/20080201
1443576481.html
[38] 石广生:《中国“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谈判回顾》,《百年潮》2009年第7期。
[40] 程兵:《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原委研究》,《中国邮政报》2009年9月9日。
[41] 袁丁、陈丽园、钟运荣:《民国政府对侨汇的管制》,第40页。
[44]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政策研究室编《侨务法规文件汇编》,内部编印,1989年8月,第349-373页。
[46] 袁丁、陈丽园、钟运荣:《民国政府对侨汇的管制》,第7页。
[47] 中国银行泉州分行行史编委会编《泉州侨批业史料》,“序言”,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
【责任编辑:邓仕超】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China:Perspective of the Overseas Remittance
Cheng Xi
(Desect1ment of Research and Communication,the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Museum of China, Beijing 100007, China)
Overseas Remittance; Overseas Chinese; China; Remittance House; Overseas Chinese Postal Agencies
When Qiaopi (the overseas remittance by private remittance houses or postal agencies) tried to declare the Memory of the World Register and succeeded on Jun. 2013, more and more people get to understand and cognize the special value of the overseas remittance and its world significance as human cultural heritage. Moreover, the rescue, protection and research of the overseas remittance are promoted actively. The business of overseas Chinese postal agencies and ShuiKe, which bear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collection, transferring, delivery, exchanging and pay, and have both functions of finance and post (especially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post), however, haven’t received:more attention. Especially their development track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PRC is rarely discussed academically or summarized. Along with the heritages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postal agencies dilapidating constantly and being converted to commercial use, they face the dilemma of being forgotten quickly and thoroughly. This year is the 120 anniversary of China post office, and this thesis tries to investigate and reveal the special status and function in near modern post and finance’s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business of overseas Chinese postal agencies and ShuiK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s transformation, effort to build a modern state and integrate into the world system. Then the thesis try to help cogn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China , as well as its significance to China deeply.
2016-05-25
程希,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研究与交流部主任,研究员。
D634A
1008-6099(2016)04-008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