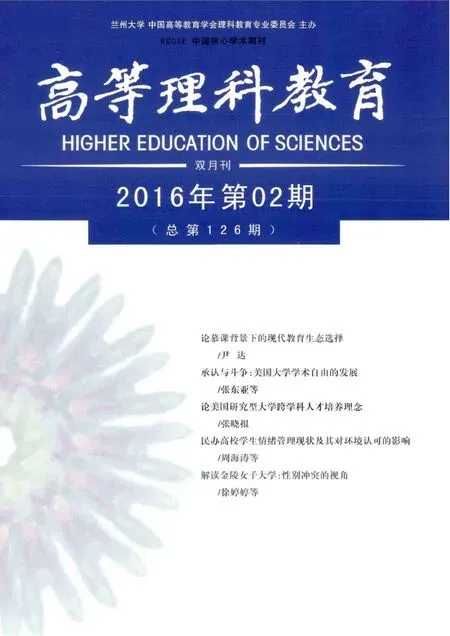承认与斗争:美国大学学术自由的发展*
张东亚 陈何芳
(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承认与斗争:美国大学学术自由的发展*
张东亚陈何芳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摘要权利和自由的获得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过程,大学的学术自由更是如此。借鉴阿克塞尔·霍耐特从“主体为承认而斗争”的发生过程建构的承认理论,文章分析了美国学者学术自由意识“从认知自我关系到实践自我关系”的转化过程和学者斗争主体从“个体到集体”的扩展过程。以此,文章阐释了美国大学学术自由的发展,并论证了美国学者的学术自由权利经历了个体和集体的不断抗争才在社会发展的某个阶段得到社会共同体的承认。
关键词承认理论;学术自由;罗斯事件;集体斗争
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生命之根[1],也是现代西方大学制度的理念支撑。由于大学高深学问性质的影响,可以说,大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追求学术自由的基因。而自由亦是上帝赋予人类的权利,但却很少有人能先天性拥有这种权利,因为权利的获得总是有前提的。在一定意义上,权利是具有遗传属性的,会在社会群体中的不同阶层进行阶层内部的代际承转,从这个意义上讲,权利是固化的,可以从上一个时期传承到下一个时期。同时,权利又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在权利主体的斗争或沉默下不断地扩展或萎缩。
作为大学经久不衰的灵魂,学术自由在思想领域从未褪色,是无数学者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口耳相传的精神道统,但亦如罗伯特·尤里斯教授翻译雅斯贝尔斯《大学之理念》时的叹息:“我们有时都对自己的能力丧失信心,觉得没有办法把高等教育的那些超越单纯功利目的的价值理念告诉一年年多起来的大学生,甚至没有办法告诉我们的同事。我们感到困惑,对于创造性学术研究来说是先决条件的沉思的美德,我们究竟给它留有多大的空间”[2]。由此可见,思想理念的实践转化是多么的艰难。虽然罗伯特教授感知精神传承之艰难,但毅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把《大学之理念》翻译成了英文,使此书能为广大学人熟知。
学者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与抗争使我们了解到,学术自由从理念层面到实践层面的转化和学术自由权利的获得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过程。现代大学的发展建立在学术自由的权利之上,而这种权利却没有那么容易地被承认,它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学术自由权利的获得是不断的斗争与承认的过程,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那么,学术自由是如何实现从理念领域到实践领域转变的呢?又是如何在实践领域逐渐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的呢?本文截取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段时期的学术自由发展状况,力图以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回答上述的问题。
一、霍耐特关于承认理论的建构
法兰克福学派阿克塞尔·霍耐特在他的专著——《为承认而斗争: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中系统地阐释了其社会承认理论,为再理解人类社会的变革和社会冲突的根源提供了崭新的视角。霍耐特针对“为承认而斗争”的核心命题,吸收耶拿时期黑格尔的承认理论模式,结合米德的社会心理学资源,再现社会承认关系结构以解释社会变革的过程。在社会互动领域3种区分的方法论下,霍耐特联系社会一体化的3种承认模式:爱、法律、团结,就个人同一性机制论述了“蔑视”这一被拒绝承认的经验是如何为“为承认而斗争”提供动力的,从而实现了其承认理论的基本架构。
霍耐特继承和发展了黑格尔“为承认而斗争”的原始模式,使之与具有规范内容的社会理论相联系。在黑格尔的早期承认学说中,不同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政治理论家认为的社会发展动力是个体原子式的对立斗争以及在原子论基础建立的社会契约的观点,黑格尔认为社会的动力源于主体间的社会关系的生成和扩展。黑格尔指出,“主体之间为相互承认而进行的斗争产生了一种社会的内在压力,有助于建立一种保障自由的实践政治制度。个体要求其认同在主体之间得到承认,从一开始就作为一种道德紧张关系扎根在社会生活之中,并且超越了现有的一切社会进步制度标准,不断冲突和不断否定,渐渐地通向一种自由交往的境界。”[3]9霍耐特重新解读黑格尔的理论模式,提出黑格尔的理论模式开始于这样一个命题:实践自我的形成依靠的是主体间的相互承认。在此命题下,黑格尔断言存在不同形式的相互承认,而不同的承认形式遵循着以道德斗争各阶段为中介的发展逻辑。按照这一命题,主体在形成认同的过程中,在其要求得到共同体承认的时候,主体就先验性的被要求进入主体间冲突,结果是,共同体满足了主体在先前交往中没有被肯定的承认要求。这样就进入黑格尔命题的两个强有力的断言:第一,成功的自我发展假设了一系列相互承认的形式;第二,主体经验到蔑视而意识到没有被承认,从而投身到“为承认而斗争”之中[3]73。也就是说,自我的发展是承认关系的生成,而因没有得到承认的蔑视经验则会使自我重新投身到“为承认而斗争”的形式之中,直到个体在共同体中获得承认。“一个主体自我认识到在主体的能力和品质方面必须为另一个主体所承认,从而与他人达成和解;同时也认识到了自身认同中的特殊性,从而再次与特殊的他者形成对立。”[3]22通过这种方式,黑格尔成功地把个体的社会活动纳入为承认而斗争的理论模式之中。
霍耐特认为黑格尔在唯心哲学逻辑中论述的承认理论已不再适用于当今的学术语境,他引入社会心理学家米德关于认识自我关系和实践自我关系的主体间性条件研究,创造性地实现了对黑格尔承认理论的自然主义转化。米德通过“客我”和“主我”的概念区分来回答认识的自我关系,即:主体是如何获得其行为的社会意义?[3]79米德认为,只有当主体能在自己身上产生与其在他者身上产生相同的刺激行为反应时,主体才能经验其行为在主体间的意义,而仅有主体获得其行为的社会意义时,主体才具有真正的自我意识。由此米德指出,主体的完整自我,包含“客我”和“主我”,前者反映他者眼中自我的形象;而后者则代表了自我未受制约的原动力。在米德看来,“只有在学会了从符号意义上再现的第二人称视角来认识他自己的行为,主体才能获得一种自我意识。”[3]81表明主体自我意识的获得是建立在“客我”存在的心理机制之上,意思是说当个体在主体间发生对自我行为的认知时,是“客我”使主体认识了自己的形象。“客我”与“主我”两者并存于主体之中,构成主体认识自我关系形成的内部对话机制。
而黑格尔承认理论的“承认”概念清晰地反映了黑格尔关注的是实践自我关系形成的主体间性条件。当然,认识自我关系的发展作为一种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只有以此为基础,实践自我关系才有可能成功地建构。而米德对自我意识理论的道德—实践同一性的转换使其理论具备了把黑格尔承认理论的内核自然主义化的资格。霍耐特这样解释米德对同一性的重构:心理力量注入承认运动,从而使得其内在动力变得可以理解。一旦主体把道德的规范方面整合到互动关系的规则中,处在互动伙伴地位上的主体努力影响自己的行为反应来应对个人环境的规范期待;因此,从第二人称的角度,主体所转向的“客我”不再代表在认识上解决难题的中立机制,而是体现一种主体间必须解决的道德冲突机制。而当社会反映延伸至涵盖规范行为语境时,“客我”就从个人特有的认识自我关系转化为实践的自我关系。“在认识的自我关系中,‘自我’对立于作为一种无意识力量的‘客我’;‘客我’内涵着个体控制自己行为并使其与社会期待相一致的行为规范,而‘主我’则外显为对社会挑战作出反应的一切内在冲动的汇集”[3]87。这使个体永远地感觉到内在的本能压力,感觉到自身与社会环境的承认规范互不相容。毫无疑问,这种带有蔑视意味的不相容是促成自我关系从认知到实践转化的重要心理因素。
在黑格尔天才般创造的构想与米德社会心理学理论的基础上,霍耐特发展这样一种社会理论:“社会生活的再生产服从于相互承认的律令,因为只有当主体学会从互动伙伴的规范视角把自己看做是社会的接受者时,他们才能确立一种实践自我关系。在这样一种实践的自我关系中,个体逐步地解除施加在相互承认意义上的束缚,在社会中表达不断扩展的主体性要求。在这个意义上,个体化的类历史过程就离不开相互承认关系不断扩展这样一个前提。但是,只有把这种发展架设再次与社会生产的过程中的事件联系起来,它才能成为社会理论的基石。正是社会群体的道德斗争,即他们集体的努力,才有助于在制度上和文化上建立起新的相互承认形式,因此,社会变革在规范意义上才成为可能”[3]101。这也是本文的出发点,尝试从霍耐特社会理论的视角解释美国大学学术自由发展的过程,试图论证美国大学学术自由的发展是学者和学者团体与社会其他参与者之间相互承认关系的不断扩展过程。
二、学者的自我意识:从认知到实践
(一)认知自我关系的形成
作为一种权利,学术自由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恩赐的,而是通过个体的斗争获得的[4]。同时,任何权利的争取必需基于权利自我意识的觉醒,这意味着权利的主体必需首先充分地认识自我。只有在主体认识到自我内涵自由的权利,并在与他者的交往过程中认识到主体需要实现成功的自我发展,为承认而斗争才具备现实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只有学者达成自我关系的认知,他才有可能转入实践自我的斗争。所以,探求美国学术自由的发展,需从学者自我关系的认知开始。
学术自由概念的提出要得益于19世纪初洪堡创建柏林大学所做的努力。1809年,洪堡在创建柏林大学时,明确提出大学教授享有学术自由和教学自由,学术自由的概念第一次在其概念内涵之上有明确的指向。虽然这种自由在概念上略显宽泛,包含学术研究、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而且这种学术自由也只是局限于大学的课程和实验室,但这无疑是学者学术自由权利意识觉醒的初鸣。随着柏林大学的成功,洪堡的学术自由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其中,自由是大学必须的,同时也是国家必须的[5],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美国是德国大学思想主要输入国之一,在19世纪,在德国大学学习进修的美国学生将近一万人,通过这些学生,通过书籍介绍的德国大学的情况使德国大学的教学思想和方法被介绍到了美国。德国大学对美国学术自由思想的主要贡献,就是使美国的大学跳出美国大学建立初期学术中科学与宗教的争论,使大学具有了学术自由以及学术研究的理念,这个简单但非常重要的思想与美国学术思想紧密相连,成为美国大学的核心理念。在美国旧学院体制时代,教会代表信仰、大学代表理性,它们之间天然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6]。在这种紧张关系下,沃特·梅兹格对美国旧学院体制下教育理念的描述:“19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学院以传统为中心,依靠远古的思维方法,视基督教的信条为生活的准则。学院强化知识对心智的训练,但限制知识的探索”[7]3。“学院根本不存在没有宗教信仰的校长,校长必须反映他所属教派的教义并为之服务”[7]24。“只有知识的保存是学院最重要的理想,学术自由就只能是为学院而存在的自由,而不是在学院中的自由”[7]46和查尔斯·艾略特在他1869年的就职演说:“一所大学应该是本土的和资金雄厚的,最重要的是,它应该是自由的。自由的微风应该吹到校园的各个角落。自由的飓风能扫走一切阴霾,理智自由的风味是文学和科学赖以生存的空气。大学要立志服务于国家,培训学生诚实道德品质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学校必须要求所有教师严肃、虔诚和高尚,同时学校给予教师自由,像给予他们学生的自由一样”[7]86可以清晰地看出德国学术自由思想输入后美国学者关于学术自由认知的转变。
以米德个体的“主我”和“客我”的区分,我们尝试这样看待美国学者自我意识的生成:作为一个个体,美国大学学术自由思想的“客我”照见德国的学术思想从而使美国学术思想认识了自我形象。这种自我形象既包含了美国学者对“客我”——德国学术自由内涵的新认知,又包括了美国学者对“主我”——美国大学学术自由的内容。两者构成美国学者关于学术自由问题的内部对话机制,这种对话主要表现为美国学者“主我”对于其所照见的“客我”(德国学术自由)的应答。用米德的话即:“客我从社会客体领域输入到所谓内在经验的无形体和无组织领域中的东西。通过对这一客体即自我的组织,这一物质本身也得以组织,并纳入到具有意识形式的个体控制之中。”[3]81-82用梅兹格的话说就是:“美国从德国那里选择了那些符合其需要、并且与其历史协调一致的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德国强大的学术影响与其说是开创了美国本土改革的趋势,倒不如说是促进了这种趋势。”[7]136德国学术思想的影响使美国学者重新建构了自己对学术自由的认知,形成了新的认知:学术自由是学者的权利,它不应该受到其他社会力量的阻碍。
(二)实践自我关系的转入
经过德国学术自由思想的影响,美国学者的学术自由意识已然觉醒。美国学者内心深处,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主我”期待着实现学者研究自由和教学自由的权利,并期望这种权利能获得社会共同体的承认。“主我”期待实现“客我”要求上的权利,“主我”对社会环境的扩大权利要求构成社会冲突结构的一端。这种要求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如此的不相容,以致在社会经验的层面,我们发现社会集体意志对个体“主我”要求的蔑视。正是由于这种蔑视,主体失去其个体同一性和在主体间获得进一步承认的资格。承认与蔑视或者说学者扩大权利的诉求与社会集体意志之间形成的冲突结构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大学生活中的典型特征,这种内在矛盾的关系结构直接催发了19世纪末一系列的学术自由事件。学术自由事件是这种冲突结构在社会活动层面的具体体现,这种冲突结构引发了不和谐状态:社会集体意志的蔑视与学者个人诉求之间的张力在社会活动层面表现得越来越显性,使学者从认知的自我关系开始转向实践的自我关系。
在这一时期的学术自由事件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提倡教师学术自由的哈佛校长查尔斯·艾略特,他在一起学术自由事件中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在其任职的早期,他曾经让一位教授在他将要出版的著作中放弃批评波士顿商人的观点或者从扉页中删除任何提及他与哈佛关系的字眼。在思想领域凯旋高歌的学术自由在实践领域却遭遇完全相悖的规范:即大学董事会拥有随意雇佣和解雇任何人的权力。董事会对学者自由权利的剥夺,使学者认识到自己是“被蔑视”的主体、是没有得到认同的个体。被蔑视的道德经验催生了学者为自己权利得到承认而抗争。具有典型意义和重大影响的是“罗斯事件”:在1900年,斯坦福经济学教授罗斯因其银本位和亚洲移民问题的观点,被斯坦福大学解雇。根据捐资者创建斯坦福大学的有关规定,完全由创建者行使董事会的权利。斯坦福大学是由一位修筑铁路而发家的共和党人创建的,他主要是依靠自由劳工贸易发家致富。1893年,斯坦福的创建者利兰·斯坦福去世。之后,他的妻子接替并履行全部职责。罗斯教授提倡市政当局拥有公共设施权,禁止亚洲移民;并在大多数经济学家支持共和党人麦金利和提倡金本位思想时,撰文支持民主党所提倡的自由银币本位思想。斯坦福夫人在了解到罗斯教授的思想之后写信给乔丹校长说:“罗斯教授离开自己的专业领域,去结交政客,夸大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从而给社会主义团伙以可乘之机,这让我痛心流泪。我必须承认我讨厌罗斯教授,我认为他不应该再留在斯坦福大学。”[7]107几年来,乔丹校长为了有过错的教师的利益不断与斯坦福夫人进行调解。他坚持认为罗斯的学术研究很出色,课堂教学很明智,个人生活也无可指责。同时,他要求罗斯尽量克制,并把罗斯从经济系调到社会系。所有努力都是枉然,斯坦福夫人坚持自己的看法,而在乔丹校长看来,大学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相对于大学的其他价值,大学的生存价值更重要。于是,1900年,罗斯教授被迫辞职。
从整件事情看,罗斯教授发表专业观点的动机是值得怀疑的,但他的抗争态度无疑是极其鲜明的,更准确地讲,罗斯教授的斗争行为是显性的。学者要求把学术规范引入与学院的互动之中,通过自己行为所表现的态度表示对重构新学术规范的期待。此时的“客我”已不再是相对“主我”的认知机制,而是个体期待实现的规范性期待——学术自由的权利;同时,此时“主我”代表个体为达成自我实现而不受制约的道德冲动——学者对大学理念的追求。学者为了实现自我同一性的建构,必然地投身到为承认而斗争的社会运动中,而当这种承认的要求被蔑视就引发了学者投入到不断的斗争中,直至得到共同体的承认。这样,就能解释罗斯教授的行为,也回到了黑格尔的承认理论模式。
乔丹校长是一位合格的校长,注重大学的利益,但乔丹校长不是伟大的,因为他没有意识到比大学的生存更重要的是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权利。乔丹校长的挣扎清晰地反映出当时美国的学术自由发展状况:既急切地要求保障学术的自由权利,又不得不屈服于社会环境的压力,学术自由的权利没能在社会共同体中得到承认。这也充分表明学术自由斗争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对罗斯教授来说,出于争取学者自由权利的初衷,静悄悄地退却在他看来是不可忍受的。在其解聘之日,他就向媒体发布声明,从而使“罗斯事件”公布于众。借助大学舆论的力量,他成功挑起关于学术自由的争论,使之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在罗斯被解聘之后,乔治·霍华德接过斗争的火炬。当斯坦福再一次成功地向乔丹校长施压,解聘这位口无遮拦的教授时,引起了连锁反应,总共有7为教授递交辞职报告以示抗议。7名教授辞职不是因为个人利益的受损,而是认为这种行为违反了大学教授共同接受的学术自由规范。在这个意义上,学者的斗争超出个体意向的境域而走向普遍化,进而会逐渐达到集体运动的程度而被称为“集体斗争”。
三、学者的斗争:从个体到集体
在“霍华德事件”中,美国学者争取学术自由权利斗争从个体的斗争开始向集体的努力转变,此时的美国大学教师表现出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坚决的斗争精神。1915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建立对于学术自由权利进一步得到承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标志着学者学术自由权利的斗争进入一个新的开端:社会群体的正式斗争。也预示着学术自由原则开始进入制度化阶段,学者的抗争进入集体努力的阶段。
在论述学者的斗争是如何从个体到集体之前,我们需要了解霍耐特对集体运动的解释。霍耐特从马克思、索雷尔和萨特理论传统中关于社会运动的自我理解的承认概念出发,提出一种看法:“社会反抗和社会叛乱的运动形成于道德经验语境,而道德经验又源于内心期望的承认遭到破坏。这些期望与个人统一性的发展有着内在联系,因为它们显示了社会承认模式使主体自我认识到在社会文化中他们既是自主的存在,又是个体化的存在。而如果社会挫败了这些规范的期望,就一定会产生那种使主体感到被蔑视时所表达的道德经验。但是,仅当主体能够在主体间的解释框架内表达对伤害的感受,并把它作为整个团体的表征时,这种对伤害的感受才能成为集体反抗的基本动机。”[3]170霍耐特的论述指明了承认斗争运动从个体到集体的两个前提:一是存在一些因规范期待未被承认的道德经验主体;二是这些经受蔑视经验的主体能在主体间表达此种伤害感受。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运动的兴起取决于一种集体语义学的存在,这种集体语义学使个人被挫败的经验可能被解释为不仅伤害个体本身、也伤害其他主体集团。”[3]170通俗地说,社会运动的兴起需要一种共识的存在,这种共识建立在交往主体间存在近似的知识背景。遗憾但也庆幸的是,这些前提基本都存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
首先,德国学术思想的影响使美国学者形成新的关于学术自由的理念,这种新的理念作为学者理念共同体得到绝大多数美国学者的认同。其次,一系列恶性的学术自由事件使太多的学者经验被蔑视学术自由权利。1886年,著名经济学者亚当斯由于在康奈尔大学发表抨击工业资本家的演讲,遭到康奈尔大学董事会的解聘;1894年,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教授艾利因发表关于劳工关系的言论和“异端”的经济学思想被威斯康星大学董事会指控犯有煽动公众动乱罪而受到审查;1895年,著名经济学者比米斯因为反对企业垄断和批评铁路工业而被芝加哥大学解聘;1897年,玛丽埃塔学院政治学教授史密斯因在教学中批评垄断而被停职;1899年,锡拉丘兹大学经济学家康芒斯因其经济观点而被解聘;1901年,西北大学校长罗杰斯因反对帝国主义而被迫辞职;1906年,经济学教授尼尔林因发表关于童工立法的文章而被宾夕法尼亚大学告知不再续约。最后,由于西方行会团体的传统,在美国也存在着众多的共同体集团,尤其是学者团体。学术共同体的存在使学者被伤害的感情能够得到表达,并得到传播。
在学术自由权利慢慢获得认同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个体斗争的困境,一系列的学术自由事件注解了这一沮丧的境况,但最后,我们看到学术自由斗争从个体转向了集体。在1900年美国经济学联合会第13届大会上,经济学家决定对“罗斯事件”展开调查,因为这个决定,建立保障教授学术自由团体组织的想法被提了出来并付诸实施,成为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AAUP)学术自由委员会的前身。在受到更多对集体力量的呼吁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之后,于1915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正式成立。美国大学教授协会这种新的斗争形式在学术职业标准和学术自由事件的调查机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AAUP成立之初,其学术自由与终身教职委员会就发表了《关于学术自由和教授终身教职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不仅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而且提出当前主要任务是开展反对大学董事和行政管理者的斗争。首先是,限制董事解聘教师的权力;其次提出建议解聘教师的裁决必须经过教师委员会的审查。1922年,美国学院联合会(American Assciation of Collage,AAC)学术自由委员会的报告认为AAUP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和非常重要的”,开始接受AAUP《报告》中几乎所有观点。1925年,美国教育理事会召开大会,大会通过了AAUP 1922年声明。又经过AAUP和AAC两个组织的进一步协商,AAC签署了经过修改的1938年《报告》,并于1940年双方达成共识,发表《声明》。虽然很难评价声明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但毋庸置疑,《声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澄清了学术自由观念的模糊认识,促使其他组织也参与学术自由原则的制定工作,使学者学术自由权的主要相关者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学者的学术自由权利在通过集体的斗争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同。后来,美国的高等教育很好地继承这种联合的经验,采用联盟的手段解决了美国大学的生成和发展问题,在美国大学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8]。
AAUP的成立同时意味着起始于第13届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决定的调查机制进入常态化。其采用的调查取证办法解决了学术自由事件领域过去一直不重视证据的问题,改善了过去无法对学术自由事件的核心冲突进行区分的局面,同时它所开展的调查使大学行政当局在采取有争议的行动时不得不三思而后行。集体的努力使学术自由在制度和文化上逐渐得到更多的承认,爱德华·希尔斯在《教师的道与德》中这样论述道:
“在今天的美国,学术自由的处境与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前相比,甚至与半个世纪之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大学的董事会已经变得更加温和;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严厉和自以为是,也没有以前那么傲慢;他们不再把自己的监管职责看成是一种用来防止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或者不正当的性行为对大学的侵袭的警察权和道德上的监护权。大学校长也不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私立中学的校长那样行事。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严密地和充满怀疑地监视教师,而且即使在这么做的时候,他们也不愿采取任何有可能会招致教师们抱怨的行动。”[9]120“更重要的事实在于,美国人的观点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以至于一个在过去看来会招致人们抗议的话题在今天甚至不会再引起人们的注意”[9]120。
当然,我们不能说经由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努力,大学学术自由就进入彻底的安全地带。而且事实上,学者学术自由的权利保障在美国教授协会建立后经历了更多的危机:“一战”时期的爱国主义运动、“二战”前的反共思潮、“二战”后麦卡锡主义迫害、20世纪60年代学生造反运动等等。但毫无疑问,经过集体的努力,学术自由得到了大学教师、大学行政当局和董事会的广泛认同和深刻理解,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自由派大法官沃伦在斯威齐新罕布什尔案(Sweezy v.New Hampshire)的判决中提供保证学术自由的论证时就说道:“在美国大学的共同体中,自由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在民主社会中,没有人敢低估指导和培养我们青年的那些人的重要性。对大学和学院中知识领袖施加任何限制都会损害我们国家的未来。教育中任何一个领域都可能存在新的发现。在社会科学中尤其如此,如果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存在一些原则的话,其中也只有很少一部分被绝对地接受。学术在怀疑和不信任中无法繁荣。教师和学生必须永远拥有探索、学习、评估和获取新知识和成长的自由;不然我们的文明将会死气沉沉。”[10]
总之,在美国终身教职制度的广泛推行和AAUP建立的调查制度成为学术自由的重要保障。集体的斗争促使社会的发展在整体上适应这种“个体”化的进步。“任何了解美国学术自由历史的人都不能不惊讶于这样的事实,即任何认识到团结和自我保护的重要性的社团组织,都应该有远见去保护自由批判和探究活动,我们目前所拥有的学术自由是人类历史上不同寻常的成果之一。”[7]264
参考文献:
[1]秦国柱,罗勇.知识分子与大学的现代性悖论[J].高等理科教育,2011,95(1):6-11.
[2]雅斯贝尔斯.大学之理念[M].邱立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5.
[3]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M].胡继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4]王建华.学术自由的缘起、变迁与挑战[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8(4):18-27.
[5]熊华军.论洪堡的大学教学思想[J].高等理科教育,2012,101(1):56-162.
[6]姚锐,陈署钧.大学与科学的关系:历史与现实[J].高等理科教育,2009,86(4):23-27.
[7]梅兹格.美国大学时代的学术自由[M].李子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8]吴越,李晓斌.高校联盟:美国走上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手段[J].高等理科教育,2013,110(4):57-63.
[9]希尔斯.教师的道与德[M].徐弢,李思凡,姚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0]波斯特.民主、专业知识与学术自由:现代国家的第一修正案理论[M].左亦鲁,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69.
(责任编辑李世萍)
Recognition and Combat:Development of Academic Freedom in the U.S Universities
ZHANGDong-ya,CHENHe-fang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210097,China)
Abstract:The acquisition of rights and freedom has never be a smooth process,especially on the academic freedom in universities.Referencing the Recognition Theory of "the Process of Subject's Combat for Recognition" constructed by Axel Honneth,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version process of academic freedom consciousness of American scholars from "the cognitive self-relation to practical self-relation" and the expansion process of combat subject from "individual to group".Therefore,this paper explains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freedom in the U.S universities from above perspectives and proves that:the rights of academic freedom of American scholars' have undergone the process of the continuous combat of individuals and groups,which finally obtain the recognition of social community at one period of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Recognition Theory;academic freedom;Ross Incident;collective combat
*收稿日期2015-09-03
作者简介张东亚(1990-)男,河南虞城县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基本原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9.3/712
文献标识码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