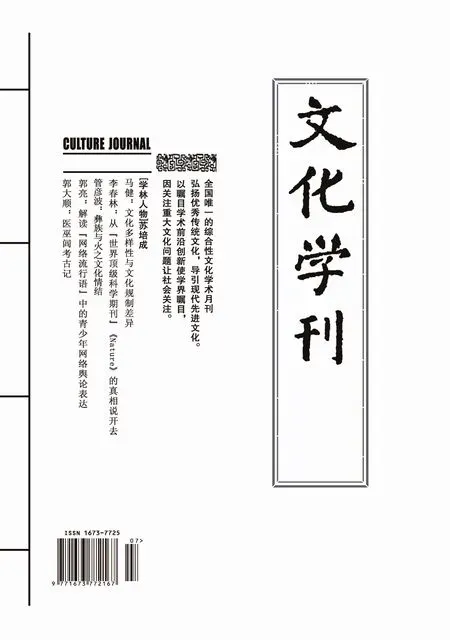以厌降为中心看“三年之丧”由“杀”到“隆”的转变过程
李兆宇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文史论苑】
以厌降为中心看“三年之丧”由“杀”到“隆”的转变过程
李兆宇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710119)
“隆杀”所关注的是礼“量”的改变,而在晋唐间,“隆杀”通过“厌降”对“三年之丧”的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晋初年,由于统治者的需要,厌降被从经典中“挖掘”出来,首先运用在为母服丧的问题上,并逐渐在更大范围内使用。东晋以降,“厌降”理论受到冲击,最终在唐朝确立了为母服齐衰三年的制度,“厌降”中最主要的关于为母服丧的理论随之被废弃。总而言之,以“厌降”为中心,对“三年之丧”的“隆杀”在晋唐间经历了一个由“杀”到“隆”的转变过程。
三年之丧;晋唐时期;隆杀;厌降
荀子云:“礼者……以隆杀为要。”唐人杨絫注曰:“隆,丰厚;杀,减降也;要,当也。礼或厚或薄,唯其所当为贵也。”[1]《史记·礼书》也云:“以隆杀为要。”索隐“隆犹厚也,杀犹薄也”。[2]《礼记·乡饮酒义》:“至于众宾,升受,坐祭,立饮,不酢而降,隆杀之义别矣。”郑玄注:“尊者礼隆,卑者礼杀,尊卑别也。”[3]古人认为不但要“缘情而制礼”,在对待已存在的礼制时,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其进行调整,或发扬或压降,并通过这个过程达到“贵贱明,隆杀辨”的目的,这便是“礼以隆杀为要”。隆杀是对薄厚多寡的改变,即关注“量”的改变,它对礼的改变是在遵循传统礼制的前提下完成的。
“三年之丧”起源甚早,它是古代丧葬礼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诞生于两周甚至更早的古礼,或多或少地带着深刻的“原生礼”痕迹[4],而记载“古礼”的礼书大多由春秋战国乃至西汉的儒学家编纂而成,他们在原生礼基础之上又加入自己对古礼的一些想象,从而导致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古礼”不仅带有早期古礼的原生性,更具有与现实脱离的特点。因此,在进入大一统时代后,“古礼”并不能完全适应王朝的需要,而王朝对其改造的方式之一就是“隆杀”,具体改造的手段是“厌降”。笔者拟以“三年之丧”为例,以厌降为中心,具体探讨“三年之丧”这种服丧制度在晋唐间的“隆杀”过程。
一、西晋年间的“隆杀”
三国时期盛行既葬除服[5],进入西晋后风气大变,武帝即位后即下诏:“诸将吏遭三年丧者,遣宁终丧,百姓复其徭役。”[6]以法令的形式承认三年之丧,并从自身开始,“武帝亦遵汉魏之典,既葬除丧,然犹深衣素冠,降席撤膳”,这遭到大臣的一致反对,他们认为新朝应继续遵循“前典”既葬除服,但武帝还是“遂以此礼终三年”。司马氏家族自称“河内儒家大族”,晋武帝也强调“吾本诸生家,传礼来久”[7],这便可以理解为什么司马氏在开国之初会如此追捧“三年之丧”,但唐长孺先生却早已指出这是司马氏家族一种以“孝之余”补“忠之不足”的措施。[8]然而,无论如何,“三年之丧”在经过了三国时期的沉寂后,通过司马氏的提倡逐渐恢复,人们开始多次讨论到底服不服“三年之丧”“三年之丧”是否合理等问题,其中典型代表就是泰始十年(274)关于太子为皇后服丧问题的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问题的焦点很快由太子是否应为皇后服三年之丧变成怎样去服“三年之丧”,而争辩的中心人物杜预提出了“心丧三年,谅躢终制”和“厌降”的解决办法,最终获得晋武帝认可。前者“心丧三年”是晋唐间“权变”的开始,而“厌降”则拉开了“三年之丧”在晋唐间“隆杀”的序幕。
“厌降”一词当然不是杜预首创,它来自《仪礼·丧服》“大夫之适(嫡)子为妻”条,传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杖也?父在则为妻不杖。”郑注释:“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厌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为人后者、女子许嫁者以出降。”[9]郑玄在这里将“降”分成四类,即尊降、厌降、旁尊降和出降。在太子服丧一事中,晋武帝是君、是尊,他可以“尊降”,所以史载他“既葬,帝及群臣除丧既吉”①《仪礼·丧服》记载妻死,父为其妻期丧。但是鉴于当时葬毕除服的观念仍然很浓厚,因此武帝“葬毕除服”也并不违规。,但太子相对于“君”是“臣”,相对于“尊”是“卑”,因此太子不可以以“尊降”,而是以“公子”的身份“厌降”,所以史书记载太子最终“遂厌降之义”。“厌降”有三个核心内容是。一是这种降服一部分针对宗亲②《仪礼·丧服》:(1)为兄弟齐衰不杖期,为人后者(作他人嗣子者)则为兄弟降至大功,即为降服;(2)为殇者之服均较为成人之服降等,也是降服。另外,女子子在室者为父母与子同,女子子适人者(已出嫁)则为父母降至齐衰不杖期,因为女子已经出嫁,所以此降服也是私亲。,但大部分针对“私亲”。关于私亲,母亲、妻子之族都叫做私亲,或有时也称外亲和妻亲,所以晋唐间的厌降大多是针对父在母亡或妻子的父母亡这两种情况,下文会举例说明。二是与尊为体,这里的尊可以指“父”或“君”,如杜预在奏疏中说:
揆度汉制,孝文之丧,红銺既毕,孝景即吉于未央,薄后、窦后必不得齐斩于别宫,
此可知也。况皇太子配贰至尊,与国为体,固宜远遵古礼,近同时制,屈除以宽诸下,协一代之成典。
又认为,如果“太子不变服,则东宫臣仆,也不能释服,出入台省,难以为继。大臣尚且有夺服之制,何况太子”。[10]
太子是皇帝的儿子、臣子,也是东宫诸臣的君,太子身份的三重性决定他不但要遵循子与父一致,也要遵循君臣一致原则,通过遵守以上两项原则,也间接保证了东宫的正常运转,否则东宫臣仆将会“难以为继”,这就是所谓“与国为体”或“与尊者为体”。三是“以主丧者为断”。主丧者顾名思义是丧事的中心人物,必须是一家之长③《礼记·杂记》先秦服制中强调主丧者必须是男子,家无男子可以亲友主丧,有时女子也可主丧,左传哀公六年注也云:“齐俗妇人首祭事”。,或继任家长,是一场丧事中丧服最重者和服丧期最长者。一般,妻子去世,丈夫就是主丧者,夫为妻服齐衰期,其他所有人服丧都不能超过齐衰期,她的子女可以服齐衰期,但到大祥就必须除服,而主丧者到銺祭才可以除服。在“以主丧者为断”中,主丧者是尊者,但当他面对更加“尊”的君主时就不能“以主丧者为断”了,而应以“尊君”为第一原则。《仪礼》中的“士丧礼”并没有体现这一点,但这一点恰恰体现了大一统专制国家的特点以及与先秦的巨大差别。
自从西晋初年正式将“厌降”纳入到皇家的服丧制度中后,这种对“三年之丧”的“隆杀”手段就被晋以降的王朝继承和保留了下来,尤其在关乎皇帝、太子为其“私亲”服不服、怎样服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晋书·礼志中》就记载: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390),淑媛陈氏卒,皇太子所生也。有司参详母以子贵,赠淑媛为夫人,置家令典丧事。太子前卫率徐邈议:“‘《丧服传》称与尊者为体,则不服其私亲。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王公妾子服其所生母练冠麻衣,既葬而除,非五服之常,则谓之无服。’从之。”[11]
徐邈认为太子必须遵循“与尊同体,不服私亲”的原则,因而在为身份较低的庶母陈氏服丧时,只能服“练冠麻衣”,但这种服叙连五服中最远的缌麻也算不上。为父亲要服斩衰三年,而为生母只能“练冠麻衣”,这种巨大差别不尽让人感慨万千,同时也说明在为“私亲”服丧时,不但要考虑“与尊同体”,也要考虑被服者的身份地位,因为以厌降作为手段的隆杀其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区别贵贱,即使是最尊贵的皇帝也不能违背这一规则,如《晋书·礼志中》记载,哀帝生母章太妃去世,哀帝欲为之重服,大臣江錋辩驳说:“先王制礼,应在缌服。”章氏是皇帝的生母,又是皇太妃,自然比孝武帝朝太子生母陈氏地位高,但也只是缌麻服而已,原因正如太常江荄所说:“位号不极,不应尽敬”。若不遵守这一原则坚持要为庶母服终丧,是皇帝,则群臣也不能如何,但会在道义上谴责皇帝,但如果是人臣,那么就可能会遭受严重的行政处罚。《晋书·顾和传》记载,晋康帝时,汝南王司马统、江夏公卫崇都为庶母制服三年,顾和上奏曰:
汝南王统为庶母居庐服重,江夏公卫崇本由疏属,开国之绪,近丧所生,复行重制,
违冒礼度,肆其私情……若弗纠正,无以齐物。皆可下太常夺服。若不祗王命,应加贬黜。
诏从 之 。[12]
可见当时厌降在当时执行非常严格,然而,王朝在严格执行时也产生了许多问题。
二、东晋以后的“隆杀”
东晋以前,以厌降为中心,对三年之丧的隆杀执行还是比较严格,而东晋以降,尤其是刘宋以降,随着三年之丧的普及,以及政策导向,违反厌降,超期或偏重的服丧事例逐渐变多。《晋书》记载,李含为秦国郎中令,秦王柬薨,“含依台仪,葬讫除丧”,尚书赵浚及州大中正傅祗借口诋毁李含,中丞傅咸则上书曰:“……实以国制不可而逾,故于既葬不敢不除。天王之丧,释除于上,藩国之臣,独遂于下,此不可安。”但结果“帝不从,含遂被贬”[13]。既葬除服是“台仪”,是“国制”,是“与尊为体”的厌降规定,但李含却被贬谪了。不管皇帝出于什么目的将李含贬谪,这都说明对于“厌降”的执行已不再那么严格。刘宋文帝时,南平王刘铄的生母吴淑仪去世,她是皇帝的普通妃子,按礼,南平王应“麻衣练冠,既葬而除”,然而有司奏曰:“古者与尊者为体,不得服其私亲。而比世诸侯咸用士礼,五服之内,悉皆成服,于其所生,反不得遂。”于是皇子皆申母服。[14]从此,为亲生母亲服丧终于从无服变为了有服,甚至后来为养母也可以服。齐武帝第五子萧子敬生母早亡,武帝命贵妃范氏养之,后来范贵妃去世,礼无关于萧子敬应服何丧的说明,尚书令王俭建议:“孙为慈孙,妇为慈妇,姑为慈姑,宜制期年服。”诏从。从为生母服无服之丧到为养母服期年服,厌降中关于私亲的服丧规定不断被打破,三年之丧中有关这一方面也逐渐由“杀”向“隆”转变。梁满仓认为:“如此是因为南朝中央集权化比东晋大大强化,统治者可通过其他渠道和方法规范朝臣的政治行为,强调国家政治关系,从而使王权进一步加强,而不再需要用服制上的强调尊尊来羞羞答答地达此目的。”[15]此外,笔者认为这与南朝的礼制发展也有一定的关系。南朝多有“缘情制礼”的思想,而这种思想从杜预说厌降、心丧时就已发端,正如牛弘所说:“且制礼作乐,事归元首,江南王俭,偏隅一臣,私撰仪注,多违古法。就庐非东阶之位,凶门岂设重之礼?两萧累代,举国遵行。”[16]
在北朝,“三年之丧”的执行刚开始也严格遵循“厌降”,徐州刺史元衍上表请求解除州职为母服丧,孝文帝下诏说:“先君余尊之所厌,礼之明文,季末陵迟,斯典或废。侯既亲王之子,宜从余尊之义,便可以大功。”由于是庶出,所以元衍只能为母服大功。宣武帝时,元遥的生母死,元遥表请解职为其母服丧,宣武帝“诏以余尊所厌,不许”[17]。然而,严格的规定并没有执行太久,如南朝一样,北朝也开始了从“杀”到“隆”的转变。元恭、元颢均为献文帝之孙,他们的祖母分别为孟椒房、高椒房,元恭、元颢该为她们服何服,礼官们有不同的意见。张惠普认为二王应服三年之丧,其理由是二王的祖母为太妃,为始封之母,以“尊”故,二王需服三年之丧。又宣武帝永平四年(511),员外将军、兼尚书都令史陈忠德祖母死,陈忠德欲服齐衰三年,“以无世爵之重,不可陵诸父,若下同众孙,恐违后祖之义,请求详正。”国子、四门和太学的博士们认为《丧服》中说祖为嫡孙期,其中也包含了嫡孙为祖服三年丧,宣武帝也同意博士们的看法,陈忠德得以服三年丧。从以上例子来看,北朝比南朝对服丧礼的改变要更大,这时为祖母服丧都已经可以行“三年之丧”,这与孝文帝提倡服三年丧以及当时把“三年丧”入于刑律有密切的关系。
进入唐朝,关于为母服丧的厌降进一步削弱,直到废除。唐高宗上元元年(674),皇后武则天上表曰:“至如父在为母服止一期,虽心丧三年,服由尊降。窃谓子之于母,慈爱特深,非母不生,非母不育……若父在为母服止一期,尊父之敬虽周,服母之慈有阙。且齐、斩之制,足为差减,更令周以一期,恐伤人子之志。今请父在为母终三年之服。”高宗下诏依议行焉。[18]又《旧唐书·则天皇后纪》记载,武则天垂拱元年(685)亲撰《垂拱格》,将此服叙编入。这一变革对西晋以来的丧服理论有两个重大影响。第一,服叙原则中为生母服丧的厌降理论从此不复存在,父亲与母亲在服丧上的待遇从斩衰三年与无服之丧,到斩衰三年与齐衰三年,差距被大大减小。第二,“以丧主为断”的理论被彻底打破,在此问题上,丧期与服叙不需要再与丧主保持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厌降的理论基础,即“与尊为体”。总之,对于为母服三年丧这一问题,隆杀完成了由“杀”到“隆”的转变。然而,关于为母服丧的争辩到此还未结束,玄宗开元五年(717),右补阙卢履冰上表指出武则天改革为母服叙的原因,认为武则天“将图僭篡,预自崇光,先请升慈爱之丧,以抗尊严之礼。虽齐、斩之仪不改,而几筵之制遂同。……垂拱之末,果行圣母之伪符,载初之元,遂启易代之深衅”。即武则天改变服叙制度是出于自己的私情,因此以后不应再为母服齐衰三年,但百官并不认可卢履冰的说法,刑部郎中田再思认为父在为母三年已成定制,并编入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格”中,且此事是高宗批准的,并非则天草创;另外,为母服三年丧也合乎情理,符合人伦,因此不需要改动。[19]虽然史书并未直接记载这场论战的胜利者是谁,但从后来颁布的《开元礼》来看,以田再思为首的主张维持现状的一派无疑取得了胜利,因为《大唐开元礼》载:
凡斩衰三年、齐衰三年者,并解官。齐衰杖周及为人后者,为其父母;若庶子为后为其母,亦解官,申其心丧,皆为生己 者 。[20]
《唐令拾遗》假宁令第二十九也记载:
诸丧,斩衰三年,齐衰三年,齐衰杖期。为人后者,为其父母并解官(勋官不解),申其心丧。诸军校尉以下、卫士防人以上,及亲勋翊卫备身,假给一百 日 。[21]
三、结语
西晋时,由于统治者的需要,“厌降”逐渐走入公众视野,并成为典制,而刘宋以降,又因为皇权的加强,三年丧的复兴及妇女地位的提高等原因,“厌降”理论不断受到冲击,最终在唐代厌降中最主要的关于为母服丧的理论完全被抛弃。因此,晋唐间,以厌降为中心对“三年之丧”的隆杀经历了一个由“杀”到“隆”的转变过程。
[1]王天海.荀子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768.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1175.
[3]阮元.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9.3655.
[4]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76.
[5]吴丽娱.关于中古皇帝丧服“权制”的再思考[J].中国史研究,2014,(4):121-156.
[6][7]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614.
[8]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拾遗[M].北京:中华书局,1983.238.
[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2391.
[10][11][12][13]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620.624.2165.1641.
[14]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401.
[15]梁满仓.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660.
[16]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156.
[17]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446.
[18][19]刘籧.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023.1023.
[20]萧嵩,张说,徐坚,等.大唐开元礼[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34-35.
[21][日]仁井田升.唐令拾遗[M].栗劲,霍存福,王占通,等译.长春:长春出版社,1989.671.
【责任编辑:王 崇】
K207
A
1673-7725(2016)07-0208-05
2016-06-05
李兆宇(1995-),男,陕西渭南人,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