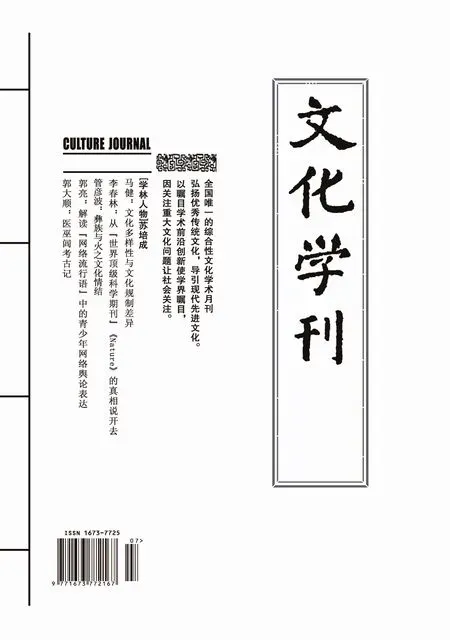探寻“人学”的意识流动
——以《融通与变异:意识流在中国新时期小说中的流变》为中心
韩雪梅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文学评论】
探寻“人学”的意识流动
——以《融通与变异:意识流在中国新时期小说中的流变》为中心
韩雪梅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116081)
古今中外,对“人学”的不断挖掘与发现才是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国内外首部研究西方现代主义意识流与中国新时期小说发展关系的文化理论专著,《融通与变异:意识流在中国新时期小说中的流变》不仅科学地梳理了两者之间的流变路线及相融吸纳的关系,而且弥补了中国现当代意识流文学研究的空白,给当代中国文学“人学观”带来新的认识和体悟。近年来莫言、阎连科、曹文轩等名家在世界文坛的熠熠闪耀,充分体现着对西方文化“中国化”科学研究的现实需求,这也正是探寻“人学”的意识流动对于推动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和社会文化价值。
“人学”;意识流;小说融通;文化价值;现实需求
中国文学这列绿皮火车,从《诗经》始发,进入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小说路段,一路开来,虽然行驶在封闭、自我、传统的古国大道,但沿途也时隐时现闪烁着“意识流”景色。改革开放,国门洞开,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一股脑儿涌入中国。打眼一看,由詹姆斯、柏格森和弗洛伊德组团驾驶的“意识流高铁”,呼啸着驶入中国文学的“绿皮场域”。一时间,在中西文化落差最为悬殊的年代,闭塞僵化的思想空间有如醍醐灌顶,中国新时期文坛处处心潮澎湃。东方的和西方的,封闭的和开放的,接受的和抗拒的,“拿来”的和改造的,这一系列传统与现代的对视和碰撞,新时期小说的跑马场,会呈现何种样态?能发生多大的变化呢?是甘当西方现代思潮的俘虏,机械地扬起意识流送来的“套马杆”,还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做主动吸纳和化觉的主人?金红教授的《融通与变异:意识流在中国新时期小说中的流变》(以下简称《流变》),透过特殊岁月的层层云雾,回到原初的社会文化语境,深入中西意识交汇时必然产生的“抗融与通络”肌理,给广大读者和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交上了一份科学的答卷。
一
探寻西方“意识流”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关系,是一道非常复杂的世界性课题。一方面,意识流小说概念的理论支柱,由詹姆斯、柏格森和弗洛伊德各自提出的心理学、哲学“绵延说”和精神分析学融合组成,三位大师又分别来自三个国家,一个理论的统一体也有并非“一体固化”的接受空间。另一方面,看似一个文学问题,实质是全球视域内社会学、人类学、哲学、政治学、历史学、民俗学、心理学等多学科交叉“意识”的充分体现,它既有“面”的涵濡,又呈“点”的独立,我们在运用时存在着饥不择食的“生吞活剥”与本体接受“有机提纯”的矛盾博弈。面对很难精准下手的研究对象,《流变》紧紧按住“文学是人学”这一根本性命门,激情而充满理性地进行剖析。专著开篇的第一句话,就鲜明地提出观点:“文学是人学,这一常提常新的话题不断启示我们从文学世界走进丰富复杂的人的世界。”[1]进而,在“人学”的视野中,《流变》聚焦意识流渗入新时期小说创作的流动态势,分析当年“思想解放”语境下个体生命社会意义的价值度,揭示其两者交汇中文学场域可然律和必然律的本真世界,促进认识西方流派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及其文学变革所产生影响的深化和提升,敞开了“人”的解放和“文”的自觉的极大可能性。
专著分为五章。整体结构凸显融通与变异中的“变”字框架和脉络,形成适宜的吸纳与演进的探测度量,科学透视洋为中用的聚集图像。第一章和第二章,以客观的目光告诉读者西方现代意识流理论产生和发展的轨迹,讲清了流动的“源点”和去向。这里,尤其重要的是,探寻“人学”的意识流动,从中西理论差异区间,将人类学要义、社会学对比和心理学叙述等,进行跨学科的深刻导入,由此突破了传统译介史的藩篱,为现代意识流在中国的流动构成了多维、立体的论证现场,给人学的内涵支设生命的产床。
那么,如何实施对核心问题的切入,《流变》采取了“艺术技巧”提挈意识流小说本质的策略。书中说:“形式是思想的外衣,任何时代的作家都会为自己的思想寻找合适的表现形式。中国新时期作家在对意识流小说的探索实验中,特别注重对艺术技巧的研究和使用,常常赋予他们以社会、历史、文化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内涵。”[2]于是,从第三章到第五章,专著将目光集中于意识流小说与“人”的艺术关联元素,构建起通变的流脉体系。全书以点带面,具体阐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王蒙意识流小说“集束手榴弹”的人文价值,还有莫言小说“魔幻化”生命感觉中底层人物的关怀。当年,王蒙和莫言作为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人物,在中国文坛上刮起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之风和创新之风。许多作家随之学习和演练这一先进的思想流派和不同寻常的创作技法。陈晓明评论说:“王蒙和莫言等人的意识流小说,作为最早的现代主义叙事文学,虽属伤痕文学范畴,但在思想意识方面明显比伤痕文学更深刻,我们可以看出王蒙等人意识流小说对‘拨乱反正’思考的深化和超前性。正是对思想解放的进一步发掘,使相当一批作家和知识分子从根本上去思考‘文革’,文学上的现代主义才真正开始崭露头角。”[3]
对文化理论的探索没有止境,专著继续拓展开来,深入下去,又对陈染、林白、海男、徐小斌等作家新时期“私语小说”的意识流写作进行了分析和对比,使他们作品的思想内涵和现代写作手法与生命意识形成客观内在的有效联系,很好地绵延了西方现代意识流思潮实现“中国化”的融通与变异的流体。尽管如此,《流变》还是没有停下探寻的脚步,继续生动地观照出新时期小说音乐性、意象化的人性诗化的叙事格局和追求,开辟又一条新的艺术通道和观察视角,为意识流在中国现场的技艺流动,传神地描绘出别致的审美容颜。
二
探寻“人学”的意识流动,必须要有一座联通的桥梁。“中国新时期小说已然在西方意识流等现代派因子的参与下成功迈出了走进心灵、走进‘人’的视域步伐,西方意识流也成功地成为新时期小说连接‘人’的世界与外部世界的桥梁。”[4]正是通过这座“人学”的联通桥梁,《流变》建立起完整的学理体系,给当代中国的人学观带来新的认识和体悟。我们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与人的极“左”思想仍然没有退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文化思想还呈现着僵化、坚硬的落后状态。面对这种特殊时期的社会环境,研究“文学是人学”的语境现象,学者牢牢地掌控主题,排除杂扰,逼切核心,实施一种由社会之人到文学之人、由自我之人到大写之人、由集体之人到个体之人、由个体之人到个人之人的本质把握与科学言说。可以这样讲,在很大程度上,《流变》弥补了中国现当代意识流文学现象研究的空白,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文学史意义。陈晓明在《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中对此给予充分肯定:“向西方学习,自现代化以来就成为我们文化的不成文的规范,这一规范意指着进步、创新,对于冲破僵化沉闷的文学格局来说,不失为有益而必要的创新尝试。”[5]
让我们再把话题回到本文的起篇段落。将近四十年前,西方的“意识流高铁”呼啸着驶入中国文学列车的“绿皮场域”,在当年全国“思想解放”的况境下,它们发生了什么,新时期文学又吸纳了什么,传统的“绿皮”与现代的高铁在与国际接轨中兼熔了多少文化因子,咱们的小说何时能在世界文坛发出中国神色?对于这些问题,国内一批学者都发出同样的真切呼唤:“形式诗学最终必然要导向文化诗学。我们应该坚信中国新时期文学在包容一切有益的外来因子、融汇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能够在新世纪的文学征途上走得更为顺畅。我们期待着能让人类普遍记住这‘不朽’的‘人’的声音能够留存在当代中国的文学作品中,期待着体现最高境界的中国文学经典的出现,期待着福克纳所说的具有特殊光荣的‘诗人和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出现。”[6]
令人欣喜的是,中国的期待正一步步变成现实。2012年,莫言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登上世界文坛的最高峰。2014年,阎连科又代表中国作家首获卡夫卡文学奖。2016年4月,曹文轩喜获国际安徒生奖,实现了华人作家此奖项零的突破。我认为,中国文学的发展与提高,正是多年来中西文化对接、交流、融通和吸纳的结果。这其中,有一个很有“意识”的事实,学者对意识流与新时期小说关系的起步研究,早于莫言获奖。《流变》对莫言“魔幻化”意识流创作的力证解读,与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的中心观点完全相同,这是百年不遇的巧合吗?还是学者的眼光、功力,还有那对科学精神鞭辟入里的粹质求索?
归结而言,当前,我们对西方文化思潮与中国文学现场发生演进嬗变关系的研究,聚焦的时间越长,观察到的实际效果就越清晰,进而显现的时代文化意义就越大。中国新时期小说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意识流价值营养的吸纳和增值,有力促进了近年来莫言、阎连科、曹文轩等一批名家在世界文坛上的熠熠闪耀,学者们对这一理论领域,对这一流派和文学史的科学研究与内涵扩容,更加充分地体现了文化的当代意义和现实需求。
[1][2][4][6]金红.融通与变异:意识流在中国新时期小说中的流变[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3.1.53.230.236.
[3][5]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12.320.
【责任编辑:王 崇】
I106
A
1673-7725(2016)07-0050-03
2016-06-26
韩雪梅(1987-),女,辽宁沈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艺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