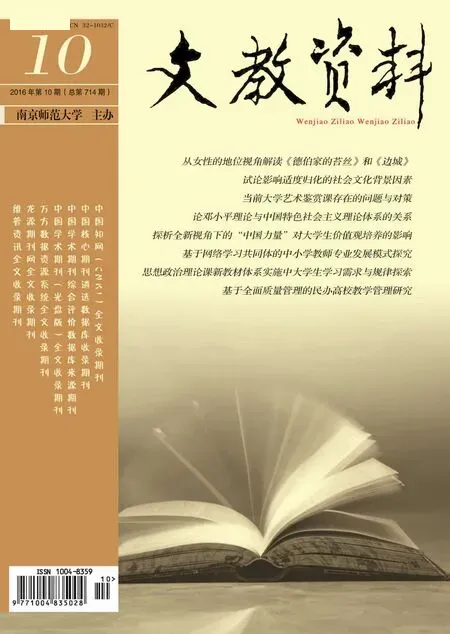市井 人物 生活
——《白雪乌鸦》中的历史与日常
李安昆 闫 洁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市井人物生活
——《白雪乌鸦》中的历史与日常
李安昆闫洁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摘要:《白雪乌鸦》取材于1911年冬到1912年春发生于哈尔滨的大鼠疫,描绘了鼠疫笼罩下的市井生活与市井人物,以温情笔触消解残酷,以去历史化的日常叙事生动地完成了文学对历史的复活。
关键词:迟子建《白雪乌鸦》市井历史生活
“我的很多作品意象是苍凉的,情调是忧伤的。在这种苍凉忧伤之中,温情应该是寒夜尽头的几缕晨曦,应该让人欣喜的”[1]。漫天飘雪,几点寒鸦,清清冷冷之中,透出的是些许难言的寒意——《白雪乌鸦》,便是一种如此苍凉忧伤的描述。当我们穿过这种苍凉忧伤,窥视百年前被鼠疫笼罩的江城哈尔滨,看到人们濒死的惶惑、恐惧、绝望、放纵,更看到危险中的安详、绝望中的生机、重生后的温暖。如果历史的残酷在于消解小人物生命的鲜活,那么文学的意义就在于复原他们行走于时空中所残留的痕迹。迟子建在《白雪乌鸦》中要表达的,是灾难笼罩下的市井生活百态,是游走于历史的小人物的多样人情,而作为一个温情主义者,她令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嗅到了老哈尔滨“动荡之中的平和之气”。
一、市井
从《树下》开始,迟子建一直钟情于环境描写。《树下》的惠集、斯洛古小镇,白卡鲁山三九工区、白航船和农场,《越过云层的晴朗》的金顶镇、大黑山、大烟坡,《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原始森林,《伪满洲国》中遍布东北的城市、农村、开拓团驻地、森林、河流,等等,以及新近出版的《群山之巅》的龙盏镇。空间作为故事展开的重要背景,在迟子建的系列长篇小说创作中的意义凸显。她常以对空间的描绘奠定作品的情感基调,并且以空间转换连缀故事的发展,而对空间的细节填充,往往又裹挟时代特点和地域与民俗特征,叙事的真实性由此得到极大的增强。
《白雪乌鸦》的叙述主要在中国人聚居区傅家甸展开,另外还包含俄国人治下的埠头区和新城区。书中出现的主要地点,如王春申的三铺炕客栈、傅百川的傅家烧锅、周耀祖和于晴秀的点心铺、加藤信夫的日本药房和酱油厂、道台府、青云书馆,在傅家甸;纪永和的粮栈、陈雪卿的糖果店、罗扎耶夫的鞋店、谢尼科娃的家,在埠头区;俄国铁路医院、高迪的钟表修理店、圣尼古拉教堂,则在新城区。彼时的江城哈尔滨,中日俄三国势力撕扯,三国民众既有混居又有分隔。一城三区,众多地点的均匀分布还原了百年前的城市样貌,叙事空间的构造不仅为故事的展开和地点的腾挪营造了合理的背景,更重要的是为富有烟火气的市井生活提供了呈现的可能性,诸多类似民俗、商业活动等的社会环境描写令穿越历史的哈尔滨变得鲜活起来。
叙述从对夏日街市上的生意的回忆开始。“那些夏日可以露天经营的生意,如理发的,修脚的,洗衣服的,代拟书信的,抽签算命的,点痦子的,画像的,兑换钱的,卖针头线脑的,擦皮鞋的…锔缸锔碗的,崩爆米花的……把柴送到饭馆、茶坊、客栈、妓寮、澡堂子和戏园”[2]。一股浓烈的北方市镇气息伴随着一连串密集的对市井行业的罗列扑面而来,傅家甸一下子跃然于纸上。“这里春季街巷因泥泞而常使马车陷落,夏季卫生不良的小市场苍蝇横飞,秋季狂风卷起的沙尘迷了人的眼睛,冬季谁家当街泼出的污水结冰,跌伤了无辜的路人”[3]。土气,而又极具真实感。北京有北京的皇城气派,上海有上海的摩登情怀,对特定地域的突出特点的着力描写才可以赋予文本真实可靠的空间背景,但这不单单源自于对地理空间的精妙设计和市井生活的细致描绘,更关键的是文本所刻画的市井中人的经历、想法、气质与所处环境蕴含的气息的和谐统一。宽厚、仗义、隐忍、悭吝、卑琐,不同的韵致附着不同人物,融进作为生活世界的傅家甸,充实氤氲在整个作品中的烟火气。王春申婚姻的波折与对谢尼科娃的暗中爱恋,傅百川与于晴秀的情愫暗生,喜岁的古灵精怪,翟芳桂的逆来顺受,纪永和的视财如命和背后隐藏的苦痛……食色男女,市井风物,各色人等在笔墨间写就的街巷内穿梭,表现着不同的情态,诉说着不同的故事,体现了傅家甸独有的风格。面对迟子建笔下纵横的街市和底层的小人物,能够体味到的不仅是鼠疫袭来时生活的庸常,更是对百年前的那座城市的想象。
二、人物
鼠疫阴影笼罩下的人们是孤立无援的,他们无法像面对饥饿那样,向别人乞讨或者直接抢夺,弄来粮食填充肚腹以躲避死神掠过的镰刀。生活在傅家甸的人们,用锈铁钉煮水等荒诞方法安慰着自己被死亡压迫着的脆弱灵魂,企图逃离濒死的悬崖。迟子建说:“我要拨开那累累的白骨,探寻深处哪怕磷火般的微光,将那缕死亡阴影下笼罩的生机,勾勒出来。”[4]抗击鼠疫的英雄自然伟大,努力求生的民众也惹人心疼,然而,灾难面前,总有人选择不同的生活,总有人呈现别样的状态。空灵、积极、隐忍或是晦暗,复杂多变的人性,才是最令人心动的部分。
陈雪卿,糖果店的主人,胡匪的女人,在鼠疫行将结束的时候,追随着自己的爱人故去了。鼠疫在她那里从来都是无足轻重的事情,她的生命系在那个游荡在山林之中,为失去的家园与俄国侵略者抗争的男人身上,那是她少年时就钟情的采参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她存活的唯一理由。装扮明艳的她挎着篮子挨家挨户地分糖,是鼠疫结束后一道美丽得令人心碎的风景,一场生命的完美谢幕,一朵错放人间的蓓蕾。她虽然在《白雪乌鸦》出场寥寥,却以一种决绝的美为百年前的那个冬季划下最深的印迹。
纪永和,变态卑锁,视财如命的粮栈栈主。对赎来的“妻子”翟芳桂百般虐待,对洋人莫名仇视,趁着鼠疫囤积居奇,做着卖粮发财的美梦,无奈最终死在俄国铁路医院的病床上。尽管他的种种行为都十分可鄙,可他也是时代风潮下的一个苦苦挣扎的苦命人:“现在啥样?你想支个窝棚,还得去人家的地亩处申请!知道为了啥?咱穷!人家富,就当爷了!”[5],在松花江上自在打鱼的童年已经一去不返,眼下是洋人横行无忌的时代;两任妻子相继横死,命中无子,注定凄惨一生。没有尊严,没有情感,没有孩子,人生还剩下什么?只有钱,可以为自己孤独的心灵建立一根凭依的轴,可以在自己的家园找到做人的尊严。每个人都是那个黑夜里无助的稻草,选择善良的人自然令人温暖,而纪永和难以被苛责,反而显露出一种无奈的辛酸。
人的现在由无数的过去孕育,没有无由来的善,也没有无由来的恶,在迟子建笔下,每个人都是值得怜悯的灵魂。“香芝兰”翟芳桂,少年时父母横死,被邻居霸占,远赴长春投奔亲戚,生活得凄凄惨惨,后被姑父卖到妓院,备受凌辱,被纪永和赎出来之后依旧受尽折磨。也许是颠沛流离太久,吃过太多的苦,她看淡所有,逆来顺受,忍辱负重,以生活中一点暗淡的光亮支持自己活下去,只要活下去,而她的哥哥翟役生,却在备受折磨之后,彻底失去活下去的意愿。家乡太苦,以残躯入宫,受到大太监的气压,但水莲给能他无限的慰藉;被打断腿赶出宫外,家被烧毁,父母双亡,但妹妹还需要他,于是他忍辱偷生;来到傅家甸,却发现妹妹也被迫做了妓女,被赎身后还受着纪永和的欺压。他对生活已经彻底绝望,是金兰给了他一丝信心,然而,鼠疫袭来,这一丝信心又熄灭了。跟妹妹相比,翟役生有过希望,但经历更多的幻灭。他轻贱自己,轻贱世界,反倒过得不错。人生于他,如同一个巨大的玩笑。翟役生无力掌控自己的人生,对这个坏人掌权的世界充满痛恨,希望鼠疫杀死所有人,然而,他是个历史中无可凭依的幽魂,渺小,可怜,受尽折磨,十分惹人怜悯。
书中涉及的各色人等还有许多,为“孝”殉母的秦八碗,贪财好色的周耀庭,大笑气绝的周于氏,如精灵一般活泼的喜岁……不同身份、不同行业的人们,全面展现了鼠疫中的傅家甸的世态。在鼠疫中,死亡铺天盖地般袭来,但生存从来就不是秦八碗、陈雪卿的头等大事,“孝”与爱才是他们生活的信条。
三、生活
人在时空中生活的痕迹因时空的变易而成为历史,与此同时,生动的生活状态变成了僵死的数据、符号、文字。文学如何表现生活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文学如何表现历史也值得扣问。从《伪满洲国》开始,迟子建有意向历史题材开拓,逐渐形成独到的历史叙事模式。她以温情解构历史的残酷,着眼于最底层民众,认真描绘日常生活,展现人性的复杂并从中发掘人性的闪光点。她的历史叙事,实际上是一种去历史化的日常叙事,但也正因此,由日常生活组成的历史才更显真实。日常与历史之间,存在时间的阻隔和选择,历史,其实是日常生活经过时间投影的碎片。当文学捡拾起这些碎片连缀成珠,也就完成文学对历史的复活。
周济一家三代的离去使于晴秀几乎失去所有,所幸老天又给了她一个喜岁。王春申答答的马车穿越傅家甸、埠头区、新城区,车上没有谢尼科娃,载着的是王春申无尽的思念。苏秀兰会给傅百川再生一个孩子,周耀庭又回到禁烟所,翟芳桂嫁给罗扎耶夫,尼娜占据了谢尼科娃的位置,和雅思卢金开始新的生活……无论善恶美丑,在经历一次死亡的洗礼后,春天到了,生活毕竟要重新开始了。幸存下来的人,有贩夫走卒,有达官贵人,有妓女、强盗、小偷,这世界本来就美丑混杂,日常生活的丰富也为历史抹上生动的光彩。
百年前的那场夺去了五千余人生命的巨大灾难,在迟子建对日常生活的忠实描绘下变得生动起来。死亡固然可怖,但即使是鼠疫笼罩下的市井,仍旧充满了生活的烟火,生活,才是历史中永恒的主题。不同的人在死亡恐惧的笼罩下选择着生活状态,鼠疫过后,幸存者带着对亡人的思念继续前行。于是历史中游动的轮廓,逐渐被填充,被充实,组成温暖的影像。死亡残酷,命运动荡,而死亡与动荡的色,却是恒久的平和。
参考文献:
[1]方守金,迟子建.自然化育文学精灵——迟子建访谈录.哈尔滨:文艺评论,2001(03).
[2]迟子建.白雪乌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1.
[3]迟子建.白雪乌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20.
[4]迟子建.白雪乌鸦(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259.
[5]迟子建.白雪乌鸦(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