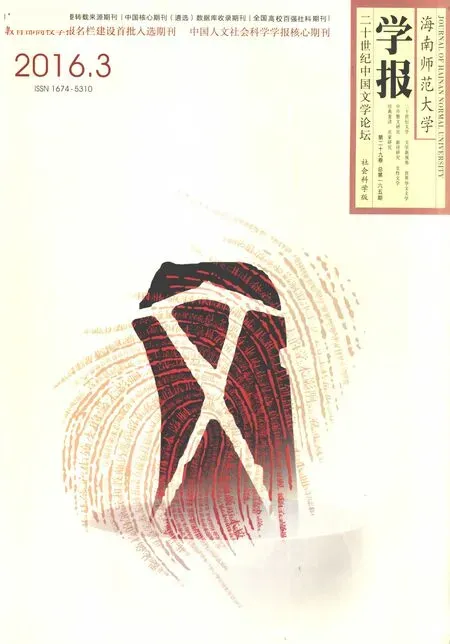创伤记忆的“修通”与“重现”
——解读《家》中弗兰克的创伤记忆
王丽丽
(哈尔滨工程大学 外语系,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创伤记忆的“修通”与“重现”
——解读《家》中弗兰克的创伤记忆
王丽丽
(哈尔滨工程大学 外语系,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要:莫里森的新作《家》是关于创伤和记忆的小说,刻画了饱受种族创伤、战争创伤之苦的黑人男性弗兰克。创伤事件的片段碎片式地存储在受创者的记忆中,创伤记忆的修通与重现是创伤治疗并痊愈的过程。建立与外界的联系并讲述创伤事件是创伤痊愈的必要条件。
关键词:弗兰克;《家》;创伤记忆;修通;重现
美国著名非裔女性作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 1931-)在她81岁高龄时又推出来了一部创伤主题的小说《家》。这是一部关于创伤记忆的小说,莫里森刻画了饱受种族创伤、战争创伤之苦的黑人男性形象——弗兰克·莫尼(Frank Money)。多重创伤打击导致弗兰克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从朝鲜战场回来之后就住院治疗。当他接到妹妹茜(Cee)生命垂危的信件后,他毅然决定逃离医院,返回家乡佐治亚去解救妹妹。返乡之路既是解救妹妹的坎坷之路,也是治疗创伤、创伤记忆“修通”与“重现”的艰难旅程。
创伤事件时常以噩梦、幻觉等碎片式的记忆反复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导致他出现失眠、麻木、暴躁等一系列创伤症状。童年遭受的种族歧视和战争恐惧成为弗兰克创伤记忆的原始场景,当与之有关联的情境再次出现时,创伤的原始场景被激发,片段式的创伤记忆反复浮现在弗兰克的脑海中,干扰他正常的生活。而创伤得以修复,创伤记忆得以修通,碎片式的创伤事件能够完整地、真实地再现,则标志着弗兰克的创伤被治愈。
一、受创:创伤记忆的原始场景
小说开篇叙述了弗兰克兄妹童年时期见证的恐惧场景,这在他们记忆中刻下了深刻的印记,甚至影响两人的心理成长。出于好奇,弗兰克和妹妹来到神秘而又恐怖的荒郊农场玩耍,见证了一幕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他们躲在草丛后面看到“几个人将独轮车上的尸体扔到早已挖好的坑里,尸体的一只脚从坑的边缘露出来,颤抖着,好像一使劲就能冲破被压的泥土跳出来……”*Toni Morrison, Hom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2,p.25.看到这一场景,他的妹妹茜整个身子在发抖,他“紧紧搂住妹妹的肩膀”*同上,第5页。来保护她。这个场景是弗兰克与茜创伤记忆的原始场景之一。弗洛伊德定义的原始场景(Primal Scenes)是指儿童看到或听到父母的性事,引起性幻想。*Sigmund Freud,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Ed, James Strachey, London: Hogarth, 1969,p.369.在莫里森的小说中,创伤的原始场景与性事无关,是指“某个关键事件(或多个事件)对于叙事生活的重要意义在事件之后得以显现,事后幸存者以联想的方式记忆引发创伤的原始场景”*Asraf H.A. Rushdy,“Rememory”: Primal Scenes and Constructions in Toni Morrison’s Novel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1990(3), p.303.。对于年仅9岁的弗兰克,死亡本身就是难以理解令人恐惧的事件,亲眼看到黑人被白人埋葬给他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恐怖的阴影。创伤原始场景的影响不在事件本身,而是事件对于受创者事后生活的影响,因为受创者通过联想会再次引发创伤的原始事件。因此当弗兰克在战场上再次经历痛失好友而无能为力,枪杀朝鲜女孩而无法接受时,一系列的创伤事件被引爆,导致他的精神彻底崩溃。
弗兰克与好友为了躲避家乡的种族歧视报名参军,到朝鲜战场前线作战。逃离了家乡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的恐慌,却无法逃离战争的恐怖。他先是看见第一个好友麦克(Mike)惨死,他“努力赶走那些盘旋在麦克身边的黑鸟,他们像轰炸机一样不断侵袭麦克的尸体”*Toni Morrison, Hom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2, p.126.。几周之后,他又不得不面对另一个好友斯托夫(Stuff)惨烈的死状:“雷德被炸得粉身碎骨,血不停地从斯托夫被炸的胳膊处喷涌出来。弗兰克帮助斯托夫找回二十英尺之外半埋在雪里的胳膊。”*Toni Morrison, Hom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2, p.127.死亡再次袭击了弗兰克的记忆,这是他经历的最痛苦、最惨烈的事件,是弗兰克“剧烈的情感痛苦经验,瞬时间引爆了他们共同经历的种族歧视以及朝鲜战场积郁已久的心理创伤”*蒋欣欣、舒建:《友情·爱情·亲情——论<家>中弗兰克的创伤》,《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129页。。从战场回来之后,弗兰克总是出现噩梦、幻觉、狂躁等创伤症状,他恍惚“看到车里斯托夫模糊的身影”*Toni Morrison, Hom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2, p.128.。他靠喝酒逃避痛苦,逃避现实,他表现出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睡眠紊乱,过度敏感,过度激动,侵入性残缺的记忆。
对于创伤原始场景的最初记忆“往往带有因否认、压抑、抑制、规避导致的记忆错误”*林庆新:《创伤记忆的“重演”与“修通”——解读科辛斯基的〈彩绘鸟〉》,《国外文学》2013年第1期,第92页。,受创者在记忆中故意回避或屏蔽甚至更改事件的真相以减轻创伤对心理的伤害。因此,在小说的开头,读者并不知道这些创伤事件的真实情况,弗兰克对事件的讲述只是片段的、单方面的,甚至掩盖了重要事件的过程。如在第一章的结尾,弗兰克对于童年目睹黑人被埋事件的讲述是“我真的忘了埋葬这件事。我只记得那些马。他们如此漂亮。如此勇猛。他们像人一样站着”*Toni Morrison, Hom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2, p.6.。在整件事情中,象征男子气概的斗马场景和黑人受虐被埋的残忍场景复杂交织缠绕在弗兰克的记忆中,他选择讲述积极的记忆却刻意掩盖和逃避创伤记忆。对于战争的讲述也只言片语,甚至对自己亲手杀害朝鲜小女孩的事件只字不提。随着弗兰克创伤逐渐恢复,创伤记忆逐渐修通,导致弗兰克精神彻底崩溃的创伤原始场景和多重创伤事件真实完整地再现。
二、治疗:创伤记忆的修通
创伤事件对于受创者记忆的影响是创伤理论学家们争论的焦点。卡茹丝将创伤定义为:“对于突如其来的、灾难性事件的一种无法回避的经历,其中对于这一事件的反应往往是延后的、无法控制的,并且通过幻觉或其他干扰性的方式反复出现。”*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1.她认为创伤具有延迟性和不可控性,突发的创伤事件具有强大的破坏性,摧毁了人们固有的认知框架,导致受创者对事件的记忆变成“东鳞西爪的记忆碎片,无法形成完整的认知过程”*Cathy Caruth,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6.。创伤事件的突发性和破坏性导致大脑无法正常处理信息使得受创者失忆,即使能够再次想起,受创者也无法用语言讲述。这一创伤理论框架被广泛应用了20年之久,如今仍然占创伤理论框架的主导地位。然而,最新的创伤心理临床观察研究结果得出了与卡茹丝的理论相反的结论。哈佛大学的理查德·麦克纳利(Richard McNally)在《记住创伤》(RememberingTrauma,2003)中指出:“创伤失忆很神秘,受创者可能选择不讲述他们的创伤,但是没有证据证明他们不能讲述。”*Joshua Pederson, Speak, Trauma: Toward a Revised Understanding of Literary Trauma Theory, Narrative, 2014(3),p.334.他的研究证明,创伤记忆是能够被记住和讲述的,并且对创伤有治疗作用。创伤事件以特殊的形式、特别强烈的印象储存在受创者的记忆中。受创者无法记起或无法讲述是因为心理强烈回避、排斥、恐惧导致受创者刻意隐瞒或掩盖事实真相。
创伤记忆具有无时性、反复性,创伤事件犹如一个个电影片段,间断性地出现在弗兰克的记忆中。在小说的第一章,他从医院里逃出来被问到发生了什么事,他能记得的是“很多血顺着脸流下来”,“就是噪音。声音很大。真的很大”,“我可能是在一场战斗中”。*Toni Morrison, Hom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2, p.15.这些战争场景的片段清晰地呈现出来,但是读者并不清楚事件的整个过程,伴随弗兰克的就是挥之不去的噩梦,总是梦见“身体的某个部分”*Toni Morrison, Hom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2, p.19.,出现幻觉、幻听等症状。直到他遇到他心爱的女孩,“那些图片逐渐模糊”*Toni Morrison, Hom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2, p.25.,他也可以睡得安稳。创伤事件“粉碎了与他人关系中形成和保持的自我建构”*朱蒂斯·赫曼:《创伤与复原》, 杨大和译, 台北: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995年,第51页。,稳定的人际关系有利于受创者产生安全感,“在幸存者与他人的更新关系中,她重建了被创伤经验损伤或扭曲的心理机能”*朱蒂斯·赫曼:《创伤与复原》, 杨大和译, 台北: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995年,第176页。。弗兰克与莉莉的感情生活抑制了创伤的影响,缓解了失眠、噩梦、幻觉等创伤症状。
当他离开莉莉后,虽然又做噩梦,但是梦中“没有狗或者鸟吞噬战友的尸体了”*Toni Morrison, Hom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2, p.41.。在回乡的路上,弗兰克受到多个黑人的帮助,“黑人集体的理解、帮助以及对待创伤受害者的态度在创伤复原过程中也起重要的作用”*王丽丽:《 走出创伤的阴霾——托妮·莫里森小说的黑人女性创伤研究》,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5页。。弗兰克的创伤症状减轻,创伤事件的记忆层层剥茧般地逐渐呈现出来。在回乡的路途中,再次目睹黑人遭受种族歧视和种族迫害使他记起并讲述了童年时期与父母被驱赶离开家乡投奔祖父母的痛苦经历。同时,他想起自己和妹妹受到祖母的虐待,妹妹在自己的保护下成长,他与妹妹深厚的兄妹之情,这成为他面对创伤的动力。在回忆的过程中,弗兰克也时常受到战争恐惧的干扰,但是他记起的越多,他摆脱创伤困扰的决心越强烈:“就在那时,我决定清算一切。那些噩梦都见鬼去吧。”*Toni Morrison, Hom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2, p.86.创伤事件的片段在弗兰克的记忆中形成无数个清晰难以挥去的碎片式记忆,通过他的讲述,创伤事件的记忆逐渐被有意识地控制,去除了创伤的侵入性和破坏性力量。
战争恐惧的记忆逐渐淡化,被弗兰克刻意屏蔽的另一个更严重的创伤事件开始浮现。他头脑中开始出现一个小女孩的情景,他反复责问“她做了什么值得有那样的下场?”*Toni Morrison, Hom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2, p.26.弗兰克开始只能记得创伤事件的最恐惧、最重要的片段,并且故意屏蔽了不敢面对的部分。小女孩的事件是弗兰克刻意回避、故意屏蔽的记忆,因为他内心的负疚感使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就是杀死小女孩的凶手。因此,小说中第26页首次提到小女孩,但是读者并不知道小女孩的身份以及发生了什么事。随着弗兰克创伤压力逐渐减轻,在小说的第122页,读者知道小女孩因饥饿难忍来到战场的垃圾堆里寻找残留的食物,当她想拿一个已经烂了的橘子,但看到有士兵把守,她乞求地对士兵微笑,露出掉了两颗的门牙,朝士兵爬过去,但是被士兵开枪打死了。直到这里,读者知道事情的经过,但这并不是事情的真相。直到弗兰克解救了妹妹,妹妹的创伤在黑人女性集体的帮助下得以恢复,弗兰克的创伤也渐渐复原,他才鼓起勇气面对最痛苦的事件。这时,他才完整地记起并坦诚地讲述整个事情:“我向女孩的脸射击。我是她摸的人。我是看见她微笑的人。”*Toni Morrison,Hom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2,p.174.同样,对于好友惨死战场的场景也是在第126页才完整地讲述出来。而童年时期与妹妹见证的恐惧场面直到小说的结尾,弗兰克摆脱创伤侵袭,勇敢面对创伤记忆之后,才与妹妹再次回到树林重新埋葬了那具尸体。这象征弗兰克和妹妹摆脱了创伤记忆的干扰,埋葬了过去的创伤。在故事的开头和结尾莫里森安排主人公在同一场景出现,这一重复循环叙事结构展现了弗兰克和妹妹从受创到创伤修复的过程。
弗兰克的恐惧记忆时常导致他麻木、忧郁、隔离,与创伤事件类似的场景甚至会刺激他产生暴力行为。战场好友死亡的记忆导致了弗兰克脆弱的神经和攻击性的性格。返回故乡路途中黑人无偿的帮助、爱人莉莉的关爱、妹妹的亲情对弗兰克的创伤都有治疗作用,有助于减轻弗兰克的创伤压力。弗兰克的记忆修通过程与创伤治疗过程是同步的、线性进展的。对创伤事件的记忆随着创伤症状减轻逐渐完整、清晰、准确。心理创伤的治愈和创伤记忆的修通是复杂的、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心理机制。《家》中弗兰克的创伤记忆修通证明创伤的可记忆性和可讲述性。
三、讲述:创伤记忆的再现
种族歧视、战争恐惧、杀人的内疚感错综复杂地交织在弗兰克的记忆中,通过精神治疗这一过程,即通过建构弗兰克的口述,对其记忆进行有意识的控制,从而令记忆失去侵扰性及破坏性。倾诉的动力本身可以看作创伤的因素之一;正如由身体创伤所引起的生理愈合过程一样,心理疗愈过程亦是如此,或许精神创伤本身亦能激发自我愈合。倾诉的能力以及回忆、感知、情感的关联能力,会成为“个体在面对道德、社会及个人挫败时用以维持自我价值感的主要机制”,据心理治疗师玛瑞纳、拉姆斯登所说,尤其就自我叙述而言,“在治疗和解决由于违背公共道德准则所引起的羞辱时更是至关重要的”。*Shadd Maruna and Derek Ramsden,Living to Tell the Tale: Redemption Narratives, Shame Management, and Offender Rehabilitation, Healing Plots: The Narrative Basis of Psychotherapy. Eds. Amia Lieblich, Dan P. McAdams, and Ruthellen Josselson. Washington: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4,p.131.对于记忆背后的真相,弗兰克的幡然醒悟显露出精神创伤事件完整再现的潜在可能性,弗兰克精神治疗过程中的这一进步所展示的,正是莫里森所设想的通过创伤回忆能够使得创伤事件的真相重见天日。这显然与卡茹丝的基本观点是相对立的,卡茹丝认为,有关精神创伤的回忆在叙述过程中创伤事件“不但有失准确性,而且会更广泛地消失”*Cathy Caruth,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54.,受创者无法言说创伤过去的真实情况,甚至讲述与创伤事件本质背道而驰。 《家》中弗兰克的创伤记忆再现是一个循环反复的过程,创伤事件的讲述伴有错误和纠正,通过不断修改和更正的口头讲述,创伤事件的真相被认知、被揭露,对弗兰克的创伤恢复产生了积极有益的效果。在弗兰克的回忆之初,即使最近发生的事件,也在他的持续讲述中得以纠正。有例为证,当弗兰克坐在火车上,看见一对黑人夫妇被白人毒打后,他认为女人回家一定会挨揍。但是在小说的第五章再次提到这件事时,他有了很大的变化,明确表示“不对,我当时完全没这么想”*Toni Morrison, Hom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2,p.86.。又如,在小说的开头他回忆了与妹妹见到在农场健壮的马和黑人被埋,但是在小说结尾他的讲述中事实真相才被披露出来。原来那里是白人“斗狗”(dogfights)表演的地方。“斗狗”是白人以两个黑人互相残杀为乐,直至一方被杀死。被埋的人是一位黑人父亲,他被迫与儿子争斗,为了让儿子得以存活,他选择被儿子杀死。在弗兰克更正补充的讲述中,读者了解了弗兰克最初的创伤源于目睹黑人遭受的灭绝人性的种族暴力,在讲述与回忆的循环反复过程中,真相才会浮现。卡茹丝关于创伤事件认知与讲述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的论断也因此遭到驳斥。弗兰克的例子证实创伤治疗过程中,创伤事件的真实记忆是可以被感知和讲述的。创伤记忆即使未必正确,也是可以被恢复、再现和更正的。
创伤讲述需要一位倾听者,“幸存者和倾听者的共同努力,共同分担才能实现对创伤记忆的再加工”*Dori Laub,Truth and Testimony,The Process and the Struggle ,Cathy Caruth(ed.).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95,p.69.。弗兰克的听众是沉默的、专注的,像隐含作者一样无形存在于文本的叙述中。“倾听者需要专注于幸存者的语言以及沉默,同样重要的是倾听者不能判断、评估或质疑幸存者的讲述”*Dori Laub and Shoshana Felman,Testimony: 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2,p.61.。倾听者在整个创伤事件讲述中需要保持客观的态度,并能容忍受害者的情绪变化。莫里森在叙事上为弗兰克安排了一个全知全能、默默聆听的倾听者。倾听者不是弗兰克的亲人、伙伴,也不是读者。在弗兰克的讲述过程中,时而自述,时而讲述给第二人称的“你”。在小说章节安排中,第十二章之前奇数章节都是弗兰克讲述他所回忆起来的事件,偶数章节是作者叙述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第十四章是弗兰克对枪杀女孩事件坦诚的告白和忏悔。莫里森设置的倾听者使弗兰克在讲述创伤事件过程中具有绝对的自主权。弗兰克的创伤逐渐被治愈,他所经历的创伤事件逐渐被讲述,他可以选择适当的时机讲述恰当的回忆。一件件经历过的创伤事件通过弗兰克的讲述完整呈现出来,也促进弗兰克创伤的痊愈。小说的最后一章仍然是自述,他讲述他眼前看到的是强壮的树木,美丽而充满生机,他与妹妹也回归到温暖的家。 他的讲述中不再充斥着死亡、恐惧,而是对新生活的向往和希冀。
在创伤治愈过程中,与他人、与社会的联系是促使受创者讲述的动力。玛莎·纳斯巴姆(Martha Nussbaum)认为创伤记忆是一种线性断裂,如果它变得与周围毫无关联,那么它就会构成一种新的创伤现实;在现实社会中信任的缺失导致受创者与团体隔离。*MarthaC Nussbaum, Upheavals of Thought: The Intelligence of Emo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1,p.318.《家》所描绘的弗兰克从战场回来经年累月待在西雅图,靠酒精麻痹自己,隔离了自己与外界的联系,犹如被监禁在封闭的创伤现实中。纳斯巴姆认为,为打破这种创伤世界,作为用以建立与他人之间必要关联的一种能力,必须拥有并重新建立自主性。正是弗兰克对于拯救妹妹的号召的回应,将他从停滞不前的状态中解救出来,迈出了他走出创伤的第一步,这是重新与他人建立关联的一种能力。莫里森在小说《宠儿》中使用了“记忆再现”(rememory)一词,这一词代表对过去创伤事件的重新记忆,完整再现。对过去的重新记忆就是要恢复断裂的关系,重新建立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受创者最终得以摆脱创伤事件的阴影,治愈心理创伤。在《家》中,莫里森强化了关于弗兰克内心深深的破坏感和缺乏归属感的描绘,同时也强化了他逐步重建关联的挣扎与成功。与此前任何一部小说相比,莫里森此次更多地断言团体给创伤治疗带来的积极影响。弗兰克的妹妹茜正是因为黑人女性团体对她的治疗和关爱才使她摆脱困境,走出创伤。解救妹妹是弗兰克打破封闭的创伤世界的原生动力,在这过程中他建立了与黑人集体的联系,也是在家乡黑人集体的鼓励和帮助下,他勇敢正视创伤,坦然面对自己枪杀女孩的罪行。创伤受害者和社会环境(例如,倾听者作为创伤讲述的第一接收人及叙事者所属团体)之间的关联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在黑人集体的帮助下,他和妹妹找到了家的归属感,坦然面对创伤事件,成功摆脱了创伤的阴影,治愈创伤。
四、 结语
《家》不仅再现了创伤记忆在弗兰克头脑中修通和再现的复杂的心理机制,也展现了莫里森创伤叙事的艺术魅力。种族暴力和战争恐惧是弗兰克创伤记忆的原始场景,导致他饱受噩梦、闪回、幻觉等干扰,将自己封闭在创伤的世界中。妹妹的求救信件促使他走上返乡的道路,也是创伤逐渐治愈的艰难历程。亲情、友情、爱情帮助他重新建立了与外界的联系,促使他将记忆的碎片重整为完整的记忆,创伤记忆得以修通。弗兰克通过讲述回忆创伤事件,再现创伤记忆,但这是一个循环往复,不断修正、不断添加的过程,直至创伤事件的真相浮出,弗兰克坦诚面对创伤事件,标志他的创伤得以痊愈。对《家》中弗兰克创伤记忆修通和再现过程的分析,一方面可以全面揭示莫里森创作中对黑人个体和黑人民族创伤经历的关注和描绘,另一方面也驳斥了卡茹丝关于创伤不可讲述的理论观点。
(责任编辑:李莉)
A Reading of Frank’s Traumatic Memory inHome
WANG Li-li
(DepartmentForeignLanguages,HarbinEngineeringUniversity,Harbin150001,China)
Abstract:Toni Morrison’s Home, a new novel about trauma and memory, depicts a black man Frank who suffers from the racial trauma and war trauma. The fragments of trauma are imprinted in the victim’s memory. The process of working through traumatic memory and the rememory of traumatic events is also the process of trauma recovery. Establishing the relations with the surroundings and telling the trauma are indispensable to healing trauma. Key words:Home; traumatic memory; working through; rememory
中图分类号:I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6)-03-0078-05
作者简介:王丽丽(1980-),女,黑龙江巴彦人,哈尔滨工程大学外语系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国女性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10-06
基金项目: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编号:14YJC752033);2015年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编号:15WWC01);2016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