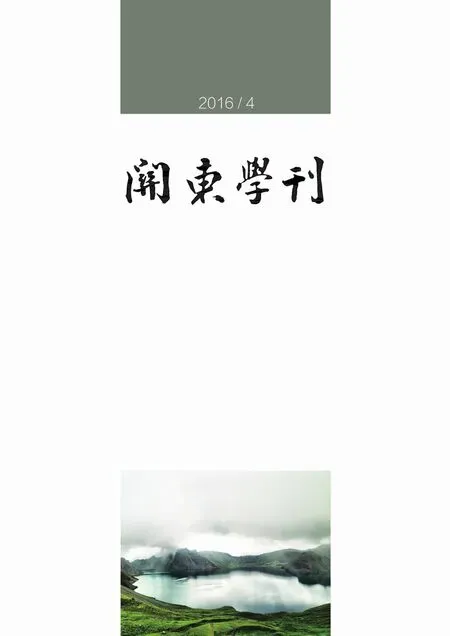“末日”中的现实和历史
——读薛忆沩“十二月三十一日”系列小说
冯新平
“末日”中的现实和历史
——读薛忆沩“十二月三十一日”系列小说
冯新平
“十二月三十一日”系列小说以X在三个年代最后一天的行踪和思虑,通过梦境与现实的频繁交叉,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叙述,将中国社会刚刚经历的三十年历史与现实融入个人悲剧性的命运,从而探寻人性与历史的奥秘。
薛忆沩;末日;现实;历史
作为中国文学界“最迷人的异类”,薛忆沩的小说具有浓厚的现代主义文学特色。在多年的写作生涯中,面对经验世界和社会语境的变化,面对精神家园的衰败和物质世界的生机勃勃,他始终专注于个体的内心奇观,始终探索个人在历史中的存在困境,始终从一个很小的角度窥探历史和人性的奥秘。在这三部“末日”系列小说中,作者娴熟地应用时间分裂、重叠和错位等叙述方法,打破了传统叙事文学的时空边框,不同时空中纷繁复杂的事件在一个心理化的多维叙述空间中发散、聚合、伸展、收缩。作者的长篇《空巢》以主人公完整的“一天”来表现其完整的“一生”。如果说那一天是老妇人一生的缩影,那么“十二月三十一日”就是三部“末日”系列小说中三个同名主人公X一生的转折点。与《空巢》将个人命运明显地融合于民族历史的命运,将个人的经验集中在复杂的历史经验与集体记忆中不同的是,作者将三个X的个人经验凸显于叙述的前景,并通过其独特的修辞学,在隐喻的层面将关于历史的记忆进行组织与转换,将历史语境中的冲突通过修辞转换成文本与历史的张力。
一
在这三部系列作品中,作者把X个人的际遇(主要是两性关系)置于多重时间的叙述之中,把X个人的命运与多种历史轨迹联系起来。它们不仅揭示了一个孤独个体和理想主义的关系,也揭示了他在市场化现实中的命运。作者将社会境遇的危机反映到身处极端困境的个人身上,并力图从中找寻出历史的渊源。隐含在《十二月三十一日》文本背后的社会语境对理解这三篇小说的内涵至关重要。1980年代,社会思潮能够影响和牵动社会实践的革新,思想的社会功能能够深入人心。这样宽松的氛围为两代中国人提供了理想主义的土壤,培育了年轻的X和他的朋友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个性。
然而,思想和现实世界之间的有机联系在八十年代末渐趋渐弱,历史在年代交界处出现的剧烈震荡开启了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这样的结果尤其对渴望介入历史的知识分子影响巨大。当他们不能从自身的经验中体验到其所塑造的象征价值时,意义感的丧失和个体经验的贬值就成为一种令人焦虑的体验。而面对无法阻止的历史,个人或逃避或自杀或精神失常或无动于衷。
在《十二月三十一日》里,曾经爽朗的X的导师突然变得悲观沉默,他想要很快死去,他想让自己的死带上历史的烙印。与郁郁而终的导师相比,在《一九九九》中作为X朋友的历史学家突然完成了“父子”之间的和解,完成了与历史的和解。与拒绝进入九十年代而卧轨自杀的诗人相比,X的朋友在逃离祖国十年之后仍以自杀的方式弃世而去。而舞厅里跳舞的人们就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进入“平庸”的九十年代,现实世界开始独立按照它自己的轨道运行。曾经激进的思想不再有草木皆兵的虚幻力量,而是退化为无伤大雅的语言游戏。八十年代阴暗的结局让X和他的朋友不再向往英雄的生活,不再渴望与历史发生关系。然而,他们又不能建构起新的理想目标,其结局就是从身体的解放感滑入精神的虚无感。这在他的朋友是以性的解放来替代不尽如人意的政治与经济的解放,而昔日的理想主义者X面对九十年代的浮华,选择了逃离。他逃出了集体,逃向了个人。他只想将自己曾经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心灵安顿在平静的婚姻生活之中。
然而,意料不到的是,他对生活简单的要求竟也遭受到生活的嘲弄。小说甫一开始,他极度迷恋的妻子就已经离家出走两天了。这样的开头既赋予叙事足够的动力,同时也将主人公X置于具有丰富意蕴的个人和历史的境地:作为时代和世纪“末日”的“十二月三十一日”,也是X赖以生存的婚姻的“末日”。叙述自然地将个人生活和时代历史联系起来。在极度的焦虑和恐惧中,与妻子往昔的亲密场景频频浮现于X的脑海,与此同时,妻子可能与他人共享的“此在”也不断出现在他的视野中。这甜蜜的回忆和灼心的想象意味着他被美好的过去、不安的现在和无望的未来同时抛弃。在“末日”的城市里,X仿佛成了一具与时间失去关系的躯壳。他以消极的姿势迎接新时代、新世纪的到来:在恐惧的黑夜里,他像一个无助的孩子蜷缩在让他焦虑的床上。他“不断地下沉下沉下沉……直到完全感觉不到自己了,直到时间停顿。”*薛忆沩:《十二月三十一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8页。
面对无法阻止的历史和不可抗拒的集体,不断“逃离”的X终于在《二零零九》中看到了“回家”的可能。《一九九九》是以主人公的焦虑开始,以他的绝望结束,而《二零零九》则是从主人公与阔别重逢的恋人之间的性爱开始的。而这意料之外的激情是混乱不堪的“十二月三十一日”之中唯一的宁静。在这极度混乱的“末日”里,移居北美已经七年的X发现曾经熟悉的故乡变成了陌生的异乡,其中上演的是亲人争夺遗产的闹剧、播报的是“海龟”坑蒙拐骗的新闻、呈现的是老外飞扬跋扈的丑态……一切都在X应接不暇的变化中扭曲和震荡。如浮萍般飘荡在海外的X在自己的故乡仍然找不到落地生根的感觉。他感觉自己成了一个彻底无“家”可归的孤儿。X无法避开的是曾经的理想主义正在遭遇资本化的社会语境的讽刺,八十年代悲剧式的历史语境在此转变为喜剧式的社会语境。他就像是一个局外人穿过别人的世界,寻求不到自我永久的家乡,唯有情爱映照着混乱的现实,照亮X迷惘的内心。
这种异乡的感觉激起了X对异化的反抗。《二零零九》因此充满了浓重的“火药味”。与薛忆沩关注个人内心景观、因而很少有“烟火”气息的小说相比,这是他小说中颇为罕见的气味。这是他从注重灵魂探索的写作到积极“介入”现实的一个标志。与流氓白人老外的两次交锋就是明显的例证。第一次是X在麦当劳里挺身而出制止了那个老外的挑衅滋事,这可以说是“斗勇”;第二次是X只用一张字条就巧妙地结束了那个老外的艳遇,这可以说是“斗智”。“在小说的最后,X还不想放过已经被他制服了两次的老外。针对那家伙满嘴的F××k,他提出了汉语教学的激进理论。他说汉语教学应该从教学“操”字开始。他说汉语成为“二十一世纪的语言”的标志就是“操”字在全世界范围内取代了飞扬跋扈的F××k。”*冯新平:《长达十年的一天》。
其实三部小说的整体叙事基调和主题意蕴早已隐含在各自的开端和结尾之中。《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头一次微不足道的“天灾”,预示着地面形形色色的“人祸”,而结尾处错过X的中学同学以幻灭的感觉迎来了九十年代。《一九九九》是以X焦虑的寻找开始,以他绝望的睡姿结束。而以X和分别七年女友的两段精彩对话作为《二零零九》的开头和结尾,更加能够显示出一直致力于小说文体探索的薛忆沩的大师手笔。开头关于梦中不断晚点列车的“零”距离对话,遥接二十年前《十二月三十一日》现实中的彼此错过,而结尾处充满深情的越洋通话,在二人一起兴奋迎接新的年代到来的同时,也宣告了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开头是激情的播种,结尾是希望的收获。梦幻与现实,过去与现在,生活与艺术,文本与历史,希望与幻灭,偶然与必然,如此等等丰富的元素,都完美地融合于两段用词简单的对话当中。
二
在这三部系列小说中,《二零零九》较为写实,也更多地介入现实,而《十二月三十一日》和《一九九九》侧重呈现的是人物的心理真实,叙事也更多地以意绪和意象化的方式呈现,追求的不是人物性格的丰满和故事内容的完整,而是着意于作品整体呈现的情绪色彩和隐喻意味。在一次访谈中,薛忆沩这样自述:“这两篇作品主要是由虚的情绪和飘的意象推动,在很大程度上,更像是诗歌而不是小说。”*薛忆沩:《文学的宿命与革命》,http://book.sina.com.cn,2015年9月22日。我想这样的概括一方面是指两部小说通过叙事语言的隐喻性而获得了诗歌用意象所达到的境界。但其呈现方式并非如诗歌那样通过词与词的组合变化来直接呈现,而是由故事性的语言结构来呈现。另一方面是指小说中人物之间、情节之间以及细节之间的连接都是时隐时现,若即若离,异常活跃的偶然因素左右着人物的生活走向。
双面隐喻是薛忆沩小说语言的特点,而由此生成的双层结构也是其小说结构的一大特色。阅读他的小说既是对表层结构中故事的阅读,也是对深层结构中隐喻性词语和话语的阅读。《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充满了大量具有隐喻属性的词语和话语,如开篇“一颗流星从清冷的天空中划过”,既给整个小说定下阴沉的基调,也预示着小说中形形色色的死亡和分离;如,长时间沉默地坐在椅子上的导师如“一座纪念碑”,既有历史烙印,又极具象征意义;让爱错过的两列相向而行的列车,也错过了拯救两个灵魂的机会;“在大海上颠簸的难民,在大街上奔跑的群众,一直在追赶着X的脚步以及‘那一趟不断晚点的列车’……这一个一个的隐喻让读者看到的既是梦境,又是现实。拥挤在梦境与现实交汇处的是现代人的恐惧。”*冯新平:《长达十年的一天》,《晶报》2015年8月23日。与“逃离”历史,逃进婚姻的X相比,妻子留下只言片语的“逃离”却是意味深长。它象征着那个已经远去的理想主义时代和浪漫主义情怀,而妻子的下落不明又象征着一种没有希望的寻找和没有结果的等待。这些词语本身具有的联想性和因话语整合而产生的隐喻效应,都依赖“夏天的事”所具有的故事性。它们将历史对个人的操纵,将身处偶然与必然之间的个人困境很好地呈现出来。
这三篇表面独立的系列小说,在形式上彼此呼应,内容上又持续延伸,细节上也彼此依存,从而在主旨上融会贯通,并在深层意义上构成了一部结构奇特的长篇小说。“薛忆沩的作品从来都富含深刻的寓意。在这里,三个‘十二月三十一日’代表着中国社会刚刚经历的三个不同的年代。薛忆沩写作这一系列作品的目的显然是要发现这三个年代之间逻辑(或者说反逻辑)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三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又的确应该视为是处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同一个人物”:*王威:《薛忆沩与三个“十二月三十一日”》,《晶报》2015年5月25日。“他已经经历过五次这样的‘最后一天’了。之前的那两次,他的感觉最为强烈。一九八九年的震荡打破了他对理想和历史的敬意。他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和无助。那一次,他是在极度失落的情绪中穿过‘十二月三十一日’,迎来新的年代的。在平庸的九十年代里,他渴望的就是平庸的生活。没有想到,那样的生活最后也会以最荒诞的方式结束。在那个荒诞透顶的‘十二月三十一日’,他已经预感到了接踵而至的将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但是,他不可能想到它会如此地混乱……今天又是一个这样的‘最后一天’。X很清楚,紧随这个‘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是一个更加混乱的年代。”*薛忆沩:《十二月三十一日》,第78、148页。
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中让有情人不成眷属的“那一趟不断晚点的列车”,也行进在《二零零九》的人物梦中,只是这一次X和他的初恋情人没有让爱错过。在大海上颠沛流离的“越南难民”是一九八九年的重大新闻,同样漂流在随后两部作品中,成为三个X共同的创伤性记忆。《十二月三十一日》中诗人魔幻的诗句也回荡在《一九九九》中X的脑海里。
《一九九九》中远在悉尼朋友的自杀,是《十二月三十一日》中诗人卧轨自杀的遥远回音,前者当年的逃离和后者的自杀都源于没有选择的宿命。《十二月三十一日》中死于魔鬼之手的X的导师以及导师的导师,对应着《一九九九》中遭受历史凌辱的历史学家和他的母亲。而忧郁而死的导师和与历史和解的历史学家又是一种对照。《十二月三十一日》中X妻子离婚前夕关于生活的滔滔不绝,与《一九九九》中X离家出走妻子的一句“我实在是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又有异曲同工之妙。《十二月三十一日》中X与妻子拒绝在那个夏天的夜晚孕育一个孩子,因为那天晚上怀上的孩子不是残废就是恶魔,而在《二零零九》中X回忆他与妻子决定在那个夜晚创造一个新的生命,为那个夜晚留下一个活的见证。前者摧毁了他们濒临破裂的婚姻,后者因无法面对孩子夭折的现实而选择了离婚。他们的婚姻都死于那个夜晚,但二者在主题表达方面却又殊途同归。
具有同样功效的是三篇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虚构文本——薛忆沩的长篇小说《遗弃》*薛忆沩:《遗弃》,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遗弃》的主人公图林是生活于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年轻人,他从日常生活的细节里敏锐地嗅到了“十二月三十一日”系列小说中呈现的种种社会问题。三个X都受预言“混乱”时代即将来临的《遗弃》的影响,他们好像是图林的三个化身。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中,《遗弃》扉页上的话语:“世界遗弃了我,我试图遗弃世界”,精准地概括了X的处境和心态。而在《一九九九》中,《遗弃》主人公与恋人的情感历程不断引发X对离家出走妻子的种种猜测与担忧。如果说这本小说在前两部作品中具有凸显人物内心世界的作用,那么它在《二零零九》中则已有推动情节发展的功效了:X的前女友因为《遗弃》而爆发了她与丈夫的暴力冲突,从而进一步把她推向了X的怀抱。
作为《十二月三十一日》中核心事件的“夏天的事”,让小说中所有人物的生活方向与心理状况产生了骤变,并且被深深地植入X的个人潜意识中,被遗忘与压抑在黑暗的深处,在随后的岁月里(在《一九九九》和《二零零九》中)以噩梦的形式困扰着X,不时折磨着他的良知,成为他摆脱不掉的心理和精神困境。这是推动三部系列小说叙事的一股强有力的暗流,同时也把三部小说紧紧地贯穿在一起。那样的噩梦既是个人心理创伤的后遗症,也是集体无意识的典型体现。而这样的写作意味着作者试图恢复被历史压抑的记忆。这样的隐喻话语把生命中不能承受的事实转变为一个话语的秘密。这既是叙事策略的需求,更是一种修辞学的仁慈。
三
如果我们把薛忆沩的三个长篇《遗弃》《一个影子的告别》*薛忆沩:《一个影子的告别》,《新地文学》2013年夏季刊。和《白求恩的孩子们》*薛忆沩:《白求恩的孩子们》,台湾:新地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与这三个系列中篇对照阅读,会饶有深意地发现:《遗弃》看到了中国社会潜在的危机,主人公图林对即将到来的“混乱”充满了焦虑,他的“消失”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而《一个影子的告别》目睹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崩塌,主人公X在一个“告别的时代”告别了祖国,他的“告别”同样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犹如一曲精神生活挽歌的《遗弃》对应着《十二月三十一日》,而拉开物质时代序幕的《一个影子的告别》,在《一九九九》和《二零零九》中又有更为深入的上演。他们都在理想破灭后逃离历史,逃向女人,逃进婚姻,最后又告别激情,告别婚姻,告别生命。“薛忆沩有意让‘所指’开放,让同一个代码下的个人命运在真实和虚幻的边界上扭曲,在历史和时间的阴影中变形。通过这种开放式的处理,系列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具备了立体主义绘画的魅力。”*王威:《薛忆沩与三个“十二月三十一日”》。
“我”为什么“必须”去加拿大是《白求恩的孩子们》的叙事动力之一。饶有趣味的是,这个“必须”之谜又与三部“十二月三十一日”系列小说有着不同程度的对应关系。除了不远万里寻找精神上的“父亲”,“我”“必须”来加拿大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还要继续妻子茵茵与蒙特利尔的神奇“缘分”:茵茵在地震后的广播中听到奥运会主办城市蒙特利尔的创伤性记忆。而深层原因是茵茵怀孕期间在那个“夏天的夜晚”不幸身亡。他们孩子的血,让这缘分变为了“血缘”,将“我”引到了蒙特利尔。只此一个细节就将《白求恩的孩子们》和三部系列小说贯穿起来。
这三部充满浓密诗意的“十二月三十一日”系列小说具备优雅的气质、精致的结构、现代的视野和哲学的高度,体现了作者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其呈现个人自由和历史局限的冲突以及个人尊严是如何遭受历史的羞辱,不是以讲述宏大叙事之下个人脆弱命运的方式来实现的,而是以日常的角度突显内心的奇观,让纷杂的现实呈现出美学的形态,历史只是作为模糊遥远的背景而存在,这正是作者悲悯情怀之所在。创作难度极大的三部“十二月三十一日”系列小说,是薛忆沩用二十五年的时间完成的作品,是他文学之途一次抵达的标志,也是他文学生命一个崭新的起点。
冯新平(1975—),男,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院基础部讲师(北京102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