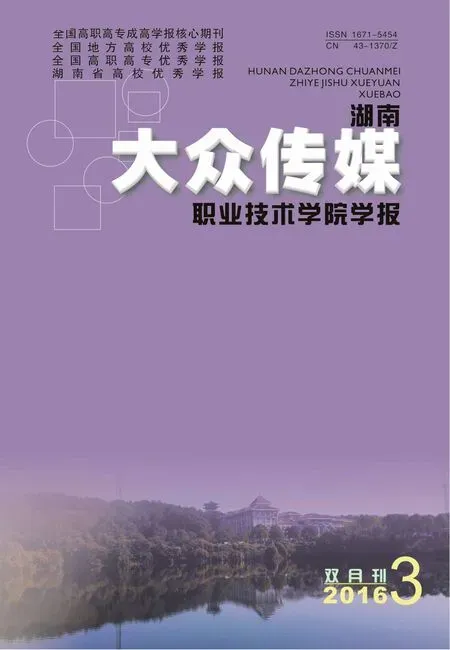假托寓言逼近人性真相
——论阎连科的寓言体创作
聂媛媛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文史哲经管·
假托寓言逼近人性真相
——论阎连科的寓言体创作
聂媛媛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河南作家阎连科致力于追求人的“心灵真实”,倾向于在极端化书写中表现生活的可能性,进而揭开人性的真相。他摒弃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利用寓言体建构起荒诞的文学世界。阎连科的寓言化书写始终围绕着生命、权力与城市三个中心,以暴露人性深层的欲望,反思与批判由欲望衍生出的人性的病态与人格的扭曲,最终形成其个人创作的艺术特色与审美特征。
[关键词]阎连科;寓言体;荒诞;人性
[DOI]10.16261/j.cnki.cn43-1370/z.2016.03.015
阎连科将自己的小说风格定义为“神实主义”,[1]215意在以“神”为桥梁,最终抵达心灵的“内真实”。与现实主义作家不同,阎连科摒弃了传统的真实观,作者笔下故事的“真实”迥异于我们所知的客观现实。与描摹客观现实相比,他更注重探求心灵的真实。为了表现自己感受到的真实,他在小说创作中运用了寓言体,同时还大胆采用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方法,呈现给读者一个神秘荒诞的文学世界。在阎连科小说极端叙事的表层下,隐藏的是他内心深处最初的信仰——对生命、权力与城市的向往。作者将人内心对这三种要素的崇拜视为人性的真实,将人对生命、权力与城市的向往,以寓言体的形式书写在文本中,为表现人的“心灵真实”找到了恰当的出路。
一、生存的执念与勇气
阎连科寓言书写的首要内核是生命。脆弱的生命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威胁。阎连科幼时最深刻的记忆便是饥饿,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够填饱肚子。饥饿与死亡的恐怖经验直接影响了阎连科的创作。其次就是疾病,年幼的阎连科亲眼目睹常年卧病在床的大姐被病痛折磨的惨状。日后他自己因长期写作被颈椎病折磨得痛不欲生,只能躺在床上像残疾人一样写作时,他切实体会到了疾病对生命的威胁。作者将自己的生命经验融入创作中,以生命为内核开启了寓言式书写。
在中篇小说《耙耧天歌》中,阎连科以生命为载体,歌颂了极致的母爱。尤四婆为了医好孩子的呆傻症,听从丈夫亡灵的建议,先将丈夫的尸骨熬制成汤给孩子服下。见效后,为了四个孩子都恢复正常,尤四婆请屠夫把自己的身体分解成尸骨送与各个孩子,最后四个孩子智力恢复,他们厚葬了尤四婆。小说中,母与子不能两全的悲剧定局与尸骨成药的情节描写堪称诡谲。“正是这种极致化叙事创造了震惊性的经验,促使阅读者真实地面对生命的困境、死亡的强大以及人身上那坚不可摧的生存信念。阎连科把生命放在非常态的世界里观察、逼视、追问,最后使之显露出极端的面貌,从而在生命的绝境里,测量人承受压力的限度,以及书写出人在生活面前的可能有的勇气。”[2]阎连科笔下的人物大多对生有着强烈渴望,又受到死亡的致命威胁。他将人物置于这样的境地,以此激发其求生存的强烈欲望。为了孩子的生存,身为母亲的尤四婆想方设法甚至甘愿牺牲自己。作者的寓言建构表现了悲壮的母爱,更突出了人性中生的执念。
在中篇小说《年月日》中,我们可感知到生命的厚重。旱灾来临全村人开始逃离故土,唯有主人公先爷独自与盲狗瞎子选择留下来守护最后一株象征着生命与希望的玉蜀黍。为了玉蜀黍幼苗的存活,先爷拼尽全力,与狼、鼠斗争,最后甚至不惜将自己作为肥料,为快要结果实的幼苗输送养分,以期留给日后回村的乡人们一点生命的希望。这样一曲生命的悲歌感染了众多读者。小说中为保护最后一株嫩苗,坚守在原地,不屈不挠的先爷,与不顾世人眼光,勇敢地同风车搏斗的堂吉诃德十分相似。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的化身,都有执著于心中信条的无畏精神。先爷视玉蜀黍嫩苗为村民回乡的唯一希望,堂吉诃德立志恢复古代的骑士道。为了各自的信仰,两个人都在孤独地拼死“战斗”着。塞万提斯借堂吉诃德性格中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表达了个人对时代的见解,而阎连科在寓言式书写中借先爷与十分通人性的盲狗以及人狼、人鼠大战等荒诞情节,写出了以先爷为代表,仰仗土地的农民对生命的崇拜与求生的勇气。
对生存更强烈的渴求,在阎连科的《日光流年》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小说讲述了三姓村人无论男女老少都活不过四十岁,好似命运对这个村子下了咒语,所有人在临近四十岁时都会患喉堵症而死。于是村人在历届村长的带领下,开始为生存而奋斗。村长先是鼓励多生多养,又提倡翻土,随后下令大面积种植传闻中可以延年益寿的油麦菜,最后鼓动全村人挖渠引水。为了筹集工程款,村长组织男人们到教火院卖皮,鼓励女人们到城市里“卖肉”,然而这样的努力到最后却没能阻止喉堵症的蔓延。《日光流年》是一出生命的悲剧,书中每一个人为了活下去与命运抗争。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一样,三姓村人将砸向生命的巨石一次次推向山顶,但却一直惨遭失败,可他们并未放弃。不难想象,村里还会有新的村长被选出来,为领导全村人反抗死亡而奋斗。阎连科通过表现人们愈是脆弱、愈是失败、愈要反抗的原始生命力量,突出人性求生的本能以及引发的强烈的生存欲。学者孙郁以《日光流年》为例,将阎连科的小说命名为“寓言体”,“《日光流年》通篇是寓言体的,一种苦难套着一种苦难,一个悲剧接着一个悲剧,情节的离奇和意绪的幽微,超出了人们忍受的限度。”[3]与病症抵抗的过程突显了三姓村人生命的韧性。人性中对生的渴求和由此激发出的强大力量,是这个具有鲜明寓言色彩的故事的核心。作者笔下三姓村人西西弗斯式的抗争也带给了读者一种生命的悲壮之感。
二、构建权力乌托邦
饥饿带给生命的威胁使阎连科萌发对生存的执念,同时因饥饿产生的痛苦与折磨也催生了作者内心的权力情结。对“权力”的书写与阎连科儿时的经历有关。当饥饿的威胁笼罩着整个村庄时,幼小的阎连科却观察到干部及其家庭并未受到饥饿的煎熬。难耐的饥饿,驱使阎连科萌发了对权力的向往。他曾表示:“一切少年的美好欲望,因为不能实现,都成为了我理想的乌托邦,都在我笔下遭到了批判和颂扬。”[1]256于是,作者开始构建自己的权力乌托邦,在人物身上融入其个人成长记忆中的权力欲。他能结合当下现实,在寓言体的书写中表露人性的真实。
阎连科早期的小说《两程故里》以村长选举为线索。老村长程正顺一心为村,心底里希望自己能够连任村长。在大跃进时期,程正顺拿着全村粮仓的钥匙,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媳妇饿死在仓库边上;在他重病时,炕席下的奖状或成功当选人大代表的消息便是他的治病良方。但他最终被自己落选的真相打击致死。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执著于权力的老村长形象。书中的另外两个人物天青和天民,为了竞选村长,不断勾心斗角,他们表面不喜形于色,内心里却波涛汹涌。为追逐权力,每个人都戴上了面具。作者以全知视角向读者展示了伪装之下的明争暗斗,揭露了隐秘真实的人性。
《受活》中的柳鹰雀更是一个嗜权如命的典型形象。他在有着浓厚革命气氛的社校长大,自小接受的革命理论促使他早早就形成了权力意识。成为柳县长后,为了带领受活庄人发家致富,他想出从俄罗斯买回列宁遗体并以此建造景点来致富的荒唐方案。为筹备“购列款”,柳鹰雀将庄里的残疾人组织成一个绝术团到各处去表演。内心不断膨胀的权欲,驱使他在家里秘密设置敬仰堂,将自己的画像与时代伟人摆放在一起。小说最后,当有人打开用于安置列宁遗体的墓坑时,惊奇地发现,柳鹰雀在这个墓坑的旁边也为自己修了一座墓。疯狂的权欲,已让柳鹰雀丧失了做人最基本的理性。他一步步地构建起自己权力的乌托邦,在空想的大道上越走越远。在柳鹰雀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笔下靠“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的阿Q的影子。学者刘再复认为这个人物形象的象征意蕴不仅指涉中国国民性,还指涉着人类的一种普遍的人性弱点,这就是天生热衷于押宝、赌博、冒险的赌徒特点。[4]阎连科给予柳鹰雀县长的身份设置,使其将个人虚妄的欲求发展到极致。结尾“天堂梦”的破灭与最初的雄心壮志形成鲜明对比。如此荒诞的情节让人想起奥威尔的《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等政治寓言小说。更有学者直接将《受活》评为中国的政治寓言小说的杰作。[5]31巧妙的是,作者最后写到带来都市文明的柳鹰雀在经历大起大落后,这个都市文明的积极传播者反倒故意让汽车压断双腿,决意落户与世隔绝的受活庄。这样的情节转换表达了作者对纠缠于仕途之人的讽刺,也使作品神实风格中的“内真实”真正产生了“公共意义和政治批判力量”。[5]45这正是阎连科寓言化书写的目的之一。
阎连科的新作《炸裂志》被誉为一部关于政治讽刺的“奇书”。“炸裂”原是一个村,随后变成了一个镇,又发展成一个县,最后竟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这样一个“裂变”传奇的完成,村长孔明亮功不可没。而他正是父亲寓言中可以当皇帝的儿子,从最先变成“万元户”当上村长,到最后成为野心勃勃的大政治家。正是孔明亮不断膨胀的野心使他在权力的金字塔上不断攀登。小说构建了以孔明亮为中心的权力乌托邦,支撑其乌托邦的是炸裂村的飞速发展。阎连科在疯狂叙事中表现了一个村庄荒诞的发展史。由村到国际大都市的迅速扩张,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人理智、精神的裂变以及道德的沦丧。病态扭曲的人性催生了一系列荒诞魔幻的情节,人心的迷失使小说蒙上了一层“狂欢”的色彩。阎连科为荒唐滑稽的情节构建了一个合理的世界,这个世界与现实的逻辑背道而驰,将一切不可能都变为了可能。在这个迷狂的世界中,阎连科决心“摆脱唯一的震惊的逻各斯”,“要用震惊的连环套,让小说高潮迭起,呼啸而去”。[6]30最后呈现给读者的小说已然具有“浓重的神话色彩”。[6]30作者借“炸裂”神话表露心灵真实,假托寓言呈现出一场荒诞的“裂变”大戏,最终在城市的非常态发展中逼近狂热追逐权力与政治乌托邦的人性真相。
三、城市的无尽诱惑
城市对幼年的阎连科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当年写作的初衷正是想逃离土地。对于这种心理,阎连科曾坦言:“对城市的崇拜,最具体的就是从小上学你身边就坐着一个你不敢和人家说话的城市小姑娘,然后出去打工,觉得城市满眼都是高楼大厦,他们的衣着、谈吐、生活方式都和自己不一样,不由你不对城市产生一种向往与崇拜。”[7]城市生活好似是一种参照标准,每个人都要去城市闯荡一番来证明自己。而乡土在阎连科笔下的人物看来,是一个迫切想要甩掉的包袱。作者正是抓住了人们这种膨胀的时代欲望进行深入挖掘,以达到自我反思和批判病态人性的目的。
在《最后一名女知青》中,女知青娅梅因为命运的安排离开了都市,在能够回城时又因为爱情留在了乡村。后来,丧子的悲痛与商品大潮的冲击使她返城,在获得巨大的名利后她顿悟自己实际上一无所有。最后,在韶华逝、容颜改之时,她又回到了乡村定居。在小说的结尾,娅梅最终选择回到乡村时,才发现原本熟悉的那片土地早已是物是人非。她本想与丈夫重温旧梦,可丈夫却要跟随另一个女人到城市去。主人公从对城市的向往,到“城市梦”的实现,再到最后的幡然醒悟,背后隐藏的是作者对乡土的悲悯情怀。逃离乡土是出走的动力,回归乡土是安歇心灵的必需。
在长篇小说《炸裂志》中,“炸裂”这个小乡村发展成一个国际大都市的过程,是中国村庄的裂变。人们以先进大都市为信仰,城市的裂变亦催生了人们精神的骤变。这部小说看似荒诞与魔幻,却写出了当今社会背景下人们内心最真实的急不可耐的欲望。作者借时代变迁的巨变,展示了人的狂野欲望及其带来的痛苦。阎连科对于城市的态度已然转变,他借寓言化的书写进行理性反思,批判过快的城市化进程中人性的扭曲与病态。
阎连科少年时期对生命、权力与城市的三个崇拜一直是他内心深处的渴望,由此三要素出发,作者开始书写自己在社会生活中体会到的“内真实”。为了突出“内真实”,阎连科采用了现代派表现手法,并且将寓言写作的方式作为包裹三种“心灵真实”的外衣。“寓言体”为作者肆意狂想的书写提供了无限可能,使其能够切断“小说内容和现实的直接联系”,[8]52用奇特的想象描绘出一个个独特的生命体。处于生命魔障中的个体因生存的执念不断挣扎在生死边缘;由文明边缘进入时代洪流中的人物充分暴露其内心的权欲并不择手段地追逐权力;城市化进程中急功近利地追求发展速度的人们最终却被都市文明狠狠一击,迷失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阎连科张扬肆意的书写为小说增添了一丝疯狂的气质。小说的寓言性不仅表现在匪夷所思的情节中,还表现在引人深思的结局上。褪去怪诞的故事外壳,作者呈现出时代背景下最真实的人性,“开始强调小说对于人类总体生存境遇的终极思考”。[8]52这就是作者寓言化书写的目的——借寓言体写作揭露真相,引人思考。寓言体写作使阎连科将荒诞表现到极致,增强了作品的内部张力,带给人震惊的审美体验。作者用寓言书写建构的世界中表露出来的“内真实”,也为传统的真实观开启了新思路。
(责任编辑 远 扬)
[参考文献]
[1]阎连科,张学昕.我的现实,我的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15.
[2]谢有顺.极致叙事的当下意义——重读《日光流年》所想到的[J].当代作家评论,2007(5):41-49.
[3]孙郁.日光下的魔影——《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读后[J].当代作家评论,2007(5):18-24.
[4]刘再复.中国出了部奇小说——读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受活》[J].当代作家评论,2007(5):38-40.
[5]陶东风.《受活》:当代中国政治寓言小说的杰作[J].当代作家评论,2013(5):31-45.
[6]陈晓明.“震惊”与历史创伤的强度——阎连科小说叙事方法探讨[J].当代作家评论,2013(5):30-45.
[7]梁鸿,阎连科.巫婆的红筷子[M].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23.
[8]葛红兵.骨子里的先锋与不必要的先锋包装——论阎连科的《日光流年》[J].当代作家评论,2011(3):47-54.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454(2016)03-0054-04
[收稿日期]2016-04-28
[作者简介]聂媛媛(1993-),女,山西晋城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间信仰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编号:14BZW136)以及湖南省教育厅课题“从20世纪中国文学看民间信仰与民族国家话语的关系”(编号:13C56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