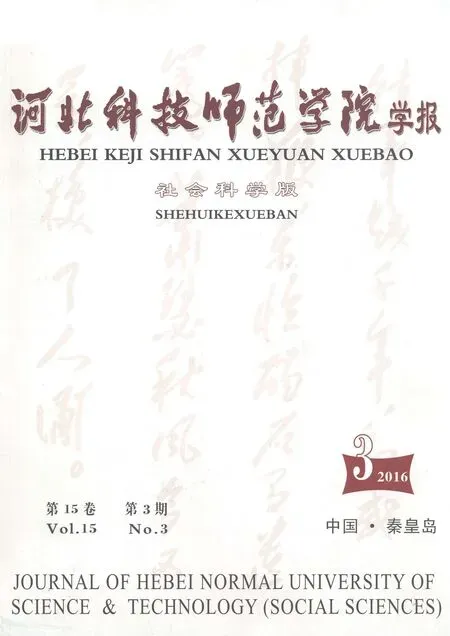隐喻与语言关系探析
——以《沙恭达罗》为例
王宝迪
(山东大学(威海) 文化传播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
隐喻与语言关系探析
——以《沙恭达罗》为例
王宝迪
(山东大学(威海) 文化传播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
隐喻作为一种普遍现象,自人类文明发展之初就引起研究者的关注,然而对于隐喻的起源问题,研究者往往各抒己见、莫衷一是。通过分析希腊、印度和中国早期文论中对于隐喻与语言起源关系的阐述,发现在人类早期的认知中存在着两种隐喻观,即古典主义的隐喻观与浪漫主义的隐喻观。本文结合印度梵语文学时期的戏剧《沙恭达罗》,在对其中的隐喻现象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浪漫主义的隐喻理论在对隐喻起源的问题上把握得更为合理。
语言的隐喻;隐喻的语言;《沙恭达罗》
一、隐喻的语言与语言的隐喻
对于隐喻本质问题的看法往往体现着人们对于隐喻与语言起源关系的认识。在传统的隐喻研究中,隐喻往往被看作文学语言之根本,是增加语言诗意性的必要元素。因此,文学语言与隐喻有着内在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这种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观念把隐喻看作一种基本的形象化语言,也即是一种修辞性的语言,是存在于语言这个“先在”概念之中的,这种观念下的隐喻是一种语言的隐喻。此外,还存在一种浪漫主义的隐喻观,他们认为语言在诞生之初就是隐喻的,因此他们认为隐喻本身就是隐喻的语言。传统认识中对于隐喻与语言的关系,主要存在这两种观点。
(一)语言的隐喻——隐喻作为语言的修饰
1.希腊:古典主义隐喻观
古希腊以亚里士多德的隐喻观为导向开创了古典主义的隐喻观。在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中,他把语言分为三个类别:逻辑的、修辞的和诗的。按照他的哲学理念来理解,这三个范畴可以被看作彼此之间独立存在的项。这种划分意味着在他看来,诗的语言有别于逻辑的语言和修辞的语言。“诗极大地依赖隐喻,与此相对,逻辑和修辞把‘明白晓畅’和‘循循善诱’作为它们各自的目标,并且,尽管它们为了某种效果,也可能时不时地来一个隐喻,但是,它们紧密地与散文媒介和‘普通’语言的结构联系在一起。”[1]9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始终认为语言的“普通的”或“散文性”的使用不同于“鲜明的”或“诗性的”使用。
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隐喻本身是作为添加在语言之上的装饰而存在的,人们可以在需要的情况下进行适当的添加。“他认为‘明白晓畅’属于‘普通’语言,它是非隐喻性的;而隐喻是一种造成特殊化和生动化的因素,是一套‘陌生的用法’,这些用法‘由于与通常的习惯说法不同’,可以‘把言语提高到日常语言的境界之上’。”[1]12也就是说,隐喻是从语言的日常使用过程中分离出来的,是不同于日常语言“明白晓畅”的特点的,亚里士多德从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出发,将语言“必然”存在着的“理性化”状态视为语言的本源,隐喻则是为了增加语言的表现力而派生出来的一种语言的附属状态。
在亚里士多德之后,西塞罗、贺拉斯、朗吉努斯分别站在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古典主义隐喻观”的阵营中对隐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但是在看待隐喻与语言的关系问题上,这一派的研究者都认为语言先于隐喻而存在。
2.印度梵语文论
印度古代梵语文学历史悠久,大致分为3个时期:吠陀时期、史诗时期和古典梵语文学时期。约在公元前后1世纪,也即印度文学由史诗时期到古典梵语文学时期的过渡阶段,梵语文学进入一种自觉的状态,梵语文学家开始以个人的名义进行独立创作,并引起梵语学者对梵语文学的性质和特征进行思考和总结,也就产生了大量的梵语文学理论,其中不乏对语言与隐喻等文学现象的理论探索。《梵语诗学著作汇编》中的《诗探》就曾论述过诗的起源与语言的问题。
《诗探》第三章这样讲述“诗原人的诞生”:娑罗私婆蒂(语言女神)渴望儿子,在雪山修炼苦行。大神梵天心中感到满意,对她说道:“我为你创造儿子”。这样,娑罗私婆蒂生下儿子“诗原人”。“诗原人”起身向母亲行触足礼。出口成诗:
世界一切皆由语言构成,展现事物形象,
我是诗原人,妈妈啊!向你行触足礼。
娑罗私婆蒂满怀喜悦,将他抱在膝上,说道:
“孩子啊!虽然我是语言之母,你的诗体语言胜过我这位母亲。音和义是你的身体,梵语是你的嘴,俗语是你的双臂,阿波布朗舍语是你的双股,毕舍遮语是你的双脚,混合语是你的胸脯。你有同一、清晰、甜蜜、崇高和壮丽的品质(诗德)。你的语言富有表现力,以味为灵魂,以韵律为汗毛,以问答、隐语等等为游戏,以谐音、比喻等等为装饰(庄严)。”[2]10
作为文学化身的“诗原人”是语言女神的儿子,作为文学创作之方法的谐音、比喻等是“诗原人”的装饰,从这种对于语言和诗的论述中,可以认识到古代梵语文论在对于语言、对于隐喻的看法上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一派的观点有很大的相同之处。他们都很崇拜语言,梵语诗人将语言尊为女神,并且在作品开头总是要先传统性地对语言女神进行一番虔诚的吟咏。而对于隐喻的态度,他们尽管很是赞赏其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但都是将隐喻视为诗的附属,是语言的派生物,是“语言之子”的一种外在修饰。而这也是印度梵语文学理论中对隐喻与语言关系的一致看法。
3.中国先秦文论
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对于隐喻与语言关系的阐述也表现出与希腊古典主义隐喻观、与印度梵语文论相同的特点。他们普遍将隐喻看作是一种修辞,就隐喻与论辩、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进行阐述,其中他们更加注重隐喻在语言表达上的实用性。
先秦时代,我国社会处于重要的变革时期,诸子百家为了宣扬自己的学说,纷纷采用语言的技巧来弘扬自家的政治主张,这使得人们尤其重视隐喻在辩论中的作用。《礼记》中曾这样对隐喻进行了强调:“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说明君子“为师”“为长”甚至“为君”都要以博喻为条件,即需要能言善辩,掌握包括隐喻在内的各种语言技巧。除此之外,《礼记·学记》中“不学博依,不能安诗”的说法也指明了在诗歌等文学作品中隐喻具有重要作用,郑玄指出,“博依”即“广譬喻”,这种说法表明对隐喻的成功运用决定了文学创作的水平高低。
由于古代学者重视隐喻的实用功能,因而在对于隐喻和语言的关系问题上关注得较少,即使存在零散的理论,也并不是从语言学层面对隐喻产生的深层原因进行阐发,但是对于隐喻能够弥补语言缺陷的功能早期学者还是具有较为清楚的认识的。例如西晋的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言拙而喻巧”的思想,揭示了隐喻表达的产生原因是由于人们在表达特定思想情感和认知体验时面临困难和局限,没有现成的语言材料可以使用,因此用隐喻来对语言进行“加工”。
从以上对三种文论的列举中可知,无论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古典主义的隐喻观,印度的梵语文学理论,还是古代中国的文学理论,都是将隐喻视作为语言的一种后天、附属性的存在。在对隐喻与语言关系的认识上,他们都将隐喻看作是语言的隐喻,即是一种装饰性的语言表达方式。
(二)隐喻的语言——语言之初就是隐喻性的
与上述观念不同的是,古代希腊以柏拉图为源头而开启了浪漫主义一派的隐喻观。他们不认同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主义隐喻观”,即认为隐喻从某方面看是与语言分离的,是可以添加在语言之上的一种修饰手段,它配合语言完成某种具体的表达功能。在他们看来,隐喻与语言存在着一种整体“有机”的关系,隐喻是语言诞生之初的形态。
1.柏拉图:有机统一原则
与亚里士多德不同,柏拉图并没有明确地解释过语言,也没有明确地解释过隐喻现象,但是他阐发了“完全偶然的、派生的自然”这一观点。柏拉图最明确地阐发过的艺术原则之一是:有机统一原则。他在《斐德若篇》中说,每一篇作品都应该“创造得像一个有生命的物体一样”。“也就是说,它一旦被分解成它的组成因素,它就毫无意义,这些因素联系在一起才构成了整体。”[2]50与此类似,语言是一个整体,他并不把修辞语言从诗的语言中分开。
柏拉图的“这些观点该当包含着一种思路,浪漫派诗人因而被吸引到比谁都狂热地宣称自己是诗人的敌人的哲学家身上来”[1]49。于是,浪漫主义者从柏拉图隐约触及到的隐喻与语言的内在同一关系出发,展开自己的理论阐述。
2.浪漫主义者的论述
浪漫主义的隐喻观从语言的源头出发探讨隐喻与语言的关系。在他们看来,语言自诞生起就是隐喻性的。
卢梭在其《论语言的起源——兼论旋律与音乐的摹仿》中提出,“最初的语言必定是象征性的”[3]318。在他看来,人的语言产生于激情,若不是为了表达爱、憎、怜、怒,人类完全可以用肢体语言完成基本的交流,正是为了传达激情,走向联合,人类才慢慢发展出带有激情的语言,而这种激情源于对事物认识上的诧异,因此其中必然包含着原始人的创造性想象。因而他认为语言自开始就是修饰性的,就是隐喻的。“古老的语言不是系统性的或理性的,而是生动的、象征性的。我们以为第一个开口说话的人的言语,是一种几何学家的语言,可是在实际上,那是一种诗人的语言。”[3]14也就是说,在卢梭看来,隐喻是语言的原始状态,并不是语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是语言的附属品,而是语言的本源。
德国批评家赫尔德在他关于语言起源的著作《论语言的起源》中也将言语本身的起源与隐喻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最早的语言是一部心灵的字典,在其中,隐喻和象征联合起来,“整个丰富多样的神造的自然正是一位语言教师,一位缪斯女神!”[4]现代的诗人其实也是原始人的,他们不仅呈现意义,或模仿自然,而且创造意义和自然,正如野蛮人创造教诲性传说和神话一样。
在此之前,意大利法学家和修辞学家维柯在《新科学》中认为,原始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诗的”能力,它通过隐喻、象征和神话向现代抽象的和分析的思维模式发展[5]。我们生活在一个我们的语言为我们设计的词语的世界里。在这里,我们的头脑被语言的属性所塑造,而不是语言由讲述着它的我们自己的头脑所塑造。
在此之后,雪莱、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人也纷纷表达了相同的观点。雪莱如此论述道,“自有人类便有诗”[6]119,并且,“语言本身就是诗”[6]122,而“语言原是武断地由想象产生的,仅仅与思想发生关系”[6]123。华兹华斯在他的《抒情歌谣集·序言》中表明了他对语言本身就充满隐喻性的认同[7]。柯勒律治同样认为,“名副其实的所谓人类语言的最好部分,是源于心灵本身活动的反映。它是通过故意使固定符号专用于内在活动、专用于想象的过程和结果而形成的。”[8]总之,浪漫主义的隐喻观认为,语言在开始阶段就是隐喻性的,语言在本质上就是“隐喻的语言”、“诗性的语言”,因此语言不可能有什么办法“洗净”隐喻。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隐喻的世界里,这是在凭借语音交流的语言诞生之初就确定了的,源自于原始人对世界神秘之象、莫明之物的想象性认知,人类也正是如此才具有合理性地创造了神话。因此,是人类自身造成了这个语言的世界,在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具体地经验着它,而当我们迷失了的时候,才认为我们自己是彼此分隔的存在,并把自然置于大脑的对立面,就象客体对主体、事物对思想、死亡对生存。这是抽象的知识,或仅限于理解的科学。但同时,具体的知识也承认其“有限的形式既不能被把握,本身也不是实在的什么,仅仅是一种领悟,一种框架”[9]243。
也就是说,浪漫派的革命根本在于强调人与自然世界的具体联系。他们对发展到他们那个时代的语言现象进行了揭秘式地溯源与分析,而不像古典主义一派,“理性化”地将发展到他们那个时代的语言看作语言现象之初,对其中包含着的发生了部分“隐喻脱落”现象的语言,以及发展到那个时代已经定型为“死隐喻”的语言,他们采用了视其为语言源头的认识方式,因此恰好颠倒了语言与隐喻的关系。
(三)隐喻与语言关系之我见:语言之初就是隐喻性的
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古典主义隐喻观”与柏拉图开启的“浪漫主义隐喻观”的区别,就像拉斐尔在壁画《雅典学院》中形象性地描画出的柏拉图手指上天而亚里士多德手指大地。在这两种隐喻观中,笔者更为认同浪漫主义的隐喻观。虽然柏拉图对于隐喻与语言起源的论述不多,也不像亚里士多德的理论那样自成系统,但其后来者的探索与阐述,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近于早期人类认识世界的思维模式,提供了一种理解语言起源与文学隐喻现象的更加自然的角度。
考察印度梵语文学时期的文学理论,发现他们曾经就隐喻与语言的问题展开过系统地界定与分析。文论家们将隐喻视为“庄严”的一种,对隐喻与语言的看法,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主义的隐喻观。但是笔者在具体的文本阅读中发现,虽然梵语研究者一致性地选择从语言修辞的角度研究文本中的隐喻,但其具体的文字创作却客观地表现出语言自起源之初就是诗性的特征,浪漫主义的隐喻观在此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为合适的解读方式。
二、语言之初就是隐喻—— 以《沙恭达罗》为例
(一)“庄严论”与《沙恭达罗》
1.“庄严论”
印度随着古典梵语文学的产生,进入了文学自觉时代,诗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早期梵语诗学的存在和发展一方面依傍梵语戏剧学,另一方面也借助梵语语言学。梵语语言学认为语言是‘音和义的结合’。早期梵语诗学直接继承这个命题,认为诗是‘音和义的结合’。但诗的语言和一般语言的区别在于诗的‘音和义’是经过装饰的。因此,梵语语言学探讨如何正确地运用音和义,而梵语诗学探讨如何正确地装饰音和义”[9]243。也就是说,在古代梵语的文学理论中,文学家认识到诗的语言是不同于日常用语的。对于文学作品的创作,掌握好对于语言的装饰尤为重要。因此,也就吸引了当时的大批理论家对文学语言的修饰问题展开研究。
婆罗多在《舞论》中最早对梵语文学的性质和特征进行了探讨。“在《舞论》第十七章论述了三十六种诗相、四种庄严、十种诗德和十种诗病。”[9]244六、七世纪《跋底的诗》以叙事诗的形式介绍了三十八种诗歌修辞方式。7世纪婆摩诃的《诗庄严论》是现存最早的脱离梵语戏剧学和语法学而独立的诗学著作。此后,相继出现了檀丁的《诗镜》、伐摩那的《诗庄严经》、优婆吒的《摄庄严论》和楼陀罗吒的《诗庄严论》等。这些著作都围绕“庄严”而著,探讨对文学语言的修饰问题。
“庄严”一词的本义是装饰或修饰,译作“庄严”是沿用汉译佛经的译法。《华严经探玄记》谓“庄严有二义:一是具德义,而是交饰义”。“具德”是指具备品德或功德。“交饰”同校饰,即装饰。狭义的“庄严”是指比喻、隐喻、明喻、双关等修辞方式,广义则指装饰诗或形成诗美的因素。9世纪后,随着梵语诗学中味论和韵论的崛起,“庄严”一词专指修辞方式[2]255。而隐喻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
2.“庄严论”下的《沙恭达罗》
分析印度梵语文学理论中对“庄严论”的研究,可以发现研究者在具体分析“庄严”时具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对一些“庄严”一分再分,不断地扩大其外延,意欲创造一套最为完备的理论系统以求涵盖任何一种具有语言修饰现象的表述。檀丁把明喻分为32种,包括性质明喻、本事明喻和原因明喻等。曼摩吒把明喻分为19种不完全的明喻和六种完全的明喻,毗首那特把明喻分为21种不完全的明喻和六种完全的明喻。在这种研究之下,对于隐喻现象的分析越来越细化,但也使研究角度越来越狭隘。这种研究建立在将隐喻看作一种语言的装饰现象的前提下,文论家为了研究而研究,各执一词的分类与阐述在推动“庄严”研究的同时,另一方面造成研究视角上的狭窄,将精力全部集中在对于语言修饰现象的研究,而缺乏对“庄严”现象的探源以及对“庄严”与语言关系等方面的探讨。
梵语文学时期将“庄严”看作是对语言的修饰,正如欢增在《韵光》中所说:“庄严是主者(味)的魅力因素,如同外衣的装饰美化人体。作为表示义的庄严,包括前人已经说到的隐喻等等。”[2]255此外,他还提醒人们要“始终记住庄严是为辅者,而不是为主者。必要时使用它,必要时放弃它。不要过分热衷于它。努力保持警惕,让它处于辅助地位”[2]255。在这种观念下,欢增结合《沙恭达罗》的隐喻来阐释其“庄严”观点:
你一再接触她移动的眼角,颤抖的眼睛,
在她耳边飞来飞去,仿佛悄悄诉说柔情,
不顾她挥舞双手,狂饮那欢乐的源泉嘴唇,
蜜蜂啊,我们未能探明秘密,你倒获得成功![2]256
欢增认为在这首诗中,对蜜蜂的如实描写,这种自性庄严与味协调一致。注释补充说,除了自性庄严,这首诗中还是用了较喻,即主人公将自己与蜜蜂作比较。
从欢增的分析可以做此推断,无论任何一种存在着语义转移现象的语言表达,梵语文论家们都可以从隐喻的角度进行无限细化,并能自圆其说。上述《沙恭达罗》的例子,诗人迦梨陀娑在对蜜蜂的情态描写中完全倾注了人类的特点,带给读者一种自然状态下人与其他生命和谐共处、万物同一的感受,自然地对“万物有灵”的生存状态进行呈现。蜜蜂这种生物在这种表述之下,体现出与人类世界的共通性,即都渴慕美丽的女子,渴慕爱情。或者,可以做这种理解,早期人类在语言的使用中,根本就不存在蜜蜂世界与人类世界之间的主客截然区分。因此在对这种语言表达的分析上,自性庄严、较喻、明喻、强喻、弱喻、相似隐喻等无尽的划分也就有些“吹毛求疵”了。因为人类语言涵盖了对神秘的世界万物的各种认知,人类往往是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关照自身,在对比中理解异同并进行语言创造,世界复杂多变,语言也复杂多变,那么文论家兢兢业业地试图对隐喻现象进行逐一地界定也就只能是一项永远“在路上”的工程了。《梵语诗学论著汇编》中的《诗镜》作者也承认,“隐喻和明喻的种类无穷无尽,这里只是指出方向。没有说到的,智者们可以依次类推。”[2]172这样一种研究思路也就使其关注点仅仅停留在对现象的罗列上而难以上升到对理论的根本把握。
(二)浪漫主义隐喻观与《沙恭达罗》
笔者在精读《沙恭达罗》文本的基础上,对其中较为明显的隐喻表达进行了逐一的分析,发现在文本中共有140处运用了隐喻。这里的隐喻主要包括传统修辞学认知范围内的隐喻(狭义)、使用明显标志如“像”“如”“似”“仿佛”等的明喻,需要结合语境分析的整体性隐喻以及已经将隐喻内化了的词汇,此外还包括传统修辞学研究中未涉及到的呈现出“万物有灵”特点的语言现象。围绕主题,即对于隐喻与语言本源关系的揭示,本文重点分析为传统隐喻研究所普遍忽视的呈现出“万物有灵”特点的语言使用现象。
1.“万物有灵”与隐喻
早期人类在对世界与自我的认识过程中,形成了“灵魂”观念。之后,他们常常把这个观念从人自身推及到与自己生活有关的万物之上,认为它们也和人类一样拥有灵魂,并支配着它们的活动。
18世纪著名的哲学家休谟在其《宗教的自然史》一书中对这种人性的自然倾向作出过深刻的分析:人类中有一种普遍趋向,要把一切存在者设想为像他们自己那样,要把他们熟悉了解的和亲密意识的那些性质转移给每个对象。……于是,毫不奇怪,当人类被置身于这样一个对原因绝对无知的状态中、同时又如此急切关怀他们的未来命运时,他们就会立即承认对拥有情感和理智的不可见的力量的依赖性。他们不断思想的那些未知的原因总是出现在同一个方面时,就全部被领悟为属于同一个种类或种族。不用多久,我们就把思想、理性和激情、有时甚至把人的肢体和形象归于他们,以便使他们更接近于与我们自己的相似性。[10]
也就是说,早期人类的认知过程是在对自我与外在事物的对比中进行的,他们对自身与外物进行对照,寻找异同,并进行创造性地归类与同一性地分析,这种观念当然也影响到早期语言发展的形态。因此也就更能理解出现在《荷马史诗》中类似于“牛眼赫拉”一类的隐喻。在人类早期思维中,这种表达可能完全只是一种自然而客观的描述,在他们看来这种表达并没有运用到任何的修辞,人和非人的生命体就是可以在异同比较的基础上进行类似的关照[11]。而传统的隐喻研究往往会做出如下的分析:诗人生动形象地运用了比喻的手法,用生物的特征来形容人。在这里,本体是人的眼睛,喻体是牛的眼睛,通过这种手法突出人的眼睛像牛的眼睛一样大……后人之所以会产生对此一问题的偏离,与人类不断发展的理性认识有关。人们在对隐喻语言的长久使用中,对部分隐喻现象进行约定俗成,使得隐喻语言出现了具有当时的时代特征的理性化“变异”,从而使作为语言本质的隐喻与最初状态相比,出现了部分的隐喻“脱落”,导致后人面对这种语言,大胆地运用他们的理性进行了本末倒置的分析。对此现象,我国的钱锺书先生曾有过极为经典的阐述:
“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不过是一种比喻、象征的、像煞有介事的、诗意的认识。用一个粗浅的比喻,好像小孩子要看镜子的光明,却在光明里发现了自己。人类最初把自己沁透了世界,把心钻进物,建设了范畴概念;这许多概念慢慢地变硬变定,失掉了本来的人性,仿佛鱼化了石。在自然科学发达,思想家把初民的认识方法翻了过来,把物来统治心,把鱼化石的科学概念来压塞养鱼的活水。”[12]
这里的“象征的、像煞有介事的、诗意的”都指“隐喻”。钱锺书先生的这段论述也表明在对待隐喻的问题上,传统的修辞学研究的确存在源流把握上的偏颇。先民在“万物有灵”的思维模式下,本着自然描述的心态将认识对象视为与自身同一的存在,而这种认知被后人的理性所遮蔽。因此我们需要对于传统修辞观认识下的语言现象进行重新审视,厘清隐喻与语言起源的关系对于进一步深化隐喻研究尤为重要。
2.“万物有灵”特点的隐喻
在对《沙恭达罗》文本中出现的140例隐喻使用现象的分析中发现,具有“万物有灵”特点的“隐喻”共有27例,约占五分之一,可见这种语言现象在《沙恭达罗》时期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现进行逐一地列举与分析:
(1)你的箭不应该射向鹿的柔弱的身躯,
这简直是无端放火把花丛来烧。
哎!鹿的生命是异常脆弱的,
你那如飞的利箭,它如何能受得了?
(2)微风吹皱了的河水冲洗着树根。
(3)朋友沙恭达罗呀!我这样想:我们的父亲干婆对净修林里的树木比对你还更加爱护……
(4)朋友阿奴苏耶啊!这不仅仅是由于父亲的命令,我爱这些花木象爱我的姊妹一样。
(5)那棵小芒果树的嫩枝给风吹着象小指头似地摆动,仿佛是在招呼我。我去向它致意。
(6)你站在它跟前,它就仿佛有了葛藤作它的保护者。
(7)这一棵小茉莉花是被你称做“林中之光”的,它自愿作芒果树的老婆。
(8)草木都在成双成对地相拥抱结婚,真可爱呀!
(9)小茉莉花炫耀自己的青春……
(10)“林中之光”……希望得到一个称心如意的郎君。
(11)春藤正象你一样,也是我们父亲亲手培植起来的。
(12)谁(蜜蜂)敢对贞静的静修者的女儿们有无礼的行为?
(13)我的身体走了,我那颗不安的心却跑回来。
(14)我伸开胳膊把微风抱住。
(15)豆扇陀给你女儿种上了光明种子,正如怀火的舍弥树。
(16)树木也是沙恭达罗的亲属,它们现在送别她,
杜鹃的甜蜜的叫声就给它们用作自己的回答。
(17)你也注意一下在你离别时净修林的情况吧!
小鹿吐出了满嘴的达梨薄草,孔雀不再舞蹈,
蔓藤甩掉褪了色的叶子,仿佛把自己的肢体甩掉。
(18)蔓藤妹妹呀,用你的枝子,也就是用你的胳臂,拥抱我吧。从今天起我就要远远地离开你了。
(19)我想把附近的那棵芒果跟蔓藤结成姻缘。
(20)朋友呀,在我们净修林里,没有一个有情的动物今天不为了你的别离而伤心。你看呀:
那野鸭不理藏在荷花丛里叫唤的母鸭,
它只注视着你,藕从它嘴里掉在地下。
(21)象蜜蜂破晓时飞绕含露的君陀花,我既不能丢开她,又不能吸吮她的芬芳。
(22)喂,雄峰呀!你为什么不辞劳苦地飞来飞去呢?
那一只含情脉脉的雌蜂虽然渴了仍然落在花朵上,
她在等着你,否则她就会孤零零地去吮吸蜜浆。
(23)我就把它藏在那里,交给斑鸠看守,另外任何人也看不见。
(24)阿噜诺(朝霞)如何能够驱除夜的暗影,
假使千光的太阳不把他带在车中?
(25)孩子呀!把这野兽的太子放了吧!我要给你一件玩意儿。
(26)好哇,亲爱的!我的记忆恢复,你又站在眼前。
月蚀之后,卢醯尼又同月亮在一起团圆。
(27)那么就让蔓藤再与它的花朵结合吧,它愿意同春天在一起。
以上列举的27例隐喻现象,虽然在具体的语言表达形式上存在差别,但是在字里行间都营造出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万物相融相通的和谐的生命状态。例(1)、例(3)、例(4)、例(5)、例(6)、例(11)、例(12)、例(23)、例(25),用一致的态度对待人类和非人类的生命体,彼此之间不存在物种、本性、等级、高低上的差别,而且这种态度的倾入是自然的、内在的。例(2)中的“皱”,极为确切地刻画出微风吹拂下的水波状态,其意义范畴包括一切具有此类特征的事物,而非现在提到这个词就条件反射似地反映出,此词用于对人的特征的修饰。例(13)、例(14)也有此特点。例(7)、例(8)、例(9)、例(10)、例(19)、例(21)、例(22)、例(27),都描写了非人类的生命体所同样存在的爱情与婚姻状态,他们同样渴慕佳偶,同样希求爱情,这种表达自然而生动。例(16)、例(17)、例(18)、例(20)则描写了人与非人类生命体离别时,它们产生的“不舍”感情。在它们的世界里也有亲情友情,体现了一种“万物同情观”。 例(15)、例(24)、例(26)则体现了在隐喻发展过程中,早期“万物有灵”思想与其后产生的神话内涵相结合而发展到的隐喻表达新阶段。
从以上对27例具有“万物有灵”特点的语言使用现象的分析中,能够认识到隐喻从作为本原状态的语言到其本质发生部分地“脱落”,从纯粹自然描摹性的语言到注入神话、宗教等因素的语言发展新阶段的转变。这种转变过程与人类思维、理性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应该承认发生这一转变是语言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理性、线性以及主客二分的认知方式,不断攀升并发展到“万物之灵长”的自然界地位,不断得到自身确认并极力发扬乃至膨胀的“主体性”,使人类不断地质疑在“万物有灵”的认知基础上建立的宇宙运行的神话,不断地冲击神秘想象状态下创造的隐喻语言世界,使得隐喻逐渐从语言的初始状态一步步“脱落”为一种装饰语,一种表达方式,一种修辞技巧。
三、由隐喻的语言到语言的隐喻
(一)语言发展之必然
由隐喻的语言到语言的隐喻,隐喻在创造了语言与认知之后逐渐“退居后台”,在修辞学方面维持着自己的影响力。对应于人类主体性及理性的发展,隐喻在概念范畴上的逐步窄化是语言发展之必然。对比隐喻在《沙恭达罗》与中国的《西厢记》中的使用状况便可以略知一二。
中国的《西厢记》作为一部发展得比较成熟的戏剧作品,在时间上晚于《沙恭达罗》近800年,而正是这种时间跨度使得两个题材相似的戏剧文本在语言上呈现出极大的差别。分析《西厢记》中的隐喻现象可知,处于12、13世纪的文学语言已经很少出现具有“万物有灵”特征的隐喻。虽然存在着体现汉民族朴素信仰的“天”“地”的隐喻性表达,但也已经很少见,更多地是作家在创作中对文学性隐喻的信手拈来。无论是带有明显标志词,如“象”“如”“似”“仿佛”“宛若” 等,从民族朴素信仰、传统文化传说、典故中发展而来的用法,还是本体与喻体结合得更加自然的用法,隐喻在这一阶段已经完全成为一种修辞手段,这是此一阶段的人们对事物进行了完全意义上的理性化认知的结果。
(二)隐喻研究的认知转向
20世纪70年代开始,修辞研究发生转向,这体现了人们对隐喻看法的转变,即将隐喻视为人类的一种认知现象,隐喻就是以某一领域的经验来说明或理解另一领域的经验,是人们对抽象范畴进行概念化的工具。进入80年代,隐喻认知研究全面展开,并迅速引发研究热潮,隐喻成为多个学科的关注对象,逐渐进入多学科、多角度研究阶段。
当代的认知语言学在研究过程中一改传统修辞观把隐喻看成纯语言现象的观点,认为隐喻是人类普遍的认知手段,并非语言的“附属”与“偏误”,隐喻存在于人类思想和认知的各个角落。这样就把隐喻研究的重心转移到思维和概念系统中,更加趋近于对于隐喻本质的把握。
然而由于“隐喻本身具有一种嘲弄所有这类关于对其过程作粗线条的解释的直接性和生动性”[1]132,因此对于隐喻的研究仍然具有难以把握之处,正如华莱士·史蒂文斯所说:“没有什么事物能够作一个隐喻的隐喻。”[13]但是我们仍能做到立足当下的语言发展,结合前人相关的阐述与今人独立的研究,对隐喻现象做出客观的界定与认知。
[1]特伦斯·霍克斯.论隐喻[M].高丙中,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
[2]季羡林.梵语诗学论著汇编(上册)[M].黄宝生,译.北京:昆仑出版社,2008.
[3]让-雅克·卢梭.论语言的起源——兼论旋律与音乐的摹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J. G. 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5]维科.新科学[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6]雪莱.为诗辩护[M]//刘若瑞.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7]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M]//刘若瑞.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8]柯勒律治.文学生涯[M]//刘若瑞.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9]黄宝生.印度古典诗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0]休谟.宗教的自然史[M].曾晓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11]杨明,闫岫峰.隐喻、隐喻性思维与相似性思维[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90-92.
[12]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 人生边上的边上 石语[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13]转引自特伦斯·霍克斯.论隐喻[M].高丙中,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刘 燕)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taphor and the Origin of Language ——TakeSakuntalafor Example
Wang Baodi
(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Weihai Shandong 264209,China)
As a universal phenomenon, Metaphor has aroused the researchers’ attentio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s civilization.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 the metaphor, however, researchers are unable to agree with each other.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analysis in Greece、India and China’s early literary theory expounded about the relation between metaphor and the origin of language, we find that there are two kinds of metaphors in early human’s cognition, namely the classical view of metaphor and the romantic view of metaphor. This paper combines with the Indian Sanskrit literature period dramaSakuntalaand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metaphorical phenomena of Sakuntala, we think that the romantic metaphor theory on the origin of the metaphor is more reasonable.
the language of metaphor; the metaphor of language;Sakuntala.
10.3969/j.issn.1672-7991.2016.03.021
2016-04-08;
;2016-05-28
王宝迪(1992-),女,山东省济南市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H059
A
1672-7991(2016)03-01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