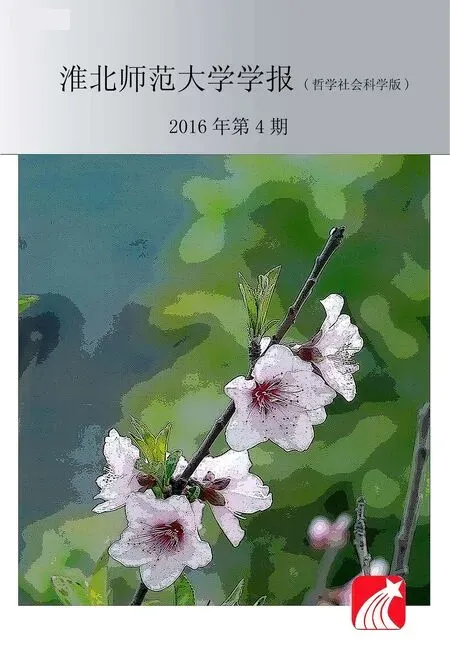论迪士尼电影《奇幻森林》的创造性叛逆
吴超平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论迪士尼电影《奇幻森林》的创造性叛逆
吴超平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迪士尼电影《梦幻森林》改编自吉卜林的《丛林故事》,影片在主题、情节与角色塑造上都存在创造性叛逆。这些叛逆由文化传统、导演个人倾向、迪士尼的传统、影片的内部机制以及电影本身的特殊性共同作用而形成。
《丛林故事》;《奇幻森林》;创造性叛逆
2016年4月15日,华特·迪士尼影片公司在中国大陆和美国同步上映了由美国著名导演乔恩·费儒执导的真人动画片《奇幻森林》。这是迪士尼公司推出的又一部大片,它拥有强大的配音演员阵容、写实的动画工艺、尖端的动作扑捉技术以及真人CG技术,上映最初一个月就创下了全球总票房8.28亿美元的辉煌战绩。
创造性叛逆是比较文学译介学中的术语,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提出。文学翻译中,文本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必然会丢失一些原语言文化的元素,同时又新增一些来自另一种语言文化的元素。这必然赋予原作一个新的面貌,翻译活动就成为一种再创造。所以,埃斯卡皮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1]今天,创造性叛逆已经不仅仅被用在翻译领域,它已经延伸到文学、文化的传播接受领域。从文本到电影,原作经历了“二度变形”,因而也被认为是一种创造性叛逆。电影《奇幻森林》是根据英国20世纪著名作家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的《丛林故事》中毛克利的故事进行的改编,它讲述了狼孩毛克利的一段冒险之旅。在丛林和狼群一起长大的毛克利,为老虎所迫不得已开始了离开丛林的旅程。但得知老虎杀害了狼爸爸后,毛克利义无反顾地回到丛林除掉老虎。然而,从文本到电影,在主题、情节、角色塑造上,创造性叛逆的存在不可忽视。
一、主题的创造性叛逆
吉卜林《丛林故事》中毛克利的故事,从不同的角度阐释可以有不同的主题。目前论界对其解读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视角,第一,从后殖民的角度来分析,这一研究视角的成果较多。例如,2013年河北师范大学张华的硕士学位论文《<丛林之书>的后殖民主义解读》、2013年内蒙古大学苑扬的硕士论文《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丛林之书>的后殖民解读》,认为《丛林故事》表达了作家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西方文化至上的思想。第二,从精神分析学角度来分析,例如,陈兵、吴宗会的《<丛林之书>的多视角研究》(载《外语研究》,2003年第5期)认为《丛林故事》表达了作家对于家和父母的渴望。第三,从成长小说的角度来分析。例如,2014年浙江大学张晖的硕士论文《<丛林故事>对青少年成长影响的研究》,认为吉卜林通过丛林动物们的故事,宣扬孩子成长过程中应该具备的智慧、勇敢、自律和团结友爱精神。第四,从文化身份的角度来分析。例如孙莉的《两栖动物——论<丛林之书>中人物的身份问题》,认为这部作品展示了毛克利对自我身份的追寻。第五,从生态的角度来分析。例如扬州大学方逍遥的《生态批评视阈下的<丛林故事>》,认为作品中的“丛林规则”富有浓郁的生态意识,表达了吉卜林渴望建立一个处于规则控制下的和谐社会的理想。
关于吉卜林《丛林故事》的主题研究,英国评论家汤姆金斯提出了“三层次”说,认为作品有三重世界,首先是儿童的游戏世界,故事中的动物在现实生活中都能找到原型;其次是寓言世界,包含一些道德教训;而比前两个世界更重要的是第三重世界,即古老久远的世界,具有神话、圣经和古老民间传说层面上的意义。[2]这充分表明,《丛林故事》的多视角解读是可能的,也提示我们:对《丛林故事》的阐释依然有待于研究者的继续努力。
与文本相比较,电影的主题简单了许多,它以毛克利的离开之旅以及回归为叙事主线,彰显了主人公对自我身份的追寻,展示了主人公的成长历程,同时赞美其在成长中体现出的真善美以及勇敢、顽强、智慧等高贵品质。当然,透过电影的画面,丛林里高耸云天的树木、淙淙流淌的小溪、活跃于其间的各种生物、与生物和谐相处的毛克利构建出一片祥和宁静的气氛,观众自然可以领会到作家浸入其中的生态思想,但这只是成长叙事的副产品。另外,影片中,毛克利被迫离开丛林后经历一场厮杀重返丛林,回到狼爸爸狼妈妈的身边,也体现了他对家和父母的渴望,但未得到完整的体现。因而,影片的创造性叛逆在于舍弃了对文本进行其他解读的可能性,以身份追寻和成长为主,来布置情节、设置角色。这也决定其影片的情节和角色的设置上必然也存在创造性叛逆。
二、情节与角色的创造性叛逆
影片中,导演乔恩·费儒对文本的情节做了大量的剪裁。在吉卜林的文本中,读者可以看到毛克利从幼儿到成年的成长故事,包括幼年时怎样来到狼群、在狼群中长大学本领,及至中间被迫回到人类村庄受到迫害又返回森林成为森林首领,最后和一个印第安女孩成家生子的过程。而在电影中,从毛克利回到人类中的故事全部被删掉,影片从毛克利离开丛林开始,中间经历了老虎的穷凶极恶的追捕、大蟒蛇卡俄的谋杀、巴鲁的采蜜生活、猴子宫殿的惊险,最后取回了“红花”,在狼群、黑豹和巴鲁的帮助下除掉了老虎,从此在丛林过着幸福的生活。电影叙述的是毛克利少年时期的一次惊险之旅,但是文本却叙述了毛克利的童年、少年和青年。在已经精简了的叙事中,导演的叛逆也清晰可见。
首先,情节上的移花接木。文本中,毛克利的身世是作家开门见山交代清楚的,但是在电影中,是以蒙太奇的手法通过卡俄讲述的。再如,影片中有一个惊心动魄的镜头:毛克利被老虎追杀不小心陷入冲锋陷阵的牛群中。这是导演浓墨重彩渲染的,体形庞大、数目惊人的牛群铺天盖地迎面冲过来,毛克利左躲右闪,上跳下蹿,好不容易才抓住牛角攀上牛背化险为夷。而这个情节在文本中出现的时间是毛克利离开丛林回归人类社会中以后,具体的情节过程是老虎追杀毛克利已经来到村庄的边缘,毛克利抓住机会,设计利用疯狂的牛群在河谷里踩死了老虎。其次,情节的增加。电影增加了很多文本中不存在的情节,例如,影片开头枯水期的动物们,自觉地进入休战状态;毛克利惯用的人类技能,用椰子壳打水喝;老虎穷凶极恶的追捕;巴鲁的采蜜生活;为了得到“红花”,唆使猴子们把毛克利带到寒穴去的黑猩猩;等等。再次,情节的删减。文本的很多情节在影片中被忽略了,例如,在把毛克利从寒穴中救出来的战役中,大蟒蛇卡俄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影片直接剪掉了这一情节。最后,情节的背叛。文本中,所有的动物都不敢与毛克利对视超过一定的时间,那是因为他的眼睛中包含的人类的智慧,这也是文本中关乎主旨的情节。但是,在影片中我们找不到它,相反,毛克利会用很真诚的目光与动物们交谈,例如,与大蟒蛇卡俄、与狼妈妈、与黑豹等。
从文本到电影,角色的塑造上进行了大的变动。首先是老虎谢利可汗形象的转变。在文本中,吉卜林赋予它胆小、愚蠢而又阴险狡猾、心胸狭隘的主要特点。它先天就是个瘸腿,这一不足使得它经常打猎失败。为了果腹,老虎经常吃饿死的耕牛,甚至去偷袭人类。这种公然破坏丛林法律的行为为狼群所不齿,它们嘲笑谢利可汗是“傻瓜”“笨蛋”。本应是丛林之王的老虎一反常态地成了狼群挖苦愚弄的对象,最后中了毛克利的圈套,被牛群活活踩踏而死。在电影中,老虎依然阴险狡猾、心胸狭隘,但威风凛凛、虎虎生威却是这一角色的主要特点。影片中,其他动物在它面前是不敢造次的,只要老虎出现的地方,动物们就是屏息静气的,连狼群也不敢轻易忤逆它的意愿,毛克利被逐出丛林就是力证。
其次,大熊巴鲁的形象更是彻底的颠覆。文本中,巴鲁是毛克利成长道路上的重要导师,它教会了毛克利丛林密语,数次在危难之中解救了毛克利,集慈爱的良师与忠诚的益友的形象于一体。但是在电影中,事情完全不是如此。毛克利是在离开丛林的惊险旅程中遇到了救命恩人巴鲁,把他从蟒蛇卡俄的致命怀抱中解救出来。但是,巴鲁精于算计,它要充分发挥这个人娃的利用价值。它哄骗人娃为自己采蜂蜜,虽然毛克利被蜇了一身疙瘩,但是巴鲁却告诉他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并利用毛克利的善良哄骗他一直做下去。直到黑豹找上门来,巴鲁才在毛克利的善良、巴希拉的斥责的双重冲击下,洗心革面,重新做熊。它为了解救被猴子抓走的毛克利,不顾掉进悬崖的危险,拖着臃肿的身躯攀爬悬崖;在猴子的宫殿中,它先是施展智慧与幽默,拖住猴群的注意力,在后来的打斗中它又充分挖掘自己体力的潜能,与黑豹协肩作战,纵然伤痕累累也要救出毛克利。影片中巴鲁的形象,经历了质的改变。
再次,就是毒蛇形象的多元糅合。文本中毒蛇有二:一是老卡俄,它阴险狡猾却又不失善良之心,在把毛克利从宫殿解放出来的战斗中给了猴群致命的一击,后来又出谋划策帮助毛克利除掉红毛狗,是毛克利的亲密挚友;二是在宫殿的地下看守财宝的毒蛇白头兜,它阴险狡猾让人不寒而栗。但是,电影中的毒蛇只有一条,那就是卡俄,但此卡俄非彼卡俄。它出现在毛克利离开森林的旅程中,而且让观众先闻其声,那甜美充满魅惑的声音,再加上丛林如诗如画的美景,让观者同毛克利一起沉醉了。但是,这沉醉带来的却是毛克利在不知不觉中被缠紧,如果不是巴鲁出手相救,毛克利必死无疑。这个卡俄是导演把文本中老卡俄的名字以及白头兜阴险狡猾的本质揉合起来,再给其添加一层温柔和美的外表而构建的形象。
三、创造性叛逆的原因
《梦幻森林》的创造性叛逆首先与公司主要的受众有关。迪士尼公司的电影主要以儿童为受众,这决定了《丛林故事》从文本到电影的改编过程中,在关于主题的诸多阐释中,自我身份追寻和成长主题必然是最佳选择。
其次,电影主题的叛逆与迪士尼电影的基本价值观密切相连。“迪士尼电影的成功并不是那些花里胡哨的卡通和搞笑,而是以其为表象和载体所蕴示和传递的一些普世和恒世的价值观或价值理念,其中主要有平等价值、因果报应价值、尚美价值、苦难和生存价值。”[3]这些价值观也直接影响了电影对文本的改编,直接促成了主题的创造性叛逆。在主题的取舍上,文本中的白人至上、西方文化至上的思想与迪士尼的平等价值观相悖,从身份追寻、成长主题切入,能够成功地回避掉这些思想。所以,电影仅仅选择了文本中的部分情节——从毛克利被驱赶到除掉老虎返回丛林。这一过程被导演处理为一次惊险之旅,毛克利顺利通过重重考验,终于除掉对手,这也恰恰暗合了迪士尼电影肯定的苦难与生存价值。[3]在苦难中,毛克利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勇敢、智慧、善良、乐观。另外,因果报应是迪士尼传统的价值观念,“在迪士尼电影中邪恶的或不正义的力量无论看似怎样强大,或无论怎样巧设心机,机关算尽,总难逃脱失败的命运。”[3]电影为了突出主题,把角色分为两大阵营,正方是毛克利及其帮助者,反方是老虎、大蟒蛇、大猩猩等。影片最后是大团圆结局,真善美战胜了假丑恶,迪士尼的尚美价值也得到了体现。
再次,主题的叛逆决定了情节的创造性叛逆。毛克利的惊险之旅,也是一次自我发现之旅。在电影的几个主要情节中,毛克利首先面对的是老虎的追捕。这在电影中有两个场面,一是在草原上巧妙地躲过老虎的猛扑,这几乎是一种动物的本能;二是在横冲直撞的牛群中,毛克利稍作观察就决定顺势而为,抓住牛角跃上牛背,让牛群把自己带出绝境,毛克利作为一个人的思考分析能力初步显现。大蟒蛇的花言巧语设置的温柔陷阱差点夺去毛克利的性命,这提示受众人性也有弱点,毛克利也是如此。与巴鲁的采蜜生活中,毛克利作为人的才智再一次得到闪光与发展。身体庞大而又狡猾的黑熊对悬崖上的蜂蜜垂涎欲滴,但一直都无计可施。但是毛克利改变了这一切,他开动脑筋想办法,利用藤条编织成工具,攀上峭壁为狗熊采下足够的蜂蜜。猴子宫殿的冒险中,面对众多的猴子,毛克利成了弱者,依靠黑豹和狗熊将其救出,这表明人类虽然足智多谋,但依然有不足之处。最后利用智谋除掉老虎,是毛克利作为一个“人”的特征发展到顶端。老虎在兽群不可一世,但却命丧人手,表面是咎由自取,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人类智慧的伟大。最后,毛克利称为丛林之首,幸福地生活在丛林里。到此,毛克利完成了自我身份的追寻,从最初离开的时候,认为自己是一只狼,现在已经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人,一个足够聪明的人,能够统领丛林动物又能与之兄弟相称。情节的发展也展示了毛克利的优秀品质。老虎追捕情节展示了毛克利的机智勇敢,遭遇大蟒蛇展示了他的单纯,为巴鲁采蜜展示了他的善良多智,对大猩猩的拒绝展示了他不为利所动的坚定信念,除掉老虎的过程则再次展示了他的谋略、英勇以及深得“兽”心。毛克利从影片最初躲在狼妈妈身后的怯懦孩童成长为一个有勇有谋、汇聚众多优秀品质的小男子汉,成长为丛林首领。
在已经被精简过的情节中,创造性叛逆产生的原因,第一是影片主题的需要,塑造人物形象的需要。例如,老虎的追杀、设计处死老虎以及巴鲁的采蜜生活等,影片需要通过它们揭示毛克利的优秀品质,展示其成长和自我发现。第二,上文提到过,迪士尼电影有其独特的价值观,电影要进行一些叛逆才能契合这种价值观。例如,毛克利与动物的对视,电影中的处理体现了迪士尼电影的平等观念。第三,电影的时间一般都在90到120分钟之内,而《丛林故事》中毛克利的故事则有两百多页。(本文选用的是北京理工大学2015年7月出版,由贾丽萍、喻红翻译的版本。)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围绕身份与成长主题进行叙事,情节的删减、增加、改变都是无法回避的。
第四,角色塑造上的创造性叛逆产生的原因有二:表达主题及展示人物性格。影片中老虎、毒蛇等角色是邪恶力量,它们是毛克利自我发现和成长道路上的阻碍,也是推动力量。正是在这些角色共同作用的情节中,电影的主题得到凸显。同时,邪恶力量的存在也从侧面烘托毛克利的形象特点。大熊从恶到善的转变,则使毛克利的善良更为突出。
第五,美国传统文化崇尚个人英雄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是为完成某一重大意义的历史任务或实现某一社会理想时表现出来的果敢、英勇和牺牲精神。个人英雄主义要反映出社会正义,敢于克服困难并与黑暗势力进行顽强不屈的斗争。”[4]取自于英国文本的《梦幻森林》,进入美国必然也要契合美国的文化传统。毛克利在电影中就是一个小英雄,克服了艰难险阻,铲除掉邪恶力量,维护了丛林的和谐宁静。
乔恩·费儒的《梦幻森林》与吉卜林的《丛林故事》同样让人回味悠长。从文本到电影,文化传统、导演个人倾向、迪士尼的传统、影片的内部机制以及电影本身的特殊性,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影片的创造性叛逆。这再一次提醒我们,文本和改编的电影之间是无法划上等号的,小说一经改编成电影,就成了一个与之不同的艺术品。不能用文本来衡量电影,也不能用电影来苛求文本,它们本身各有特色。
[1]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131.
[2]Tomkins,J.M.S.The Art of Rudyard Kipling[M].Herford: The Shenval Press,1959.
[3]张安律,刘安洪.迪士尼电影的隐蕴价值解读[J].电影文学,2010(7):34-35.
[4]黄骏.文化霸权视角下的《钢铁侠》系列电影[J].声屏世界, 2014(12):67-68.
责任编校 边之
I106.4
A
2095-0683(2016)04-0066-03
2016-06-21
吴超平(1978-),女,安徽淮北人,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