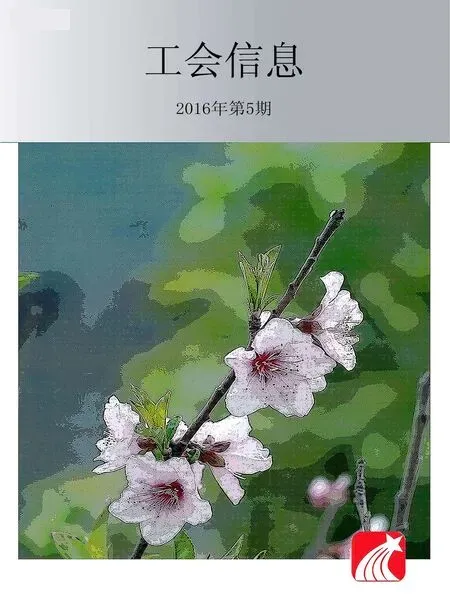一个院士眼中的生老病死
中国工程院院士 秦伯益 口述 健康时报记者叶正兴 整理
一个院士眼中的生老病死
中国工程院院士 秦伯益 口述 健康时报记者叶正兴 整理
精彩阅读
■“病人是医生的衣食父母,医生是病人的救命恩人”,这两句话沿用上千年,本义没错。然而,现在却常常容易引起误会,病人误以为“我是你的父母,你该关照我”,医生认为“我是你的恩人,你应该感恩”,如果大家彼此这样要求,医患关系就好不了了。归其根本,关键还是我们的基础教育有问题。
■我不刻意养生,但健康状况不错,目前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清楚、通畅、不高、不大。清楚,头脑眼睛耳朵感官清楚;通畅,呼吸道和两便(大小便)通畅;不高,血压血脂血糖不高;不大,前列腺和肝脾不大。我的各种化验结果,直到今年都还正常,一辈子没有住过医院。
■我很欣赏广东省委老书记任仲夷的乐观态度。60多岁时,一只眼睛瞎了,他说我照样“一目了然”;过了几年,耳朵聋了,他说我“偏听了”但 “不偏信”。又再过几年,胆囊不行,摘了,他说我浑身是胆了,照样大胆改革;到了80多岁时,胃不行了,大部分被切除后,他又大笑着说,反正到这个年龄了,“无所谓(胃)”了,这样一直活到92岁。
■我们都希望健康长寿,享尽天年,无疾而终。我印象中,能无疾而终的人多半健康长寿,之所以健康长寿,是因为器官内脏均衡地衰老,衰老到一定程度后,瓜熟蒂落,一了百了,这种走法是最好的。
人的一生,从出生到老去,从染病到死去,处处离不开医学关怀。作为与疾病和药物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贡献卓著的药理、毒理学家,83岁的秦伯益对人的生老病死与医学的关系有着很深的感悟。
近日,在中国医药教育大会暨中泰慢病防治国际论坛上,秦伯益讲述了自己对待生老病死的乐观心态,启人心智,令人深思。
生 爱心教育和理性教育
“病人是医生的衣食父母,医生是病人的救命恩人”,这两句话沿用上千年,本义没错。然而,现在却常常容易引起误会,病人误以为“我是你的父母,你该关照我”,医生认为“我是你的恩人,你应该感恩”,如果大家彼此这样要求,医患关系就好不了了。
此时,医学人文的性质就变了,变成“有付出,有报酬”的单一回馈形式,归其根本,关键还是我们的基础教育有问题。
人从呱呱落地,就开始面对教育,这贯穿了人的一生。教育的规律应是以人为中心,按人的生理、心理、心智发育过程来设计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其中爱心教育和理性教育尤为重要。有了爱心,有了理性才能是完整的人;如果从基础教育起,培养的是没有爱心和理性的人,长大就会闯大祸。
那么,一生的教育应如何去做?出生前6年的学前阶段,小孩从妈妈体内子宫刚出来,什么都不懂,充满好奇,实际上他是在观察和了解周围环境,我们应放手让他去探究、多问问题,给予简单易懂的回答,启发他去思考;
而到了小学,接触外界范围扩大,认识不同的人,关键应是培养爱心,爱父母、爱老师、爱同学、公共财物、个人卫生,以及对家乡的爱;
多一些爱心教育,少一些仇恨教育;多一些道和理,少一些技和术。只有有了爱心,有了理性才能是完整的人。
上高中后,就应该培养理性,学会思考,学习哲学、逻辑学、公民学等。而到了大学,更重要的是培养人格,能不能说真话,能不能坚持真理,在各种压力面前,能不能坚持独立的人格,这将决定一个人能否成为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人。
现在学生的条件比起我们上世纪50年代上学的教科书多了三、四倍,但是细细看来,理的教育并不多,全都是技和术。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然而,只有读者用自己的思维和智慧去将知识实践,付诸行动,才会产生力量,取得成功,从知识到力量是一个转化和放大的过程。如果到了大学以后,还是满堂灌课就大错特错了。
有一次,国家教委安排培训全国优秀中学老师,一连三届让我去讲课,培训内容包括了文科和理科的关系,文学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关系,却独独没有“公民课”的内容。
会后主持会议的司长对我说,现在“公民课”放在“政治课”里了。我说,政治课里讲的公民是遵守纪律,遵纪守法,权利义务,做合格的螺丝钉;而公民课里讲公民,第一句话就讲公民是国家的主人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培养独立人格的公民,有诚信和契约精神。这一点上,思想政治课显然代替不了这些课程,而这正是我们现在教育最缺乏的一环。
老 老年健康贵在心态
不必刻意养生,一切顺其自然。
从直立猿人到智人,再进化到现在已经300万年,古代人平均寿命50多年,现代人的骨骼、肌肉、关节、内脏使用时间已远远超出古代,我现在83岁,已远远超过各器官的“保质期”,出问题也不奇怪,关键是要有好的心态,做到身心健康,预防保健,定期体检,早诊早治。
我目前的健康情况可以概括为八个字,清楚、通畅、不高、不大。清楚,头脑眼睛耳朵感官清楚;通畅,呼吸道和两便(大小便)通畅;不高,血压血脂血糖不高;不大,前列腺和肝脾不大。各种化验结果都还正常,这辈子没有住过一天医院。
老年健康,贵在心态,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活法。人生角色,总在不断转化,不要一条路走到底。我主张,在位时,全力以赴,废寝忘食,义无反顾;退位时,欣然领命,戛然而止,飘然而去。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要活得潇洒,懂得享受老年的快乐。如果在位时,磨磨蹭蹭,拖拖拉拉,不当回事,退位时,这也没做,那也还想做,恋栈不去,那就没意思。
回顾自己一生最快乐的时候,就是退休以后这十多年来的时光。因为责任已尽,负担已除,经济无虞,身体还好,感悟人生,懂得了生活,也知道已经到这个年龄,夕阳晚霞,稍纵即逝。要抓紧每一天,稍微一放松,就没了;我会珍惜每一天,过好每一天的生活。
老年人有成熟之乐,天伦之乐,发挥个性之乐,孤独之乐。一个人在时,有最大的思想空间,具有和书中的古人沟通,和世界上万事万物思想沟通的条件和智慧,不受各种打搅和干扰,获得一些自己想享受的心灵愉悦。陈独秀曾说过,做学问最好的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实验室,一个是在监狱,是否真正会生活的人,关键在是否有兴趣和追求。
很多大艺术家、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创造性高潮来临的时候,往往是在静中、夜中、雨中、枕中、狱中、病中。真正会生活的人是不会寂寞的,我就没有寂寞的时候,一天到晚有干不完的事情,现在每天不到1点不熄灯,去年此时,我不到2点不睡觉。
老年最大的快乐就是,知足常乐,自得其乐,助人为乐。年轻的时候,赚钱是快活的,老年的时候,用的地方对,能雪中送炭是快乐;我们一生艰苦,晚年幸福愉快,观念也可相应调整。无所求就无所失,大彻大悟后就没有大悲大痛。
病 医生安慰的不同解读
人类未必能够消灭疾病,而疾病也肯定消灭不了人类。医学不断在进步,但医学也有它的局限性,例如结核菌产生了耐药,它迫使我们研究,但仍有8%耐多药结核不好治。
医学历史上,有位著名的特鲁多医生,1848年,他诞生在美国纽约撒拉纳克湖旁,25岁医学院毕业开始从医,却发现自己就是肺结核患者。肺结核,在当时以为是绝症,他回到老家疗养,通过营养加强,空气环境改善,骑马、散步、打猎,有所好转,但回到纽约后又因劳累而病情反复;37岁时,他辞退工作,在老家建立世界上第一家结核病疗养院。
100年前的1915年,特鲁多67岁去世,患结核多年的他比当时美国平均寿命还长。他临终时说了三句著名的话,刻在墓碑上,作为墓志铭,很多医生去美国旅游,都会前去吊唁。
“To cure,sometimes;to relieve,often;to comfort,always”(有时去治疗,常常去缓解,总是去安慰)。可是,现在这句话被宣传过头成了误导,似乎要让病人知道,我们的医生只能总去安慰,来缓解医患矛盾。
我很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因为这不是事实。病人半夜三更去排队,就诊三五分钟,只是去求个安慰?那还不如去佛堂拜菩萨。
我认为这句话可以作些修正,应该是“T o cure,in time;to relieve,anytime;to comfort,sometimes”(及时去治愈,随时去帮助,有时去安慰)。安慰,是需要安慰时去安慰,不需要去安慰时没意义。面对绝症,能治就治,不能治就别治。不必过分强调医生的安慰作用,医生的安慰也不只是微笑、和蔼、客气。
如果我是病人,我对我的医生只要求两点,如果你能做到这两点,我信你,把整个性命交给你。一是站在我面前,让我感觉医生是个有气质和风度的人,一位严肃认真思考我的问题的人,仁爱,认真,知识博学,技术精湛,这样的医生我信任;二是讲真情,说真话,哪怕只有三天可活也要如实告诉我,让我做好这三天的事。
任仲夷,是一位我很敬重的长者,他对疾病乐观的精神很让我佩服。作为广东省委老书记,他是建设深圳特区、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的领导人。60多岁时,他的一只眼睛瞎了,但是他说我照样“一目了然”;过了几年,耳朵聋了,他说我“偏听了”,但我“不偏信”。又再过几年,胆囊切除了,却照样大胆改革,他说我现在“浑身是胆了”(胆汁往血液流);到了八九十岁时,胃不行了,大部分被切除后,又大笑着说,反正到这个年龄了,“无所谓(胃)”了,没有也不要紧了,一直活到92岁,他对广东和深圳的开发都起着决定性作用。
死走要走得安详有尊严
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辉煌一生,或窝囊一世;或健康长寿,无疾而终,或久病缠身,生不如死;或走得舒坦、安详、有尊严,或走得痛苦、凄凉。
东西方人有着不同的生死观。孔夫子有言,“不知生焉知死”,孝子是不能在父母面前谈“老”的。自古以来,中国人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尽管赖活着远不如好死。西方人有宗教信仰,灵魂和肉体是附着在一体的,死亡的状态是归宿、圆寂、涅槃、超度和净土。
在我10岁那年,爷爷去世,棺材放在厅堂里祭天,客人们纷纷吊唁,家属哭声不断。到了第三天,哭不动了,突然看到两个老太婆大哭,后来知道是职业哭丧婆。原来,悲的气氛也可以拿钱制造,让我幼年的心灵就知道,婚丧喜庆全要花钱,不一定都是感情,有些礼仪都是靠钱换来的。
西方人死去,会当面谈死亡的问题,亲人围着临终的病人读圣经、唱诗、听悲乐,安静地送家人走最后一段路。这或许就是文化的不同。有本书叫《死亡如此多情》,里面有句“我的死亡谁做主?”我明确地回答:“我的死亡我做主”。我会书面列出“生前预嘱”,也希望“生前预嘱”问题能得到全国人大的立法解决。
另外,临终关怀,在中国也应该发展起来。1967年,英国女医生西塞莉·桑德斯博士首先在英国伦敦圣·克里斯托弗建立临终关怀医院。我曾经到这家医院访问,在一间大活动室里,那些病人有的看画报、打扑克,有的织毛衣、看书、看电视、聊天,他们的寿命都不会超过一个月。临终的病人,前一个月还能享受正常的生活,让我很受触动。
圣·克里斯托弗临终关怀医院的院长告诉我,对于这些病人,一是对症药物用够,过去我国吗啡一般是10mg,用到100mg以上就很担心,而英国一般会用到1g,多的时候到2~3g;二是安慰,我国照顾临终病人的全部压力都在医护人员,但英国却有五种人(心理学家、医护人员、社工、志愿者、牧师)去疏导各种不同时期的心理障碍。
中国的志愿者很少,牧师更是基本没有,中国志愿者都是学生有组织地去,回来写一篇日记,按应试内容在做;而英国的医院里,每天会公布病人情况,包括年龄、性别、职业,社会人员会很自然地利用休息时间主动预约,同一行业领域的人会很亲切、无偿的聊他们生活和了解的事情,形成一种愉快的文化氛围。
死亡,是人生最后的归宿,我们应该直面归宿,走得安详舒坦有尊严,至少不要制造新的痛苦。比如,呼吸心跳停止后,用机器抢救叫生命支持系统,我不同意这个名称,用替代系统维持已经结束的生命,是自己骗自己。
最近,我为三联书店的新书《死亡如此多情2》作序,我明确地写着:迫于道义和舆论而过度抢救不是上策,出于感情而无意义地救治并不理性,为了救治绝症患者而倾家荡产没有必要,家属为了保持高干待遇而让已经濒临死亡的亲人长期住在ICU抢救徒受痛苦形同虐待,让植物人长期住医院很不人道。
我们都希望健康长寿,享尽天年,无疾而终。我的印象中,能无疾而终的人多半是健康长寿的,之所以健康长寿,是因为器官内脏均衡地衰老,如果衰老到一定程度,瓜熟蒂落,一了百了,这种走法是最好的。
我对自己临终的态度:抢救啊,复苏啊,切开啊,插管啊,除颤啊,统统不要,我的预嘱准备这样写,我疼痛了镇痛要用够,我烦躁了镇静安眠药用够,临走时请告诉大家,我曾经是一个长寿而快乐的老头,我充分享受了人生,我知足了。就请放一曲舒曼的《梦幻曲》或者萨克斯管的《Going home》!我回家啦!
摘编自《健康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