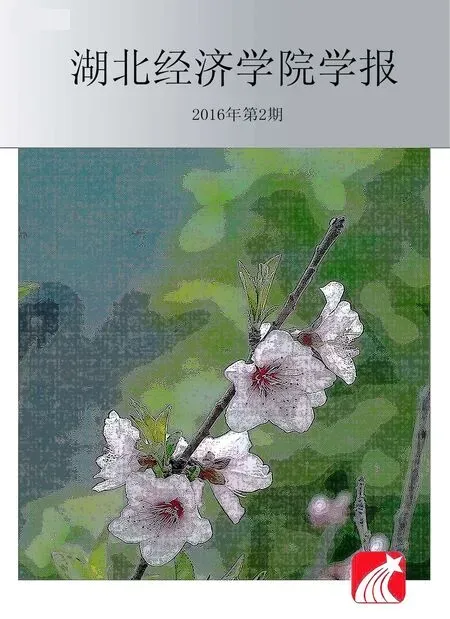治理理论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实现路径
吴 宾,李 娟
(1.中国海洋大学 法政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2.东北大学 文法学院,辽宁 沈阳 110169)
治理理论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实现路径
吴宾1,2,李娟1
(1.中国海洋大学 法政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2.东北大学 文法学院,辽宁 沈阳 110169)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外出务工人员的主体,是最有可能实现市民化的群体,但住房保障的不足已成为制约其市民化进程的瓶颈。公共租赁住房是唯一面向新生代农民工开放的住房保障形式,由于中央层面政策设计缺乏操作性,地方政府采取“经济上吸纳,制度上排斥”手段,新生代农民工实际获得公租房数量相当有限,难以从住房困境中解脱出来。建议借鉴治理理论,构建多元参与的治理机制,最终实现政府、用人单位、新生代农民工以及社会组织四主体合力解决住房的格局。
治理理论;新生代农民工;公共租赁住房
截至2013年底,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已达10061万,占全部外出务工人员总数的60%,①显然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一个庞大群体。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渴望融入城市,享受市民待遇。其中住房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并实现市民化的前提,但目前我国城市房价收入比过高,而农民工自身收入有限,使得其通过市场解决住房变得相当困难。②因此,在全面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住有所居”的目标,理应主要依靠住房保障来逐步实现,如果其获取保障房的渠道受阻,必将影响其住房困境的破解以及市民化的进程,进而产生城市内部新的二元结构,与新型城镇化的目标相差甚远。
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引起众多学者关注,张志胜主张开通新生代农民工住房服务渠道并逐步将其纳入保障房范围;[1]金萍论述了住房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保障,应通过改革和完善公租房制度来化解他们的住房困境;[2]王星倡议根本出路在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促使新生代农民工、政府、市场、社会各方共同参与;[3]孙万玉则提出了拓宽住房供应渠道的策略,用人单位提供住房,政府制定租房补贴政策。[4]以上研究只是简单提及了政府、社会、用人单位及农民工各主体应采取的措施,并未深入分析农民工住房保障与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同时缺乏系统理论的支持。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和外部性,亟需合各家之力才能彻底根除。基于此,本文拟借鉴治理理论从政府、用人单位、社会、农民工自身四主体来探索新生代农民工住房困境原因以及住房保障实现路径。
一、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的价值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周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更愿从事安全系数高和具有发展潜力的工作,具有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和工作耐受力低等特征。该群体在生活习性、身份认同、价值观、人生追求等诸方面都不同于父辈,更渴望融入城市。这些差异客观上要求政策的制定与出台由以就业为主逐渐转向以住房为保障。只有抓住时机着力推动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的改革与完善,才能促使其由“职业非农化”向“居所非农化”转变,最终实现“生活市民化”。因此,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问题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价值。
第一,有助于逐步化解城市内部现存的二元结构,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量农民工进入城镇就业和居住,但长期以来未能享受到住房、医疗、就业、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以2012年为例,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综合指数为39.63%,与上年度相比,仅上升了0.07个百分点;同时在基本公共服务享有方面,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差距仍较为悬殊,二者的比值为44.49%。[5]市民化的进程较为缓慢,在住房领域表现为当地政府将较多的保障房分配给户籍人口,外来人口大多聚居在城乡结合部、临时简易房等环境较差的出租屋中,同一城市内亦出现了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员的新二元结构。新生代农民工所具有的特性决定了其是最具市民潜力的群体,然而目前住房成为影响其在务工地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重要因素。因此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问题会极大改善其居住环境,改变城市内部二元结构,有利于改变农民工以业缘、地缘为主的社会支持网络,逐步融入主流社会,消解内心存在的 “漂泊感”和“边缘感”,增强城市主人翁意识,促使其更加努力工作并不断学习城市文明的行为方式,从而最终实现市民化。
第二,有利于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坚持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并强调要解决好“三个1亿人”的问题。这意味着我国的城镇化要改变片面追求土地和城镇规模的旧模式,转向注重以人为核心的质的提升。城镇化过程的表象是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实质上蕴含着进城农民对城市公共资源的需求以及对公共服务制度可及性与可获得性的平等诉求。[6]新型城镇化注重质的发展,不断增加公共服务的供给,实现服务对象的全覆盖,其实质是促使农业转移人口同城市居民共享城市公共资源。但城市众多的公共资源都是附着在区位之上的,而住房又是与区位相关的公共服务的一部分。[7]作为准公共产品的保障房,一般均配套有教育、医疗、卫生、交通等公共服务设施,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住房保障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有利于增加其就近获取城市公共资源的机会,进而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最终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第三,有益于产业结构调整。农民工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是城市就业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就业主体。虽然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相对较高,但工作经验较少加之受价值观念等影响,主要从事制造业与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工作,同时由于居无定所、居住分离具有工作变换频繁的特点。随着进城务工人员规模的扩大,短期内增加了劳动力总产出,满足经济发展需要。但长期来看,当城市产业由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时,人力资本所实现的“量”的积累已经不能满足产业发展的需要,亟需从“质”方面提高。而社区环境会对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社会资本质量的提升以及机会、信息的获取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劳动力的产出和经济增长。[7]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问题,为其提供固定的住房,有利于改变“过客”心理,减少其在行业间、企业间、工种间流动的频率,促使其主动提高劳动技能,积累工作经验,增加人力资本的存量,成长为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所需要的知识化创新型产业工人,满足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
二、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住房困境及其成因
(一)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现状
新生代农民工所具有的务农经验较少、受教育程度较高、择业期望值高等特点决定了其融入城市生活的意愿更加强烈,但其住房现状令人堪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居住条件差,满意度低。据调查,34.1%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在员工宿舍,40.4%与他人合租,①其中员工宿舍空间狭小,生活设施缺乏;而租住的房屋一半以上位于城乡结合部,大多存在着阴暗潮湿、建筑密度大、安全隐患高、卫生条件差等问题;(2)住房消费支出较大,降低了生活质量。2013年新生代农民工月租房支出占月生活消费支出的一半以上,与此同时农民工收入增长13.9%,而人均居住支出增长27%,房价上涨明显快于收入增长,迫使农民工不得不压缩非住房方面的消费,从而降低了生活质量;①(3)公租房分配数额较少,难以惠及更多群体。如北京市2013年最大一次规模的公共租赁住房配租,并且首次面向流动人口,此次配租中可分配的房源总量为3336套,其中有118套③是专门面向流动人口提供的,仅占总数3.53%;湖南省在2009年就提出了要将在本地有稳定工作并达到一定居住年限的农民工纳入公租房分配范围,但到2012年底,仅有4%④农民工分配到公租房;其他地区情况类似。
(二)新生代农民工住房困境的成因
在房价持续攀升和收入缓慢增加的背景下,农民工自身难以通过市场解决其居住问题,迫切需要政府介入为其提供保障性住房,但目前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很大部分来源于土地,供给保障性住房会减少土地出让金进而减少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所以地方政府分配给外来务工人员保障房的数量极其有限。因此,造成新生代农民工住房困境的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政府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政策虚置与执行偏差。2005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住建部等部门已连续发布八个有关农民工住房政策的文件,提出尽快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的住房问题,地方政府也按照中央指示在制定本地住房政策文件时逐步将农民工纳入公租房范围,政策文本日趋完备,但实际工作中有些部门以部门利益为主,存在对政策文本的不执行与选择性执行两种情况,造成了政策运行与政策文本严重不一致,形成了“政策虚置”的现象。具体表现在:一是城市决策者与执行者认知偏差。当前城市决策者与执行者存在农民工是“经济发展的成本”的短视思维,以降低成本为利益出发点,只为城市居民提供较好的公共服务,农民工享受到的相对来说范围较窄,待遇较差。二是受资金限制,地方政府采取“经济上吸纳,制度上排斥”手段。纵向层面,中央和地方实行财政上收、事权下沉的权责配置机制,造成了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等,地方政府承担大部分建设费用;横向层面,流入地与流出地政府协调不畅,尚未形成利益补偿机制。公租房不仅具有地域属性的特点还具有福利性质,具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供给保障房用地会减少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减少财政收入。在土地财政的背景下,流入地政府不愿将流动人口纳入住房保障范围。对于流出地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离开农村和农业,造成房屋和土地资源大量闲置。三是政府绩效考核中仍以GDP为主而忽视了民生问题。在传统发展理念影响下,各地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往往贪大求全,盲目追求GDP,官员考核也是以GDP为主,“民生”被让位于“经济”,较少考虑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四是在城市极化倾向背景下,各级政府未做好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规模以及住房需求测算工作。我国城镇化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资源配置偏向行政中心城市和大城市,加之城市是人口、要素和非农产业的集聚地,可以获得多方面的集聚规模效应,在市场作用基础之上,促使更多的人口和资源流入大城市,使得大城市具有较好的就业机会、公共服务和较高的收入水平,农民工也大都愿意流向这些大城市,造成了大城市人口不断增加,规模急剧膨胀,逼近或超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而小城市人口比重不断较少的两极化倾向。在此种背景下,政府在城市规划中未考虑到进城农民工的规模,缺乏对保障房数量和结构的详细测算等工作,造成了大量农民工聚居在城乡结合部等边缘地带,形成了新二元结构;而中小城市因工业实力不足加之没有政策优惠难以吸引农民工前来就业,面临着“空心化”的局面。
其次,用人单位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责任缺失。虽然国务院出台相关文件指出“招用农民工数量较多的企业,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可在依法取得的企业用地范围内建设农民工集体宿舍”。[8]但在实际中集体宿舍的供给量远远低于需求量。一方面有些用人单位经济实力薄弱,难以负担建设集体宿舍所需要的地价,加之政府尚未出台优惠政策,从而无法为其员工提供住房;另一方面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理性人,只单纯用人,未考虑提供相应保障,尤其是中小企业,为了降低企业运行成本,更是将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推向社会。此外,一些用工单位急功近利,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和不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等现象,严重侵害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再次,新生代农民工市民意识薄弱及货币支付能力有限。一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意识薄弱,缺乏对公租房政策了解的积极性,缴纳社会保险的意识不强,获取租赁类的保障房较为困难。目前各地对保障房申请人缴纳的社会保险均有相应年限的限制,而实际中农民工参加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的比例仅占15.7%、17.6%、28.5%、9.1%,①影响了公租房的申请。二是房价收入比过高。一方面,没有能力去买商品房。2013年,全国商品房售价达到6237元/平方米,⑤新生代农民工月均收入仅2609元,①远超出其承受范围。而北京、上海和广州等新生代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城市,房屋均价早已突破1万元/平方米,这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更是难以负担。另一方面,没有能力购买经济适用房、限价房等保障性住房。一线城市保障房价格早已突破6000元,若购买一套70平方米的住房,需要支付首付近10万元,房价与支付能力之间的巨大悬殊,使其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屋变得遥不可及,同时制度上也是排斥的。
最后,社会组织参与保障房的建设与供给力度不够。纵观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住房制度不难发现,非营利住房组织大部分以住房合作社、住房协会等形式参与住房建设、经营和供应。以英国和荷兰为例,前者非营利住房组织以住房协会形式存在,主要面向有住房需求的低收入者或其他弱势群体。政府不仅在政策、财力、土地、税收等方面给予了较大的支持,而且也将自身已建成的住房交给协会管理,同时住房协会拥有较大自主性,目前已承担了该国一半以上社会住房的建设与供给。后者的住房协会经过不断的发展和完善,目前已变为实力雄厚的社会企业,负责全国范围内的住房建设与分配,极大缓解了该国住房紧张的局面并减轻了政府的负担。而相比较我国的住房方面的社会组织数量较少,面向对象比较窄。基本形态是早期的职工型住房合作社,该合作社主要利用单位自有土地建房,面向内部员工,具有较强的单位属性。许多没有稳定工作的人员的住房问题仍然未解决,造成了新的不公平。
三、治理理论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实现路径
治理理论强调主体多元性,各主体通过协商、互动、合作达到共同治理。政府不再是权利唯一的主体,不能总揽一切合法的权利,它与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私人机构等多种主体处于平等的地位,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各主体依据不同的行为准则,发挥不同的社会功能。需要注意的是治理也不是万能的,也存在治理失灵的现象,为了避免治理失灵,政府虽然在公共事务管理中不再具有绝对权威,但仍然指导着大方向,占据着主导作用。如前所述,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保障问题可以更加有效地解决其住房问题,而保障性住房涉及政府、用人单位、社会组织以及农民工等主体,这就需要强化治理理念形成各主体合力解决住房的格局。同时由于保障房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点和避免治理失灵,政府仍应发挥主导作用。
(一)政府采取多种手段着力解决政策虚置与执行偏差问题
第一,对于各地政府来讲,需要改变成本观念,建立资本思维,切实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公租房范围。当前一些政府官员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经济发展的成本,将其看作财政压力、经济负担等问题,地方政府以降低成本为利益出发点,并不想将农民工纳入公租房范围。相反,该群体是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生产和消费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本。所以资本思维的建立有助于促进政策制定者和城市管理者完善当前的住房保障政策,拓宽保障房分配范围,逐步实现公共资源的均等化,进而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第二,政府应增大财政支持力度,促进府际合作。首先,中央与地方政府建立明晰的财权与事权分担机制。稳定的住房不仅可以改善农民工的居住环境,还可以促进其融入城市生活,扩大社会交往范围,有利于工作技能的提升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农民工具有流动性的特点,但这些收益在全国层面是不会外溢的,因此在保障房资金方面中央政府应承担主要的财政责任。其次,流入地与流出地政府要通力合作,探索跨区域的住房土地指标交易机制,实现全国建设土地的高效合理利用。目前我国土地管理法尚无相关条例允许农民可将暂时闲置的宅基地转卖给他人,既影响了农民工老家住房高效利用又使得农民工囿于收入有限只能租住在环境较差的出租屋中。所以目前应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土地管理法,将宅基地流转纳入法定程序,促使新生代农民工积极申请退出宅基地并在政策和资金方面给予鼓励,既有利于增强农民工购房支付能力,又能合理规划农村土地。最后,增强流入地政府责任意识,改进官员考核机制。“将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促进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生活”已成为我国政府工作内容的一部分。[9]改进官员考核机制,设立多项评价指标,例如可将农民工住房满意度作为一项关键指标,引导政府官员更多关注民生领域,实现城市经济与民生的良性发展。
第三,做好农民工住房保障需求测算工作,提升中小城市的吸纳能力。一方面,城市管理者在做城市规划时,要充分考虑到进城农民工的规模以及住房需求,尽可能将其与城市居民安排在一起,实现混合居住,也要考虑到住房的户型和面积与农民工群体特点相对应。同时,对目前农民工聚居比较集中的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地区要加强规范与管理,避免违法犯罪的发生,影响社会安全。另一方面,考虑到我国目前城市两极化倾向明显,应通过政府尤其中央、省一级政府的调控,将更多公共资源特别是住房保障资源配置到中小城市,增强这些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吸纳能力,加快中小城市的发展。对于大型城市,鼓励地方政府利用当地的财政资金,就地化解目前在本地稳定就业的中低收入流动人口,从而实现我国大中小城市的良性协调发展。
(二)用人单位量力而行改善员工居住环境
农民工住房问题涉及投资、建设、管理等一系列工作,仅靠政府一家之力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而且农民工的居住环境会影响劳动力的产出。对企业来说,劳动力产出水平的高低与其效益密切相关,所以从长远来看企业也应尽可能采取多种措施改善员工居住环境。考虑到有些用人单位经济实力悬殊较大,据此可根据自身情况量力而行:一是实力雄厚的企业可申请建设用地建设集体宿舍就地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这样不仅可以促进劳动力稳定性,减少农民工不必要的交通支出,还可以减少企业流动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可减轻政府的负担,一举三得。二是经济实力薄弱的企业可提供一定比例的资金投资保障房的建设。在实际中企业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当地特色,灵活应变改善员工住房环境。例如“重庆模式”是企业参与改善员工居住环境的典型代表,其将城市中闲置的楼房改造为农民工公寓,并配套一定的生活设施,既实现了城市资源的充分利用又极大改善了员工的居住环境。
(三)重视技能培训,着力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
政府应为农民工提供劳动技能培训,提高其就业能力,提供尽可能多的就业就会,与此同时积极引导有条件的农民工创业,为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企业也要定期为雇员提供免费的技能培训,既可以减少员工的流动性,也可以提高农民工的技能,增强市场竞争力,实现双赢。农民工自身要积极参加政府、企业提供的职业培训,增强一技之长,进而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同时农民工要增强市民意识,积极缴纳社会保险,采取合理和合法的手段维护自身权益。一方面,农民工要对当地的住房保障政策熟悉在心,当满足申请条件时主动申请保障房。71.49%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没有参加当地任何一项社会保险,[10]这严重不符合各地对保障房申请人的资格要求,所以农民工自身要主动缴纳社会保险。另一方面,当用人单位出现不缴纳社会保险损害自身权益的行为时,农民工要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或采用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四)大力培育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是应对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并存的双重窘境下有效解决问题的最好路径,其参与公共产品的供给与管理,有助于转变政府职能,促进“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形成,进而实现“善治”。[11]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在住房领域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借鉴英国和荷兰经验,首先应大力培育住房方面的社会组织,重视其在提供社会住房方面的优势。在人员组成方面,可以鼓励具有一定支付能力的中低收入者或是雇佣农民工人数较多的企业积极参与住房合作组织的建设。在资金方面,政府可以给予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或是直接给予资金补贴,也可以引导社会资金的投入。在土地供给方面,政府可将部分保障房用地划拨给住房组织,由该组织负责房屋的建设与供给,大力鼓励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如此既可以增强市民的公民意识又可以改善农民工居住环境,实现双赢。
四、结语
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预言: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课题。城镇化的核心在于市民化,其中住房问题又是实现市民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保障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社会的稳定与城市化的未来走向。基于此,本文借鉴治理理论多方主体参与的思想,分析了政府、用人单位、农民工自身及社会组织四主体在住房保障方面的不足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由于长期分割的城乡二元户籍体制、公民社会发育程度较低,促进四主体之间的合作,实现共同治理还存在一定的困难。这就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加强规划与指导,并从土地和房产政策等方面给予参与治理主体一定的优惠。
注释:
①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 stats.gov.cn/tjsj/zxfb/201405/t20140512_551585.html。
② 由国家统计局2013年抽样调查数据可知,2013年全国外出农民工能够居住在自购房的比重不足1%,在直辖市或者省会工作的农民工能够居住在自购房的比重则更低,只有 0.7%,有超过六成的农民工大多聚居在“城中村”、地下室和建筑工棚等价格低廉的住房中。
③ 数据来源于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网站http:// www.bphc.cn/。
④ 数据来源于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网http://www.hunanjs. gov.cn/zjtmh/15/88/538/default.htm。
⑤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data. stats.gov.cn/search.htm?s=2013。
[1]张志胜.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的阙如与重构[J].城市问题,2011,(2):90-95.
[2]金萍.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及其化解——对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现状的调查与思考[J].学习与实践,2012,(7):99-103.
[3]王星.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政策分析[J].江海学刊,2013,(1):101-108.
[4]孙万玉,石宏伟.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15,(4):13-15.
[5]李仕波,陈开江.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制约因素及破解路径[J].城市问题,2014,(5):74-78.
[6]刘明慧,路鹏.城镇化转型中的公共服务供给约束与政府融资路径[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3,(4):89-95.
[7]郑思齐,曹洋.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从经济增长与社会融合角度的研究[J].广东社会科学,2009,(5):34-41.
[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EB/ OL].http://www.gov.cn/jrzg/2006-03/27/content_237644.htm,2006-03-27.
[9]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EB/OL].http://news.xinhuanet. com/politics/2007/01/22/content_5637713.htm,2007-01-22.
[10]刘谦,邹湘江.“是否更幸福?”——有关新生代流动人口生活感受的定量与定性尝试性分析[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47-56.
[11]汪志强.我国非政府组织:检视、批评与超越[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191-196.
(责任编辑:卢君)
The Path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Housing Secur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overnance Theory
WU Bin1,2,LI Juan1
(1.School of Law&Politics,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Shandong Qingdao 266100,China;2.School of Culture and Law,Northeast University,Shenyang Liaoning 110169,China)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s the main body of migrant workers is most likely to realize urbanization,but the lack of housing security has become a constraining bottleneck in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Public rental housing is the only form of housing security for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due to the lack of operational policy designed by the central level and"the economy to absorb,institutional exclusion"means taken by the local government,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ctually get a limited number of public housing and it is difficult to extricate from the housing dilemma.This paper uses the governance theory to construct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multiple participation,and ultimately realize the pattern of the four main forces of the government,the employer,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to solve the housing.
governance theory;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public rental housing
F287.8
A
1672-626X(2016)02-0075-06
10.3969/j.issn.1672-626x.2016.02.012
2016-01-15
高等学校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201213073)
吴宾(1974-),男,陕西洛南人,中国海洋大学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东北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社会保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