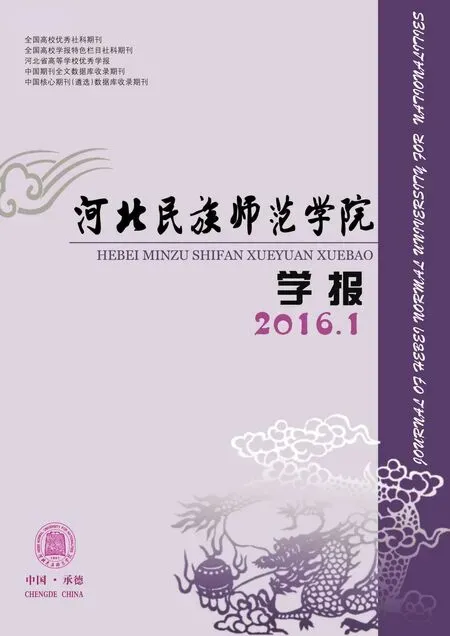从差异共生到文学共和:评刘大先《文学的共和》
李慧玲 魏韶华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00)
从差异共生到文学共和:评刘大先《文学的共和》
李慧玲魏韶华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00)
长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一直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它的存在常常被主流文学话语所掩盖。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逐渐进入到大家的视野当中,也出现了一批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论著,可以说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研究当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有这么几点:其一,一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往往将自己的研究局限于某个或者几个少数民族的文学,或者是仅仅探究少数民族文学的本身,且一味强调少数民族的文学个体性和独特性,脱离了与主流文学话语的对话,漠视了少数民族文学与主流文学的关系;其二,在当下语境中,某些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方法与批评理念失去了时效性,一种更为有效的针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批评方法与理念尚未建立起来;其三,有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进入了研究的死胡同,缺乏对于其他学科的关注,没有将少数民族文学放置更为广阔领域之中进行研究,使少数民族文学丧失了与其他学科的互相观照,从而导致了少数民族文学对于时代重大话题的参与度很低。
刘大先《文学的共和》一书,对于之前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本书从史、论、文本、影像、田野五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少数民族文学”到“多民族文学”的历程,把少数民族文学放在现代语境中重新定位,对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进行了反思,用先进的文学理论重新阐释少数民族文学,建立起少数民族文学和主流文学及其它学科间的对话,针对少数民族的文学文本、电影进行了独特的解读,同时通过亲自体验,作者对少数民族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关注,发掘了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多民族文学的体系结构。总而言之,较之于之前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来说,刘大先的研究具有更加多元化的视角,批评方法更为合理,现代先进的文学理论与文本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有一种严谨而又踏实的研究态度,他能够亲自去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体验和考察,所以他的阐释更加具有科学性。
一、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思考
在《文学的共和》史和论这两个部分中,刘大先对少数民族的文学发展进程进行了梳理,同时还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科建设、批评体系进行了反思。从这两个部分的结构框架来看,作者以少数民族文学为核心,以“历史——文化”为主线,以政治、国家政策、法律法规为复线,同时兼及对中西方文学理论的观照,形成了对少数民族文学较为完整的学术脉络。这套体系显然是对于之前少数民族研究的一个突破,一是,作者按照时间的顺序,建立起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纵向体系;二是,作者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并非仅仅局限于这一学科领域,而是与其他学科相联系,涉及到了历史学、政治学、文学社会学、语言学及文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体系,同时又把中外理论引入到论述中来,这就又建立起一种横向的维度。总体来说,其框架体系是较为完整的。
这种框架结构基于多元一体的文学历史观,以少数民族文学为焦点,强调少数民族文学与主流文学的主动对话,注重各民族及其文学之间的联系,认为各民族及其文学之间是“本无你我之别,我就是你,你就是我,原本就是在一起生长的”[1]17。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作者过度强调了多民族文学的一体性,可以说多民族文学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基于地域、文化、政策、经济等多个方面的差异,各个民族及其文学的发展是不均衡的,其生长轨迹、发展速度也是不同的,不能说是“本无你我之别”。当然,作者强调少数民族文学与主流文学之间的同构的阐释,这一点是极具现实意义的,少数民族“人民性”话语得到了重视,将当代文学的重要观念和少数民族文学联系起来,重新确立了少数民族文学之于当代中国文化的意义。
从内容来看,作者还给予了少数民族文学特殊的重视不仅仅是对于少数民族文学作家作品的关注,同时也对其学科建设和批评予以关注。作者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体系进行了梳理,认为其目前的学科意识依然较为封闭,既没有发挥其文化上的多重功能,又没有参与到现实生活中来。这一点是之前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没有关注到的,对于我们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科建设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警示作用,如何更好地发挥这一学科的各项功能,提高学科的日常参与度是值得大家重新思考的问题。
同时,作者指出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设性意见,在这一部分,作家运用了大量的东西方文学理论,足见其理论功底是十分深厚的,而能够把理论与文本、批评巧妙融合,这是十分不易的。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僵硬地套用批评理论,并没有考虑到本土特点。在此,作者着重强调了少数民族文学与主流文学乃至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学之间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而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必须建立在这一关系之上。把少数民族文学上升到与主流文学同等的地位,这是具有突破性的,之前的研究往往把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种边缘的声音,忽视了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性和独立性,而刘大先则为少数民族文学实现了“正名”。
二、在新媒体时代与全球语境中思考多民族文学的发展
在新媒体的冲击及其全球语境中,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作者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新媒体时代的多民族文学:从格萨尔王谈起》一文中,作者以格萨尔为例阐述了少数民族文学在多媒体时代的转变。在新媒体时代,文学的传播方式日益多样化,传播速度日益加快,一方面,这有利于文学的传播,传播范围更广泛,形式更加新颖,也更具时效性;另一方面,口头传承与文字书写营造出的触动心弦的效果也丧失了。作者认为在新媒体的冲击下,我们应该树立一种“多元文学史观”,化劣势为优势,把少数民族文学推广到主流文学当中去。其中“多”的意义含纳着四个层次:一是,多族群,具体到中国,就有56个民族;二是,多语言,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语言;三是,多文学,不同的文学界定与标准;四是,多历史,就是对前二者迥异的书写方式。而少数民族文学在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观照中就是与其他民族平等的一员。“事实与书写、文学与历史、真实与想象之间有着难以割裂的互文性,事实被书写改变,历史与文学互渗,想象向真实生成。我们可以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书写都是想象,作为文学史能动的书写主体同样会加入到书写真实历史的行列中来,多民族文学史观同样是重述中国历史的一条途径,它在重写过去中也会改写未来。”[2]这一点而言,作者有着明确的文化实践性,将文学研究视作一种文化交媾。这种态度给其他批评家做出了表率,当下社会,很多批评家缺乏思考的能力和创新性,一味地把责任推给社会、时代、体制等等,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在当下环境中寻求突破口,探索解决之道,正如刘大先所言:“神灵从来就没有远去 ,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眼睛蒙上了灰尘。”[1]88
在《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全球语境——兼及多元性与共同价值》这篇文章中,作者认为少数民族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处于全球语境当中,西方强势话语对地方性观念造成了冲击,同时少数民族文学也在主动融入到这种宏大的语境当中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为了防止全盘西化,一些少数民族文学刻意强调了本民族的独特性,而忽视了多民族文学之间的一体性,时至今日很多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依然执着于这种片面的、狭隘的身份认同之中,在全球语境下,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刘大先却跳出了这种思维,他认为正是因为本土源发性话语的缺乏导致了这种狭隘的身份认同,纵然少数民族文学有着自己的独特性,但是它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本身就具有一种国家性,刻意地撇清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不科学的。
在此作者创造性地提出了多元性与共同价值的观点,作者认为少数民族文学具有多元性,我们要在多元性当中寻求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这一观点并不是对少数民族文学个性的漠视,而是尊重差异基础之上的价值的共存、文学的共生。各民族文学都是一个个不同的存在,有着各民族的独特根性,正是这些形形色色的不同,使得中国文学更加具有生机与活力,所以说是“多样性的集体”构成了“集体的多样性”。这正是刘大先《文学的共和》这本书所要传达给大家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念,是对“和而不同”这一传统观点的深度阐释,之前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往往刻意强调少数民族文学和主流文学的差异,以此为基础挖掘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刘大先的这一提法却看到了表层现象下的更深层的本质的东西。这个深层关注背后则是对于当下中国整体文化氛围中弥漫的个人主义、犬儒主义的反思,他申言要“重建集体性”[3],其实就是召唤社会主义初期集体主义的文化遗产,并以之形成一种带有总体性关怀的文化立场。
三、文本、影像、田野三个维度下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关注
在文本部分,刘大先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文本进行了深刻解读,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学风貌,他的解读达到了与其他学科之间互动认知的高度。刘大先通过对潘年英作品的解读,阐释了文学人类学写作的特点,对作品中传达出来的文化多元共生观念与少数民族文学的自信进行了肯定;通过对吴岩的作品的解读,他找到了本土科幻文学的影子,他指出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可以在民族生活的基础上有所开拓,研究家也可以运用不同的理论进行解读;通过对叶梅作品的解读,对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给予了关注,他认为少数民族与女性的处境有相似之处;通过对朱春雨《血菩提》的解读,阐释了现代化道路上少数民族文学的探索;最后他对《2011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年选》进行了评论。文本这一部分,作者分析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个案,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解读不是泛泛而谈,而是运用不同理论找到了其中的一个点进行论述,理论与文本紧密结合,学科之间融会贯通、交错纵横。
在影像这一部分,刘大先对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进行了研究。他运用人类学的整体观与比较法,对少数民族电影文本进行了剖析,探讨了少数民族电影的功能与叙事模式,发掘了少数民族电影中的文化特质,从而让大家认识到少数民族电影在争夺话语权方面的重要性;他从新经济时代的少数民族电影中,发现了其中的文化遗产元素,让我们重视起少数民族电影在精神层面的重要意义;他通过对有关西藏电影的研究,指出了电影在展现西藏时存在的问题,倡导文化制造者应该重视文化内涵的塑造和普通藏民的日常展示,从而完整真实地把西藏展示在大家面前。刘大先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关注涉及到了与之相关的各种形式,他对于电影方面的关注,展现了他对于新媒体时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思考,引人深思。
刘大先的研究不是毫无生机的文本解读,而是亲历其境之后的真实感发。他长期去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考察,行走在广袤的田野,正是因为这种行走的力量才使得他对少数民族文学有了更加真实的认识和坚定的自信心,从而形成了思想的“田野”。在最后这部分中,他以新疆文化安全为例,探讨了少数民族与国家关系问题;以广西田阳敢壮山的神话重塑与文化创意为例,探讨了如何开发与消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文学遗产创造性的现代转化;同时通过亲历不同的地区,他对云南、海南、甘肃和湖北的民间文化现象进行了描绘,让异族人对这些地区有了初步的了解。他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习俗、禁忌、仪式、音乐、舞蹈等现象的研究,为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汪荣在一篇论文中准确地指出:“如果说《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体现的是刘大先‘理论的自觉’,那么《文学的共和》中的‘史’则呈现出‘历史的自觉’”;有意识地在新的学科视野和新的理论坐标中重新探索少数民族文学的相关议题,对学科方法论的重视和实践,体现了“视野的自觉”;“边走边想”的“文学研究的田野转向”则是一种“实践的自觉”。[4]
通过这三个维度和“四种自觉”,刘大先对少数民族文学的不同形式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的意义在于从不同的文学样式中发现多民族文学中蕴含的中国文学的共同价值,其目的在于实现从多民族文学的差异共生走向“文学的共和”。这个命题背后隐含着“重写文学”的冲动,即反思近现代以来由现代西方文学观念所界定的“文学”含义,在本土精神和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发掘和提炼出具有突破意义的理论命题,从“民族”发现“文学”[5]。这个“文学”已经不再是被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所束缚,虽然也涵括了这些文类,但是中国各民族文学则以其自身的多样性文学文类、风格、审美理念的遗产补充了更为丰富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的共和”对于重新塑造中国文学的主体性有着深远的意义。
四、结 语
“少数民族文学之于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等其他文学学科,特殊的地方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由于文学主体的身份差异而形成的文学门类,更在于它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实践,关联着丰富的文学现实——包括文类、语言、审美风格、运思模式、价值观、伦理态度、认识观念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与中国族群、地域、文化的差异性息息相关。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它在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支持力度的增加、作家创作与活动的繁荣而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6]如何应对这种新兴的文学现场,为研究者提出了新的问题。《文学的共和》分为史、论、文本、影像、田野五个部分,完成了从少数民族文学到多民族文学的学术脉络梳理,探讨了新媒体时代和全球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批评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著作涉及了人类学、历史学、政策法规、文化遗产等多个领域,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多民族文学图景。此书超越既有研究的窠臼,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知识格局、理论框架和技术路线上纵横开掘,说它将传统陈旧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一点也不为过。而定位于“文学的共和”的主题,足见作者对学术的非凡追求、胆略和雄心,因为这“不仅是一种极具启示意味的文学史观,也是一种兼顾少数民族文学价值建构和叙事伦理的富有张力的批评方法”[7]。
参考文献:
[1]刘大先.文学的共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7.
[2]刘大先.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兴起[J].民族文学研究,2008,(4).
[3]刘大先.重建集体性——恢复“中国故事”的多元共生[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
[4]汪荣.复活的词语与改变的规则 ——评刘大先《文学的共和》[J].现代中文学刊,2015,(3).
[5]刘大先.从“民族”发现“文学”[J].民族文学研究,2014,(4).
[6]刘大先.差异共生与文学共和——2014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侧记[J].文艺报,2014-08-06.
[7]谢刚.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重构——读刘大先新著《文学的共和》[J].文艺报,2014-12-0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鲁迅东亚影响力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号:14BZW107。
作者简介:李慧玲(1991-),女,山东青岛人,青岛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魏韶华(1963-),男,山东东阿人,青岛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收稿日期:2015-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