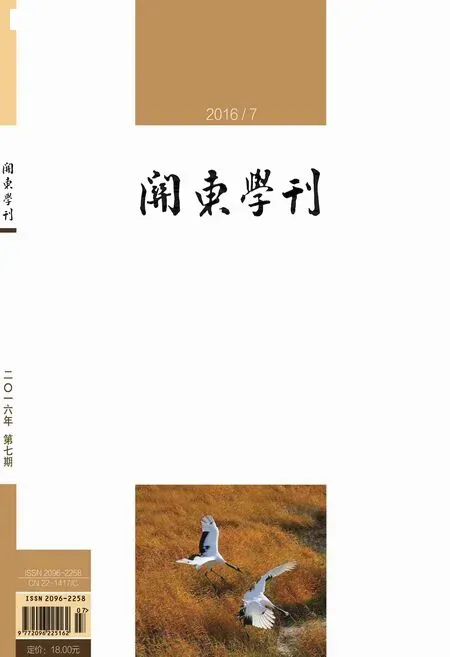学者散文的新收获
——读李新宇先生的《故园往事》
张厚刚
学者散文的新收获
——读李新宇先生的《故园往事》
张厚刚
《故园往事》记载了学者李新宇,作为一个离开故乡的漂泊者,对故园的回想与怀念。凝结了一代人镌刻着生命温度和生死恐惧的记忆。《故园往事》是学者散文领域的新收获,李新宇先生的文字背后是浓厚的故园情结。他通过对“故园”的回忆,为我们复活了专属于他的历史见证,并为每一个有过乡村生活经历的人,创造了一个纸上的“故园”。
李新宇;《故园往事》;学者散文;当代散文
李新宇先生是著名的文学史家、文化史学者,他在鲁迅研究、文化史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大成就,做出过大贡献。他编纂的33卷本《鲁迅大全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是迄今为止史上收录鲁迅著作最全的集子,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他做过细致的民国人物思想考据,这些研究领域虽有着各自的学术边界和研究范式,但本质上又都是他对“启蒙”问题的持续思考。他对文学、对学术的挚爱,带有个体生命的人性关怀,具有强烈的“人间本位”性质。他所涉猎的学问如果概括为一个关键词的话,那就是“启蒙”——这启蒙是立足于“人”的,关注的还是人的解放、自由、平等。
在严肃的治学之余,萦绕在李新宇先生心头的故园情思,随着父母的离世,愈加浓烈,不可化解,这些故园情思不可遏止地凝结在笔端,就有了这些随笔文字的结集——《故园往事》。全书分为两集:一集写史地、乡俗、志异;二集写血亲、自我、生计。作为一个离开故乡的漂泊者,这些文字不仅记载了他对故园的怀念和回想,而且凝结了一代人镌刻着生命温度和生死恐惧的记忆。他对这些文字非常珍视,有一种朝圣般的敬畏心情,尽管书中的人物颇多传奇性,但他还是不愿把这些“故园往事”处理成小说,因为它缘起于对母亲的怀念,是饱蘸泪水的生活实录。
一、“故园”的空间诗学
“故园”这一地理空间凝聚、统摄、吸附了李新宇先生的“往事”,是他的乡愁指向所在。故园这片土地的“历史”也被复活,呈现出活的灵魂,搅扰、参与着他现实的思考和精神生活。《故园在青州》《遥想当年广固城》《回望宋朝的青州》,虽是写青州的历史,但这并不同于以往的正史和当下的教科书历史,这些“历史”是李新宇的精神产物,同时又是历史存在的产物,是他与历史相遇的产物。
“故园”的概念是以“老宅子”为坐标的。“老宅子”实际上是“故园情结”的核心空间,并由此延展开,连缀起来的还有西园、南园、店里,这些曾经熟悉的活动环境,构成青冢——这个富有诗意的村子。故园的洼、故园的裙带河、故园的大水,这一个个故园地理空间,通过回忆都被填充上生动的细节,成为作者精神的滋养。“故园”在他的精神结构中是活的,是运动着的,也是成长着的,自我日常中实现出来的现实性,也是这个精神中故园自己运动的结果。
《故园在青州》是《故园往事》的开篇。本以为从中能看到李新宇先生对故园青州山水、风土、人情的表扬,却并非。他提供的是另一种让人震撼的图景:一次次屠城,一次次迁徙,历史上真正的青州土著及其后裔,早已不复存在,“我的先人是在大明永乐年间被绳子牵着移民青州的。”这段被历史之血浇灌的土地,本是异乡,却成了故土,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这故园的深沉的热爱,因为,他的生命已经和那块土地牢牢地扭结在一起,这故园不仅是他生活的环境,本身就是他的生活。另一篇《我的家乡是个洼》,这个“洼”却是颇有些来历的,村名叫“青冢”,是为纪念隐居的帝师——后周皇帝郭威的师傅,死后埋在这里。古代头盔、宝剑和钱币的出土,证明这个地方曾经的厮杀和繁华。
李新宇对故园的“河”情有所钟,一个人的童年拥有一条河是幸福的,它拓展了童年生活经验和乐趣。他记忆中的这条河是清澈的,也是浑浊的,但绝没有现在污染的可怕情景。
以自己的“老宅子”为原点坐标,李新宇先生构建了他的“故园”,这“故园”既是他曾经生活过的“故园”,也是经过记忆汰选过的“故园”,它是现实的,或者说曾经是现实的,从自我意识的内在面来看,这“故园”仍然是现实的。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它又是文学的,是李新宇先生自己的创造物,是在纸上建立起的“故园”,为每一个异乡人所共有。
二、血亲与乡俗书写
“故园”总是和“家”联系在一起的,这里所说的“家”是那个曾经有过、但已失去的“家”,说它失去是指在现实意义上已经不再存在了,仅仅是在精神中“活”下来。“故园”的真正主人是“血亲”,所以写“血亲”就成了“故园往事”中最重的一笔。
《血亲》中写母亲、父亲、祖父、曾祖、高祖,本圣大爷、本典大爷、最初的茶友、雨花嫂子、四妹。这些亲人中,又着力写了母亲——《母亲逝世周年记》《母亲逝世三年祭》《母亲的遗憾——母亲逝世十年祭》。古往今来,写母亲的文字浩如烟海,而这些文章又大都写于母亲去世后,这些文字多有“字字泣血”的沉重力量。尘世间的母子关系仅仅是一个时间段,离开了这个时间段,现实中的母子关系实际上已经被时间的必然性所褫夺,但“母亲”却在精神存在中获得了永生,一方面母亲的影响持续存在;另一方面,“母亲”已经融为泥土、归于大地,母爱弥散在天空云霓之间。隔开时空距离、生死之遥,人们对于母亲的认识却更加清晰。《故园往事》中的“母亲”,主要回忆母亲在大灾难面前做事的仪式感。三年灾害大饥饿时期,母亲每天都准时开饭,无论是什么总得让大家吃点东西,即使仅仅是一种开饭仪式,也足以能给人力量,这也是全家人能活下来的一种保障。文中写母亲的从容、镇静,写母亲的大家气象,字字血泪,给读者强大的感动力量。而写父亲的严厉、父亲的未展襟抱的淡淡遗憾,带有对自己当时未曾理解的愧疚。文中对祖父、曾祖、高祖的事迹考据,颇有些无根漂泊者的寻根冲动——故乡是回不去了,也只有回不去的,才能成其为“故乡”。
在“返乡冲动”中,李新宇对传统呈现出复杂的选择:一方面对传统中的不利于现代人格独立、人格健全的方面,给予坚决摒弃;另一方面,对一些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仪式,同样给予了温情的回望和瞩目,并对这种传统的消失抱有深深的遗憾。虽然李新宇先生深得鲁迅先生“反传统”真味,但要把他看成是一个不分皂白的全面的反传统者,也是不准确的。在《故园往事》中写到婚礼、年俗等。婚礼仪式是千百年来这片土地上的人的自我选择,是中国人繁衍生息合法性、存在感的基础。这些仪式在文革之后被主流意识形态征用,传统婚礼中的拜天地改换成向政治领袖像鞠躬发誓,就显得滑稽荒诞,这也反映出政治权力对社会生活无孔不入的覆盖。在年俗中,中国人通过辞灶、忙年、拜年,确立自我与世界的存在关系,一代代中国人通过这些民俗活动,使得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即使在艰难困厄中也能有所持守、有所希望。
李新宇对乡村文化的毁灭表达了自己的惋惜。他写道:
旧习俗并不值得留恋,……却不是自然淘汰和进化的结果,而是由于权力的介入,所以毁灭的突然而迅速,又因旧的毁灭之后并未出现更好的,那被毁灭的就更加令人惋惜。有些文化的毁灭,固然是与“权力的介入”难脱干系,但多数是因为这种文化自身已经不再具有现实的生命力,毁灭就毁灭吧,没什么值得惋惜的。而且一种新的文化正在生成中,这种新文化的生成与旧文化的毁灭是同步的,或者说就是一回事。
李新宇对传统中某些可贵因素的继承,使得他成为“最后一个士大夫”——这是他不同于一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面。他要解决的还是人的精神独立问题,当然这方面西方已经有非常成熟的做法和经验,但基于环境的巨大差异,他并不认为这是容易解决的事,因为事情的复杂性往往超过一般想象。他对鲁迅精神的传承:启蒙、对专制的反抗、对人性的呼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变得更加复杂、更加积重难返,但同时也产生出新的机遇与可能,由此,对于人,对于人的美好,李老师给予了肯定,显示着他的希望。
三、一个人的历史见证
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他们的成长轨迹,都打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这一代人所经历的物事,随着社会推进,正在慢慢消失。用史家笔法记录下这一代人的生活往事,不仅是个人的心灵记录,也是一个时代不可再来的面影。李新宇记录下《儿时的歌谣》《我也上过幼儿园》《初小的课堂》,尤其是表忠心、查“反标”、找“传单”、以及“拾粪”等。那个小学同学雨中保护红旗的事迹,打下了一个时代的深刻烙印,是不可复制的独特的历史见证。“为了不让红旗淋雨,他还脱下衣服把红旗包了起来”,从而成为了英雄。这难得的历史记录,现在看来有其荒唐的一面,但从另一方面来看,那时的学生生活也有很多的社会实践,对比历史,现在的教育并没有变得更好。
50年代出生的人,在他们的人生记忆中无法抹去的是:大饥荒。这是这一代人回忆中的难以忽略的“情结”,是文学表达的一个重要题材阈。饥饿是恐怖的,是要饿死人的。李老师为这一段历史写下了浓重的一笔:《榆皮》《谷荻》《毛大嫂》《倒地瓜》《晒瓜干》《馇豆腐》等这些篇目本身就都与“吃”有关。《榆皮》中记录了他掌握的“绝学”——剥树皮——这是饥饿岁月练就的吃饭的硬本领。“活着”已经内化为中国人的信仰,尽量活着,尽量活得长,并尽量多的繁衍后代——这几乎是所有物种最原始的本能,唯此我们才能理解爷爷为后辈们栽种一片榆园。
在《谷荻》中可以看到,谷荻是李新宇先生小时候吃的一种茅草的芽,那时候即使是童年的娱乐和游戏,也与寻找吃的有关。找谷荻既是一种具有吃饭的功利目的,也充满了童年的乐趣,否则只管吃就是了,哪里还有什么此起彼伏的歌声:
谷荻谷荻
抽筋剥皮
今年出来
明年还你
现在每每谈起这段让人们难忘的饥饿往事,80后、90后以至于以后的后们,往往感觉陌生而荒诞,他们并没有任何这方面的体验。即使有想认真了解的年轻人,也往往想当然地认为,那个年代除了饥饿之外,毫无欢乐可言,这是与事实不相符的。作者在他的文字中复活、呈现了这一段的记忆,无论生活多么艰难,也仍然有快乐。当然,人们对记忆的修改过程是复杂的,在回忆中,往往记住了一些愉快的成分,即便是这样,也给我们提供并分享了他自己的记忆和体验。即使是在面临饿死的恐惧中,人们依然可以保持有尊严地生活,并保持自己的欢乐心境。这首谷荻歌,不就是孩子们唱出的欢乐和希望吗?也正是依靠了这些欢乐和希望,无论经历多大的灾难,这个民族还是延续下来,并能有所发展。这大概是李老师文字给我们的宝贵启发吧。
四、故园“志异”
李新宇先生的故园处在齐文化中心区域,与鲁国文化不喜“怪力乱神”相反,齐文化喜欢谈论这些神神鬼鬼、花妖狐魅,甚至不只是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是作为生活中的文化因子参与进人们的精神建构与日常生活中。对故园的怀念,使得他遵循严苛的写史笔法,但在《故园往事》中专门列出了一辑《志异》,专门标出,列为一类。这并为了猎奇,而是这些“奇异”并不离奇,而是人们的心理现实的一种呈现,并且这些已经参与和融入到当时的现实生活之中。《故园往事》中的《志异》当然与《聊斋志异》不同:这些神神鬼鬼的怪异,是人们生活中的一种心理所致,也许李新宇先生并不信以为真,但从心理真实、心理幻象的角度来理解这些来自于故乡和童年的怪异,这些文字不仅仅增加阅读的情趣,还记录当时情境下人们的情感活动。当然这些神仙鬼怪的世界,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想象的世界,为现实生活的逼仄和艰难提供了一个精神寄托的处所。《两个怕鬼的老师》《一个还魂的神医》《大姐家的火灾》《西洼的“火蛋”》,都带有“传奇”色彩,这些故事或者联系着敬畏、恐惧与劝解,或者是故乡人对生活现象的解释,寄托了人们的愿望,也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随着社会现代化、城镇化的推进,这些神神鬼鬼的怪异故事已经缺乏存生的乡野空间,这本身是一种遗憾,也为我们反思这种并非自然演进的、政治强力干预下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种视角。
《故园往事》对体裁的自我确认是这样的:“我知道,如果写成小说,加上一些想象的细节,加一点矛盾的冲突,会更生动。但我有点舍不得,因为我所经历的,是这个民族真实的历史,我不忍心让它成为‘小说家言’。这与我反对一些评论家把作家严肃的历史思考解释为新历史主义一样。”(《故园往事·二集》,第143页。)正是因为对“史”与“小说”的这种区别性理解,李新宇先生才对自己的近邻老乡有了比一般论者更透彻、更妥帖的理解:“面对莫言的小说,有人用‘新历史主义’概括,我总感觉很可惜。因为我总是看到莫言饱含热泪写他的经历和见闻,为此冒着风险。……但我知道,莫言并不是说着玩儿的,他的史家之笔也绝不是在历史叙述的真与伪。所以,他的小说大概也有足够的历史事实作为依据。”
李新宇先生以文学研究见长,但他并不大希望别人把《故园往事》当成纯正的文学来读,这里牵涉到一个对文学概念的理解问题,他还是愿意读者把这当成历史来读。
《故园往事》是学者散文领域的新收获,李新宇先生的文字背后是浓厚的故园情结。他通过对“故园”的回忆,为我们复活了专属于他的历史见证,为每一个有过乡村生活经历的人,创造了一个纸上的“故园”。这里面有眼泪、有温情,有惋惜,是曾经鲜活的生命,是他生命的来处的流动,一直流到今天的。缘此,我们能够在失去故乡的漂泊流浪中,重获故乡,借此慰藉那渐行渐远的乡愁。
张厚刚(1970-),男,文学博士,聊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聊城 252000),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桂林 54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