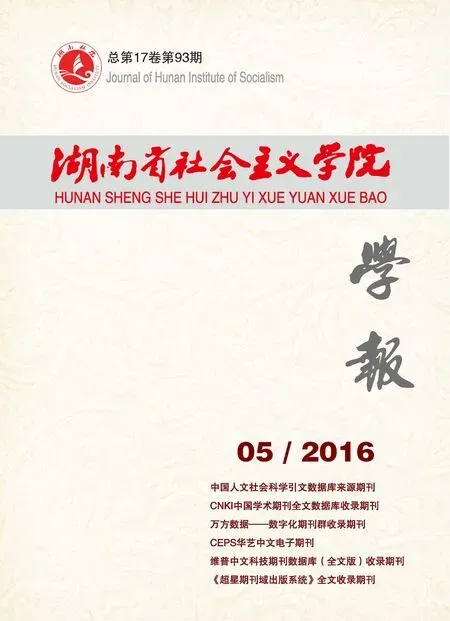美国战略联盟对中国的影响及应对之策
彭培根
(湖南省社科联,湖南 长沙 410003)
美国战略联盟对中国的影响及应对之策
彭培根
(湖南省社科联,湖南 长沙 410003)
长期以来,美国利用说服、诱导等多种手段方式积极强化对联盟的管理与控制,实现自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最终目的。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美国也逐步调整并强化自己的战略联盟,制约着中国周边安全、经济影响力提升以及国家形象塑造等。为此,中国应该在积极发展与中美友好战略伙伴关系的进程当中,促使美国控制好自身的盟友,并且同时与众多的美国盟友也建立起相应的友好关系,加强交流与合作,制定对策与方法,最大限度内避免美国战略联盟带来的干涉和影响。
美国战略联盟;中美关系;影响;对策
自古以来,战略联盟一直是各个国家和地区普遍使用的实效性较强的国家安全战略。二战以来,美国的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发展联盟政策,在世界范围内都建立起了诸多的正式与非正式或其他形式各样的联盟组织,以实现自己在全球范围内的霸权和利益,北约组织就是美国实现对苏联的制约和抗衡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强大的军事联盟。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等一些国家的不断强大和崛起,美国感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进一步调整和强化了联盟战略,重新修订北约东扩和美日安保条约就是明显的例证。今年以来,美国先后幕后操纵了南海仲裁案、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等动作,美国联盟政策的不断调整与强化,无疑会对处在发展关键期的中国产生诸多的影响,这就必然要求中国审时度势,积极应对美国的联盟战略,处理好与美国盟友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内避免遭受美国战略联盟的干涉以及影响,以实现自身的安全稳定发展。综合来看,美国的战略联盟本身具有极强的研究价值,就其对中国的安全稳定与发展的影响,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美国战略联盟的管理方式
由于联盟成员之间存在着利益的不一致以及独自制定并实施对外政策的权利和自主性,相对应地,美国战略联盟的管理方式也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主要看来有以下三种。
(一)利益协调式管理
利益协调式管理就是联盟成员国之间就自己的各自利益达成一种相互之间的协调,并形成一种新的具有共同性质的利益。要实现联盟的核心力作用,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要让成员国之间形成利益的一致性。但在现实中,这种利益的目标并不是一致的,由于各个成员国的对外政策、国内政治体制以及领导人等因素不同,会导致成员国争取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帕累托”最优原则。这种联盟成员国之间的利益一致性程度主要取决于对联盟的需求、承诺以及相关的议题关联程度。如果在这三个方面拥有和占据着非常有利的地位,那么成员国在利益竞争中就能够取得相对主动地位。这种利益协调式的联盟管理方式能很好对成员国实现抑制与制约,从而方便美国对其他成员国的控制与管理。
(二)制度规则式管理
制度规则式管理主要是将联盟看作是一种维护自身安全与发展的规章制度,注重通过规章制度来实现对联盟组织的控制与管理。美国依据这种新的自由制度主义的联盟观点,为成员国之间提供一种相互交流与沟通的平台。这种制度使得它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需要共同遵守的规范,各成员国之间的利益能够有效的得到相互协调,有利于美国对成员国之间进行良好的管理,有利于发挥成员国之间的核心凝聚力,也有利于为成员国之间产生的分歧以及矛盾提供一种制度性的依据和解决方式。
(三)霸权主导式管理
霸权主导式管理主要是美国以主导国的身份,通过利用一些强制性的措施或者价值观输入等霸权手段,来管理以及控制其联盟国和联盟组织。就目前的国际等级体系来看,其实是以美国为主导的等级体系,是美国战略联盟中最为重要的一种。
二、美国战略联盟的特征
美国的联盟外交政策是较为复杂的,而且伴随着国际形势以及自身发展态势在不断地变化和调整当中,但是总的来看,在联盟政策的不断调整过程当中,其最终的指向还是基本一致的,并且显示出如下几方面的重要特征。
(一)扩张性的联盟
美国扩张性联盟主要表现在区域范围的扩张以及职能范畴的扩张。一方面,在二战之后,美国的联盟区域由自己的邻国加拿大、邻洲拉丁美洲扩展到了大西洋彼岸的欧洲地区,进而扩大到了更加遥远的亚洲及其他地区。冷战结束后,苏联的解体没能让美国解散自己的联盟,反而继续扩大联盟的发展。如今,美国不仅已经建立并主导了囊括所有美洲国家的“美洲国家组织”,在亚洲地区,美国建立起了所谓的新月型战略防线,该防线北起韩国,中间经过印度、日本、中国台湾,南部到达菲律宾,一直延伸到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可以说覆盖了大部分亚洲地区。加上美国已经实行了北约东扩计划,自己的联盟范围和规模会日益增大。另一方面,美国联盟政策在职能范畴上面也得到了扩张。二战之后,联盟建立最初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派遣海外驻军,加强武器准备等,随着国际形势变化以及美国自身发展的需要,美国的联盟外交的职能也在不断地变化、调整和扩大当中,包括战略协商、情报共享、科技联合研发、军火武器销售、联合军事演习等多个方面,甚至包括诸如打击暴力反恐、应对走私贩毒、维持地区和平也成为了战略联盟的主要任务。
(二)灵活性的调整
美国在二战之后以及冷战结束之前的联盟一直都是通过签署长期军事盟约的方式实施的,美国仅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中期就确立了多达10个以上的双边以及多边联盟,总共涉及多达46个国家。冷战之后,美国逐渐调整了自己的联盟方式,出现了正式联盟、非正式联盟、条约与默契相结合的联盟方式,联盟的界限也愈加模糊了。美国军事存在方式也随着联盟方式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军事部署也从“前沿防御”逐步转向以“兵力投送”为主、海外关键地区军事存在为辅灵活反应的新形式。”[1]
(三)意识形态浓厚
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相互对立,苏联的壮大以及共产主义的发展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于是美国联合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种“遏苏抗共”的外交战略。正如迈克尔·H·亨特所说:“忽略了意识形态,想重新调整美国外交政策就可能遗漏关键性的一步”。[2]所以,美国联盟外交的意识形态性质是一开始就拥有的,就是为了遏制竞争对手,达到维护世界霸主地位和利益的目的。
(四)不对等的联盟
美国在其联盟外交政策当中始终是处于主导性的地位,始终是处于自身利益出发来调整和实施自己的联盟外交政策的,这就必然导致美国联盟外交的不对等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表现就是权力的不对等。美韩在结盟之初,韩国作战的指挥权就一直由美国控制,作为一个国家的核心权利部分,作战指挥权让出就相当于国家主权的让出,虽然美韩结盟有利于维护韩国的国家安全,但另一方面却失去了国家自主权与尊严。此外,还表现在与盟国义务上的不对等。美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签订联盟条约,为的是双方之间共同承担保护本地区安全的责任。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美国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以及风险,其他盟国没有承担保护美国安全的责任,这种联盟失去了平等的性质。美国联盟外交的不平等性使得美国的联盟体系形成了一个以美国为核心,辐射全球的特征结构。因此,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也逐渐的加强。
三、美国联盟外交的诱因
理论界对美国联盟外交的诱因的论述是非常丰富的,主要的集中在关于“威胁”“权利”“利益”“军事”以及“价值观念”等几个重要方面,根据二战后的国际政治格局以及美国自身发展的特点,导致美国联盟外交主要有以下几大诱因。
(一)应对面临的国际威胁
二战之后,美苏双方都成为彼此称霸世界最为主要的障碍。于是,美国为了削弱和抑制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生力量,打起了保护“自由资本主义”的旗帜,联合当时有着强烈“恐苏”“恐共”心理的国家形成联盟,共同对付并打击苏联。美国还通过舆论的方式对一些联盟成员国大肆宣传,鼓吹受到了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威胁,要求结成联盟共同面对苏联的直接或者间接的威胁及挑战。由此可见,二战后美国实行联盟战略的主要直接原因就是为了应对强烈的国际威胁。正如乔治·李卡斯和威廉·赖克所判断:“在美国的现实主义视角里,首要的概念就是不允许有美国之外的其他势力范围存在。”[3]
冷战之后,虽然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苏联解体,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又重新生出了诸多的矛盾和问题。例如一些区域性的动荡、时段性的经济危机、流行疾病的传播、难民的流入等等,这些问题都制约和困扰着美国的发展并对其自身利益构成一定的威胁,于是,美国需要联合相应的国家共同应对这些复杂多变的危机。
(二)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便于其在全球扩张
美国对于别国的干涉和控制不仅限于政治、经济等领域,还涵盖了文化价值观的渗入以及社会制度的影响。美国外交家基辛格曾说过:“美国的价值观使美国人自认为有义务向全世界推广这些价值观”。[4]二战结束后,美国在与盟国密切联系的关系下,逐步在全世界宣扬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以及所谓的民主制度,宣扬这种价值观和制度能够为全世界带来福祉和便利。2015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强调要“推动建设民主制度”。这种价值观和制度的输出,使其他国家逐步认同和接受美国文化和制度,有利于美国更容易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自身的国家利益,这也为美国实现自身利益的扩张和构建以其为主导的超级大国体系奠定了强大的文化前提和制度基础。
(三)加强对盟国的干涉与控制
加强对盟国的控制和干预,有利于美国实现一系列的其他目的。首先,美国对盟国的军事力量发展进行一定的干预和控制,以防止其威胁到自己的发展利益。二战之后,遏制法西斯势力的再度崛起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任务,美国也及其担忧,诸如日、德这样曾经的法西斯国家的崛起会对自己产生威胁,进而也不断的加强对它们的军事力量的遏制与干涉,使得德日的军事力量出现了片面发展的局面。其次,二战至今,美国还一直以自己超级大国的地位身份和强大的军事力量直接或间接的干涉他国的内政。二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美国政府都操纵着德国和日本政府并对其国内进行“民主改革”和“重新武装”,这一联盟形式使美国干预和控制他国的行为成为一种“合理”行为。最后,美国还积极通过战略联盟攫取成员国的各种战略资源,例如资金、能源、技术、人才、基地等。越南战争中菲律宾和泰国的大力支持就是显著的明证。
(四)获取海外军事存在和军事干涉的合法性
美国经常以保护盟国安全为理由向盟国地区进驻军队,促使盟国听信并服从其军事管理。在冷战期间,美国就以遏制苏联等目的为由,在盟约的安全许诺下获得了在盟国保持大规模军事力量的合法性。有数据显示,至1989年以来,美国在海外的驻军就高达458740人(不包括停泊在公海上的海军)[5]。冷战结束后,美国依然没有放弃通过联盟来继续获得更广范围的海外军事存在以及军事干涉的合法性。近30年来,美国向外驻军的数量不断地增多,尤其是克林顿政府、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期间,美国在欧亚以及亚太两个地区各自维持了大约10万人的军队,而且在东南亚、西南亚以及东北亚等地区也进驻了一定数量的海军。美国国防部在2014年《四年防务审查报告》中重申了军队能力建设目标,创新海外军事存在,深化与重要盟国之间的合作。[6]总而言之,美国利用多种手段不断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联盟,这种联盟政策为其在海外获得军事存在以及军事干涉找到了合理的理由。
四、战略联盟调整对中国的影响
一直以来,美国的联盟政策,尤其是亚太联盟均与中国的发展息息相关,也显得极为微妙。虽然美国一直打着维护地区安全的旗子开展联盟政策,但是在面对中国日益崛起的情形下,美国战略联盟外交政策防范和抑制中国崛起发展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一)造成中国周边安全的巨大压力
美国联盟政策最为显著的影响就是对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冷战以来,美国就一直联络和调整与中国存有争端的一些国家的关系,对它们予以军事、资金、技术、人才的支持,借此来抵抗和抑制中国的发展。近些年来,美国不断加快调整其亚太联盟政策,积极调整和部署其在日本、韩国、菲律宾、新加坡等地的军事战略,间歇性的与其东亚的盟友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活动,在强大的武力震慑下,许多亚太国家不得不听信和服从美国的安排和调遣。美国的亚太联盟政策对中国周边环境的威胁是极大的,造成了中国安全发展的巨大压力。
(二)消解了中国在亚太经济上的领导地位和影响力
美国联盟外交的调整还试图削弱和消解中国在亚太经济上的主要领导地位和影响力,使得中国正常的外贸交易以及区域合作的不稳定因素大大增强。中国经济社会的大力发展,促使东亚已经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盟自由贸易区,但是,美国却一直试图推动其在东亚的盟友推行TPP谈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来架空自由贸易安排,将中国纳入自己及其盟友设定的多边框架之中。而中国一旦进入这种多边框架之中,其对外贸易的发展必然受到制约和阻碍,自主性就会大大丧失,在亚太地区的经济领导地位也将会大幅度下降;但如果不加入TPP谈判,则中国就会游离在外,其多边贸易就会受到巨大的影响,以至于导致整个中国经济发展遭受巨大的阻碍。
(三)促使中国受困于地区国家间竞争增加崛起成本
美国时常联合其亚太地区的盟友在中国周边以及安全地缘边界进行军事威慑和围堵,迫使中国必须做好军事防御措施。此外,许多周边国家之间与中国时而产生各种各样的摩擦、冲突,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就是显著的例证。中国在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竞争市场受到困扰和制约,而中国本身却由于需要实现自身的发展,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相对妥协的空间很少,这样一来,必然导致中国国家形象呈现出一种四面出击、咄咄逼人的状态,这种近乎强硬的态势又再一次加重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忧虑感,促使它们与美国的联盟关系更加的紧密而与中国的关系则更加的紧张甚至恶化。中国的国家形象便在这种国家和地区间的竞争当中遭受到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对中国的崛起也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增加了中国发展的成本。
五、中国应对美国战略联盟的策略建议
根据以上对于美国联盟对于中国发展的影响分析,可以清楚的看到,虽然目前美国的联盟战略对中国产生了一定的挑战与威胁,但是这种挑战与威胁至今还是处于潜在的,并没有爆发出的状态,故而“中国的世界态势应当是既有防范和斗争,又有协调和顺应,而且协调和顺应应当多于防范和斗争。”[7]
(一)大力提升综合国力
强大的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取得国际地位的重要保障。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尤其需要良好稳定的内外环境,只有稳定才能求得发展,才能实现最终的国家利益。中国要积极利用当前和平的发展环境,不断完善自身不合理的体系,加速改革开放,健全体制机制,全面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二)正确处理好对外关系
中国要实现自身发展,就必须处理好自己的外交关系,这是影响中国发展的十分关键性的因素。中国应当致力于与其他国家一起共同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的步伐;保持与俄罗斯的友好伙伴关系;构建良好的周边发展环境和周边安全机制;积极促成构建新的国际安全观,努力打破美国的联盟安全观和绝对安全观的束缚。
(三)加强军队国防现代化建设
强大的军队以及国防现代化是保证国家统一,实现发展的基本保障。中国的和平与发展必须要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坚强后盾。建议国家进一步加强重视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加大投入,创新理论,培养人才,构建和完善新的、有效的发展机制,实现整个军队和国防整体实力的有效快速提升。
[1]刘芹.二战后美国的联盟外交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0:40.
[2]汪诗明,王艳芬.论二战期间澳美军事同盟关系的建立[J].安徽史学,2005,(2):5-10.
[3]赵嵘.美国联盟战略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35.
[4]亨利·基辛格.大外交[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2.
[5]陈波.李承晚政权与美韩同盟[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7:45.
[6]美国国防部2014年四年防务审查报告[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4.
[7]时殷弘,宋德星.21世纪前期中国国际态度、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J].战略与管理,2001,(l):10-19.
(责任编辑:许 烨)
D523
A
1009-2293(2016)05-0085-04
本文系湖南省美国问题研究中心立项课题(项目编号156MGWTZD9)阶段性成果。
彭培根,湖南省社科联助理研究员。
【DOI】10.3969/j. issn.1009-2293.2016.05.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