迹象论和高校美术教育
钟孺乾
一个问题与另一个问题
一直以来,高等院校的美术考试内容是以绘画为基础,而且是以古典写实的西画为基础的。不管学生将来最终学习和从事何种专业,在高考这一环节上,你得就范。有没有人怀疑这种模式的合理性?有没有人想到要改变这种模式?至少在当前,还来不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尽管许多人承认这是一个问题。很明显,古典写实西画作为一切美术专业的基础其实是大可怀疑的。以真实对象的造型和色彩摹写为依据来判断学生的艺术才能和发展前景,这种模式只能适用与审美标准相对固定、艺术功用相对单一的某个历史时期,在当代已经捉襟见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画(尤其是水墨画)在高考和整个大学美术教育的大格局中处境窘迫的原因。不仅中国画是如此,凡属西方写实绘画血缘以外的门类都会遇到尴尬,因为人们在设置这一模式时,只想到照顾实际操作的权宜性,而没有为它准备好与当代艺术现实相对应的理论依据。中国发生的这个现象在国际大环境中具有很典型的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往深里略一追究就会提出另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出现一种认识,一种概念,从而产生一系列的阐释方法和品鉴途径,来指导视觉艺术如绘画的学习、创作与教学?也就是说,视觉艺术是不是应该从基因和元素入手来建立与实践相匹配的基础理论?不仅为考试、为教学,而且为视觉艺术这个学科提供一块基石。如果肯定了这个必要性,那么,迹象论就可以说是应运而生的了。
迹象论的应用特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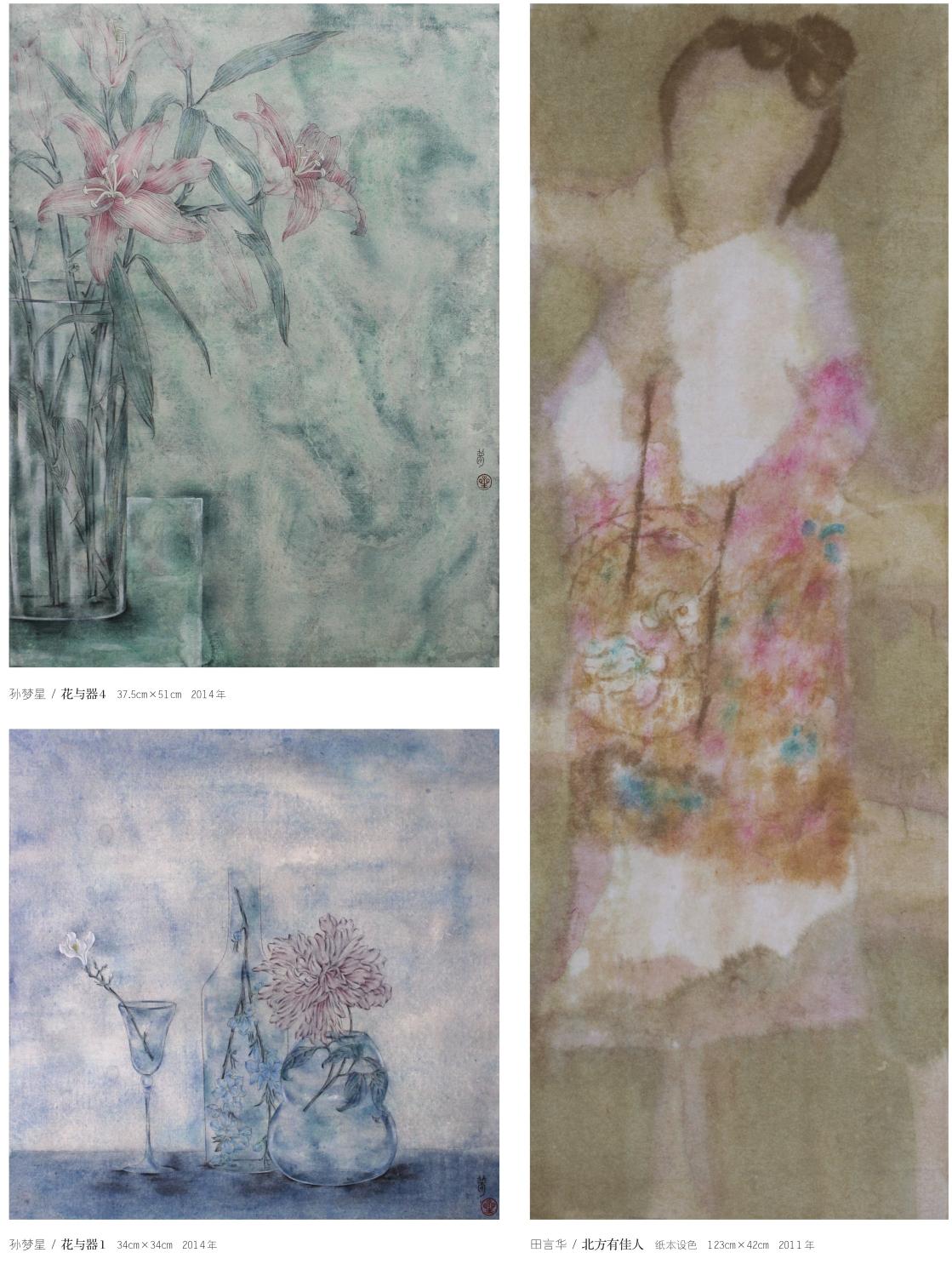
所谓迹象論,简而言之,就是将视觉艺术的基因和元素分解为迹与象两个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概念,比如绘画,我们认识上应该把绘画理解为一种作迹造象的工作,这种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地表达。从这个关系中可以提炼出这样的公式:迹+象+X =画。迹象,或者分而言之,迹与象,是绘画的视觉基础。我们画(制、作)出来的所有可辨识的和不可辨识的迹与象,都是可以在迹象论(我之所谓基础理论)的范围内加以阐释和评价的。对于一件作品,即便是一幅习作,都可以依据一定的迹象标准来论定成败优劣,分析出品鉴的道理和来由。迹象论直接从理论述说中抽绎出实用性能。
认识的捷径
凡事认识到了,就成功了大半。找到了一个独特而便捷的视角来认识事物,当然会省去许多迷障,从而一步到位地认清问题的真相,领悟解决问题之道。以中国画为例:自从将笔墨论定为水墨画的认识途径和技法原理之后,学习和创作就有了可以简化理解和便当把握的理论凭借,笔墨(或者笔、墨),因而成为水墨画的制作法,同时又是品鉴法。这种情形,正与迹象论相类似,只是迹象论远远超越水墨画一个画种,而在一切视觉艺术领域内发挥作用。任何一件视觉类的作品,我们都可以这样认识和探究它:这样的画面或实体是用什么样的迹、什么样的象以及用什么样的迹象生成方式来完成的?这些迹象能够表达什么?或者,它使我们接受到了什么信息?在这样的基础上做出的判断具有多大的效力,这要看你的认识质量,还要取决于审美的多种内部和外部条件。不管怎样,从迹象论的角度来考量作品,切合古今中外的各种实践,尤其切合当前与未来的创新实践,
迹象论也适宜于设计艺术
以上的议论基本上能说清楚拙著《绘画迹象论》的大意,不过这个书名是为了集中表述的需要而有意压缩了的,其实,在绘画之外的视界,也脱不出迹象论的涵盖。因为常识告诉我们,凡视觉艺术作品必然起始于痕迹,而有迹就必定有象,(虽然有时无迹也可能有象,比如画面上的空白之象),有迹有象又有所表达,就纳入了迹象论。从艺术设计的“出身”来追溯,设计源于绘画,因此所有属于绘画的元素,设计都应具备。设计的特殊性在于其审美特征与功用特征的适应性;但就工作结果而论,就视觉本体而论,完全可以说,设计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于迹象的更为程式化的推敲与谋划。从创作论和接受学的互动关系上考察,愈接近于现代,愈适用于当代,愈致力未来趋势的探究,就愈远离既往的模式而出现失范和失语,以往的观念、认识、概念和话语,越来越不能解释新的实践,迹象论正是在这样的境地上登台的。在高校美术课堂上,教师和学生常常面对一件“前卫”的设计作品无言以对,临阵脱逃的说法往往是让大家自己去“感受”,甚至认为“好作品是无法解释的”,这实际上等于取消了美术教育,至少是取消了美术教育中的理论和鉴赏。我认为其实不然。我们应该换一种思路,换一个视角来理解视觉艺术,迹+象+X,这正是视觉创作和验收时行之有效的方法。综合、分析是人类的两大思维方式,设计的创作法,从根本上说就是象征性内涵(“X”)的发散思维法,迹象的组织法,迹象传达的“游戏软件”编制法。对于像设计这样特别强调秩序感和独特性的门类来说,迹象论是不可不重视和加以运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