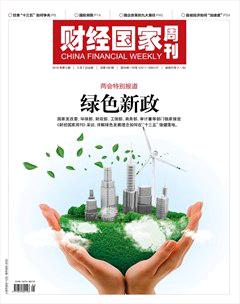课堂上的金融帝国
王亚宏
如果在同学的微信群里推出这项服务,那么妥妥地就是互联网金融了。
女儿读小学一年级。老师为了更好地激起孩子们的学习热情,推出了一套奖励方案:只要累积足够优良的表现,比如认真做作业、上课积极发言,就能得到一张印有奖杯图案的小奖票。而每个同学在累计到10张奖票后,就能从老师那里得到一张奖状。
这套在我看起来与自己小时候得小红花一脉相承的制度是完美的,起码经过了时间的考验,但我却忽视了在与时俱进的语境下,自己当年拼命积攒的行为貌似有些过时了。
不能低估六岁孩子对荣誉的渴望,女儿在即将得到自己奖状的前夕,甚至为最快速度地获得下一张奖状设计出了一套方法。她问我能不能先借别人暂时不用的奖票,来获得下一张奖状,然后自己有了再还。或者她在得到奖状后,也能把先不用的奖票借给别人。她给出的理由是这样能让大家手里存的奖票“用得更快更优”。
当从稚嫩的童音中听到“更快更优”四个字时,颇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没错,在全球四大央行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上,这不就是常见的“增加流动性”和“债权打包”吗?只是换了一个说法而已。一个孩子的逻辑怎么和华尔街的那些银行家们如出一辙,莫非是偷看了放在桌上的分析报告,或者受到从小和她一起玩耍的犹太朋友考普斯一家的影响?难道孟母三迁是对的?
当务之急是打消孩子这种会对现存“奖票-奖状本位制度”造成颠覆性影响的想法。于是再三苦口婆心地劝诫娃只有通过自身努力,好好表现得到一张张的奖票,积攒下来换的奖状才是正道。说了一大通后她貌似接受了我的看法,可在巴拉巴拉的说教间自己却觉得她的想法貌似真的不错,于是等她睡后就打开分析工具开始写写画画,发现这和固定收益交易颇有相通之处。
首先“课堂市场”上对奖票存在需求空间,而且也有尚待盘活的存量可以作为隐性的供应方。在开学12个周里,班上已有8个孩子凑齐了10张奖票,其中最短的一位用了9周时间。通过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可以看出,奖票兑换奖状的高峰将在14-18周出现,届时出于结构性压力,或许是来自家长,接近换取奖状的同学都会对最后一两张奖票有巨大的需求。而另一方面,鉴于一个学期再有6周左右就会结束,因此孩子们第二轮用奖票兑换奖状的概率不大,而那些已经换取了第一张奖状的孩子们,在这期间手里又能趱下多至6张奖票,他们倒是可以借出这些奖票,从而作为老师之外的第二个奖票来源。
为了解决奖票资源错配问题,一个借贷平台便可解决。当然借要有成本,贷要有收益,因此信用凭证和抵押凭证就能应运而生。对孩子们来说,抵押品和收益或许只是一支铅笔之类文具的使用权,此类东西已经足以作为他们喜闻乐见的标的。
既然抵押的问题解决了,对于制度来说就是合规与风控的问题了。虽说在老师眼皮底下互通奖票有无本来就和规矩相去甚远,但一些必要的流程设计还是能够降低崩盘风险。比如要定期整理借贷账目和抵押品,考虑如何让更多同学参与进来——这一流程属于司库和资产二次打包范畴;另一方面甚至可以引入熔断制度,比如有同学想要回自己的奖票,但资产储备的奖票又不足兑换时,可以放言“我要赶着去上兴趣班,今天就玩到这儿了。”当然,银行一般管这一过程叫做“系统升级”。
在风险方面,应该庆幸孩子能够从机制的角度来考虑解决方案,而没有去淘宝上搜老师印奖票的同款印章。否则的话在短时间内会有大量奖票进入流通领域,不受抑制的通胀现象会引起老师的察觉,顺藤摸瓜就能找到增发的根源。和私印奖票相比,构建框架无疑要安全得多。而且由于本身并不影响M2奖票的总供应量,而只是增加流动性,因此也更容易逃过老师这一监管机构加发行机构的法眼。
至此,一个基于老师发行的“奖票-奖状本位制度”基础上的借贷框架已经雏形初现。如果在同学的微信群里推出这项服务,那么妥妥地就是互联网金融了,而且在奖票的传递过程,还天生带有O2O的属性。画面太美不敢接着想了,这是冲着去纳斯达克敲钟的节奏。
不过在这美梦成真前,按照女儿的说法就是不能让老师知道这个构想。因为从理论上说这种最大的黑天鹅事件足以引起金融海啸摧毁任何制度设计——强大如巴林银行以及雷曼兄弟都会灰飞烟灭——作为发行方和监管方,老师一个小小的改动就会让这个尚待构建的金融帝国轰然倒下:比如给每个孩子发的奖票上都写上名字——这种行为叫定向发行。
(作者为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