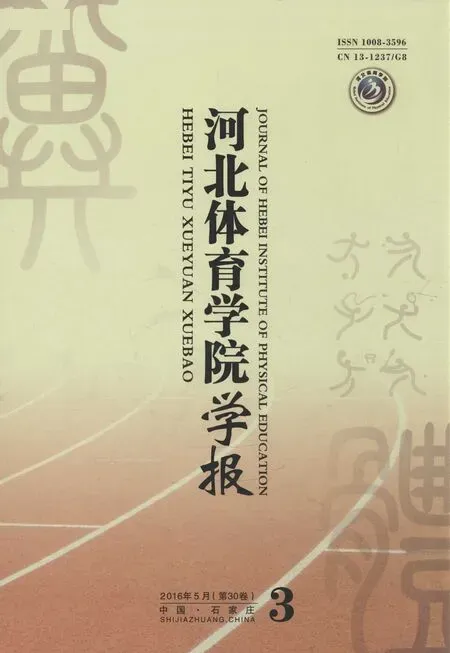道德、认知、美学:广场舞事件的三重维度
侯胜川
(闽江学院 体育教学部,福州 350108)
道德、认知、美学:广场舞事件的三重维度
侯胜川
(闽江学院 体育教学部,福州350108)
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对近年来的广场舞事件进行分析。指出广场舞事件已成为现实版的武林,并非场地设施、“招安”“收编”等技术层面的办法可以完全解决。进而从道德、认知、美学的三重维度阐释广场舞事件,认为广场舞事件双方都不具道德责任,在道德监控和镜头监控乏力的情况下,对广场舞事件的认知格外重要,由于老人和年轻人对“家”的认同的差异,加之社会长期以来对老人的忽视和不尊重,以及碎片化时代对技术的依赖造成的社会整体道德滑坡,老人对安全、温暖共同体的向往等诸多原因导致广场舞事件发生。陌生人只有融入情感、参与其中才能体验美学意义的广场舞。
广场舞;道德;认知;美学
1 舞林即武林——广场舞的江湖
1.1现实中的武林
扔水袋、鸣枪、泼粪、泼汽油、放狗、倒玻璃碴、放气、贴车窗、定向音响等等不一而足的暴力行为在近年来的广场舞事件中一一上演,本应是极乐之地的社区广场却成了以暴制暴的极恶之地。四川绵阳市邓稼先广场一位广场舞大妈在跳舞时忽然倒地,疑似被来历不明的散弹击中;福州市一位司机在上班路上汽车忽然失控,却是因为汽车占据广场被广场舞大妈扎破轮胎;武汉市黄陂区的一位广场舞教练在即将离开时被三个蒙面歹徒砍了20多刀……广场舞的江湖里,舞蹈者和被扰者之间上演了一幕幕现实版的武林。在堵不如疏的理念下,政府采用“收编”“招安”等策略来管理广场舞群体,企业也通过耳麦、定向音响等科技手段解决类似纷争,虽似有短期效果,广场舞大妈也有所收敛,但是大妈们“不跳舞,你让我们干啥?”[1]的质问,预示着广场舞事件远未偃旗息鼓。
1.2网络舆情中的江湖
相对于纸媒和视媒,在网络媒体的话语中,广场舞群体更是被“妖魔化”了,“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等言论虽不值一驳,却激发了舆情的放大效应,网民的无边泄愤心理在这一事件中推波助澜,广场舞事件的负面新闻被深度挖掘,积极影响被忽视。在公众最为关注的高考期间,广场舞群体主动减噪音或停止跳舞被有意无视,而极少部分广场舞群体在媒体的“找茬心理”“娱乐心理”中被刻意放大,对空巢老人、失独老人的业余生活以及老龄化社会中老人的休闲、健康需求视而不见。在舆情的抑扬褒贬中,广场舞群体成为大众口诛笔伐的对象,大妈们更是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成为和谐社会的毒瘤,几欲除之而后快!人们不禁疑惑:何以外国大妈没有广场舞?本应慈眉善目的老人何以成为社会唾弃的对象?
2 广场舞事件的三重维度
在近年的相关研究中,有学者从公民基本权利等法律视角来探究广场舞事件的解决之道,如“统筹利用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从立法、司法、社会三个层面实现体育权利与居民安居权利的动态利益平衡。”[2]然而,早有学者指出:“仅就广场舞噪音污染而言,中国和国外最大的差异是执法力度”[3],为何对广场舞噪音污染无行政处罚非本文的讨论范围,但从中至少可以看出通过立法、司法形式处理广场舞事件条件尚不成熟。问题的表象可能千差万别,而实质却往往相同。本研究试图从道德、认知、美学三重维度来阐释广场舞事件背后的深层社会问题。
3 广场舞事件的道德维度
当广场舞事件出现时,多数人想到求助于法律,实际上,如上文所述的交恶事件中,法律所能起到的作用仅是震慑和控制事态升级;于是又有人提出道德问题,但是国家层面上并无道德立法,即便是党和国家大力倡导的“以德治国”“八荣八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也是旨在构建和谐社会和传递社会正能量,并无法律上的约束力。在国家道德立法缺席的情况下,人们开始了道德领域的自治。
在莫里斯·布兰切特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监狱,在每个人的监狱中,他们都是自由的。莫氏笔下的监狱即道德,它需要生活在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每个人自觉遵守,是一种不自觉的契约精神在束缚每个人的自由,一旦有人逾越就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效应。然而,“道德在自我模糊的环境中运行、感知和实践,充斥着不确定性。”[4]14在某个环境被认为是约定俗成的习惯可能在其他地方或其他时间被直接无视或者反对,也因此,某些人的盛宴可能是另一些人的毒药。道德的这种不确定性恰恰给广场舞事件中的双方在依靠道德解决争端时埋下了交恶的种子。
3.1作为广场舞事件受害者的“我”和他者
广场舞的受害者与广场舞群体共处一个相对封闭的物理空间,作为陌生的邻居而存在,共享和共有该物理空间。作为共存同一物理空间的“我”和他者是平等对称的,不存在“我”为他者而存在的问题。在人们的潜意识中,道德问题一定是包含了某种互惠的观念,即“你敬我一尺,我让你一丈”的道德交易范式,在互惠的过程中,陌生的邻居成为熟识的邻居,为今后扩大互惠创造了条件。然而在道德问题上,关于责任一词,仅仅是对“我”而言的,这些道德规则都是“我”所遵循的,对他者并无约束力,因此,就“我”来说,责任就是道德;而当“我”想用道德来约束他者时,问题就出现了:在广场舞事件中,他者侵占和扰乱了共有空间,在这一过程中,“我”和他者不具互惠关系,“我”和他者变得不平等对称了,即他者破坏了这种原有的道德平衡关系。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真正道德的人,应该是为他者而存在的。那些为祖国、民族、多数人的利益而无私付出甚至牺牲生命的人成了道德上的英雄。它告诉我们,无论广场舞事件中的他者是否履行了和“我”一样的道德责任,“我”都应该继续履行自己的道德责任。而事实并非如此,道德理想永远都具有乌托邦的性质,所以,“我一贯是带着将压垮道德冷漠这只骆驼之背的稻草的人。”[4]60并以此作为“我”的道德冲动和非法激情的挡箭牌:因为他者先不道德,所以,以泼粪、撒玻璃碴等破坏共享场地的方式来驱除“我”内心的道德冲动,共享变成共不享。结果是每一个道德冲动的人都导致了不道德的后果。“温州600多住户凑26万买远程定向强声扩音系统”,大妈们一开始跳,就循环放‘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立即停止违法行为!’”[5]在这一事件中,“我”放下了自己的道德责任,加入到不道德的队伍中来。此时,广场舞事件中的“我”和他者重新回到了道德范畴的平等和可以以此为基础进行互惠、交换的水平线上,于是,双方开始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开始争论、谈判,并参照其他标准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最终的结果是双方达成短暂妥协,各退一步再次平衡:“我”撤回定向音响,他者减少噪音,在规定的时间内有限地占有共享的物理空间。
始于“我”对道德权力自治的信任,终于对道德羁绊的游戏。广场舞事件的双方短时的停战和临时解决方案注定将失败,因为道德最终都成了不道德。
3.2作为广场舞群体的“我”和他者
长期以来,人们理想的老人的生活状态是“吃好、喝好、不生病”,丝毫没有顾及老人最基本的平等权利: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以及根据这一权利编织出的自我共同体。
在立交桥下、公园中、社区广场,一群群数十人组成的情感、安全、互助、健身共同体中,社会身份被抹平了,陌生的邻里关系在这里变得熟悉起来,实现了传统意义上地缘共同体中“远亲不如近邻”的社会现实。在鲍曼看来:“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就像一个家,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风避雨;它又像一个壁炉,在严寒的日子里,靠近它,可以暖和我们的手。”[6]在这样的“家”中,成员间的个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集体心理和集体信仰,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个体因为不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而成为大众心理学家勒庞眼中“受到催眠的人一样,一些能力遭到了破坏,同时另一些能力却有可能得到极大的强化。”[7]为了维护共同体的温暖现状,成员在人多力量大的潜意识下,做出“英雄主义”的举动——勇敢地驱除威胁到共同体安全的人,表现出慷慨赴义的特点。所以,勒庞认为群体的智商总是低于个人,这也就不难理解广场舞大妈做出的扎汽车轮胎等荒唐举动了。
4 广场舞事件的认知维度
4.1认知策略的转向
马克思·布莱尔指出:“我不同意那些相信我们面对的问题将会被所谓的技术装置解决的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的观点……我偶尔想到技术进步引起的问题可能是不可解决的。”[4]220的确,技术进步在带给人们物质丰富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始料不及的精神危机和社会危机。技术进步不一定都是人类的天堂,当医疗技术不断进步时,一些不常见和不知名的疾病也开始“普及”开来,期望通过一种技术的进步来解决另一种技术的负效应的科学主义日益显现出它的缺陷来。
基于这一认知,笔者不禁要问,是否建设更多的健身娱乐设施,类似广场舞事件就会得以解决呢?如果仅将广场舞事件定义为城镇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或是老龄化社会、失独家庭、空巢老人家庭增多等问题的显现,是否陷入了科学主义将由技术问题导致的失误当做是自己发展不充分的结果,只有技术才能改进技术,进而需要进一步发展技术以使自己更加完善的逻辑思维中去呢?事实上,目前关于广场舞事件的解决办法是:提供耳麦以减少噪音,用定向音响以改变噪音的方向,提供更多的场地以减少争端,编制规定套路以统一广场舞“门派”等等。笔者以为,广场舞事件不能依靠“只有技术才能改进技术”的思维和上述各种技术手段来解决。即便是有一天城市有足够的场地提供给大妈们尽情舞动,笔者也相信,还会有其他的类似事件不断涌现。碎片化的技术或许可以“立竿见影”,但依然难以应对广场舞事件这种整体性的现代社会问题,充其量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之策,而我们需要的是从伦理、道德、心理等层面整体介入、同步解决的治本之法。
4.2城市社区的安全隔离
不同于乡村的随意坐落,城市社区经过了规划部门的精密测量和组织机构的严密管理,旨在保证潜在的不安全因素在可控制范围之内,而所有这些都得益于技术的进步。于是,城市社区中的门禁系统和阳台的栅栏以及新一代的防盗门等安全措施使得“隔离和保持距离成为近来在城市中最通用的生存策略。”[8]正如冈伯特和德鲁克所言:“家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其中的居住者而不是为了让人与社群融为一体。”[9]对于相对年轻的社会精英而言,他们的社会空间通常并不与所在的物理空间重叠,家只是一个安全的栖息地,他们乐于接受更为广阔空间的信息和体验,只要在社区的家里生活自由自在、舒适可人就再无其他兴趣了;而与之相对的生活在同一社区的老人则是另一个极端,他们已经或正在退出精英圈子,注定要“拘禁”此地,也因此他们的关注焦点和梦想无法脱离本地事物,所以老人们的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相互重叠。西美尔认为都市生活的特点是:“次要接触代替主要接触,血缘纽带式微,家庭的社会意义变小,邻居消失,社会团结的传统基础遭到破坏。”[10]因此,在追求安全舒适和向往梦想之间,老人和社会精英有着难以契合的本质,因此,矛盾冲突一出现便难以停止,直到一个相互可以忍受的折中办法出现。
4.3道德监控和镜头监控
鲍曼说:“最愉快的共存是相互之间不相互作用。”[4]276彼此陌生、彼此共存却不相侵犯成为城市人的理想法则。而事实并非如此,总有人会逾越红线。史蒂芬·图尔敏认为:“在陌生人的伦理学中,对规则的遵守是全部,自我判断的机会很少;而在亲密人的伦理学中,自我判断是全部,对严格规则的肯定是很少的。”[11]在与陌生人共存的物理空间中,保持公共安全的基本要素就是各自对规则的遵守,史蒂芬的规则实际上就是道德准则。然而,如上文所述,道德是不确定和模糊的,一个人想当然地认为必须遵守的准则,另一个人或许并不在意。换言之,即看似无处不在的对公共安全负责的道德监控并不靠谱。
除道德监控外,各个物理空间都有几乎无盲区的镜头监控。在陌生的邻居间,心灵的距离越远就越需要环境的监控手段,而镜头监控的效果又会怎么样呢?在泼粪、打枪、扎轮胎等冲突事件中,镜头监控几无作为,偶尔能够找到肇事者,也往往不了了之。高昂的监控设施在广场舞事件中何至于碌碌无为呢?事实上,在技术进步的支持下,社区、公园以及广场基本具备了全景式的监控,对违反规矩的人而言,他们时刻处于监控人员的注视之下,但前提是监管人员要时刻盯守在监视屏前,并及时对违规人员作出处罚。然而在广场舞事件中,社区、公园、广场的管理者所能作出的仅是规劝而非处罚,因为全景摄像头监控不过是一种亡羊补牢式的对破坏、盗窃等违法分子的追踪手段,其初始目的并非是针对社区居民的“人民内部矛盾”。
4.4社会对老人的忽视
长久以来,社会对老人显示出极度的忽视,虽然在满足基本生存的老有所养的基础上,提出老有所乐的口号,但是在大众心中的老人之“乐”多是天伦之乐,是带孙子、相互扶持的夕阳之乐,老人不具自我存在感;所以,当老人真的“有其所乐”时,又因非大众之所“乐”而备受非议。如广场舞事件中,老人在社会中刷出的存在感再一次蒙尘。因为人们习惯的老人的幸福状态与老年人内心追求的幸福状态之间存在太大差距:当每一个“我”在用手机、网络等新媒体社交时,自私地以为老人只是看看电视而已,对老人的化妆品、鲜艳衣服、时髦语言不屑一顾,乃至于戏谑广场舞舞姿老土,嘲讽其音乐庸俗,在心理上俯视着老人们不可多得的娱乐活动。
日本作家渡边淳一说:“年老,意味着更多可以随心所欲地享受生活”,并鼓励老人开启退休后的第二次人生。事实上,渡边淳一笔下的老人在日本社会是最有钱(他们资金占整个国家的70%)和最有闲的阶层。而在我国,单位退休的老人已经是幸福的,相比他们有稳定的退休金和各种社会保障,还有很多空巢、失独、城乡结合部、农村老人“老无所依”。2013年人口学家预计,我国的失独家庭未来将达到1 000万;“根据2013年湖南省统计公报,全省需要专业的养老护理员70多万人,但目前实际拥有的还不足5万人。”[12]在国家和社会的养老保障还不到位的情况下,“健康老龄化”从何谈起?有人“倡议市民群众晚间以散步、纳凉等相对安静的休闲方式”[13]替代广场舞活动,从而解决扰民问题;更有直白建议:老人最好什么也不做,老实呆在家中看看电视、带带孩子,做好饭菜。其背后隐藏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老年人生活和需求的极度忽视和不尊重。
4.5碎片化时代的道德窘境
吉登斯把整个现代世界看成是一堆碎片的集合,鲍曼进一步指出这一切乃是技术使然,即技术将整个生活打成碎片,然后再由技术将其整合。“技术意味着将生活打碎成一系列问题,将自我打碎成一个产生问题的多面体,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要求有单独的技术和单独的大量专门知识。”[4]232即一种技术解决生活中一种问题,如果用病因学的解释,则是一种药物治疗一种疾病。和碎片化治疗疾病一样,技术的碎片化问题解决都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鲍曼认为:“道德自我是在技术牺牲品当中最明显、最突出的一个。”[4]232借此观点来分析广场舞事件中的主体,或许能够窥视其中一二。
老年人对广场舞的需求是一种碎片化的需求,诸如他们对孤独的恐惧、对交流的渴求、对集体温暖的流连以及对青春的回忆等。此时的老人并非一个“整体的人”,他仅仅想解决自己的焦虑,其所采取的行动不会太多去观照“他者”或者观照整个“世界”(如顾及整个社区的和谐),当他采取的行动超出了自己碎片化解决问题之外时,他会心安理得地认为“事先没有想到”“只是运气不好”“本意不是这样”等等。很显然,在以广场舞解决老人自身问题的“技术世界”中,习惯了对整体把握的道德被视为不受欢迎的异类而无法存在。
对人类而言,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则是导致道德上的“祛魅”,当这一“祛魅”焦点转移到老人身上时,常常将老人与碰瓷、讹人、“扶不起”等问题联系起来并被刻意放大,事实上,这仅是社会道德失范的一个问题而已。作为弱势群体的老人被放置在道德问题的焦点之上,本身就是社会道德失范的一个表现。令人欣喜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积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传统美德,从全方位来规治道德滑坡,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笔者深信,这才是道德问题的根本。
5 广场舞的美学维度
理解了广场舞事件中的认知和道德问题,广场舞的美学问题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当然,广场舞的美学维度绝不在于舞蹈本身,其核心价值在于共同体中的温暖。
城市的物理空间当然是一个美学空间,老人的广场舞活动同样也是一种美的展示,而大多数人不这么认为,这是因为人们对广场舞的美学和认知不在一个维度上,而且他们是陌生人,在陌生人的眼中,广场舞自然不甚优美,只有融入感情,陌生人成为熟人后才能产生美学意义上的广场舞。试想,在流行歌曲的律动中,亲人、邻居纵情舞动,他们热情奔放、开怀大笑、缅怀青春,融休闲、交流、健身娱乐一体,他们展现出的是一颗朝气蓬勃的心,这难道不是一种美的场景吗?笔者看来,这应该是一种晴朗之美——对孤独不再恐惧,对陌生人不设防。这种美是对社会长久以来“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另一种抵抗,在此意义上,更是重拾中华道德之美的一种另类方式。作为广场舞群体之外的他者,虽然物理空间上接近,但因无亲身体验又导致心理距离上疏远,作为观光客自然无法感知广场舞的美学意义。
6 结论
在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今天,健康老龄化成为人们的普遍追求。而事实上,城市老人对于孤独的恐惧与日俱增,作为一种本能的反应,“在广场舞群体中,他们实现了传统意义上‘远亲不如近邻’的心理慰藉。”[5]当然,在这样的共同体中,只要亲身体验,它可以是一个美学意义的共同体。本文之意在于发现问题而非解决问题。在广场舞事件的道德、认知和美学三个维度中,道德是最直接的问题,认知是深层的问题,美学则是两者的升华。现代城市中的道德危机以及人们普遍对此认识过于平淡造成了广场舞事件的出现,如鲍曼所言:“道德责任是人类最具私人性和最不可分割的财富,是最宝贵的人权,不能为了安全而剥夺、瓜分、抛弃、抵押或沉淀道德责任。”[4]295策略和战略的双管齐下才是广场舞事件的治本之道,也为今后可能出现的类广场舞现象奠定认知和疏导的基础。
[1]郭剑夫.广场舞:中国大妈的江湖[J].新城乡,2014(6):18-21.
[2]于秋芬.社区体育运动开展中权利冲突分析——以广场舞纠纷为视角[J].体育与科学,2014,35(2):83-87.
[3]王爱群.论侵害生活环境权的法律救济——由广场舞扰民事件引发的思考[J].行政与法,2014(6):80-83.
[4]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M].张成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5]侯胜川,宋梁.“广场舞事件”所折射出的社会问题探析[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9(2):44-48.
[6]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M].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2.
[7]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2.
[8]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时代[M].谷蕾,武媛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87.
[9]Gumpert G,Drucker S.The mediated home in a global village[J].Communication Reaearch,1996(4):422-38.
[10]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M].顾明仁,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6.
[11]杰弗里·布鲁斯坦.关爱与签约:从个人的观点看[M].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218.
[12]黄利飞.湖南老年产业博览会今日启幕 百余家涉老企业亮相[EB/OL].(2014-10-10)[2015-10-01]. http://www.hn.xinhuanet.com/2014-10/10/c_1112758512.htm.
[13]张信思,刘明辉,赵丽娜.“广场舞矛盾”与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规划管理[J].中国园林,2014(8):112-115.
Morality, Cognition, Aesthetics:Three Dimensions in the Square Dance Events
HOU Sheng-chuan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Minjiang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This article applies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square dance events in recent years. Studies suggest that the square dance have become a reality version of martial arts, which cannot be completely solved with technical aspects such as venues and facilities, amnesty and incorporation. From moral, cognitive and aesthetic dimensions, it explains the square dance events, and puts forward that both sides in the square dance events do not have a mor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fatigue of moral and camera monitoring, cognition towards square dance event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e different family recognition between elderly and young people, long-standing social neglect and disrespect for the elderly, overall moral decline of society caused by reliance on technology in the era of fragmentation, the elderly’s yearning for a safe and warm community caused by the occurrence of square dance events. Only when a stranger who involves emotions and participates can he experience the aesthetic significance of the square dance.
square dances; morality; cognition; aesthetics
2016-02-02
侯胜川(1980-),男,河南洛阳人,讲师,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民族传统体育学和体育社会学。
G80-05
A
1008-3596(2016)03-00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