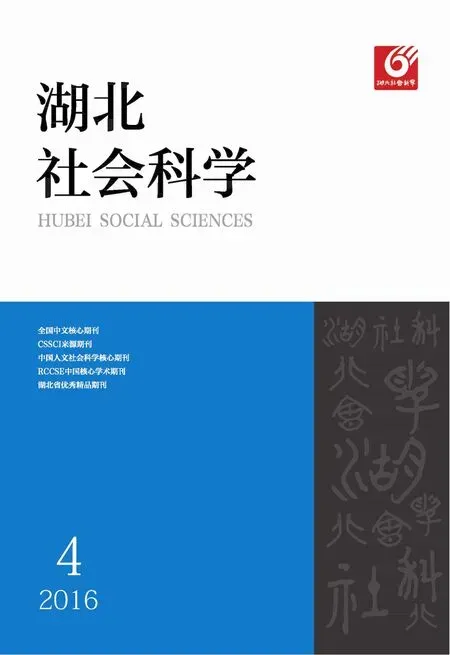“无可无不可”:浅析儒家的行道精神
刘春婵(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无可无不可”:浅析儒家的行道精神
刘春婵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根据对《论语》、《孟子》中相关思想的诠释,能够理解儒家的“行道”精神。通过孔子的身体力行,“行道”精神开始注入儒家的传统之中,孔子所说的“无可无不可”集中体现了这种“行道”的精神,孟子则直接继承了这一精神,并予以完善和发展。由于孔、孟二人的努力,“行道”精神最终发展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一面,从而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得以继承与发扬,而“行道”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及其价值追求。
关键词:孔子;孟子;儒家“行道”精神;“无可无不可”
一、从《乌托邦》中的比喻说起
“明智之士,或者说真正的哲学家,何以会逃避政治?”关于这一问题,柏拉图的《理想国》曾经做了说明,而托马斯·莫尔则在《乌托邦》一书中,借助于自己所假想的、游历广泛的哲人拉斐尔·希斯拉德之口,给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哲学家看见其他人冲到街上,在瓢泼大雨中被淋得浑身湿透。哲学家无法劝服他们进屋避雨,他知道,自己若是也走出去的话,只能同样被淋湿,因此,他就自己待在屋子里,而且,由于对他人的愚蠢束手无策,也就只能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好吧,不管怎样,至少我自己还不错。’”[1](p71)
如果仅从历史的情境来分析,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所说的这个比喻,对于儒学的两位奠基者孔子和孟子来说,无疑也是十分恰当的。孔、孟二人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正是一个“礼崩乐坏、处士横议”的时代,因此,明智之士大概会选择“独善其身”,而不肖之辈恰足以汲汲营营。面对如此不堪的现实,儒学的两位奠基者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独善其身”,抑或是“汲汲营营”?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一种不失为有益的“后见之明”为我们提供了帮助,正如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儒家的两位奠基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答案。事实上,孔、孟二人的选择既不是躲进屋里,充当独善其身的“自了汉”,也不是庸俗地融入现实,投身于追名逐利的大潮之中。凭借着一股坚定的“行道”精神和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孔、孟二人为我们展现了另一种别具风采的人生道路。
通过对《论语》、《孟子》中相关思想的诠释,本文试图抓住“行道”精神在这两部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呈现方式,从而更好地理解“行道”精神是如何被注入到儒学的传统之中。文章从论述孔子的“行道”精神出发,紧接着考察了孟子对“行道”精神的继承和完善,最后,本文简要地分析了“行道”精神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间的传承与影响,简单地说,“行道”精神至少部分地塑造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及其价值追求。
二、“无可无不可”:孔子的“行道”精神
在《论语·微子》篇中,记录了一段孔子对前贤的评论:“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其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根据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里的注释:“逸,遗逸。民者,无位之称。”[2](p186)所谓“逸民”,大概也就略等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隐士之类的人物,或者是柏拉图、托马斯·莫尔等人所说的“明智之士”、“哲学家”。因此,通过孔子对“逸民”的评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那种“待在屋子里”的避世方式,孔子本人实际上也是非常清楚的,并且,还有着很高的评价,孔子认为:“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论语·宪问)。然而,他却进一步指出:“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那么,孔子所说的“无可无不可”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或者说,“无可无不可”何以异于伯夷、柳下惠等人的处世方式呢?
如果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就必须更好地理解孔子本人的人生追求,事实上,通过“无可无不可”这一表述,孔子想要说明的也恰恰是他自己的人生追求。在与其弟子的问答中,孔子对颜渊、子路等人宣称,他的志向即在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孔子自信,“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因此,孔子最根本的关怀即在于“行道”。为了实现这样的理想,孔子周游列国,一生皆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然而,当时的政治环境却并没有为他提供一个实现其理想、抱负的机会,直到在瓢泼大雨中被淋得浑身湿透之后,孔子也忍不住发出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感叹。
此外,在《论语》一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孔子的行为经常会遭到当时的隐士之流的嘲弄。例如,石门的司门者说他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荷蓧丈人则讥讽其“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论语·微子),而长沮、桀溺更是直截了当地对子路说:“与其从辟人之士,不如从辟世之士”(论语·微子)。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来看,对于这些隐逸之流的评价,孔子基本上还是比较认可的,不过,他也为自己的行为做了辩解:“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朱熹将其进一步解释为“天下若已平治,则我无用变易之。正为天下无道,故欲以道易之耳。”[2](p185)换句话说,恰恰是在这种“天下无道”的情况下,孔子才坚持要以其“道”易天下,欲将海潮音化作狮子吼,因此,朱熹的上述诠释可谓是深得圣人之心。行文至此,孔子之所以不愿意“待在屋子里”的原因也就很明白了,简单地说,孔子的一生即是以“行道”作为其使命的,因为“行道”之使命感的存在,促使他既不愿意也不可能会选择“待在屋子里”。通过“无可无不可”,孔子所想要表达的,其实也就是这种“行道”的精神。
但我们也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行道”的使命感对于孔子来说,不仅仅意味着一种“入世”的积极努力,更为重要的是,“行道”还是一种极为丰富的精神资源,并为其种种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正是通过孔子的言传身教,“行道”的精神开始被注入儒家的生命之中,从而帮助儒家找到了一种“可恃以批评政治社会、礼抗王侯”的精神凭藉,[3](p88)余英时先生曾经使用“哲学的突破”来概括孔子的这一贡献,在我们看来,这种评价是十分恰当的。孔子认为,“士”应当以“道”为己任:“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因此,孔子为儒家所注入的其实是一种全新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儒家的“行道”精神不仅体现为一种“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关怀,更重要的是,“行道”精神还表现在对“道”的固守与坚持,这就使得原本即已存在的“儒”,[4](p149-152)开始展现出完全不同的精神风貌。
“行道”精神是孔子一生的价值皈依,此外,“行道”精神也是孔子在仕途中进退、取舍的判断标准。正是由于感受到了自身所承担的“行道”使命,所以纵然是公山弗扰、佛肸这样的“乱臣贼子”相召,孔子亦“欲往”,“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此所谓“无不可”是也;同样是因为对“行道”的坚持,所以“卫灵公问陈”,“(孔子)明日遂行”(论语·卫灵公)、“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论语·微子),此所谓“无可”是也。因此,从这种“无可无不可”中所折射出的,正是孔子为儒家所注入的那种“行道”精神。
在这一部分的最后,我们还想多花点笔墨,简单地说明一下孔子所谓的“道”的内涵。既然孔子的一生是以“行道”为志业的,那么,孔子所欲行之“道”又是指什么呢?虽然孔子并没有明确地对其进行说明,然而,通过对《论语》的阅读和把握,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难回答。事实上,孔子所说的“道”无外乎仍是以“仁”和“礼”为其核心的,因此,“行道”也就是“行仁政、复礼乐”。根据《论语·颜渊》中的记载,孔子曾告之其最得意的弟子颜渊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而当颜渊进一步“请问其目”的时候,孔子答之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通过这样的一问一答,孔子所欲行之“道”,已然是不言而喻的了,由此,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颜渊之死何以会让孔子“哭之恸”,并且宣称这真是“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
三、“愿学孔子”:孟子对“行道”精神的继承与完善
孔子为儒家所注入的这股“行道”精神,在孟子那里得到了很好的继承。由于处在一个“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的时代,孟子不仅继承,而且也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基本理念,正如程颐所说的:“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如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5](p1-58)仅以“行道”精神而论,孟子对孔子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十分明显的。
与孔子一样,孟子所处的时代也可称得上“大雨倾盆”,而且,情况似乎更为严重,诚如顾炎武在《日知录·周末风俗》中所指出的:“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6](p221)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之下,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对于孟子来说,同样也是一个极为严峻的现实问题。孟子关于“圣”之类型的划分,其实就是在孔子“逸民”之论的基础上所做的进一步拓展,并且,还特别加入了“治亦进,乱亦进”的伊尹以及孔子本人,而孟子所说的“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孟子·公孙丑)也正是孔子所说的“无可无不可”的具体阐释,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朱熹在其为《论语》所做的集注当中,也恰恰是用孟子的这句话来解释“无可无不可”的。[2](p715)通过孟子的阐释,孔子所说的“无可与不可”的内涵变得更加明确,所谓“无可无不可”,孔子强调的其实是要寻求“行道”的时机,亦即孟子所谓的“圣之时者”。通过不同人生选择的比较,孟子指出:“乃所愿,则学孔子”(孟子·公孙丑上),这就清楚地向我们揭示出了孟子对孔子的继承。
但问题在于,孟子到底从孔子那里继承了什么?或者,用孟子自己的话来说,他本人“愿学孔子”的哪些方面?关于这个问题,研究孟子之学甚力的台湾学人黄俊杰先生曾指出:“孟子想学的是孔子毕生为人处世那种建构在深刻的时间意识之上的与时俱进的精神。”[7](p187)但在我们看来,这种“建构在深刻的时间意识之上的与时俱进的精神”,具体而言,就是本文所论述的“行道”精神。事实上,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滕文公下),无非就是在寻觅一个行道的机会,正因为如此,即便是像滕、宋之类的小国,孟子也不愿意放弃其“行道”的努力,而对于曾经的东方霸主齐国和齐宣王,想要“援天下以道”(孟子·离娄上)的孟子,则更是寄予了相当高的期望,因此,当他由于种种原因而不得不离开齐国的时候,孟子“若有不豫色然”,他向自己的学生充虞感叹道:“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孟子·公孙丑下)于斯可见,孟子“行道”之心的迫切。
除了积极地寻觅“行道”的机会之外,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孟子还真正地继承了孔子“以道自任”的精神。由于生活在一个“诸侯放恣,处士横议”的时代,当时的策士之流,如周霄、公孙衍、张仪以及惠施等人,皆曾出入于各国公侯的王庭,尤其是公孙衍、张仪之辈,更具有所谓的“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的威势,然而,孟子却很少与这些人交往,[8](p24)并且,他还曾严厉地斥责这种人不过是“以顺为正”,乃“妾妇之道”,孟子认为,真正的“大丈夫”,应当“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正是因为承载着这种“行道”的使命,孟子坚持主张,“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孟子·公孙丑下)凭借着这一点,孟子得以在精神上礼抗王侯,即便是与梁、齐等大国的国君相处,也始终能够不卑不亢。例如:孟子曾直言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孟子·梁惠王上);尽管齐宣王对其礼遇有加,“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孟子·公孙丑下),然而,孟子却坚决地予以拒绝。孟子的这种“进退必以其道”的处事方式,的确迥异于当时的公孙衍、张仪之流,但与孔子所说的“无可无不可”,却是若合符节的。
与孔子不同的是,孟子实际上更为明确地说明了其所欲行之“道”,也就是他本人所一再宣称的“王道政治”的理想,诚如黄俊杰先生指出的,“(孟子)所谓‘王道’,是指‘先王之道’,以德治为基础,以民本为其依归”,[7](p246-248)因此,我们认为,孟子所欲行之“道”仍然不离孔子所说的“仁”和“礼”等基本范畴,只不过,孟子更多地讨论了一些制度设置的问题(如君臣关系、井田制度、五等爵制等等),但从根本上来讲,孟子所欲行之“道”基本上仍是对孔子的继承和发展。
四、“忧以天下,乐以天下”:“行道”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孔子开始将“行道”精神注入到儒学的传统之中,孟子则进一步完善并发展了孔子的这一“行道”精神。由于孔、孟这两位儒学奠基者的不懈努力,“行道”精神开始融入儒家传统,成为儒学的基本特质之一,并在此后的儒家知识分子那里得到了继承与发扬,北宋政治家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集中地反映了儒家知识分子对这种“行道”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当然,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儒家知识分子们的“行道”努力也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的色彩:
首先,一部分儒家知识分子继续走“上行”的路线,随着君主制的确立,这种“上行”路线自然而然地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君主身上,亦即“格君心之非”、“得君行道”。例如:作为第二期儒学的展开,宋明理学通常被视作一种“义理”、“心性”之学,[9](p162)然而,理学家们却并没有躲进书斋里,与之相反,他们几乎从未放弃过“得君行道”的努力。关于两宋理学家们的不懈努力,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有过相关的描述,至今读来,仍令人为之动
容。[10](p3-64)
其次,由于秦汉之后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儒家的“行道”理想更为经常地感受到来自于“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皇权的压力,因此,也有一部分儒家知识分子开始转入“下行”的路线,而这种“下行”路线即试图从民间社会中挖掘资源,所谓儒者之效,“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通过对一乡、一里的改善,儒家知识分子们至少能够在部分上实现其“行道”的理想,事实上,北宋的张载、“吕氏乡约”的发起者吕大钧、吕大临等人均有过类似的思想或者尝试。[11](p35)
最后,我们还想简要地要讨论一下牟复礼(F.W.Mote)、杜维明等人所说的“儒家隐逸主义”(Confucian Eremitism),[12](p60)这一类型的儒家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表有元代的刘因、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等人,事实上,儒学传统中的“曾点精神”,以及在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等人的身上,[1](p213-215)我们都或多或少地能够看到这种“隐逸主义”的倾向。问题在于,这种“隐逸主义”是否与本文所论及的“行道”精神相冲突呢,二者之间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但却并不是互相矛盾的。这里的原因在于,刘因、顾炎武等人所处的政治环境,使得他们的“隐逸主义”看上去更像是一种无奈之举,此外,“刘因并非完全没有接受过官方委任”,[5](p59)而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更是不忘关怀天下,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正始),我们很难想象,一位真正的隐逸之士会有类似的主张。关于这一点,陆九渊所说的“儒者虽至于无声、无臭、无方、无体,皆主于经世”,[13](p80)真可谓是一语中的。因此,在我们看来,“隐逸主义”并不否定“行道”精神在儒家知识分子之间的传承。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认为,尽管在形式上仍然存在着差异,但孔、孟为儒学所注入的这股“行道”精神却仍然得到了继承与发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行道”足以称得上是儒学的典型特征之一,也是儒家知识分子们最为根本的价值理想与人生追求。
对于任何一代人来说,是否投身于政治或者说公共事业,都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么,明智之士应该如何面对政治?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大致为我们提出了三种不同的选择:一是道家所主张的“隐”;二是法家所主张的“仕”;三是本文所论述的儒家“行道”精神,亦即孔子所说的“无可无不可”。[13](p17)其中,道家倾向于洁身自好的“隐”与儒家怀抱着道德和政治理想而出仕经世的努力,都相应地得到了人们很高的评价,但由于道家式的“隐”通常显得更为逍遥和自在,因此,也更容易引起知识分子们的认同(如前文所说的柏拉图、托马斯·莫尔)。然而,本文认为,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责任,既能够有所担当,又能坚守住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正如儒家所展现出来的这种“行道”精神,不仅自有其独特的魅力,而且也应获得人们更多的尊敬。事实上,“行道”精神在儒家知识分子之间的传承与发扬,已经为我们充分地展现了其自身的活力,而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以及公务人员来说,这种“行道”精神也仍然没有失去自身的意义,从而能给予我们一定的启发。
参考文献:
[1]杜维明.道·学·政:儒家公共知识分子的三个面向[M].钱文忠,盛勤,译.北京:三联书店,2013.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章太炎.国故论衡[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5]王孝鱼.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
[6]陈垣.日知录校注[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
[7]黄俊杰.孟子[M].北京:三联书店,2013.
[8]钱穆.先秦诸子系年[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9]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一卷)[M].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
[10]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11]钱穆.宋明理学概论[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12]Frederick W.Mote.Confucian Eremitism in the Yuan Period[C].in Wright A F.ed.,The Confucian Persua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0.
[13]钟哲.陆九渊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
责任编辑高思新
作者简介:刘春婵(1980—),女,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先秦散文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15YJC710032)。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6)04-0123-05
——由刖者三逃季羔论儒家的仁与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