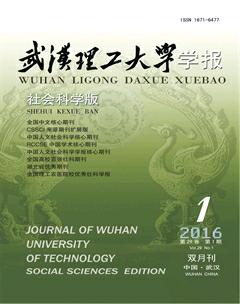冷战后欧洲左翼的共产主义思潮研究现状*
简 繁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冷战后欧洲左翼的共产主义思潮研究现状*
简繁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曾作为20世纪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指导思想的共产主义,在冷战后遭到来自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各方势力的挑战,面临前所未有的话语危机。欧洲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一些左翼学者则毅然扛起“共产主义”大旗,捍卫共产主义的真实形象,为复兴共产主义话语而努力,形成了新一波共产主义思潮。这引起了国内外一些学者的兴趣。他们纷纷对此进行介绍、研究和讨论,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进一步扩大了这波思潮的影响力。因此,尝试从国内和国外、政党和学者四个交叉维度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分类梳理和介绍,以期引起国内学者对这一前沿问题更广泛的关注。
关键词:冷战后;欧洲;左翼;共产主义
从19世纪中期科学社会主义创立起,共产主义就逐渐成为学术研究和政治讨论的热门话题,并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共产主义思潮。这也使得关于这些思潮的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与之相比,以冷战后的共产主义思潮为对象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冷战结束至今不过25年光景,从历史阵痛中走来的共产主义也不过刚刚出现继承和复兴的势头,其发展壮大仍需要时间,而以这波新思潮为对象的研究则更加只是刚刚起步;二是苏东剧变的历史之谜一直为很多学者津津乐道,乃至今日仍有许多学者愿意将研究共产主义的精力聚焦于苏东历史及苏联模式的最终崩溃上,又或是追踪所谓“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原苏东地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这种学术兴趣的转向也需要一定时间;三是苏东剧变的重大挫折使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饱受争议、批判甚至诋毁、抹黑,共产主义成为“专制”、“独裁”的代名词而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话语危机,共产主义思想的生存空间急剧缩小,国际上曾一度出现“惧谈共产主义”甚至“耻谈共产主义”的现象,直至今日仍不绝于耳。
但是,冷战后欧洲仍有一些共产主义政党和左翼学者坚信共产主义没有失败,他们毅然扛起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论大旗,并冲破资本主义自由民主话语的桎梏,“去了解并完全投身于共产主义,去再次以行动完全忠诚于共产主义观念”[1]。面对福山“历史终结论”的质疑和霍布斯鲍姆“社会主义已经失败,资本主义现在破产了,接下来是什么”的疑问,他们的回答是:共产主义!为此,他们纷纷提出了一些对于共产主义理论内涵和实现方式的新理解、新观念,试图说明共产主义存在于当代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誓要实现共产主义的复兴,从而形成了新一波新的共产主义思潮。相应地,国内外一些学者也积极展开对他们思想的追踪研究。下面本文从国内和国外、政党和学者四个交叉维度阐述冷战后欧洲左翼的共产主义思潮的研究现状。
一、国内关于冷战后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的共产主义思潮的研究现状
国内学术界一直密切关注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尤其是冷战后各个政党为应对苏东剧变的重大历史挫折,顺应21世纪国际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而在其共产主义指导思想、纲领政策和实践运动方面作出的重要改变,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首先,国内学术界对法国共产党的“新共产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多数形成了自己对这一理论的观点和评价。例如,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曹松豪在冷战后曾多次造访法国,先后考察并参与了法共第二十九次、第三十二次代表大会和“人道报节”活动,是国内较早关注法共“新共产主义”理论政策的人之一。他认为“新共产主义”的理论主张最早见于由法共全国书记罗贝尔·于撰写,出版于1995年11月的《共产主义:变革》(Communisme:lamutation)一书。而这一理论正式作为法共指导思想则始于1996年12月召开的法共二十九大,以“新共产主义”代替使用了近二十年的“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的提法,这“标志着法共在探索共产主义变革理论的道路上迈开了重要的一步”[2]。曹松豪从理想社会、党的建设、苏联历史、奋斗目标、资本主义、新全球化、左翼联盟、参政策略、公民参与、争取民主这十个方面系统阐述了“新共产主义”的理论主张,并指出其目的是要顺应国内外形势和斗争需要,改善党的形象,摆脱党的困境,促进党的重振和发展。中央编译局的费新录同样较早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跟踪研究,他将法共的“新共产主义”总结为“三个超越”和“两个革命”,即超越“传统”、“马克思”和“资本主义”,强调“信息时代”的革命和“个人时代”的革命。同时,他认为于面向21世纪的共产主义规划是崭新且切合法国实际的宏伟蓝图,以至于法国像“需要新鲜空气”一样“需要共产主义”[3]。李周在《探索中的法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一书中以法共的“新共产主义”理论为主题,从七个主要方面展开详尽论述:一是理论的产生,包括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形成过程的各个阶段;二是理论的来源,包括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与“欧洲共产主义”的逻辑关联以及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冲击;三是理论的精髓,即“超越马克思”,从而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四是理论的拓展,即面向21世纪的法共纲领和政策改革的新规划;五是理论的反省,着重讨论法共三十二大对国内外形势与挑战的判断,对选举失败的教训总结,以及对共产主义理论观点的变化;六是理论的变革,着重探讨法共通过其三十三大、2007年特别会议和三十四大如何调整战略,实现了共产主义理论的自我扬弃;七是理论的评价,集中总结了法共共产主义变革理论与实践的主要特点、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意义和当前面临的挑战。她认为,这一理论“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恢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地位,推动欧美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发展也有积极意义”[4]。
其次,国内研究者通过追踪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组织和参与的洲际和国际会议,挖掘了这些政党在共产主义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国际共产主义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mmunist Seminar,ICS)是1992年以来由比利时工人党主办的一年一度的世界性共产主义政党会议。丁俊萍和亓胜林发现第十五次会议的最终决议提出了在当前时代环境和形势下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共产主义的实际建议,即“在准备共产主义革命时,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国家共产主义者必须发展和加强相互之间的联合,组成一个委员会,联合起来反对当前由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5]。一些学者也同样从近年来的若干届国际共产主义研讨会中挖掘了当代共产主义政党和共产主义者的历史使命和共同策略,包括批判资本主义及其制度危机,反对帝国主义及其战争冲突,宣传共产主义及其理论主张,促进世界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推动共产主义政党的发展壮大等等。“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Meeting of Communist and Workers’ Parties,IMCWP)是1998年以来由欧洲共产主义政党主导的一年一度的世界性共产主义政党会议。一些对历届会议作整体研究的学者认为,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把共产主义社会最终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当作世界发展不可阻挡的规律,强调通过现代化的通讯、媒体和网络工具开展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是该会议的一个重要特点和理论主张[6]。聂运麟则注意到该会议早期对是否坚持会议的共产主义性质存在分歧:一些政党认为,要丰富会议的成员构成,淡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色彩,向左翼政党会议的方向转变;多数政党则认为应保持会议的共产主义性质,只是在是否设置权力机关的问题上产生分歧。最终“会议的实践完全排除了向一般‘左翼政党’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保持了自己的共产主义性质”[7]。欧洲共产党会议(European Communist Meeting,ECM)是自2011年起在希腊共产党的倡议和组织下召开的一年一度的欧洲洲际性质的共产主义政党会议。刘春元对这一会议进行了跟踪研究,从她对历次会议的综述中我们不难得出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在共产主义问题上达成的三点共识:一是坚决反对欧洲资产阶级政府将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等同,攻击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历史,意图引导民众仇视共产主义的“反共产主义”策略;二是在组织工人运动过程中共产党人承担着向劳动群众宣传共产主义的任务,告诉他们共产主义纲领是可行的现实而非美好的梦境;三是共产党人要将共产主义的战略目标置于议事日程,为争取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共产主义未来社会而奋斗[8]。
最后,国内学术界对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的个案和整体研究为我们详尽呈现了这些政党的共产主义观。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淑春研究员的《欧洲社会主义研究》一书大量阐释了俄罗斯、新东欧、中亚、中东欧和西欧共产党人与左翼人士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观点,如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在科学共产主义观视野下阐述了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的理解,并强调“21世纪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成为在理智和人道的基础上、为了劳动者的利益而改造当代世界面貌的物质力量”[9]83;保加利亚共产党论述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矛盾斗争关系以及共产主义道路的前进性和曲折性,并强调将坚持共产主义基本原则与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发展相统一;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基于本国实际情况首次提出了对21世纪的共产主义的具体设想;西欧共产主义政党则普遍在党的纲领和实践中强调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捍卫党的共产主义身份特征,以应对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不断泛滥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组以当今世界16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为对象进行个案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综合得出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的整体性结论。从这些“整体性结论”可以发现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在看待共产主义问题上的几个特点:第一,主张通过和平、民主的道路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不再提倡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第二,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漫长而曲折的过程,需要分阶段、分步骤进行;第三,工人阶级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力量,团结中间社会阶级是取得共产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性重要问题;第四,在论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内涵时,往往把民主作为其本质特征,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联系起来;第五,各党对共产主义社会的“两阶段”理论或者说走向共产主义是否要经过“社会主义过渡阶段”这一问题存在分歧[10]。从这些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对未来社会形态和制度的设想中,笔者发现它们虽然多数更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一词,但实际上描述的却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状况。在个案研究方面,课题组成员阐述了希腊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以及共产主义必然性的认识;葡萄牙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般界定以及葡共对共产主义在葡萄牙社会实现后的设想;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在共产主义问题上的“重建”特质,包括重新认识共产主义历史、重新建立共产主义形象、重新阐释共产主义理论和原则、重新定义共产主义特性,等等。
二、国外关于冷战后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的共产主义思潮的研究现状
冷战后,国外学术界尤其是英语学术界对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的研究整体上陷入低谷,但并未消失。总的来说,这些研究更热衷于关注和分析这些政党在发展党员、加入联盟、争取选民、竞争议席等方面的表现及其影响因素,而对共产主义政党本身的独特性质及其特殊的理论、政策关注较少,对其共产主义思想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但我们仍可以从国外研究文献中挖掘出他们对这些政党的共产主义观的见解。
首先,国外学术界倾向于将欧洲共产主义政党作为欧洲激进左翼的重要力量进行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从中可以窥见这些政党的共产主义观。凯特·哈德森“聚焦于已经发生在‘左翼的左翼’身上的政治革新进程”[11],她的著作《1989年以来的欧洲共产主义:走向新欧洲左翼?》(EuropeanCommunismsince1989:TowardsaNewEuropeanLeft? )重点选取了冷战后西欧和中东欧八国的共产主义政党作为研究对象,有力地驳斥了“作为严肃政治力量的共产主义已经终结”的流行观点。她认为这些继续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政党和站在社会民主党左侧的其它政党一道构筑了“新欧洲左翼”兴起的基础,它们的共产主义既拒绝社会民主主义,也拒绝独裁的社会主义,而是拥抱女权主义、绿色政治和反种族主义,并采用更民主、更多元的政治策略,从而与其它激进力量一道构成了批判欧洲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新左翼[12]。安娜·M·格齐马拉-巴斯的著作《挽救共产主义的过去:中东欧共产党的重建》(RedeemingtheCommunistPast:TheRegenerationofCommunistPartiesinEastCentralEurope)集中关注原苏东地区共产主义后继政党的重建历程,这些后继党既包括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也包括共产主义政党,其中大部分在苏东剧变后几年又出乎意料地在民主选举中表现突出甚至上台执政。在格齐马拉-巴斯看来,这一现象可以归功于历史上的“共产主义遗产”为这些政党转型带来的正面影响。这些遗产包括政治精英的政策创新能力、社会协商能力和高效的组织策略,它们“不仅仅是‘话语和动员的工具’,而且决定了可用的资源和党重建的策略”[13]20;“不仅仅是政党转型的逻辑前提”,而且“对政党转型的方式、速度、内容和政党向民主过渡过程中的策略的相对成功产生了重要影响”[13]66-68。卢克·马奇在他的著作《欧洲激进左翼政党》(RadicalLeftPartiesinEurope)中考察了大量冷战后留存下来的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并将之纳入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的视野中,把当前规模较大的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划分为“保守的共产党”和“改革的共产党”两大阵营,并大致总结了二者在对待共产主义传统和苏联历史遗产上的差异。他认为“保守的共产党”仍然坚持“正统的”共产主义,这表现在没有抛弃马克思主义信仰,而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并透过“帝国主义”的冷战棱镜观察世界;没有抛弃共产党的名称和标志,仍旧缅怀激进分子的历史“运动”,并试图“保持”苏联的革命传统,包括对苏联遗产持相对不予批判的立场,以及通过民主集中制组织自己的党。相反,“改革的共产党”则偏离了共产主义走向折中主义,这表现在抛弃苏联模式的内容——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以及拒斥市场经济,并至少在口头上接受“新左翼议程”,如女性主义、环境保护、草根民主等等[14]。
其次,国外学术界对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的个案研究也包含了对这些政党的共产主义观的阐释和看法。其中对法国共产党及其“新共产主义规划”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但多数研究者并不看好“新共产主义规划”。菲利普·泰勒在研读了法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后总结道:“新共产主义规划的参考要点包括:充分就业;政治均势;法国总统权力的去除和一切选举中比例代表制的运用;现代法兰西共和国的新宪法;基于人权、民主、社会发展和文化而非利益的一个扩大的欧洲共同体”,但他同时直指法共“尝试重启并希望尽快作为象征的更新过的共产主义规划,看来似乎漫无目的地陷入了意识形态不确定、财政困难和涉嫌腐败的泥潭。”[15]弗兰克·L·威尔逊也认为法共1994年更换领导人后的共产主义新政不过是“旧瓶装新酒”,甚至有去意识形态的倾向,因为“罗贝尔·于的政策目标宽泛而毫无革命性,他很少援引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阶级斗争的修辞”[16]。大卫·S·贝尔则对在共产主义框架内寻求改革的法共持完全悲观的态度。一方面,“共产主义曾是经历磨砺的哲学体系,它吸引新成员寻求一种哲学”,而且“共产主义有一个敌人(资产阶级)和一套方案:废除财产以及生产、分配、交换资料归集体所有用以运行计划经济”[17],这种根深蒂固的印象使共产主义已然声名狼藉。另一方面,“法国共产主义与各种左翼有着密切关系,但它却在保持其正统身份的需要和革新的义务之间拉扯。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共产主义的历史伴随着革新自身的失败尝试而成为垃圾被丢弃,这应证了那句古话:共产主义可以破裂但不能屈服。”[17]贝尔认为法共将“新共产主义规划”与东方国家的实践相分离以期重塑共产主义形象的做法,正是坚持共产主义而“不屈服”的表现。但这无异于将自己依旧囚禁于被唾弃的意识形态中,只会使自己难以制定出令人信服的战略,从而陷入改革困境,其结果就是“法国激进左翼的改造可能要求毁灭法共”[17]。马奇在研究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发展现状时发现“对团结俄联共至关重要的、作为组织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18]存在一种奇特的窘境,即把共产主义作为苏联传统保持下来,但作为传统的共产主义本身却是反传统的、革命的。“这种窘境使后勃列日涅夫时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运用得到强化,藉此,共产主义逐渐因其象征意义、制度建构并作为国家传统而具有合理性,而非最初因其理论合理性或目的论上的目标。”[18]但如今,失去执政地位而仍然持有保守共产主义立场的俄联共不得不再次直面这种窘境,以及由此带来的选举危机。
最后,国外研究者发现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往往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欧洲一体化的现实因素间发生动摇,其内部对共产主义的坚持程度也存在差异。吉亚科莫·贝奈戴托和露西娅·夸利亚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的共产主义欧洲怀疑论的比较政治学》(TheComparativePoliticsofCommunistEuroscepticisminFrance,ItalyandSpain)一文中比较了西欧三国共产主义政党适应欧洲一体化的曲折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影响三个政党态度转变的重要因素。文章认为,过去以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共性为前提,将共产主义政党作为无差别整体归为一个族群加以研究的方式有待商榷,并指出:“如果有人思考西欧的共产党家族,那么共产党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多样化的回应会使意识形态的解释面临经验主义的质疑。它们已经同时在国与国之间,以及久而久之在同一政党内部及时调整变化。这是令人费解的,因为如果意识形态是影响党在欧洲问题上定位的主要自变量,那么我们应该可以预期同一政党家族内的统一倾向,以及各国政党的轻微变化。”[19]但事实上,西班牙的共产党从不持欧洲怀疑论,而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对欧洲一体化的反对态度也由强硬转向软弱,甚至开始支持。文章据此认为,国内外一系列现实因素,尤其是出于“追求选举和联盟的考虑”,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内部逐渐被动摇和稀释。久尔卡斯·查拉兰鲍斯的著作《欧洲一体化和共产主义的困境:希腊、塞浦路斯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对欧洲的回应》同样以欧洲三个共产主义政党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和回应为切入点,展示了希腊共产党、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和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实用主义的现实利益间迥然相异的复杂抉择过程。在他看来,“每一个这样的政党,就其自身独特的背景和特点而言,都值得被分析和评估”[20]。因为即使在共产主义政党内部,也存在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认识上的分歧和坚持程度上的差异,即坚持共产主义指导思想还是根据现实情况适度缓和自己的激进立场。这种分歧和差异往往会从它们面对现实问题的态度和抉择中反映出来。正如达芙妮·哈利克珀劳对此著作的总结说道:“贯穿全书的中心的‘概念镜头’是所谓的‘共产主义困境’,即在意识形态一致性与缓和之间的选择;或者,换句话说,大多数边缘政党面临的经典困境:保持其激进意识形态但要冒在选举上被边缘化的风险,还是缓和但要冒失去意识形态特性的风险。”[21]
三、国内关于冷战后欧洲左翼学者的共产主义思潮的研究现状
当前国内学术界对冷战后欧洲左翼学者的共产主义思潮仍处于关注、引进、介绍阶段,方法上以文献研究和访谈为主。直接翻译这些学者的学术成果而产生的译著、译文较多,而专门以这些学者的共产主义思想为研究对象,从而形成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的认识、判断、评价的专著、论文则较少。从国内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内容上看,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共性。
首先,国内学术界普遍认可冷战后欧洲左翼学者正致力于复兴共产主义话语,回归到共产主义观念,引领新一波共产主义思潮。关于这次共产主义话语复兴的起始时间,复旦大学汪行福教授陈述过两种观点:一种观点[22]认为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代表作是皮埃尔-菲利克斯·加塔利和托尼·奈格里1985年出版的《自由新空间》(Lesnouveauxespacesdeliberté),以及让-吕克·南希1986年出版的《非功效的共同体》(Lacommunautédésuvrée);另一种观点[23]认为应追溯到2006年,代表作是安东尼奥·奈格里同年出版的《告别社会主义先生》(Goodbye Mr. Socialism)①。此后对“共产主义”的探讨不断出现在欧洲左翼学者的著作中,为共产主义的复兴积蓄能量。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共产主义在欧洲左翼学者群体中回归的标志性事件是2009年由斯拉沃热·齐泽克主持召开的伦敦“共产主义观念”大会。汪行福教授认为这次会议“具有标志性意义,它不仅是激进左派思想家的集体亮相,也是共产主义观念回归的重要仪式”[24]。他指出了共产主义话语得以在欧洲左翼学者群体中复兴的两个原因:一是要肃清对“苏联模式就是共产主义”的误解,明确表示苏联式共产主义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二是激进左派为了与自由民主派区别开来,需要独立而明确的政治标签。他进一步认为,尽管当前激进左派的共产主义话语由于内在分裂,尚没有成为规范、系统、现实的理论,但无可置疑的是,“新的共产主义已经成为激进政治的标志性符号”[18]。中国社会科学院范春燕则明确指出,从2009年至2014年间召开的四次以“共产主义观念”为主题的系列研讨会及其后续讨论“昭示着新一波的共产主义思潮正在欧洲左翼学界兴起”[25]。她认为欧洲左翼学者重新启用“共产主义”这一术语,意在扭转冷战后欧洲左派衰落、迷茫的窘境,提出一种彻底、激进、革命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并在“和国家保持距离”的基础上重构政治。吴冠军也认为,当前欧洲左翼学者重新激活“共产主义”一词具有“理论的正当性基础”,是一种基于整体意义上的、真正创痛性地改变资本主义的诉求[26]。
其次,国内对来自欧洲左翼学界的这波共产主义思潮的研究成果展示了一幅在统一的旗帜之下既达成了一些共识又暗含思想交锋的图景。欧洲左翼学界的共识体现在恢复“共产主义”的理论意义或必要性上:一方面曾在左派历史上被积极运用的激进词汇,诸如公平、平等、正义、民主、权利甚至社会主义,如今都被资本主义统治话语所吞噬,成为改良资本主义社会、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政治工具,丧失了从外部彻底颠覆资本主义的激进性和革命性,而“唯有‘共产主义’这个名称因其和‘实在界’的内在关联而保有一种幽灵般的力量”[25];另一方面苏联和东欧历史上存在过并最终失败的“现实的社会主义”或称“经验的共产主义”模式,经济上表现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治上表现为官僚主义和自上而下的集权主义,是一种过时的共产主义,甚至走向了共产主义的反面,因此当前有必要与苏联式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彻底决裂,重构新的共产主义观念,以使人们重新认识和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然而,这些欧洲左翼学者在新的共产主义内涵理解上并没有形成统一看法,这些观点之间的矛盾和争锋本质上体现的是各自学术背景和立场的分歧。欧洲激进左翼的领军人物阿兰·巴迪欧站在超验主义立场,从超越的事件哲学出发,把共产主义观念理解为永恒的假设。从巴迪欧这一理解出发,既有学者对“共产主义假设”(The Communist Hypothesis)进行延展和补充,也有学者提出质疑和反驳。如齐泽克就跟随巴迪欧的脚步,指出资本主义体系内含的四种对抗性,并据此确证共产主义概念回归的正当性,提出自己的“共产主义假设”。布鲁诺·波斯蒂尔则批判了巴迪欧这种纯粹思辨的、哲学的共产主义,强调共产主义的现实性、实践性。朱迪·迪恩则又在波斯蒂尔的批判基础上试图从三个维度出发构建共产主义之势,为共产主义的理论大厦寻找实现动力[27]。迈克尔·哈特和奈格里等人则站在内在论立场,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出发,把共产主义理解为全球化和非物质劳动的内在趋势。以雅克·朗西埃为代表的学者从文化和美学的角度把共产主义理解为文化和艺术的共同创造和共同分享本性的体现[28]。除此之外,一些比较“小众”甚至“另类”的共产主义思想,包括“生态共产主义”、“美学共产主义”、“灾难共产主义”、“黑客共产主义”等等,也引起了国内研究者的关注。
最后,国内研究者并未被当前复兴共产主义的激情冲昏头脑,而是对这波共产主义思潮保持了冷静、理智、客观的判断。国内研究者普遍肯定欧洲左翼学者在全球资本主义统治时代敢于挑战新自由主义霸权、回归共产主义观念的理论勇气,但也清醒认识到这些学者中多数的“共产主义观念”和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的科学共产主义有着本质区别。他们理智、冷静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这波新的共产主义的理论观点进行了客观的辨析。例如,南京大学蓝江教授在研究了巴迪欧在本体论上建构共产主义观念,并试图以此涵盖现实的政治过程和政治目标的解放政治学逻辑后,毫不留情地指出这种纯哲学化论证下的“共产(公社)主义仍然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目的论幻想”[29]。复旦大学王金林教授在研究了齐泽克的“共产主义假设”后发现,他把一切被剥夺了公共体、实体或内容的主体都纳入到无产阶级范畴。王金林教授敏锐地指出这种将无产阶级概念激进化、泛化的方式“固然容纳了经典无产阶级概念所轻视的边缘群体,但却同时使这一概念丧失了原有的革命性”[30]。在河南大学副教授宋晓杰看来,即使在复兴共产主义的左翼学者群体中被认为最忠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奈格里,也由于过分强调革命的主体性因素,脱离了客观的物质生产关系,并把历史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动力简单归结为阶级意志的对抗和冲突,而存在“唯意志论的嫌疑、审美乌托邦的色彩和相对主义的风险”[31]。由此可见,国内研究者普遍认识到这些欧洲左翼学者尽管选取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的词语,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研究视角和方法,但他们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更多的是试图通过重新激活共产主义这一尘封已久的概念,表明自己的激进立场,彻底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统治秩序,建构符合当下情况和形势的理想国。然而,正如汪行福教授一针见血地总结所言:“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使自己的理论与现实发生联系……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共产主义从非现实性向现实性的转变,而当代激进左派走的却是相反的道路。”[32]
四、国外关于冷战后欧洲左翼学者的共产主义思潮的研究现状
国外对冷战后欧洲左翼学者的共产主义思潮的研究现状可以通过三个途径获知。一是对重要学者的共产主义思想进行专题研究的专著和学术论文;二是对重要学术会议进行述评的文章,包括标志性的“共产主义观念”大会和各种颇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刊物举办的学术年会;三是数量最庞大的书评,对以“共产主义思想”为主题的专著的观点进行综述,并发表自己的评价。国外的研究成果在内容上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共性:
首先,国外学术界相对更早地意识到了欧洲左翼学者试图重塑共产主义形象、复兴共产主义话语的努力。1991年罗宾·布莱克本主编的论文集《衰落之后:共产主义的失败和社会主义的未来》(AftertheFall:TheFailureofCommunismandtheFutureofSocialism)收录了苏东剧变期间“出自忧虑的社会主义者而非欣喜的政见相异者或反共分子笔下”[33]的一系列论文,集中探讨苏联式共产主义失败的原因和未来社会主义的可行性。克莉丝汀·莱德认为这本论文集有力地回应了“一种错误观念,即把‘共产主义’看作对抗民主的、多元的西方的一股不变的、单一的力量”[34],而忽略了它的多元性以及在反对法西斯主义、殖民主义,促进西方社会改革方面的贡献。同年由弗拉基米尔·蒂斯默纳鲁和朱迪丝·夏皮罗主编的论文集《关于共产主义未来的争论》(DebatesontheFutureofCommunism)也“对共产主义的缺陷和改革潜力的争论方面以及对共产主义崩溃的部分解释作出了切实的贡献”[35]。雅克·德里达被认为是冷战结束后欧洲最早旗帜鲜明地反对福山“历史终结论”,主张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辩护的左翼学者之一。乔纳森·约瑟夫认为他在苏东剧变后不久后的1993年就敢于顶住压力召回共产主义,是因为“共产主义幽灵可能是,并保持着对存在的超越。但它至少有能力徘徊。并且这一特质正是这一时期德里达希望及时唤醒的。”[36]亚历克斯·卡利尼克斯则认为新的共产主义思潮在批判理论家中兴起的“过程始于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2000年的著作《帝国》,其中著名的结束句激起了‘作为共产主义者无法抑制的轻盈与喜悦’[37]”,“但在唤醒共产主义的讨论中最具决定性的事件却来自于一个非常不同且在某些方面令人惊喜的方向”——2007年阿兰·巴迪欧著作《萨科齐代表什么?》(DequoiSarkozyedt-iflenom? )中的“共产主义假设”章节,“此文引起的关注对2009年伦敦的一场大型而广泛的公开讨论会产生了激励,该会议主要由齐泽克精心筹划,专注于‘共产主义观念’。巴迪欧的原始论文以及他提交给伦敦会议的文章反过来成为齐泽克和(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其他左翼哲学家广泛讨论的主题”[38]。而以帕纳吉奥提斯·索迪里斯和乔兰·波格丹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则从巴迪欧2003年的文集《无限思想:真理与哲学的回归》(InfiniteThought:TruthandtheReturnofPhilosophy)的其中一章“哲学与共产主义的死亡”(“Philosophy and the Death Communism”)里看到了他其实在提出“共产主义假设”之前就一直“试图复兴共产主义精神并对抗东欧所谓的共产主义民族国家的衰落”[39],并“始终忠诚于共产主义立场”[40]。
其次,国外研究者普遍明确认识到欧洲左翼学者这波共产主义思潮内部存在着把“共产主义”作为哲学观念还是现实运动的分歧,并对这种分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韦恩州立大学的史蒂文·夏维罗把2009年的伦敦“共产主义观念”大会所呈现的欧洲左翼学界对共产主义问题的分歧看作是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争论的历史回响。过去争论的一方是为了掌握权力而探索暴力革命策略的先锋,另一方是相信历史的逻辑会几乎自动地将资本主义导向社会主义并接着导向共产主义的人。而如今这两股张力的其中一支是齐泽克和巴迪欧回归革命激情的主张,但只坚持“激进的唯意志论”的必要性,以对抗无处不在的资本统治;另一支是哈特和奈格里以“诸众”作为力量对抗“帝国”的洞见,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全球化从结果上说已经创造了共产主义的客观条件。夏维罗认为:“在21世纪,这种对抗已如此了无生气以至于我们需要以某种方式完全超越它。但此次会议没有人能够提供这种方案。”[41]阿姆斯特丹大学著名政治与社会哲学家罗宾·西利凯茨还直截了当地以《共产主义:观念对“现实运动”?》(Communism:IdeaVS. 'RealMovement'?)[42]为题发表了自己对这次左翼内部关于共产主义的争论的倾向和看法。他肯定了艾蒂安·巴里巴尔和弗兰克·菲施巴赫不屈从于经济还原论、历史决定论或弥赛亚式的无产阶级高地,坚持绝对政治的、非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这种立场与理论、政治实践和社会经验有系统地关联起来,从而“为这场关于共产主义的讨论作出了重要贡献”。相应地,他批判以巴迪欧、齐泽克为代表的学者所提出的“共产主义观念”或“共产主义假设”,认为它完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对现状的社会理论分析。“这种对社会理论(更不要说经验主义的社会研究)的拒斥与唯意志论和纯粹主义相吻合,其固有立场是把对主体到奇特事件的‘忠诚’看作政治激进主义的标志。与现状的彻底决裂脱离了其潜在的社会条件而似乎成了关乎决心的问题。‘为什么是共产主义’或‘为什么成为共产主义者’也因此倾向于成为一个信仰问题。”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共产主义,如果仍然意味着什么,它只能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言,被理解为‘现实的运动’而不是观念或假设,即是说一种在历史和政治意义上内在于实际社会历史状况并同时彻底否定现存社会秩序的运动”。当然,也有像艾伦·约翰森这样的学者将这波新共产主义思潮集体判定为“旧共产主义的简单重复”,认为它仍旧“处在左翼极权主义的轨道内”,并对这些左翼学者反讽道:“新共产主义是如此诱人,我们承受不起而只能对它摇摇头然后离开。”[43]
最后,一些国外研究者已经开始尝试将欧洲左翼学者的新的共产主义思想运用于其它理论学科或现实问题的分析和研究中。约翰·罗伯茨在论文《导论:艺术、“飞地理论”与共产主义想象》(Introduction:Art, ‘EnclaveTheory’andtheCommunistImaginary)中就试图将近年来欧洲左翼学者的共产主义思想与文化美学研究相结合。在他看来,“科幻小说文学和反文化实践中的‘乌托邦飞地’(Utopian Enclave)②概念变成了与共产主义传统的隐秘(不引人注意的)对话”[44]。据此,他运用新型的“飞地思想”(“Enclave Thinking”)重新解读和阐释了这波新的共产主义思潮,包括巴迪欧的“共产主义‘不变量’” (Communism ‘Invariant’)理论、加塔利和奈格里的“共产主义的奇特性解放”(Communism’s Liberation of Singularities)思想和南希的“文学的共产主义”(Literary Communism)模型。通过这种跨学科解读,作者认为:“当务之急是什么样的共产主义适合于遭到挫败的共产主义遗产,而不是疯狂迷恋于共产主义名字本身。而且对先进的文化实践而言,必然关键的事实上是政治的审美化与美学的政治化在一种开幕的共产主义(Inaugural Communism)③或作为流动(先锋)试验空间的飞地思想的地带的相遇。”[40]市场专业的伯纳德·科瓦教授则和保林·麦克拉伦、艾伦·布莱德肖共同阐述了这波新共产主义思潮中的观点和方法如何影响了市场营销学。他们的论文《重思消费文化理论:从后现代到共产主义视野》(RethinkingConsumerCultureTheoryfromthePostmoderntotheCommunistHorizon)把目光“聚焦于一群复兴共产主义的理论家,同时思考这些观念如何帮助我们批判和重新设想消费文化理论(Consumer Culture Theory,CCT)”[45]。他们认为曾对消费者研究领域影响深远的后现代理论目前已经饱和,学术界对“后现代之后是什么”的疑问和迷茫则可以从共产主义观念里寻求答案。如果说巴迪欧把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看作打断历史自然演进过程的特殊事件,那么“不同于共产主义理论趋向于强调使现状断裂的事件,CCT选择只关注夺取和复制的时机”[41],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后后现代”(Post-postmodernism)路径,已经对CCT产生了无法回避的影响。正如作者指出:“向拥抱共产主义的转变意味着要考虑政治方向和CCT能动的主体地位。这种转变带来的分析模式不是仅仅设法解释消费文化,而是转而找出并培育抵抗和断裂的时机。”“共产主义不验自明地内化于CCT之中”以至于“CCT一直是共产主义的”[41]。还有一些研究者运用这些左翼学者的共产主义理论来解释和分析当前网络社会的现状和未来趋势,如费姆可·考林弗雷克斯和鲁德·考林弗雷克斯试图“探究当代基于互联网群体中的平民观念,作为对巴迪欧意义上的当代共产主义出场的探索”[46]。
习近平同志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而这个最高理想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的。”[47]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必须始终把共产主义作为我们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为此,在学术领域,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关注和研究世界共产主义思潮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动向、新发展。在介绍和研究冷战后欧洲左翼共产主义思潮时,必须时刻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判断这波新的共产主义思潮的标准,为真正的、科学的共产主义的复兴而努力探索。
注释:
①原文将《Goodbye Mr. Socialism》的出版时间写为1990年,但经笔者查证,此著作的最初版本为意大利文版,出版于2006年。
②所谓“飞地”,是一种特殊的人文地理概念,原指由某一行政区管辖却不与此行政区毗连的地区。但约翰森援引的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与其它科幻小说》(ArchaeologiesoftheFuture:TheDesireCalledUtopiaandOtherScienceFictions)中的“乌托邦飞地”的概念:“这种飞地如同社会中的外来物:飞地中的变异过程暂时被捕获到,以至于当这种变异过程一时间超越了社会的范围并且表明了其政治上的无力感时,飞地保留了下来,同时飞地提供了一种空间,在其中新的社会愿望图景得以设计和试用。”
③约翰森对他所理解的南希的“文学的共产主义”模式的一种称谓。
[参考文献]
[1]Ž ižek, S. 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 [M].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9: 7.
[2]曹松豪.法共二十九大用“新共产主义”取代“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的提法[J].国外理论动态,1997(16):121-127.
[3]费新录.法国共产党的兴衰之路:法共的历史演变与创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98.
[4]李周.探索中的法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250.
[5]丁俊萍,亓胜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过去和现在的经验:第十五次国际共产主义者研讨会综述[J].社会主义研究,2006(6):7-10.
[6]王喜满,王子凤.1999-2011年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评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4):144-150.
[7]聂运麟.论当代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性质[J].当代世界,2013(9):33-35.
[8]刘春元.2014年欧洲共产党会议述评[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34-38.
[9]刘淑春.欧洲社会主义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10]聂运麟.新时期新探索新征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209-240.
[11]Bulaitis, J. European Communism since 1989: Towards a New European Left? [J]. Political Quarterly, 2000,71(4):474-475.
[12]Hudson, K. European Communism since 1989: Towards a New European Left? [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3-16.
[13]Grzymala-Busse, A. M. Redeeming the Communist Past: The Regeneration of Communist Partie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4]卢克·马奇.欧洲激进左翼政党[M].于海青,王静,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26-27.
[15]Taylor, P. Martigues and After the French Communist Party in Its Eightieth Year [J]. French Studies Bulletin, 2001,22(80):16-19.
[16]Wilson, F. L. After the Deluge: The French Communist Party after the End of Communism [J]. German Policy Studies, 2002,2(2):259-289.
[17]Bell, D. S. The French Communist Party within the Left and Alternative Movements [J]. Modern & Contemporary France, 2004,12(1):23-34.
[18]March, L. For Victory? The Crises and Dilemma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J]. Europe-Asia Studies, 2001,53(2):263-290.
[19]Benedetto, G., Quaglia, L. The Comparative Politics of Communist Euroscepticism in France, Italy and Spain [J]. Party Politics, 2007,13(4):478-499.
[20]Holmes, M.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the Communist Dilemma: Communist Party Responses to Europe in Greece, Cyprus and Italy [J]. The Cyprus Review, 2013,25(2):141-142.
[21]Halikiopoulou, D.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the Communist Dilemma: Communist Party Responses to Europe in Greece, Cyprus and Italy [J].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014,37(3):672-673.
[22]汪行福.国外马克思主义2013[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3-25(B02).
[23]汪行福.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总报告(2013)[M]//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13.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9.
[24]汪行福.为什么是共产主义:激进左派政治话语的新发明[M]∥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8).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4.
[25]范春燕.一种新的共产主义:当代西方左翼学者论“共产主义观念”[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5):148-154.
[26]吴冠军.齐泽克的“第十一论纲”[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5):102-108.
[27]蓝江.新共产主义之势:简论乔蒂·狄恩的《共产主义地平线》[J].教学与研究,2013(9):81-89.
[28]汪行福.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总报告(2010)[R]∥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10.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3.
[29]蓝江.巴黎公社与共产主义观念:析巴迪欧的解放政治学逻辑[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5-12.
[30]王金林.唯物史观视阈中的齐泽克“共产主义假设”:《首先作为悲剧,然后作为喜剧》剖析之一[J].学习与探索,2010(3):17-23.
[31]宋晓杰.共产主义:革命主体性话语与替代性政治想象:奈格里对共产主义思想的重构[J].广西社会科学,2013(4):44-50.
[32]汪行福.共产主义的回归:伦敦“共产主义观念”大会的透视与反思[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3-11(005).
[33]Ryan, A. The Poverty of Theory:After the Fall: The Failure of Communism and the Future of Socialism[J]. edited by Robin Blackburn. The New Republic, 1992,206(13):34-38.
[34]Rider, C. After the Fall: The Failure of Communism and the Future of Socialism[J]. Robin Blackburn, editor.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4,6(4):493-496.
[35]Sanford, G. Tismaneanu, Vladimir and Shapiro, Judith. Debates on the Future of Communism [J].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1992,70(2):368-369.
[36]Joseph, J. Derrida’s Spectres of Ideology [J].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2001,6(1):95-115.
[37]Hardt, M., Negri, A. Empire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413.
[38]Callinicos, A. Alain Badiou and the Idea of Communism [J]. The Socialist register, 2013,49(1):326-344.
[39]Bogdan, J. Sovereignty and the Death of Communism [J]. Word & Text: A Journal of Literary Studies & Linguistics, 2012,2(1):137-153.
[40]Sotiris, P. Beyond Simple Fidelity to the Event: The Limits of Alain Badiou’s Ontology [J]. Historical Materialism,2011,19(2):35-59.
[41]Shaviro, S. Communism at Birkbeck [J]. Criticism, 2009,5(1):147-155.
[42]Celikates, R. Communism: Idea VS. ‘Real Movement’? [J]. Krisis, 2011(1):2-3.
[43]Johnson, A. The New Communism: Resurrecting the Utopian Delusion [J]. World Affairs, 2012,175(1):62-70.
[44]Roberts, J. Introduction: Art, ‘Enclave Theory’ and the Communist Imaginary [J]. Third Text, 2009,23(4):353-367.
[45]Cova, B., Maclaran, P., Bradshaw, A. Rethinking Consumer Culture Theory from the Postmodern to the Communist Horizon [J]. Marketing Theory, 2013,13(2):213-225.
[46]Kaulingfreks, F., Kaulingfreks, R. Open-access Communism [J]. Business Ethics: A European Review, 2013,22(4):417-429.
[47]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N].学习时报,2015-09-07(A1).
(责任编辑王婷婷)
Research Summary of the European Left-wing’s Communist Thought after Cold War
JIAN Fan
(SchoolofMarxism,The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
Abstract:Communism, which had been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in the 20thcentury, was challenged after the Cold War by many forces coming from liberalism, conservatism, social democracy and so on, and faced an unprecedented discourse crisis. Communist and workers' Parties and some left-wing scholars in Europe decided to lift the flag “Communism” to defend the true image of communism and make efforts to revive communist discourse, which became a new wave of communist thought. This attracted the interests of some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They introduce, research and discuss on it, and has produced a number of research achievements, which further expands the impact of this trend of though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rrange and introduce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classification according to four crossing dimension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parties and scholars, and expects to attract more extensive attention on this frontier topic from domestic scholars.
Key words:post-cold war; Europe; left-wing; communism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15XNH078)
作者简介:简繁(1989-),男,湖北省武汉市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收稿日期:2015-08-12
中图分类号:B089.1;D18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1.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