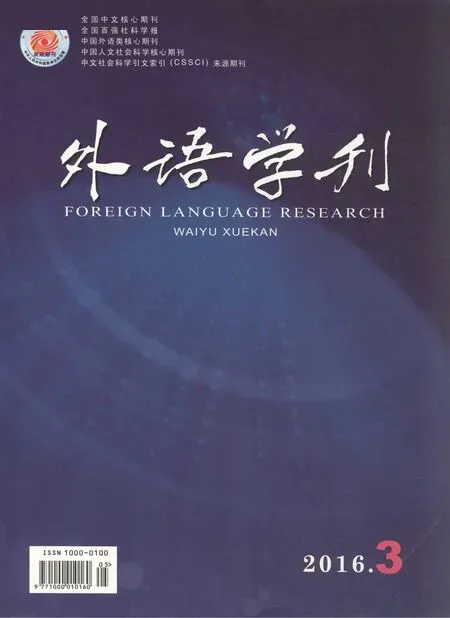觅材取材的动态特征与修辞哲学基础*
姜言胜 洪仁善
(东北师范大学,长春 130024;青岛大学,青岛 266071)
觅材取材的动态特征与修辞哲学基础*
姜言胜 洪仁善
(东北师范大学,长春 130024;青岛大学,青岛 266071)
觅材取材,作为修辞五艺的第一要素,在修辞研究中的地位可见一斑。伴随着修辞学的起起伏伏,觅材取材在认识论方面也经历由动态至静态再至动态的、鲜明的历史演变过程。同时,这些变化的产生根植于对真理本质属性的认识以及修辞学与哲学关系的解读。
觅材取材;动态特征;修辞学
1 引言
觅材取材,无论在修辞理论还是在修辞实践中都占据核心地位。正如所言,“修辞的力量与价值与觅材取材紧密相关。这是由于当修辞学与系统的探究方法以及实质内容相分离时,就会变得肤浅且微不足道”(Young, Alton 1975:123)。这里的探究方法和实质内容均根植于觅材取材,从觅材取材中汲取营养。自古典修辞学伊始,觅材取材作为“修辞五艺”的第一要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20世纪新修辞学的兴起,觅材取材再一次受到广泛关注,重新成为修辞学研究的一大焦点。觅材取材之所以重要主要在于任何言说者交际的实质内容皆蕴含着大量的策略性行为,而这些行为可以为修辞者在修辞过程中提供明确的方向、建设性的想法以及建立在或然性基础上的判断,从而熟稔修辞情境,为修辞行为的顺利实施打下坚实基础。与此同时,觅材取材还涉及对文本的解读以及对受众的分析。事实上,文艺复兴后,在拉米斯的作用下,觅材取材从修辞学领域中的脱离也印证其对于修辞学的重要性。这一脱离的直接结果就是,修辞学成为仅仅关注文体风格、表达思想的工具,与交际的实质内容毫无关系可言。从上述说明中不难看出觅材取材相对于修辞学的重要性;同时,修辞学领域有关觅材取材的研究极为必要。值得关注的是,在修辞学的历史发展长河中,觅材取材一贯保持的重要性并不能掩盖其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呈现出的不同特征以及在认识论方面存在的差异。本文聚焦于古典修辞学以及新修辞学视阈中的觅材取材,并以此为视角探究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的差异。
2 古典修辞学视阈中的觅材取材
不只是对于觅材取材,甚至对其依附的修辞学进行追根溯源的时候,都必须首先考虑古希腊哲辩师。事实上,探究觅材取材在古希腊时期的具体状况应围绕着古希腊哲辩师、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对其的看法展开。就哲辩师而言,他们对觅材取材的看法以及在相关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们提出并倡导的相关概念。就这些概念而言,首先是kairos.该词含有时机、契机之意,英语中并没有对应词汇。古希腊哲辩师们认为,考虑一个修辞情境应首先考虑它的kairos. 他们对kairos的重视度可以从他们对不同时间点下的修辞行为的不同效果的评价中看出。在正确的时间点做的事情总是怡人的;在错误的时间点做的事情是令人羞耻的。对他们而言,kairos是一个灵活多变且多维度的术语,蕴含着时间与空间的相关概念。Kairos根植于修辞情境,直接指向开启语篇的最佳时间点。它的时间维度可由冗长的时间段抑或由短暂的时间点来表现。基于kairos的语篇并不以探究先验的真理为己任。与之相反,它否定真理的绝对性与先验性,并将写与说视为探索事物本质、获取知识的途径。与此同时,将kairos奉为觅材取材重要原则的修辞学并不为找寻论据提供规则,而是鼓励修辞者关注相关主题的历史,提高对使用论据的适宜时机的意识。换言之,修辞者应密切关注修辞情境内相关主题涉及的时间与地点,并探究主题与时间、地点等因素的关联性。
考究kairos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是通过关注不同论辩方就特定主题采用的论据,从而更好地了解论辩者在特定的时间段抑或时间点内达不成统一意见的原因。提及修辞者在论辩中的分歧必涉及到古希腊哲辩师所提出的另一个概念——对言(dissoi Logoi)。作为对言理论的倡导者,普罗泰戈拉认为,就任何主体而言都存在从正反两方面论证的可能性。这一论述又根植于他的论断“人是判断一切事物的标尺”。普罗泰戈拉认为,人的感知不论在任何时刻对于其本人而言都是真实的,并且根本就不存在能够证明在若干观点中何种观点为真理的终极手段。事实上,并不存在更真的概念,而只存在更好的概念。他对人的感知力的推崇以及对真理的超验属性的否定致使他摒弃同一属性在同一方面既可同时属于亦可不属于同一事物的论断。在此认识基础上,普罗泰戈拉宣称,针对任何事物都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且两种说法均有道理。刘亚猛说,该原则(对言)推翻“针对所有事物都只有一种正确的观点,即体现于传统见解或流行说法的那一个观点”(刘亚猛2008:31)。认可正反两方面均存在说得通的观点,即认可言说者间针对任何事物存在分歧的合理性,必将指向产生分歧的点,也就是说,持不同观点者在何时以及何处产生分歧。古希腊哲辩师们继而提出stasis理论,旨在帮助修辞者们发掘分歧点。Stasis一词始于希腊语,意为立场。由此,stasis指代修辞者采取立场的地方。就论辩双方而言,它标识两种相悖力量的交融以及对于分歧点达成的共识。哲辩师们认为,在任何修辞情境中都必须存在一个持不同观点者均认同的分歧点。哲辩师的这一观点也得到古罗马修辞学家的响应。Quintilian提出,“任何问题都必须根植于论辩一方的支持以及另一方的否定”(Quintilian 1980:7)。作为觅材取材的手段,stasis为修辞者提供一系列的问题用以探究相关主题以及修辞情境的特征,从而帮助修辞者决定他们与受众产生分歧的点,双方均认可的分歧点。显而易见,此点作为觅材取材的出发点受观点间的分歧所助推。正如Crowley和Debra所言,“决定分歧点对于任何修辞论辩而言皆是至关重要的,而找到此分歧点的难度要远比看上去大得多”(Crowley, Debra 1994:54)。
从古希腊哲辩师在觅材取材中热衷的概念阐释中不难发现,对他们而言,觅材取材的整个过程是一个强调修辞主体的动态过程,是一个探索真知且饱含不确定性的过程。将人视为评判万物的标尺,不仅确立人在修辞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同时也表明人在知识产生以及创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认为人的感知是产生知识的直接过程且强调人与人之间感知的差异性,则否定知识的超验属性,同时为觅材取材的动态属性创造先决条件。Kairos通过着眼特定修辞情境下的时间点,强调在不同时间点下修辞行为的修辞效果截然不同,从而提高修辞者对于开展修辞行为的适宜时间点的意识。通过推崇其在觅材取材过程中的地位,即在知识产生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古希腊哲辩师们清楚地摒弃知识先验属性的立场。对言理论通过强调不论任何事物正反两方面均存在说得通的道理,与柏拉图倡导的知识绝对属性直接相悖,它不仅为修辞活动的具体开展提供理论支撑,同时规划与界定修辞的范畴。Stasis理论通过一系列的相关问题帮助修辞者找寻开启修辞活动的着眼点,即论辩中持不同观点者皆认可的分歧点,为接下来的劝说行为进行有机的铺垫。综上所述,在古希腊哲辩师就觅材取材提出的概念中,不管是相对宏观的概念,如以人为本的概念以及对言理论,抑或是针对具体修辞行为的概念,如kairos和stasis理论,都表明他们将这一修辞要素视为知识产生的动态过程,而非对在他处产生的知识进行简单搜寻的静态过程。尽管如此,哲辩师眼中觅材取材的这一动态属性并没有被之后的所有学者接受。
3 亚里士多德理论框架下的觅材取材
相较于他之前的古希腊哲辩师而言,亚里士多德在古典修辞学视阈中觅材取材方面的贡献堪称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他们皆给予觅材取材以足够多的重视,不论是在目的和性质方面,抑或是在认识论方面,他们对觅材取材的见解都存在显著不同。我们认为,亚里士多德在觅材取材方面的建树主要体现在他对话题(topoi)的阐释之上。话题早在公元前6世纪甚至更早就已存在,亚里士多德的突出贡献在于他系统地发展话题理论。然而他并没有给予话题一个明确的定义。其实,对话题进行定义并非易事。Slomkowski说,“在过去的50年间,有关话题的定义问题一直困扰着对该领域感兴趣的所有学者”(Slomkowski 1997:1-2)。这是因为定义话题必将涉及以下与它密切相关的问题:意义、性质、分类和功能等。此外,规划一个较为完善的话题体系必须以具体的目的为指引;同时,这一体系下的具体话题项必须呈现出话题的性质与功能。自古至今,修辞学者们关于话题的认识论也持有不同的见解。部分学者将话题视为一个静态的概念,而其他学者视之为一个动态的概念。Cicero将话题定义为“论据所处之地”(Cicero 1968:122)。Quintilian将话题定义为“置放论据的秘密场所,同时也是提取论据之处”(Quintilian 1980:45)。Eemeren等(1996:38)将话题描述为策略性地帮助修辞者战胜论辩对手的论辩手段。其他修辞学者,如Vancil(1977)和Rubinelli(2009)将话题视为动态概念。他们把话题当成建构论据的策略而非简单放置抑或找寻论据的处所。
话题领域的修辞学者不管是古时抑或是今日均视亚里士多德的话题体系为该研究领域的基石。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话题》中共包含三百多个话题项,他在《修辞学》一书中详细阐述其中的部分话题项。根据Grimaldi所言,亚里士多德的话题体系运作于3个层面上。这3个层面具体包括能够产生信念的源材料,通过利用在第一层面收集到的材料赋予事物以形式的方法或技巧,以及在受众脑海中产生的映像(Grimaldi 1957:188-189)。大体上,话题可以分为材料型话题 (material topoi)和形式话题 (formal topoi)。材料型话题指代可以发现蕴含或然性命题的场所,而形式话题指根植于三段论的具体推理方式以及证据类型。材料型话题又可以继续划分为特殊性话题(special topoi)和一般性话题(universal topoi)。特殊性话题与一般性话题的主要区别在于话题的应用范围。特殊性话题指那些根植于仅可应用于特殊群体以及类别的命题的论据和策略。特殊性话题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有关专项主题的话题、有关3大演讲语篇的话题、有关3大修辞诉诸的话题和有关演讲术的组成部分的话题。其中,演讲术包括引言、叙事、论辩以及结论。一般性话题指可以应用到所有主题的话题,不管涉及到何种演讲术,也不管修辞者采用何种视角。据亚里士多德所言,一般性话题主要包含4项:“什么是有可能或不可能发生的”,“过去是否发生过这种事”,“将来是否可能发生”以及“多大程度上如此”(刘亚猛 2008:58)。
对于修辞者而言,一般性话题与特殊性话题的主要功能皆在于为修辞三段论找寻内容,而形式话题主要负责为他们提供论辩以及推理模式。与材料型话题不同,形式话题并不是具体的论辩材料,而是组织材料,并将其建构成相关论辩证据的推理模式或者规则。形式话题下的任何一种话题项都能够产生大量根植于修辞三段论的具体论据。它们均产生于亚里士多德对演说中推理模式的观察。由以上阐述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的话题体系主要建立在两大假设基础上。其一为:觅材取材的源材料是可以经过系统化的过程以话题的方式确定下来。其二为:话题先于修辞者而存在,同时,修辞者并不参与话题的产生过程。话题的划分是根据材料本身的性质以及用途而完成。宏观来讲,一部分话题由于自身包含论辩内容可以为修辞者直接提供论辩中针对具体主题的相关论据;而另一部分话题则为修辞者提供组织以及运用这些话题的模式和策略。由此,亚里士多德明确处在具体修辞情境中的修辞者在觅材取材过程中的任务。换言之,他解决修辞者在觅材取材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即“修辞者在论辩过程中应该采用什么材料”以及“如何去使用这些材料”两大问题。在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话题体系内,觅材取材的过程变得异常简单。针对具体话题,修辞者仅须从一般性话题以及特殊性话题中选定相关的论据,继而由形式性话题中选定论辩的方式和策略。经过高度形式化以及系统化的话题为修辞者的觅材取材提供巨大便利,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这一做法极大地削弱作为修辞主体的修辞者在觅材取材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修辞者无须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建构符合自己修辞目的的论据。他仅须照搬话题体系里的话题项,无须对所选话题进行修改。将修辞者排除在话题的产生过程外无形中承认话题的静态属性以及各话题项内容的权威性。
4 新修辞学视阈中的觅材取材
新修辞学以降,尤其是在修辞学的生成理论产生之后,觅材取材的动态属性再一次焕发青春,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Scott 1971:229)。生成修辞学概念的提出从根本上扩展修辞学的研究范围。在这一概念下,修辞学不再是表达意义、真理抑或知识的技巧及手段,而是生成知识、创造真理的一门艺术。Young认为,“生成理论视阈中的修辞学正在经历本质的变化,其旗下的觅材取材成为一门统治性的艺术”(Young 1982:2)。Lauer阐述这一理论对文章学的影响:“觅材取材从写作学科的课程设置至文化研究、再至有关性别、种族以及文化差异的研究,业已融入至且确立并形成文章学范围内的相关理论与实践”(Lauer 1982:89)。Muchelbauer表达相似的观点:“不论其范围多么有限,生成修辞学内的觅材取材带来一种复兴,孕育着一种全新开始的可能性”(Muchelbauer 2008:16)。
修辞学的生成理论严厉地批判传统修辞学的局限性,因为在传统修辞学模式下,修辞学完全被排除在知识的产生过程外,其存在价值仅仅在于传送于他处产生的知识。它赋予觅材取材一种全新的意义。觅材取材的任务不再仅仅局限在发现那些用以传送于他处产生的知识的劝说性策略。觅材取材本身就参与到知识的产生过程。修辞学亦成为发现知识的一门艺术。传统修辞学强调劝说,生成修辞学的关注点在于知识的产生。在生成理论体系下,知识不再享有超验的地位,而是与其产生于其中的极富偶然性的修辞情境息息相关。换言之,知识的产生不但不再独立于内嵌于修辞情境的众多因素,而且受制于这些因素。修辞学不再是罔顾事实真相、仅通过操控受众而获得实际利益的言语伎俩。一旦跨越传统修辞学的羁绊,修辞学就不再游离于知识创造的大门外;相反地,它成为产生知识的重要源泉。伴随着这一变化,觅材取材的动态属性也得到强有力的诠释。其不再是单纯地找寻有利于主题的相关话题以及相应的论辩、表达技巧或策略,而是一个饱含变数的建构语篇的创造性过程,也是一个动态的求知过程。
觅材取材动态属性的回归亦可从新修辞学以降尤其是修辞学的生成理论问世之后兴起的、与觅材取材密切相关的若干词汇中得到体现。首先需要关注的词汇为“认知论”(epistemic)。Epistemic一词在修辞学视域内指产生抑或创造知识的能力。植于认知论的修辞学通过运用语篇建构知识,其关注点在于产生知识的过程。它基于求知且以求知为己任,强烈反对将修辞学视为传送于他处产生的先验知识的工具。认知论下的觅材取材认为,修辞行为始于包含不确定性的问题,经由求知的过程,最终得出基于或然性而非确定性的结论。由此不难看出,认知论主张知识的多元属性,尤其关注那些产生于具体修辞情境内根植于或然性的知识。这不仅为觅材取材作为求知的动态过程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亦为这一修辞行为的具体开展指明方向。除epistemic外,“启发式策略”(heuristics)一词亦值得提及。该词出现于上世纪60年代,关注发现知识的过程,具体指在创造性过程中起引导作用的策略。相悖于形式逻辑,heuristics无须遵循演绎的公式般程序。相反,它被视为更加灵活以及有效地开展创造性活动的一种方式抑或方法,具体包括一系列启发性问题、具体的实践行为和用以引导求知的视角。这些策略既非完全受控于条规,亦非完全随意而行,鼓励修辞者在探究过程中针对相关问题采用多重视角,从而获得新的理解,创造新的知识。
从对修辞学的生成理论以及对上述两个词汇的阐述中不难看出,新修辞学后的觅材取材继古希腊哲辩师之后再一次成为建构语篇和创造知识的动态过程。它主张知识的多元属性,推崇根植于舆论与观点的、饱含不确定性的或然性知识,同时视修辞情境以及受众为知识创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这些与古希腊哲辩师对觅材取材的看法相吻合。由此,觅材取材在近二千五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呈现出鲜明的特征。古希腊哲辩师视其为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动态过程,它充分肯定受众以及修辞情境在整个修辞活动中的重要性,同时赋予修辞者相当程度的灵活性及主动性。然而自从亚里士多德将话题分类系统化之后,觅材取材的动态属性逐渐消失殆尽,已不再是生产知识的创造性过程,而变成寻觅与主题相关的话题的机械性静态行为。新修辞学以降,随着修辞学挣脱自古典时期以来的桎梏再一次成为创造知识的源泉,其动态属性亦随之而回归。我们认为,觅材取材的动态与静态属性间的更替并不是偶然行为,其根植于对于修辞本质的认定以及对于修辞学与哲学间关系的解读。
5 觅材取材的修辞哲学基础
柏拉图在《费德鲁斯》一文中提出好坏修辞学的概念。所谓“好的修辞学”应服务于真理,视真理为超验的存在,其主要价值体现在将真理以尽可能准确的方式由已知的哲学家一方传送到未知的受众一方。修辞学并不关注真理的内容,因为其与真理的内容以及真理的产生过程无丝毫关联,它在意真理在传送过程中是否能够得到完全复制,同时作为真理的接受者的受众是否能够将其理解并且掌握。由以上柏拉图的阐释中不难看出,所谓好的修辞学也不过是表现真理的工具,其视域内的觅材取材承担的无非是确定于他处产生的真理。另一方面,柏拉图眼中所谓“坏的修辞学”直接指向古希腊哲辩师推崇的言语劝说行为。相较好的修辞学而言,此类修辞学更关注意义的复制以及传送在受众方面引起的效果,而非意义本身。此模式下的修辞学亦可被誉为发明的艺术,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它发明的并不是知识抑或真理,而是传送真理及知识、用以应对灵活多变的修辞情境的适宜策略及手段。总之,柏拉图定义下的修辞学,不管是“好的修辞学”或是“坏的修辞学”,都是表现和传送知识的工具而已。归属于此修辞学的觅材取材也无非是找寻以及确定与主题相关的话题而已,其与知识的发现与产生无丝毫关联,故而静态属性分明。
一旦将修辞学认定为创造知识的艺术,觅材取材的属性完成由静态至动态的转变就成为必然。换言之,认可修辞情境和受众在意义产生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意义本身的偶然特性,就为修辞生产意义以及觅材取材呈现动态属性提供先决条件。这一有关修辞本质属性的界定同时蕴含着对于真理本质属性以及修辞学与哲学间关系的认识与思考。如若真理被认定为单元的、超验的,那么只有那些经过严格、缜密、客观、辩证和科学的逻辑推理过程而得出的结论才可以被确定为知识抑或真理。如此一来,必将切断以强调人的因素、社会舆论、大众观点、常识和饱含偶然性的修辞情境为根本特征的修辞学与真理的一切关联。反之,若认定真理的多元属性,真理不再被局限为柏拉图推崇的超验真理,这就为修辞学产生知识创造先决条件。位居古典修辞学之首的觅材取材自然也成为这一创造性活动的主要执行者,其动态属性亦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觅材取材的属性亦可以从修辞学与哲学间的关系上得到解读。自柏拉图开始,修辞学与哲学在分工与性质方面可谓泾渭分明。哲学视追求真理为己任,而修辞学依附于以或然性及偶然性为特征的观点、舆论和常识等;哲学探究史实性与客观性,而修辞学寻求并不遵从于史实的主观性;哲学热衷于现实的结构,而修辞学指向受众性格中的弱点;哲学强调其探求真理方式的理性方面,而修辞学重视对于受众态度的操控方面。如此认识下的修辞学自然而然地与知识的创造完全脱钩,其旗下的觅材取材亦成为找寻话题的静态过程。然而当我们质疑哲学与真理间的业已约定俗成的内在联系时,就会产生对于两者间关系的重新认识。哲学家并非先知,所以他们的理论亦非超验,故而极难得到普世的认可。这一认识就为修辞学与哲学的有机融合提供交融点。Johnstone提出,“视修辞学为经验的一种必要模式的哲学与忽视修辞学存在的哲学截然不同”(Johnstone 1966:43)。修辞学与哲学间不再呈水火不相容的态势,两者相互依附,相互补充,哲学不再对修辞学嗤之以鼻,相反,它成为区分此哲学与彼哲学的标尺以及将哲学家解脱出来的唯一有效方式。总之,当真理不再凌驾于时间与空间之上,哲学与修辞学间的界限开始模糊起来,哲学充分认可意见、观点、信念、或然性和偶然性等在知识创造过程中的重要性,修辞学创造知识就有其坚实的修辞哲学基础,觅材取材的动态属性亦拥有理论支撑。
刘亚猛. 西方修辞学史[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Cicero, M.T.Topic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Crowley, S., Debra, H.AncientRhetoricsforContemporaryStudents[M]. New York: Macmillan, 1994.
Eemeren, F.H., Grootendost, R., Henkemans, F.S.FundamentalofArgumentationTheory:AHandbookofHistoricalBackgroundsandContemporaryDevelopments[M]. New York: Lawrence Erlbaum, 1996.
Grimaldi, W. M. A.A Note on the Pisteis in Aristotle’s Rhetoric 1354-1356[J].AmericanJournalofPhilosophy, 1957(78).
Johnstone, H. W. The Relevance of Rhetoric to Philosophy and of Philosophy to Rhetoric[J].QuarterlyJournalofSpeech, 1966(1).
Lauer, J. Writing as Inquiry: Some Questions for Teachers[J].CollegeCompositionandCommunication, 1982(33).
Muchelbauer, J.TheFutureofInvention:Rhetoric,Postmo-dernism,andtheProblemofChange[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8.
Quintilian, M.F.TheInstitutesofOratory[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Rubinelli, S.TheClassicalTechniqueofConstructingArgumentsfromAristotletoCicero[M]. Lugano: University of Lugano, 2009.
Scott, R.ReportoftheCommitteeontheNatureofRhetoricalInventioninTheProspectofRhetoric[M]. New York: Prentice Hall, 1971.
Slomkowski, P.Aristotle’sTopics[M]. New York: Koln, 1997.
Vancil, D. L.TheDisappearanceofTopoiinEnglishRhetoric, 1550-1830[M]. Ann Arbor: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77.
Young, R. Conceptions of Art and the Teaching of Writing[A]. In: Murphy, J.(Ed.),TheRhetoricalTraditionandModernWriting[C]. New York: MLA, 1982.
Young, R., Alton, B.ContemporaryRhetoric:AContemporaryBackgroundwithReading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k, 1975.
DynamicFeaturesofRhetoricalInventionandItsRhetoric-philosophyBasis
Jiang Yan-sheng Hong Ren-sha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s the first canon of classical rhetoric, rhetorical invention occupies a prominent position in the study of rhetoric. Along with the falls and rises of rhetoric, rhetorical invention in its epistemology exhibites striking variations from being dynamic to being static and to being dynamic in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In addition, the shift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its nature is planted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nature of truth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hetoric and philosophy.
rhetorical invention; dynamic features; rhetoric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意义进化视角的英汉语法隐喻研究”(12BYY008)的阶段性成果。
H05
A
1000-0100(2016)03-0037-5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3.008
定稿日期:2016-01-25
【责任编辑谢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