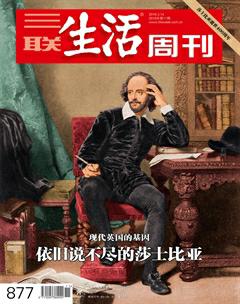周小燕,“中国夜莺”之歌
王丹阳

周小燕
桃李不言
周小燕的一生是真正配得上杨绛的那句诗:“我的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她是一个单纯到仅有音乐和学生的人,以至于没有学生便焦虑不安,在她既病痛又想念教学的最后的一段日子,上海瑞金医院甚至设想过给她在医院里开一个钢琴教室。
上海彩虹合唱团的艺术总监金承志也是师出上海音乐学院,他说:“她就像马革顺(中国合唱开山者)一样,是我们学校的宝藏。”周小燕作为一名教师,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典范,在上海音乐学院,无论是否曾受教于她,这位终身老教授的兰蕙之质、芳华品格都是一个标杆化的存在。她位于上海复兴中路的老公寓客厅,就像一个敞开的艺术舞台,学生络绎不绝地上门,她为他们上一对一的专业课,每天上午四节课,下午三节课,直至住进医院那一天。
即使在意识模糊时,学生去医院探望,她已不能说话,但还是会下意识地挥手做指挥动作。
4个月前,病榻上的周小燕突然对李秀英慎重地说道:“我还有几个研究生,希望你可以帮我带他们。”说完,她就流下了眼泪。李秀英是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的教授,1994年始师从周小燕,她知道当如此离不开学生的恩师对自己提这个要求时,说明她当时已多有力不从心。那晚李秀英难过了很久。“直到今天,我每次想到,我再也见不到她了,都会觉得遗憾。”学生们都唤她“周先生”,那是那个年代对知识分子的特有的礼节式尊称。
著名音乐评论家居其宏曾说过,在声乐界,把创建中国声乐学派当作目标理想的有志之士大有人在,其中有以美丽动人的唱歌艺术独树一帜堪称大师者如郭兰英等人;有高徒辈出而惊艳国际乐坛的如沈湘等人,而将这两者合二为一、兼而得之的双料大师,仅周小燕一人而已。
“在美声唱法界,周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巨擘,在美声的同行心中她是最受尊敬的一个。”李秀英说。“她虽然不是我的老师,但她是我们大家的老师。”著名女高音、现在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执教的黄英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周小燕有种魔力和磁场,她身形娇小、面容清癯,但说起话来眼里却透出炯炯如炬的光,从那副永远不离的金丝框眼镜后面射来。无论是她直系的弟子,还是曾受其指导,甚至仅有短暂交集的同行,都为她的气度和绵柔里透出的铿锵而念念不忘。美声唱法里讲究的节拍不容模糊,正如在中国戏曲里,节拍就是“心脉”和“板眼”,周小燕说,唱歌或戏剧表演都要有板有眼,要留意音乐中的“板眼”之神韵。
如果说周小燕唱的歌、教的歌讲求参差多态、婀娜生姿,那她的人生也堪比音乐般美妙和跌宕。见过她的人都公认,无论在哪种场合,跟谁说话,她讲话的逻辑感、思维的敏捷性叫人吃惊。哪怕是在去世前,她都依然神志清晰,不容含糊,她的血液中都流淌着良好家世所培养出的“板眼”。
音乐之家
1917年,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开始了一场讨伐北洋军阀独裁的护法运动,周小燕出生在武昌黎黄陂路的一个富裕的工商世家。其父周苍柏是汉口上海银行的经理,毕业自纽约大学经济系,也是一名具有进步思想的实业家。周家富甲一方,在当地经营过名头不小的民族企业——重庆华中化工厂、汉中制革厂。
1930年,周苍柏深感市民沉迷赌博与鸦片之害,在东湖西岸兴建了占地600亩的“海光农圃”。据周小燕回忆:“农圃三面环水,湖光山色,景色宜人。”不过,周苍柏说:“这地方将来不是你们的,我把它建设好了要献给人民。”海光农圃就成了城市公用之地,一个苗圃、一片桃林、一个动物园、一潭观鱼的天鹅池,还有香坊和米坊。这就是今天的东湖公园,周苍柏被誉为“东湖之父”。
周苍柏虽不识音律,却是出了名的“音乐迷”,周小燕与弟妹从小在家中与西洋乐器为伴,玩转钢琴、小提琴、萨克斯、吉他,几乎可组小型室内交响乐团。在满目疮痍的战争背景下,这个颇有《音乐之声》风范的家族在财富的庇佑下暂得艺术的滋润,他们常受西洋歌剧启发,穿戴各种宫廷服、假发套扮演歌剧人物,周小燕喜欢自扮公爵或小丑,而弟妹就被她扮成漂亮温柔的公主。
周小燕对于歌唱的热爱与生俱来,以至于前几年接受采访时,她说自己除了唱歌没有别的什么爱好。在富足安逸的生活方式的底子中长大,她始终是个单纯与高雅共存的人。有次父亲问她,你那么喜欢唱歌,想不想考个学校?少年时的周小燕诧异道,原来唱歌还要学啊?但抗战爆发后,这种单纯的对艺术之爱彻底被抗日救亡的洪流改造。
1938年,上海遭遇“八一三事变”,周小燕已经在上海国立音专(上海音乐学院前身)求学一年,迫于形势,不得不辍学。这时武汉变成了大后方,周恩来、聂耳、冼星海都在那里,她作为唯一一个会唱歌的专业生加入了抗日救亡宣传队。其实当时她声音的问题都没解决,“唱到fa都要破”,但是身处抗战洪流之中,需要随时被推向田间地头、医院学校,恰恰在临阵前急火一攻心,就唱上去了。
周小燕的成名得益于抗日救亡,20岁还懵懂的年纪,就因首唱《长城谣》、《歌八百壮士》、《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而红遍全国。她就像《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不管是身不由己还是受时代情绪鼓动,在伴随着心智的成熟里,永不缺位的是如草般萌生的朴素的爱国主义情结。1995年,抗战50周年之际,她被邀请登上长城再唱一遍《长城谣》时,曾对媒体回忆起在烽火中唱歌的心情:“我就想最早我唱《长城谣》的时候,中国是个啥样子,大家心里都是怕做亡国奴。”
那时,这位资本家大小姐的大弟德佑也从上海回到武汉组建了抗战剧团,身兼导演、编剧、演员,在鄂北、山西一带工作,但工作强度之大导致积劳成疾,不到19岁就累死在前线。追悼会那天,周总理、邓颖超、董必武都来了。“我不晓得他们,但我觉得有与众不同的一种感觉。”周小燕说。她不懂马列主义,但对共产党人的好感源于他们救国图存。
中国夜莺
1938年,周小燕再次踏上音乐求学路,本打算去意大利,但因意大利加入希特勒阵营而改道法国。在那里,她碰见了著名作曲家亚历山大·齐尔品(Alexander Tcherepnin),经推荐师从纳迪娅·布朗热(Nadia Boulanger)。那时,她自学了蝴蝶夫人咏叹调,自以为可以,院里传“来了一个小蝴蝶”。但老师一把脉,就听出她并不纯正的美声腔。“因为都是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中国不会亡》这样的歌跑过去,说我喉音太重。”布朗热教她用横膈膜呼吸,结果她脸涨得通红,声音也发不出来。
她是中国最早到西洋取经正宗美声唱法的一代人,因为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天然沟壑而不得不从零开始。即使在中国已是小明星,但在正宗的音乐殿堂里就要“靠躲靠混”,乃至音准也不对了。周小燕就这样哭着找齐尔品,那真是进退两难,想回去也回不成。
周小燕又进入巴黎俄罗斯音乐学院,师从意大利著名声乐教授贝纳尔迪。这位大师禁止她唱歌,只许练声,这招纠正了她的痼疾,乃至在7年后的1947年,她有幸登上20世纪最重要的一场音乐会——布拉格之春音乐会。
那场音乐会上,国际顶级的音乐大师到齐了。苏联的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小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英国的小提琴家梅纽因,美国的钢琴家伯恩斯坦……周小燕初次以贺绿汀的《神女》、刘雪庵的《红豆词》亮相,这也是以美声唱法演绎民族歌曲,在这点上她是开了先河。
有次吴祖光对周小燕说,他去法国出访,遇到一位法国汉学家,后者告诉他,对汉语的热爱来自曾听一位中国姑娘唱中国歌,觉得中国语言非常美。那首歌就是《紫竹调》,在布拉格之春音乐会后,她已被世界称作“中国的夜莺”。
她本来可以成为世界歌剧舞台上经久不息的常青树,但在1949年如日中天时选择回国执教,在上海音乐学院一待便到寿终。她还不计报酬到大学为师生演唱,交通大学学生会赠她锦旗“唱破这阴湿的天”,还有的锦旗上绣着“从黑夜歌唱到天明”。
这也是为何她得到的赞誉要高于纯粹的以表演自居的舞台艺术家,她前半生辉煌的歌唱事业,后来被糅进了更耀眼的奉献的光芒。周小燕出身高贵,也懂得从自己的高位上放下身段,为声乐普及化散布光热。
“文革”伉俪
1949年,她接到去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通知。她对周恩来说,自己没为革命做过什么,怕被说是投机。周恩来回答她“但你投人民的机”,于是她激情澎湃地写入党申请,终于在1956年入了党。
不可遗漏的是她那位电影才子丈夫张骏祥,文艺界里有说法是周恩来牵线促成他们秦晋之好。1951年,新中国派出了第一个大型文化交流团赴印度和缅甸,阵容之强有郑振铎、钱伟长、季羡林、冯友兰、吴作人,还有耶鲁戏剧研究院毕业回国的张骏祥……唯一的女性就是周小燕。两人在那里骑了大象,数月之后,同团的吴作人就要送一幅“双象图”作为对他们的结婚贺礼。
他们的一对子女曾告诉媒体,母亲对于学生的爱要甚于对他们。有时母亲在客厅里教学生,父亲便带上门,同两个孩子在卧室里偷玩。周小燕忙起来还会丢东西,拎包、眼镜、围巾都丢过,张骏祥直呼“天女散花”,“漏斗脑袋”,“马大哈不可及也”。
周小燕一生最痛苦的时刻就是“文革”,她忍痛把高跟鞋的跟拔掉,把黑胶唱片放在不平的地上踩碎。一家人星散四方,夫妇俩在奉贤海滩上的干校里劳动,分隔一条河,被规定不能来往。张骏祥被派去养猪,周小燕则分工养鸡,干校的同事戏称他们为“猪公”“鸡婆”。
晚年张骏祥为病痛所困,还伴有耳疾,却常以幽默对之。有一次,他对上海电影导演陈鲤庭夫人毛吟芬说:“女人的声音音频高,易听清。”毛吟芬打趣:“那你家那位花腔女高音的声音你最听得清了。”张答道:“不,是听得烦了。”
周小燕聚集学生在客厅里唱歌,“高朋满座”,“鬼哭神嚎”,他只是待到自己里面的小房间去,有时也不用关,因为耳聋,“反正听不见”。1996年,张骏祥逝世于上海华东医院,周小燕波澜不惊的教学生涯从此埋下一丝不易被察觉的阴霾。
她每次回忆老伴的时候,并不显露忧郁。“她总是说张先生风趣的地方,说得自己哈哈大笑,其实越是这样,我们越是心疼她。”李秀英回忆十几年前还是她上门弟子的时候,她总是这样,但是她会在学生都走光后流露出忧郁。子女都在美国,张骏祥去世时曾劝说周小燕去美国生活,但周小燕很自然地想到“那学生怎么办?”她没有很重的传统老年颐养观念的束累,这20年来,就与一位保姆生活在复兴中路的旧家里,等待每天学生上门,被课程塞满。
舞台艺术是审美的综合,她在耄耋之年还跟学生探讨着发型和服装。李秀英对本刊记者回忆,1999年她去美国求发展,那是第一次出国远游,周小燕请她吃了顿牛排,为她讲西餐礼仪。这是李秀英第一次用刀叉吃牛排,两个食指都按酸了,老师就一个劲地笑。
一位朋友向本刊记者描述起1993年与周小燕的“一面之缘”。那时她与周的小外甥David是外企同事,约在了当时上海一个高档的商务会友之地——静安宾馆吃饭,当时周小燕也在。时隔20多年,她已经回忆不起来周那天说了什么,但始终记得她身穿灰白相间毛衣,戴一副极其细致精巧的眼镜,没有一丝白发,优雅从容、气若吐兰,坐在那边不说话也是焦点。
清音入杳冥
2005年,李秀英从纽约回国执教,周小燕在电话里笑得合不拢嘴,她说:“我真的很高兴你选择这条路。舞台上的辉煌是一个人一天晚上的事情,但是做老师是几代人的事情。”
而著名歌唱家黄英在2012年回国执教时,周小燕也一样激动地握住她的手。黄英在上海音乐学院求学时师从男中音葛朝祉,因为门第之别而一直不怎么敢去找周小燕。也就是在自己成名后,开始不断请教她,每次她开独唱会,周小燕总坐在下面,事后提些意见。2011年,上海交响乐团在上海夏季音乐节(Music in the Summer Air)期间邀请黄英担任演唱法国作曲家柏辽兹的六首声乐套曲《夏夜》,这是被公认难度极高的一套作品,有半小时之长,周小燕给她上了三节课。
“她在语言风格上给把了关后,演出很成功,连指挥家都认为我能够把法语演得如此到位。”她说。周小燕总是在关键时刻画龙点睛,在她成长的每个关键节点总有先生的身影。声乐看起来容易,但跟唱梨园戏一样,是“台上显贵,幕后受罪”的活计,它涉及的门类广,综合要求又高。“中国很缺周老师这样既当声乐主课老师,又当声乐教练(vocal coach)的人,不光讲声音,从零基础抓起,还讲风格、语言、作品色彩。”黄英告诉本刊记者。
所以,周小燕在行内是出了名的懂“因材施教”,李秀英说她纤细到“要抓每个学生的每根神经”,从生理构造到成长环境她都尝试去抓透,这样才能了解每个人适合唱怎样的作品。“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她的眼光精到,被她挖掘出的学生不看门第,只看是否真的适合唱歌,喜欢唱。“所以她带出来的学生基本上都在世界各地发光发热。”李秀英说。
50年代时我国教学只重女高音,注重示范演唱,结果出现了声音模式化的现象。此后,周小燕不断砥砺教学方式,提出了因材施教、明确训练规格,突出艺术个性相统一的教学主张。于是一大批不同声部、不同个性的美声演员从她手里诞生。他们中知名的有廖昌永、张建一、魏松、王莹、李秀英、高曼华……
1988年,周小燕在上海音乐学院内创办独立机构“周小燕歌剧艺术中心”,并亲自出任艺术总监。虽然没有任何演出活动经费,但她每周上课的日程排得很满。90年代开始,歌剧中心面向全社会招募专业人员,许多在地方上唱歌的年轻人为了受教于周先生而来一试。1989年,歌剧中心原班人马排演的首部威尔第的歌剧《弄臣》大获成功,当时在亚洲都很难有剧院将威尔第歌剧作品整本演出的。
2014年,周小燕完成了一个人生大愿,亲自挂帅将首部中国人自己的歌剧《一江春水》推上上海国际艺术节。如今,全国各地剧院都在尝试自创歌剧,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周小燕歌剧艺术中心的带动。
“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这句唐代钱起的诗用来形容她日夜探索声乐教学可谓妥帖。周小燕年轻的时候在欧洲各国巡唱,有记者问她为何总是穿着旗袍登台,而不是礼服,她说因为她总是被人问起是否是日本人,“一问到这个问题就烦,我说是中国人”。于是就索性次次穿旗袍。
她的关门弟子在她逝去后每次想起不能再见到她了,心里就会痛,但聊着聊着,发现都是快乐的事情。“那么多人在聊起她的时候都是快乐的事情。”李秀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