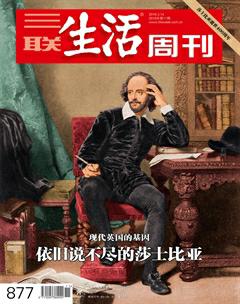英格兰的罪与罚:莎士比亚的“亨利亚特”
张沛

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演员们正在排演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六世》 (摄于2008年)
莎士比亚一生创作了十部英国历史剧,分别是:《亨利六世》上(1590)、《亨利六世》中(1590~1591)、《亨利六世》下(1592)、《理查三世》(1592~1593)、《理查二世》(1595~1596)、《约翰王》(1596)、《亨利四世》上(1596~1597)、《亨利四世》下(1598)、《亨利五世》(1598~1599)、《亨利八世》(1612~1613)。这十部戏剧分别以英国金雀花王朝、兰开斯特王朝、约克王朝和都铎王朝的七位君主命名,他们是:金雀花王朝的约翰王(1199~1216年在位)和理查二世(1377~1399年在位),兰开斯特王朝的亨利四世(1399~1413年在位)、亨利五世(1413~1422年在位)和亨利六世(1422~1461年在位),约克王朝的理查三世(1483~1485年在位)以及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1509~1547年在位)。
从《约翰王》到《亨利八世》,这是一部完整的“英国故事”。不过,这个故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几经修正才最后成形。
莎士比亚首先讲述了这个故事的后半部分,即有“第一四联剧”之称的《亨利六世》三部曲和《理查三世》,然后续写、追叙了它的前半部分,即《理查二世》、《约翰王》和“亨利三部曲”——亦称“亨利亚特”(Henriad),其名仿自荷马史诗《伊利亚特》(Iliad)——即《亨利四世》(上、下)与《亨利五世》;其中《理查二世》和“亨利三部曲”又称“第二四联剧”,它与“第一四联剧”共同演绎了第一版“英国故事”,这个故事以《理查二世》开端,以《理查三世》结束;与此同时,莎士比亚在《理查二世》和“亨利三部曲”之间插入写作了《约翰王》,后者为“英国故事”提供了新的开端和向度,从而引出一个新的“英国故事”,这个故事以“亨利三部曲”为核心,具有双重开端(《约翰王》-《理查二世》)和双重结尾(《亨利五世》-《理查三世》);英国改朝换代(1603)后,“都铎神话”成为前朝往事,于是莎士比亚又续写了《亨利八世》,作为他的“英国故事”的第三结尾和最后完成。至此,他的十部英国历史剧首尾环合为一部完整的英国史诗,这部史诗以英格兰国家为主人公,而讲述它的成长历程和最后胜利,即构成了戏剧诗人、政治哲人莎士比亚的“作者之意”。
在《亨利六世》三部曲中,莎士比亚的政治-历史哲学首次得到了表述。他以波利多尔(Polydore Vergil)、霍尔(Edward Hall)和霍林希德(Raphael Holinshed)等人的历史著作为蓝本,戏剧再现了从1422年11月7日亨利五世下葬到1471年约克家族取得仇克斯伯里(Tewkesbury)战役胜利并随后杀害亨利六世这一段历史。这三部戏具有统一的主题,即英国的堕落:由于亨利四世弑君自立,英国受到上天惩罚,亨利五世英年早逝,嗣君(亨利六世)暗弱,外畏于强敌(贞德-法国),内受制于权臣(温彻斯特大主教、约克公爵等),上下交征而战乱频仍(流民造反、玫瑰战争),最终弑君悲剧重演,国家命运危在旦夕……这几乎是基督教人类堕落故事的一个世俗历史版,只不过故事的主人公由人类(亚当-夏娃)变成了以国王为人格象征的英格兰民族国家。
如果说《亨利六世》讲述了英国的堕落,那么《理查三世》则讲述了英国的恶贯满盈和否极泰来。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三世作为恶魔(Vice)化身与善良无能的亨利六世形成了鲜明对照,并与后者同时构成理想君主的两极偏离。众所周知,伊丽莎白时代的历史写作深受意大利人文主义特别是马基雅维里政治哲学的影响,而通过《理查三世》,莎士比亚向世人演示了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失败。在马基雅维里看来,理想的君主须同时效法狐狸和狮子,兼集诈力于一身,此即人君之能事(Virtù),而他为达到目的完全可以不择手段,所谓“只要结果为善,行为总会得到宽宥”。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三世正是一名典型的马基雅维里式君主:他在剧中倒行逆施、无恶不作,以至于人神共愤、众叛亲离,最后死于亨利·都铎之手——确切说是上帝假后者之手诛灭了这个暴君。事实上,恶魔理查和天使亨利都是上帝的工具:前者作为上帝的工具促成了有罪的英国的恶贯满盈和死亡,后者作为上帝的工具实现了净罪后的英国的新生与蒙福。就此而言,他们合力实现了英国的拯救——净罪之后的拯救。而净罪和拯救(或者说恶贯满盈而否极泰来),正是第一四联剧的核心命意所在。
莎士比亚在第一四联剧中讲述了故事的后半部分,现在他进而讲述故事的前半部分,这就是第二四联剧。第二四联剧是第一四联剧的前传,而第一四联剧是第二四联剧的后续:如果说第一四联剧讲述了英国的恶贯满盈和否极泰来,第二四联剧则追叙了原初的堕落或罪孽的发生;两部四联剧共同讲述了一个完整的“英国故事”,罪与罚、堕落与拯救即构成了这个故事的意义结构和主题内涵。
在《理查二世》中,莎士比亚追溯了近代英国的原罪,即英国自波林勃洛克(兰开斯特公爵,后来的亨利四世)弑君篡位至理查三世败死博斯沃斯(Bosworth)这一段不幸历史(1399~1485)的起源。理查二世是英国王权的正统传人(确切说是英国中世纪王权正统的最后传人),即所谓合法君王(King de Jure),但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君王。与之相反,波林勃洛克是一个合格而不合法的君王。自信“天命在予”的理查二世失败了,他的死象征了英国中世纪的终结;假仁义行的波林勃洛克取得了胜利,但这胜利同时也是失败:由于弑君自立的罪行,亨利四世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国王,而只是一名成功的篡位者(King de Facto),他的成功为英国带来了罪孽,他本人固然未能幸免,而其后继者——从亨利五世到理查三世——也都延续和分享了这一罪孽。
有研究者指出,“兰开斯特四联剧”(即第二四联剧)旨在“描绘不同类型的王者并指出理想王者的特性”。事实上,莎士比亚在第一四联剧中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一系列不同的王者形象:软弱无能的国王(亨利六世)、有勇无谋的摄政(格洛斯特公爵)、阴险狡诈的王位挑战者(约克公爵)、小丑跳梁的草头王(杰克·凯德)、穷凶极恶的暴君(理查三世)……和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一样,他们都不是真正的王者。真正的王者迄今只是惊鸿一瞥(参见《理查三世》中的里士满伯爵、《约翰王》中的少年亚瑟以及《亨利八世》中的婴儿伊丽莎白)。
什么是真正的王者?古人和今人(前者以柏拉图为代表,后者以马基雅维里为代表)分别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而他们都寄希望于教育。这样问题的重心就从“什么”转向了“怎样”:怎样是真正的王者?莎士比亚的“亨利亚特”即是对这一问题的正面回答。三部曲的主人公是同一个人,他就是《亨利四世》中的哈尔王子和《亨利五世》中的亨利五世;但他们也不是同一个人:亨利五世是一名真正的王者,而哈尔王子只是一名预备王者。作为未来的王者,哈里一开始不被任何人看好:他的父亲为他忧心自责,而他的敌人(包括他的狐朋狗友)却因此欢欣鼓舞。但是他们都看错了:王子混迹无赖(如其自承)只是为了韬光养晦,以便将来一鸣惊人。他没有说谎(尽管他欺骗了周围所有的人):通过与福斯塔夫等人的交往,哈里了解并克服了自身的恶或阴影人格(以他战胜同名对手霍茨波、弃绝旧时腻友福斯塔夫为标志)——这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救赎的过程——而成为真正的自己、真正的人和真正的王者。随着王者归来,莎士比亚的政治理想终于修成正果而道成肉身。
归来的王者——亨利五世攘外安内,以数年之功完成了前无古人(包括爱德华三世父子在内)的事业,被国人誉为“所有基督教君主的楷模”。然而他并没有真正拯救英格兰:即如剧终时分致辞人(Chorus)所说,这位“英格兰之星”依仗“机运之剑”斩获了“世上最美的花园”,但是好景不长,一代雄主英年早逝,继位者年幼,英国在短暂中兴之后重新陷入了更加严重的内忧外患(如《亨利六世》三部曲所示)。就此而言,亨利五世实在是一名失败的王者。
在“亨利亚特”的华彩乐章《亨利五世》中,莎士比亚向我们揭示了这位伟大王者的根本困境(Aporia)。反讽的转折-启示发生于高潮即将到来之前的第四幕第一场。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从浪子到“基督教君王的典范”,天才的政治家亨利让他的观众等了14年(1399~1413);而为了展示这一过程,天才的戏剧家莎士比亚让他的观众等待了三年时间(1596~1599)——亨利五世终于来至法国的阿金库尔(Agincourt)荒原。现在已是凌晨(确切说是1415年12月25日凌晨),几小时后,决定双方命运的战役即将打响。这时亨利突然屏退左右,独自微服出巡。临行前他特意吩咐手下:“我要和自己的内心争辩一番,在此期间我不希望身边有人。”说毕,“英格兰之星”隐入了暗夜。
王者亨利开始了漫游。事实上,这已经是他生命中的第二次漫游。他的第一次漫游是在他父亲亨利四世的统治时期(1399~1413)。这是一次灵魂的漫游,确切说是王者的灵魂在尘世的漫游;在此期间,他从叛逆堕落的少年王子成长为雄才大略的青年君主。在现在这场漫游中,隐身的王者或者说“内自讼”的王者之心与他“外在的良心”不期而遇了。这是三名普通的士兵:约翰·贝茨(John Bates)、亚历山大·科特(Alexander Court)和迈克尔·威廉斯(Michael Williams),他们的名字很是耐人寻味:“John”源于古希伯来语,意为“上帝的仁慈”;“Bates”为盎格鲁-撒克逊姓氏,源自人名“Bartholomew”;“Alexander”源自古希腊人名“Alexandros”,意为“人类的保护者”;“Court”是盎格鲁-撒克逊姓氏,源于“王庭”(Court)一词;“Michael”本是古希伯来男子名,意为“(谁)像上帝”;“Williams”是威尔士姓氏,源自日耳曼人名“Willihelm/Willelm”,意为“威廉之子”,1066年诺曼征服后一度成为英国最常见的人名(如莎士比亚即名“威廉”)。作者这样命名,似乎寓有深意:莫非,“迈克尔·威廉斯”——“谁像上帝·威廉之子”——即是作者威廉·莎士比亚在剧中的代言化身?
现在这三人正在谈论即将发生的战争。科特首先发问:“约翰·贝茨兄弟,那边天是不是已经亮了?”贝茨没好气地回答说:“我想是吧;不过我们可没有重大理由盼望天亮哟。”威廉斯更是对“明天”感到悲观:“我们看到了天亮,可是永远看不到这一天的结束了。”正说话间,他们发现了亨利,喝问他是何人。亨利自称是托马斯爵士的部下,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亚历山大·科特(如前所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国王-宫廷”)始终保持沉默:他的位置被隐身/伪装的王者亨利取代了。威廉斯首先向来者发问:“托马斯爵士怎么看大家现在的处境?”亨利回答说:“就像一个人沉船搁浅,等待下次来潮水把他冲走。”贝茨接着又问:“他没有把他的想法告诉国王吧?”一言触动心事,亨利借机抒发胸臆,声称“国王也不过是人,和我一样”,面对危险,他同样会感到恐惧,只是不能流露在外,以免动摇军心云云。对于他的说法,贝茨嗤之以鼻:“他尽可以表现他的勇敢;不过我相信,就在今夜这样的冷天,他宁肯在泰晤士河里,哪怕水淹到脖子;但愿他在那儿,我也在旁边,不管有多危险,只要我们能离开这里。”亨利正色道:“说真的,我要为国王的良心说句话:我想他现在除了这个地方,哪里也不想去。”贝茨随即接言:“那么我希望他一个人在这里;这样他可以赎身保命,而许多可怜人也就免得送死了。”

英国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阿金库尔战役600周年纪念活动,来自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演员萨姆·马克斯在活动中扮演亨利五世 (摄于2015年)

电影《理查三世》剧照 (摄于1995年)
现在谈话变成了争论:士兵——亨利口中的“兄弟、朋友和同胞”(第四幕致辞人语)——或者说民众与国王的争论,甚至是民众对国王的审判。王者以民众之心为心,因此民众的审判也就是王者之心的“内自讼”。面对良心(自我意识)的审判,亨利将如何为自己辩护呢?亨利决定用“爱”和“正义”的修辞为自己辩护。他反问贝茨:“我敢说你不会那么不爱他,竟希望他一个人在这里吧?”并以自己为例——当然,是作为“非我”的无名战士而不是他本人——现身(其实是“隐身”)说法:“我觉得无论死在哪里,只要和国王在一起,我就心满意足了:他的事业是正义的,他的战斗是光荣的。”对于这番说辞,大家反应冷淡。威廉斯的回答就一句话:“那我们就不知道了。”贝茨也随声附和:“是啊,这些我们也管不了;我们只要明白自己归国王管就行啦。就算他的事业不正义,我们效忠国王,也就免去罪责啦。”——“但是”,威廉斯马上又接过话头,“如果不是正义的事业,那国王本人可就欠下一大笔债了”,因为“打仗死的人恐怕没有几个是好死的”,他们服从王命而不得好死,这样“把他们领向死路的国王就有罪了”。
国王有罪:这真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指控!隐身的王者亨利,或者说他隐匿的良心,一下子被击中了。和父亲一样,亨利五世试图通过军事征服证明自身统治-王权的合法性;但是不同于父亲,他的目标并非宗教圣地耶路撒冷,而是世俗的法兰西——“世界上最美的花园”(第二幕致辞人语)。这是一场非此即彼的冒险:它是否正义,直接取决于它是否成功,所谓“结果证明手段”。然而,战争本身即是罪孽,而罪孽无法通过罪孽洗白。亨利宣称“他的事业是正义的,他的战斗是光荣的”,这不过是他的政治修辞或者说宣传罢了。现在,威廉斯和他的战友——亨利的“兄弟、朋友和同胞”一致认定“国王有罪”,这让亨利情何以堪,又将何言以对呢?
如前所说,“亨利问题”的根本症结在于良心-正统王权的败坏-失落。亨利本人对此有充分的自觉,也曾试图通过漫游(出走)逃避罪责与良心的责难;但是现在他已无路可走,只能铤而走险,以生命作注,与命运豪赌一场。
天将拂晓,他要回去-离开了。在回归(同时也是背弃)自我之前,亨利跪倒在茫茫夜色下的荒原之上,狂热地祈祷上帝。在他最后的祈祷中,亨利坦露了内心深处的隐秘欲望(或者说恐惧)。首先,他祈求作为“万军之主”的上帝(God of Battles)让他的战士无知无畏而奋勇杀敌。亨利深知他必须赢得这场战争,这将是他最后的救赎希望;为了赢得战争,他必须让自己的战士相信“他的事业是正义的,他的战斗是光荣的”;而为了让他们相信这一点,就必须欺骗他们。可是事与愿违:就在刚才,他的士兵向他质疑这场战争的合法性,认为国王的说辞并不可信,甚至直言国王有罪。亨利的良心被彻底击中了。此时他再也无法伪装和隐藏,只能裸身——作为王者,也作为罪人——求告上帝。他自知罪无可逭,但他辩解说这是“父亲的过错”,而他已为此忏悔谢罪,并许诺将来会做更多善功“以求宽恕”。亨利所谓的“将来”,是指战争胜利之后,这意味着上帝必须宽恕而且赞助他的罪行。亨利声称“上帝掌管一切”,但他内心希望(甚至认为)上帝可以收买;就此而言,他的上帝无非是功利主义的“经济人”上帝(Deus Economicus),而他的忏悔和许诺不过是试探和谈判的筹码罢了。这是绝望的交易,也是最后的赌博:他或是失去一切而拯救自己的良心和灵魂,或是战胜这个世界而良心-灵魂永远沉沦。在前一种情况下,上帝拒绝他的请求而接受他本人;在后一种情况下,上帝接受他的请求而拒绝他本人。无论如何,必须做出选择,而选择的权利和责任皆归上帝。
上帝做出了选择:亨利赢得了战争(同时也是赌赛)的胜利。他将这一胜利完全归功于上帝。这并不是高贵的自我谦抑,而是别有深意的责任转嫁:归功同时就是委过,亨利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自己与上帝同在,确切说是让上帝成为自己的同谋。在世人看来,他获得了成功,而且是空前伟大的成功;但是亨利自己心里明白,这一成功意味着什么。世俗的成功暂时延缓了上帝的惩罚,但它并没有消除反而加重了罪行。不妨说,成功就是罪恶(或者说罪恶的重演),同时也是罪恶满盈的判决。亨利为自己的成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将和他的前辈该隐(《旧约·创世记》第四章第8~12节、16~17节)一样,在心灵的暗夜中,在生命的荒原上,绝望无助地流浪,直到永远。
这,或许就是都铎英格兰国家-国王神话的作者莎士比亚在当下书写的(因此也是正在发生的)历史中秘密嘱咐未来的大义微言。正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