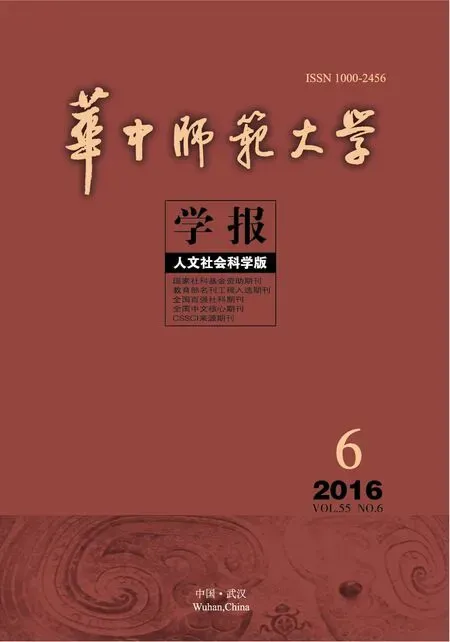一只踩着赤色火焰的火烈鸟
——论唐祈的诗
吴思敬
(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北京 100048)
一只踩着赤色火焰的火烈鸟
——论唐祈的诗
吴思敬
(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北京 100048)
诗人唐祈,其诗歌创作贯穿一生,除去因政治因素被迫中断的二十余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期(1936年至1949年)的唐祈,由青春写作起步,直面洪波涌动的社会现实,自动衔接现代主义诗潮,成为“中国新诗派”的重要成员和1940年代知性写作的主要代表。中期(1950年至1960年)的唐祈,在屈辱的日子里昂起高傲的头颅,以一个殉难者的眼光审视周围的一切,其在流放的岁月里所写的“北大荒短笛”,给读者强烈的情绪冲击并引起读者对那一悲剧年代的反思,从而自身也就具有了“诗史”的品格。晚期(1980年代)的唐祈,怀着对少数民族兄弟的大爱,回到西北,其诗作力图把感觉与经验沟通起来,把今天与过去沟通起来,流贯着一种历史的纵深感,渗透着他的情思与意志,成为其内心世界的象征。但唐祈此时期未能摆脱以往的抒情腔调,忽视艺术语言的更新,对于他企图重构少数民族诗学的宏大理想而言,未免留下了遗憾。
唐祈; 诗歌; 中国新诗; 知性写作
我们都是火烈鸟
终生踩着赤色的火焰
穿过地狱,烧断了天桥
没有发出失去身份的呻吟
这是诗人郑敏1990年得知唐祈突然逝世后,写下的组诗《诗人与死》中的几行。这组诗是为唐祈而写,涉及生命、死亡、诗人的天职、知识分子的命运等丰富内涵,为我们提供了考察唐祈生平及其创作的一个视角。在我看来,唐祈正像郑敏所描述的,是一只踩着赤色火焰的火烈鸟,是一位燃烧自我,用生命写诗的诗人。
1987年的冬天,唐祈在编完了《唐祈诗选》之后,在“后记”中说了这样一段话:“这里,这个雪夜的三层楼上,屋里正好没有旁人,我在孤独中也总感到:我的头顶上没有遮盖的屋顶,雪花飘落在我的眼睛里,我行走在诗的旷野上。但我却总要写,要不停地探索,一生也不放下这支笔,正如里尔克所说的,这将是一个归宿。”①在唐祈看来,只有诗才给了他生命,给了他信念,给了他永不衰竭的青春的力量。他的一生都行走在诗的旷野上,并最终在诗中寻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一
唐祈,是一位儒雅的、才华横溢的诗人。他生于苏州,一生到处漂泊,大半辈子生活在北方。他的诗歌创作贯穿一生,除去因政治因素被迫中断的二十余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36年至1949年为前期;1950年至1960年为中期;1981年至1989年为晚期。
前期的唐祈,由青春写作起步,直面洪波涌动的社会现实,自动衔接现代主义诗潮,成为“中国新诗派”的重要成员和1940年代知性写作的主要代表。
唐祈是位早慧的诗人,早在16岁出头,他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就写出了处女作《在森林中》:
我漫步,/在森林中,/听,岁月里,/悠悠的风。
我听到了/远处的山上的钟,/像永久的歌声/上升到天空。
谁的一个声音,/在森林中,/谁的一个声音,/又在森林中。
远处的风;/山上的钟;/我将向哪里走,/在森林中。
这是一位早熟少年面对生活的思索,对未来既向往又感到深不可测,透过略带神秘色彩的森林和“悠悠的风”、“远山上的钟”等意象,显出了忧郁、沉思的气质。这首小诗受到了他的同学、诗友文健的鼓励,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走上了诗歌创作的道路。
大学时期,是唐祈诗歌写作旺盛的时代,也是他的诗歌观念开始形成的时代。他所就读的西北联大,环境虽然艰苦,但许多教授来自北大、师大,保持了浓厚的学术氛围和民主气息。他说:“我能在那里广泛地涉猎知识,在图书馆里像河马一样吞食各种各样的书。更多的是在夜晚自己悄悄地写诗。我很喜欢法国象征主义和德国浪漫美学,从叔本华、尼采……到波特莱尔、里尔克,使我把诗不仅看作一种艺术现象,而且感悟到它是在不断寻求人生的诗化。这对于自己日后写诗留下了浓重的影响。”②在大学四年中,每年寒暑假他都经过陕西的黄土地,翻过荒凉的六盘山,在甘肃、青海一带漫游,搜集民歌、牧歌,接触到蒙古族、藏族、回族、维吾尔族等兄弟民族,从他们真诚、纯朴、粗犷的性格中受到深深的感染。这不仅使他终生保持了对少数民族的热爱,写出了特色独具的少数民族题材的诗篇,而且使他从诗歌创作的起步就保持了对现实的关注,对底层的关怀,而没有遁入唯美的象牙之塔。
1945年至1948年,唐祈先是在重庆,后是在上海度过。这时的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矛盾尖锐,人民承受着深重的苦难,光明与黑暗进行着殊死的搏斗。唐祈投入了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斗争的行列,并在斗争中写下了呼唤民主、鞭挞黑暗的诗篇。他就像声声啼血的布谷鸟,诉说人民的苦难,表达对自由、民主的渴望。难得的是,这些诗篇不仅体现了唐祈思想上的成熟与进步,也鲜明地显示了唐祈在诗歌创作上的探索与追求。
唐祈早年的人生经验和大学时对国内外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诗歌的广泛涉猎,使他从内心深处对何其芳、卞之琳等创作的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诗歌产生了共鸣。然而1940年代他所经历的社会现实,使他不太可能去追求带有虚幻的理想主义色彩的“纯诗”,而是以一个诗人的真诚与勇气,直面社会现实,反思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自我与世界之间、传统与外来影响之间、社会使命与个体审美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平衡,在诗作中展示了群体的社会心态和诗人的紧张感与焦虑感,从而使他的诗歌呈现了不同于此前中国的现代派诗人的新面貌,成为1940年代中国诗坛知性写作的一位出色代表。
知性,原本是德国古典哲学术语。康德认为,认识能力共有三个层次,从感性开始,然后是知性,最后是理性。知性是介于感性与理性之间的一种认识能力,具体说来指的是主体对感性对象进行思维,把特殊的没有联系的感性对象加以综合处理,并且联结成为有规律的科学知识的一种先天的认识能力。在认识的感性阶段,实现的是外部世界的信息由物理到生理的转化,主要依赖诗人的生理机制和本能。在认识的知性阶段,则实现由生理到心理的转化,即主体把新输入的信息与以前贮存的信息联系起来,这就不单纯是感觉信息的复合,而是在主体经验世界作用下的一种建构了。在这一过程中,主体所知觉的已不再是自然状态下的那一事物,而是融有主体心理因素在内的关于那一事物的映象。这中间会有选择、有过滤、有强调、有变形,这就会更多地依赖诗人已有的生活经验、艺术素养和艺术个性。
西方现代诗歌的知性写作则代表了现代诗人追求感情与理智相统一的趋向。知性理论源于英国诗人柯尔律治,经英国文论家瑞恰慈、诗人艾略特等加以发展,其在中国的传播,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瑞恰慈来清华大学讲学。此后,英国文论家燕卜荪先后在燕京大学、西南联大执教,美籍英国诗人奥登也于1940年代到西南联大讲学。这都直接促成了“中国新诗”派诗人对知性理论的理解与对知性写作的热衷。“九叶”诗人唐湜在1975年所写的长诗《遐思:诗与美——献给远方的友人》中曾这样描述“九叶”诗人所受到的西方现代诗歌的影响:“你们也喜爱那罪恶的花铃,/波特莱尔,从巴黎泥淖中崛起;/又马拉美,勾描午后的牧神,/为林泽的仙子们吹爱的芦笛;/你们,爱乘着兰波的‘醉舟’,/由风暴的祝福在大海上复苏;/更爱上阿波里奈尔的温柔,/看朵朵火焰在跳着孔雀舞;/可你们更倾心里尔克的虔诚,/神往于军旗手的英勇突进;/那奏出四个四重奏的歌人,/可描尽了欧罗巴文明的凋零;/梵乐希,你们也向他倾听,/向水仙倾听着希望的歌吟”
正是基于西方现代诗人的“知性理论”及其诗歌写作,1940年代后期,袁可嘉曾对当时的中国诗坛有过这样的批评:“在目前我们所读到的多数诗作,大致不出二大类型:一类是说明自己强烈的意志或信仰,希望通过诗篇有效地影响别人的意志或信仰的。另一类是表现自己某一种狂热的感情,同样希望通过诗作来感染别人的”。然而由于把材料化为成品的过程的欠缺,“说明意志的最后都成为说教的(Didactic),表现情感的则沦为感伤的(Sentimental),二者都只是自我描写,都不足以说服读者或感动他人。”③那么,如何使意志与情感转化为诗的经验?袁可嘉提出的办法是新诗戏剧化,即设法使意志与情感都得到戏剧的表现,而闪避说教或感伤的恶劣倾向。与此同时,唐湜高度评价经验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认为拜伦的“诗就是情感”的说法早已过去,他强调诗人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同时这些经验又需要深入到潜意识领域中去发酵。他还提出:“真正的诗,却应该由浮动的音乐走向凝定的建筑,由光芒焕发的浪漫主义走向坚定凝重的古典主义。这是一切的沉挚的诗人的道路,是R.M.里尔克的道路,也是冯至的道路”。④
袁可嘉和唐湜的理论主张,代表了包括唐祈在内的“中国新诗派”诗人的知性写作的共同追求。
唐祈这一时期的创作,深受艾略特的影响。艾略特的代表作《四个四重奏》,完全是围绕着时间的主题而展开的,借用个人经验、历史事件、宗教传说,表现出对过去时间、现在时间、将来时间的复杂关系的思考:“时间的现在和时间过去/也许都存在于时间将来/而时间将来包容于时间过去”。这表明时间是互相渗透的,每一个瞬间都有着多种内涵。受艾略特的启发,唐祈意识到对任何事物的理解都离不开时间,对任何经验的处理都要在时间的框架中进行,时间成了他引发诗情的触媒。唐祈在1940年代后期的诗作,有些便是直接以时间为题的,如《严肃的时辰》《最末的时辰》《时间的焦虑》《时间与旗》等。
我看见:/许多男人,/深夜里低声哭泣。
许多温驯的/女人,突然/变成疯狂。
早晨,阴暗的/垃圾堆旁,/我将饿狗赶开,/拾起新生的婴孩。
沉思里:/他们向我走来。
(《严肃的时辰》)
深夜哭泣的男人,变成疯狂的女人,拾起弃婴的诗人,三个镜头叠加在一起,指向一个共同的“严肃的时辰”,时间现在被赋予了深刻的内涵,它融入了过去发生的苦难,也暗示了即将到来的巨变。意象的呈现与时间的切割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诗人的情感与判断不言自明。
唐祈更多的诗作尽管题目上没有点明时间,却同样充满了一种对时间的焦虑,如《雪夜森林》:
恐怖的白森林呀/一条条丧布飞舞/我的红鬃马疾驰前去/抵抗着风的呼呼/什么时辰了,乳母?
严寒占领着的/森林上面/天空结冰了吧/冻死了/一切温和发光的星/附近的人民呵/怎能长久在/寒冷里睡眠?
乳母呵,我却看见/你微笑,催我向前/这深深雪夜的/一只知更鸟/将报告人民以太阳的时间
这首诗完全在想象中展开,狂风肆虐、白雪覆盖的森林暗示了生存环境的恶劣,乳母代表着人世间的温暖与爱,诗人骑着马疾驰体现了对真理、对光明的追求。诗中有两处时间的表述,前一处在恐怖的白雪覆盖的森林中的提问:“什么时辰了,乳母?”指的是时间现在;而结尾处,诗人在想象中看到乳母在微笑中催他向前,而他似乎也听到知更鸟“将报告人民以太阳的时间”,这则是时间将来了。在时间的推进中,诗人把哲理的思考融入象征的图景当中,真正做到了像艾略特所主张的,像“感觉玫瑰花”一样感觉思想。
而把对时间的思考与诗情的燃烧完满地融合在一起,繁富而又浑然天成的,当推这阶段最有分量的代表作《时间与旗》。关于这首诗的写作,唐祈回忆道:“1947年,诗人陈敬容和曹辛之在上海为了探索中国新诗的发展,约我去上海,后来又约了老诗人辛笛、唐湜,我们创办了《中国新诗》诗刊……我在这段时期,因为身上还带着重庆斗争的火焰,又投身到这个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都会——上海,这里,是一片贪婪与歹毒的饕餮的海洋,也是一个透视旧中国社会更大的窗口,我找到了自己新的视角,我几乎只熬了两个通宵,写下了长诗《时间与旗》”。⑤唐祈找到的这个新的视角是什么呢?据唐湜回忆:“1948年6月,我在上海致远中学唐祈的房里,曾见到他一边把艾略特的诗竖着放在面前,一边在下笔写这首诗”。⑥这明确地指出了唐祈的《时间与旗》的写作是在艾略特的影响下进行的。艾略特《四个四重奏》中有这样的诗句:“钟声响亮/计着不是我们的时间的时间……”。钟声,中国寺庙的钟声也好,西方教堂的钟声也好,江海关大楼的钟声也好,不只标志着时间的计量,更是把无声、无形的时间之流转化为诉诸人的听觉的一种手段,也是把时间诗化的一种手段。《时间与旗》开头便紧紧抓住了这动人心魄的钟声:
你听见钟声吗?/光线中震荡的,黑暗中震荡的,时常萦回在/这个空间前前后后/它把白日带走,黑夜带走……
人在时间中生活,历史在时间中形成。时间永远朝着一个方向,按过去、现在、将来的顺序而一去不返,已经过去的时间不会复现,尚未到来的时间也不会突然蹦到眼前。然而艾略特打破了对时间的惯有观念,在他的诗歌里,时间过去、时间现在、时间未来的顺序可以打破,可以颠倒,可以并置,可以交织,从而充分揭示现代社会快速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运动,以及在这种运动中人的心灵或剧烈或微妙的变化。细味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能感到诗人对时间的空幻感,这种空幻感又进一步触发了他内心深处的宗教观念。
唐祈从艾略特诗中所借鉴的主要是艾略特对单纯的时序交替的时间观的打破,至于他们各自独立构筑的时间框架,以及在时间框架中展开的背景、意象、诗情与思维,却是截然不同的。
如唐祈所言,他是把上海当作透视旧中国社会一个大窗口来看待的,其间沉淀着他对中国社会现状的长期观察、判断与思考,而这种观察、判断与思考并不是以直白的、概念化、政治化的话语来传达的,而是用间接的、形象的、隐喻的意象来表现的。《时间与旗》所呈现的意象世界,就像上海这座喧哗、浮躁的大城一样,枝蔓纠缠,繁富错综,尽管如此,经过仔细考察,可以发现它的意象还是可以粗分为两大系列的。
一个系列是地火系列:
无穷的忍耐是火焰——在那工厂的层层铁丝网后面/在提篮桥监狱阴暗的铁窗边/在覆盖着严霜的贫民窟/在押送农民当壮丁的乌篷船里面/在贩卖少女的荐头店竹椅旁/在苏州河边饿死者无光的瞳孔里/在街头任何一个阴影笼罩的角落/饥饿、反抗的怒火烤炙着太多的你和我,/人们在冰块与火焰中沉默地等待/啊,取火的人在黑暗中已经走来……
一个系列是高岗系列:
冷清的下旬日,我走近/淡黄金色落日的上海高岗,一片眩眼的/资本家和机器占有的地方,/墨晶玉似的大理石,磨光的岩石的建筑物/……施高塔路附近英国教堂的夜晚/最有说教能力的古式灯光,/一个月亮和霓虹灯混合着的/虚华下面,白昼的天空不见了,/高速度的电车匆忙地奔驰,/到底,虚伪的浮夸使人们集中注意/财产与名誉,墓园中发光的/名字,红罂粟似的丰彩,多姿的/花根被深植于通阴沟的下水道/伸出黑色的手,运动、支持、通过上层/种种关系,挥霍着一切贪污的政治……
全诗就在这地火系列与高岗系列的意象对比中展开,而不加更多评论。诗人之所以采取这种手法,是由于生活中的任何事物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正如法国诗人雨果所说:“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⑦这两个系列的意象,孤立地看,也许有些单调,但是经过并置使读者触发的对比联想,则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地火系列与高岗系列意象的多层次地交叉与并置,使读者的情绪不断垒积,当临近顶点的时候,诗人精心营造的中心意象——旗,出现了:
斗争将改变一切意义,/未来发展于这个巨大的过程里,残酷的/却又是仁慈的时间,完成于一面/人民底旗——/……过去的时间留在这里,这里/不完全是过去,现在也在内膨胀/又常是将来;包容了一致的/方向,一个巨大的历史形象完成于这面光辉的/人民底旗,炫耀的太阳光那样闪熠,/映照在我们空间前前后后/从这里到那里。
如果说地火系列与高岗系列的层层推进是画龙,这“人民底旗”就是点睛。这里有中国传统诗歌卒章显志的味道,但又不完全是,古诗的卒章显志是在结尾把诗人的主张明确说出来,而《时间与旗》最终出现的“旗”依然是个象征,它的含义是什么,读者尽可以自由想象、自由言说,但诗人的表述却戛然而止,留不尽之意于言外。这也正是知性写作区别于一般言情体与论辩体诗作的地方。随着知性写作逐步为诗界所认识所推崇,唐祈的《时间与旗》也日渐显示其魅力与价值。唐湜说过:“唐祈,把时间的旗/直插上了上海巨伟的大厦”(《遐思:诗与美——献给远方的友人》)。在新诗诞生百年之际,由三联书店出版,由洪子诚、奚密等编选的《百年新诗选·上·时间和旗》,其书名就正是取自于唐祈的名篇《时间与旗》,可见唐祈此诗内涵之丰富与影响之深远。
二
中期的唐祈,其写作时间可界定为1950年至196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唐祈到了北京,先后在《人民文学》和《诗刊》做编辑,直到1957年“反右”的到来。在这期间,唐祈极少写诗。只在1956年,因英法侵略埃及,《人民文学》临时缺少诗稿,才发表了三首《献给埃及的诗》;另外还在《诗刊》上发表了《水库三章》,在《教师报》上发表了两首写给教师的诗:《三月的夜晚》和《苏联专家阿芙朵霞》。七八年的时间才写了几首诗,工作繁忙还在其次,更主要的是唐祈遇到了与辛笛等“中国新诗派”诗人共同面临的原有创作思想与新时代不相协调的问题。1949年7月,辛笛到北京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辛笛请朋友们给他题词。靳以的题词是:“‘不惜歌者苦,但恨知音稀’,这是一句老话,如果为人民而歌或是歌颂人民,那么知音就有千千万万了!”苏金伞的题词是:“过去我们善于歌唱自己,/今后必须善于歌唱人民。/但这种转变并不是容易的,/首先得离开自己,/真正走到人民大众中去。”吴组缃的题词是:“跳出个人主义的小圈子,把感情和思想与人民紧紧结合,以充满乐观的精神,歌颂新中国新世界的诞生和成长。”仅从这些老朋友之间的私人题词,就足以感受到当时的政治气氛,这些作家与诗人已深深地体会到,不能再按照以前的写作路数写下去了。回到上海后,辛笛曾按照新的要求,试写了一首《保卫和平,保卫文化》,但写出来后,自己左看右看不像诗,而像标语口号,就此搁笔。辛笛决定远离文学圈,转入上海市工业部门工作,从而逃过了1957年的劫难。而唐祈尽管也感到写不下去,但缺乏辛笛的眼光与果断,没有跳出文艺口,终于被大风大浪卷了进去,被打成右派,成为阶级斗争的牺牲品。
1958年,唐祈被发配到了北大荒。险恶的政治风浪,残酷的生活环境,多少人把性命留在了那里,而唐祈侥幸活了下来。不仅如此,他还在那里留下了诗篇。他说:“令我感到惊奇的是,尽管险恶的政治风浪把我拋得很远,几乎连生命都将埋葬在那片荒原上,但就在那冰雪覆盖的茅草顶的泥屋里,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我竟没有放下这支写诗的笔,也从来没有动摇过我对诗的信念。我默默写下了《北大荒短笛》系列组诗”⑧在那个时候,诗人成了政治上的贱民,繁重的劳动,窘困的生活,没完没了的检查……他只有私下里拿起诗笔的时候,才能坦诚地面对真实的自我,才能在屈辱的日子里暗中昂起那高傲的头颅,以一个殉难者的眼光审视周围的一切。他的这些诗篇属于“潜在写作”,在当时环境下,保存不易,多有散失,直到新时期到来,才有了重见天日的机会。
唐祈把1958年至1960年写于北大荒的这些诗作命名为《北大荒短笛》,是颇有些反讽味道的。在中国当代诗歌中,“短笛”多是田园的、浪漫的、欢快的歌唱;而唐祈的“北大荒短笛”却是沉重的、悲怆的、痛彻心扉的控诉,透过北大荒的自然景观和劳改场景,逼真地写出了受难者的心灵之旅。
初到北大荒,唐祈便写下了《黎明》一诗,记下了在一个大风雪的夜晚,诗人与一批受难者乘火车被押运到北大荒的情景:
黎明,我们将乘火车到达/死寂的囚车里锁住了喧哗/只有车轮声惶恐不安地响着喀嚓喀嚓/从暗夜的玻璃窗上一瞥/旷野仿佛飘落着黑色的雪花
“黑色的雪花”,真是个奇特而又触目惊心的意象!雪花都是白的,哪里有“黑色的雪花”?原来,火车在夜色中行驶,窗外大片的雪花飞落,一片白色,黑暗的夜色反成了星星点点,乍一看便疑为黑色的雪花了,这里确有写实的成分;然而“黑色的雪花”又不只是疾驶列车的窗外所见,更是诗人心绪的写照。诗人因言获罪,被发配到北大荒劳改,此一去前途渺茫,吉凶莫测:“等待着这些人的命运是/原始森林中的苦役/斧锯将锯断生命的年轮/土地上无尽的耕耘呵/犁头会碾碎发亮的青春”。因极度压抑的心情,白色的雪花在诗人眼中变成黑色也就很自然了。一长串的劳改队伍,向荒无人烟的雪原行进,沉重的苦役开始了。诗人虽蒙受沉重的压力,却没有绝望:“黎明的青色的光/洁白的雪/将为这些人作证/虽然痛苦很深、很深呵/却没有叹息、呻吟”。正是这种正视苦难,顽强图存的生活态度,才使他能够在苦难的日子里与诗相伴。
北大荒,虽是受难者流放的所在,却不是一片死寂的不毛之地。这里是祖国的北疆,广袤的黑土地是肥沃的,是充满生机的。在这里,每一片自然景色,每一种物态的变化,都能勾起诗人带有忧思的遐想。
在中午的阳光下,目睹北大荒无边的黑土地,诗人发出深沉的感慨:“呵,土地,你是母亲/你宽阔的胸怀总给人以希望、慰藉/给人类捧出粮食、浆果、金黄的麦粒……”诗人把自己看成大地之子,对大地怀有由衷的热爱,即使以“戴罪之身”流放在祖国的土地上,他“也愿以无罪的血滴/化成你春天溶溶的浆液”(《土地》)。
看到一只水鸟从湖面上飞起,诗人的思绪也随之飞翔起来,他在水鸟身上寄托了对自由的渴望:
水鸟从湖面起飞/带着自由的愿望/为了作愉快的旅行而飞翔/它的头向前伸/洁白的翅膀抖落霞光/在云彩中消失了飞掠的形象
水鸟可以自由飞翔,诗人却被禁锢在绿色的草原上:“水鸟知道我在这里凝望/我脚下的草场、柞树林、哨岗/这绿色的监狱呵,禁锢着人的思想”(《水鸟》)。然而诗人对此发出了质疑:
思想,难道是监禁得住的吗?/如今希望并不全写在水上/灰暗的云层终究挡不住太阳
“如今希望并不全写在水上”一句,暗用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典故。济慈逝世前曾自撰墓志铭:“这里安息着一个把名字写在水上的人”,意思是说,诗人的名声是写在水上的,随着时间像水一样流逝,诗人的名声也就自然消失了。这里表示长期受病痛折磨的济慈在去世前的悲观,他不相信自己的作品会流传下去。唐祈接过济慈的话,把“名字”改为“希望”,是说“希望”不会像流水一样消失,一切苦难的日子终将过去,光明的未来将会到来。
除去这种受自然意象而触发的写作外,“北大荒短笛”中,还有一些是透过对北大荒独特的生活场景的描写,抒发诗人的心志。
《坟场》是对北大荒劳改中屈死的、饿死的、累死的冤魂的缅怀与礼赞。诗人用素描的手法写了坟场的凄凉:荒凉的月亮岗,一片乱坟场,一个个木牌在土堆前默立,以致赶车的姑娘不忍观看,割草的孩子不忍惊扰。然而,“风雨留下一行墨水的泪渍/早霞拂去名字上的浓霜/太阳出来依然闪闪发光”,诗人悲愤地呼喊:“他们头颅里燃烧理想/周身还都是火焰/却在黑土里埋葬”!唐祈之所以有勇气这样写,是由于他知道:“我的诗里虽然有痛苦,却没有悲观绝望的音调。因为我从祖国的大地上,接触到广大的人民,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我懂得人民是文艺的母亲这个最简单的真理,不论何时何地,我都要亲近他们,把自己的心和声音交给他们”。⑨
在《短笛——位青年画家的“检讨书”》一诗中,唐祈写了一支特殊的短笛。那是一位青年画家先用一柄废弃的镰刀磨成小刻刀,再用一个老犯人临死用过的竹棍,削成的一支短笛,尽管笛管粗糙,却能吹奏出黄土高原上的民谣。在诗中这位青年画家身上,无疑地融入了唐祈的自我形象。画家的竹笛和刻刀,与他的“潜在写作”一样,是与阴沉、严酷的政治环境相对抗的一种手段。他透过青年画家的口,严正地宣告:“我的这些雕像、竹笛和刻刀/即使犯了天条,我一件也不上交”。这表明,尽管压力重重,诗人却为自己筑了一道心理的防线,他要保持内心的自由,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坚持独立人格,矢志不改初衷。
《永不消逝的歌》是“北大荒短笛”中最有分量的一篇抒情之作,可视为诗人的精神自传,他在世界面前敞开了自己的心扉:
我的青春像柔韧的/軏拉草,将枯死在荒原上。在疯狂的火焰中,/我从来没有回避,/黑色的政治风暴对准我/致命的诬陷和打击,/它想让我的鼻孔虽然在呼吸,/心却要躺在坟墓里。
但我相信:/未来的结论。/我和同伴们白雪上的脚印,/每个时辰都在证明,/这一群荒原上无罪的人,/头颅里燃烧着信念和理想,/周身都是炽热的火焰,/严冬的冰雪无法把它冻僵,/风的刀剑也不能把它砍光。/黎明中的地平线啊,/你看见一位老诗人,/在北大荒的旷野上哭泣,/他曾呼唤过太阳。/你将作证:/伙伴和我/是被奇异的风吹进罗网。
这是带血的呼喊,这是愤怒的抗争,这是面对历史的宣告!铮铮铁骨,大义凛然,这位外表温文尔雅的诗人,显示了他的金刚怒目的一面。他正像郑敏所描绘的火烈鸟,穿过地狱,穿过烧断了的天桥,却“没有发出失去身份的呻吟”。
德国诗人麦克尔说过,诗歌不是天使的栖身之所,而是苦难的编年史。唐祈被放逐到北大荒之后的诗作,完全印证了这一说法。
值得注意的是,“北大荒短笛”这组诗的写法,不同于唐祈1940年代后期的写作。唐祈1940年代后期的作品,属于知性写作,强调生活经验的集中,从中提炼出诗人所独具的意象群落,追求的是感性与理性的融合、形象的感受与抽象的思想的交织,多运用象征、反讽、暗示的手段,把内心的情思用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北大荒短笛”的写作,则基于浪漫主义的抒情方式,敞开内心,直抒胸臆,主体性极为鲜明。实际上,在当时毫无发表可能的情况下,诗歌成了他释放苦难生活巨大压力的一种手段,诗人只想把自己的所思所感倾泻出来,这是面向自身的写作,他自说自话,而无须借用象征、暗示、隐语来表达。当然这种写法也是有失有得。其好处是真诚,自然,内蕴的激情喷薄而出,给人带来强烈的情绪冲击力和感染力,其不足则在于不能给读者留下广阔的再创造的空间。
“北大荒短笛”的写作,继承了屈原、杜甫这些古代诗人咏志抒情的传统,在特殊年代北大荒的独特背景下,其大胆、真诚的吟唱,给读者强烈的情绪冲击,并引起读者对那一悲剧年代的反思,从而自身也就具有了“诗史”的品格。如今,亲历过1957年反右运动浩劫的人在世的已经不多,无论从还原历史真相来说,还是从真实地抒写诗人的心灵世界而言,唐祈的“北大荒短笛”均在当代诗歌史上留下了不容忽视的一页。
三
1981年至1989年,是唐祈诗歌创作的晚期。
进入新时期后,唐祈的“右派”冤案得以改正,1978年回到中国作协。1979年,唐祈到了兰州,先后在西北师范学院、西北民族学院任教。他回西北的目的还是为了诗,他要在西北高原找回年轻时写诗的感觉,他要回到曾经用诗情哺育过他的少数民族兄弟的身边重获创作的底气。
天遂人愿,到西北后,果然迎来了他继1940年代诗歌写作以来又一个诗歌创作的喷发期。他的“五色彩笔”回来了,他又可以放开喉咙歌唱了。然而,毕竟不再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时间不会倒退,伤口还未抚平,他洒脱的身影背后还有犹疑,他欢愉的歌声后边还有隐痛。正如郑敏所言:“他们有时会在画布上涂下鲜红的色块,他们整装再上征途,但永远不再会在两眼里闪出星光,像一个年青战士那样。他们的心情常比他们所能找到的语言复杂,谁若是停留在他们的诗的表面单纯上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他们”。⑩

当年唐祈在西北求学、写诗的时候,不过二十出头,他再来西北的时候已经年过花甲了。相隔30余年,少数民族地区的面貌发生的巨大变化,不由地触发起他的诗情。当看到黄河上“白色汽帆船飞掠而过”的时候,他想起了当年的“羊皮筏子”:
像一块棕褐色的破布/一片树叶在水上飘/空羊皮和湿漉漉的柳木条/驾驶着万顷黄浊的波涛
浪花溅湿了我的脚趾我的腰/我的皮袄灌满了风的喊叫/划筏子的老人眼里噙着泪水/泪水流出了迷人的歌谣
(《羊皮筏子》)
但今天的黄河上已经见不到羊皮筏子和划筏子老人的踪影,这不免让诗人怅然若失,然而诗人不会忘怀“筏子的谣曲”,它将在诗人心中回荡,从昨天,到今天,到永远。
草原上选举人民代表,唐祈看到草原上的女人虔诚地捏紧选票的那双手,那双兴奋得发抖的手,他的眼前不由得浮现出30年前他所见过的草原女人的手:
那黑暗的夜晚/在羊脂灯下捧着空木碗/枯树皮一样的母亲的手
那些披散了发辫 月光里/泪水像露珠滴落在草叶上/被人用粗绳捆綁的少女的手
那在寺院阴森的殿堂前/长跪在木板上喃喃祈祷/捻着佛珠的苍白的手
(《草原女人的手》)



从1940年代以来,唐祈便致力于把生活经验提炼为诗人独自拥有的意象,追求知性和感性的融合。唐祈本人不是少数民族,但是他笔下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意象、人物,凡是写得较好的,无不渗透着他的情思与意志,成为他的内心世界的象征。这是他笔下的戈壁:
戈壁上发亮的黑卵石/没边没沿的沙砾/呵 大海死去了/海底凝固了这么多泪滴
我请戈壁接受我的敬意/把亿万年的生命化成了溶液/像血管隐藏在贫瘠的大地/然后像个巫师紧闭住呼吸
风就站在面前/鞭打 践踏 撕裂它的背脊/允许我也化成一块戈壁/任暴风啮咬我紧握钻杆的手臂
有一天我会变成石油河/捧着黑色的火焰从大地走过
(《戈壁》)
这是寸草不生,无边无沿的黑卵石和粗沙砾构成的戈壁吗?是,但它也是诗人主观心灵的对应物。诗人笔下的戈壁,与他受尽屈辱、受尽鞭挞,洒满泪滴的前半生,何其相似!而“任暴风啮咬我紧握钻杆的手臂”,不也正是诗人虽九死而终不悔的对祖国、对人民忠诚的心灵的写照吗?
再如这首《盐湖》中的老牧人:
我年轻时在草原上流浪/离别家乡飘流过许多地方/命运的悲苦像盐粒啊/梦中总想回盐湖哭一场
扎来特旗的萨仁姑娘/是一轮温柔忧伤的月亮/当我们的孩子和帐篷失去了/眼泪像盐湖闪出白光
她现在不知道去了哪方/我脸上岁月的皱纹枯树皮一样/我不喝酒 也不歌唱/悲哀的盐湖早已遗忘
啊 一滴老牧人的泪多孤独/它才是我内心的一片盐湖
(《盐湖》)
这是一位在草原上流浪的老牧人的自白,他失去了家乡,失去了爱情,他经历的苦难像数不清的盐粒,他孤独的眼泪汇成了盐湖苦咸的水。诗人在诗中逼真地塑造了一个历经苦难的老牧人的形象,但读者感受到的却不止于此,而是从老牧人的形象中发现了唐祈那个终生与苦难相伴而又抗争不息的灵魂。

1977年,唐祈在得知自己的挚友何其芳逝世时,曾写下《悲哀——缅怀诗人何其芳》一诗,其中有句云:“太阳出来了,你却含恨过早地死亡!”这句话不幸成谶。唐祈死于一次医疗事故,去世时才69岁。如能假以时日,以唐祈的悟性、学养与勤奋,他也许会完成新的蜕变。然而“有力的手指∕折断了这冬日的水仙”(郑敏诗句),命运没有再给唐祈提供这样的机会,这不能不让我们深深地感到惋惜。
注释

③袁可嘉:《新诗戏剧化》,《诗创造》第12期,1948年6月。
④唐湜:《论意象的凝定》,《新意度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第15页。

⑦雨果:《〈克伦威尔〉序言》,《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24页。





责任编辑 王雪松
A Flamingo Stepping on a Mess of Red Flame——A Study of Tang Qi’s Poetry
Wu Sijing
(Research Center of Chinese Poetr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As a poet,Tang Qi has created poetry throughout his whole life, except the twenty years which due to political factors he was forced to suspend writing.Tang Qi’s creative career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Initially (from 1936 to 1949) by youth writing, Tang Qi faced the surging waves of social reality,actively accepting Chinese modern poetry tide,and became one of the important members of Chinese New Poetry School and the main representatives of intellectual writing in 1940s. Medium term (from 1950 to 1960),during the days of humiliation,Tang Qi always headed up and seriously reviewed every thing around him as a martyr.GreatNorthernWilderness’sPiccolo,created by Tang Qi in the days of his banishment,brought a strong emotional impact on readers and aroused readers to reflect on the tragic age, which gave this work some characters of epic. Late stage (1980s),Tang Qi with his love of the brothers of ethnic minorities,went back to the northwest of China,trying to communicate feelings and experience,today and the past in his works. His creation, filled with a sense of history depth and permeated with his feelings and will,became the symbol of his inner world. But the existing of the lyric tone used in his creation and ignorance of the innovation of artistic language inevitably left a regret for his grand ideal of attempting to reconstruct minority poetics.
Tang Qi; poetry; Chinese modern poetry; intellectual writing
2016-06-1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诗歌史资料选辑”(05JJD750.11-44012)
-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关于文化产业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
- 自然主义心理学的困境与思考